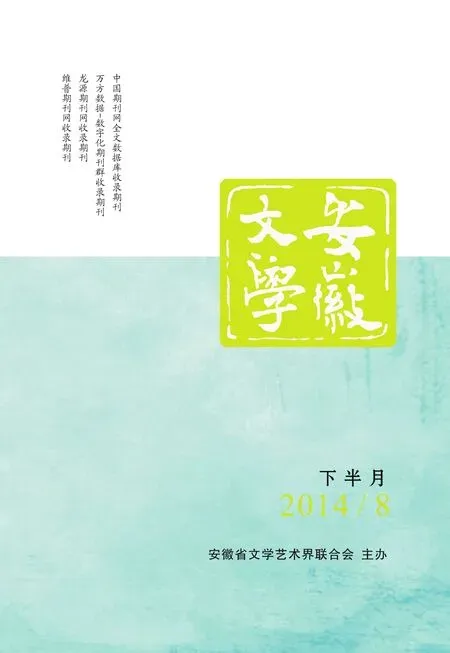“干旱九月”的罪恶
——解读福克纳《干旱的九月》
康有金 朱碧荣
(武汉科技大学)
“干旱九月”的罪恶
——解读福克纳《干旱的九月》
康有金 朱碧荣
(武汉科技大学)
标志着福克纳短篇小说创作最为成熟水平的《干旱的九月》是他杰出的代表作品。小说讲述了发生在美国南方小镇杰弗逊一个干旱九月的夜晚一群暴徒因一起强奸传闻而对一个黑人实施私刑的故事。小说围绕“干旱”和“九月”两个核心,讲述了一群狂躁的男暴徒在麦克莱顿带领下通过向黑人威尔·梅耶斯实施私刑释放了他们的种族主义狂热,另一群女“暴徒”以恶作剧形式对米妮·库珀实施了另一种“私刑”来释放她的性燥热。小说中两位年龄步入人生“九月”的男女主人公所迎来的种种饥渴,恰逢干旱引发了小镇的罪恶。最终上帝遗弃了被弥漫沙尘淹没的罪恶小镇。
干旱 九月 罪恶
一、引言
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是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在20世纪的美国文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威廉·福克纳不仅写出了一批史诗般的长篇小说,还在短篇小说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短篇小说大部分都是以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题材广泛深刻,技巧匠心独运,充分显示他故事大师的才能。《干旱的九月》(Dry September)是他短篇小说中非常出色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标志着作者短篇小说创作最为成熟的水平”的作品(钱青,1999)。
《干旱的九月》发表于1931年,正值福克纳小说创作的黄金期。小说讲述了发生在作者虚拟的美国南方“杰弗逊”小镇上的一起暴力谋杀事件,事件缘于一个谣言:黑人威尔·梅耶斯强奸了年近四十尚未成婚的白人女子米妮·库柏。而以麦克莱顿为首的几个白人暴徒,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九月的一个夜晚,杀害了这个无辜的黑人。关于《干旱的九月》比较典型的观点是作品反映了南方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堕落和南方淑女神话主题,备受学者关注的还有福克纳高超的非线性时序技巧、立体结构和模糊化叙述以及文章的文体特点和意象解读。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小说名字的改变。故事最初完成于1929年秋季,并于次年投递于《美国信使》,其原名为《干旱》(Drouth)。1930年2月《美国信使》拒绝了福克纳。福克纳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立即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做了三处重大改动。首先,他改动了前两节的顺序,“开头热浪”这一小节放在了小说篇首,米妮·库珀个人的背景介绍放在了第二部分。第二处改动是对威尔·梅耶斯实施私刑的头儿由原来的Plunkett改成了现在的麦克莱顿。第三处改动就是将原来的题目《干旱》改为了现在的《干旱的九月》。从这些改动不难看出福克纳将小说的重心从这位白人女子移向了天气。斯克里布纳(Scribner’s)于1930年5月接受了改动之后的版本,并于1931年1月出版(Blotner,1974)。本文旨在分析小说中的外因“干旱”和内因“九月”,从而得出黑人威尔·梅耶斯的死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干旱的九月》的解读
小说围绕“干旱”和“九月”两个核心,讲述了一群狂躁的男暴徒在麦克莱顿带领下通过向黑人威尔·梅耶斯实施私刑释放了他们的种族主义狂热,另一群女“暴徒”以恶作剧形式对米妮·库珀实施了另一种“私刑”来释放她的性燥热。小说中两位年龄步入人生“九月”的男女主人公所迎来的种种饥渴,恰逢干旱一起引发了小镇的罪恶。最终上帝遗弃了被弥漫沙尘淹没的罪恶小镇。
(一)“干旱”与罪恶
小说的开始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久旱后——整整六十二天没有下过一场雨的黄昏,聚集在理发店里的人们就一个谣言,即黑人威尔·梅斯是否强奸了年近四十尚未成婚的白人女子米妮·库柏而展开了讨论和争执。其中一个人说:“全都得怪这该死的天气!天气热得让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即使是对米妮·库柏这样的老处女也一样。”(福克纳,2013:14)在场参加讨论的人们的情绪异常狂躁。这种狂躁与当时干燥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正如小说的开头说到的那样:“久旱后的黄昏,有一件事像燎原烈火般迅速传播开来。”(福克纳,2013: 13)这说明紧张的氛围中潜伏着一种一触即发的危险,这种紧张氛围为描述“谣言”的巨大威力埋下了伏笔。“干旱的、灼热的九月”天似乎使小镇居民备受煎熬,惶惶不可终日,迫使他们想做些什么,而这种焦灼的自然环境是小镇人狂躁、几近疯狂心态的外化。正如利莲·费德在 《文学中的疯狂》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疯狂通常是个人对环境的影响所产生的反应。这里的环境影响包括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压力,个人的心理、生理需求与这些压力相对应、相矛盾就会使人产生不安全感,因此造成心理失衡而狂躁不安。人们要宣泄这种情绪,就不免要做出极端的行动。”(Feder,1980)米妮小姐的极端行动就是为了重新得到大家的关注而散布遭受强奸的谣言,间接害死黑人威尔;而麦克莱顿的极端行动就是为了找回自信和树立威信,而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黑人威尔抓去动用私刑枪毙了。在杀害黑人威尔这件事上,米妮小姐使用的是软暴力,而与之相对的麦克莱顿使用的是硬暴力。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小说第二节和第四节关于主人公米妮小姐的描述,便不难看出她在性欲方面表现出过度强烈的欲望。年轻时她在社交场合总是表现得很兴奋,甚至活泼得有些过分,比起她的同伴来,她“是朵更为欢蹦乱跳的火焰”(福克纳,2001:57)。“火焰”一词形象地描述了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疯傻傻的年轻姑娘对异性热情似火的渴望和追求,充分显示了她对性爱与婚姻的美好愿望。小说第二部分描写米妮小姐的七百二十四个字中,“憔悴”(haggard)一词就出现了三次。“憔悴”说明米妮小姐“干旱”了,需要得到滋润。在小说的第四节,作者描写明妮小姐发烧时她的女伴们照料她的时候,把她的裙子、内衣和丝袜都脱去了。这是福克纳给我们设的一个“恶作剧”:正当以麦克莱顿为首的一群男暴徒在对黑人威尔动 “私刑”,没有通过任何法律途径就活生生地把他弄死的同时,一群女“暴徒”在对米妮小姐动“私刑”,给她降温,驱除她体内的“燥热”。
我们来看一下她们是如何为她驱热的。“她们便主动照料她,不时压低嗓门尖叫一声”(福克纳,2013:26)的原文是“so they ministered to her with hushed ejaculations”,本句话极可能是作者的双声叙事。“ministered”的意思是“照料,满足……的需求”,这里作者一定是暗示着什么。“hushed”是“压低声音”。但是这个单词从外形和读音上更像,也更容易让人们联想到“husband”,其汉语意思是“丈夫”。因为后面的单词“ejaculations”主要意思是“射精”,也有“尖叫”的意思。但是,结合原文,从“干旱炎热”角度解读小说,此处福克纳的黄色幽默是“她们用模仿丈夫射精的方式满足着她”。如果不是这样,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脱掉她的“薄内衣”(福克纳,2013:26),没必要将她脱得一丝不挂。另外,接下来的“呻吟”(moaning)和“喷涌”(welled)以及“尖叫”(screaming)都印证了前面的黄色幽默。福克纳本人也曾说:“写长篇小说时,可以马虎,但在写短篇小说时就不可以……它要求几乎绝对的精确……几乎每一个字都必须完全正确恰当。”(李文俊,2003:159)。本着严谨的态度研读作品,福克纳在这里并不是和文学评论界与读者们开了个玩笑,而是用他特有的一语双关和双声叙事辛辣地讽刺和挖苦了当时美国南方一些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上述幽默场景是小镇女子们在米妮身上搞的恶作剧。这正是小镇的微缩景观,他们把杀人当儿戏,这里的社会生活就是闹剧。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福克纳研究专家凯瑟琳·G·柯达特教授有过这样的论断:“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在福克纳的诗歌、小说、散文还有新闻采访中——弥漫着性的内容:热情洋溢、高潮迭起还有纠缠不休。”(Kodat,2004)理查德·戈登解码了一些福克纳使用的粗俗语。在他看来,福克纳用一些黄色幽默来讽刺和责难当时美国南方破烂不堪的社会经济环境。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来看都说明了米妮小姐对性的过度专注和幻想。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一下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的概念。弗洛伊德将力比多定义为包含于所谓的本我——精神内部主要的无意识结构——中的本能能量或动力。他指出这些力比多驱力可能与现有的文明行为规范相抵触,这些规范在精神结构当中表现为超我。从众求同与控制力比多的需要导致了个体的不安与紊乱,进而促使个体利用自我防卫机制将这些未满足的,而且主要是无意识的心灵能量在其他形式当中得到释放,而这一机制的过度使用可以导致神经症。小说最后一节麦克莱顿的妻子说了句“热”(heat),而字典里关于“heat”的解释说道:哺乳动物的性兴奋期或状态(A.S.Hornby,2000:817),即发情期,所以明妮小姐身体的“干旱”其实是一种本能需要,是她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是无可厚非的。由于她身体上的“干旱”得不到滋润,再加上小镇人的冷嘲热讽,最终导致了她的神经质状态:一会儿声称有人偷看她脱衣服,一会儿声称自己被人强奸,其实都不过是她自己的凭空臆想罢了。可是她虽然内心骚动不安,但在与人打交道时却显得很冷静(cold),如“她们在商店里对各种货物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虽无意购买,仍冷静而快嘴快舌地讨价还价”。(福克纳,2013:18)这种表里不如一是因为她要靠表面上的冷静来掩饰其内心里的躁动。这些是米妮小姐身体上的 “干旱”,那她精神层面上的“干旱”又体现在哪呢?
米妮小姐的母亲常年卧病不起,足不出户,没见她在床边照顾;她骨瘦如柴的姑姑整天忙着操持家务,也没见她帮忙料理家务事。只见她整天穿着花色鲜艳的裙服荡荡秋千逛逛街,无所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她不止没有孝心和爱心,也没有社会责任感。这些是她精神层面上的“干旱”。
而白人麦克莱顿的“干旱”不同于米妮小姐。作为一名曾经获得过荣誉勋章的退伍军人,他极度渴望荣誉,迫切地想要找回过去的辉煌,而现实却事与愿违:他只能住在鸟笼似的房子里,像囚犯一样活着。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想找个机会来表现自己。而小说开头谣言的出现就给了他出手的机会。由于南方淑女神话(南方淑女神话就是指那些被视为“白百合”般的南方女人,在南方社会中,人们时时处处都要保护她们。因为她们是白人,南方文化将其置于神话的 “宝座”之上,创造出一个保护伞,南方贵族利用它保证南方女人免受身心上的危害。(Fox-Genovese,1988))和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造成了南方白人对南方白人女人的强烈保护欲和对黑人强烈的痛恨和排斥欲。而黑人威尔·梅耶斯强奸米妮·库柏小姐这个谣言无疑是触碰了他们最敏感的两根神经。所以当麦克莱顿义正词严地站出来要为米妮小姐主持公道而去惩罚那个黑人的时候,大家是把他当成正义凛然的民族英雄一样看待的。这也极大地满足了麦克莱顿的虚荣心。
理发师亨利·霍克肖是这群人中唯一相信黑人威尔·梅耶斯是清白且认为应该先找到证据再对威尔采取行动的人。在由谣言所造成的张力之中,霍克肖代表的是理性的声音。他在追求事实和正义时所表现出的耐心和毅力同其他人非理性的暴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他不久就被“亲黑鬼的混账东西”的称呼所困。所以对一个南方白人而言,在当时这样的称呼无疑要比追求事实和正义严重得多。因此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加入到迫害黑人威尔的行列。虽然他半路上跳下了车,终止了自己错误的行径,可是他最终还是做了胆小鬼,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制止麦克莱顿一行人。所以他只能算是心里和口头上的好人,而不是行动上的好人。当然,这也不能怪他,整个小镇的空气中都弥漫着“沙尘”(dust),就像当时由于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杰弗逊小镇上,甚至整个美国南方,都被狂热的种族主义思想笼罩着一样。
(二)“九月”与罪恶
九月是夏末初秋,本该是收获的季节。但小说中的九月却悲剧般的干旱无比。如果把人的一生看做12个月份的话,九月是过了朝气蓬勃的春天和青春荡漾的夏天之后的中年时期。小说写于1929年,当时明妮小姐是三十八九岁,而12年前她正是小镇社交生活的风云人物,风光无限;往回追溯12年恰是1917年,正值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麦克莱顿正在激烈的战场上“建功立业”,还因为作战英勇而被授予了勋章。而现在米妮小姐和麦克莱顿正都处于“九月”这个中年危机时期。
米妮小姐年轻时曾是小镇社交生活的核心人物,深受年轻男士的青睐。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可她不想接受这个现实,甚至要求她同学的孩子不要叫她“阿姨”而是叫她“表姐”。她依旧每年夏天定做几身新纱裙,穿着它们跟邻居家的女人去闹市区逛街看电影。可是无论她怎样地招摇和渴望,男人们的眼光再也不注视她、追随她了,她的心理开始出现极度的落差。而小镇上的人不仅不同情她,还用异样的眼光看她,甚至是刻意地冷嘲热讽,这些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她从未得到爱的安抚与滋润,性饥渴与来自社会的压力使她几近疯狂,甚至出现思维混乱。所以她要找一个发泄处,于是便不惜凭空捏造黑人威尔强奸她的谣言。
麦克莱顿曾经因为在一战中表现英勇而被授予勋章,可是现在12年过去了,已经人到中年了,他却没有任何建树。这从他住在很小的鸟笼似的房子里可以看出来。正因为他在外面没有什么建树,所以他回家经常拿温顺的妻子来发泄,已经接近疯狂的状态。在小说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麦克莱顿在外面维护白人女人米妮小姐时表现出来的是 “怒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民族英雄形象,可是回到家里呢?他对温顺的妻子随意地动粗,毫无尊重与疼惜可言。这不仅让我们反思一个问题:麦克莱顿他们是真正关心妇女吗?又或者只不过是给自己的暴行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已呢?麦克莱顿的这种在外面和在家里的言行不一与米妮小姐的表里不一如出一辙。
“干旱的九月”是该小说的题目,也是其关键词之一。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九月”是一年中的一个月份,是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但是,从弗莱的原型意象的解析来看,“九月”隐含着“悲剧”的意义。“九月”是秋季的月份。“秋季”具有深厚的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积淀,与“落日”一样,引发人们联想到“死亡”与“衰败”。它是悲剧与挽歌的原型意象,象征着暴死与牺牲(Frye,1964)。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揭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来源是社会。社会的环境是具体的人形成的重要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提及:“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56)因此我们不难知道,米妮小姐真正所缺乏的其实是大家广义上的关爱和理解;麦克莱顿真正所缺乏的是自信心和来自他人的认可;亨利·霍克肖真正所缺乏的是坚持正义的决心和勇气。
福克纳在另外一篇以理发师亨利·霍克肖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头发》(Hair)里很多次用了“地狱”(hell)这个词来形容“杰弗逊”小镇。而《干旱的九月》里面多次出现“沙尘”(dust)这个词,而“沙尘”象征着死亡和罪恶。在小说中,无辜的黑人威尔被杀害,归于永恒的“沙尘”,谋杀者随即也“被沙尘吞没了”。这些无孔不入的“沙尘”笼罩着整个小镇,就像种族主义思想在小镇的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一样。在这里地位优越的白人可以随意杀死身份低下的黑人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谋杀事件和谋杀者都会被全镇人所原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连亨利·霍克肖这样的好人都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和公道,而是被迫选择加入到迫害者的行列当中。另外小说第三节一开始说到“两轮圆月”也是在暗示我们:由于“沙尘”的笼罩,真相已经被扭曲了。而此时上帝正如同满天的月光和星光一样冷静地审视着这个凡尘俗世上发生的一切。如此地视生命如草芥,如此地倒行逆施,连上帝都寒心了,难怪小镇居民会被认为是 “被上帝所抛弃的子民”(Volpe,1989:60)。
三、结语
干旱的九月的炎热以及由它所带来的沙尘作为外在因素加剧了米妮·库珀体内累积多年欲望的燥热和小镇种族主义暴徒心里的狂热,还有一直憋闷在麦克莱顿心中的灼热,这三股火合三为一烧死了无辜的黑人威尔·梅耶斯。在干旱的九月炎热的氛围中,在弥漫沙尘的笼罩下,罪恶的行径得到了整个小镇的原谅。整个小镇皆热,唯有月光清凉。整个小镇皆浊,唯有月亮独清。整个小镇皆被沙尘覆盖,只有星光未被乌云遮挡。整个镇子没有了一个好人,上帝遗弃了这座村庄。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如果内心清凉,无论环境多热,人也不会燥,不会灼,不会狂,也就不会有无辜为此遭殃。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把握自我才能一世清凉。
[1]A.S.Hornby.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Sixth editio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817.
[2]Catherine Gunther Kodat.“Posting Yoknapatawpha”,Mississippi Quarterly,57:4(Fall 2004 special issue:William Faulkner and Yoknapatawpha),593-618.
[3]Faulkner,William.“Dry Septembe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nd Ed.Nine By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85.
[4]Faulkner,William.Dry September[A]//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407-421.
[5]Feder,Lillian.Madness in Literature[M].Princeton UP,1980.
[6]Fox-Genovese,Elizabeth.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M].ChapeI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8.
[7]Frye,Northrop.The Educated Imagination[M].Bloomington: UP of Indiana,1964.
[8]Joseph Blotner.Faulkner:ABiography[M].New York:Random House,1974.
[9]Volpe,Edmond L.“Dry September”:Metaphor for Despair.College Literature Fall,1989:60-65.
[10]福克纳.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M].李文俊,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1]李文俊.福克纳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翻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