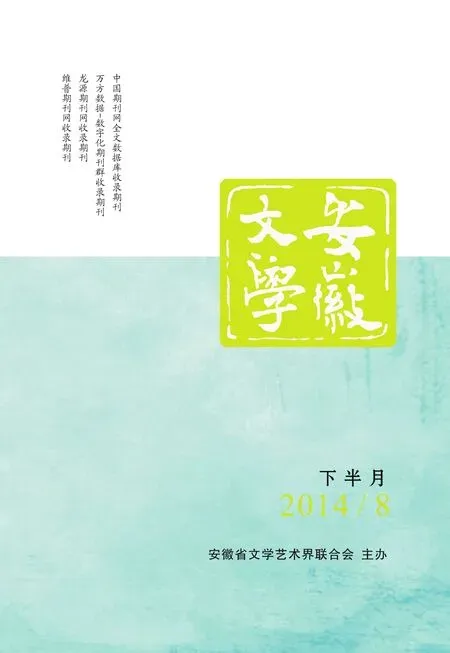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传统
——《天赋》中纳博科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观念的反思
唐英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以自己的方式超越传统
——《天赋》中纳博科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观念的反思
唐英
(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天赋》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用自己的母语俄语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采用对俄罗斯文学观念及传统做出梳理与沉思的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俄罗斯语言及文学的最高礼赞。在书中提到的作家群中,普希金是他推崇备至的一位,被他奉为自己的文学之父。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更是用了一整章来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传,在对于车氏苦难人生经历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他将焦点对准人们早已奉为圭臬的车氏文学观念,对其进行系统阐释与深刻反思。纳博科夫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挑战“权威”、挑战文学定论的非凡的理论勇气向俄罗斯文学传统致敬。
《天赋》 N.G.车尔尼雪夫斯基 纳博科夫文学观念 普希金
《天赋》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用自己的母语俄语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采用对俄罗斯文学观念及传统做出梳理与沉思的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俄罗斯语言及文学的最高礼赞,用他自己的话说,《天赋》中的“女主人公并非芝娜,而是俄罗斯文学”。[1]8
小说讲述了流亡德国的俄罗斯文学青年费奥多尔·古都诺夫·谢尔丁切夫从青涩的诗歌创作开始步入文坛,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而最终成为一位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的成长过程。他先以创作诗歌出道,在壁垒森严的德国俄侨文学圈内难以被人认可。后来,他逐渐转向小说创作,并最终取得了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的文学主题纵横交错,他的主线之一描述的是一位俄侨文学青年的成长史,但更为重要的主题却是他对于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的系统反思,其中包含了俄罗斯作家的传记以及作者本人对19世纪某些俄罗斯文学家的看法和评论。这些作家对纳博科夫的创作都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在他们当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现身次数最多的一位。纳博科夫甚至用了一整章来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尽管由于政治原因,这一章在首版《天赋》中遭到删减,但在1952年出版的完整版《天赋》中,这一章又得到了补充)。为什么纳氏花费如此之多的心血来描写车氏?是因为车氏对纳氏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或者,这仅仅是纳博科夫戏谑车氏的伎俩?本文将会通过对《天赋》的文本细读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为车氏作传的文学意图
对于纳氏为何不惜笔墨在自己作品中用一整章来替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传,许多评论家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研究兴致。纳氏对此早有预见,因此他在《天赋》中通过亚历山德拉·雅科夫勒夫娜(亚历山大·雅科夫勒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妻子)之口提出了同一问题并让他的代言人费奥多尔对此做出了回答。费奥多尔给出的答案相当简单却又暗含深意:射击练习。[1]194布莱恩·博伊德认为,只有将费奥多尔写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策略看做是他对父亲传记的纠偏,读者才能充分欣赏这个作品。[2]597《天赋》第二章中有提及费奥多尔试图为自己的探险家父亲作传的想法,但由于担心自己所作的传记不能让父亲满意,他便让此计划流产了。而为N.G.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传记,一方面让费奥多尔摆脱了亲缘关系的羁绊,能够公正地对待自己的主人公;同时,它还为后来费奥多尔涉及更复杂的命运主题的写作提供了一次练习的机会。
然而,同那些歌功颂德的传记作家明显不同的是,在纳氏的笔下,车氏被塑造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无论触及任何主题,得到的总会是相反的结果。[1]214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他却屡犯“见林不见树”的错误,忽略具体生活的丰富特性。[5]74他喜欢宣扬自己的理论,同时也拥有大批的听众,还拥有《当代纪事》这个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而最终他却过着孤独寂寥的流亡生活。他信仰常识,却被疯子包围着。他推崇艺术自由,却定下了“艺术的最高职务是服务于社会改革事业”的戒律,导致左派书报审查制度的形成,而这个制度最终限制了艺术的自由性。[2]591-592这就是纳氏为车氏所作的传记:处处充满了嘲讽与戏谑。
纳氏之所以如此“不恭敬”地对待车氏是因为N.G.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公认为是一个讨厌普希金的人。而他的这个名号的得来则源于以下事件。1855年,安年科夫发表了一部普希金作品集。两年后,车氏为其所作的评论被刊登了出来。这个评论被德里克·奥福德看做是激进派对普希金和普希金阵营的反对炮火中最强的一击。[3]273因此,1857年就被看做是车氏开始公然反对普希金的一年。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事件使得车氏的“讨厌普希金的人”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进一步加深了。众所周知,车氏在文学方面有两大重要成就:一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另一个则是他的小说《怎么办?》。在这部小说里有对人物薇拉·巴甫洛夫娜的第三个梦的描写,而在她的梦中出现过对普希金的诗歌的引用,并附上了她对这首诗歌的评价:“多滑稽的词!她是从哪儿发掘出这样粗俗的打油诗的呢?”[4]237普希金的支持者将此看做是车氏对普希金进行的直接侮辱。他们认为《怎么办?》的作者对于这位广受俄国大众认可和尊敬的文学家毫无敬意。[3]272-273正因为此,车氏的“讨厌普希金的人”的形象就在许多学者的脑海里扎下了根。
这一系列事件使车氏对普希金的恨意变得人尽皆知。而纳氏一直将普希金奉为他的文学之父,因此,他当然不会袖手旁观自己的“父亲”受到侮辱。于是,他又再次拿起他惯用的武器——在自己的作品中戏谑车尔尼雪夫斯基来抵抗这个文学劲敌。
二、用自己的方式超越传统
纳氏对车氏不满的原因虽然从表面上看当归咎于车氏的“讨厌普希金的人”的名号,其实质则是因为他们各自持有的文学观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冲突。由于车氏在俄罗斯文学界,尤其是政治界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因此许多学者将他的理论奉为至宝,从未对其正确性提出过任何质疑。而纳氏恰恰是一个敢于挑战权威、颠覆传统的人,因此他首先站了出来,指明了车氏理论所存在的缺陷。
纳氏认为,车氏理论存在的第一个缺陷就是认为现实高于艺术。车氏在硕士毕业论文《艺术与现实之美学关系》中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基本观点,认为现实本身原已有美,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艺术只是对现实的模仿,因此艺术所能再现的不但不能多于现实,而且远低于现实。[5]74纳氏则认为应该颠倒过来,是生活在模仿艺术。[2]592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纳氏在《天赋》第三章中策划了费奥多尔的出版商瓦西里耶夫拒绝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传》这一事件。而事后,当《天赋》首次被出版时,编辑也同样因为政治原因将第四章删除了。[1]ⅶ这恰好成了艺术预知现实,现实模仿艺术的一个绝佳实例。
纳氏一贯声称:优秀的作家皆为技艺精湛的魔法师,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手中的魔棒所制造出来的幻象。因此,在文学中寻找现实被他看做是十分荒谬的作法。[6]24-25文学与现实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而车氏的“美即是生活”很明显是间接地在艺术与现实之间画上了等号。在纳氏看来,艺术不是刻板地照搬照抄现实,而是对现实进行的创造性的改造。甚至连“现实”本身也不是客观存在的,而只存在现实的许多主观形象。它们经由作者想象力加工改造之后得以脱离混沌而变得有序。[7]440每个人在面对“现实”时都会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而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现实”。不同的人得到的“现实”还因他们距离“现实”的远近不同而有所不同。而车氏却把“现实”当做了凝滞不动,可供人永久观察的静物。纳博科夫借费奥多尔之口总结道:“[以车氏为代表的]这一类型的唯物主义者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忽略事物本身的品质。他们持续将自己那套极端唯物主义的方法仅仅用于物体之间的关系,用于物体之间的空隙,而不是用于物质本身。”[1]240总之,纳氏认为,要弄清“现实”的本真就必须努力摒弃对现实世界的成见,消除强加在“现实”之上的人为界限。[5]75由此可见,引起车氏和纳氏理论冲突的第二大因素就是“现实”。
此外,纳氏还对车氏教条式地要求文学发挥功利主义的社会作用这一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看来,艺术是自由的,不具备任何说教性和教育意义。车氏所认为的“艺术应当服务于生活”让艺术变得庸俗化,同时,这样的思想还为对艺术的控制铺平了道路——“左派书报审查制度”钳制了俄罗斯诗歌发展达三十年之久。[2]23
在对车氏进行辛辣讽刺的背后,隐约透露出了纳氏对俄罗斯文学的激情,对引起民族精神衰颓的原因的探寻。纳氏在《天赋》中对车氏的文学观念进行抨击并不是因为他与车氏之间存在个人恩怨,实际上,他也为车氏遭到的沙皇的不公正待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之所以对车氏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其根本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于继承文学传统的态度:不应一味地盲从传统,而应对其进行批判性的接收,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摒弃其中的糟粕部分,留存其精华。纳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文学家,他对有缺陷的传统不会随波逐流地接受,而会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此表明向文学传统致敬的最好方式是超越传统。
《天赋》是纳氏最后也是最长的一部俄文作品,也被许多评论家们认为是纳氏众多俄文小说中最为出色的一部。它运用了独特的自传体加评论体的写作文体,以时间为线索,在表达作者向普希金及果戈理等大师级人物的敬意的同时,也将作者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挚爱表现了出来。然而,在纳氏看来,一个好的作家并非任何方面都是好的,同样,一个坏的作家也并非一无是处。因此,当持辩证的态度看待每一个作家。同理,对于他们所留存下来的传统的继承也应当持批判性接收的态度,而不应当一味盲从:继承传统的最佳做法是在吸收传统的过程中超越传统,为传统注入新鲜的血液。由此,传统才能得以长存。
[1]Nabokov,Vladimir.The Gift[M].London:Penguin Book,2001.
[2]布莱恩·博伊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M].刘佳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Drozd,Andrew M.Cernysevskij and Puskin.Russian Literature LXII.III,2007:271-292.
[4]Chernyshevski,Nikolay.What Is To Be Done?.Trans,Michael R.Katz and William G.Wagn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5]赵君.探寻“现实”的本真内涵——论纳博科夫“后现代式”现实观[J].外国文学评论,2008(4):72-79.
[6]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
[7]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M].刘文飞,陈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