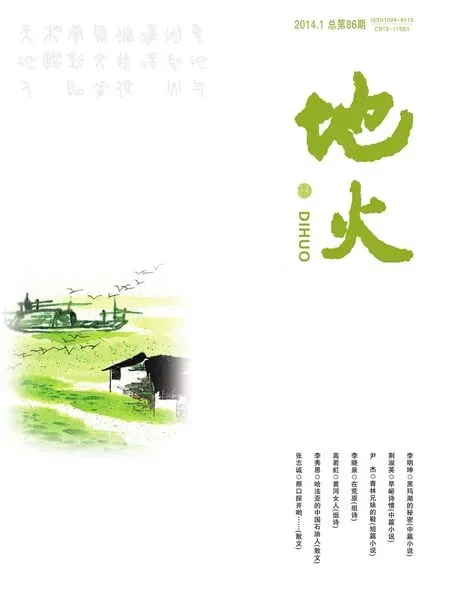青林兄妹的鞋
■尹杰

鸟 巢 版画/王洪峰 作
一
日后,青林四兄妹对方爱真的回忆,就停留在这鞋样子上了。好像一个那么好身条的女人,还不比一双鞋底子好看。
这么说,像是在作践人,其实完全不是。和一般的把人比喻成破鞋烂袜子,根本就是一个白一个黑,一个往东一个往西。
好好地送老爹上了山,烧了纸,宰了公鸡,百天也过了,青林兄妹商量着家里怎么收拾一下。拆到木板床,掀开褥子,就看到了那鞋样子。
开始,青林兄妹都没认出来。这不能怪着谁,都多少年了,谁会一下子就记得起来。那就是两片发黄的报纸,叠在一起,摊开,有两道锋利漂亮的折痕。常年在人身子下面压着,平整是平整,可受了翻滚碾压,又有点起毛。上面有印刷的小字,看不太清了。仔细地看,倒是能看出“油”的字样。
这鞋样子只能是方爱真的,也是那段日子青林兄妹的。
那段日子,青林兄妹记得,是老爹掉了魂的日子。
初秋的中午,阳光还很好。光柱子透过天窗,斜着落在一个搪瓷盘上。盘里盛了几块散碎的红豆腐乳。很多小的尘土,受到骚扰,在四四方方的光柱子里不安地游动着。
老爹和青林兄妹,好好的板凳不去坐,却四散蹲着。老爹说,你们不要学我,那像什么样子,你们是新中国的孩娃,未来的石油主人翁。
青林兄妹就四处瞅,瞅着个板凳,就坐上去。可坐不久,又蹲起来,只是蹲在了板凳上。
吃的是汤面,青林兄妹从食堂用盆端回来的。端回来,不直接盛到碗里,又倒进铁锅。灶前的水缸倒是满的,四兄妹两人一天,木棍子抬水,想逃是逃不掉的。两瓢清水加进面锅,熬开,放辣椒面和醋,等老爹从井上下来,就开吃。一人几大碗,都不许抢。这是稀的。还有干的,发糕,也是食堂的,可以就红豆腐乳吃,大人孩子都喜欢。
老爹从井上下来,刚进院门,洗脸水就打好端过来。也是缸里的水,不管夏天冬天,直接舀来,都是凉的。说是洗脸水,老爹却不洗脸,就用一块固体肥皂头在手上攥攥,去去汽油味。在井上已经洗过两遍了,先抓了一把沙子,手心手背指头缝里搓,把粘着的原油搓掉,再用汽油,汽油盛在盆里,洗过多少遍多少人,都黑成原油了,还能洗。
洗了手,就喝饭吧。刚喝出汗,李胖子就来了,踩在厨房门槛上,说出来一下。老爹就端碗拎凳子,上了院子。凳子塞给李胖子,自己还是蹲着。
咋样,你觉得咋样?李胖子说。老爹说会做鞋不?会吧。李胖子回答。老爹说,那就行。
方爱真就来了家。说是谁的小姨子,姐姐姐夫帮着找过对象,刚结婚,男人就死了。三九天,井上的大夜班,嘎斯气取暖,中毒了。寡守了半年,南方的老家倒是想回,可咋回呀?结婚照都邮回去了。回去就难找了。又享受了这里冬天屋里的温暖,倒舍不下了。
扒拉扒拉手指头,数你家困难,就便宜你了。这是李胖子给的理由。老爹本就不太信。见了面,心里更骂得狠,脸上都显出来了。就知道,好的能轮到老爹?
方爱真倒是大方,两间里屋,一间外屋,厨房、院子、鸡栏也里外看了,再把青林兄妹一眼一眼地瞅。叹口气,就坐在了床边。床,晚上睡人,白天坐人。
听见叹气,就知道方爱真同意了。老爹脸色也敞亮不少。方爱真脸蛋虽然不很好,身材倒是顺溜,又胸挺腰圆的。方爱真转着看家里,老爹的眼就跟着方爱真。
多年后,青林想起来,只说,世上怕是剩不下女人。
方爱真还是提了要求,要老爹把铺盖搬出里屋,挪进外屋。这个要求当然不过分。因为方爱真也会跟着住进去。放在桌面上的理由,外屋守着院门,大人睡觉轻,就不怕有人翻墙越户。
老爹目光游移,显然对方爱真的理由怀疑着,猜不透。可还是卷了铺盖,扛了双人床板,在外屋安顿了自己和方爱真。
新婚第二天,老爹头天还游移的目光就坚定了,笑容挂在脸上。大早上就刮胡子,刀片久不用了,锈得发钝,又专去贸易公司,买了粉红纸包的刀片,晚上又刮一遍。
外屋本来住着青林,里屋和外屋隔着鸡栏,搬去里屋,玩得热闹,青林兄妹自然高兴。全家人都很高兴。
李胖子回访,问老爹咋样?老爹吐着烟圈说,行,周到,懂事。也不知道,说的是换屋这事还是别的什么事。
青林兄妹的尿桶,夜里都是提进里屋,用着方便。偶尔忘了一回,又偷吃了过冬的西瓜,半夜撒尿,听外屋动静不一般,怕是谁病了,问声爸没事吧,就立马没了声音。
二
嫁过来第二天,上井的上井,上学的上学,方爱真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方爱真才嫁过来,只能留在家里,等着家属管理站编排。想的是,编到基建班就和黄泥盖房子,编到土方班就跑野外挖管沟。好一点的,能去食堂择菜洗碗,去托儿所当阿姨,说不定还能干上内外科护士、语文老师呢。不管怎样,就是不能在家里待着。也没有谁硬规定,自己想干就干,不想干拉倒。又不是正式工,钱也给得少。可女人们还是抢着去干,为的是不让人看低,也为了挣点钱贴补贴补家里。
方爱真起得不算晚。老爹起,她也起了。青林兄妹也互相招呼着,轮着上了尿桶,又钻回被窝,躺着斗嘴。斗够了,才爬出来,也还不算晚。相跟着进了厨房,打开笼屉,一人一个馒头,咬着,上了学校。老爹是两个馒头,已经先拿了,也走了。笼屉就六个馒头。昨天在食堂打晚饭的时候,顺带连早饭也买了,是算过了数字才买的,刚刚好,一直都是六个。
都忘了算上方爱真了,把她当成了空气。方爱真就饿着肚子过了一上午。
转眼快到了中午,青林回来,奔到厨房,找铝盆,却找不到。
方爱真问干啥。
干啥?找盆打饭呀?晚了就没好菜了。青林翻着橱柜,嘟囔着,怪了,盆呢?
方爱真说,别找了,饭我都做好了。
可不是,锅里不是白菜肉是什么。
方爱真饿着肚子,本来也盼着到中午饭时间,快去食堂打饭。可是又想想,那去食堂打饭的都是姑娘小伙子,凑这个热闹,有什么意思。
老爹说你不也是当姑娘的年纪,你不说,谁知道你早不是姑娘都两回了。
方爱真只是身子一颤,说,里外寻摸遍了,就有小半袋苞谷面,还是潮的,还有半坛红豆腐乳。就自己去买了白菜,看着五花肉好,又割了一条,还买了米。
老爹停了筷子,放下碗,在衬衣心口的地方捏了捏。肩膀已经端起来,又放下了,拿筷子继续吃饭。
方爱真眼睛在老爹心口停了停,又转回碗里,说,我自己带了点儿钱过来,算是嫁妆,我们那里兴嫁妆,女人嫁人没嫁妆不吉利,也没地位。不到时候,也不动嫁妆。
这菜肉是方爱真用嫁妆买的。
老爹抹了嘴,从心口摸出几张钱,分成两部分,放在饭桌上,说是这顿的伙食还有下顿的。
方爱真眼睛在盘碗之间忙活,一刻也没看那钱,只说,算了,今天就算了,就从明天的伙食算吧。吃饭的时候,钱就放着。收盘子了,才不见在桌上。
老爹先吃完了,开水倒半碗,吸溜吸溜地喝。喝饱,又手指头抹着洗碗。方爱真说,你别动了,我来吧。青林兄妹也要各洗自己的饭碗,说一直都是这样,只有菜盘子大家轮着洗,今天该老二洗。也被方爱真拦下了,统统她洗。
老爹纳闷。晚上,和串门的李胖子,一人夹一根小指头粗的莫合烟,坐在满院子的烟里。莫合烟在俩人肺里转了圈出来,辣人眼睛。
老爹在烟里说,南方女人,倒也贤惠。
李胖子在烟里说,不光贤惠,还当家哩,越往南越能当家。
那你在南方当过兵,你肯定知道。老爹说。
当家都不算什么,我见过的,都是养家,女人下地,男人在家里抽烟。李胖子说得有点儿兴奋,莫合烟连抽几口,青林兄妹就连着咳嗽。
三
给老爹办事那几天,青林兄妹想改回吃面。说是吃米,身上湿气重。改了几天,又改回去吃米了。都说,湿就湿吧。
老爹是北方人,青林兄妹的亲娘和老爹一个村的,青林兄妹也就是地道的北方人。北方人爱吃面,可自打方爱真来了,就吃米了。
可米比面贵呀,还费细粮票。才连吃了两顿,老爹就冷了脸说,看谁家这样过。
方爱真也不说什么,只低头用筷子扒饭,不就咸菜,无声地嚼着。
下顿,还是米饭,却变了色儿。大半的黄,小半的白,黄白相间。青林兄妹知道,是米里掺了苞谷碴子。在嘴里嚼嚼,又改了说法,是苞谷碴子掺了米。不过吃起来还可以。
青林兄妹长大后,老三精于厨艺,爱做一种炒饭,叫做金银炒米饭,也是一半白一半黄。白的自然是米饭,又用蛋清裹了再炒,就更白。黄的也是米饭,却用蛋黄裹着,炒出来就是黄的。
还有一种豆子,便宜还好吃。对了,就是老豆角的豆子。老豆角,方爱真一买就是一菜篮,买来就剥。也好剥,一捏就开口,大拇指一捋,豆子就下来了。一篮豆角,剥下来也就一小盆豆子,才够吃一顿豆子饭的。又去买来,接着剥。剥出来的,当下也吃,大部分都放在太阳地里晒了。干了,就在筐里吊着,冬天好吃。剥下来的豆角皮,也要吃掉,可是要下重油炖煮才好吃。油当然金贵,方爱真怎敢多讨老爹的白眼,自然不敢多用。就盐水煮吧。吃多了,大家都不爱吃了。
可方爱真还是照常把老豆角买回来。剥完豆子,豆角皮小山似的一堆。可没见吃几顿,菜篮子就见底了。都觉得是吃惯了,顺了嘴,不觉得腻歪,吃得就快了。
老三上大字课,忘了带毛笔,回家拿笔,开门就见方爱真剁鸡菜,用的是鸡栏旁边的木墩子。方爱真边剁,鸡们就把头伸出栏,啄墩子。
老三几次想喊,别剁了鸡。菜刀离鸡脖子就只差一点,鸡脖子都没事。剁的什么?鸡这么馋。不是豆角皮是什么。方爱真还掺了苞谷面,难怪鸡们不要命。
青林兄妹都知道方爱真拿豆角拌苞谷面喂了鸡,唯独老爹不知道,都不做声,等着,看喂了鸡怎样?
那鸡果然见肥,毛都是油亮的。尤其公鸡,像披了被面子。母鸡毛短,又好趴窝,毛色上不太显摆,体型上看得出来富态、臃肿了,蛋也多了。老三老四每天放学抢着钻鸡栏,温热的蛋捧在手里,那感觉,老三老四现在还常琢磨,嘴上却说不来。
鸡生的蛋都放在一个铁桶里。铁桶是李胖子自己砸的,当新婚贺礼送给老爹的。铁桶里的蛋多了,方爱真要规划。先是手电筒挨个儿照一遍,挑出来的几个就拿出来另放。一再嘱咐,不能煮了,更不能打了。春天要用来抱窝的。
抱不了窝的,也不是随便怎么就吃。青林兄妹算了一下,一个礼拜大概能吃两回蛋。礼拜二,要不就礼拜三早上,兄妹四个一人一个煮的。有的时候,礼拜天也有水煮蛋,但一般是一盘炒蛋,搪瓷铁盘盛着,葱炒、韭菜炒、青辣椒炒、西红柿炒、青辣椒西红柿合炒。就这几种炒法,看菜场,有什么炒什么。
老爹自有独食的蛋。和青林他们吃法不一样。两个,也是水煮,却磕开了,做成荷包蛋,盛在碗里,另加两汤勺大油。这碗大油荷包蛋,要到礼拜六晚上临睡前才端出来。方爱真以为青林兄妹都睡了。
四
蛋多,那是母鸡的事。一般的公鸡帮不上忙,就宰了吃掉。毛好看顶屁用,又不要你打鸣报时,大家都嫌烦呢,再说还有马蹄表。只留下一两个行的,配合母鸡抱窝。方爱真会看,说哪个行哪个就行。后来,春天能抱窝的蛋太多了,还不得不吃掉一些。
有时也吃母鸡,那些实在下不出来蛋的,瞅个啥节的,就宰了。
宰的时候,青林兄妹都围着看。母鸡没有公鸡死得壮烈,都比较平和。褪了毛,开了膛,掏出肠子心肝,重点扒拉蛋叉子,看有没有一粒粒的小蛋蛋。没有,就对了。有只母鸡,吃了敌敌畏苍蝇,方爱真立刻宰了,肚子里有好几个蛋。
方爱真边收拾边叹气。
公鸡爆炒,母鸡方爱真喜欢上锅蒸。兄妹四个里,老三现在最爱吃鸡,也最会鼓捣鸡。都想着,是不是跟方爱真学的。老三也爱蒸母鸡,看不上那些炖汤的,说是太寡淡,没油水,蒸上,肉吃完,油汤拌饭拌面,啥都跑不掉。
方爱真才嫁过来一年,老爹就把鸡栏换成了鸡圈。半截砖砌的矮墙做底,固着铁丝编的网,占了半个院子。
鸡食,当然不会一直是豆角拌苞谷面。说是四季豆,也只是夏天才会有。方爱真就啥菜都喂。没事就提着筐,到菜场,捡菜叶子。
刚入冬当口,大白菜要扒一遍,才好下窖过冬。下完窖,留一片烂白菜叶子。菜场也不收拾,就让烂叶子在场上厚厚地风干冻住,这正好便宜了方爱真和青林兄妹。用铁钩钩一桶,开水一烫,就是熟白菜,剁巴剁巴,拌上苞谷面,就是鸡们的一顿好饭。
不管啥菜,都离不了苞谷面。日后青林兄妹说,全靠这苞谷面了,菜叶子也就是调个味,补个维生素,长肉还得靠苞谷面。表面上看着,苞谷面给鸡吃了,作践了,人还不够吃呢,可人吃了鸡肉和鸡蛋,肚子里有油水,面不就吃得少了。
还有大肉,方爱真爱买膘厚的。大家都喜欢买后膘肉,可方爱真一个月里买的次数多。老爹说这馋婆娘。方爱真嘴上不说什么,要买肉了还照样伸手要钱买肉。还是那个道理,肉多吃一点,肚里油水厚一点,粮食就吃得省一点。
五
方爱真还是遇到麻烦了。吃,解决了,还有穿呢。老爹的,自然不用操心。有公家管着,一年四季,两身工作服,一套单的,一套棉的。省一省,可以一套穿两年,三年也穿了。
方爱真没嫁过来的时候,青林穿的就是老爹的工作服,小号的。发工作服的笑老爹,越长越抽抽了。方爱真来了,青林穿的还是工作服。方爱真自己也穿着工作服呢,当嫁妆带过来的,应该是前面那位在的时候,就有的。
青林能穿工作服,弟弟妹妹们不能。太大太长了。截掉一截子,收收腰,也要到缝纫组去改才行。缝纫组也不愿收。哪有这样的活儿,一个工作服改来改去,费工费时,还费针费机子。那么老厚的布料,走起针来都吃力。
也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买布做衣裳吧。方爱真没来,买布的事都是老爹的。布买得不分男女,都是黄的,要不都是蓝的。方爱真来了,分了男女,红的是红的,黑的是黑的。可是,也得拿到缝纫组去做。兄妹四个,领着一个两个,一下可不能全领上,没那么多布票。扯了布,到缝纫组量了身材,就回家等着穿新衣服吧。
这是外面的,里面的就难办了。一个裤衩拿去缝纫组,老爹去还好办些,一个男人带着孩子不容易,裤衩就裤衩吧,也简单,嘁哩喀喳一剪,横竖匝上,穿在里面,不怕好看难看。方爱真都来了,再去缝纫组,怕是要找骂。
方爱真就自己做。两片布铰个大概的样子,不分前后,缝上,倒也能穿。就是爱开线。还有个方法,铰秋裤。穿旧的秋裤,从大腿根一铰,就是裤衩,穿着比平布的舒服。
可秋裤也没那么多,还好好的,就更不能铰了,要不秋冬穿啥。秋裤改的裤衩还不禁穿,裆上老破洞。本来就是旧秋裤嘛。不是有那截掉的秋裤腿吗?铰一块,补上。补多了,走起路来磨得慌。
青林兄妹说,别看方爱真吃得上行,从缝裤衩就看得出,她针线活儿不行。
六
里外的衣服也就将就了,冬天棉衣棉裤,夏天背心裤衩,有工作服,还有缝纫组呢。
可鞋呢。
鞋活儿,缝纫组不接,说不会。最小号的劳保鞋,青林穿上还能塞进一个拳头。贸易公司去买,也没有小孩子的鞋。营业员说,小孩鞋提不上货,提上也没人买,还是让你老婆学着做吧。
怎么办?方爱真,学着做吧。老爹说,当时李胖子可说你是会做鞋的。
日后,学做鞋学累了,常听方爱真嘟囔,哪个知道,这里还要穿鞋,还要穿棉鞋,给我草来,我打草鞋,行不行?
方爱真就努力学做鞋。到处找鞋样子,找来鞋样子,就打袼褙。浆糊熬了又熬,布头贴了也有几层。又纳鞋底。麻绳、锥子都买齐了。
鞋样子,先量的是青林的脚。头回做,选个大脚,做起来把握大。老爹也看着有希望。
方爱真不是自学,跟着一个隔了几栋房子的邻居嫂子学。鞋样子也是从邻居嫂子那里借来的。邻居嫂子一针,方爱真一针,这么纳鞋底。鞋底不需要纳很多层,也不厚。和常说的千层底不一样,这儿有这儿的讲究。常说的靠山吃山,也不是个贬义词。厂里皮子多,旧汽车外胎、井上盘根,这样那样的皮子,割下一块,衬在鞋底,耐磨耐穿,还省了纳鞋底。
有一种底子,塑料的,冬天一冻就硬。穿上这样的鞋,走在冰上,滑得很。把火钩子烧红,在上面烙出花儿,都不行。男孩子喜欢这样的鞋。冬天滑冰可以不用穿冰刀。青林向邻居大嫂的孩子打听好了,说是废料库有,约好了,快入冬的时候,去捡回来,做鞋底子用。
鞋底子解决了,还要整个鞋帮。方爱真选的是平口样式,黑布面的。一只鞋再配上两个松紧,这样穿起来好穿。
邻居大嫂说,你真行,学得真快,是把好手。大家听了,都很高兴。
可鞋做好,穿到青林脚上,没两天,就出了问题。咧嘴了,鞋帮鞋底分家了。方爱真找大嫂分析原因,想的是头回做,麻线拉得不紧,再做一双吧。
还是这样。不光鞋帮鞋底分家,鞋底子自己还分家,哪儿哪儿都分家。
邻居大嫂看看方爱真的活儿,鞋底、鞋帮,单看都很好,怎么做成了鞋就不行了呢。
反复了几次,还是不行。大嫂说,还是我来做吧。结果,那鞋青林穿完了整个夏秋。
青林兄妹里,老二爱吃粽子。打小就爱,长大了更爱。爱吃,就想学着包。看别人包着简单,就那么两下子。可自己怎么学,怎么也不对,米就是包不进叶子里面去。
老二总结,这玩意儿,要是不开窍,怎么学都不行,开了窍,不学也会了。
所以,老二后来特理解方爱真不会做鞋。
可是不行啊,家里人等着穿鞋呢。老爹的眼睛像刀子,逼得方爱真没法子。
只能再求邻居大嫂帮忙做几双,又四处打听着买。还写信给老家,让帮着买小孩鞋。寄来了几双,都是凉鞋。夏天倒是好对付了。
七
穿皮鞋的人,还不算多,就有了修鞋的。都是扛三条腿的机子,有男有女,走街串巷,“修鞋”“砸鞋”地吆喝。也是南方人,和方爱真的口音很像。普通话也都说不好,修了鞋,收钱费劲,得说好几遍,才让人听得懂。
这些修鞋的,只修皮鞋、塑料鞋,不修布鞋。翻毛劳保鞋也是皮鞋。方爱真喜欢把老爹的旧翻毛劳保鞋拿出来,让这些人修。人家修,她就在边儿上看。
谁都没当回事儿。
这天,青林兄妹放学回家,就闻见肉香。掀开锅盖,是一大锅晶晶亮的红烧肉。方爱真却不在家。青林兄妹和老爹吃了肉,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回来。四处去找,邻居说,早上还见了,才买肉回来。邻居还问,不过年过节,买这多肉啊!
方爱真就这么不见了。
老爹上方爱真姐姐家找过,说不知道,也没来过。李胖子也帮着找,也没找到。老爹就此和李胖子翻了脸,说,当初不是说会做鞋吗?
有人说,方爱真是和一个修鞋的走的。还有个人说,在北方的某个城市,遇见过一个修鞋的,扛着补鞋机吆喝,女的,和方爱真很像,可是人太多,一转眼就看丢了。
那人说得真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