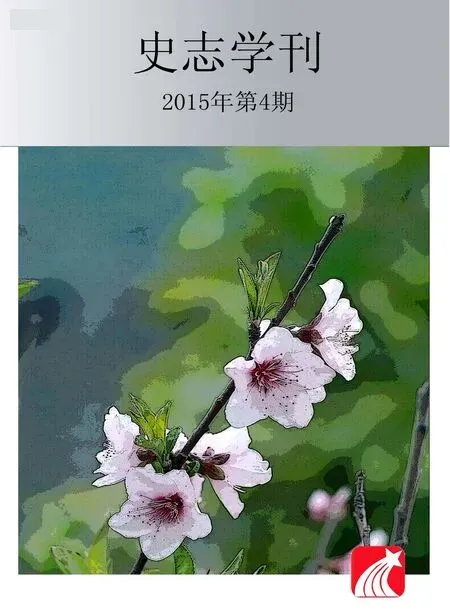清代方志艺文志之分类体系与类目设置探析
刁美林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100009)
所谓艺文志,指的是我国历代史书、政书、方志等,将历代及当代有关的图书典籍、文集、诗歌、辞赋、金石、碑刻、墓志铭等古文献,按照一定的分类体系,汇编成目录,谓之“艺文志”,亦省称“艺文”。班固据刘歆《七略》而编撰《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藏书状况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势,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目录学著作。其后《新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稿》亦相继编纂“艺文志”。其间《隋书》《旧唐书》等改称“经籍志”,性质则相同。艺文志的编纂,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考订学术源流,颇具参考价值。清代是我国古代地方志书编纂的极盛期,也是传统方志学发展的成熟期。在此期间,方志体例日趋完善和成熟,其中的“艺文志”门类在理论与实践上也取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方志艺文志集方志学和目录学性质于一体,既能发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览之可知某时某地之学术大势与文化风尚,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存传承历史文献,因此,对方志艺文志的分类体系与类目设置等进行深入考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清代方志艺文志的分类体系
(一)四部分类法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常见的分类体系,也是清代方志艺文志中比较常见的分类体系。其起源于魏晋之际,魏元帝时秘书郎郑默编定了《中经》这一目录学著作。到了晋武帝咸宁年间,秘书监荀勖在此基础上撰著新的目录典籍《中经新簿》,以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总括全书,初步创立了四部分类法。东晋时期,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删除烦重,以类相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1](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序.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55.(P8393),进一步完善了四部分类法。厥后,唐初修《隋书·经籍志》,便直接以经、史、子、集之名代替甲、乙、丙、丁名称,成为我国古代最早采用经、史、子、集类目名称著录典籍的目录学著作,确立了四部分类法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对我国目录学分类体系影响极大。自此而后,唐《开成四部书目》《古今书录》,宋《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崇文总目》,元《宋史·艺文志》,明《国史·经籍志》,清《四库全书总目》等重要官私书目均将四部分类法“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77)。
清代学者在编修方志艺文志时,大多数参照比较流行的目录学和史志著作,采用四部分类法,如尹继善修、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谢启昆修、胡虔纂道光《广西通志》,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常明修、杨芳灿纂嘉庆《四川通志》,唐仲冕修、汪梅鼎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等等。正如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云:
经籍之志始于《隋书》,而实源于刘歆《七略》、荀旭(勖)四部。自兹以降,代有著录,而各史因之,郡县各志又因之。所以网络散失,包举群籍,备历代之简编,统一方之著作也[3](清)王赠芳修.成瓘纂.济南府志(卷六十四经籍志小序).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然而,仔细对比会发现,虽然这些方志艺文志均是依据四部来进行分类的,但其中具体的分类也是有所不同的。
第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史、子、集四分法,除此四部,别无他类。如尹继善修、黄之隽纂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九十至一百九十四,唐仲冕修、汪梅鼎纂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卷二十七,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八十九至一百九十八,陶澍修、李振庸纂道光《安徽通志》卷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六,曾国荃修、王轩纂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七至八十八等等,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正如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云:
历史艺文志载一朝之书,多至千余种,宜也。今一县之撰述,多亦至百余种,盛矣。其先后亦仿历史之例,分甲、乙、丙、丁四部。其书之存佚及未见者,间注于下,参用朱检讨彝尊《经义考》例焉[4](清)李德淦修.洪亮吉纂.泾县志(卷二十六艺文小序).清嘉庆十一年刻本.。
这种经、史、子、集分类法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后被应用得更为普遍。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云:
班固志艺文,本刘氏《七略》,条其篇目,《隋书》则直曰“经籍志”,唐史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分经、史、子、集四库,郑樵谓书之亡也。由于例类之不明,故特著校雠略一篇。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分部辨类,朗如列眉,诚编纂之定法……兹广为搜采,依例著录[5](清)邓琛等修.英启等纂.黄州府志(凡例).清光绪十年刻本.。
道光《济南府志》亦云:
国朝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分子目,而评论得失,如鉴如衡,诚载籍之金科,艺林之玉律也,论古者之所折衷矣[3]。
乾嘉以后,地方文献专科书目炽兴,出现了孙诒让《温州经籍志》、邢澍《全秦艺文录》、管庭芬《海昌艺文志》、吴庆焘《襄阳艺文略》、胡宗楙《金华经籍志》、丁祖荫《常熟艺文志》等专志经典。以孙诒让《温州经籍志》为例,其分类体系一尊四部,而其子目分合,更是以乾隆四库志目为宗尚,此为后世所仿效。厥后光绪《永嘉县志》艺文门即“据孙比部诒让《温州经籍志》,补所未备”[1](清)张宝琳修.孙诒让纂.永嘉县志(凡例).清光绪八年刻本.,“刺取县人之作,稍加删润”[2](清)张宝琳修.孙诒让纂.永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志小序).清光绪八年刻本.而成,足见四部分类体系对方志艺文志影响之深远。
第二种是,有些方志艺文志在分类时虽然没有标明四部,但实际上是按经、史、子、集四分法来进行列目排序的。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认为“唐人四部之书……乃为后代著录不祧之成法,而天下学术,益纷然而无复纲纪矣!。盖《七略》承六典之敝,而知存六典之遗法;四部承《七略》之敝,而不知存《七略》之遗法。是《七略》能以部次治书籍,而四部不能不以书籍乱部次也”[3](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中华书局,1985.(P655)。似乎对四部之分类方法颇有微词。可章氏却也不得不承认“欲执《七略》之旧法,部末世之文章,比于枘凿方圆,岂能有合?……《七略》之势,不得不变而为四部”[3](P655)。其撰乾隆《和州志·文征序例》就对《和州志》的编纂方法做出阐释说,“奏议拟之于纪,而文移拟之政略,皆掌故之藏也”,所以奏议第一;“征述,记、传、序、述、志、状、碑、铭诸体也……可裨史事”,所以征述第二;“论著者,诸子遗风,所以托之古之立言垂不朽”,所以论著第三;“诗赋者,所以六义之遗”,所以诗赋第四。不难看出,以内容而论,这实际上就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的内容结构。以章氏之言循之,不难发现,有诸多方志艺文志虽然在名称上丝毫未涉及经、史、子、集名称,但是在编纂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影响,按照四部顺序来编排门类。如下表所举:

?
第三种是在四部之外著有其它类目的情况。如李瀚章修、曾国荃纂光绪《湖南通志》就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金石”类:
艺文志,历代以来湖湘人士所述作者,分经、史、子、集四类,具载于编,并条其篇目,撮其旨要,以为考证之资。禹碑出于南越岣嵝峰,文字奇石,是为古来金石之鼻祖。旧志所辑金石二十卷,兹略补所遗,并将称引过繁者稍加裁节,以见志乘当举其重者,不仅作金薤琳琅观也。总为艺文,凡四十五卷[4](清)李瀚章修.曾国荃纂.湖南通志(叙目).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郑见龙修、周植纂乾隆《如皋县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杂类”:
艺文既不纂集诗文,特仿《汉书·艺文》体胪烈皋人撰述书目,分经、史、子、集、杂类编之。又仿朱(彝尊)竹垞《经义考》例,或录其序跋,或录其凡例,以存征文之微意[1](清)郑见龙修.周植纂.如皋县志(凡例).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其它如张宝琳修、孙诒让纂光绪《永嘉县志》在经、史、子、集之外设“文外编”收录制诰、书简、赠序、序跋、传状、祭文、杂记、杂文,“文内编”收录奏议、论著、书简、赠序、序跋、传状、祭文、杂记、杂文、诗外编、诗内编。李鸿章修、黄彭年纂光绪《畿辅通志》与吴中彦修、胡景桂纂光绪《广平府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方志”类,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与常明修、杨芳灿纂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别部”“附录”,俞廉三纂修光绪《代州志》在经、史、子、集之外加入“附录书目”等。谢启昆修、胡虔纂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更是匠心独运,其分上、下两部,上部以经、史、子、集为类,“专载粤西人作述,以正著录之体”,下部则为传记、事记、地记、杂记、志乘、奏疏、诗文等,乃“游宦粤西者,据所见闻,专为纪载”[2](清)谢启昆修.胡虔纂.广西通志(叙例).清嘉庆六年刻同治四年补刻本.。
(二)经籍、金石、艺文三分法
除了四部分类法之外,有些清代学者秉持狭义的艺文志观念,仅将传统意义上的文章、诗词文本视为艺文,而将书目(经籍)、金石(碑碣)等排斥在艺文志外。如清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乾隆《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一至卷二百五十四为经籍,卷二百五十五至卷二百五十八为碑碣,卷二百五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为艺文。清汪曰桢撰《南浔镇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为碑刻,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为著述,卷三十一为集文,卷三十二为集诗。这种经籍、金石、艺文的三分法体系在清代方志艺文志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其能够在方志艺文志编纂中得到相当范围的应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方志纂修人员将诗文看得比较重要:“文章经国之大业,与政治通,故曰‘文以载道’。”[3](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五九艺文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不忍舍弃文章文本内容,遂打算以文征、文选的形式收录全文。而若“诗文散附各门”,则面对“献贤撰述可录甚多”的情况时就很难操作,“不能悉附”[4](清)陈钟英修.王棻纂.黄岩县志(凡例).清光绪三年刻本.也。正如章学诚言:“文集日繁,不列专部,无所统摄也。”[5](清)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中华书局,1985.(P655)而一设经籍志,辑录书目,备史家采择,另设艺文志收录诗文全篇,便是个两全之法。王赠芳等修、成琅等纂道光《济南府志》艺文志就分经籍、艺文二门:
惟旧志艺文散见各志中,全录则患其繁冗,节录则失之简略,故删繁取要,另为一编。而经籍与艺文分为二门,则眉目清而精英聚矣[6](清)王赠芳修.成琅纂.济南府志(卷六十五艺文志小序).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二是受到了方志中金石单独设立门类思想的影响。清人对金石价值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清代学者一般都能认识到“金石补史之缺”的价值,如嵇曾筠等修、沈翼机等纂乾隆《浙江通志》云:
金石之作用,以标叙盛德,昭纪鸿懿,其传世绵远,逾于竹素而参稽同异,每足补史氏之缺文[7](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五五金石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
随着对金石研究的逐步深入,有清代学者极力主张“金石入志”,即方志中应当收入与金石有关的所有内容。如邓琛等修、英启等纂光绪《黄州府志》云:
至金石之书,欧、曾、洪、赵处著专家,蕲州陈诗著《湖北金石存佚考》,最为详核。自宋朱长文《续吴郡记》、元徐硕《嘉禾志》,皆具碑碣一门,则金石入地志之始。兹择其言尤雅者著于篇,志艺文第九[1](清)邓琛等修.英启等纂.黄州府志(凡例).清光绪十年刻本.。
更有学者主张金石在志书中应当单独设立门类,进一步凸显金石在方志中的重要价值。清乾隆以前,历代方志的编纂大多是有“艺文志”而无“金石志”,相关的金石内容都被统系于“艺文志”下,与诗、文、墓志铭等目并列,也就是金石可以“入志”而不“立志”。这一方面是由于相关内容不多,不足以单独成卷,方志的编纂者便把其归列到相近的门类当中,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其所蕴含的价值无法与文献档案类相比,难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则不以为然,他们充分认识到金石碑刻的特殊价值,主张在方志编纂中应为金石单独立志,以求更大限度地保存金石资料:
关中金石之文甲于海内,古未有专志之也,惟陈思宝《丛编》载陕西永兴军路石刻四卷,其中多引《京兆金石录》,则西安一府所有者也,其余多散见于欧、赵、洪、郑诸家著录。顾自唐末五季兵燹,而后一坏于宋姜遵之营浮图,再坏于韩缜之修灞桥,三坏于嘉靖乙卯地震,先后数百年间,十盖已亡其七八。夫金石小道,而其中岁月、地理、职官、事迹多与史传相证明。知亡者之可惜,则幸存者当愈知宝贵矣。兹为寻求钞拓,就取目击者,录其书撰人名刊石年月及存置处所,计目三百一十余通,凡二卷[2](清)舒其绅修.严长明纂.西安府志(卷七十二金石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还有清代学者不囿于方志艺文志的编纂思维,着眼于中国目录学发展史,运用辩证法观点,深入思考,详细论述经籍、艺文与金石的密切联系。光绪十九年《营州图志》云:
志艺文而入金石,非古也。自秦灭后,百籍播灭,刘氏父子,网罗散失,总括概叙,以为《七略》,而班氏因之,成《汉书·艺文志》。说者谓《汉书》诸志类袭《史记》,唯“艺文”特撰,备存三代以来圣哲之遗绪,六艺百子,赖以不废,实足外八书之疏失,而为千古掌故之祖,厥功盖不泯焉。然原目所入,无金石也。至《隋书》,易曰《经藉志》,新、旧《唐书》因之,可分大概无殊,仅益以佛典、道录,亦未及金石也。适宋郑樵氏为《通志》诸略,乃有“艺文略”、“金石略”,然亦析而二之,非合而一之。今方志之志艺文,每列艺文卷上,金石卷下,似金石即艺文也存,殊乖其益矣。尝考方志之最古者,如《吴郡》《嘉禾志》存碑竭,《澈水志》存碑记,《嘉兴县志》存金石尤广。金石非不是存也,与艺文分若而并存之,不尤善之善者乎[3](光绪十九年)营州图志(序例).。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浙江通志》艺文门为经籍、金石、艺文三分法,虽然不是四部分类法体系,但其经籍志具体划分却也受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影响:
文章者,道德之轮辕,政治之黼黻也,故载籍之博学者,资以考信焉。……谨依《隋书·经籍》之例,各分部录,探微证坠,文献足征,匪特熴耀是邦,亦以备史氏之采录云尔[4](清)嵇曾筠修.沈翼机纂.浙江通志(卷二四一经籍志小序).清乾隆元年刻光绪二十五年浙江书局重印本.。
其经籍细目如下表所示:

?
由此足见四部分类法对清代方志艺文志影响之深。
(三)文体分类法
在四分法、六分法之外,也有方志艺文志突破陈规而另创新的分类体系,“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52)。文体分类法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所谓文体分类法,顾名思义,就是将方志艺文志拟收内容按照诗、文、赋、序、记、墓志铭、赞等不同文体作为类目设置的分类标准。如王穆纂修康熙《西乡县志》卷五至卷十艺文志门,分诗、文、居官要箴、催科十则、区田图说、招徕、文告共七类。再如卫既齐修、吴中蕃纂康熙《贵州通志》也是采用文体分类法收录全文的。其艺文全志共7卷29类文体,具体为:卷三十一敕、谕、疏、状、颂、书、赞、篇、铭;卷三十二诗、赋;卷三十三论、解、考、问答、传、志略;卷三十四序、纪、记、引、跋;卷三十五碑记;卷三十六檄、文、议、公移、示;卷三十七杂记。
(四)时间顺序分类法
同文体分类法一样,时间顺序分类法也是方志艺文志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两种分类方式的单独运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志书编修人员做事敷衍的体现,其应用范围主要集中在级别较低的县志和内容涉及面较窄的专志中,如清甘鹏云《潜江书征》云:
或曰,以四部部次群书,故有先例,茲不从之何也?曰潜人著述,佚者十八九矣,其学术流别不可知,不可知则类别而区分也难,且此编意在因人以征书,因书以存人,故不从四部旧例为,而但以作者时代先后为次[2](清)甘鹏云.潜江书征.甘云鹏自序.1936年甘氏崇雅堂印本.。
后李权博《钟祥艺文考》、徐世昌《畿辅书征》皆沿此例,按时间顺序以人为主线分列诸书,每条下均列人物传记。
(五)文体、区域划分与时间顺序相结合分类法
一部成功的志书,其艺文内容的编排往往不会仅仅采用一种分类法,而是多种分类方式的结合。如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艺文志按地区如历城、章丘、邹平、临邑、长清、平原等收录《唐文宗赈山东水灾诏》、《谒舜庙文》等全文,每地又按时间为序排列:
艺文旧志散列于舆地、建置各条下,附著多于正志,稍乖体制。兹遵通志例,汇为艺文一门,文不分记序、碑铭,诗不分歌行、古律,统以时代为次[3](清)王赠芳修.成瓘纂.道光济南府志(凡例).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清宋名立纂修乾隆《汝州续志》艺文志也是采用了区域与时间顺序相结合的方式,以府、县分其大类,以时间排列内容。其卷八上为艺文志(汝州艺文),中为艺文志(汝州艺文附诗),下为艺文志(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四县艺文附诗)。
再如王锦修、吴光升纂乾隆《柳州府志》艺文志是以文体与时间相结合的方式设置类目,其共八卷,具体为:卷三十一至三十四历朝艺文(敕、表、疏、策、议、箴、铭、露布、文、赋、记、序、引、传);卷三十五至三十六国朝艺文(疏、议、书、序、记、传、文、说、引、考、示);卷三十七至三十八艺文(五言古、七言古、五七言律、五七言排律、五七言绝、诗余)。
二、清代方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
与传统艺文志类目相比,清代方志艺文志在具体类目设置上,既有承袭,又有创新。一方面,清代方志艺文志保留了各家目录著作中的一些传统类目,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收书的具体情况做了相应的调整。如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就主张:
今既重事修纂,不宜更相沿袭,谨依宋朱长文撰《吴郡图经续记》以诗文别为《吴门总集》之例,删除艺文一目,经籍别为专门,碑碣入之金石,其余诗文出志有关涉者分隶各门[1](清)孙诒让.籒廎遗文.转引自马春晖.试析戴、章学派之争下的方志艺文志走向.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8).。
王棻编纂光绪《仙居县志》时,也根据实际情况对旧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进行了调整:
旧志合诗文为一编,实于志例未协。今取其系于山川、建置、古迹、典籍者,分附各门,而以其附之未尽及不能附者,别为《仙居集》一编,与志相辅而行,庶文足征而献亦与之并传矣[2](清)王寿颐修.王棻纂.仙居县志.王棻序.清光绪二十年刻本.。
以宋如林修、孙星衍纂嘉庆《松江府志》与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为例,二志艺文志具体类目的设置(见下表),通过与《七略》《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这些四部分类书目对比后可以发现,二志的类目设置与《四库全书总目》吻合度最高,尤其是“五经总义类”“天文算法类”“政书类”这些名称,只有《四库全书总目》具有,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嘉庆《松江府志·艺文志》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艺文志》的类目设置应当主要是参考《四库全书总目》而成。而“经解类”这一类目名称则是参照了《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诸书而取,与《四库全书总目》“五经总义类”涵义相通。
清代学者非常看重正史、方志、家谱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国有史,邑有志,家有谱,并非具文也。”[3](清)郑善述重修.潘昌纂.固安县志.郑善述序.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因此,嘉庆《松江府志》与嘉庆《重修扬州府志》的纂修者都无一例外地在艺文志中设立“谱学类”“谱牒类”类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主要是参考了《七录》《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诸书而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附录”一门类,将“凡诸书未尽扬人撰述,而有关地志者列后”,凸显出方志类书目与其它史书及专科书目的不同之处,很有特色,值得肯定。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艺文志还调整了史部等所属类目的位置,如其史钞、奏议、政书、传记、地理、谱牒的位置顺序,与《四库全书总目》奏议、传记、谱学、史钞、地理的排列方式已经大不相同,细心领会便会发现,与国家、政治、人事相关的类目全都提前了,这正是清代方志重人文而轻经济思想的体现。其它如乾隆《江南通志》艺文志调整类目隶属关系,将“奏议”从史部改隶集部等等,都是清代方志艺文志类目设置的主要方式。
总之,清代方志艺文志在类目设置上,一方面参考、承袭了以往众多书目著作,包括正史、补史及专科目录中的优秀类目,另一方面又能根据地方、时代特色及志书本身特点,通过新增、删减、更易名称、调整类目位置及隶属关系等方式规划设立自己独特的类目体系。正如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所说:“部类之分合,随宜而定。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则部类亦随之而变。”[4]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143)这种以图书的实际情况进行类目设置,而不固守前人分类的做法是严谨而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