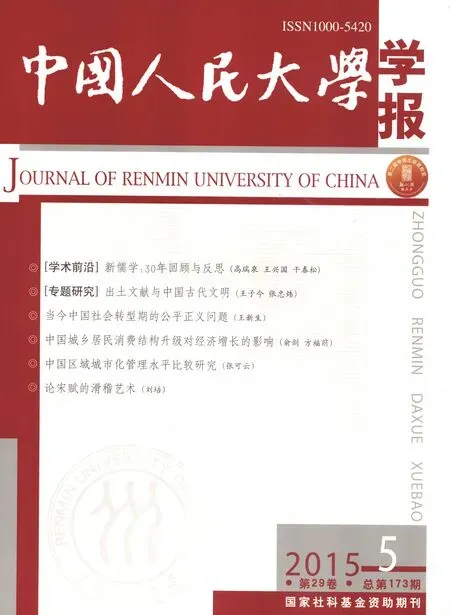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
——民初《眉语》杂志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
马勤勤
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
——民初《眉语》杂志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
马勤勤
中国古代的女性几不涉足小说创作,而民初时期的《眉语》杂志,却公开宣称以女作者小说为特色,在女性小说史上堪称重要一环。利用最新搜集的报刊资料,有助于对《眉语》进行原生态的考察,还原主持者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在解释其是如何对“女作者”这一商业符码进行利用的同时,努力探索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市场逻辑、欲望结构和女性文学增长的空间。
《眉语》;闺秀说部;小说女作者;商业符码
1914年11月18日,《眉语》杂志在上海出刊。该刊由上海新学会社发行,月出一号*查现存十八期《眉语》的出版时间,似乎非常规律地月出一册,但事实上,自第5号《眉语》晚出半月之后,杂志自署的出版时间都有问题。对此,参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呈现(1898—1919)》之“附录三:《〈眉语〉发刊时间推算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自署高剑华女士主编、许啸天协助编辑;其余女编辑还有马嗣梅等九人,是清末民初时期罕见的容纳大量女作者作品的杂志。《眉语》以发表小说为主,辅以诗文和杂纂。上海因地缘优势,历来得风气之先,晚清以来许多重要的小说杂志都最先出现在此。然而,自宣统元年(1909年)起,小说界突然陷入了一个长达五年的低潮期[1],一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才再次活络繁忙。也许因为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特殊的时代氛围,抑或是对前一年的“癸丑报灾”心有余悸,此前激昂的政治热情陡然失去准的,加之上海特殊的都市生活与市民文化,一时文坛骤变、消闲成风,小说杂志也为了迎合市场和读者,大力推扬趣味、休闲和娱乐性。《眉语》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诞生的。
与同期的畅销杂志如《礼拜六》和《小说月报》相比,《眉语》既无庞大的出版背景,也无优秀的作者团队,可以说不具备任何在竞争激烈的小说市场上夺取一席生存之地的筹码。然而,该刊主持者却以极强的商业眼光,找准市场空白与增值点,提出“闺秀说部”这样一种新奇的小说理念。《眉语》一经问世,即大获成功,销量扶摇直上,屡次再版。1931年,鲁迅回忆旧上海文坛时曾提到:“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胡(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2](P294)
然而,对于这样一份重要而又特殊的杂志,学界目前的重视显然不够:不仅最基本的发刊情况没有弄清,而且即便研究也大都着眼于对女作者小说的分析解读。*具有代表性的分析可参见沈燕:《20世纪初女性小说杂志〈眉语〉及其女性小说作者》,载《德州学院学报》,2004(3);黄锦珠:《女性主体的掩映:〈眉语〉女作家小说的情爱书写》,载《中国文学学报》,2012(3)。本文以最新搜集的报刊资料为核心,对《眉语》进行原生态的考察,还原杂志主持者对“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进而剖析其如何从“女作者”这一商业卖点出发,逐渐扩散到对整个带有情欲化的“女性”符码的使用,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的文化心理、市场逻辑、欲望结构和女性文学(小说)增长的空间。
一、“闺秀说部”的构想与实践
1914年11月14日,即《眉语》正式出版的前四天,上海新学会社在《申报》刊出广告:
踏青招凉,赏月话雪,璇闺姊妹,风雅名流,多有及时行乐。然良辰美景,寂寂相对,是亦不可以无伴。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荒唐演述、闺中游戏,而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未始无感化之功也。每当月子弯时,是本杂志诞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语”。[3]
可见,《眉语》与同期多种文学杂志一样,将“游戏”、“消闲”作为刊物的宗旨。同时,广告中“谲谏微讽”、“感化之功”一类的说明也未能免俗,在立意消闲的同时还要披上一件官样文章的外衣。但不同的是,在本条广告上方,有大号字体注明“闺秀之说部月刊”,交代了刊物的自我定位;配合正文,可以很快明白《眉语》是集众多“闺秀”之“说部”而成——此即本文所谓“闺秀说部”概念的由来与内涵。广告最下方,又以特大号字体标示“高剑华女士主任本杂志编撰”,进一步透露了刊物编撰者亦是女子。随后,这段文字经过扩充,易名为《〈眉语〉宣言》[4],刊在《眉语》创刊号上。于是,一份从编者到著者均是女性、以消闲为旨归,标榜“闺秀说部”的新型小说杂志,就展现在了世人眼前。
清末民初,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尚在形成期,不仅常与传统的“说部”相互纠葛,有时还会将戏剧、弹词等“说部”的“子概念”一并纳入麾下。需要说明的是,《眉语》编者对“说部”与“小说”的概念以及分殊已经相当清晰,这从精心设置的栏目可见一斑。在《眉语》上,除了卷首的“图画”,只有四个栏目,依次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文苑、杂纂。其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不仅位置靠前,而且每期都占四分之三以上篇幅。《眉语》杂志卷首也赫然写着“眉语小说杂志第×卷第×号目录”。此外,仅创刊号上,就至少有两处称该刊为“眉语小说杂志”,其一是列于封底的广告[5];其二出自“编辑主任”高剑华的“同学”李蕙珠[6]。非常明显,在《眉语》中,“小说”的地位显系正宗;其余“说部”著述,大概是为了增强杂志的多样性,进一步突出“休闲”个性,以补小说之不足。
研究者指出,早期的“说部”概念,既包括阐释义理、考辨名物的论说体,也包括记载史实、讲述故事的叙事体。晚清以来,“说部”逐渐将论说体排除在外而专指叙事体,最终成为“小说”之“部”[7]。反观《眉语》,其“说部”相当于叙事体的总和;而“小说”在杂志中的重要地位,也完全符合清末民初“小说”在“说部”中日益独大的发展趋势。此外,《眉语》所谓之“小说”,有自著、亦有翻译,语体上文白兼备,实际是新兴短篇小说与传统长篇章回小说的合称,与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相去不远。
《眉语》创刊号刊登了“编辑主任”高剑华和“编辑员”马嗣梅、梁桂琴、顾纫茞的照片;随后第二号,又增加柳佩瑜、梁桂琴和许毓华三人;到了第三号,又有孙清未、谢幼韫、姚淑孟加入。至此,“编撰部”的女性成员已有九人,加上主任高剑华,《眉语》“编撰部”女作者“十人团队”已然形成。从照片内容来看,诸女士或对镜、或奏琴、或抚花、或阅报,还有身着西装的柳佩瑜和戴着金丝眼镜的高剑华,照应了《申报》广告所谓之“闺秀”特色。同时,这些充满细节的生活摄影使女作者们变得具体而真实,也有助于读者大众对《眉语》标榜的“闺秀说部”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
翻开《眉语》第一号,首先看到的是许毓华的短篇小说《一声去也》;开篇之作即出自女性,再次凸显了该刊以女性为编撰主体的办刊宗旨。随后,是许毓华叔父许啸天的《桃花娘》。对比两篇作品,不难发现许毓华的小说情节简单、文笔稚嫩,远不及许啸天下笔老道、叙事曲折。事实上,许毓华既为女子,又系许啸天晚辈,若放在寻常报刊,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委以杂志开篇的重任。之后,《眉语》第二号至第五号的首篇小说,均出自女作者“十人团队”。凡此种种,俱可折射出《眉语》对其标榜的“闺秀说部”一种昭告周知并自我认可的姿态。
与此同时,《眉语》着力渲染刊物“锦心绣口”和“句香意雅”的“闺秀”特色,称之“雅人韵士花前月下之良伴”[8]、“春日怡情之伴侣”[9]。随后,亦可见杂志社为这一概念付出的实践与努力。第二号载有《眉语宣言·本社征求女界墨宝宣言》的广告:
笔歌墨舞,清吟雅唱,风流自娱,无强人同。凡属蕙兰清品、闺阁名流,深冀琼瑶之报,聊结翰苑之缘,入社无拘文节,天涯尽多神交。乃发大愿,于本杂志第三号征求女界墨宝汇作临时增刊,或字、或画、或诗、或文、或说部、或杂记。限于阴历十一月内交社,并随赐作者倩影,以便同付铸印;发表之日,并当选胜地作雅叙,想亦我清雅姊妹所乐许也。
从广告可知,杂志社还计划组建一个招纳多方“闺阁名流”的女性社团。较之传统的才女结社,《眉语》对文类的预设显然有了新扩充——“说部”赫然列于其间;而“发表之日,并当选胜地作雅叙”一句,还未脱传统闺秀诗社雅集的痕迹。
但是到了第三号,本该刊出的“女界墨宝”临时增刊,却被换成了“各界妇女之影片”的《中国女子百面观》。对此,编者在第三号的《〈眉语〉宣言》中这样解释:“至本志前次所征女界墨宝,原拟在本号披露。然珠玉满前,无从割爱,且收集甚伙,非此小册子所能容纳,拟另刊成帙,作新岁之赠品。”可是,到了《眉语》第四号及之后,却再也未见有关“女界墨宝”的任何消息。据此推测,想必编者所谓“收集甚伙”大概只是台面话;真实情况可能反而是应者寥寥,致使这一计划不得不半路夭折。
既然无法征集更多的闺阁社员,也就难以扩充女作者团队,自然会导致《眉语》本身与其标榜的“闺秀说部”名实不符。于是,杂志社采取了系列对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一些雌雄莫辨的女性署名来凑数。目前,可以确定《眉语》的部分小说为男性代笔,如“梅倩女史”即顾明道[10];但更多时候,作者的真实身份还是难以辨别。在清末民初,这种自署为“某某女士”的现象并不鲜见。但《眉语》之独特在于,“她们”不仅如此密集地登场,而且还不断证明女性身份的真实性。例如第七号《箱笼闲煞嫁衣裳》之后,有“黹英女史曰”的文末自评;十六号《雪红惨劫》之前,又有“韫玉自识”的篇前小引;顾明道甚至在《郎心妾心》中,同时化身为“侠儿”与“梅倩”表演双簧,“梅倩女史”的评语更是占尽三页篇幅。
此外,在《眉语》杂志社所有的实践与尝试中,最特别也最具价值的,是大量生产了以女性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统计18期《眉语》,短篇小说154篇、长篇小说14部,其中女性第一人称分别有18篇、2部*具体篇目详见马勤勤:《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的兴起与呈现(1898—1919)》,162-163页,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占各自比例的10%以上。这个数字无论在中国传统小说的脉络中,还是近代新兴小说的语境中,都绝无仅有。同时,小说以“侬”(我、妾、余、予)为叙事者,大多讲述“侬”自己的故事;并不像中国古代第一人称叙事的文言小说,“我”只是记录者和观察者,而这恰是第一人称叙事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这些诞生于《眉语》、以女性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不仅维护了该刊“闺秀说部”之“名”,而且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丰富也有很大贡献。
总之,《眉语》女作者“十人团队”的照片和小说,集中出现于前三号;此后,除了偶尔出现的柳佩瑜,持续发表小说的只剩高剑华一人。《眉语》后期,另一重要的女作者是第十号出现的徐张蕙如。因此,《眉语》第五号之后,可以确定的女作者其实只剩三人。同时,该刊以女作者开篇的惯例,自第六号起,亦被打破。此后数期,大多变为许啸天第一、高剑华第二的开场格局。事实上,从第五号起,《眉语》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中可以明晰地看出编者如何“炒作”作为商业卖点的“女作者”,同时亦可对其在小说市场上散发的能量与持久性进行评判和重估。
二、作为商业符码的“女作者”
很显然,《眉语》“闺秀说部”的新奇理念,出自杂志社精心策划;除了《闺秀之说部月刊〈眉语〉》告白以及具有发刊词性质的《〈眉语〉宣言》之外,该刊在《申报》上持续登出的广告,亦可概见对“闺秀”这一特殊作者团队的反复强调。第二号广告标注“闺秀之作”,并强调要“添聘女士多人主持笔政”[11];第三号又以十分端秀的大号字体,标明“闺阁著作”[12]。如果说,以上广告中“女作者”作为商业卖点的气息还不算浓郁,那么,《眉语》第四号有了更加突出的显露:
诸君有见元旦出版之杂志乎?诸君有见闺阁著作之说部乎?诸君有见精美丰富之图画乎?诸君有见艳丽雅静之文章乎?诸君有见春日怡情之伴侣乎?诸君有见印刷完好之册籍乎?是惟我《眉语》矣。[13]
其实,推销理由的第一条,只是第四号《眉语》的特殊之处;随后五条,才是《眉语》的真正卖点,列于榜首的即“诸君有见闺阁著作之说部乎”。的确,中国古代女性从不涉足小说创作,读者看到此处自然眼前一亮;况且,它又是占据女性文化正统的“闺秀”,与历来位处文化边缘“说部”的结合品,如何不令人浮想联翩?
《眉语》是商办期刊,能否存亡取决于杂志销量,而销量多寡又会直接决定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广告。对此,杂志社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试看其如何招揽广告生意:
宝号买卖很好啊,请到《眉语》社来登告白,宝号的生意当更加兴隆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眉语》小说杂志是女界有名的人著的……况且这《眉语》都是女界的人看得多。凡是首饰店、绸缎店、香粉店、药房、书坊、眼镜公司、衣庄,女人用物件多的店家,在我们《眉语》杂志上登了告白,生意包他发达。[14]
可见,“女作者”作为《眉语》第一商业筹码,不仅被用来招揽读者,甚至在“招商”广告中也被当成重要的策略加以运营。
其实,读者之所以对《眉语》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是小说作品出自闺阁。于是,小说对读者来说,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字消费品——因为文本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女作者,这才是激起他们猎奇心态进而一探究竟的根源。《眉语》前三号密集地展览女作者“十人团队”照片,事实上已是将隐含在读者阅读空间中对女作者的窥视欲望导向明朗化。然而,图像毕竟还只是一种“静态叙述”,它所提供的观看空间狭小而有限;因此,第四号“文苑”栏刊载了许啸天写给高剑华的《新情书》十首,将在外的许啸天对妻子的牵挂与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语句至今读来还觉露骨:“得芳翰,谨向缄口处三接吻以寄爱”(简四)、“返家后当勤捧玉人以补过”(简十)等。随后的第五号,又有柳佩瑜的小说《才子佳人信有之》,全文以宠物猫“雪婢”为叙事视角,描写高剑华和许啸天的婚姻生活,笔法绮丽旖旎,如“郎揽而坐诸怀,俯颈与夫人接吻”、“匆匆拂拭,披衣起,纳郎入房,回顾夫人,则犹红裳半袒,酥胸微露”。相较于图像,文字无疑更加具体而真实,大大拓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眉语》前三号还非常注意突出“闺秀”的形象和趣味,那么,至第五号的《才子佳人信有之》,似乎预示着这一特色的全面消解。作为《眉语》“金字招牌”的女作者,不仅沦为“消费”的对象,而且还与读者阅读空间中“性”文化的某种想象相结合,成为一种带有情欲化的“女性”符号。事实上,这种倾向的出现,绝非偶然。《眉语》创刊号封面,登载了一幅“清白女儿身”的裸体美人画。画中人仅以一件薄纱蔽体,若隐若现,甚至胸部一侧还显露在外,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一改晚清以来封面仕女图大多形象性弱、叙事性强的特点。在十八期的《眉语》中,这样的封面女性并非仅此一例。封面常常被看做是刊物的形象代言人,“裸体美人”的出现,似乎构成了对整部《眉语》的某种隐喻:一方面,它暗示闺阁女子的率性天真,天然去雕饰*高剑华在第4号的《裸体美人语》中称,“伪君子以伪道德为饰,淫荡儿以衣履为饰”,所以“裸体美人”代表着“天然之皎洁”和“天性之浑朴”。;另一方面,它又将传统文化中隐蔽的“女体”风景化、物品化、公共化,进而刺激读者阅读空间中情欲化的某种想象。也正是这一点,预示了《眉语》日后的发展与倾向。
极具深意的还有《眉语》的命名。对此,杂志称:“每当月子弯时,是本杂志诞生之期,爰名之曰‘眉语’。”[15]若按此,“眉语”的名称不过是对出版时间的强调而已。但是,唐庆增在清华读书时,曾撰文评价《眉语》“阅其名即足令人作三日呕”[16]。事实上,“眉语”一词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本意指会说话的眼睛,在古诗词中常用来指代女子以眉目传情,是为“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李白《上元夫人》)。眉而能语,确实足够动人;何况它还是一种无声之“语”,女子特有的娇羞,全在一颦一蹙之间。可见,《眉语》编者选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本身与刊物分享着一种深层的“同质”关系——他们计划将《眉语》打造成一个女性化的公共情人,期待“她”能在小说市场上摇曳生姿,对读者眉目传情,以期青睐。
综上,《眉语》从最初的标榜“闺秀说部”,到负载“女作者”以性文化的某种想象,最终再次让渡这一情欲化的“女性”符号,将杂志导向一丝不挂的“女体”隐喻。事实上,这个结果不仅回应了《眉语》自创刊之初就表现出的对女性身体的兴趣,而且还反映出相当深刻的现实原因和商业因素,从中亦可概见《眉语》编者在市场浮沉中的焦虑与不安。
三、从大获成功到返归平淡
凭着新奇的“闺秀说部”理念,以及对“女性”符码的娴熟操作,《眉语》一经问世,就大受欢迎,创刊号仅面世20多天,就已再版[17]。随后也不断重印,这从《申报》广告上可见一斑。例如,《眉语》第三号出版时,“一号三版、二号再版均已出书”[18];第七号面世时,“本杂志自第一号起,已一律重印万册”[19];到了第十六号,“第一、二号五版又出”[20]。至于《眉语》销量,据该刊宣称,为“五千”[21]或“一万”[22];结合杂志的密集再版,也许此数字并不夸张。此外,也可从广告价目上得到印证。《眉语》第一号《本杂志告白例》,称广告价格全页12元、封面12元、底面10元。这条《告白例》一直持续刊登到第四号,与同期的女性报刊如《女子世界》和《香艳杂志》定价持平。*与《眉语》同一年创刊的《女子世界》和《香艳杂志》,其广告价目均为每期每全页12元。见《广告价目》,《香艳杂志》第1~12期,约1914年6月—1916年6月;《惠登广告者注意》,《女子世界》第1~6期,1914年12月—1915年7月。但是,自第五号起,《眉语》开始刊登新的《广告价目表》,价格大幅上涨,“特等”广告已全页60元,是同期小说杂志如《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和《中华小说界》的两倍。*同期,《小说丛报》、《小说新报》和《中华小说界》“特等”广告定价均为一面30元。见《小说丛报》之《广告》、《小说新报》之《广告刊例》、《中华小说界》之《定价表·广告》。当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此外,也许是由于前来接洽广告事宜的商家骤然增多,主持者又分身乏术,于是聘请了一位“广告经理人”,并刊载了他的启事[23]。
《眉语》用以刊载广告的常规位置共有五处,即封二、目录后、栏目夹页、封三前、封底。此外,封三有时也会刊出半页广告,但更多还是登载该刊自己的启事。翻检《眉语》可以发现,前四号每一期的外来广告仅有2面,都在栏目夹页;但第五号的广告明显增多,变为7面,且封二、封底这样的“特等”位置也用来刊登广告了。或许,这也是本期制定新《价目表》的原因之一。尽管价目大幅提高,但第六号出现的广告不减反增,飙升至14面;随后第七、八号大体保持了这个趋势。可以说,《眉语》至此已是巅峰;第七号广告称“本杂志自第一号起,已一律重印万册”[24],正值此时。可惜这样的势头并未持续太久,第九号广告陡然下降到6面,回复到第五号的水平;此后数期一直到终刊,均在这个数字上下轻微浮动,没有大的改变。
非常有趣的是,《申报》上的四幅广告图画,亦可对这一趋势做补充印证。据笔者搜集的资料,《眉语》前八号广告很少出现图画,偏向素雅;自第九号起,《眉语》连续四期在广告中“化身”女性*参见《申报》所刊《眉语》广告,1915-08-09、1915-09-09、1915-10-21、1915-11-17。,而此时,杂志的广告数量却陡然下降。倘若按照次序阅读这四幅广告图画,可以非常清晰地感受编者越发焦虑的内心——简言之,在第十号,与《眉语》发生“同构”的,还只是一个穿着衣服的传统仕女;而到了十一号,则变成裸体美人。或许,此时《眉语》的光景已大不如前,杂志社只好用色情手段来吸引读者眼球。也许是收效甚微,至第十二号,编者又抛出当时常见的促销手段——赠物,称购书即赠“精印美术明信片画三张,香艳美丽”[25]。随后第十三号,小张“明信片”又进化成“长二尺、宽尺余之大幅裸体美人名画”[26],一直维持到杂志终刊,再未翻出新奇花样。
究其原因,《眉语》最初打出“闺秀说部”的旗号,调动了读者的猎奇心态,这也是《眉语》最初大获成功的原因。但事实上,当时有能力写作小说的女性寥若晨星,也就导致了“闺秀说部”注定名实不符。从读者一面来说,初见或许不免惊艳;然而几期之后,发现不过如此,也就不像之前那样趋之若鹜了。此后,尽管《眉语》苦心经营、努力尝试,尽可能赋予“女性”符码更多意涵,甚至不惜导向香艳露骨的“女体”隐喻;然而胜势难续、返归平淡是它的必然命运。
四、停刊、余绪、影响
后期《眉语》引入情色化的“女性”符号,希望吸引读者眼球。但是,这种做法不仅没能挽回杂志的颓势,反而引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注意,以一纸禁令,彻底断绝了《眉语》在市场上流通的可能。
通俗教育研究会于1915年7月由汤化龙提议设立,旨在“改良小说、戏曲、讲演各项普通人民切近事项”,以期“挽颓俗而正人心”[27](P2)。同年9月6日,该会成立;随后,在12月27日第3次大会上,时任小说股主任的鲁迅报告了两项决议:一为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一为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28](P9)。此后,小说股的工作大体围绕着这两项进行。
关于《眉语》的查禁,始于1916年7月5日的小说股第21次会议,称该刊“尚在审核中,一俟审核完竣,再行决定”;随后,第23次会议又说“现经复核,认为应禁;究竟应否禁止,可俟下届股会决议”;到了第24次会议,则会员一致主张禁止[29] (P12、15-16)。随后,呈报教育部咨内务部查禁,呈文曰:
经本会查得有《眉语》一种,其措辞命意,几若专以抉破道德藩篱、损害社会风纪为目的,在各种小说杂志中,实为流弊最大……拟请咨内务部转饬所属严禁发售,并令停止出版,似于风俗人心不无裨益。[30] (P16-17)
9月7日,教育部经过复议,正式批准通俗教育研究会递交的查禁《眉语》杂志的申请,并咨内务部予以执行[31];9月25日,内务部正式对全国下达了严禁印售《眉语》的训令[32]。
以上大概是《眉语》被查禁的全过程。但是,即便教育部一纸禁令,《眉语》的影响也没有真正消歇,此后一年,它不断地变换各种身份,继续在出版市场上与读者见面。
1916年下半年,新学会社又推出“小本小说”系列和短篇小说集《说腋》;自9月6日起,《申报》连续五日登载了《许啸天先生及高剑华女士之名著》的广告予以推销。由此可知,“小本小说”系列共十三种,大多是在《眉语》上连载过的长篇小说。与之同时出版的,还有《说腋》一书,广告称:
本书系集短篇小说而成,敷辞旖旎,设患风流,每册刊载七八篇至十余篇不等,每篇自为起迄。忙里偷闲,读之最宜,现已出至第十六册……[33](P5)
与“小本小说”主推长篇小说不同,《说腋》为短篇小说,且“内有多篇即系从《眉语》中抽出复印”。可见,此次新学会社推出的“小本小说”和《说腋》,其实是对《眉语》进行“二次贩售”。而且,从“敷辞旖旎,设患风流”、“忙里偷闲,读之最宜”等广告词句,也不难看出与《眉语》宗旨的一脉相承之处。
1917年,这两种出版物又一次引起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注意。在小说股审核的著作中,有六种出自新学会的“小本小说”;其中《苦尽甘来》严禁印售,《太可怜》、《长恨》和《凤姨》列入“下等”,另有“中等”的《侬之心》和《婉娜小传》*参见《小说股第一次审核小说一览表》(第二次报告书)、《小说股第二次审核小说一览表》(第三次报告书)。,态度颇为不一。对此,时任小说股代理主任的高步瀛曾说:“本会前者禁止《眉语》杂志,系就其编辑体例立论,非谓其中所列之小说皆必须禁止。”[34](P13-14)对于《说腋》,则主张全体查禁[35](P7)。随后,股员一致同意,当即呈文教育部:
本会近查坊间贩售小册一种,名曰《说腋》,系杂志性质,详加审核,与本会前次呈请钧部咨禁之《眉语》杂志,虽名目与形式不同,而内容实大同小异,且内有多篇即系从《眉语》中抽出复印者,显系将已禁之书易名复售,似此有意蒙混……[36](P5)
一周以后,教育部经过复议,正式批准通俗教育研究会查禁《说腋》的申请,并咨令内务部予以执行[37]。
不知是由于《说腋》被禁,还是许啸天夫妇在《眉语》停刊时就如《礼拜六》一样心存“一俟时局平定,商市回复,纸源不虞匮缺,当定期续出”*参见《礼拜六》第100期之《中华图书馆启事》。的心愿;1917年的4月,他们又推出一部模仿《眉语》的杂志,名曰《闺声》。出版预告称:
以绵密之思想,撰哀感之说部,惟女子为能尽其能事。至文笔之雅静,陈义之正当,图画之精美,装订之华丽,尤足珍爱。翰苑雅士,璇阁名妹,幸赐教正,出版在即,特此预告。[38]
广告先渲染女子撰写说部的独特之处,又以特大号字体“女界撰作之小说杂志”为刊物定位;其下是一句诗意的宣传语——“一片闺人笑语声”,寥寥七个字,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小说世界。几天之后,《闺声》第一集面世,出版广告中“闺人著作,香艳高雅”几个字同样十分醒目[39]。很明显,这是在模仿《眉语》的“闺秀说部”概念。可见,时隔几年,《眉语》主持者仍对这个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业筹码记忆犹新,并试图以《闺声》重建往日辉煌。然而,《闺声》终究无法复制《眉语》的成功,一期之后便宣告停刊。至此,《眉语》的余绪和影响才算真正终结。
五、余论
《眉语》创刊伊始,即定位为“闺秀说部”,表明执行从编者到撰者均为女性的办刊宗旨。事实上,不仅女作者“十人团队”在三期之后大多消失不见,就连高剑华为杂志“编辑主任”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眉语》自第七号起,开篇小说大半出自许啸天;而高剑华发表于《眉语》的小说,亦有夫君代笔之作。*如《梅雪争春记》,新学会社1916年7月出版的单行本,正文与版权页均署“许啸天”著。另外,杂志封面的“眉语”二字,也大多由许啸天亲自撰写。可见,许啸天或为《眉语》的真正主持者。
可见,《眉语》仍是一本由男性主导的女性报刊,其中也可以看出男性主体的文化权利和消费位置。首先,从“闺秀说部”的定义来看,似乎别出新意,然而其特色不过是“锦心绣口”、“句香意雅”,尚未脱胎传统闺秀诗词的评价体系。又,《眉语》的“孪生姐妹”《闺声》称“以绵密之思想,撰哀感之说部,惟女子为能尽其能事”,又将这一性别“差异”与文化中对女性的某种定型化想象结合在一起——即女子的细腻多情、柔弱善感。可见,这种看似凸显女性“主体”特色的标语旗号,不仅没有一丝女性的自省与自觉,而且还在不断重复传统性别观念对女性角色的定义。
再从“女作者”本身来说。自《眉语》创刊伊始,“闺秀说部”就作为杂志的第一卖点登场。仔细品味这四个字,“说部”是其次,“闺秀”才是首位。也就是说,编者在不断强调一个性别化的小说写作主体。而这个做法不过是为了满足读者的猎奇心态与窥视欲望,对他们来说,与其说是在读小说,不如说对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女作者”更感兴趣。因此,小说和女作者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奇妙的“互动”与“互文”——《眉语》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字消费品,而是更加集中针对“女作者”的消费。
走笔至此,不妨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上的一场关于“女性”意义的争夺战与之并观。简言之,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出现了大量标榜“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丛书,且“女作家的身份成为构造畅销的卖点”[40]。然而,借助这一阶段积累的文化市场资本,“女性文学热潮”却很快导向了90年代后期的“美女写作”和“身体写作”,并利用女作家的身份营造一种“性”文化的想象。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文学本身的复杂性逐渐被剥离,‘女性文学’的文化构成和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化”[41](P505)。
应该说,上述判断十分精辟地估量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市场的基本情况。然而在百年前,女性的主体建构尚未完成之前,一种看似消极的图景背后,其实更多蕴含着新的冲动和可能,并为女性文学的增长提供了空间。例如,女性不涉足小说创作已有千年,而《眉语》标举的“闺秀说部”,为女性与小说的结缘打开一个重要缺口。同时,它单独向女作者发出邀请致意,在男性一统天下的小说格局中,意义不可谓不重大。即使《眉语》后期使用许多假冒的“女作者”来充数,仍然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为女性登上小说文坛做了充分铺垫。更有意义的是,不管出于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眉语》刊载了大量以女性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丰富与转型中,堪称重要一环。
此外,上述图景促使我们再度思考,为什么小说女作者会大量出现于被称为“逆流”的“鸳蝴派”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为什么她们进入文坛需要借助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和消费方式?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这些身为闺秀、学生、教师或职业作家的“女作者”们,对这一现状究竟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合谋?《眉语》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女性缩影,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女作家在民初通俗文坛上的角色与位置,更能触发对当下大众文化笼罩的女性文学之困境的省思。
[1] 谢仁敏:《晚清小说低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载《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闺秀之说部月刊〈眉语〉》,载《申报》,1914-11-14。
[4][8][15] 《〈眉语〉宣言》,载《眉语》,1914(1)。
[5][14][21] 《快到眉语上来登告白,包你生意要更加发达了》,载《眉语》,1914(1)-1915(4)。
[6] 李蕙珠:《倚蓉室野乘》,载《眉语》,1914(1)。
[7] 刘晓军:《“说部”考》,载《学术研究》,2009(2)。
[9][13] 《〈眉语〉第一卷第四号》,载《申报》,1915-02-17。
[10] 明道:《正谊斋随笔·新情书》,载《小说新报》,1919(5)。
[11] 《第二号〈眉语〉出版》,载《申报》,1914-12-15。
[12][18] 《〈眉语〉第三号已出版》,载《申报》,1915-01-15。
[16] 唐庆增:《出版物》,载《清华周刊》,1918-10-31。
[17] 《〈眉语〉一号再版已出》,载《申报》,1914-12-05。
[19][24] 《材料最丰富趣味最浓郁〈眉语〉》,载《申报》,1915-06-01。
[20] 《〈眉语〉第十六号出版,第一、二号五版又出》,载《申报》,1916-03-22。
[22][26] 《本杂志特赠大幅裸体美人画月份牌预告》,载《眉语》,1915(13)-1916(17)。
[23] 《王厚余启事》,载《眉语》,1915(5)-(6)。
[25] 《〈眉语〉十二号,附送/现卖美术画三张》,载《申报》,1915-11-17。
[27]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专件》,北京,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
[28]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记事》,北京,京华印书局代印,1916。
[29]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藏,未标出版信息,当为1917)。
[30]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二次报告书·文牍二》(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藏,未标出版信息,当为1917)。
[31] 《咨内务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呈请咨禁〈眉语〉杂志请查照文》,载《教育公报》,1916(11)。
[32] 《训令通俗教育研究会准内务部咨复〈眉语〉杂志已通行严禁文》,载《教育公报》,1916(11)。
[33][36]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文牍二》(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藏,未标出版信息,当为1918)。
[34][35] 《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三次报告书·股员会议事录一》,(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藏,未标出版信息,当为1918)。
[37] 《咨内务部据通俗教育研究会呈请咨禁〈说腋〉一书请查照文》,载《教育公报》,1917(7)。
[38] 《女界撰作之小说杂志〈闺声〉》,载《申报》,1917-04-04。
[39] 《〈闺声〉小说杂志一集出版》,载《申报》,1917-04-08。
[40] 戴锦华、王干:《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1)。
[41] 贺桂梅:《1990年代的“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载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张 静)
Female Writer as the Commercial Code——Th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MeiYuin the Early Republic to Guixiu Shuobu
MA Qin-q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Women in ancient China scarcely engaged in fiction writing.Yet a magazine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ei Yu openly declared that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female writers,which could be said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female literature history.Based on the latest data,this paper seeks to conduct an original survey on Mei Yu,restoring the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writers concerning Guixiu Shuobu.While explaining how to use the commercial code of “female writers”,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its cultural psychology,marketing logic,desire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space for female literature.
Mei Yu;Guixiu Shuobu;female writers;commercial code
马勤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