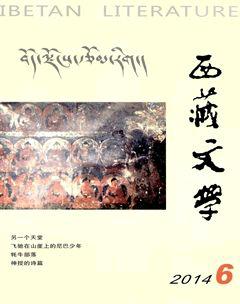神授的诗篇
1
在很多书籍里被誉为雪域的西藏,坐落在看似与世隔绝的雪原之上,其实它并不如想象中的封闭,仔细研读其文化之构成,会有很多令人意外的发现。西藏正好位于中、印之间,长久以来深受婆罗门教吠陀经典与史诗文化、佛教金刚乘思想和萨满教巫术信仰的影响,此外,它对中原道教及汉族传统文化也有一定程度的吸收。以原始苯教为基石的本土人文环境,在中、印两大文化系统的汇流之下,逐渐融铸成令人眩目神迷的西藏传统文化,为西藏古典传统文学供给大量的素材、主题、能量和精神依据,也为后来的当代西藏汉语写作储备了极为可观的“文化铀矿”。
西藏传统文学是一个完完全全由藏族作家的藏语写作构成的文学板块,尽管汉藏语系同源,但两者在后来的发展途径相去太远,已成陌路,若无翻译,汉藏文学无法交流。汉语写作在西藏地区的萌芽很晚,距今不过六十余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九五一年五月廿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九月九日,解放军二野十八军的先遣部队正式进驻拉萨;翌年二月十日,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随着十八军的驻藏,大批军旅作家和援藏的大学生写手,怀抱着解放西藏旧社会的热情、建设荒乡僻壤的理想,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原汉人的视野,歌颂了“祖国的新西藏”的诞生,开启了第一期的西藏汉语写作。
率先浮现在第一期西藏汉语写作地平线的是诗歌,从高平(1932-)的《打通雀儿山》(1952)、《阿妈,你不要远送》(1953)和长诗《大雪纷飞》(1957)、杨星火(1925-2000)的《山岗上的字迹》(1954)和《会说话的营房》(1955),到汪承栋(1930-)的《拉萨河的性格》(1962)和《三听卓玛歌》(1963),都是解放初期较具代表性的诗作。这一代年轻军旅诗人所建构的西藏图象,有一个简单的写作模式,他们总是用单向的热情去描绘陌生的异域,将视觉风景一一转化为诗中意象,夹带在高分贝的呼唤中,尝试去勾勒无比雄伟的雪域地景和驻藏的心境。除此之外,当然少不了歌颂解放西藏的崇高意义,还有各种工程建设的成果。可惜这些年轻的异乡人,毕竟缺少了真正的土地情感和宗教信仰,无法了解传统西藏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透过大量颂词和意象铺陈出来的文本西藏,始终是虚幻的,流于字面,不见血肉。不过,这股建设西藏的热情和政治氛围,深刻地感染了具有崇高地位的藏族诗人擦珠·阿旺洛桑活佛(1880-1957),他先后发表了《歌颂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1955)、《欢迎汽车之歌》(1955)《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6)等诗作,另一名解放军诗人饶阶巴桑(1935-)也忍不住写下《步步向太阳》(1960)的颂歌,西藏文化原有的珍贵素材,被这股过热的汉语颂歌写作浪潮所淹没。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西藏汉语诗坛,不论汉藏诗人皆全面投入颂歌与战歌的写作行列,再加上跟中原地区几乎同步发展的民歌写作,这期间的西藏汉语诗歌创作实在乏善可陈。好不容易才熬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闫振中(1944-)和洋滔(1947-)等人在一九八三年的《西藏文艺》提出“雪野诗”,洋滔说是为了“向传统现实主义和五六十年代盛行的歌颂型文学提出挑战”(《西部时报》2013.07.19),在朦胧诗对抗官方诗界的诗歌改革大势中,雪野诗顺势而为,终结了历时三十年的“解放西藏的颂歌”。
其它文类在这三十年间的创作情况,比容易流于口号的诗歌来得理想一些,虽然歌颂建设和解放西藏的大方向相似,但年轻散文和小说作家对社会现况提出较多的批判,特别是农奴问题,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里都有较具体的描写,为第一期西藏汉语写作累积了一些成果。整体而言,各文类的创作皆可统摄在“解放西藏的颂歌”之下。
2
从西藏汉语写作的第一期“解放西藏的颂歌”,跨入一九八0年代的第二期“藏文化的诠释”,雪野诗算是相当显眼的参考坐标,可惜它的创作质量不够强大,对整个西藏汉语文学在形象与本质上的改造十分有限,真正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西藏文学》(汉文版)和它策划刊出的“西藏新小说”。《西藏文学》(汉文版)的前身是《西藏文艺》,在一九七七年创刊,迅速成为西藏汉语写作的中心。一九七九年刊载了扎西达娃(1959-)的小说“沉默”,一九八二年刊载另一篇“白杨林,花环,梦”,并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九八三年开辟“雪野诗专栏”,连续刊载了二十四首雪野诗和多篇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改名为《西藏文学》,转型成纯文学刊物(同时创立了藏文版),并且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八月刊出马原(1953-)的名篇“拉萨河女神”;一九八五年一月刊出扎西达娃后来获得“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名篇《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同年六月盛大推出由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金志国《水绿色衣袖》、色波《幻呜》、刘伟《没有油彩的画布》、李启达《巴伐的传说》等五篇小说组成的“魔幻小说特辑”,宣告“西藏新小说”的诞生。从这个特辑可以看到西藏作家的自信,他们不但悟出了魔幻写实主义跟西藏文化地理之间,有一种先天的契合性,也发现了进一步演化或涵化之道。
《西藏文学》从一九七七创刊到一九八五年推出魔幻小说特辑,花了八年,终于成功打造出西藏文学——不只是西藏汉语文学——的新形象,彻底改造了颂歌时期的文学地貌,并取得全国性的能见度。这是一场有意识的先锋写作,扎西达娃等年轻作家甩掉僵化的政治意识型态,借用拉美魔幻写实技巧,重新探勘、形塑古老的文化传统,在现代性冲击等重要议题上,比所有的前驱走得更深更远。如果没有产生这种富有魔幻特质的西藏新小说,“藏文化的诠释”难以达成。
在讨论魔幻写实之前,先谈马原。马原在《拉萨河女神》(1984)借用西藏素材进行了高难度的先锋小说实验,接着又发表《冈底斯的诱惑》(1985)进一步巩固了所谓的“叙事圈套”,最后在《虚构》(1986)里直接剖开了自身小说的实验性本质。西藏的文化想象孕育了马原的小说创作,但马原小说并没有真正抵达西藏文化的核心,西藏比较像是他用来写小说的道具,任何人都无法从中了解什么是藏文化。这个大任不得不交由扎西达娃来完成。本名张念生的藏族作家扎西达瓦,在四川藏区巴塘出生,在母亲的家乡重庆渡过了童年时光,八岁重返藏文化的怀抱,后来易“瓦”为“娃”,以“扎西达娃”之名开始其汉语写作。汉藏文化的视野融合,让扎西达娃比纯粹汉人或藏人对西藏问题的思考,更为开阔,而且到位。姑且不谈技巧上的创新,《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所动用的藏文化铀矿是前所未见的,在扎西达娃探讨现代科技文明对西藏传统文化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冲击时,活佛转世和香巴拉传说所产生的那股浑然天成的魔幻感,让这一则末日寓言变得深沉,震撼力十足。被颂歌时期埋葬三十年的文化铀矿,终于得到淋漓尽致的能量释放。这一点是马原的西藏主题小说所不及之处。
在《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一系列以藏文化与现实社会问题为核心的小说,可读出扎西达娃对拉美魔幻的磨合痕迹。一九八0年代初,拉美魔幻进入中国文坛,在汉人作家笔下发出锐不可当的光芒,莫言借此创造出真幻莫辨的高密东北乡;在西藏,拉美魔幻找到最适合落地生根的神秘土壤。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宗教色彩超级浓厚的西藏雪原,似乎比拉美雨林更富有神秘感和魔幻感,俨然就是魔幻写实主义的最后归宿。当初印度金刚乘佛教传入西藏,消化了苯教的巫术信仰,将其神灵收编为金刚护法,同时吸收了婆罗门教吠陀思想和中原道教的九宫八卦,以此建构了本土化的藏传佛教(又称密宗或金刚乘)。藏传佛教,象征了印度佛法在藏地的“文化涵化”,最终发展成色彩强烈的佛教宗派。藏传佛教对传统西藏社会的支配是全方位,从日常生活、节庆习俗、生命思考,到宇宙观,都深受其影响(但苯教不灭,目前在整个藏区尚保存着三百多座保有宗教活动的苯教寺庙)。
加西亚·马奎斯的《百年孤独》,像一支钥匙,开启了自解放以来封印了三十年的藏文化铀矿,扎西达娃等人发现自身所处的藏文化圈,根本就是魔幻写实主义的先天宝藏,以藏传佛教为主(兼融苯教)的藏民日常生活与思考方式,跟外来的拉美魔幻一拍即合,拉美魔幻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人事物,竟然是那么寻常的发生在身边,不必刻意为之,俯拾皆是。以西藏生死观而言,中阴、业力、转世、天葬等观念,远比拉美魔幻小说所营造的鬼魂观和圆型时间观来得深厚、迷人,还可以在佛教经典中取得系统化的理论依据。西藏的迷信,有博大精深的佛学理论在撑腰,诠释空间因而相对宽广。拉美魔幻传人西藏之后,在扎西达娃等藏族作家手里,如鱼得水,源源不绝的从宗教文化宝藏中取得写作的素材和能量,发展出一套以“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为底蕴,结合拉美魔幻写实主义手法的藏文化主题写作,将藏族文化精神与日常言行事物,在小说文本中浑然天成的呈现出来,却在穿透域外读者的陌异眼神时,折射出原始的神秘感和迷信色彩。这种以藏文化为体,以拉美魔幻为用的小说创作,可名之为“藏传魔幻写实主义小说”。
“藏传”一词,取自藏传佛教,一来强调它体质里所饱含的藏传佛教(兼容苯教)的文化元素,二来突显它作为一个传统(或传承谱系)的存在,其实涵盖了拉美魔幻在文化传播上的三大环节:传人藏区、就地藏化、藏内传承。若光有传播而没有传承,便不成传统,这一脉相承的传统,已成为西藏汉语小说非常重要的成就。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虽然不是最早面世的西藏主题魔幻写实小说,但它绝对称得上藏传魔幻的开山之作,向海内外的读者展示了独一无二的西藏图象。
3
在这个谱系传承中,紧接在扎西达娃、色波等人之后登场的,是藏回混血的阿来(1959-)、藏族的次仁罗布(1965-)。和汉族的柴春芽(1975-)等人,血缘与文化上的多元组合,让藏传魔幻有非常开阔的发展潜能。魔幻写实并非阿来唯一的血缘传承,他最初继承的是拉美文学谱系中的另一位大师一一聂鲁达。聂鲁达的诗集《让那伐木者醒来吧》从一九五0年转译成中文之后,十余年间印行了八万册,流通范围十分广泛。《漫歌集》里的民族文化史诗《马丘·比丘高处》,则在一九六四年由蔡其矫译成中文,杨炼读到了,也学到聂鲁达史诗式的雄浑语言,还有奇崛的超现实意象。杨炼无法体会的是聂鲁达对民族和土地的炽烈情感,中国的山川大地对他而言,是一种纯粹理性的知识或史料,很难激起什么样的感触。在阿来的生命经验里,就有那么一块蕴含着大量文化铀矿的藏地厚土,他完全可以体会聂鲁达对祖国土地和民族文化的颂歌,并由此意识到诗人与土地的关系,绝非过去那种流于表面的“解放西藏的颂歌”,而是更深层的挖掘,属于一个小我跟大地的对话。聂鲁达的颂体诗,有政治上的自主意识,有对国族文化的省思,还有无比开阔、雄浑的气度。阿来滤除了聂鲁达诗歌的政治意念,导向较单纯的,对“藏魂”——藏文化的精魂——的召唤与回应。
“藏魂”是比较诗意的说法,学术上的用词是“场所精神”(genusloci),原是古罗马人的想法。诺伯舒兹(ChristianNorberg-Schulz)在《场所精神一一迈向建筑现象学》一书中指出:自然场所的地理结构为居住者提供了保护性,有些则带来威胁性,有时又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一个界定完美的宇宙中心。希腊人在理解自然场所的自然元素时(包括地质条件、地貌外观、生活机能),往往将之拟人化为“神人同形”的众神,而且任何显著的场所特质,都成该神灵的特殊表征(台北:田园城市,1995,页23-28)。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自然地理的结构性特质,对居民习性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习性又反过来构筑了新的人为场所,透过文化地景的创造,来响应所在的自然地理,由此逐渐形成场所精神。在西藏自然地理与藏民之间,同样存在着许多被泛神论思维加以人格化的“在地神灵”,他们等同于罗马人的场所守护神,从其神格形象与神迹进行反向分析,即可分析出当地的场所精神。
阿来对“藏魂”的召唤与回应,最出色的表现是《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1987)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1989)这两首长诗,写得大开大合、意气风发,而且藏味十足。藏味并非来自风景或意象的罗列(那是雪野诗的写法),而是来自诗人对地方文化或场所精神的深刻感悟,再经由一体成型的原始藏地意象系统和文化思维的双重运转,所营造出来的阅读氛围。整首诗读起来,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诗人的壮游已经融入群山和草原之中,山川不是外在的东西,既是客体又是主体,名曰颂辞,实为诗人的内在追寻;至于那片五万三千平方公里的若尔盖草原,对三十岁的阿来而言,漫游即是对藏文化的发掘、回归与洗礼,处处隐含着《马丘·比丘高处》那种浪漫主义式的情怀,那是阿来写给自己的《漫歌集》。
在同期的藏族诗人当中,唯有列美平措(1961-)的《风景》(1988)、《节日》(1988)、《哀伤的舞蹈》(1991),以及旺秀才丹(1967-)的《一场忧郁的雪使大地美丽》(1991)和《鲜花》(1990)等诗作,能够表现出类似的文化视野和藏味。比起雪野诗针对自然地景和人文符号所进行的浅层视觉营造,列美平措和旺秀才丹的诗作展示了层次感丰富的藏族心灵图象,其中包含了诗人对土地的认同、民族文化的回归、藏传佛法的参悟,甚至是对圣洁与纯净的形上追寻。西藏,再也不是一个喊出来的字眼,它被质朴、粗砺的语言精密地编织在众多细节之中,经由主客体合一的叙述,新一代藏族诗人越来越能够掌握对藏魂的召唤和响应,甚至流露出宗教灵性较高的“朝圣之心”与“净土思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列美平措的长篇组诗《圣地之旅》(三十首,1990-1993),那是一个格局宏大的朝圣诗篇,他在不同的时空里循着一条预设的虚线前进,一边召唤出场所精神,一边向自己提问。
在一九九0年代的西藏汉语诗歌当中。长期生活在甘肃藏区的扎西才让(1972-),以甘南为题写了《在甘南桑科》(1993)、《黑夜掠过甘南》(1994)、《甘南诗抄》(1995)等一系列抒情性浓厚的田园组诗,建立了具有地志书写成份的甘南印象。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从早期高蹈的甘南传统文化抒情,转入微观的现代甘南市井特写,《腾志街》(2012)和《饭馆里》(2012)是诗人在现代城镇里生活的剪影。也是抒情诗人深入现代叙事时的蜕变。同样来自甘南的嘎代才让(1981-)也写了多首甘南的诗,之后他努力“回到自己的西藏”,寻找自己在现代理性思维与宗教神性文化之间的定位点,陆续发表了《去年冬天在拉卜楞寺》(2002)、《佛陀的眼泪》(2009)、《七月的幻术》(2010)等一系列或以佛寺为据点,或以佛法为题的探索诗作,他在诗歌的精神世界里,逐步踏上朝圣之路。在此同时,女诗人西娃(1972-)尝试了另一种非常叛逆、犀利的前卫情诗写作,她的《外公》(2002)将轮回与伦常元素置入爱欲纠葛之中,《或许,情诗》(2010)则让佛法和诸佛菩萨踏入五浊恶世,在与诸佛对话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世界。新世纪以后的西藏汉语诗歌,就这么朝着藏传佛教的核心走去,比任何时期都来得真诚,来得专注。
诗歌不必讲求魔幻,诗里的宗教性会自然产生玄幻的意象、冥想的氛围,时而开阔,时而宁静。从阿来的壮游看到诗人对藏文化的回归,那是相对纯粹的藏族意识和土地认同之觉醒;列美平措等人展示了另一条属于藏传佛教的朝圣之路,净土写作遂成为第二期西藏汉语诗歌图象的核心架构。
4
完成若尔盖壮游之后,诗人阿来随即转向阿坝地方文化的挖掘。
他出生和成长的四川阿坝,是苯教的信仰区域,有别于以拉萨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区域,他认为文学“不是阐释一种文化,而是帮助建设和丰富一种文化”(《看见》,长沙:湖南文艺,2011,页177),藏区的传统民间文学、阿坝的苯教文化,遂成为阿来小说的重要元素。此外,聂鲁达的血缘不断提醒他:魔幻写实不是他唯一的选择。在西藏汉语小说中迅速取得统治性地位的藏传魔幻,在阿来的评估里,恐怕会产生单一化的写作危机,所以他有意识的调降了小说里的魔幻成色,让它表现得再自然一些,不管是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里写到喇嘛持咒治病或巫师驱唤冰雹,或者在短篇小说《鱼》(2000)里头写到鱼前仆后继上钩后的叫喊,都把它们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寻常事件或文化禁忌之隐喻来处理。西藏本来就如此,看似魔幻的事物,只是陌生的现实,读者只需进一步了解藏人的传统文化习俗,自然就会明白《瘸子,或天神的法则》(2007)的迷信想法,就会了解银匠、农奴,活佛、土司在旧时代的角色意义。阿来在小说里召唤出苯教的场所精神,交由神秘巫术和土司制度连手统治这个现实的世界,魔幻仍旧无法割舍,那是藏文化的先天体质。
调降成色的藏传魔幻,亦非阿来之首创,扎西达娃在《自由人契米》(1985),亦尝试用轻描淡写的笔调,来刻画藏人的生活态度和思维逻辑,那些不可理喻的言行,正是民族性的表现。这条路再走下去,就通往“日常西藏”的写作。扎西达娃在一九八五年同时发表了高成色和低成色的两种魔幻写实小说,对后来者有很大的启发。
次仁罗布的《放生羊》(2009)走的正是“日常西藏”的写作路径,他很写实的刻画了放生羊其背后的佛教业力观(绝非基督教救赎观),刻画了主角的虔诚、羊的灵性,以及企图为亡故的情人消除恶业好让她早日投胎的善念,透过无距离感的散文叙事语调,细腻的体现了藏传佛教对生死和业力的思考,这在西藏是常见的善行。简单写来,却撼动人心。两年后发表的《神授》(2011)写的是《格萨尔》史诗的神秘传承,不管怎么处理,“神授”的过程都会覆上一层神秘色彩。在杨恩洪《超越时空的艺术传承》的田野考察中,《格萨尔》常有“梦授”的例子,大多数年轻艺人都说是童年做梦醒来之后,开口就会说唱《格萨尔》,其中达哇扎巴的梦授过程记述得最完整(《文艺评论》2008年第6期,页9-10)。次仁罗布用“神授”一词,描绘了传统藏族社会普遍接受的神授事实,即使写得老老实实,其魔幻色彩自动产生。日常西藏,隐藏着魔幻。
藏传魔幻到柴春芽手里,却变得更加魔幻。出生在甘肃的柴春芽是汉人,两位藏族作家朋友开启了他跟藏文化的接触,后来他到藏区义务执教,开始深入了解西藏。他在《西藏红羊皮书》里说:“一种原始朴素的有神论信仰和善恶报应的观念其实早就在我的血液里扎下了根”,最后他“把藏传佛教的思想确立为自己的世界观”(台北:联合文学,2009,页320-321),他在小说里运用的佛法思想,比大部分前辈都来得深奥,当然,他也认定西藏的魔幻即是真实。在这个理念下,成色越高的魔幻写实技巧,越能诠释他预期中的西藏文化。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贯穿全部长、短篇小说的人物祖母阿依玛,往她身上注入藏传佛教的奥义,和马奎斯式的高纯度魔幻精神,在《阿依玛的种子》(2009)化为密宗的心识种子,在《一只玻璃瓶里的小母牛》(2009)轮回转世,同时她也见证了《神奴》(2009)里原始苯教的降神术。柴春芽的短篇小说集《西藏红羊皮书》和长篇政治寓言小说《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2010),可说是藏传魔幻最炫目的传承。
江洋才让(1970-)也是藏传魔幻谱系中的一员,《金刚杵》(2005)、《风过墟村》(2006)、《闪电雕像》(2009)等一系列短篇小说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魔幻成份。《闪电雕像》里的牛皮桦树被闪电烧成一尊燃灯古佛,消息伴随着七匹野狼的深长嗥叫,三天便传遍了草原。《风过墟村》则表现出诗人的本色,饱含诗意的叙事语言,优美地驱动了这一则虚中带实的故事,调和出软硬适中的魔幻成色。
在强大的藏传魔幻写实传统之外,有没有优秀的小说家呢?班丹(1961-)正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非魔幻”说故事者,他的小说总是在探讨传统藏人的文化性格,《星辰不知为谁殒灭》(2007)以都市摄影家和诗人之死,逼使故事里的藏人重新思考自己对民族性和藏文化的麻痹;《刀》(2010)则以一把有来历的藏刀,启动了藏人对刀器的执念,以及被执念牵引而来的重重杀机。那不是什么微言大意的故事,但人物思维与言行,充满平实、耐嚼的藏味。班丹的小说隶属于另一支非魔幻的日常叙事,央珍(1963-)和梅卓(1966-)都是这一长串名单中的重要代表。
毫无疑问,“藏传魔幻”是构成当代西藏图象最重要的一个传统,其光芒难免会遮蔽了其它小说类型或流派的创作成果,唯一能够跟它分庭抗礼的是诗歌的“净土写作”。“朝圣之心”与“净土思维”在众多诗人的耕耘下累积了丰富的成果,但诗歌毕竟是较冷门的文类,非专精于此的读者,难以发现这条道路的存在。倒是散文对“藏文化一民族风土”的书写,已经成为图书市场里的主流西藏读物,比小说还要主流。
5
当代西藏汉语散文里的民族风土志书写,界于旅游散文和文化散文之间,有时又带上几分文史导览的实用功能,自然成为大众阅读视野的首选读物,特别是准备到西藏自助旅行的游客。赤烈曲扎(1939-)在《西藏风土志》(1982)算是前驱之作,他在书中罗列了大量西藏宗教、历史知识、各地区的习俗与传说,可作为域外读者最理想的文史导览。进藏十八年的马丽华(1953-),将个人在藏地的游历经验写成三个超级长篇的文化散文《藏北游历》、《西行阿里》和《灵魂像风》,结集成《走过西藏》(1994)一书,曾在海内外风靡一时。从《西藏风土志》到《走过西藏》,意味着带有游记与文史导览性质的“藏文化一民俗风土”主题散文,开始瓜分藏传魔幻写实小说对藏文化的诠释权。同时,它逐步转型成较严谨的文化散文,也凝聚出一群对藏文化的神秘性有高度憧憬的理想读者。
在这股“走过/走进西藏”的浪潮里,塔热·次仁玉珍(1943-2000)是非常特殊的例子。在藏北工作的三十余年间,她踏遍四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成许多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创办并主编《西藏民俗》杂志,是著名的藏文化研究专家。一九九一和九二年,她两度率领探险队前往藏北那曲地区,考察素有“死神领地”之称的无人地带,在面积十万平方公里的荒原里出生入死,写下惊险的故事,后来结集成《我和羌塘草原》(1995)和《藏北民间故事》(1993)等书。她那篇《矮门之谜》(1994)记述了藏地尸变的原因和事件,以及为了防止僵尸入侵的矮门设计,绝对是最独特的一篇文化散文。此外,塔热·次仁玉珍也写下《藏族妇女与美容》(1995)这种以日常生活为题的文化散文。奇正两路,双轨并进。格央(1972-)即是重要继承人,她在《西藏民俗》先后发表了《女降神者》(2002)和《我在老家察雅过新年》(2003),前者是从亲眼目睹的事件,来讲述降神者(藏语为“拉培聂”)的奇异民俗现象,还谈到哲蚌寺的神谕师和地位崇高降神女巫,这种写法兼具文化散文和民俗文献的价值;后者巨细靡遗的描绘了藏历新年的精神内容,在整整一个月的年节活动里,她找回现代藏人已经疏远的族群生活。
当文化散文舍弃了民俗风土,轮廓亦随之改变。少壮派军旅作家凌仕江(1975-)和曾经从军十六年的嘎玛丹增(1960-),分别以《天葬师》(2013)和《桑耶寺的声音》(2013),演练了文化性与语言诗性的融合。天葬是一般闲杂人等无法窥得真面目的神秘葬仪,凌仕江以庄严、肃穆的语调,宏观地陈述了天葬的构成之后,折返现实,特写一场毕生难忘的天葬,及其背后的一些禁忌和技艺,至于那个被天葬师肢解的,是他认识的僧人。嘎玛丹增从非佛教徒的角度来写桑耶寺,先找出它在整个西藏佛教史上的崇高定位和文化积累,再转入微观的叙事,以诗化的语言,捕捉千年古寺的建筑细节、僧人举止、宗教氛围的感染力。这两篇出自军旅作家的文化散文,一奇一正,皆能切入藏传佛教的内壁。
除了文化散文的路数,个人独特的生命记忆也是西藏汉语散文另一个常见的主题。王宗仁(1939-)的《一把藏刀》(2006)、丹增(1947-)的《童年的梦》(2008)、次仁罗布(1965-)的《绿度母》(2011),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佳作。表面上十分寻常的事件,平凡的人物,却在藏文化情境里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王宗仁是一九五0年代进藏的前辈军旅作家,丹增也是见证过西藏解放初期的文坛前辈,他们拥有数十年的藏地体验,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再回头,去挖掘珍贵的记忆片段。一把购自八廓街的藏刀,揭开了王宗仁既心痛又心酸的旧事;丹增童年的一面镜子和手电筒,竟成为现代性冲击的缩影。至于次仁罗布,则在散文中转译了一则令人感伤的故事。从这些篇章,得以窥视藏人的心思和想法。
当散文作家带着预期中的理想读者,从壮阔的藏地风光、神秘的民俗风土、藏传的佛教文化、半世纪前的记忆,一步步走进当前的西藏现实社会,就会看到魔鬼。不是魔幻写实,而是货真价实的,现代文明的魔鬼。白玛娜珍(1967-)的散文除了备受评论家肯定的艺术美感,还有一颗悲悯之心,关照着藏人在现代社会里的生存困境。《村庄里的魔鬼》(2007)和《没有歌声的劳作》(2007)彻底粉碎了神秘与神圣,拉萨不再是什么净土,她在城北娘热乡看到现代都市文明及其资本的入侵,对传统藏人的生计带来重大转变。现代化是无法回头的路,传统西藏社会势必遭受巨大的冲击,教育体制亦难幸免。白玛娜珍在《西藏的孩子》(2011)里记述了自己儿子的受教过程,有磨擦,有坚持,也有亲子之间的感人互动。它俨然成为现代西藏孩童教育的一个样本,逼使教育体制的问题在温馨的亲子叙事中赤裸现形。
如何为藏族人和藏文化找到一条出路,是所有当代藏人的共同问题。扎西达娃在《聆听西藏》(1991)写到康巴人的民族性:“我的祖先是西藏东部人,被人称为康巴人,他们彪悍好斗,憎爱分明,只有幽默,没有含蓄,天性喜爱流浪,是西藏的‘吉卜赛人。直到今天,在西藏各地还能看见他们流浪的身影,我觉得他们是最自由也是最痛苦的一群人;也许由于千百年沿袭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他们在流浪的路上永远不停地寻找什么,却永远也找不到。他们在路上发生的故事令我着迷,令我震撼,令我迷惘”(锺怡雯、陈大为编《当代西藏汉语文学精选1983-2013》,台北:万卷楼,2014,页108)。如今二十三年过去,康巴人(应该可以涵盖所有西藏人)对生命的领悟,原有的那种超越物质文明的精神自由,是否还存在?他们会不会陷入白玛娜珍所描述的困境当中?西藏汉语写作,就在这形而上的冥想和形而下的审视之间,持续拓展它的版图。
6
以一九八三年雪野诗为起点的第二期“藏文化的诠释”,是西藏汉语写作从边疆走向中国文坛中心的重要阶段,众多名家共同建构了一个宛如坛城般,精致绚丽,历久而不衰的西藏图象。源源不绝的藏文化铀矿,支持着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各路人马在此各取所需。
阿来在《大地的阶梯》的后记,尝试去界定眼前这个西藏,他说:“在中国有着两个概念的西藏。一个是居住在西藏的人们的西藏,平实,强大,同样充满着人间悲欢的西藏。那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现实,每天睁开眼睛,打开房门,就在那里的西藏。另一个是远离西藏的人们的西藏,神秘,遥远,比纯净的雪山本身更加具有形而上的特征,当然还有浪漫,一个在中国人嘴中歧义最多的字眼”(《人民文学》,2001,页272)。
对西藏的理解,“日常”与“神秘”正是一体之两面。日常未必是寻常,有可能是对神秘事物的麻痹,或视若无睹;神秘所产生的魔幻,也许是对陌生事物的过度诠释,或相由心生。藏传魔幻,日常西藏,都是西藏汉语写作的魅力所在,都是神授的诗篇。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