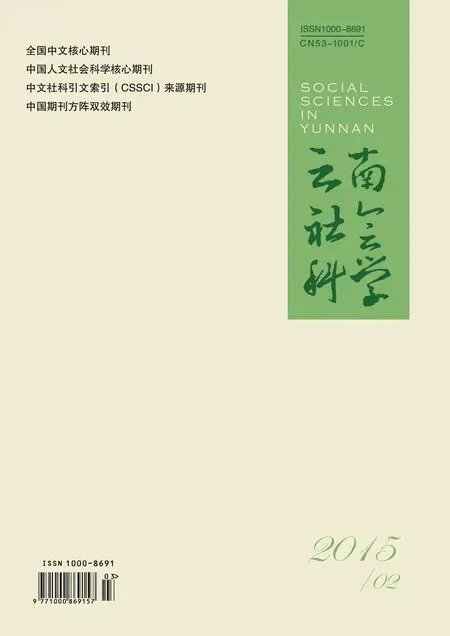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王 正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对这一命题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探讨。而对比儒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先秦其他诸子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儒家和其他诸子对人禽之辨的不同态度?同时,在儒家内部,孔子、孟子、荀子等对人禽之辨的切入点也有所不同,进而形成的道德哲学也颇有差异。那么,又应当如何理解儒家内部的这些不同?本文试图以这样两个问题作为导引,切入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探讨其中的道德哲学内涵,并试图勾勒出儒家道德哲学的一些特征。
一、孔子及孔门弟子的人禽之辨
人禽之辨在孔子这里尚非核心问题,不过他已经开始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孔子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孔子在这里虽然感叹的是同道的难得,但同时也透露出了人禽之辨的意味,甚至可以说,这一论述为人禽之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皇侃《义疏》引江熙语云:“理有大伦,吾所不获已也。若欲洁其身,韬其踪,同群鸟兽,不可与斯民,则所以居大伦者废矣。”这里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论语·微子》下一节中子路对隐者的一段评论:“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对于子路来说,隐者那种不与人同群的行为是丧失或混乱了人伦之道的,因而是不正当的。应当说,孔子对子路的这个评价是接受的,也即在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不能离开他人和鸟兽同群的原因,就在于人根本无法逃离于人伦之外。换句话说,孔子事实上已经认识到,人和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是以人伦生活为根本规定的人文性或人文化的存在,而禽兽则没有这个规定性,它们仅仅是自然的生物性的存在。而“作为文明时代的主体,人不能倒退到自然状态,而只能在人化的基础上,彼此结成一种社会的联系”*杨国荣:《善的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因此,人就应当按照人伦规定来生活,任何试图逃离人伦之外隐居的想法和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
孔子这一想法为孔门弟子所继承。《大学》云:“《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朱子认为,这里的五条人伦道德乃“人当知所当止之处”的“其目之大者”,也就是说人伦之道是人应当达到而不可改易的当然理则。有趣的是,《大学》作者将此与孔子论“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合在一起,显然是认为人如果做不到符合人伦之行,就还不如鸟尚且知道自己该居处在哪里。虽然这句话不是紧扣着人禽之辨讲的,但可以看到,《大学》作者认为就如鸟当知自己该居处何地,人同样当知自己该居处何地,也即人应当知道自己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什么。显然,《大学》作者将人伦道德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因而三纲领、八条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着成人这个话题进行的,这也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人之学”“成德之教”的缘故。
二、孟子的人禽之辨
孟子特别重视人禽之辨,在他看来,人禽之辨是确立人的道德主体性和道德普遍性的基础。孟子指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孟子首先肯定了人和禽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人无法回避自己的动物性存在,人在反思自己的生存时不能丢掉动物性这一维度;而正是由这一维度出发,可以进一步发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性所在,那就是人伦之善。“按照孟子对人性的界定,人的‘食色’等生理感性欲望虽然也是人生来就有的,但‘君子不谓性’,因为这不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特殊属性。”*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7页。孟子认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仅仅追求不挨冻、不挨饿的生理性的温饱生活,这实际上和动物没有差别,因此这些也就不能算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而真正使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人伦”,“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伦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是人与禽兽区分开来的根本,是人在动物性存在之外的另一层存在。当然,人之所以会有人伦道德,是在于人是具有“四端之心”的存在,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是人的“良知良能”,而它们的发用,就形成了人伦道德。
孟子的人禽之辨,在很大程度上是试图通过“类”观念来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他曾指出不知类的危害:“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则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孟子·告子上》)身体上有疾患、不像他人那样正常,人们就会厌恶自己的不足,进而苦苦寻求方法以求使自己变得正常起来,而当人们的心理有问题、心术不正的时候,却常常不能厌恶自己这方面的不足以寻求改变。这表明,人们在认识上混淆了自己归属的类别,即未能把心灵上的不正常归于不正常,进而无法认识到什么是正常。因此,孟子认为人必须知类,而知类中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禽之辨,通过人禽之辨人可以发现“善性良知是天赋予人的,是先于经验的,是人区别于他物的类特性、类本质,在人之类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性的”。*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7页。可见,孟子通过“类”的论证,逻辑的将道德注入到了人性之中,从而真正对旧有的天生人成的人性论进行了突破,使得性善在人性中得以扎根。
但普通人却常因为不知类而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结果无法使自己真真正正地符合一个“人”的要求,他只能一会是人的行为,一会是禽兽的行为。而一个彻底堕落到禽兽层面的人,因为丧失了人伦的观念,所以首先无法与人为善,他待人“以横逆”,即使对方自反自新,而“横逆由是也”(《孟子·离娄下》);不仅如此,他的处世原则很大程度上近似于霍布斯的“人与人是狼”的“丛林法则”,《孟子》中曾批评这样的统治者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滕文公下》),正因为没有人伦观念,所以堕落到禽兽性存在层面的人,根本没有同情心,他有的只是对欲望满足的无限追求,因而他只会伤害、侵犯他人。
正因为孟子认识到人和禽兽的差别很少,人很有可能堕落到禽兽的层面去,所以他特别重视工夫论。因为如果没有工夫进行作用的话,人无法保证自己始终存在在人的层次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如前所述,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禽的区别就在于人性是善的 ,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因而人只要时时刻刻把仁和礼存在心中,这样就能使自己远离禽兽性的存在。因为仁是人伦的内在道德本性基础和道德情感来源,礼是人伦的外在道德体现和具体道德规范,对此二者的操存,意味着时时刻刻将人伦存在心中,也即事事物物都按人伦去做,这样人就能始终是超越了动物性的符合人性的存在。
正因为人禽之辨在孟子的道德哲学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所以孟子以人伦来批评杨朱和墨子,“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这样一个严厉的批评,表明孟子的确以人伦为人和禽兽的判别标准,也即有无道德的评判标准,人能依人伦进行思维和生存便是人,人若背离了人伦的思维和生存便不是人了。
三、荀子的人禽之辨
由上所述,孟子那里的人禽之辨是从人伦的角度进行的,而孟子的人伦更多的是内在仁义道德的维度。而在儒家的另外一派那里,则更注重从礼的维度来区分人与禽兽。“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上》)西方道德哲学经过语言哲学的转向和发展后,将人和动物的差别很大程度放在语言能力和符号思维上,认为动物欠缺语言组织能力和概念构造能力,而这两种能力是人所独具的。但在《礼记》本篇的作者看来 ,禽兽并不欠缺语言能力和符号思维,或许它们在这两方面的能力没有人类那么强,但也绝非没有;所以人和禽兽的根本差异不在于语言,而在禽兽无礼而人有礼。这里的礼,侧重的是礼所体现的分义。“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礼记》作者认为礼的根本含义在于其中的区别、差异意义,而这种意义建立的根本在于男女有别。我们知道,根据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考察,人类在母系社会时期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因而会发生很多在现在看来是乱伦的事情,这种习俗,直到后代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仍有残留。而《礼记》批评这种代际间的乱伦行为,认为这是禽兽的行为,“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礼记·曲礼上》)。
荀子继承了礼学派的这一论述,并且有一套更全面的考量,“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广泛考察了各种存在物,指出动物也是有知的,即人和禽兽的差别不在认知能力上;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根本差异在于人有义,这个义,就是分,而分能使人产生不同于禽兽的社会组织性。“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这里的分,等同于《礼记》所说的别,即分别的类观念和区别能力。显然,荀子将这种分别的能力作为人和禽兽的根本差异。而这种分别的能力,正是超越了母系社会的伦常不分后之对父子、男女具有清晰分别的一种意识。“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因此这种分之义的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的类判断,更是一种对人的具体伦理角色的清晰意识,同时也是对作为社会组织性的人的认识。
可见,对于荀子来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既然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不在于其自然的生物性,而在于其人伦道德的社会组织性,所以人的生存就应当以这种社会组织性的人伦为根本。因此荀子虽然持“本始材朴”的人性论,但正如徐复观先生分析的,荀子的人性论可以分解为几类内容:“第一类,饥而欲食等,指的是官能的欲望。第二类,目辨黑白美恶等,指的是官能的能力。第三类,可以为尧禹等,……指的是性的可塑造性。”*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事实上,在荀子这里,正是要用第二类的人的本能来改造第一类的人的自然生物本性,从而实现第三类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因此,荀子认为人具有独特的分别能力——心知与辨、分,因而人的认识能力是最强的,也即人具有无限的学习能力。那么人应当如何运用这一能力,或者说人应当如何学呢?“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人应当利用自己最为独特而强大的分别性的学习能力来进行学习,而学习的内容就是人伦,也就是礼——礼是人群差异的大纲大纪,通过学礼和实践礼即可以渐渐达到人伦的极致而成为圣人,因为圣人是“尽伦者也”(《荀子·解蔽》)。
应当说,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他们的人禽之辨都是从人伦这一点展开的,只不过孟子更注重人伦中所体现的内在于人心灵的道德意识和价值判断,而荀子更看重人伦中所体现的人的分别意识和礼的规范。但是这种差异是在对人伦进行肯定下的具体差别,实际上,孟子也对人伦中的角色伦理之分别有清醒意识,所以他有五伦的划分;而荀子也对人伦中的道德意识有所认知,他曾指出恶人是“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荀子·修身》)。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全面的人伦概念,应当是综合了道德意识和分别意识的,也即是仁和礼共同形成的。而先秦儒家通过将人伦作为人禽之辨的本质差异,首先指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这种确定,既发现了人作为一个不同于禽兽的特殊之类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从而凸显了人的高贵性和自主性;同时又为所有人类都确定了一个不可逃避的道德普遍性,即:只要你还自认为自己是人,你就应当按照人伦去行,否则你就不再是个人了。就这个方面说,人禽之辨帮助儒家完成了从实然领域到应然领域的过渡,为儒家道德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先秦儒家虽重视人禽之辨,却并没有将人和禽兽彻底断绝开来,儒家在进行人禽之辨时,清醒地意识到人与禽兽的差异是非常小的,人不仅是道德的存在,也同禽兽一样,是认知的存在、肉体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会有认知的错误、肉体的欲望,而这两者都可能将人导向于作恶;所以先秦儒家便构造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修养方法和工夫理论,以求让人能改正认知错误、形成正确认知,合理肉体欲望、去除不当情欲。最后,儒家以人伦作为人禽之辨的根本,这样的一个区别表明儒家始终将人置于社会组织当中,有学者论证儒家的道德哲学近似于西方的社群主义,的确,儒家讲道德并不脱离人伦来讲,无论是五伦还是礼都是在社会、社群之中;但是,儒家又绝不忽视个体的道德独立性,无论是对工夫论的高度重视,还是对个体在社会中道德实践之困难的清醒意识,都表明儒家的道德哲学力图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位置,它既不是原子主义的个人观、又不是偏重公共善的社群主义,它是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求得中庸的道德哲学。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在儒家的事物的理序中,一个活生生地活着的个我,远比仅作为短暂存在的生物体要复杂得多和有意义得多。……人的结构中,本来就有无限的生长潜能和取之不竭的发展资源。”*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的确,儒家通过人禽之辨建立的道德哲学以及人的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当代乃至未来道德哲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余 论
以上所述,均显示出先秦儒家对人禽之辨的特殊重视,因为由人禽之辨的证成,可以进一步推导出道德的普遍性和儒家修养工夫的必要性,可见,它是儒家构建其道德哲学的重要基础。而作为儒家论辩对象的诸子,则对人禽之辨有不同的意见。如道家因为从根本上提倡自然主义、并否定人伦道德,所以他们基本是反对人禽之辨的。《庄子》中讲道:“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道德是“真”而“天”的自然无为,是纯任自然的,人不应有一丝一毫的机巧心思、认识智慧、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和禽兽不应当有所区别。因为从道家哲学出发,是不需要人禽之辨的,因为如果进行人禽之辨,就意味着要进行理性分别和价值判断,而这就会割裂这个自然而然的世界,所以道家哲学反对人禽之辨,要求人们从这种分别中解脱出来。“牛马四足,是谓天;穿马首,络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人道绝不应当违背自然,而是应当去除刻意、消除欲望、返归自然,也就是复归到人与禽兽都是自然而然的浑融状态中去,在那个状态中,人、天都混沌无别,更何况人禽之辨了。显然,消除人禽之辨,是道家非人伦道德的自然主义的基本倾向,由此,我们可以反过来看到人禽之辨对儒家构建道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果不能确认人与禽兽的根本差异,人的道德独特性就无法证明,进而人类世界的道德普遍性也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而由儒家分裂出去的墨子,显然对儒家好谈人禽之辨有一定心得,他了解人禽之辨对构建道德哲学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也曾对人禽之辨有过论述,但他的论点则完全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墨子·非乐上》)墨子也认为人禽之间有重要的差异:即禽兽依凭着他们自身的先天自然条件就可以生存,所以它们不需要再刻意的努力;但是人则不然,人若只凭借着自身的自然条件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人需要“力”,也就是努力、勉强。所以在墨子看来,人禽之辨的根本处在于人必须付出极大的后天努力才可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他的道德哲学乃至政治哲学就是消除一切有害于人后天努力的因素,而构建起一个最有利于人进行努力的社会。经由墨子,我们可以发现,即使认可人禽之辨,但是如果立论的角度不同,最后产生的结果也是差异极大的。
由道家和墨家对人禽之辨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了解人禽之辨的确对构建道德哲学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由墨家和儒家的不同人禽之辨,我们更可以了解到,不同的理解可以导致不同的道德哲学,而儒家道德哲学的独特性也由此可以发现。
综上所述,先秦儒家之所以重视人禽之辨,就在于它能勾勒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这一方面是儒家构建其道德哲学中道德普遍性的理论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儒家确立人的道德自主性的理论必然。正如明代儒者陈献章在《禽兽说》中所写“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陈献章:《陈献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1页。儒家对人禽之辨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异非常之小,就一个人来说,他本身有非常多的禽兽因素,比如肉体、欲望乃至于一些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不可回避的,而如果人不能对这些自然的生物属性进行超越,那么人就和禽兽没有任何差异。然而,人又是与禽兽不同的,人都有其独特性所在,这就是人的人伦道德性和社会组织性。西方社群主义的代表麦金太尔曾批评西方道德哲学“没有承认或者拒绝充分承认我们的存在有一个肉体的维度的观念”,而且将人和动物的区别单纯放在理性的维度上,“即我们的理性作为思考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我们的动物性”。由此,西方道德哲学“就忘记了肉体”,“忘记了我们的思考乃是一种动物物种的思考”,于是无法对人的依赖性、脆弱性和苦难、残疾予以正视。对此,麦金太尔重新对人进行了定义,他将人界定为“依赖性的理性动物”,进而认为要讨论作为这样一种存在的人的德性,就必须将“我们的依赖性、理性和动物性置于相互关系之中来理解。”*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6-12页。应当说,先秦儒家的人禽之辨,既突出了人的仁、礼、义的道德独特性,而又不忽视人自身难以逃避的动物性欲、情,这表明儒家的道德哲学,既没有身心二分、遗忘肉体的弊病,又将人置于个人与社会之间、正视人的独特性和依赖性的关系,因而,从儒家的角度重新思考道德哲学,或许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道德哲学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