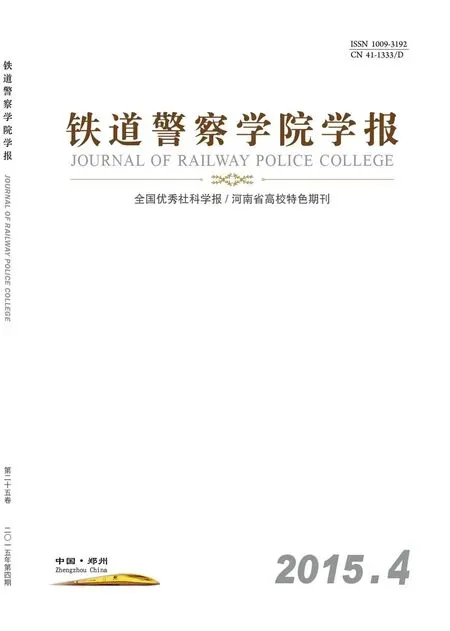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92(2015)04-0051-08
收稿日期:2015-05-10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广西玉林人,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存在着实害犯和危险犯之分。实害犯是指以出现法定的危害结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而危险犯是指以实施危害行为并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何谓危险犯中的“危险”?国内外许多刑法学者认为,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致使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可能受到侵害的危险。若根据这一理解,所有故意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和未遂以及行为犯均属于危险犯,这导致了危险犯的泛化,让危险犯与行为犯难以区分,因此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为了厘定危险犯与行为犯的界限,合理限制和准确惩治危险犯,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危险犯的“危险”应从狭义上来理解,其应仅指“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前者是指以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为构成要件内容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即属于故意的具体危险犯,第332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则属于过失的具体危险犯。后者是指刑法规定的、一旦实施即可推定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的犯罪。例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即属于抽象危险犯。刑法规定,该法定行为一旦实施,即可推定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
由于刑法规定了危险状态是一种特殊的危害结果,危险状态是危险犯的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而危险状态是会进一步发展为实害结果的,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对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会呈现出复杂的联结状态。正因如此,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对一些危险犯的罪过形式在理解上产生了重大分歧。譬如,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后,人们对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危险驾驶行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我国刑法将危险驾驶罪放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一般认为,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但是,关于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人们争议较大,具体观点主要有两种:(1)故意说。该说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驾驶人员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结果的态度是故意的 [1]。(2)过失说。该说认为,(故意的)危险犯和实害犯明知的对象应是同一的,即明知实施危险行为会造成实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出现,只不过,实害结果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出现。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由于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也是紧密联系的,虽然该罪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行为是故意的,但是,行为人对一切严重危害结果是持否定态度的 [2]。
笔者认为,围绕危险驾驶罪产生“故意说”与“过失说”之争的原因在于,当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时,人们对其罪过形式指向的对象(危害结果)理解不一。前者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所指向的对象(危害结果)应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其对危险状态的心态为故意,因而其罪过形式是故意。后者认为,该罪的罪过形式所指向的对象(危害结果)应是危险行为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其对实害结果的心态是过失,因此其罪过形式是过失。
危险驾驶罪这一抽象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情况是较为复杂的。行为人在实施危险驾驶行为时,在心理上必然面向两个结果,一是法定的危险状态结果,二是可能的实害结果。就法定的危险状态结果而言,行为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就可能的实害结果而言,行为人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该罪的罪过形式是以对法定的危险状态结果的心态为准还是以对可能的实害结果的心态为准——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在分析危险驾驶罪的心态情况时,行为人对法定的危险状态结果和可能的实害结果的心理联系是存在许多种可能的,因而对其罪过形式的确定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在危险犯的各种心理联结模式中,其罪过形式是以对危险状态的过错心理为准,还是以对可能造成的实害结果的过错心理为准,这是确定危险犯罪过形式的关键。
从前文分析可知,刑法既规定了危险犯,同时又规定了与之相应的实害犯,因此,在危险犯中,行为人对法定危险状态结果与可能的实害结果的心理联结情况较为复杂,人们对于其罪过形式如何确定,也存在诸多争议。危险犯可分为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前文论述的危险驾驶罪的心理联结模式仅是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中的一种。危险犯究竟还有哪些心理联结模式,在不同心理联结模式下其罪过形式如何确定,这些问题都是亟待人们去探索和解决的。
二、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的确定
危险犯以法定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判断其既遂的标准。危险状态是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实害结果的,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危险行为时,其对危险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所形成的心理联结模式会呈现多种情况,而在不同的心理联结模式里,其罪过形式的准确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一)危险犯心理联结模式与罪过形式确定的原理
在危险犯里,当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时,其罪过形式如何认定?当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时,其罪过形式又如何确定?在别的心理联结模式下,其罪过形式又依据什么来确定呢?笔者认为,罪过形式的确定应以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为依据。
我国《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分别规定了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两种罪过形式。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从上述规定看,罪过形式的确定是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为标准的。笔者认为,对于危险犯和实害犯来说,这里所说的危害结果应指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危险犯的法定危害结果是危险状态,而实害犯的法定危害结果是法定的、物质性的危害结果。
对于危险犯而言,其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是其法定的危险状态,危险犯的既遂应以法定的危险状态出现作为判断的标准。在罪过形式认定上应以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和态度来判断。在危险犯中,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不能作为其罪过形式,因为这一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并不是危险犯的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只有实害犯才可能以对实害结果(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作为其罪过形式。
例如,从《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看,在危险驾驶罪中,行为人对法定的危险状态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故意,对可能的实害结果只能是过失,因为若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故意,则构成《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就是说,其心理联结模式为:对法定危险状态的结果持故意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即“故意—过失”模式。在我国刑法中,除了危险驾驶罪是这种心理联结模式外,还有一些危险犯也属于这种心理联结模式。
对于心理联结模式为“对法定危险状态持故意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的危险犯而言,由于其犯罪构成的危害结果为危险状态,而该类危险犯的实施者对这一危险状态的发生持故意心态,因而应以故意为其罪过形式。这种危险犯的实施者所持的“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过失心态”并不是其罪过心态,因为尚未发生的实害结果并不是该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客观危害结果。犯罪构成中罪过形式以主体对必要客观危害结果(或实害结果或危险状态,或行为犯的无形结果)的心态来认定。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虽然“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过失心态”并不是这种危险犯的罪过心态,但这一心态在主观上对这种危险犯的认定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与“对危险状态持故意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故意”的心态模式的危险犯(如《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等)在主观上区分开来,它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也是这种危险犯的犯罪主观要件中的独特要素。
(二)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的确定
危险犯“明知”的危害结果是法定的危险状态。危险状态进一步发展的危害结果是实害结果,因此在实施危险犯罪时,行为人对实害结果是否预见以及持何种态度会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危险犯对法定危险状态结果和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联结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故意—过失”模式
该模式是指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这种心理联结模式属于故意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该种危险犯的法定危害结果为危险状态,它应以行为人对危险状态心理认知为其罪过形式,即该种犯罪的罪过形式为故意。危险驾驶罪的心理联结模式即属于这种模式。在危险驾驶罪中,行为人对实害结果的发生是持过失心态的,如果行为人对危险状态及实害结果均持故意心态,其行为就不构成危险驾驶罪,而是构成性质比较严重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危险驾驶时,如果行为人造成多人死亡,而其对危害结果持过失心态,其行为就应定为交通肇事罪,构成想象竞合犯,应从重处罚。
2.“故意—故意或过失”模式
该模式是指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故意或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由于持这种心理联结模式的危险犯的法定危害结果是危险状态,而行为人对法定危险状态结果持故意心态,因此,这种危险犯的罪过形式也属于故意。
我国《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许多故意危险犯即属于这种心理联结模式。涉及的罪名主要有:第114条、115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6条、117条、118条、119条规定的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等。这种犯罪的心理联结模式又可细分为两情况:
(1)“故意—故意”模式,即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的模式。对于这种心理联结模式的犯罪直接按相关犯罪的条文以故意犯罪定罪是没有争议的。例如,对于放火罪,行为人在放火时明知放火行为会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以及可能造成实害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发生,这时,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放火罪。
(2)“故意—过失”模式,即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模式。
对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言,如果行为人实施前述的放火等行为时已经预见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的发生,并希望或放任这种危险状态的发生,同时,行为人对已预见到的、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否定态度(如轻信能够避免),那么,对该行为是以故意危险犯认定,还是以过失犯罪认定呢?
例如,甲驾驶一辆中型的客运班车,车上有20名乘客,其中包括甲的妻子、儿子和父母,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一辆面包车不小心刮碰了甲的客车,但驾驶面包车的乙为了躲避赔偿而加速逃离。甲为了让乙赔偿,驾驶客车快速追赶。追上后,甲在快速行驶中不断地用客车挤压面包车,想迫使面包车停下,当时车上乘客非常害怕,有的还发出尖叫声,乘客们叫甲不要挤压了,否则,可能出现翻车事故,或造成其他伤亡事故,甲不听并继续挤压,十几分钟后,面包车碰到电线杆后停了下来,面包车轻微受损,甲的客车在挤压中也轻微受损,损失几千元。
在本案中,甲在车辆快速行驶中用客车挤压面包车达十多分钟之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对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持放任态度,但是对车毁人亡的实害结果应该是持否定态度,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儿子和父母均在车上,他自信自己已有十多年的驾龄不可能会造成严重实害结果的,因此,甲对实害结果持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态。
对于这一案件,是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还是不认定为犯罪(若以“过失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其实害结果还不严重,因而不能定罪)呢?
笔者认为,这种“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与危险驾驶罪的心理联结模式是一样的,应以“危险状态”这一危害结果为其“明知”对象,并以故意危险犯论处,因此,前述案件中甲的行为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过失—过失”模式
该模式是指对危险状态持过失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危险犯可分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前面所述的两种心理联结模式均属于故意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而这里所述的“对危险状态持过失心态而对可能的危害结果也持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则属于过失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所谓过失危险犯是指刑法规定的、过失地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发生的危险犯。在过失危险犯里,行为人对导致的危险状态持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对于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同样持过失心态。例如,《刑法》第330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即属于过失危险犯。在该罪里,行为人对于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持的是过失心态,而对于造成实害结果所持的心态也是过失心态。如果行为人对危险状态的发生或实害结果发生持故意心态,就不构成该罪,而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犯罪。一般认为,我国《刑法》第332条规定的妨害边境卫生检疫罪也属于过失危险犯,其心理联结模式也属于“对危险状态持过失心态而对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心理联结模式”。
三、危险犯心理联结模式与司法实践
正确分析危险犯对危险状态与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正确理解危险驾驶罪分别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联系和区别,准确把握《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关系,以及搞清《刑法》第114条规定的危险犯和第115条规定的实害加重犯与其相对应的过失犯罪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联系与区别
危险驾驶罪的心理联结模式是“故意—过失”模式,它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出现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而且该罪应以危险状态的危害结果为必要构成要件,其主观罪过以对危险状态的心态(即故意心态)为标准,属于危险犯。有人提出,该罪主观罪过应以行为人对实害结果的过失心态为标准,应属于过失犯。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如果将对实害结果的心态确定为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那么,该罪就应以实害结果为其犯罪构成的客观必要条件,但从《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规定看,危险驾驶罪并不要求以出现实害结果为其必要要件。可见,将危险驾驶罪认定为过失犯罪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出现错误,是因为其未搞清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联系与区别。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联系
在危险驾驶罪中,行为人主观心理联结模式是“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持过失心态”。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醉酒驾车或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并造成了危险状态。
在危险驾驶罪案件里,行为人的行为在危险驾驶的心态支配下,一旦过失地发生严重的实害结果,即构成交通肇事罪。此时,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形成想象竞合关系,即危险驾驶行为既触犯了危险驾驶罪,也触犯了交通肇事罪,应以重罪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而在没有导致严重实害结果的情况下,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具有“实害结果的心理联结”关系。因为在这一情况下,危险驾驶罪在主观心态上对实害结果的不同心理态度是影响到犯罪定性的。如果行为人对严重实害结果的心态和交通肇事罪的心态一致,就可定危险驾驶罪,这两者对严重实害结果均存在着过失心理联系。但是,如果其对严重危害结果持故意心态,就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能定危险驾驶罪,因为危险驾驶罪对“可能的严重实害结果”的心态仅指过失心理联系的心态。
2.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为:实害结果是否是客观要件的必要要素。危险驾驶罪在客观方面不以实害结果为必要要素,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则以实害结果为必要要素。
(二)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而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具体危险犯是以产生具体的、现实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危险犯。而抽象危险犯是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产生抽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作为犯罪构成必要条件的危险犯。对于抽象危险犯而言,其所指的抽象的危险是指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经验,实施这一危害行为通常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对于抽象危险的认定,只要行为人实施的法定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存在,在一般情况下,就可认定抽象危险的存在,而无需在具体个案中判定是否存在具体的、现实危险状态。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有两种心态模式:(1)“故意—过失”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2)“故意—故意”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后,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一般按以下情况处理:
第一,若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符合第(1)种心态模式,并造成了严重实害结果,应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因为这一种情况下的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交通肇事罪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外的、一个独立的犯罪。这时,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竞合关系。
第二,若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符合第(1)种心态模式,但是危险驾驶行为仅造成危险状态,而没有造成实害结果,则应定危险驾驶罪。因为这时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是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竞合关系,因而,应以具体的危险驾驶罪定罪。
第三,若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符合第(2)种心态模式,不论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危险状态还是严重的实害结果,均应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在危险驾驶情况下,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态是故意抑或是过失,是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别的关键,因此,当危险驾驶行为实施后,若其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持故意,就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第(2)种心态模式下,因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所以,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明确的具体危险时,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如果查明危险驾驶行为发生后没有造成具体危险时,能否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者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呢?笔者认为,由于危险驾驶罪的心态模式是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因此,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故意心态”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态的,因此不能定危险驾驶罪。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具体危险犯,其犯罪既遂的标准是发生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在危险驾驶时,如果行为人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那么,在查明具体危险没有实际发生的情况下,若行为人对严重的实害结果持希望的心态,其行为仍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但是,应按犯罪未遂处理。若行为人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放任态度,那么,由于具体危险或可能的实害结果发生与否均不违背行为人意愿,因此,该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心态关系
《刑法》第114条规定了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危险犯类型,而第115条规定的是这些犯罪的结果加重犯类型。第114条规定的内容是第115规定的各个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构成。对于结果加重犯,按基本犯罪构成的罪名定罪,不实行数罪并罪。
《刑法》第115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与第114条规定的危险犯具有的心态联结关系,具体有两种:
第一,“故意—过失”的联结关系,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加重结果(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心态联结关系。
《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放火罪是故意犯罪,这些犯罪对危险状态肯定持故意心态,但对加重结果既可能持过失心态,也可能持故意心态。所以说,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加重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心态联结模式属于这些结果加重犯的一种心态联结模式。例如,李某是一名初中生,他很想加入共青团,但是他的成绩不好,其他方面也不突出,因此未能如愿。有一天,他看到村边有一大堆干燥的稻草,即产生了趁人不注意时燃烧这堆稻草,然后去救火,让群众看到他救火的事迹,以此达到入团的目的。在放火前,他知道这一大堆稻草毗连着易燃的房屋群,只要稻草燃烧,就会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并有可能造成重大火灾。为了防止造成重大火灾,他在现场准备了几桶水作灭火用。他在将稻草点燃一段时间后即大喊:“救火!救火!”并积极去救火,附近的群众也赶来救火,但由于火势过猛,最终还是将几间房屋烧毁了。在这个案件里,李某故意放火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但他对可能发生的重大实害结果所持的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心态。因此,对其行为应定放火罪,按《刑法》第115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处理。
第二,“故意—故意”的联结关系,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加重结果也持故意心态的心态联结关系。这种心态联结关系在实践中是最为常见的。例如,在发生严重实害结果的爆炸案中,行为人对爆炸行为可能会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施危险犯罪之后出现的结果加重犯与传统上所说的结果加重犯相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其基本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是危险状态。在通说里,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构成中的危害结果是实害结果,例如,《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罪(重伤或致人死亡)是结果加重犯,其基本犯罪构成规定在第134条第1款,这一条规定的基本危害结果是实害结果(轻伤)。但是,对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危险犯来说,其危害结果为危险状态。因而,《刑法》第115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构成规定在第114条,其基本犯罪构成的危害结果为危险状态。这一点,在司法实践中应予以注意。
(2)对加重结果的心态既可以是故意心态也可以是过失心态。在通说中,结果加重犯中对加重结果的心态只能是过失心态,例如,《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其对重伤、致人死亡的加重结果的心态是过失心态。但是,在《刑法》第115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中,其对严重的实害结果的心态既可以故意心态,也可以是过失心态,而且从实践来看,大多数案件对实害结果持故意心态。
(四)《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罪与相关危险行为的心态联系
《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过失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严重实害结果发生的,构成相对应的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这些过失犯罪对发生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是无争议的,但对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和以其他方法导致危险状态的心态是持故意还是过失呢?笔者认为,前文论述《刑法》第115条第1款和第114条的心态联系时已阐明,第115条第1款的放火罪等与第114条的心态联结包括两种情况:(1)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2)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从这里可知,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的,应按《刑法》第115条第1款以故意犯罪认定,因此,《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过失犯罪中,行为人对先前的危险状态仅能是持过失心态。其心态联结关系是“过失—过失”的联结关系,即对危险状态持过失心态而对实害结果也持过失心态。
四、关于危险犯的立法思考
根据对危险状态和实害结果所持心态的不同,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可分为三种。心态模式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对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从而影响其法定刑的设置。从前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危险犯存在着一定的立法缺陷,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
(一)对故意危险犯的立法思考
故意危险犯的心态模式有两种:一是“故意—故意”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二是“故意—过失”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从这两种故意危险犯的心态模式比较来看,由于第一种故意危险犯对可能的实害结果持故意心态,而第二种故意危险犯对可能的实害结果则持过失心态,第一种故意危险犯的社会危害性显然比第二种大。但是,我国《刑法》第114条、第116条、第118条等故意危险犯的规定均将上述两种心态类型合而为一,不加区分,并使用同一法定刑,这是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为此,我们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将这两种心态类型的故意危险犯分别规定为两种独立的犯罪类型,并规定各自的法定刑。例如,对于《刑法》第114条可这样规定:故意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并对可能发生的严重结果持故意心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前述故意犯罪,若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严重结果仅持过失心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
(二)对故意危险犯延伸而形成的结果加重犯的立法思考
《刑法》第115条第1款、第119条第1款等规定的结果加重犯是由第114条、第116条、第117条和第118条等规定的故意危险犯延伸而成的。这些结果加重犯的心态模式也有两个:(1)“故意—故意”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严重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2)“故意—过失”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严重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两种心态模式相比,第一种心态模式下的结果加重犯的社会危害性要大于第二种心态模式下的结果加重犯,其法定刑也理应不同,但是,《刑法》第115条第1款、第119条第1款却将这两种不同心态模式的结果加重犯合而为一,不分彼此,并适用同一法定刑,这同样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为此,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将这两种不同心态模式的结果加重犯也分别规定,并采用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对于《刑法》第115条第1款可修改为:故意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并且对造成的严重结果持故意心态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对于前述故意犯罪,若行为人对造成的严重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三)对过失危险行为引起的过失犯罪的立法思考
《刑法》第115条第2款规定的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均为过失犯罪。导致这些过失犯罪的危害结果的前提行为均为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行为人实施这些危险行为时,对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的心态以及对严重实害结果的心态分别是什么呢?《刑法》第115条第1款和第2款是这样规定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从上述条文规定可知,该类犯罪对严重的实害结果的发生持过失心态是无疑的,但对于行为人在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行为时,其对危险状态是持故意心态还是过失心态,该条并未明确规定。从前述对《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第1款分析可知,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的危险犯划归为故意危险犯,即使其中有一种心态模式为“故意—过失”的危险犯也归属于故意危险犯。《刑法》第115条第2款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法定刑较低,因此,笔者认为,这些过失犯罪是由过失危险行为延伸而出的过失犯罪,行为人在这些犯罪行为中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只能是持过失心态,即其心态模式为“过失—过失”模式(对危险状态持过失心态而对实害结果也持过失心态)。
综上,为了在立法上明晰前述内容,可将《刑法》第115条第2款修改为:过失实施前款犯罪的,并过失造成前款严重结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思考
危险驾驶罪的心态模式是“故意—过失”模式,即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性的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当行为人实施危险驾驶行为的心态类型为“故意—故意”(对危险状态持故意心态而对可能的实害结果也持故意心态)时,该行为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是,《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并不能明晰这一心态联系,因而在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形式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区别等领域引起了较大纷争。为此,有必要对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法完善。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之一可修改为:故意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故意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并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实害结果持过失心态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犯前款罪,并已实际造成严重实害结果的,按《刑法》第133条以交通肇罪定罪处刑。犯第一款故意犯罪,对可能发生的严重实害结果持故意心态的,按《刑法》第114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这一修改明晰了危险驾驶罪的心态模式及其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以及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有助于准确地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