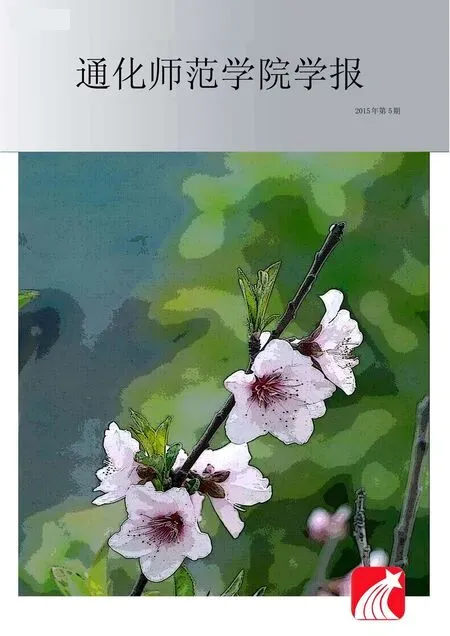索绪尔:青少年和求学时代回忆录
聂志平,译;王世臣,校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索绪尔:青少年和求学时代回忆录
聂志平1,译;王世臣2,校
(1.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2.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主持人的话】本栏目由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言理论和教学专业委员会协办
■浙江师范大学聂志平教授等翻译了索绪尔少年和求学时代的回忆录,使我们能够了解“从那时起对语言学的热情让我不能平静”的索绪尔是怎样曲折爱上语言学的及其求学时代对语言学的探索情况。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叶建军教授认为:现代汉语“果真”从状中结构(果然真实)词组词汇化,成为语气副词,再变成假设连词,对语言变化理论具有实证作用。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陈莉老师等认为:“那什么”是一个口语代词,除了替代功能,还起缓冲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语用意义代词,用来起委婉、应急等作用的占位代词。文章启发我们关注口语新现象。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倪涛认为英语“from A to B”表示时间、数量、事物和事件等范围,是它的空间范围意义的隐喻投射,对认识语言变化中的认知理论有价值。
(彭泽润,关彦庆)
1
(p.1)1876及1877年,莱比锡大学是对印欧语言学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流派的主要中心。这个学派把日耳曼学家、斯拉夫学家和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同时集中在一起。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学派活动的结果便是几乎完全改变了印欧语历史比较语法学的面貌;但更直接并很快被接受的结果,是证明存在着一系列被这一学科以前所忽略的因素,给自己造成了对原始语语音系统状况的错误认识,这个错误认识构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基础。
既然我的一本标题为 《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Мемуар 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гласных в инд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языках”)的书①见索绪尔1977俄语译文。——Н.А.斯柳萨列娃注。是这个阶段刊行的图书之一,既然这本书出版于莱比锡,此外,我1876年10月到 []②日期没有注明。毫无疑问,指的是1878年,因为索绪尔从下一年冬季学期(1878/79)开始在柏林学习。——R.戈德尔注7月是莱比锡大学的学生,那么,任何一个即将读完这本书人,完全理所当然而又自然而然地推断出,它是1876—1878年间直接在莱比锡这块土壤上成熟起来的好的或不好的果实之一。
如果这是一个结论,那么当读完这部手稿后就能够断言它是远离真相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推翻这个错误意见的想法,甚至在私人札记中也没有这个想法。首先,当这里指的是不需要什么人名字的科学的一般成果时,各种人身攻击异乎寻常地让我害怕;接着,自然而言,不管现在还是以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指责我缺乏对[]的真诚的谢意。
(p.3)在这些问题上思索了好一阵子后,我决定不必对此生气,因为实际上情况是这样,这种结论会自己产生。但略作思考后,我暗自拿定主意,如果“这样的结论自己产生”,那么,随着各种矛盾渐渐消失,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是,我自己的沉默会是有害的。看来,可能自我放任会完全曲解我的[],并且——应该完全能预料到——,超越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的优先权问题的范围之外后,也许就能提出关于难以区分自己的和别人的这一关于剽窃或怀疑性的问题了。
当我预见到这些可能的纠葛,并收到施特莱特伯尔格①施特莱特伯尔格·比尔格尔姆 (Streiberg W.1864-1925)——德国印欧语言学家、日耳曼语言学家,《印度日耳曼语研究》(“Indogermanische Forschungen”)杂志出版者(与K.勃鲁格曼协作),《原始日耳曼语语法》(“Urgermanische Grammtik”.海特伯格,1896)的作者。——Н.А.斯柳萨列娃注。教授先生的来信(1903年2月)后,——这封信是这些思考的动因——,我请求施特莱特伯尔格教授先生本人作为这些包括个人回忆的手稿的临时保管者。
(p.4)我完全信任地把这份手稿亲手交给我亲爱的令人尊敬的同事[ ]。②应该加上被删句子的开头。——R.戈德尔注。
(p.5)在我12或者13岁的时候,令人尊重的阿多里夫·皮科特,《欧洲的来源》(“Origines européennes”)③见皮克特1859。——俄文译者注。一书的作者,是我们呆在庄园那个时期的邻居。我经常去维尔附近他的马拉尼亚庄园和他见面,同时,尽管我不是很敢提出各种疑问粘着他,背着他我赞赏他的书是那么深刻,如同孩子般的直率;这部书的某些章节我认真地④所写注释令人怀疑。——R.戈德尔注。研究过。借助梵语中的一两个音节可以重建已经消失的民族的生活的,——这个想法的确是这本书的主旨,总之像那个时代的语言学家,——使我天真地感到无以伦比的热情;我没有比这真正的语言学的享受所带来的快乐更快乐的回忆了,而当今天我读这本童年时代的书时,这些快乐的回忆还让我心潮澎湃。
说实话,与这个愉快回忆同时存在的,是我在我外公阿列克斯伯爵的藏书室中给我的语言学爱好找到了另一种精神食粮。[]⑤阿列克山德拉-若杰法·德·普尔塔列沙 (没有写名字留下了空白)。——R.戈德尔注。,它在与外公的谈话中,因为他是民族学和词源学研究的超级爱好者,——没有任何方法,但有丰富思想的那种爱好者。同样也可以说他另一个嗜好——依据数学原理建造快艇;他最终没有找到这个原理,他以把自己的快艇在日内瓦湖中下水作为消遣,但是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在推论的基础上造船。这样,他的研究方向证明他智力的不平凡性。
(p.6)显然,从那时起对语言学的热情让我不能平静,因为中学里仅仅掌握了希腊语语法的初步知识,我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去描述“语言的普遍系统”,把它献给阿多里夫·皮克特。据我所知,这个想法的幼稚在于,试图证明,如果只把p、b、f、v,或者k、h、g、ch,或者t、d、th看做是相同的东西,那么所有可能的语言中都有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可以归结为只由三个辅音构成 (而在更古老的时期甚至由两个辅音构成)的词根。这样,我记得,R-K是通用的强势或垄断符号:rex,regis‘王,王的’,ργνυμι‘毁灭’,Rache‘报复’,rügen‘责备’等等;P-N-K是窒息、烟的符号:πν γω‘掐死’,Funke‘火花’,pango‘钉进’,pungo‘叮咬’等等!
卓越的学者是那么善良,他给了书面答复,其中另外写道:“我年轻的朋友,我看到您抓住了公牛的角……”,然后又对我说了一些夸赞的话,这些话产生了效力,打消了我研究语言普遍系统的兴趣。
从那时(1872年)起,我做好了接受某种另一学说的准备,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学说的话,但实际上,在非常厌倦自己一些不成功的写作后,我把语言学整整放弃了两年。
(p.7) 2⑥在手稿:3.——R.戈德尔注。
1872年秋,不知道为什么,我进了日内瓦中等学校,在那里过了整整一年而没有任何收获。被录取的理由是太年轻;我那时14岁半,尽管有很好的毕业证书,我还是不能从私立学校转到日内瓦中学,同时我的一些朋友也跟我一样处于那种情况,根据我们父母的一致决定,我们一起在公共中等学校学习一年,以便准备考入公共中学。但这一年绝对没有给我们中的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然而,那年我成功发现,在别的地方我可能不会有所发现。在第一或第二学期,——不能准确回忆起季节——我们读希罗多德的一篇课文。在这篇课文中遇到一个形式τετáχαται(ταδδω“安置,摆放”的第三人称,复数,完成时,被动态)。这个形式我完全不认识。在马尔金先生的学校里,我学会了哈斯语法中引用的这个形式τεταγμ νοι ειδι,哈斯语法是这个学校独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并是唯一被视为典雅形式的语法。在“复习”那年,我的注意力是极其分散的,这是自然的,当我一看到τετáχαται这个形式,我就立即被这个实例所吸引,因为在这以前不久,我做了以下推论,它到现在还保存在我的①在页面的左下角写道:马尔金 1870—72中等学校 1872—73普通中学 1873—75大学 1875—76 ——R.戈德尔注。(p.8)记忆里:λεγμεθα:λ γονται,因此,τετáγμεθα:τετáχNται;由此可见N=α是由此得出的必然结果。我从中等学校毕业的时候,还思索着n怎样能变成ɑ,并且还做了一系列的语音学实验。在重复做这些实验时,我确信,的确能从 τετáχNται变成τετáχαται,但是,当然,我心里也没有想到用一个特殊符号来表示这个n(比如n或其他什么类似的东西)。我认为,位于两个辅音之间是它显著的特点(从生理学观点来看的确是对的),因此希腊语中它发作α,但这仍然是通常的n(I)。
(p.7,在这页的背面)(I)现在评价突出地铭刻在我记忆里的这个事件,我今天很好地理解,为什么τετáχαται形式吸引我的注意力。的确,我们最初以为,与τετáχαται相比较,存在着难以计数的大量形式,这些形式在希腊语中能够导致响鼻音(носовой сонант, 或译鼻音领音、 鼻浊音)的构拟(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但这是不正确的。无论是“脚”的宾格形式πδα(单数)或者πδα?(复数),还是πτ(七),甚至 ιαται([他们]坐着),等等,在初看起来形态关系并不明显。只有第三人称复数中动语态完成时形式——按τετáγμεθα的存在原因——在希腊语中是完全明显的,令人信服的。Τετáχαται形式在种类上是唯一的,看到这个形式后我立刻恍然大悟,同时,这个恍然大悟在我自己看来好像莫名其妙,如果进行恰当的分析就会得到解释。
(p.8) 3
从1873年到1875年,我在日内瓦中学上课。在学习的第二年,我依然感受到对语言学的兴趣,开始按照在公共图书馆找到的葆朴的语法书学习梵语;同时,我开始研究古尔替乌斯的书《基本原则》(Grundzüge)(第二版)②G.古尔替乌斯:《希腊语词源学的基本原则》(“Grundzüge der griechischen Etymologie”),第二版,莱比锡,1858/62。,文艺作品图书馆存有一册这本书。
那时古尔替乌斯的思想与葆朴的思想在我脑中产生了冲突,在古尔替乌斯那里我找到了大量例证,像τατ(有伸展性的)或者μεμα(期望的、迷人的)(p.9),他确定了它们与带有-n音词根③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比古尔替乌斯更多地注意到ε以另外形式存在,但这里可能有的鼻音的缺失使我感到惊奇,然而,当有鼻音时,我找到了α。——费·德·索绪尔注。的关系。回忆起我在中等学校认识的τετáχαται这个形式,我徘徊在寻找借助鼻音能否解释这个ɑ的答案中。读葆朴的书时,我得知梵语中曾有个元音r,我刹那间发现了真相,比借助于τετáχαται这个形式更加突出,在心里把bhar-、bhrtas④在手稿中是天城体梵文字母。——R.戈德尔注。进行了对比;可能正是如此,tntas?很遗憾,在这里在1876年我顺利拿到的葆朴的《梵语语法》或《比较语法》⑤索绪尔偶尔提到F.葆朴两本语法书:《梵语语法》和著名的《梵语、古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古斯拉夫语、哥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见F.葆朴 “Grammatik der Sanskritsprache in kurzerer Fassung”.柏林,1834;“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Send,Armenischen,Griechischen,Lateinnischen,Litauischen,Altslawischen,Gotischen und Deutschen”.柏林,1833)。——Н. А.斯柳萨列娃注。中,我几乎意外碰到一处地方,在那里葆朴确定,不应注意梵语中的r和“毫无疑问地证明φερτ正对应于bhrtas”。我特别回忆到φερτ这个形式,葆朴对它的评论对我的(p.10)胆怯的想象力产生了惊人的、毫无根据的作用,由于我的关于语言的不幸经历,我领悟到了应该信奉权威而不是去创造自己的理论,从这以后我变得胆怯了。
也就是在1875或1876年,我向别尔根先生⑥阿贝尔·别尔根 (Bergaine A.,1938[聂注:原文如此,疑为“1838”之误]-1888)——法国语言学家,研究东方语言,是一部梵语教科书和一系列印欧语比较语法方面著作的作者。——Н.А.斯柳萨列娃注。(住在日内瓦的列欧保尔德·法夫尔先生的朋友)提出接纳我加入巴黎语言学会的请求,并从日内瓦给他寄去关于后缀-t-的文章①索绪尔的论文 《论后缀-t-》发表在 《巴黎语言学会会刊》(MSLP)1887年第3卷。——Н.А.斯柳萨列娃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到了害怕,每一行字都深思熟虑,担心表露出某种与葆朴的观点相冲突的东西,他可是我唯一的导师。
4
1875-1876年,我还虚度了一年的时间,因为按自己家族的传统,在日内瓦大学上了一年的物理和化学课。我就剩下很少的时间来做其他的事情,而在此前不久创建的日内瓦大学 (p.9在页的背面)里,只有编外副教授路易·莫列尔的课才能给愿意听课的人提供印欧语导论。我满怀谢意地回忆这门课,尽管它完全只是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课程的逐字逐句的照搬,在此之前,莫列尔先生在莱比锡听过这门课一年。从路易·莫列尔那里我汲取了比来自印刷著作更鲜活的材料。此外,路易·莫列尔的名字使我有可能指出我关于响鼻音思想产生的准确日期,并强调我所赋予那个响鼻音的重要性。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地铭记着课后我和他散步时的交谈,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您听过古尔替乌斯的课,关于这一点他说的是什么?”
(p.10) 5
这样,1876年10月我来到莱比锡②应该补充一下,我去莱比锡是“偶然的”,只是因为我日内瓦的朋友柳辛、拉乌尔·郭杰、埃德蒙·郭杰和埃杜阿尔德·法弗尔都在这个城市学习,他们一部分在神学院,另一部分在法学院。因此我只有18岁半,我父母宁愿选择国外的某个城市,在整个城市里会有一些同胞陪伴在我身边。——费·德 索绪尔注。,除了我自学的梵语和几种古典语言[ ]外,我总之没有关于日耳曼语族中的任何一种,甚至哥特语,乃至整个印欧语系中任何一种语言的认识。
(p.11) 6
浏览大学的教学大纲时,我另外注意到一条休布斯曼先生③根里克斯·休布斯曼 (Hübschmann G.,1848-1908)——德国语言学家,研究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和其他东方语言,是著名的《波斯语研究》(“Persische Studien”.斯特拉斯堡,1895)的作者。——Н.А.斯柳萨列娃注。的公告,他准备开设(完全业余的)altpersich课程(古波斯语)。我前去离奥古斯都斯普拉特茨不远的他的家中找他,目的是向他自我介绍。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德国教授,他非常友善地接待了我,这立刻让我感到高兴。他几乎马上就跟我谈起印欧语。并且问我勃鲁格曼④卡尔·勃鲁格曼(Brugmann K.,1849-1919)——莱比锡青年语法学派创始人。论文《论印度日耳曼原始语响鼻音》,它的推论几乎与索绪尔的猜测一致,它的出版早于《原始系统》。但是瑞士语言学家在自己结论的基础上对整个元音系统做了更为广泛的概括(见K.勃鲁格曼 《论印度日耳曼原始语响鼻音》[“Nasalis sonans in der indogermanischen Grundsprache”].——载古尔替乌斯主编《希腊拉丁语法研究》[“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Grammatik”]第9期,莱比锡,1876年)。——Н.А.斯柳萨列娃注。假期发表的关于响鼻音的文章。我甚至不知道到底谁是勃鲁格曼,这在那时是可以原谅的,尤其对于我来说,那时休布斯曼先生告诉我,这是已经争论几周的关于希腊语中某些α是不是来自n演变的结果的问题,换言之,某些n能否变成了α。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跟一位德国学者的第一次见面时,作为一项科学成果他展现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三年半时已经认识到的浅显真理,关于它我不敢说,因为认为这篇文章那么有名,我胆怯地向休布斯曼先生指出⑤原文被弄脏。索绪尔留下“我给他”(而不是“我指出”)。——R.戈德尔注。,这个发现我感觉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或者新的东西。当时休布斯曼强调日耳曼学者认为这个问题多么重要,并向我解释日耳曼语——关于日耳曼语我没有任何观念——中组合-un-对应于希腊语中的α。走出他家后我买了一份登载《新发现》的《研究》,但⑥最初被删去的文字是:“此时我意外地理解了,到最后我的思想一点也不差于那些像读者赞赏地接受的那些思想,甚至在没有任何印欧语基本知识情况下,我也不害怕从分析的观点,根据每种语言所掌握的程度来研究它们。”——R.戈德尔注。与期待相反,我读完它并没有使我很激动。这一刻我不能准确地比较[]。
7
按说在莱比锡大学我应该勤恳地学习,来学会所有那些在具体知识领域我缺乏的东西。但与此相反,我的这些知识枯竭了。说实在的,我只是去听了雷思琴的斯拉夫语和立陶宛语课,休布斯曼古波斯语课和部分的维金斯所讲的凯尔特语课⑦索绪尔所作的凯尔特语课笔记还保留着。——R.戈德尔注。。除了两次导论课外,我一次也没有去上过奥斯特霍夫①赫尔曼·奥斯特霍夫(Osthoff H.,1847-1909)——青年语法学派创始人。著名的印欧语言学家,与К.勃鲁格曼一起出版《形态学研究》(出版了6卷;《形态学研究》[“Моrphologische Untersuchungen”],莱比锡,1878-1910)。 ——Н.А.斯柳萨列娃注。讲的梵语课;我完全没有去上过哥特语或任何一种日耳曼语的语法课,但我上过布劳恩②比尔盖姆·布劳恩(Braune W.,1850-1926)——德国著名的印欧语言学家和德语史、哥特语史方面的专家。——Н.А.斯柳萨列娃注。一些德语史课。
至于比较语法方面的课,那个我[]。
1.我定期去上古尔替乌斯的课,记得在他的讨论课上还做过两次Vorträge(报告),我是讨论课的成员,而不只是去参加(一次Vortrag是关于词尾,比如τóκα—τóτε,另一次Vortrag是关于没有被其他人注意到的日耳曼语词根元音交替:λθετν:λ —λθα和δμν-μι:δμν-μει)。
2.我上了奥斯特霍夫所讲授的其中一门课程的最初几节(1876?),但不记得是哪门课了。此后很快奥斯特霍夫就离开了莱比锡。
3.1887年听完勃鲁格曼最初的课后,由于下文③这里应该放入下文中(p.17)给出的6а 7а条。——R.戈德尔注。所指出的原因,我中断了学习④最初被删去的文字是:“在准备自己的 《论元音的原始系统》时,我确定把我准备发表的内容分作几个条目。”——R.戈德尔注。。
8
(p.14)如果说我相当少,甚至极少地去大学教室上课,后来我不止一次对此感到遗憾,那么,我也在很小程度上与喝啤酒或不喝啤酒的圈子有联系,这个圈子的成员经常聚集在莱比锡语言学派年轻的学术领袖周围。我对此也感到遗憾,但这是那么自然,要知道我是一名外国人,法语是我的母语,而且那时我刚刚19岁,同时我很难融入博士社团中;最终,我是那么依恋我们来自日内瓦的大学生在莱比锡市组建的小团体,以至于我应该承认,[ ]。
不过,我有个很大的优势:在莱比锡市我与大学生杰欧多尔·巴乌那科⑤焦·巴乌那科发表了与其兄长尤干涅斯合著的学术著作,其标题为《Gortyn的题铭》(《Die Inschrift von Gortyn》),莱比锡,1885(156页,在书的最后有一张附页),索绪尔收到的一册题有赠阅签名。——R.戈德尔注。和鲁道夫·焦格尔⑥弟子查尔恩克和布劳恩·鲁·焦格尔寄给索绪尔两本自己的著作《Kero的难词汇编,古高地德语研究》(“Ueber das keronische Glossar,Studien zur ahd.Grammatik”),哈勒,1879(192 p.);《对鼻音领音的不同观点》(“Gegen Nasalis sonans,Gram,Studien(Festschrift Eckstеin)”),哈勒,1881(26 p.in-4)。 ——R.戈德尔注。⑦弗里德里希·查尔恩克 (Zarnke F.1825-1891)——德国德语史方面的专家。 ——Н.А.斯柳萨列娃注。有过短暂的相识,那时他们的天才已经预言今天他们所拥有的卓越成就。此外,我首先认识了勃鲁格曼先生。我刚打算谈谈他和蔼可亲的性格,突然意识到我写作这篇文章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证明我没有抄袭勃鲁格曼先生的任何东西。当然,他会为此原谅我,因为他知道所有一切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儿[]。
虽然我视与勃鲁格曼先生的友好关系高于一切,但我们关系不是那种类型的,在这里对其不谈论。
因此,我把我们的这种关系放到一边,而来谈谈我们的学术交往。我们的交往关系在以下三个方面是很有特点,每当回忆起这些情况都非常清晰。
1.1877年,当我在古尔替乌斯讨论课上做上面提及的关于ā和ǎ有规律交替的报告时,勃鲁格曼没有出席这次讨论,但第二天在学校第二庭院(大庭院)他遇到我时,走到我跟前,以友好的语气问我,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接下来是勃鲁格曼的原话):“Ob noch weitere Beispielt als stātor:stǎtus und māter: pǎter⑧大概我还给了第三个例子,但想不起它来了。——费·德·索绪尔注。wirklich für diesen Ablaut vorliegen?”(“除了stātor‘救星’:stǎtus‘状态;身份’和māter‘母亲’:pǎer‘父亲’以外,现实中还有没有这种词根元音替换的其他例子?)如果今天说勃鲁格曼先生怎样问除了被引用过的三个例子外,还有没有ā:ǎ词根元音替换的其他例子,人们会责备讲述者荒谬绝伦的杜撰。但这只能证明,当代人到多大程度上既不能评判1887年对问题的研究状态,也不能评判某个研究者的具体贡献。比如,最简单的是打开古斯塔夫·梅耶尔的《语法》⑨G.梅耶尔 (Меуеr G.)《希腊语语法》(“Griechische Grammatik”),莱比锡,1880年。,他是第一个忽视我的研究,同时又摘录了词根元音交替ǎ:ā:ō;ǎ:ē:ō;ǎ:ō:ō,鉴于事实的充分明显性可以想象,谁也不会去探索而自寻烦恼;因此,我再重复一遍,很有特点的是,在1877年勃鲁格曼先生自己不能准确知道,是不是能挑选出很多他原则上感觉是新的唯一的ɑ:ɑ①俄文本如此;疑有误。从上文来看,此处应该是ā:ǎ。——聂注。词根元音交替片段的例子 (所有论及о的一切都是毫无争议的,并取自我的备忘录)。
(p.17) 6а 7а(上述插入)
在我的《论元音的原始系统》中找不到那个事实的任何痕迹(除了一个注解以外,我以后会说到它),这个事实是响鼻音为我所知早于勃鲁格曼。为什么提出这个莫名其妙、甚至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人的可能的优先权问题?巧合的是,1878年我晚来了几个星期,完全没有因此难过,但当我1878年写作时,是有时间的,我也不能坚决地要求确立优先权,因为我没有立刻这么做。请注意,就是现在我也不需要这个优先权,现在,大概是为了证明,在不为广大读者提供兴趣的纯粹智力方面,我对响鼻音描写是独立的、不依赖任何人的。
我成功地做到了《论元音的原始系统》中大部分,我还记得我是带着某种精神上的痛苦写它的,这种痛苦是那些情况的最好证明,我在那些情况之下做这个工作的。尽管明知我本人不需要勃鲁格曼或者奥斯特霍夫的工作,我还是写了以下一句话:“由于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的工作,我们得知了响辅音n和r”②请比较Mémoirep…6;p.42,n.1.(聂注:徐志民先生指出,这里指的是索绪尔第一篇重要著作 《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Mé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但是我按下列方式解决了问题:
1.有充分的根据拒绝重新审视优先权或原创性这些问题。就算那个没来得及第一个发表自己的成果的人可能更糟,继续这个谈话也可能是不好的强调。
2.没有外来的支持我写这样的作品,它一定会逐条地遭受到毫不客气的批评,这是显而易见而又priori(先验)的。我们不要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好处为自己招致敌意,造成一种印象[ ]。③索绪尔写了然后又删掉了:我们想要在某方面撇开德国学者的功绩。——R.戈德尔注。
让我们把这个响鼻音让给他们吧,不是一半而是整个地让出,因为我的确不能给出任何一个出版日期的证明,而我又诚实地遵循出版日期的原则。
关于这一点我也写到了。我总是把我的备忘录看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除了拉丁语or和r被视为等同以外 (这也是更加坚决地把全部功绩归于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的根据之一),这两部分都同样是原创性的。
(p.18)④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前面有6页空白。——R.戈德尔注。至于我,我相当不高兴的是,类推这一方法论原则不再被视为莱比锡学派的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追求第一名完全和响鼻音的情况一样,是没有益处的,我打算放弃不再关注这点,但是,既然我决定一次写出实质性的真相,我应该承认这个只是非常间接地来自[]的恩赐。
对于作为语言学家的我的发展,应当认为,如同对于许多其他语言学家的发展,这一事实是有意义的:当我知道它的存在以后,我感觉不是类比现象,而是语音现象“令人感到惊奇”。要知道,应该没有任何观察或者思考能力上的暗示地研究语言学,为了从一开始就把这种现象等同于现实中个人的经验对之无能为力的语音规律和类推作用,这种类推作用每个人从童年时期就能完全独立地意识到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德国人的极端固执。
(责任编辑:章永林)
H0-09
A
1008—7974(2015)03—0017—06
2015-02-20
聂志平,黑龙江富锦人,教授;王世臣,山东沂南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