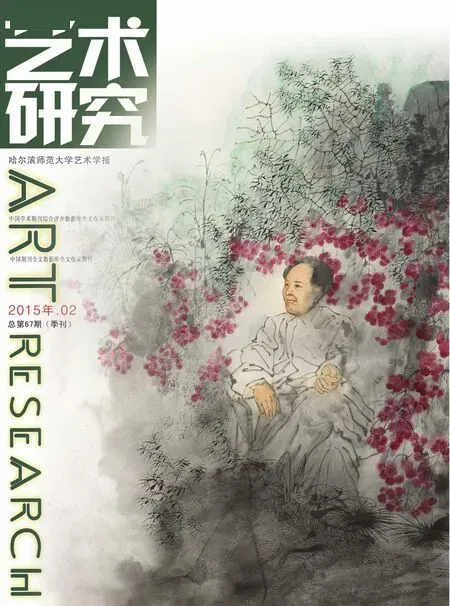在两种真实之间的中西方绘画
毕璐
在两种真实之间的中西方绘画
毕璐
中国传统绘画追求“生命真实”,而西方绘画则遵循“科学真实”,两种真实都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理解。东西方在哲学、文化等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作为生存在自然世界的人来说,对于艺术的追求,应该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并不应该被文化差异、身份政治以及知识要求所束缚。因此,不论是中国传统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是艺术家们深刻体验这个世界之后的精神产物,这中间的差异即使再巨大,与人类对于自然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探求相比,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东西方绘画的差异 科学真实 生命真实
中国传统绘画,是对于生命真实的回应,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感应的产物。相对于西方写实绘画的焦点透视、以及造型与色彩的自然还原程度,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以及相对单一的绘画材料使用,使得中国传统绘画显得非常不“科学”,也不“自然”。其实,这正是中西方对于“真实”的不同视角所产生的差异,即“科学真实”与“生命真实”之间的差异。
理解这两种“真实”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对于中西方各自哲学思考的理解。但这种思考的路径,会将我们带入到一个陈旧的套路中,即对于艺术家及艺术作品背后隐喻的过度阐释。这是今天艺术批评界惯用的思考模式,通过过度阐释作品背后的故事来解释作品,这种解读最后所能表达出来的,仅仅是批评家自说自话的知识表演,与艺术家及其创作的艺术品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通往罗马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条,跳出既定的研究范围,只是单纯尝试通过与之平行的现象来说明问题,如果可以达到目的,同样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在绘画领域,在理解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写实绘画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往往需要比较各自的哲学思考以及文化阐释,这是理论界的拿手好戏,是小范围学术圈子的游戏,同时,更像是一种精英霸权,在学术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巨大的理论障碍。没有接受过任何美学知识教育的普通观众,并不代表他因此就失去判断艺术的权利,其实最深刻的道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而不是所谓权威专家的知识表演。
中国传统绘画所崇尚的“生命真实”,与西方绘画所崇尚的“科学真实”,这中间的差异,其实就如同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一样。同样是治病救人,西医是“显学”,“举实事,去无用”,依靠仪器与数据,治疗时间短,效果明显。而中医是“隐学”,“重和谐,兼表里”,依靠经验,且因人而异,治疗时间长,效果不以短期显现为目的,而注重于长久调理,达到通则无病的效果。两种医学不仅仅是治疗手段与目的的不同,也是对待生命看法的不同,而今天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则是将两种对待“真实”的看法进行融合的产物,“焦点”与“散点”并用,在今天所带来的结果,肯定不止“3D 电影”那么简单。
两种医学的差异,还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对于死亡的态度。西方对于死亡会采取比较直接的面对方式,这是进化论,解剖学等科学知识普及后的结果。在宗教层面,则只有天堂和地狱两种结果,也就是说,只有 A 与 B 之间的单项选择。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无论是道教还是后来的佛教,对于死亡的看法,都有轮回之说,如同太极图所示一般,是循环往复的轮转。表现在绘画方面,西方绘画大多以人的自然视角来观察世界,即使是圣像画题材,也可以直接表现死亡。而中国传统绘画中,对于死亡是有所避讳的,但对于神鬼鸟兽形象,却往往不惜笔墨。其实所谓的神鬼鸟兽,依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过是不同形态下,人的多种存在方式而已,但是在“科学真实”的框架下,这显然是有悖于自然常理的事情。而在“生命真实”中,这一切却因为包罗万象,而显得格外写实。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绘画中,山水相对于其他题材,所占的比重很大。山水是最为直观的自然,是更为接近西方绘画“自然真实”的存在。中国的艺术批评中,多将山水归纳为一种古人精神观想的栖身场所,山水的隐喻功能被放大,其承载的志存高远与宏大叙事,简直就是其全部价值的所在。这是一种合理的解释或推测,但这样合理的解释或推测,同样可以在西方绘画之中的风景题材里,起到同样的作用。比如弗里德里希笔下那些宏大而空灵的风景,相对于黄公望的山水,完全可以套用同样的理论,抒发同样的精神寄托,完成同样伟大的隐喻。
理论是建立在评论者的知识体系与想象的基础之上的,这与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联系。弗里德里希与黄公望之间,直观上的不同,在于绘画材质的不同,相对于弗里德里希模拟自然的油画色彩,黄公望只有黑白的宣纸笔墨,无论如何与自然之间,搭不上任何联系,至少,自然界在光的作用下,所呈现出来的景象,一定是彩色的,而不是黄公望所描绘的只有黑白的世界。另外的不同,是视角。“焦点透视”的方法,使弗里德里希的画面充满令人凝视的欲望,仿佛可以遵循“焦点”,在视觉差的作用下,进入到画面所呈现出来的空间距离里。而黄公望的山水长卷,没有给观众寻找焦点的机会,却并不影响观众领略其磅礴气势的心情与能力。这是中国传统绘画对于追求“生命真实”的价值所在。尽管没用“焦点”来产生视觉距离,却因为精妙的“留白”,以及变换的笔墨,达到了同样引人入胜的效果。正是“生命真实”所激发的人类本能,帮助观众完成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沟通。
“留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其重要性并不逊色于笔墨的作用。“留白”是为了增强想象的空间,这种行为本身就需要极高的人生智慧。中国传统绘画就是黑与白的游戏,在追求“生命真实”的过程中,“留白”可以是空间与距离,亦可以是流动的空气,可以是天空或云彩,也可以是湖面或大海。因为“留白”的出现,成就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意”。“意”与“留白”所追寻的精神世界,近似于西方绘画中的抽象,通过极简或繁杂的笔触与画面,尝试建立与精神世界的某种联系。如果按照艺术批评家的思路,当我们面对于蒙德里安的几何抽象绘画,画面中冷静的分割线与艳丽的颜色块之间,是否揭示了生命的节奏与韵律。而八大山人那些寥寥几笔的花鸟绘画,又何尝不是对于纷繁浮生的深沉思考。
当我们面对罗斯科那些尺幅巨大的色域绘画,微妙的颜色变化淹没在巨大的颜色之间,肯定无法被观众在第一时间观察与注意到。但随着凝视的时间加强,画面中微妙的变化开始逐渐展现,如同诉说故事的人,需要时间的递进来展开线索一般,等到达故事高潮的时候,观众自然会觉得,之前所花的时间并没有白白浪费。所以,在罗斯科的画面中,“满”是为了获得“空”或“悟”,最后得到“意”的体验。这是西方绘画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留白”的一种呼应,用与之相反的手段,最后达到相同的精神追寻。相对于西方绘画中更为物质化的“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吴镇的“空”则在追寻“意”的过程中,平添了“禅”的味道。吴镇对于“留白”的使用,完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而“留白”在他画面中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大面积的“留白”与寥寥几笔的“渔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成就了吴镇独特构图的精神内涵。关于吴镇绘画的种种隐喻,如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是艺术批评家的种种想象而已,这种脱离艺术家创作本源的想象,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吴镇独特构图所呈现出来的直观感受,即“留白”与“笔墨”之间的互补与共生,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空间距离。这种凭借“留白”所产生的空间距离,要远远大过凭借“焦点”所产生的空间距离。“焦点”所产生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遵循“物理”的原理,并没有摆脱“科学真实”的框架。而“留白”所产生的空间距离,却因为“焦点”的消失或不可确定,而促使观者放弃利用视觉差来制造距离,而改为利用“感受”来还原作者所创造的空间距离,而这恰恰是“生命真实”所要达到的效果。不同的“真实”,不同的“满”与“空”,如同一场有关“显”与“隐”的游戏,而这场游戏的结果,却是“隐”与“显”的悄然互换,如同日与夜的交替,才是生命与自然最为日常的景象。
如同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月亮会落下一样,世界就像太极图所显示的那样,在黑夜与白天的交替中循环往复。西方绘画的“自然真实”,从古典写实绘画发展到抽象绘画,一直到今天多样的当代绘画形态,原有的对于自然的真实再现,变成了理性的抽象,再到纷繁复杂的表现,从发展路径上来看,是一个从“自然真实”到“生命真实”的环形回路,只不过这个环形回路所遵循的中心,依然是以“科学”为基点。而反观中国绘画的发展,从传统中国绘画的“生命真实”,到现实写实主义的绘画方式,再到多种形态的当代绘画形式,同样完成了一个从“生命真实”到“自然真实”的环形回路。不论这两种路径的发展方向有什么不同,但最后所要抵达的目的地,却是一样的。那就是深刻体验这个世界之后的精神表达。
金农的“茫茫宇宙,何处投人?”与高更的《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将向何方?》,同样都是关乎人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寻①。面对艺术家真挚的追寻,作为观众的我们,还会纠结于这种追寻到底来自于东方,还是源自西方,到底是出于对“生命真实”的追寻,还是对于“科学真实”的追寻吗?
其实不论是中国传统绘画所追求的“生命真实”,还是西方绘画则遵循得“科学真实”,两种真实都是对于生命与自然的深刻理解。东西方在哲学、文化等等方面,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作为生存在自然世界的人来说,对于艺术的追求,应该是每个人最为基本的权利,并不应该被文化差异、身份政治以及知识要求所束缚。因此,不论是中国传统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是艺术家们深刻体验这个世界之后的精神产物,这中间的差异即使再巨大,与人类对于自然以及自我精神世界的探求相比,都会显得微不足道。
注释:
①参见朱良志著.南画十六观[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