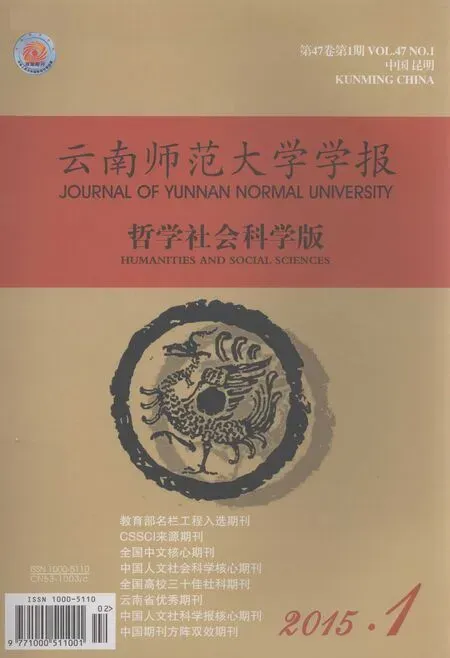文学视域中清末侠义精神的重塑*
蔡爱国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文学视域中清末侠义精神的重塑*
蔡爱国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清末时期,侠义精神体现出更多的时代色彩。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借鉴,试图将侠义精神改造为可资“新民”的道德体系,这一点,得到了同时代的思想先驱如杨度、马叙伦等人的应和,以及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的自由阐发。而体现在文学方面,一是诸多的原创侠义小说强调了侠的为国为民的特征,二是不少翻译小说也为这种侠义精神新质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当然,这些小说在倡导新的侠义精神的同时,也不免掺杂了一些传统因子。
武士道;侠;原创;译作
正如诸多研究者在追溯武侠小说历史时所明确指出的,侠在我国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但也是众所周知的,至少在维新变法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与此前延续上千年的超稳定状态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大变局。那么,在这个变局中,侠义精神呈现出怎样的状态?侠义小说有没有随时代而动?本文将通过对维新变法之后到辛亥革命之前,也就是清末时期的相关理论倡导及小说写作与翻译进行梳理,对上述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
一、新民说与武士道:侠义精神的倡导与国民性的思考
关于清末的社会变迁,曾有人如此描述:“甲午以后,欲雪割地赔款之耻,于时人人言自强;庚子以后,欲弥赔款失劝之憾,于时人人言自立;至于癸卯以来,日俄开衅……国患方迫,于是忧时之士,人人则言自存。”①佚名.自存篇[J].东方杂志,1905,(5).虽始终有仁人志士做着号召和变革的努力,但缺乏响应,没有根基,当历史进入20世纪之时,偌大中国,内忧外患,终究不免要走到救亡图存的关口。
实际上,此时已经有人就这一困局试探着提出解决方案。麦孟华在1900年就曾经指出:“我国民素无国家之思想,素自放弃其责任,故国至衰落,而民至困穷。今事变日逼,火及眉睫,我国民既知祸福皆由自取,利害皆所身受,其责任为我之责任矣。又知上无可恃,外无相助,其责任既非他人之所能代矣,其身既为国民中之一人,其力即当任国民中之一事,智运其谋,勇奋其力。”②伤心人.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J].清议报,1900,53.这段话出自一篇名为《论今日中国存亡其责专在于国民》的文章,从其题目来看,观点可谓极其鲜明。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清议报》的主持人,麦孟华对“国民”的强调意味着维新派对自身失败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未来路径的积极探索。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梁启勋在《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关于“国民性”的定义:“确然有所谓公共之心理特性者存,取族中各人之心理特性而总合之,即所谓国民性也,即一民族之平均模型也。”③梁启勋.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J].新民丛报,1903,25.从对现实问题的深刻体认,到充分的理论准备,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得以呈现,接下来,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就可以从总而论之的层面延展到盘点与实践的层面了。
梁启超《新民说》问世于1902年,略早于梁启勋的《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新民说》凡二十节,以现实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就公德、私德、自由、自治、权利、义务、尚武等若干主题进行讨论,一一划出国民性改造的着力点,按图索骥,可见当时的思想先驱对国民性的全面认识,也可预知他们即将努力的方向。《新民说》可谓清末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此基础上,梁启超1903年又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提出中国国民品格的四大缺陷: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阙。①中国之新民.论中国国民之品格[J].新民丛报,1903,27.与《新民说》相比,这是一个简化版。于实践而言,很多时候,简化版更有意义。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之武士道》。这本著作当然不是武侠小说,其实质是一部选本、一部教材,主要是对《新民说》第十七节“论尚武”思想的生动阐释和具体展开,同时又涉及《新民说》的其他方方面面。它对于尚武、侠义精神的阐释有着比较丰富的层次。需要指出的是,“武士道”这一名词尽管是舶来品,但该书中所推出的“中国之武士道”,实际上完全隶属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
《中国之武士道》的三篇重要序言,全面展现了梁启超等人对“武士道”的理解和设计。蒋智由的序言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援引“文明其精神,不可不野蛮其体魄”来强调尚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通过“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的断言来提炼侠义精神之于国家、民族的核心价值。②蒋智由.中国之武士道·蒋序[A].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76~1378.杨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强调了武士道的普世价值:“以云武士道,则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凡日本之人,盖无不宗斯道者。此其道与西洋各国所谓人道Humanity者本无以异。”进而,他又以日本武士道精神中儒佛二教的互为表里为参照系,指出中国名为儒教之国,实质以杨朱为尊,从而导致“吾国国民本欲各营其私利,而不顾公利,而其结果则以不顾公利之故,至私利亦不可得”。从以上论述,就不难明白杨度对武士道的评价:“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③杨度.中国之武士道·杨叙[A].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78~1383.在《自叙》中,梁启超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信仰的具体内容,并一一进行了罗列,如“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等十数条。并总结说:“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他还通过回顾武士道的历史,总结指出“三千年前最武之民族,而奄奄极于今日”的原因,期盼该书能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④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A].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383~1386.
从这三篇序言可知,梁启超等人所钟情的侠义精神的主要方面及其缘起。贯穿三篇序言的,是诸人对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前途的焦虑。尽管当时知识界存在“有公理无强权”和“有强权无公理”的争论,但就是时的中国命运而言,人们选择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该主义的承诺是如何美丽诱人,而是它确实能够解释国人面对来自丛林社会列强威胁时的诸多困惑。作为偏向于公理一面的代表者,严复在《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与信奉强权者划清了界限。但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论辩对手的立场和观点予以了回护。他说:“故有强权无公理之说虽大谬,而其中有至信者存焉。盖于此可见有文德者必有武备,无强权而独恃公理者,其物亦不足存也。故国不诘戎,民不尚武,虽风俗温良,终归侮夺。”⑤严几道.有强权无公理此说信欤[J].广益丛报,1906,103.所谓武士道,抑或侠义精神,在国族层面,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以强权对抗强权,从而获得存在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当时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诸多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尽管遭到诸多诟病,但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当然,梁启超等人所提出的武士道精神,同时包含着对国民性的思考和重新设定。何以是国民性?在《新民说》的开篇,梁启超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⑥梁启超.新民说[A].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5.由此可见,国族的存亡和国民性的改造,实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在梁启超之前,传教士明恩傅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明恩傅对中国人素质的观察显现了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而梁启超等人的总结则包含着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他在《新民说》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中指出的国人国民性的若干不足,都与救亡图存的主题密切相关,他通过《中国之武士道》对侠义精神“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等内涵的强调,显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实质上是对国民精神的重塑。故而,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是其“新民说”的一个合理延伸。《中国之武士道》对于侠义精神推陈出新式的阐发,其实质是开出了一剂新民的药方。
二、时代的和弦:侠义精神的推崇与重新阐释知识分子的共识
梁启超的观点自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一关于武士道精神的阐释既非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在清末,不少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侠的推崇和重新阐释。
章炳麟在1897年发表的《儒侠》中说:“夫儒有其下,侠有其上,言儒者操上,而言侠者操下,是以累寿不相遇。”①章炳麟.儒侠[A].实学报·实学报馆通论(卷一)[M].1897:218.这就已经突破人们历来关于“侠以武犯禁”的顽固认识,非常明白地要为“侠”正名了。章曾著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康、梁等人存在一些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侠”的一致认同。章有诗句“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布看”(《时危》),写于1913年,颇有力挽狂澜、以侠客自命的意思,这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己任的精神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中国之武士道”相当接近,“这些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更不可置疑地证明了:在他们这些具有公义精神的领导者的引领下,中国人是能够被触动,从而做出最英勇的举动的。”②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New York,Chicago,Toronto:Fleming H.Revell Company,1894:114.由此也可见,梁启超等人在当时对侠义精神的提倡,因实践层面的大力呼应,拥有了可扎根的土壤。
《知新报》第九十九册又刊载《尊任侠》一文。该文说:“今中国俄德捽其首,英日扼其腹,法人拊腰而掣足,溺深渊焉,坠大阱矣。欲救之起之,佩玉鸣裾,不利走趋,非其任矣。我仪图之,非任侠吾奚依?主侠为上,相侠次之,士大夫侠为下,至匹夫之侠则不得已。”作者看到了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困境,所以提出以侠救国的主张。文章又指出:“居今之日,由今之道,不得不深有望于任侠之匹夫。”并指出任侠乃救我“四万万同溺”的“起死之药、返魂之方”。③佚名.尊任侠[J].知新报,第九十九册,1899-09-15.这篇文章的意思非常明确:当此国难之时,指望别国来主持正义是不可能的,指望官僚阶层来实现自救也是不现实的,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国民能发扬任侠的精神,承担对国家、对民族的应有责任。
马叙伦的《原侠》刊载于《新世界学报》第六期,是一篇论证比较严谨、表意极为清晰的文字。这篇文章首先翻译了日本田中智学子所写的《江户侠之恢复论》一文,田中的文字大力褒扬侠义,称之为“吾国第一美风善俗”。④马叙伦.原侠[J].新世界学报,1902,(6).在此基础上,马叙伦考证了侠的“四原”,分别为:地势、政治、教育、风俗,这一考证旨在说明侠是我国的传统精神,为国民实践侠义精神提供了理论支持。紧接着,他还指出,侠的派别众多,并列举了以下派别:政治家之侠、法律家之侠、宗教家之侠、教育家之侠、农学家之侠、工学家之侠、商学家之侠、兵学家之侠、刺客家之侠。这一列举,就大大地拓展了侠的出身领域,显现出对那些拥有各种具体职业身份的国民积极投身救亡事业的殷切希望。
以上种种,仅为当时诸多提倡侠的文字中的代表者,其中不少观点,可见与梁启超思想的近似,显现出知识分子思想的时代共性。
与以上流连于在精神层面探讨侠的举动相比,《侠会章程》则显得急切得多,它显现的是将侠组织化的冲动。《侠会章程》一文从《知新报》,1897年第38册开始连载,到第41册载完,作者沈学。《侠会章程》开篇即讲:“侠者,天下之至友也。其心至诚至公,以天下为己任,同天下为肥瘠者也。子等甫离学塾,观摩世风,有不可言者,辄伤心叹曰:吾华友伦亡焉。安得会侠者而友之?立一侠会,以为天下友表。”这一段文字为“侠”和“侠会”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给予“侠”一个极高的地位,可见作者的期望值。在此基础上,这一章程于如何组织侠会及会中之人如何行事等都给出了很有意思的规定,如侠会设正主会、左主会、右主会等自上而下若干职位,并各有职责的界定。这样一来,《侠会章程》就具有了党会的组织纲领的色彩。《侠会章程》的亮点还在于其提出了很具有现代意味的宗旨。章程中说:“侠会总旨:一人重如一会,一会重如天下。”这一总旨多少带有平等意识,其后文中所称的“此会贫富长幼,一律在会内,依会内称呼,尊称先生,自谦晚生,平称你我他可也”①沈学.侠会章程[J].知新报,第三十八册,1897-11-24.,与此宗旨可谓相辅相成。
然而,《侠会章程》的平等意识是不稳定的,其着力彰显的平等很快在下文中被自己削弱。章程说:“此所以公举外人入会,当慎之再三。其例有五:一,年纪不及二十、已过四十可不举,以年幼稚气未除,年大牢不可破,致少年英俊或老诚练达者另议;二,事业卑贱,或位高禄重不可举,以所志不同,或利欲熏心,致人长气短,或有意富强,虽屠夫织履,王公侯爵,可为侠友;三,残疾不举;四,废人不举,如僧道阉宦之流;五,世籍来历不明,不举,恐有逃犯匪徒混入。”②沈学.侠会章程[J].知新报,第三十九册,1897-12-04.这一表述,就一个组织的成员构成着眼,或许有合理之处。但与前文所突出的“侠”的平等性相对照,则显得思路狭窄,精英色彩过浓。这一论调数年之后又出现在陈景韩笔下《刀余生传》的“杀人谱”中,改头换貌,过激的姿态尤为明显。沈学出生于1873年,陈景韩出生于1878年,发出这种言论时,两人都仅有20来岁,或可以年轻为理由加以开拓。但此时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本含有人人平等之意,何以就有排斥甚至剥夺一部分人的参与权和生存权的意图明目张胆地出现?许纪霖在分析梁启超的国民观时曾指出:“受到欧陆和近代日本思想影响的梁启超所理解的国民,则是一个集合概念,是卢梭式的整体性的人民。而这种整体性的国民,与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是内在想通的,儒家思想中的‘民’,显然也不是拥有权利的个体,而是需要被整体对待、整体代表的集合性概念。”③许纪霖.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A].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14.这是梁启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一个缺陷,是同时代诸多思想者认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于清末时期重塑的侠义精神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薄弱点。
三、活跃的原创:侠义精神为大众接受的新路径
基于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观及随之兴起的小说期刊兴办热潮,清末报章小说大量出现,对于“侠”的时代书写也因此搭了顺风车,呈繁荣景象。清末小说对于侠的呈现,以阐释梁启超等人所持的侠义精神观念为主,表现出多种态势,体现出特别的旨趣,而如此种种,均由原创小说与翻译小说渐次呈现。先来谈原创小说的表现。
《仙侠五花剑》的价值在于延续传统和提供一个阅读的参照系。小说讲的是红线女等剑仙重回凡间收徒传功,并引领徒儿行侠仗义的事情。这是一部剑侠小说,此前类似的作品也并不乏见,《七剑十三侠》又是一例,可以说它延续了一种写作传统。它有值得言说的地方,比如小说写到,众剑仙是为行刺奸贼秦桧而下山,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既为侠客,即使已成仙,也不能对人间的疾苦置若罔闻。小说又写到,空空儿下凡后收燕子飞为徒,并授以芙蓉剑,不料燕子飞心术不正,得真传后干净坏事,众剑仙竟奈何其不得,只好请出公孙大娘出山,特地使用克敌秘器,方能为人间除恶。这样的情节设置很有意味,它至少暗示了这么一层意思:功夫的作用,取决于人品;倘使人的道德存在问题,则功夫越高,为恶越甚。这样的认识是有意义的,相信也能够被时人所接受,同时也为道德与智识的分歧提供了一个小说家言式的答案。但小说最终所安排的结局,是众剑仙带领徒儿回仙山去了。从这一结局可以看出,小说虽然也曾摆出介入历史的架势,但众剑仙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介入人间历史的进程,而是要为他们的仙家名誉加一个人间的注解,他们的最终归隐要传递的立场,是出世,而非入世。
陈景韩的“侠客谈”致力于改造世界,体现出入世的情怀。他在当时无疑是“侠”的最有力的推崇者之一,但或许不偏激就难以说明问题,陈的部分观点显现出了极端的色彩。陈景韩所编的《新新小说》杂志重点突出“侠客谈”这一栏目,在对“侠”的宣传方面无疑是不遗余力的。关于这一点,拙文《〈新新小说〉:侠的实验性书写》有较为详细的阐释,此处不赘。这本杂志的最显眼之处,在于陈景韩自撰《刀余生传》中所列出的“杀人谱”。“杀人谱”列出了一系列必杀之人,老弱病残皆在其中,它传递的,是当时的一部分时代精英的激进心态。仔细探究,可以发现这样的心态也并不新鲜。一度被称为武侠小说成熟之作的《水浒传》当中,梁山好汉们杀人不皱眉头的英勇气概很受追捧,而追捧者往往并不思考被杀之人是否已经到了该杀的地步,陈景韩的“杀人谱”是有传统的。上文也提到,这种写法,本身又是此时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知识分子思想的一种文学呈现。西哲有云: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但这句话的意思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得到更多的认同,还需要时日。
相比《仙侠五花剑》和《刀余生传》等作品,清末时期其他致力于书写侠义精神的小说显得不太像我们所熟知的武侠小说,它们往往将侠置于一个更为广泛的语境之中,突出其为国为民的特征,从而使其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新小说》杂志第一期刊载了梁启超所撰写的“传奇”《侠情记传奇》。虽为“传奇”,但在梁启超等人的观念中,实际上也是小说的一种。《侠情记传奇》要素齐全,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种标范。首先,它着力描写的是在“无天日”之处为建立“少年意大利”这一宏大目标而奋斗的一群年轻人的故事。其次,当中出场的两姐弟,与被侧面烘托的加里波的,皆满腔热血,勇于且乐于“为意大利祖国出一口气”。①饮冰室主人.侠情记传奇[J].新小说,第一号1902,(11).再次,它对姐姐马尼他这一女子的书写,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应是突出下面的话:“难道举国中一千多万人,竟无一个男儿?还要靠我女孩儿们争这口气不成?”②饮冰室主人.侠情记传奇[J].新小说,第一号,1902,(11).《侠情记传奇》用文学的形式显现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时代精英对于“侠”的基本认识。与之相似,黄海锋郎在《日本侠尼传》中也曾发出如下的呼唤:“试读日本维新史,便知那班维新豪杰、开国元勋,从前多是读书的、行医的、经商的、无业的,无权无力、困苦流离,所倚赖的,全是一条爱国的热肠,满腔忧时的血泪,人人都抱顶天立地的气概,个个都有成仁取义的精神。”③黄海锋郎.日本侠尼传[J].杭州白话报,1902,(1).从梁启超等人开始,文学作品中的侠获得了脱离武而独立存在的机会,作为一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它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体现在诸多的理想国民身上。作为一种国民精神的侠,在此时高调走进中国文学。
随后的一些小说延续着这一思路,从不同身份、职业的人身上寻找和放大侠义精神的印迹,从而加强对侠的宣传力度。《新小说》杂志“劄记小说”栏目自第八号开始登载啸天庐主所撰写的《啸天庐拾异》,啸天庐主即为马叙伦。《啸天庐拾异》中有《侠胥》、《义盗》、《侠客》等数篇,短小精悍,寓意深长。当中所述之诸侠,其出身各有不同,但都能够为保护他人而努力,为扭转社会不平而付出。谈虎客在《东欧女豪杰》第一回的批言中说:“著者是望人皆为英雄的意思,我辈不可不勉。便不做大的,也要做小的,不做有名的,也要做无名的。”④谈虎客.东欧女豪杰·批注[J].新小说,1902,(1).将这段阐释用于解释这些作品的写作目的,比较贴切。还值得一提的是,《啸天庐拾异》头一篇为《瓯邑寡妇》,讲述庚子年间一寡妇伙同数名“无赖子”在乡间“思乱”,最后被歼的事情。这一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定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传递不同的理念,但这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本文要强调的是作者的一句评论:“瓯俗之武,异日中国之复强,或将有赖与。虽然,彼寡妇者,余爱其勇,余又恶其愚也。”⑤啸天庐主.啸天庐拾异·瓯邑寡妇[J].新小说,第八号1903,(10).显然,《啸天庐拾异》与同时期的诸多文字一样,其着力的就是开启民智,因为在他们看来,国人并不缺武或者勇,真正缺乏的是精神、智力,这种想法在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学写作中是一直贯穿的。
清末的小说在侠义精神的弘扬方面比较突出之处,还在于对女性的侠义精神的渲染。女性在当时是社会的弱者,从弱者的自强写起,自然更有说服力。关于这一点,《女娲石》中是如此表述的:“我国山河秀丽,富于柔美之观,人民思想多以妇女为中心,故社会改革以男子难,而以妇女易。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⑥卧虎浪士.女娲石·叙[A].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190.《女娲石》出版于1904年,题签为“闺秀救国小说”,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时人对于妇女解放的殷切希望,这与《日本侠尼传》呈呼应之势。当然,就清末时期大众的阅读视野而言,传统小说中的女侠并不乏见,传奇、话本姑且不论,《儿女英雄传》的十三妹想来当时的人还记忆犹新,所以本时段初期一部分作品中的女侠形象塑造延续了唐传奇以来的写作传统,觅得了写作资源。《醒狮》杂志第二期(1905年10月)刊载“游侠小说”《母大虫》,作者为侠少年,小说中的女子“家世绿林,然不杀无辜,专为社会除罪恶”,且颇有视死如归的精神,不过“大虫”一词的采用,有趣味,可深究。《女子世界》杂志于第四期(1904年4月)刊载《中国女剑侠红线、聂隐娘传》,第七期续完,同期又载《梁红玉传》,作者皆为松陵女子潘小璜。红线、隐娘等形象传统色彩强烈,折射出精英知识分子无处着力的尴尬,但细细品味,还是能找到女权主义者努力前行的痕迹。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女权主义者到底是何种身份?松陵女子潘小璜系何人?柳亚子是也。在此时,男作家取一女性化的笔名,算得一种时尚,譬如同时期著名的岭南羽衣女士,阿英先生指其为女子,但后世人则考证出其男性的身份。一位男性作家,化名为女性,在为女性而办的专门杂志上,发表促使女性觉醒的文章,这一模式颇有意味。然而,传统终究是稳固而强大的,到1911年赵焕亭《蓝田女侠》出版,沅华修习少林、武当派功夫以报家仇、力助弟兄,遂成一名女侠。这一文本的存在提醒我们,大约对女性来说,救国之事过于渺茫,扶助父兄更为实际一点。
此时“侠情小说”也已经气势渐起。登载于《月月小说》第九号、第十四号的《岳群》就是其中一篇。小说中的岳群乃庚子年间“被乱”之勇将,“诸君但知其为勇士,其为冒险者,其为文人。必不知其为天下之一痴情者也。惟英雄乃能多情,其说果然。”①天民.岳群[J].月月小说,第九号1907,(10).在此认识之下,与之唱对手戏的女子寿奴既美,且有才,当为必然。而自《月月小说》第十一号开始连载的“侠情小说”《柳非烟》,作者署名为“天虚我生”,小说文笔极好,开头即呈现代气息,悬念迭起、引人入胜,随着故事的推进,作者熟练运用误会、延宕等情节建构的方法,把代表“侠”的陆位明设法成全才子施逖生与美人柳非烟的情这么一段故事演绎得扣人心弦,加上功夫、易容、机关等有趣的元素,可读性较强。侠情小说的出现,可以被理解成为当时的作者为了普及“侠”的理念而与大众的喜好深度结合,走上了一条更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路径。从辛亥革命之后的侠情小说之风行来看,这一路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译作的风情:侠义精神新质的阐释和宣传
此时期自国外翻译而来的小说,冠之以“侠”名的,也大多致力于对侠的时代内涵进行阐释和宣传,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它们也传递了不少的阶级意识、民族精神、平等观念,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映射出当时国内思想界的分歧。
此时的部分翻译小说似有共同的立场,即皆愿从奴隶身上找出侠之踪迹。麦孟华有《说奴隶》一文,呼吁道:“若我四万万人,不必服从而可自生活,不必倚赖而可造世界,其毒未成,其根犹浅,湔而拔之,则独立之国民、自主之人权,可以雄耀于天下。”②伤心人.说奴隶[J].清议报,1900,69.这些翻译小说通过奴隶形象的塑造,在宣传国民意识方面功绩甚伟。1905年,包天笑翻译了雨果的小说《布格·雅加尔》,更名为《侠奴血》,突出强调了黑奴知恩图报的好品质。这种品质后来在《侠黑奴》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东方杂志》第三年第一期(1906年2月)开始连载短篇小说《侠黑奴》,该小说署名为:(日)尾崎红叶著,钱唐吴梼译演。小说讲的是西印度哲美加岛上有两个英国殖民者,一刻薄之人名为郗菲里,一善良之人名为爱德华。爱德华因对黑奴有仁义之心,从郗菲里手中救出西查、克拉拉这对黑奴夫妇,并善待之,从而在黑奴的造反运动中得二人救助。小说特别渲染了黑奴夫妇如何面对威胁而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要救护恩人,即使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好品质,这是小说所谓“义侠”的具体所指。但不知一旦认同了这个,又该如何评价小说中领导造反的黑奴海克道?小说中说:“海克道为人猛鸷彪悍、喜动好乱。”又说:“海克道和人交接,任是丝毫小怨,若不报复,必不能安心。报复起来,任是刀枪水火,他也不怕。”③尾崎红叶著,钱唐吴梼译演.侠黑奴[J].东方杂志,1906,(1).这些文字,试图从个人品德方面来对海克道进行否定。但是,海克道的诉求是黑奴的解放,这难道不是侠义精神的最好阐释吗?
与原创小说同步的是,女子的侠义形象,也是此时期翻译小说的表现重点。致力于推动女性觉醒的翻译小说中较好的,是连载于《月月小说》第一号(1906年11月)与第二号(1906年11月)的“侠情小说”《弱女救兄记》,由品三译述。小说主要讲英国年轻女子蕙仙与坏人斗智斗勇以救其兄的故事。《月月小说》主编吴趼人(我佛山人)在小说的结尾处评论道:“以一弱女子……而如是勇敢、如是机警,殊无一丝嚣张操切、自命为女英雄女豪杰之习气,又为近日新小说中所绝少之构撰,谓非改良女社会之善本不可得也。”①我佛山人.评论[J].月月小说,第二号1906,(11).吴趼人极为熟悉新小说之进展,此言当不虚。还值得一提的是《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年8月)开始连载的《侠女奴》,译者署名萍云女士。萍云女士实乃周作人,而《侠女奴》系《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译名。周作人在《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硬生生读出了侠女的意味,为此,他在翻译过程中作了两项重要的改动:一是通过小说题目的改写将读者视线从阿里巴巴转移到女仆曼绮那身上;一是在女仆完成小说中所有的工作之后,将其原先的与阿里巴巴侄儿结婚的结局改为“不知所终”。前一项改动符合《女子世界》杂志的题旨,后一项改动则满足自古以来我国读者对“侠隐”的想象与认同。译者在前言中说:“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②萍云女士.侠女奴[J].女子世界,1904,(8).这一阐述,立意颇高:一弱女子尚可如此,尔等“奴骨天成者”该当如何?可惜的是,“萍云女士”的这类翻译作品较少,否则,以其如此立场,一定能够给此时期的侠义小说带来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贵族青年的行侠仗义也成为此时期翻译小说关注的重点,不过当中暗含了保守和激进两种姿态的分歧。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更名为《侠隐记》,译者君朔(伍光剑)。小说写道达特安及他的三个火枪手好友结为生死知己,历经波折,完成使命,报仇雪恨。这种侠义精神中国人并不陌生,不过,全书重要的故事情节的展开,有一个效忠王室的基础存于其中,这一点跟小说《紫罗兰》的呈现颇为不同。《月月小说》自二十一号(1908年10月)开始连载“奇侠小说”《紫罗兰》,该书为云汀所译,但未能完整刊出。其所写之人物,是一个名为勃林的没落贵族青年,有过人之力和应变之才,本可袭伯爵衔,却沦落至乞丐、刺客,在威尼斯城内几经辗转,在已刊载的内容之最终,卷入了统领与叛党之间的纠纷。其“虽刺客,自许不肯居人下”,③云汀.紫罗兰[J].月月小说,第二十四号1909,(1).心中还留有几分自爱。勃林的形象虽不完美,但其个人品质亦有可圈点之处,特别是他对威尼斯统领说道:“然我与尔,今已同为威尼斯之伟大人物,但各行其志而已。”此言包含着非常深刻的不畏强权的平等意识,当为现代国民思想的重要信条之一。
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是林纾翻译的《大侠红蘩蕗传》和磻溪子、天笑生翻译的《大侠锦帔客传》。《大侠红蘩蕗传》讲述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被推翻后,法国民众四处搜捕贵族并将他们都送上断头台的背景下,英国一男爵化身为大侠红蘩蕗,率领多名贵族青年,设法拯救法国贵族并将其带回英国的故事。小说开头讲红蘩蕗是如何乔装打扮护送贵族出关以避开搜捕之事,极为引人入胜。红蘩蕗聪明而又热血,且倾尽全力帮助弱者,自然先入为主,成为读者心仪的侠客形象。至法国民党代表出场,称一切行为皆为国家利益,并试图诱杀红蘩蕗之时,读者的疑惑就出现了:到底谁代表正义?国家利益与正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林纾在本书序言中指出:“此书贬法而崇英,竟推尊一大侠红蘩蕗,谓能出难人于险,此亦贵族中不平之言。至红蘩蕗之有无其人,姑不具论。然而法人当日,咆哮如狂如痫,人人皆张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真,此复成何国度?以流血为善果,此史家所不经见之事。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俾知好为改革之谈者于事良无益也。”④林纾.大侠红蘩蕗传·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林纾,在序言中表露这样的观点应可以理解。与此立场类同的是《大侠锦帔客传》。该小说连载于《小说时报》第二期(1909年11月)和第三期(1910年1月),原作者为英国的哈葛德。锦帔客是一位勋爵,一诺千金,专好劫富济贫,后介入一政治斗争中,协助弱势一方,从公爵处争得公义,取得最终胜利,升任男爵,并抱得美人归。《大侠锦帔客传》的“大侠”二字,应与《大侠红蘩蕗传》一样,系翻译者所加,体现出国人试图用我传统之思想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努力。这样一来,也就给清末小说所呈现的侠义精神添加了更多的保守内质。
小说翻译中的改写也可能会造成逆向的理解落差与立场分歧。《小说林》第五期(1907年8月)登载了王蕴章所译的《绿林侠谭》,当中塑造了一个名为绿苹的绿林英雄。虽然小说没有指出本文是依据哪一部外国小说而译,但仔细观察,依然可以看出,绿苹其实就是侠盗罗宾汉,小说所写的故事主要来自大仲马所著《侠盗罗宾汉》中“幸福的婚礼”及相关章节。小说在突出其中一条抢亲的主线的同时,删除了诸多其他故事线索。但是,《绿林侠谭》删去了原著关于罗宾汉抢劫的主要对象的设定,这就回避了《侠盗罗宾汉》中原有的关于民族矛盾、关于反抗民族压迫的线索,这样一来,即使他个人经历曾非常痛苦,哪怕也曾经做过几件帮助穷人的好事,将刀枪对准也许同样经受苦难、只不过略有资财的来往客商,实在不能称之为侠。译者用中国传统侠义小说的套路对罗宾汉的故事进行改写之后,小说中的这个绿苹就只能是一个中国式的绿林好汉,而不再是一个英国的傲人的民间英雄了。这部小说题目虽然也用“侠”字,但其定义与梁启超等人的“侠”呈迥异之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结 语
维新变法失败后,部分思想者痛定思痛,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主张。以国民性改造为基础的侠义精神的重塑,既是清末思想史的一个亮点,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丰富的写作资源。从上文所提及的清末时期的小说来看,其关于侠义精神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跟该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潮密切相关。基于小说“新民”的基本认识,不妨认为:此时期小说对“侠”的着力呈现,实际上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唤醒与鼓舞大众的爱国、爱人、爱己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它们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一环。当然,也需要看到,这些小说虽然努力求新求异,传统的力量依然还强大地存在着,那些新式的侠义小说中还多少混杂着旧因子,这或可用尊重读者阅读习惯等理由来解释,但依然值得关注和警醒,并因此对变革的艰难形成更为切实的认识。而这一认识,显然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下复杂的文化语境。
Remodeling of the chivalrous spiri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CAl Ai-guo
(School of Humanities,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chivalrous spirit showed more epochal color.Liang Qichao's Chinese Bushido,by referring to the Japanese Bushido,tried to rebuild the chivalrous spirit into a moral system for the“new people”,which was echoed by the contemporary thinkers like Yang Du, Ma Xulun and other intellectuals.In terms of literature,many original chivalrous fictions highlighted the chivalrymen for their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people.Numerous translated fictions were also in favor of the new quality in such chivalrous spirit.However,some traditional elements still remained in these fictions.
Bushido;chivalry;original creation;translated fiction
I242
A
1000-5110(2015)01-0149-08
[责任编辑: 杨育彬]
蔡爱国,男,江苏盐城人,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的侠义小说与国民性改造的研究”(14YJC751001)阶段性成果;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