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兴起*
——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谈起
肖巍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兴起*
——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谈起
肖巍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大脑性别差异
在当代神经科学领域,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这一研究已经在悄然中催生出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它是一种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和解释神经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生命伦理学理论。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是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当前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试图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和解释当代神经科学对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各种新发现。
在当代神经科学领域,有一个课题一直备受关注,就是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脑的性别差异,例如能力类型、大脑结构和大脑容量的差异,等等。然而,由于社会和政治原因,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人们在解释这些差异时颇为谨慎,虽然不断问世的相关研究成果尚未引起一门新兴的生命伦理学分支——神经伦理学(Neuroethics)的热情关注,却在悄然中催生出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Feminist Neuroethics)。本文试图对这一尚
处在襁褓中的趋向进行描述,以便观察其如何从当代神经生物学、神经伦理学与女性主义的结合中为如今的性别研究带来新的曙光、问题和启示。
一、对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
长期以来,西方哲学一直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属性,而大脑无疑是体现人类理性、意识、潜意识、道德、宗教与艺术等精神创造物的生物载体,这些精神创造物支配着人的所有行为。这样一来,主要以研究大脑为己任的神经科学似乎也可以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理性、创造性、艺术创作和欣赏能力、敬畏和超越能力,以及人类建构的各种知识体系和概念,其中无疑也包括性别与社会性别概念。
不仅如此,神经科学家也一直颇为自信地相信神经科学关乎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德国医学哲学家延斯·克劳森(Jens Clausen)等人在《神经生物伦理学手册》中强调:“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神经科学都关乎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人们也都在期待着它会带来更大的影响。精神疾病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占到12%或者更高的比率。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痴呆症也迅速发展,在80岁以上的人口中有高于30%的人会患上这种疾病。这些都是大脑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神经科学似乎最有希望理解和减少这种疾病的发生率,甚至有可能治愈它。”[1](Pv)而且,近些年来美国和欧盟分别启动了两个神经科学研究项目——“欧洲人脑研究计划”和“美国大脑活动基因图谱”(BAM),它们都旨在阐释大脑如何工作的知识,试图理解大脑和精神疾病的病因,并找到相应的治疗方法。欧洲人脑研究计划强调,神经科学的最终目的是用计算机模拟人脑(computationally simulating the brain),而美国的相关研究则试图探讨大脑活动的知识,阐释单个神经元与全脑功能的规模。
随着神经科学对于大脑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大脑的“性别差异”问题,20世纪末期,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学者狄立波·朱尼亚(Direeb Junyra)便提出男女大脑在能力类型上存在着差异的观点,认为男性在空间处理上要胜过女性。同样,在数学推导测试和领航工作中,男性也要优于女性。而在感知相似物的能力测试中,女性则比男性速度更快。此外,女性还更具有语言天赋,在算术计算和回忆路途标志方面胜过男性。同时,在做一些细致的手工活方面,女性也比男性更快。尽管朱尼亚没有得出男女智商水平不同的结论,但还是相信在解决智力问题时,男女存在着方式上的差异[2]。
还有一些研究者更为关注从大脑组织结构方面研究性别差异,根据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洛伯(Judith Lorber)的考察,这类研究大体上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而这刚好是西方社会性别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社会性别概念已经改变人们对于性别的传统认知。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开始宣称女性性别测量标准的变化,强调被视为男性的特征如今也适合于女性。但是,他们对这种变化并未给予过多的评论,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雄性和雌性激素,即所谓的“性别荷尔蒙”对于男女性别塑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大脑组织结构研究的核心观点是:无论染色体的性别如何,胎儿期的荷尔蒙环境导致男性或者女性生殖器的发育,以及男性或者女性的爱欲取向、认知和兴趣。”[3](P407)2006年,女精神病学家卢安·布里曾丹(Luan Brizendine)的《女性大脑》一书在美国问世。她试图总结关于大脑组织结构“性别差异”研究的成果,并得出男女的一些思考和行为差异缘于他们大脑结构不同的结论,强调女性大脑如同“高速路”,男性大脑却似“乡间路”。无论男孩还是成年男性,都不如女孩和成年女性“能说会道”。女性平均每天要说2万个单词,比男性多出1.3万个,而且女性说话的语速也比男性快。大脑组织结构的差异也使女性更为健谈,而这种差异从胎儿发育时期便开始了。但男性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性意识方面却比女性更为强烈,因为男性大脑中的相关控制区域要比女性大一倍[4]。
近十年以来,神经科学不断宣布的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新发现,促使女性主义学者认真地思考大脑的性别差异问题。2014年,有文献报道说: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20多年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男女的大脑的确存在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大脑的结构和容量方面。研究人员在《神经科学和生物行为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宣称他们查阅了从1990年至2013年发表的126篇论文,对大
量脑成像图片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人类大脑容量与结构方面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男性的大脑容量总体上要比女性大8%到13%。平均来说,男性在多项容量指标方面比女性拥有更高的绝对值,而且大脑结构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几个特定的区域,其中包括大脑的边缘系统和语言系统。此外,两性大脑边缘系统的结构差异也与精神疾病相关,这可以解释不同性别之间在自闭症、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方面的差异。同时,研究人员也注意到,尽管这些差异可能由于受到某些环境或者社会因素的影响,但生理学影响是不容忽视的[5]。
这些对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结论引发出许多伦理学争论,也导致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问世。
二、神经伦理学与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
神经伦理学是伴随神经生物科学发展诞生于21世纪初期的一门生命伦理学新学科,“神经伦理学是对于神经科学及其解释,以及相关的精神科学(包括不同形式的心理学、精神病学、人工智能等)所进行的系统性的和告知性反思,目的在于理解它对于人类自我理解力的含义、风险和应用的前景”[1](Pvi)。“神经伦理学关系到在实验室、临床以及公共领域里与神经科学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6](P618)
根据神经伦理学的先驱者阿迪娜·罗斯基思(Adina Roskies)的看法,神经伦理学应当有两个分支:神经科学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neuroscience)和伦理学的神经科学(the neuroscience of ethics)。前者关乎神经科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例如招募受试者、神经外科行为、在学术期刊和大众传媒领域如何报道神经科学发现等等伦理问题,同时也包括在应用神经科学技术过程中所遇到的伦理问题;而后者则试图利用神经科学来理解伦理学,例如解释道德推理的途径,理解其他古老的哲学问题——知识的本质、自我控制的方式以及自由意志和大脑/精神作用的途径和方式,等等。罗斯基思相信神经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道德本身,包括理性遵循的原则,情感和非情感过程对于道德思考的贡献,甚至能解释我们的道德思考为什么会出错以及错误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女性主义学者杰西卡·米勒(Jessica P.Miller)则认为神经伦理学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是:神经科学对于传统哲学关于伦理行为者的理解提出挑战,神经科学伦理学研究与实践,在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中所遇到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近些年来,神经伦理学在国际生命伦理学领域得到迅猛的发展,成立了专业学会,例如“神经伦理学学会”(The Neuroethics Society),并建立起研究中心,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以及“牛津维尔库姆神经伦理学中心”,还出版了专业期刊《神经伦理学》《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神经科学》等[6](P618)。
然而,在一些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家如美国代顿大学的佩吉·德桑特尔斯(Peggy DesAutels)等人看来,尽管神经科学的新发现导致神经伦理学的问世,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里却很少有人关注神经科学对于大脑性别差异的研究,或者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2002年,由致力于促进大脑研究的美国“达纳基金会”(The Dana Foundation)出版的《神经伦理学:绘制领地的地图》,以及2006年朱迪·艾利斯(Judy Illes)出版的《神经生物学,对于理论、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界说》两本著作都对神经伦理学做出了贡献,但却没有探讨神经科学关于“性别差异”的发现对于社会和神经伦理学的意义问题。而德桑特尔斯则强调,人们必须追问这些新发现对于神经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意味着什么?它们所包含的伦理和政治意义是什么,以及对于女性可能预见的利益或伤害是什么?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些追问才直接促进了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诞生。
伴随着许多神经科学家在大脑解剖学、化学、功能学以及诸如情感、记忆和学习等认知领域的研究进程,也包括他们对于性别差异的记录,女性主义思维逐渐步入神经伦理学领域,而最先关注的问题是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的发现及其解释,因为这一问题对于社会生活、人类性别关系塑造、性别身份等政治伦理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从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学者便把“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并把后者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石。因而,倘若这些大脑“性别差异”的新发现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女性主义学术的理论基石便会面临着挑战,所以女性主义学者必须通过建立自己的神经伦理学来探讨这些新发现,以应对这些挑战。简言
之,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是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研究和解释神经科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的一种生命伦理学理论。罗斯基思所提出的神经伦理学的两个分支同样也适于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这表明,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一方面要以女性主义视角解释神经科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探讨伦理学的神经科学,包括以女性主义视角,基于神经科学的新发现解释人们的道德认知、道德选择和评价等道德活动和伦理选择。
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问世是新近发生的事情。2008年,《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女性的神经伦理学?为什么神经伦理学关乎性别》,这篇文章的编辑朱迪·艾利斯发表编者按,主要解释女性神经伦理学,或许也是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起源。2007年10月,美国生命伦理学与人文学会神经伦理学联合会(ASBH,The Neuroethics Affinity Group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举行第三次会议,总结神经伦理学领域的进步,分析它将对未来产生的重要影响,会议事先要求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些新问题和新观念。三位年轻学者——斯坦福大学生命“医学伦理学中心”的莫莉·C.查尔芬(Molly C.Chalfin)和艾米丽·R.墨菲(Emily R.Murphy),以及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与生命科学中心”的卡崔娜·A.卡尔卡兹(Katrina A.Karkazis)提出神经伦理学的一个新方向——性别差异的神经科学,并其后在《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上发表这组文章,艾利斯把它们比喻为如同“魔术师舞弄燃烧着的火把般地”开启了神经伦理学的新方向[7](PP1-2)。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有国外学者把这组文章明确地视为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问世的标志,但从其把“性别”和“女性主义”思维引入神经伦理学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视它为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诞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三、问题与争论
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是大脑“性别差异”的神经科学发现及其解释,并试图从不同角度针对已有的相关发现提出问题和做出新的解释。
首先,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一些发现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例如德桑特尔斯针对布里曾丹的《女性大脑》一书提出批评,认为它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具有千疮百孔的科学错误,正在误导对于大脑发展过程、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及性别差异性质过程”的解释,而且“令人失望地没有满足最基本的科学准确性和平衡标准”[8](P96)。她也看到,许多神经科学家关于人类大脑的发现主要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这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影像学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所引发的血液动力的改变。但却有神经科学家对这种仅仅基于fMRI平均值数据做出关于人类大脑认知的结论的做法提出质疑。而且,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也不断刷新人类对这些数据的认识,例如哈佛大学关于新数据分析方法的研究就没有显示出大脑情感中心与判断中心相互联系的因果机制。此外,研究者在解释fMRI数据时,也很难把自然与养育区分开来,难以说明女性的脑线如何不同于男性,这些脑线的差异究竟源于自然还是养育,以及如果存在这些差异,它们对于男女的认知方式和潜能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其次,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指出,大脑“性别差异”的发现实际上已经包含“性别本质论”的前提预设。洛伯认为,这种女性性别的测量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些大脑组织结构的研究都是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及荷尔蒙的“性别对抗”模式设计的,这不仅使其研究概念无法立足,也摧毁了大脑组织和性别研究现有的证据网络。“迄今为止,大脑组织研究者所设计的研究一直假设标准的性别是异性恋,同性的欲望和行为被定义为不正常的,进而推衍出非典型胎儿期大脑组织的证据。他们也假定性别取向是稳定的、一生不变的,因而这种对于胎儿期因果关系的探讨是似是而非的。”[3](P407)斯坦福大学的年轻学者也指出,神经伦理学对于性别差异的关注十分重要,因为它涉及对“人的本质”和“性别平等”问题的认识。神经科学关于男女行为和认知差异的解释关系到人的本质以及性别本质的预设,所以,我们必须要追问一系列问题:如何在拥有性别歧视历史的敏感社会中传播这些信息?这些工作对于理解男女性别构成意味着什么?如何把这些研究用于医疗、教育和法律
领域?同样,德桑特尔斯也批评说,任何强调以“本质论”方式主张男女大脑具有固定不变的生物学差异的观点都需要应对来自科学和女性主义的挑战,男女两性都拥有人类的大脑,都是被镶嵌到特有社会结构中的生物,都是以习得的行为方式学会如何组织和形成大脑的。
再次,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为解释大脑“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提供了新的路径。2011年,洛伯在评论科迪莉亚·法因(Cordelia Fine)所著的《性别的幻觉——我们的精神、社会和神经性别歧视如何制造了差异》和丽贝卡·M.乔丹-扬(Rebecca M.Jordan-Young)的《大脑风暴:性别差异科学中的缺陷》时强调,女性主义把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之后,人们普遍接受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和生理学区别是基因和荷尔蒙的结果,而其他区分是社会和文化所致的看法。然而,正如性别与社会性别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那样,洛伯也指出身体、大脑和生活体验、社会环境,骨密度与经期都是互相影响的。如果神经科学家的相关研究一味地追求对于“性别差异”做出生物学解释,而不关心性别与社会性别、历史和文化变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的话,便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法因和乔丹-扬的两本著作也都持有同样的看法,都反对神经科学的这种主张——男女思维和行为不同是由于他们大脑组织结构的不同,以及荷尔蒙对胎儿大脑发展的影响。事实上,法因等人所批评的主张最初是通过把对动物大脑研究的结论推及到人类产生的。1967年,研究者把1959年通过动物研究提出的大脑组织理论应用到人类,并在60年代写入教科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男女行为的模式。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胎儿荷尔蒙影响性别差异的观点一直备受争议,引发许多关于女性数学和科学能力问题的争论。在《大脑风暴》中,乔丹-扬把对同性恋的解释作为关于男女性别起源问题争论的核心,她分析了300项从1967年到2008年发表的相关研究,走访了21名从事大脑组织结构研究的神经科学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越深入大脑组织结构研究中去,就越发现它的不合理,“我最初集中关注方法问题,但逐渐地意识到,这些研究证据显然不能支持它的理论”[3](PP405-406)。她认为,仅仅凭借对胎儿荷尔蒙影响的解释不能得出男女大脑组织结构决定其性别差异的结论。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德国精神病学家海诺·M.达尔伯格(Heino Meyer Dahlberg)则丰富了乔丹-扬的这一结论,强调荷尔蒙、性别指派和养育对于性别身份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3](P406)。
最后,针对一些神经科学家对于大脑“性别差异”发现的解释,女性主义学者也发出警惕“神经性别歧视论”的呼声,强调那种相信孩子出生时便已配备性别差异硬件的研究不仅在研究方法论上是错误的,结果也是否定性的,缺少社会文化的变量,因而具有主张和增加男女性别不平等的风险。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在解释大脑“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时颇为谨慎和冷静,不仅对这些结论、证据和研究方法提出质疑,也把关于性别与社会性别关系的思考置于对这些发现的解释中,强调人的大脑组织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而如今的神经科学研究在前提的预设、证据的提供以及结果的解释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性别刻板印象以及性别本质论的影响。因而,在传播和解释这些相关发现时,不仅要有尊重科学成果的态度,同时也要警惕性别歧视以“神经科学”的新面目出现,避免“神经性别歧视论”。
四、简要结论
至此,可以得出三点简要结论:其一,神经科学关乎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它推动了人类社会对于思维器官——大脑的研究,并以对脑科学、认知科学的新发展造福于人类。同时,神经科学也有利于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和防治,为促进社会的精神健康做出了贡献。这一学科也通过科学手段重新诠释自古希腊时代起便一直争论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和伦理学范畴,例如精神、理性、意识、情感、自我、道德、自由意志和身心关系等等,不仅促进了当代哲学和伦理学的新发展,也为应用伦理学的新学科——生命伦理学、神经伦理学以及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肯定的是,神经科学所开放的无限研究空间和前景将会为人类社会带来一个迄今为止我们所无法描述的新未来。
其二,作为神经科学和伦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
科,神经伦理学也拥有巨大的潜能和研究空间,它不仅可以重新诠释疾病与健康、精神疾病与精神障碍、身体与大脑、意识与行为、自我与人格、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善与恶等重要的医学、哲学和伦理学关系范畴,也可以以脑科学为基础建立生命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的新领域。然而,也正是由于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神经伦理学的内涵、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学科边界都尚处于模糊阶段和争论之中。在国际生命伦理学领域,神经伦理学的研究环境和氛围也正处在迅速地形成和发展之中,它对于神经科学发现的解释和应用也备受瞩目和争议。同时,在与神经科学的交叉发展中,神经伦理学提出的质疑和问题也在不断地引发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内部冲突,例如神经科学的一些“生物决定论”和“性别本质论”的发现和解释受到神经伦理学的批评等等。然而,这一矛盾也构成这两个学科并肩交叉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矛盾,也就失去了各自的学科生长点和生命力。
其三,作为神经伦理学的新分支,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已经问世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一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向尚如晨曦中的朝阳,所关注的重点颇为现实和直接,例如对于神经科学家关于大脑性别差异发现的追问,对于这些发现的解释以及它们对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性别关系影响的伦理分析。然而,神经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学科的内涵、研究方法、学科的边界等问题也是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在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无论怎样,它在神经伦理学中引入的性别分析视角和女性主义批判思维都为神经科学、神经伦理学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谐、社会公正与性别公正方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契机。
神经伦理学和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所提出的问题已经并将继续拓展和丰富神经科学的思维空间。在一些学者看来,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而神经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作为控制人的自我意识、人格与行为重要器官的大脑。然而,神经伦理学尤其是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已经打破这种狭隘的学科认知,把神经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人的大脑也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大脑的构成与后天的生长环境相关,而且这一研究思路也不断地得到科学新发现的证实,例如美国《自然神经科学》杂志新近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对1000多名年龄在3-20岁之间的人们脑部扫描显示,他们的大脑区域受到父母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在大脑的重要区域,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孩子要大于其他孩子。在考察对于语言和执行能力有重要影响的大脑区域时,研究者发现,来自富裕家庭孩子的这一区域的面积更大,智力测试成绩也更优秀。洛杉矶儿童医院的研究员对此解释说:“我们的数据显示,更富裕家庭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这可能导致儿童脑部结构的不同”,同时“富裕家庭的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更多的刺激脑部发育的物质,以及更多在外学习的机会”,这些都可能是导致儿童脑部差异的原因[9]。这一研究结果似乎也在证实本文讨论的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家的相关看法——即便男女的大脑结构如同神经科学家所言是有性别差异的,这些差异也受到后天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家庭背景以及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与性别差异联系起来,那就是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更乐于把教育资源投放在男孩身上,而在各方面轻视对于女孩的投入,会导致男女在教育、就业、参与社会生活甚至智力开发方面的后天差异。而女性主义运动、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的目标是利用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追求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消除或缩小来自由于性别歧视所导致的资源分配、教育、健康、大脑发育等方面的性别差异。
最后,还有必要提及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目前关于大脑的“性别差异”研究尚无法得出确定的科学真理,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总是引来各方的怀疑和争论。因而迄今为止,无论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还是神经生物学关于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新发现都无法最终给出一个把人类的男女生物本性和社会本质截然分开的有力解释,因为人类一出生便具有了社会性。除了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之外,一旦进入到认知和道德判断等精神层面,便再也摆脱不掉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神经生物学对于性别差异的研究以及神经科学家、哲学家与女性主义学者各执一词的争论没有意义,或许正如神经科学
家所言,这些研究对于促进两性的精神健康和预防精神疾病具有积极的意义。或许对于神经科学家、神经伦理学家以及女性主义神经伦理学家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应以一种超越性别本质论和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大脑性别差异研究的种种新发现,其道理十分简单,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性别与社会性别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是人的精神世界,人们通常认为是物质性的人之大脑和身体也都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1]Jen Clausen and Neil Levy eds..Handbook of Neuroethics[M].Springer Netherlands,2015.
[2]Direeb Junyra,张社列译.脑的性别差异[J].大学英语,1995,(5).
[3]Judith Lorber.Genderd and Sexed Brain[J].Contemporary Sociology,2011,40(4).
[4]王一.女性大脑如“高速路”,男性大脑似“乡间路”?[N].新华每日电讯,2006-11-29.
[5]刘海英.大脑容量与结构男女有别[N].科技日报,2014-02-18.
[6]Jessica P.Miller,Whose Brain,Which Ethics?[J].Hypatia,2010,25(3).
[7]Molly C.Chalfin etc..Women’s Neuroethics?Why Sex Matters for Neuroethics?[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08,8(1).
[8]Peggy DesAutels.Sex Differences and Neuroethics[J].Philosophy Psychology,2010,23,(1).
[9]《自然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富家子弟智商更高[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337245/20150401html.
责任编辑:含章
XIAO 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feminism;neuroethics;sex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
In contemporary neuroscience,a key concern is about the study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Since the 21st century,the study has been quietly giving rise to a new trend in feminist bioethics-feminist neuroethics,a new bioethical theory,which aims at researching and explaining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 series of social,ethical and legal issues stemm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neuroscientific work.Currently,feminist neuroethics pays strong attention to the topic of sex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Some scholars attempt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a variety of new neuroscientific discoveries concerning sex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B82-06
:A
:1004-2563(2015)05-008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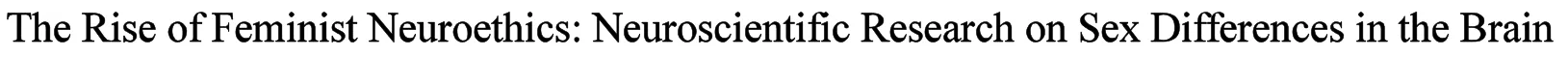
肖巍(1957-),女,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性别哲学。
*资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伦理学思想史的女性主义解读”(项目编号:12AZX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精神健康问题的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2YJAZH16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