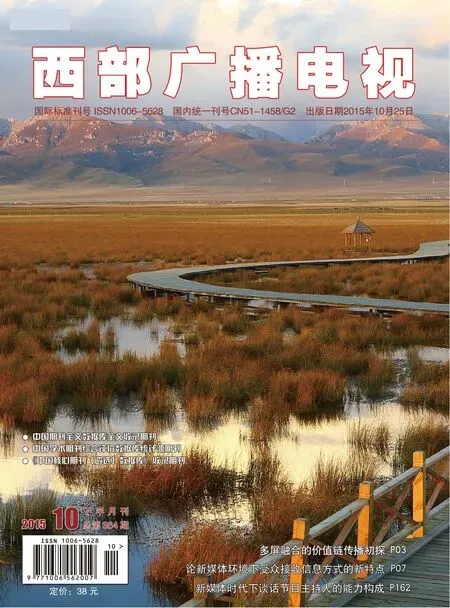动漫中的审美意象及价值传播研究
——以宫崎骏动画为例
杨晓燕 周晓霞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
动漫中的审美意象及价值传播研究
——以宫崎骏动画为例
杨晓燕 周晓霞
(作者单位:三明学院)
美在于意象。宫崎骏动画借意象拉开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距离,为观众创造了美的视觉盛宴和心灵的净化圣地。在对审美距离相关理论理解的基础上,解读宫崎骏动画中的意象有其独特的审美特质,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其审美意象结合了日本的原始信仰和民族审美意识,传达出宫崎骏动画理念及其在动画中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动漫作品是美学的阐释,同时又是传播载体,从美学和传播学这两重视角分析典型动漫作品,寻找动漫作品良好的传播生态环境,进一步探讨其对我国动漫制作及价值传播的启示意义。
审美距离;意象;价值传播;宫崎骏
宫崎骏动画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加入了超现实、魔幻、梦幻的特殊意境,使之成为儿童乃至成人的至爱,尤其是宫崎骏在其动画电影中传达的关乎人类世界的深切情怀,赋予了电影超出一般动画的思想境界。1922年,法国影评家埃利·福尔就曾预言:“终有一天动画片会具有纵深感,造型高超,色彩有层次,有德拉克洛瓦的心灵、鲁本斯的魅力、戈雅的激情、米开朗基罗的活力。一种视觉交响乐,较之最伟大的音乐家创作的有声交响乐更为令人激动。[1]”宫崎骏动画多以青少年经历魔幻世界,在体验到特殊世界的欢乐或痛苦后,借他们的视角来反观现实世界战争、工业文明、利益角逐所带来的诸如环境破坏、人心侵蚀等一系列恶果。如《风之谷》《幽灵公主》《龙猫》等,尽管风格迥异,但宫崎骏无不通过动画艺术感与现实感的完美交融折射出痛定思痛的人文情怀,是对于现实的有力批判——宫崎骏注重动画给予人们精神力量。儿童的成长问题同样受到宫崎骏的高度重视,在一部部反映成长话题的作品中,宫崎骏投入了自己对于儿童独立成长问题的深切关怀,通过塑造千寻与琪琪等动画形象,表达了宫崎骏对儿童在成长道路上的自我发展与培养坚强人格的肯定性期盼。对于影视作品的解读,更多在于审美观念的影响。
1 审美及审美意象
1.1“审美需要”及“审美距离”
“美”遍及世界,在自然与社会中美化着世界也浸润着人们的视觉与心理。正是因为美所具有的愉悦人的视觉与心理的双重功效,“审美”作为人们接触世界的特殊方式,凝聚着人类对美的赞誉与情感的倾注。人类的审美特质在某些方面被视作是与生俱来的,但美也需要发现的眼睛,依靠人们在后天的具体情境和事件中深化而成,“人类的审美行为可以被视为人类天生的、生物遗传的审美素质与一定的社会审美文化经验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2]”审美活动因为人们具有审美需要而成立,审美需要是发自人类内心并在意识上主动接近审美对象的一种内驱力。随着现代社会物质经济的极大丰富,人们对于审美的需求也在进一步提高,审美作为人类自我实现需要的一部分,是一种高级层次的需要,能实现人们心理上、情感上的愉悦和满足。
动漫作为时下流行产业,越来越呈现出亲民特质,其产品是某种程度上的艺术品,创作者借艺术形式提炼生活,使动漫不仅在意象上具有美的形态,同时在意蕴上也饱含艺术的风情。作为艺术的动漫是一种精神产品,凝聚着艺术家的满怀激情或深深寓意;作为视听产品的动漫同样成为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有效形式。
宫崎骏电影之所以给人留下“美”的感觉,在于动画本身与审美主体保持了适当的距离。“距离产生美”。这已经在众多的实践中获得了切实的证据,例如,丘吉尔一次见到影视明星费雯丽,不自觉地被费雯丽的美所深深震撼,静静地关注着她。旁边的手下建议丘吉尔完全可以进一步注视,但丘吉尔表示美就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欣赏。丘吉尔关于保持距离欣赏美女的想法是他坚持“距离产生美”的有效表达。审美距离除了空间距离,还可以指时间上的距离。那些具有时间遥远性的事物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进而达到独特的美的享受。
然而,英国美学家布洛提出的审美距离是指人的“心理距离”,它存在于人的内部,是人的主观意识所限定的距离。布洛借“雾海航行”的例子对心理距离进行了解释:船在海上航行时,突然被聚拢而来的漫天雾气所遮蔽,看不清前方,出于对航行的安全性以及未知天气的担忧,使人们忧心忡忡,不能开怀。但是,换个角度思考,如若此时有人能抛开所有关于安全与航速的问题,集中精力观看眼前的海雾,那么他将会收获一片人间难有的美景。那漫天雪白的雾气,轻纱似的飘舞打转,流水般轻盈飞舞,远处忽隐忽现的海平面点缀着白雾,胜似雾里看花,尽收美的盛宴。正是抛开一切无关于审美的因素,才能在心理上拉开与美的距离,真正欣赏到美、感受到美。
对于心理距离,朱光潜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朱光潜借一棵古松进行了分析。他提到:木商、植物学家以及画家同时走到一棵古松前,木商脱离不了对这课古松木料价值的评估,沉浸在对古松使用价值的研究上;植物学家则是研究着古松的针状叶与果实样貌等植物学问题;只有画家在内心世界里呈现出了一棵完完整整的,具有苍劲有力的树干和枝繁叶茂的树冠的古松。可以看出,木商和植物学家分别是从植物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性出发看待古松,因此不能称他们是审美的主体;画家则不同,他抛开了关乎古松的实用与性质的种种想法,在外观上把握对象,看到了古松的形体美和旺盛生命力,画家保持了审美距离原则,收获了艺术美感。
宫崎骏动画电影所给予我们的多重美感,得益于宫崎骏对于“审美距离”的拿捏恰到好处。宫崎骏可谓是缔造美感的大师,他能够借用绘画、音乐、文学等有效手段丰富动画电影的内容和形式。现实与魔幻的完美结合保持了“审美距离”的适中性,扩展了动画电影的可观性,让人们在获得观赏愉悦的同时收获内在思想内涵的美感。
1.2审美距离中的意象表达
宫崎骏动画的审美距离包括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在前两者基础上进一步得到的心理距离。然而,为把握好距离的范围,宫崎骏在动画中借意象使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对于吸引观众的视觉注意和满足观众的情感慰藉都收效甚佳。
意象是指文学作品中寓意深远的某种特定的艺术形象,“意”就是意念,“象”就是物象,是指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相结合而形成的某种带有意蕴与情调的东西[3]。《易经·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设立意象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正如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说:“用你的想象套上人间这辆大马车去飞奔。”刘海涛教授进一步表示:“意象也是一种审美刺激。”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主要指作家笔下的语言具象,而动画作品中的意象则是指画家笔下的绘画具象,相对前者,动画意象具有更强的可感性,对于视觉、想象与情感的冲击力更大,容易激起审美主体的情感涟漪。
结合审美距离的需要,宫崎骏在其动画中通过设立意象,同时在时空架构、视觉营造以及场景设置方面拉开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为故事的叙述和情感的表达起到了铺垫作用;观众也在此情况下由审美需要和审美注意的满足渐渐升华到审美情感的实现,达到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保持距离产生的美的享受。
2 审美意象与价值传达的交织
意象在宫崎骏作品中随处可见,如火车、森林、飞行器、少女、水、神、色彩等,这些意象主要分为人文意象、自然意象和艺术意象。意象作为具体的物象充盈或点缀画面,在具体情节中含带不同的情感寓意,宫崎骏动画借意象以立意对他描绘古朴纯美的自然意境、传递日本民族悠远的民族文化与信仰以及表达他对人类社会深切的人文关怀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目前,地外天体采样探测最为直接且最为有效的手段是无人自主钻取采样[1]。我国探月三期工程计划发射一个搭载无人自主钻取采样设备的月面探测器,以获得深度为2 m且保持原有剖面层理信息的月壤样品,并将封装的月壤样品带回地球[2-3]。月面探测器的一侧搭载钻取采样设备,采样设备主要有与探测器一同经历的发射、地月转移、环月、动力下降、月面着陆以及着陆后的钻取采样等6个工作阶段[4-5]。钻具可看作一个细长型的简支梁,且钻取采样设备在飞行工作阶段会产生较大的过载振动,所以钻具极易产生挠曲变形[6]。
2.1时空架构下的“神”意象——历史感的传达
“神”意象在宫崎骏作品中最为常见,大到森林神、海神、河神,小到猪神、青蛙神、萝卜神等。“神”意象,指具有神妙、异常、幻变、飘渺等基本特征的文学意象。宫崎骏正是借用神意象的神秘与魔幻色彩,并且结合日本民族神话传说及神灵信仰塑造了一个个怪异、奇特的神意象,以此拉开了观众与审美对象的距离;但是,又在现实认识与实物借鉴的基础上保持了这个距离,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要。宫崎骏动画中的神意象都形象各异、性格不一,有着掌控特定领域的神力,决定着生物的自由与生死,但大部分神都性格和蔼、与人为善,且居于静谧的环境中,保护着一方水土。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代表着日本原始森林信仰的森林之神。在宫崎骏电影里,森林之神除了《龙猫》中的龙猫,还有《幽灵公主》中的山兽神——鹿神。其中,鹿神的历史文化感颇为深厚。
山兽神是《幽灵公主》中森林的主宰者,它有着鹿的身子和人的脸面,颇显怪异。它集慈爱与威严于一体,经它触碰的植物瞬间被吸取生命而死亡,同时它也是明辨是非的,不仅救助了阿西达卡的生命,最终还以牺牲自己换取了森林的再生,饶恕了杀害自己的罪恶的人类。工业文明与自然和谐的极端冲突成为这部动画电影沉重之所在。宫崎骏采用鹿作为森林之神的原型也是依照日本原始信仰创造出的神意象。日本是一个多山国家,森林覆盖率占全国70%,因此形成了人们对森林的原始崇拜。古人上山狩猎,采食植物果腹。鹿作为古时人们狩猎的动物之一,其数量较大,《日本书纪》就有记载:麋鹿甚多,气如朝雾,足如茂林[4]。在绳纹时代中、后期,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然而到弥生时代,鹿的捕猎就受到了限制,鹿也被奉为“土地的精灵”[5]。随着时代的变迁,鹿渐渐被奉为神灵,具有使人长寿、升仙,给人带来平安和富裕的力量。日本对于“杀鹿祭祀”也是出于对鹿的旺盛生命力和灵力的崇拜,并期盼从鹿身上获得延年益寿的药力。宫崎骏基于日本原始鹿神信仰将其刻画为《幽灵公主》中的森林之神,同时结合自己的想象赋予鹿人面兽身的特征,加大了鹿神的神秘与怪异色彩,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盼和审美需要。
此外,《幽灵公主》描写的是日本室町时代,使影片具有悠远民族特色的韵味。山兽神作为影片的森林之神,被寄予了宫崎骏对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意念。宫崎骏以神灵信仰赋予了动画影片深刻的人文意味,让观众在神秘意境中体味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以及深深的情感寓意。
“神”意象是使宫崎骏动画在众多动画中胜出并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原因之一,神意象所具有的时空遥远性在故事架构上带给观众新鲜感和新奇感。同时,神意象所具有的日本民族特色让观众暂时忘记了现世的烦扰,专情于宫崎骏动画的魔幻世界,体味着这亦真亦假的神奇故事,并随着主人公的神奇之旅领略一番别样的美感。
2.2视觉营造下的“色彩”意象——文化感的营造
对于动画电影来说,色彩的使用对于体现动画的风格、基调乃至思想情感都是至关重要的。色彩作为观众审美的主要对象之一,承载艺术家情感的重要渠道,或清丽或浓重,或素淡或艳丽,或明亮或暗淡,是沟通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心灵感应的重要方式。
“色彩意象”使人们在看到色彩时,除了感觉其物理方面的影响,心里也会立即产生感觉。这种感觉与人们的情绪体验有密切关系,同时也融入了丰富的情感内涵[6]。宫崎骏动画在色彩的应用上同样体现出了日本民族的色彩信仰与观念,展现出了日式美的特色。同时,宫崎骏在色彩的应用上还赋予了其独特的情感,有助于观众在审美过程中深刻体会色彩意象中所涵盖的情感因素,形成审美主体从视觉感受到情感体味的递进式发展,在视觉美的前提下体会人文思想美。
在宫崎骏动画中,红白搭配是常用的色彩,在场景设置和人物着装上都经常使用红白相配,尤其是在少女身上,少女会着红色服装置身于白色背景中形成强烈对比,以凸显主人公形象。另外,在描绘自然色彩时也常结合红白两色,以表现阳光普照下的美丽世界。例如,在《红猪》《千与千寻》中就有大量使用红白色作为场景主色,在《悬崖上的金鱼姬》《龙猫》《千与千寻》《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作品中少女着装都是以红为主。这些红白相配的颜色不仅在场景设置上形成了温暖的色调,产生温馨惬意之感,同时对于宫崎骏动画来说还蕴含着日本民族传统的美意识以及特殊的民族色彩信仰。其中,要以《千与千寻》最为典型。
《千与千寻》是红白色彩使用最多的一部电影,在整部电影中红色作为主色调强烈冲击着人的视觉感官,白色也时常交融红色以协调画面的平稳感。在《千与千寻》中红白搭配主要使用在场景的设置中,也就是千寻误入的神魔世界。在千寻和父母刚进入神魔世界时,到处都是红墙白面的房子,红色的商品琳琅满目,白色的油布映衬着红色的油屋,给人以神秘、魔力的感觉。在夜晚降临的那一刻满街通亮的红色灯笼为影片铺上了神秘、诡异的色彩。在日本色彩意识中红色正是象征着魔力与神秘的意味,千寻进入到的“红色世界”正是符合该片的主题——“千与千寻的神隐”,在日本“神隐”指小孩失踪不见,宫崎骏正是借用红色在开头隐喻千寻到临的神魔境界,在场景设置中红白色搭配,让观众在视觉审美的体验下,察觉影片即将上演的神魔故事,宫崎骏也正是以此刺激了观众的视觉感官,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使观众在色彩的冲击下保持高度的审美注意力。接下来,油屋的内景设置也是以红白搭配为主,尤其是千寻红色的衣服与浴池水气缭绕的白色背景的搭配,使画面色彩平稳、协调又稍显温暖。虽然汤婆婆性格怪癖、利益熏心,但是油屋里的其他角色却给了千寻温暖。因此,红色作为暖色系在动画的中场不再是仅仅喻示神秘、魔力,而是作为暖色调搭配白色等冷色烘托场景氛围的融洽以及人物关系的协调。同时,红色作为象征少女的颜色,暗示着千寻进入到油屋工作后性格由软弱到坚强、由依赖到独立的成长过程。另外,红白搭配在自然环境中也被大量使用。在千寻为寻求钱婆婆原谅而乘坐有轨电车在海上行进时,海天的颜色在霞光的映照下红白相接,红色的电车置身其中与其浑然一体,这一高潮环节,喻示着千寻和小白真挚的爱恋以及暗示着千寻即将冲破魔咒到达幸福的曙光。在日本人的色彩观中,“太阳的颜色——赤红自然也就成为日本人心中的首选之色。”日本歌也是“以红来表现一种热烈的感情,形容爱心和恋情。[7]”
宫崎骏动画借“色彩意象”达到了拉开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距离的目的,展现了日本特有的色彩信仰,形成了宫崎骏动画独特的审美风格——从视觉到心灵的双重震撼。
2.3场景设置下的“水”意象——美意识的宣扬
宫崎骏动画在场景设置上以“亦真亦幻”的自然场景设置最为突出,自然场景的设置也是宫崎骏倾注其情感的主要地方。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水环境自然是日本人熟悉又亲切的自然环境。水意象的涵盖范围较广,包括海洋、河流、湖泊等,“水”意象作为宫崎骏动画场景设置的主要对象,结合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水信仰成为了宫崎骏笔下最触动人审美心理的因素;另外,宫崎骏还结合了日本民族“物哀与幽玄”的美意识,为动画水场景的设置增添了不少独特的韵味。
《悬崖上的金鱼姬》是宫崎骏在动画上的一次成功转型,不仅动画的画风有很大改变,就连宫崎骏本身的动画思想也得到了突破。影片中,海洋代表着人类的本源——人与自然、爱与责任,正如影片的歌曲唱到:是否还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你在蔚蓝色的大海里一起畅游/海蜇和海胆,还有鱼儿和螃蟹/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该片所展示的海洋意象让观众看到了人类与海洋和谐共存的重要性;同时,借波妞与宗介真挚的情感向人们进一步展示人类本源的爱与责任。
此外,在宫崎骏多数作品中“水”意象主要表现为湖泊,影片将湖泊与森林或草地相搭配,构成日本民族推崇的“物哀与幽玄”的审美意境,展现了日本民族特色的审美意识。在《哈尔的移动城堡》《幽灵公主》《千与千寻》中,湖泊作为水意象的表现具象在动画中展现了一种寂静美,透过这份寂静展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本源。“物哀”是以“哀”为中心的一种审美情感,与代表着“空寂”与“闲寂”的“幽玄”共同组成日本民族精神源迸发出来的艺术审美情趣。这种美意识支配着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物哀”的“哀”具有表现哀伤、赞颂、爱怜、共鸣、感伤的多种情感要素。而幽玄也主要是一种“以悲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朴素的美,一种寂寥和孤绝的美”,进而达到了“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的超越意识的美的幽玄世界。[8]”
《幽灵公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山兽神所在的森林湖泊,该湖泊处于森林深处,一直以来是人类所不敢触及的天然圣地。对于这样的森林湖泊,与喧嚣外界的对比下,湖泊的静谧深深感染着观众。在影片的结尾,观众还见识到了湖泊所具有的洁净去邪的力量,剧情的行如流水和场景的震撼,再一次让人为湖泊的生命力所触动。影片所传达出的人类一再破坏森林和水土,在即将毁灭自然的情景下却得到了水源的拯救。人类的自私和水的无私,这些深刻的问题在影片中被具化而令人扼腕。宫崎骏借《幽灵公主》中森林湖泊向我们展现了森林水源的静谧之美,同时在对水源的崇敬之情中透露了宫崎骏淡淡的哀伤。
“物哀与幽玄”的场景设置在宫崎骏动画中主要表现为湖泊的深幽与静谧,湖泊的青色搭配植物的青色以及天空的湛蓝,形成了海天一色的“空寂”与“幽玄”的画面感;而画面中流露的孤独与绝美为形成主体审美心理而造势,为在主体心理形成心理距离铺设了基础。随着观众沉浸在空寂的意境美中,那份蕴含在意境中的人文情怀深深地触动了审美主体的心理,在感情的深处触及人类内心最深刻的情怀。宫崎骏动画正是站在人文情怀的高度上用艺术感动着观众。
3 审美中的价值传播
从《风之谷》开始,宫崎骏动画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奇世界,动画中所展现的魔幻世界以及体现的人文情怀为浮躁不安的世界带来了美的精神愉悦,对真正体味到其精神内涵的人来说,宫崎骏动画意味着美的视听享受和精神的放逐与解脱。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之一——将价值观念传达蕴含于美之中。尽管宫崎骏动画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美意识,但宫崎骏寄寓在意象中的深刻人文情怀却跨越了国界。这一做法对我国动漫产业具有很好的导向性。在我国,受历史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限制,动漫产业尽管也有意走本土化路线,却在制作和传播效果上不尽如人意。
3.1动漫是文化传播的可取方式
动漫作为朝阳产业,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可以接受的媒介表达方式,随之产生越来越好的传播效果。2015年获得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第12届动漫金龙奖最佳动画长片金奖的3D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国内口碑极佳,片子中对于中国文化元素的传达不遗余力:从题材到价值传达,从细节到整体风格,从音乐到画面,都带有强烈的中国风格。具体到宫崎骏动画中,首先,作品以奇异的神魔形象营造出超自然的气氛,同时结合日本民族的传统民俗和信仰构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遥远性,迎合了当下人的审美需要。其次,动画作品以美轮美奂的场景和离奇神幻的故事架构编排了具有非常性质的人物、情景与情节,进而抓住了受众的审美注意。最后,动画以其所蕴含的抒情成分,即爱情、亲情、友情乃至对自然的深深依恋引起了受众内心情感的共鸣,达到了捕获观众审美情感的深层次阶段。创作者通过对观众审美的递进式掌控,使人沉浸于动画作品所塑造的时空美感,以及影片所要传达的文化价值和理念中。
3.2将动漫受众细分化
通过对宫崎骏动画意象所体现的审美距离特质,并基于日本民族信仰和传统美意识,分析宫崎骏动画深刻的视觉美与人文美,对现代的破坏性行为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宫崎骏借动画唤起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共鸣,让人类在艺术审美的过程中深刻反思人的生存价值和解读人的生存危机。不是所有的动画都能做到如宫崎骏动画电影一般具有普适性和人文情怀。目前,我国动漫最为人所诟病的在于低幼化,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通过改变人们对动漫态度,才能改变人们对动漫市场和作品的见解。基于此,与其去分割全龄动漫这块蛋糕,不如进行动漫受众细分化的作品策划及制作。同时,对于低幼化市场,处理好低幼与低俗的分界线,对于一些明显违反低幼儿童行为习惯的作品,要尽量避免会引起的负面效应。
3.3动漫传播效果改善的研究:动漫产业传播生态的建构
动漫产业只有被消费市场接受,才能最终实现其产业价值。这个以受众为最终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过程需要诸多传播因素的参与。“动漫产品的价值在于其意义、信息或者文化,即它的内容,它提供更加细分化、差异化的信息,是吸引独特目标受众所需要的、满足他们个性化需要的东西。”作为内容的动漫,人们也同样希望从中获得信息,甚至是价值引导。例如,近来在电视台热播的“讲文明树新风——中国梦·梦系列”公益广告中,那个带有浓郁中国特色、憨态可掬的小女孩“梦娃”,既传达了社会主流价值观,又在形式上让人喜爱至极,生动而有活力。动漫已经不仅仅是青少年认同的传播方式,更是一种社会全员认可的良好的价值引导载体。此外,从大众传播的功能出发,动漫内容可以成为社交中的话题,成为人们寻求认同感的重要平台。动漫产业传播生态的建构,关键在于受众生态的引导与维持。(1)受众消费热情高涨,需要一个完整的动漫产业链。创作-运营-管理-衍生品,每一个环节都影响到受众对动漫的热情度。特别是动漫衍生品市场,既是动漫产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又是动漫品牌深化的重要方式。(2)受众的培育。动漫的传播不同于其他媒介产品,有一个较强的缓冲过程。动漫作品《喜羊羊与灰太狼》就是一个典型。通过众多系列几百集的电视动漫的投放,将这一动漫品牌开发重点放在其衍生品上。动画、漫画、网络游戏、cosplay、动漫衍生品,不同的动漫产品有不同年龄层次的重点受众群,通过不同受众群体的接受心理差异,建立全面的动漫受众生态。
[1]陈奇佳.日本动漫艺术概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63.
[2]潘智彪.审美心理研究[M].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9.
[3]涂建华.神秘意象在小说结构中的作用[J].写作,2002(2).
[4]舍人亲王,太安万侣.日本书纪(卷7)[M].720.
[5]王金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6]铁军.中日色彩的文化解读[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3.
[7]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
[8]邵培仁.文化产业经营管理通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91-92.
2015年福建省新闻理论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5B27)。
杨晓燕,女,讲师。研究方向:传播学。
周晓霞(1992-),女,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