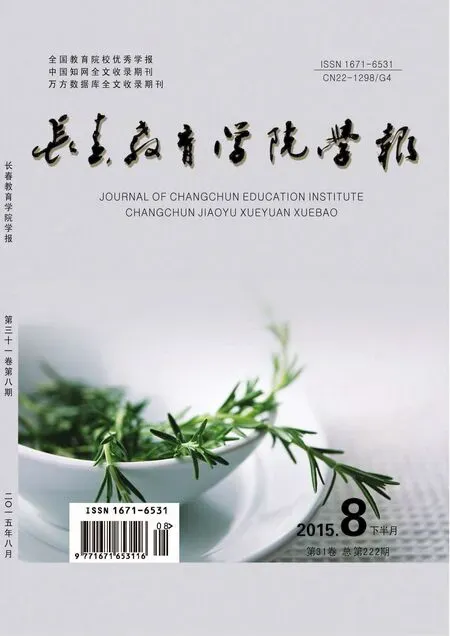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消费与身份认同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艺术消费与身份认同
邹兵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商品的艺术价值呈现泛化的趋势,从而带动艺术进入生产与再生产领域,大众艺术消费社会开始出现。同时,整个社会群体的消费方式的身份认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众的艺术消费把商品市场推向一种文化的维度,促成人们在一种大众文化的语境下获得审美需求。
关键词:艺术生产;大众文化;艺术消费;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一、工业社会环境下的艺术生产
20世纪以来,工业社会愈来愈发达,机械复制技术给人类生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机械复制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复制。此外,社会分工也催生了艺术生产活动成为独立的商品化产业,大规模的复制艺术作品进入商品市场。例如,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文学艺术作品的大规模生产,然后遍及全球各个商品市场;电子音响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可以不限时间、地点的获得音乐艺术的复制品等等。但是,由此带来的大规模艺术品也引发现代人对这种文化现象的焦虑。通过机械复制的大规模艺术生产出来的作品到底是不是艺术品?实质上,具体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背景下被赋予的“质”的内涵。艺术品只是这种被特殊性规定了的“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例如,我们拿到市场上的任意一本文学作品《红楼梦》,从审美心理角度去认可这种机械复制出来的艺术品本身的价值,也不会疑虑和纠结于它的“真”,从而锐减它的艺术价值。就艺术品本身来说,它就是一个现存的价值符号,而符号就是一种形式,人们能够理解形式背后的价值属性,从而实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随着商品化、产业化的艺术消费时代的到来,大量的艺术品都是通过机械复制生产出来的“摹本”。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原始手工制作的“原本”和“摹本”之间存在的真实差异,因此,大量的机械复制的艺术品之间就存在着同一性和可替换性。就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形态的复制性问题,董志强先生认为,工业化时代带来的艺术品复制,艺术品成为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艺术的堕落,而是艺术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如果要在这种工业环境中成功地完成整个社会的艺术生产活动,推进艺术产业的发展和始终保留艺术本身的价值,我们必须尊重艺术品的内在规定性。对于一个艺术品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是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例如,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物——故宫,独特历史内涵决定着它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在任何一座城市建立一座故宫。董志强先生也对建筑物不可随意复制做出明确的论述。他说:“一个被称作艺术作品的建筑物的诞生,总是产生于当下某种独特的现实需要和独特的生命活动方式,这些东西直接就是建筑作品的有机构成因素,而这些因素是无法复制的。”[1]此外,我们在进行艺术品复制生产时,要重视艺术本身所担负的社会教化功能,保持历史留存在艺术作品中的“原真性”。 不能只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而颠覆传统文化艺术,从而失去艺术本身担负的社会教化功能。
二、艺术品成为大众消费品
随着机械复制生产空前繁荣,艺术进入生产与再生产领域,大众艺术消费市场应运而生,个人追求艺术的价值需求与消费行为密不可分了。一方面,在商品化机制下的艺术生产,艺术家作为专门的职业工作者,出于利润的驱使和适应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自觉自愿地创造更多的真正满足社会需要的艺术品。这样一来,市场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艺术品,艺术形式的生活用品进入大众的审美眼光,人们可以观赏到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艺术品,从而形成普遍的审美心理。商品作为一种审美的物质载体,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人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例如,当我们购买一个杯子时,看见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杯子,它们的使用价值相当,而我们定会选择一个外观精美,有着独特的观赏价值的杯子,更多的是强调杯子的审美价值,而忽略它的使用价值。大众文化氛围中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满足日常生活审美的心理。因此,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艺术家把大众的审美需求和使用价值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越来越多的艺术品,然后通过机械复制生产投入市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艺术品作为商品要更大程度地实现本身的价值必然要求它最终面向大众。例如,针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实现,董志强先生在《消解与重构》中说:“艺术作品是具有公共性的,即它要求的读者是公众而不是某一个独特的主体。艺术作为源初的文化教化的规定性,也使艺术作品内在地要求尽可能地面向广大的公众世界。”[2]传统观念认为“唯一存在的才是艺术品”,以及强调形式和内容的纯艺术,比如诗歌、绘画等专门的艺术门类。但这种观念是狭隘的,把艺术仅仅局限在部分场合与空间。它已不能满足大众对艺术品的消费需要,更加无法实现其担负的社会教化功能。然而,“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自己的环境中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3]艺术品要获得现实的活力,必须面向广阔的空间和更多场合。通过机械复制技术的大量传播,才能真正实现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教化功能。因此,艺术品能够成为大众消费品既是大众精神生活消费的需要,也是艺术品自身存在的内在要求。
在审美化的商品市场中,人们要求更可能多地去实现商品价值,但是只有当艺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才能促成个体商品最初的价值得以更好地实现。在这过程中,不仅满足大众消费心理需求上的精神愉悦,而且艺术家的创造性也能得到大众的认可,并且获得回报。“作为消费的艺术,在这个艺术品可以被机械大量复制的时代,艺术生产和消费与物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不少作家甚至公开宣称自己的创作跟物质生产者的劳动没有多大分别”。[4]这并不是艺术家的审美趣味为迎合大众文化开始庸俗化,而是拉近了人们生活和艺术的距离。艺术消费催生了文化工业,让艺术真正市场化、商品化,不再保持原有的神圣性,从而真正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中。
三、大众艺术消费以来身份认同的变化
宋代以前,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商品交换仅仅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这就严重影响艺术向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传播。于是,艺术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当人们一提到“艺术”便会想到典型的“高雅艺术”或者“精英艺术”,这意味着艺术只是作为整个社会范围内少数精英们欣赏的对象。自古以来,人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追求审美心理,但是只有审美客体符合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时,客体的自身价值才能被理解和认可。而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是建立在自己熟悉和了解的对象上,首先要从自我认同出发,实现自我的审美。
艺术消费作为人们的文化身份、社会阶级的象征,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还能慰藉消费者追求美的心灵。自古以来,艺术品似乎自觉地把整个社会大众划分为高级趣味和低级趣味的人。通常高级趣味的人是这个社会财富和地位的代表,低级趣味的人则是大众平民。整个社会把艺术视为身份阶级的象征符号,艺术作为上层阶级品味的工具。所谓的精英艺术是一种偏激的艺术,把艺术偏向于精英群体,阻碍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的进步。米兰·昆德拉把这种现象称“媚俗”,而他在《生命无法承受之轻》中提到“媚俗”的定义:“制造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这个范围的一切。”[5]舒斯特曼对精英主义艺术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哲学美学已经将艺术赶上了一条空洞的精神化的路径上,血色丰满的和被广泛分享的审美愉快被少数人精炼为贫血的和有距离的鉴赏力”。[6]这一批判打破了精英群体独有的审美享受,让大众在艺术审美的领域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时,无论何种年龄、何种阶级出身的人都能进入艺术的世界。这是对社会大众身份认同的倾向,而不是把非艺术家拒之门外。
由于机械复制技术带来的艺术生产空前繁荣,艺术品进入商品市场,面向社会群体而成为大众消费品。尽管它是一种满足大众精神文化需求而形成的文化,但是它足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人们的消费观念从对“物”占有和消耗转向以审美为中心的消费心理,从而对消费品的要求就超越其本身的实用性,追求高层次的精神满足和精神愉悦。由此,在消费社会领域里,艺术消费不仅改变着日常生活,而且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身份观、价值观、世界观,使得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参考文献:
[1][2]董志强.消解与重构[M].人民出版社,2002.
[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4]陈定家.市场经济与艺术消费[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
[5]米兰·昆德拉.生命无法承受之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 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魏明程

李青/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福建福州35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