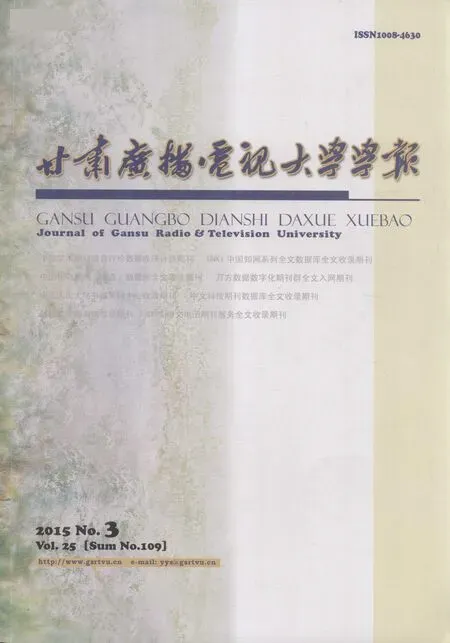爱的异曲同工
——莱辛和沃克作品中的母女关系探微
王欣欣
(大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爱的异曲同工
——莱辛和沃克作品中的母女关系探微
王欣欣
(大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母女关系是女性主义作家作品中的常见主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在其作品《在玫瑰花丛中》中展现了复杂矛盾的一种母女关系;妇女主义者爱丽丝·沃克在其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中则展现了充满信任的一种母女关系。本文以叙述角度和关系内涵等为切入点分析了两位作家对母女关系这一主题的认识。尽管两位作家描写了母女关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但其互相包容、信任和支持的主题是一致的。
母女关系;矛盾;信任;共同发展
一、引言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年)一生著作颇丰,主题多样,但其中对女性生存问题的关注尤为引人注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称她的作品为“女性经验的史诗”。因此,莱辛对“女性主义”标签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性主义思想的拒绝,而是反对将其作品看作单一的性别之战的宣言书。莱辛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关注绝不仅仅局限于对两性关系的描写,作为女性作家,她对女性间关系的描写和女性生存的关注更为细腻和突出。
《在玫瑰花丛中》选自多丽丝·莱辛的短篇故事集《真情》,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女,迈拉和雪莉。其中讲述了母女关系从矛盾重重、激化发展到最后互相妥协的过程。莱辛给读者展示了一种复杂的母女关系,这是一种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表达的关系。尽管在这一关系中充满波折和风暴,但母女二人通过不断尝试,最终达成互相包容和共识。在这部作品中,莱辛超越了对男权中心主义批判的单一立场,把对女性问题的探索引向了女性间关系的对立与妥协。
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1944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第二次妇女运动之后)美国文坛最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其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黑人女性的苦难,歌颂了她们与逆境搏斗的精神和奋发自立的坚强性格。
1983年,沃克在黑人女性主义的重要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前言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妇女主义者”(Womanist)和“妇女主义”(Womanism)的概念,以取代听起来令女性不快的“Feminism”。她的“妇女主义”理论主张建立姐妹情谊和女性联盟,丰富了女性主义的思想内涵。在这部散文集中,沃克着重探讨了女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母女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女性要想真正在男权社会中走出自己的一方天地,就要爱其他女性,重视并欣赏女性文化,包括女性情感的不稳定性(像珍视笑容样珍视眼泪)和女性力量,尤其要重视和热爱女性本身。她主张黑人妇女之间结成亲密的“姐妹情谊”(sisterhood)和“女性联盟”(woman-bonding)。在沃克的作品中,尤其在对母亲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出沃克强调的另一点,即除了爱自己外,还应该热爱自己的生活。
二、莱辛作品中的母女关系:从抵触到认同的平衡
多丽丝·莱辛的作品涉及的主题很宽泛,她更愿意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道出她对人性和对人类的思考。她的思考跨越了种族和时代的局限,将触角伸向更深更广的人心深处。母女关系是莱辛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而在《在玫瑰花丛中》这部短篇小说中,母女关系成为了最重要的主题,母女关系从互相排斥到互相接纳的过程是故事的最大焦点。在这个故事中,男性的角色从某个方面来看似乎是缺失的,他们只不过是完整的女性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只是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的态度,而男性的影响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部作品短小精悍,正是因为篇幅的限制,作者没有过多地讨论关于生命的其他话题,而是集中刻画了母女关系的发展。莱辛心中的母女关系是辩证的,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糟。莱辛笔下的母女二人一定是吵吵闹闹的,不论母亲的性格多么内向,她对女儿的很多事情几乎都是零容忍的。而这种零容忍必然会导致女儿的反抗,反抗引发冲突,无数小冲突必然引起大爆发。但有时爆发反而是契机,故事中的母女在三年冷战后都发现原来彼此在对方的生命中依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两个本来以为截然不同的人其实在本质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一样地固执和执拗。爆发后的和解以女儿去玫瑰花园中偶遇母亲开始,之后两人便重新走到一起。
母亲迈拉在一个公园的玫瑰园中偶遇女儿雪莉,这是二人在三年前一次吵架后的第一次见面。迈拉在这里看到女儿难免心生怀疑,因为在很久以前雪莉已经明确表示出对母亲迈拉爱好园艺的憎恶:“依她的性格,这种花园她一辈子都不会来,而且她还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这根本完全不是她的风格!”[1]118“雪莉不仅讨厌这些花花草草,更讨厌这种花园式的乡村生活。她认为做园艺的人愚钝无趣,但是她来玫瑰园干什么?”[1]120迈拉想来想去,恍然大悟,“原来女儿来此是为了能遇见我,女儿知道我是经常愿意到这里来的”[1]120。迈拉离开花园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女儿远远追随的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她于是确定这是女儿迈出冷战之后求和的第一步。这一步在整个故事中极其重要,是两人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任何母女关系都需要有一个人先低头,有时是女儿,有时是母亲。雪莉对母亲说:“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想你了。”[1]123故事中是女儿先低头,因为做母亲的总感觉自己有做母亲的优越感,并且往往有一种长者的固执。
母女两人在三年时间里互相逃避,原因何在?原来,三年前的一天,母亲迈拉去女儿家撞见了雪莉与一个男人的婚外情,母女二人因此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两人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想法不一致。迈拉是传统温驯的女性,她害怕卷入纷乱的人情往来中,她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自信和自控的母亲,只有在花园中她才能找到主宰和控制的自信,因此她选择在宁静的玫瑰花园中避世。女儿对母亲的想法则不以为然,甚至害怕自己也受到母亲的影响而走到母亲那一步,“这样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1]118。因此在这次吵架中,她丝毫不想妥协,于是冷战就持续了三年。
若说仅仅因为以上事件就能造成母女二人三年互不相见,似乎有些离奇。其实在这次大爆发之前,故事中许多地方都已经体现出了母亲迈拉对女儿雪莉的各种行为非常不满的细节。她认为女儿雪莉缺乏细腻含蓄的女儿情态,总是过于大胆和狂放。她不喜欢女儿穿紧身衣裙,因为在保守的她的眼中,这些裙子“过于暴露曲线,毫不含蓄,毫无美感,却不知为何能一直都吸引男人的目光”[1]117-121。迈拉对雪莉的看法很明显是因为偏见而扭曲偏激的,事实上她对女儿迷人的身体曲线是既羡慕又嫉妒的,因为这些恰恰都是她自身所极度缺乏的。性感的雪莉让她尤其不自在,因为她把对性感的渴望早已深埋心底。但女儿并没有因为母亲的想法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雪莉和迈拉都因为两人巨大的思想和行为差异而陷入无奈与沮丧。两人不愿意坦诚地互相倾诉,反而由于彼此思想的分歧而越走越远,使得矛盾日益激化。处在这种母女关系中,迈出妥协的第一步是很难的。
母女两人都认为对方与自己完全不同,但事实却相反,两人是非常相似的。在女儿迈出了妥协的第一步之后,母亲也有意识地做出了认同的举动。这说明两人都有互相包容、和谐共处的意愿。于是雪莉开始接受母亲的园艺爱好,迈拉也邀请女儿来欣赏她的玫瑰花园。母女本就相似,理应团结一致。此处可以看到希腊神话中德墨忒尔(Demeter)与女儿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故事的影子。在希腊神话中,珀耳塞福涅与她的母亲德墨忒尔往往被同时提及,代表了母女情深。珀耳塞福涅误采了代表冥王的圣花——水仙花,被冥王的战车掠到死亡之国做冥后。失去女儿的丰产农业女神德墨忒尔悲伤难以抑制,她离开奥林匹斯到处疯狂地寻找女儿,于是大地上万物停止生长。主神宙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地荒芜,只好向冥王哈迪斯说情。冥王不愿意失去冥后,因此哄骗珀耳塞福涅吃了四颗冥界的石榴籽。如此一来,珀耳塞福涅虽然得以和母亲团聚,但一年中却有六个月的时间要回到冥界。在母女团聚的六个月里,温柔娴淑、慷慨大方的春天女神珀耳塞福涅把春天带到人间,使万物复苏生长,但在回到冥界的六个月中大地万物枯竭。可以说莱辛故事中的母女分离和重聚也映射出了莱辛所受到的希腊神话的影响。和谐共处的母女关系带来生机与活力,冰冷分裂的母女关系必然带来荒芜与枯竭。
故事最后,母女二人终于打破了坚冰,慢慢学习,互相磨合,重新走到了一起。因此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成长小说,成长的是两位女主人公,女儿学会了如何理解和接近母亲,母亲学会了如何宽容和支持女儿。女儿和母亲都是女性成长的必经阶段,女性只有在真正深刻地体会到这两种身份的意义,并学会与其中另一身份相处后,才能真正走上性格成熟的道路,也才能真正实现女性作为整体的团结和统一。而女性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努力才能解决更深更广的社会问题。莱辛认为母女情中有适意、有爱意、有感激,更有相互认同。莱辛笔下的母女关系既辩证又循环,两人不断争吵又不断和解,以此往复。通过对这一没有主导性男性角色的故事的叙述,莱辛指出女性的未来在于女性自身,在于女性间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道路必然是曲折难行的,只有互相包容、互相妥协,才能坚持走向平衡和自在。
三、沃克心目中的母女关系:磨难中的呵护与传承
与莱辛讲故事的方式不同,沃克对母女关系的刻画主要来自她的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沃克散文式的叙述方式与莱辛小说式的叙述方式不同,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主观色彩,也不存在过多的戏剧冲突。她从一个被保护、被鼓励、被支持的女儿的角度描述了一位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又心怀善意、充满创造艺术灵性的母亲形象。沃克的作品素来以揭露白人社会的歧视和男性劣行而闻名,她的作品也因此被认为是充满偏见的。她对母亲的描述必然也充满了主观色彩,但这也是母女团圆情感的直接表达。沃克认为她的母亲代表了所有受到白人社会和黑人男性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她们尽管承受了生活的种种艰辛,却并没有因此自怨自艾,而是在不同的生活细节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热爱。
沃克将其作为一名作家的成就都归功于她的母亲——米妮·卢·沃克。在她的心目中,母亲坚韧、坚强,是她自信人生的支持来源。在1982年接受玛丽·华盛顿的采访时,她曾明确表示,她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期文学事业的发展都源自她母亲的倾力支持。她母亲所做的一切在无形中表明了她允许并支持女儿写作的态度。“爱丽丝·沃克小时候本应该像其他所有黑人女孩一样在家里做家务,可她母亲却因为发现了读写对爱丽丝·沃克的特殊意义而不让她做家务。在给予了爱丽丝·沃克广阔的创作空间的同时,母亲自行担负起生活的重担——为白人做女佣挣钱养家。这位母亲深深地认识到,把爱丽丝·沃克培养成当时社会上广泛认可的非洲女性形象会折损女儿的文学艺术天赋。正因为母亲的这种给予和理解,使爱丽丝·沃克深受感动。出于对母亲的爱意,尽管母亲不让她做任何家务,她还是能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劳作。当时的打印机和打印桌价值不菲,但做母亲的却不顾自己每周20美金的微薄收入为女儿置办了一套”[2]38。类似这一例例朴实的记录都表达了母亲对女儿的支持。因小至大,由微知著,从一件件生活琐事中,一位鲜活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若读者对沃克的其他作品有所关注,那么便很容易了解到当时的社会及家庭对黑人女性的压迫。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一位母亲却对自己的女儿全然信任,毫无保留地付出全部,这一点正是爱丽丝·沃克反复强调的。
“我母亲毫无保留地完全信任我,她从没怀疑过我与男孩的关系,她相信我有走入社会学习世间万象的能力。”[2]38正因为母亲对爱丽丝·沃克的信任和支持,爱丽丝·沃克才能成为读者眼中诚实、勇敢又自信的作家,一位敢于去写别人只敢想一想的东西的作家。
爱丽丝·沃克的母亲尤善园艺,因此她认为沃克写作的天赋也源于遗传。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这样写道:“无论我们住的房子多简陋,我母亲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来装饰。凭借她对生活的热爱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对贫穷的记忆也都伴随着阵阵花香,记忆中总有各种花,太阳花、矮牵牛花、玫瑰花、大丽花、连翘花、绣线菊花、飞燕草、美女樱……竞相开放。”[3]母亲养育了八个孩子,每个孩子的衣服都由她亲手缝制。她还得在田里劳作,面对种族主义者的歧视,忍受语言和身体上的暴力。尽管如此,她仍在花园中为自己的才艺找到了一展身手之地。经她之手养的花都茂盛美丽,远近闻名。爱丽丝·沃克一直为母亲的创造力而骄傲,也一直坚信自己的文学创作正是黑人女性艺术创造力的传承。
爱丽丝·沃克认为园艺也是艺术的一种表达,她的母亲也如同千千万万充满创造力和对生命的热情的黑人女性一样,正在通过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将这种智慧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因此她将其妇女主义散文集命名为《寻找母亲的花园》。这一传统的传承主题是爱丽丝·沃克在作品中常有的表达。在作家心中,每一位非洲传统女性都具备许多高贵的品质和对传统独特的见解和解读。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这些宝贵的品质和传统不应在时代的洪流中被掩埋,而是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在爱丽丝·沃克眼中,母亲的花园正是黑人女性热爱生命和发扬艺术灵感的具体表现,满园的花朵不仅给疲惫的生活带来了勃勃生机,更让女儿和母亲的心灵更加接近。
爱丽丝·沃克笔下的母亲形象是高大的、任劳任怨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在社会和家庭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没有让这位坚强的女性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女儿的宽容和支持,她就是作家心中的创作动力和灵感源泉。有了如此强大的后盾,作家的创作之路才能越走越稳、越走越远。由此可见,爱丽丝·沃克笔下的母女关系是一种和谐融洽的母女关系。传统母性中的包容不仅给母女感情带来和谐,同时也使得这种母女关系更具传承色彩。
四、结语
上述讨论的两位女性作家尽管生活背景、人生经历、教育背景甚至种族肤色都不尽相同,但二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多丽丝·莱辛直接声称自己不是,而沃克给自己的倾向取了一个新名字“妇女主义”。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都用花园来映射母女关系。尽管在表达手法、叙述角度及处理方式上都各有不同,但二者对母女关系的认识却是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的。
两位作家从不同的叙述角度——莱辛的母亲角度和沃克的女儿角度讲述了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因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对母女关系表达出了自己的认识。爱丽丝·沃克心中的母女关系超越了普通女性之间的关系,她眼中的母亲是艺术的化身、贴心的支柱,更是普爱的象征、传承和延续,而女儿在面对这样的母亲时也必然以一颗拳拳之心反哺这种切切之爱。多丽丝·莱辛更清醒深刻地认识到了母女二人都是独立的主体这一现实,这两个独立主体经过互相牵绊与争执然后达到融合。在莱辛眼中,母女关系不同于简单的女性关系,因为这二者既相同又不同。因不同而排斥,因相同而接纳。虽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二者对母女关系的解读都是一样的,即喜团圆则春暖花开,悲分离则花木凋零。
两部作品中都提到了花园,其象征意义也异曲同工。短篇小说《在玫瑰花丛中》的玫瑰花园是母亲寻求生命庇护之所在,象征着母女关系的改善和母女情感的加深。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的花园也是母亲一腔生活热情之所依,象征着母女的灵感传承和情感相牵。两部作品都将花园作为母亲的代表,由此体现出了既包容又热烈的母性光辉。
两位女性作家生于不同时代,其文章言论却一样精彩。两位作家都不愿意做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都意识到女性的未来其实掌握在女性自己的手中。在女性的自我成长历程中,母女关系的健康发展尤为重要。因为母亲和女儿都是女性个体成长的必经角色,女性处理好了母女关系,便能走出一条更加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和共同成长的道路。
[1]Lessing, Doris. The Real Thing: Stories and Sketches[M].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1992.
[2] Washington, Mary H. An Essay on Alice Walker[J]. Alice Walk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Ed. Henry L. Gates Jr., New York: Amistad, 1993.
[3] Walker, Alice.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M]. San Diego: Harcourt, 1983:240-241.
[责任编辑 龚 勋]
2015-03-11
大庆师范学院科学研究项目“莱辛和沃克的女性主义对比研究”(12RW15)。
王欣欣(1984-),女,黑龙江鸡东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翻译研究。
I041
A
1008-4630(2015)03-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