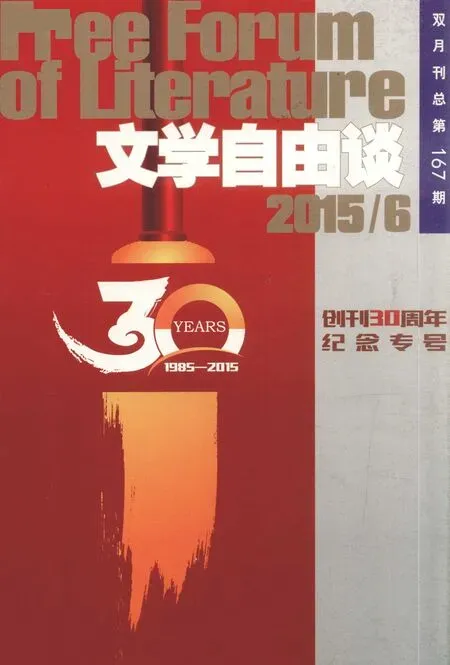更上层楼
李国文
更上层楼
李国文
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请大家现在到六号楼一楼四季厅吃早餐。”一看是25日上午8:00发出的。遂明白了《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年的刊庆活动,终于如期如约地开始了。心向天津,身在北京的我,向这次庆典,献上至诚的祝福。
三十年时光,不算很长,但近两百本刊物,摆在那里,半人多高,就觉得日子实在是不短的了。若想到编辑部每两月要推出一本不让读者失望的刊物,那一分煞费苦心,不由得更加肃然起敬了。冲这半人多高的一百多本刊物,所走过来的三十年,大家欢聚一堂,确实是一件值得祝贺,也应该祝贺的文坛盛事。特别在这个成熟和收获的季节里,很多《文学自由谈》的朋友,来到天津,多少有一点春华秋实,硕果丰收的意味。可以想象,古老饭店,群贤毕至;四季花厅,高朋满座;旧雨新知,谈笑风生;四方来客,相聚甚欢。因为年龄的原因,腿脚不便,未能躬逢其盛,深以为憾。
我早先当过编辑,后来还当过主编,深知办刊物的其中三昧,酸甜苦辣,难以尽对人言。办一本文学刊物,要想三全其美,一是读者的青睐,二是作者的支撑,三是文坛的认可,那是相当不容易的。在林林总总的文学期刊中,享有五十年高龄者,屈指可数,而乘新时期文学潮流,创刊至今,拥有三十年刊龄者,为数不少。无论老牌,还是新秀,要生存,就要竞争,《文学自由谈》能在这场文学期刊的友谊比赛中,脱颖而出,在文学界拥有它的一份不可小视的发言权,自是努力所得。如果说“十年辛苦不寻常”,乘以三,这本始终32开本的不大刊物的不大编辑部,真正出了力,费了劲,下了功夫,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如此,说是也罢,说非也罢,褒贬总会有,好坏两说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所以,《文学自由谈》身量虽小,薄薄一册,发出的声音未必振聋发聩,但其影响不可忽视,无法埋没,能够奠定今天这样说不上大好,但也绝非小好的局面,说明三十年这个不大的编辑部,大家很给力,没白干。
这多年来,我很佩服《文学自由谈》的同仁,能如此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地做事业,能如此情有独钟,昂扬自信地干工作,作为一个办过刊物的过来人,他们这份一不做二不休的精气神,让我深受鼓舞,这也是我这多年来,持续不断为之供稿的动力。我太了解,主持一份文学杂志,说到底,没有衣食父母掏钱订你的刊物,没有上级的资金扶持,那捉襟见肘的艰窘,是很难混得开心的;没有耍笔杆的诸位老兄给你卖力气写作,撑不住场面,总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清汤挂面,淡而无味,恐怕也会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而没有文学界长年读这份刊物所形成的基本认识,觉得可看,值得品味的话,以及读者、作者形成的舆论,口碑,站不稳脚跟,得不到认可,也会越干越没劲,越办越泄气的。所以,创刊三十年,有如此声势,说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成了气候,有了名望,朋友来了,放两个炮仗,敲一通锣鼓,热闹一番,回顾一下,大有必要。
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文学自由谈》创刊伊始,不看好者,也是有的。我也因此有过一次切身体会,那是过了几年以后,由于在这份刊物上发表文章多了,承蒙一家出版社的好意,说老李你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东西,能不能结集,交由我社出版?我说,这当然是再好不过。于是,来了一位编辑,商谈出书事宜。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笔耕,仍保持传统的手工业写作方式,自来水笔加稿纸,一笔一划地爬格子,当时,既没有保留原稿另抄一份投稿的兴趣,也没有收藏发表作品报刊的习惯,这样,只好请这位编辑驾临天津新华路的《文学自由谈》编辑部,在那里一本一本,一篇一篇地找出来复印,拿回来编书。过了一段时间,那位编辑好像难以启齿地对我说,李先生,我们领导的意思,想请你将书名改一改。因为这本书选自《文学自由谈》,所以就以《自由谈文学》来作书名,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不知这位出版社老总何以如此敏感,这也似乎是一些人当初对这份刊物,不抱乐观的原因。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也未必觉得这个书名多么理想,但如此多余的谨慎,我倒不想迁就了。当时,我突然想起一则故事:
战国时期,天下合从拒秦,以楚考烈王为从长,时任令尹的春申君黄歇主其事。
集内政外交于一身的他,位高权重,不可一世。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虽名相国,实楚王也。”有一次,来自赵国的使臣魏加,问起谁会来统帅这支合从国的联军,黄歇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即将委任临武君景阳为主将。显然,这个小道消息,魏加早有所闻,才专门求证于这位权侔楚考烈王的春申君。经此落实,不由心凉半截。他太了解这个空谈兵法绝对在行,动手打仗绝对不在行的临武君了,根本不是强兵悍将的秦军对手。
他记得很清楚,公元前259年,秦军围赵国都城邯郸十七个月,形势危殆。赵平原君驰楚求援,“日出而言之,中午不决”,平原君的舍人毛遂火冒三丈,拔剑出鞘,黄歇这才派临武君领军北上解围。景阳此前与秦交手多次,每战必败,因此心存畏惧。军至钜鹿,遂趑趄不前。幸亏魏信陵君窃得用兵虎符,率精兵八万救赵,大败秦军于邯郸城下,赵国才免于灭亡命运。
魏加为外交官,深谙语言艺术,自然不能直指黄歇用人非当,便转移话题,说起自己早年也曾是喜好弓箭之辈,算得上略通骑射。春申君有点匪夷所思地看着他,怎么一下子扯到引弓挽箭了。魏加一笑,因为您欲起用临武君为将,臣不禁想起一件往事,不知当说不当说?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与楚春申君,史称战国四大公子,都以养士闻名。凡养士者,不管真的假的,都要做出来有容人之量的宽阔胸怀。春申君说:“且讲无妨,黄某洗耳恭听。”
魏加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早年间,有一位叫做更羸的神箭手,与魏王站在高高的台阁之下,仰望天空,只见一群一群的雁阵,或人字形,或一字行,嘹唳飞过。更羸对魏王说:“大王,您信不信,我引弓虚发,箭不脱手,也能打下鸟来?”魏王怀疑不信,直是摇头:“难道你的射击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吗?”稍顷,有雁由东而来,往西飞去。更羸果然挽弓虚发,弓响而箭犹在弦,只见那雁扑腾两下,飕地一声跌落下来。从人捡了来给魏王看,魏王惊叹不已,直是点头:“看来你的射击术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
更羸说:“此孽也(这是一只受伤的雁)。”魏王问他:“何以知之?”更羸回答:“因为它飞得慢而且叫声惨。飞得慢,由于受过伤;叫声惨,由于离群久。创伤未愈,惊心不宁,听到弓弦的响声,吓得往更高处飞。往高飞,要用力气;用大力,创口挣裂;创口破,剧痛难忍,就只会应声坠地了。”说到这里,魏加补充了一句也许是春申君最不爱听的话:“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拒秦之将也。”(《战国策·楚四》)
后来,那本书,因为我的坚持,如果一定要改书名,而且也没有什么足以说服我的理由,我就只好放弃这次出版机会,待之来日了。结果,那位老总还是放行了。《自由谈文学》终于出版,当然与春秋战国那则故事毫无关系。看来,更羸所说的“孽”,应该可分两种状况,一为生理上的暗创,一为心理上的阴影。若是皮肉上的伤痛,也许容易医治,如果是心志上的缺陷,恐怕就要进行精神上的治疗了。而想有助于思想的康健,文学的功能,便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作为《文学自由谈》的长期作者,长期读者,对这本刊物的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它具有神箭手更羸的真刀真枪,直指病灶,点名道姓,痛陈利害的批判精神。这也是每期刊物到手以后,迫不及待,一睹为快的几篇淋漓尽致,锋芒毕露,不忌生冷,令人眼睛一亮,足以体现“文学自由谈”或“自由谈文学”精神的佳作的缘由。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只要始终如一,等到下个十年,大家再次相聚,《文学自由谈》依旧会令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