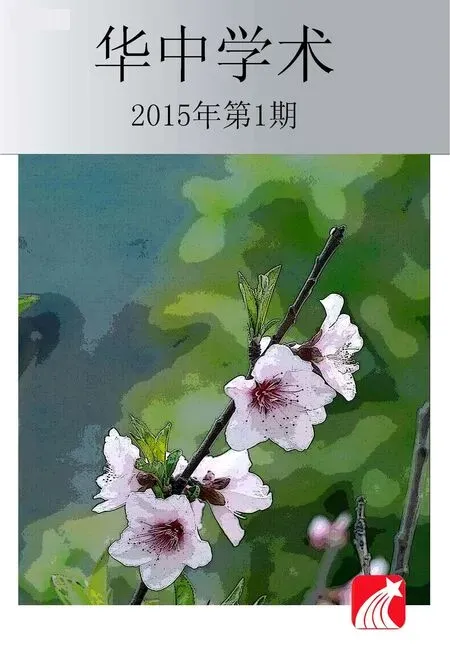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一)
周启超 张 进(整理)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
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述评(一)
周启超1张 进2(整理)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情况做了系统梳理和简要述评,并试图通过六个时段的划分把握中国学界在译介和研究工作上的不同特点,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发展轨迹。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文论 翻译 研究
一、第一个十年(1949—1959)
中国学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其基础与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学与艺术问题的论述——的引介与接受,并不是自1949年10月1日才开始的。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就刊发了一些单篇译文[1],甚至已经有几本专书面世[2]。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确立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目标,提出了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介绍、研究工作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马恩列斯的文艺论著成为我们引介与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首要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基本文献资料的引介路径其实是多元的。有源自苏联的,也有源自法国、美国的。1951年这一年,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上有两本书面世。一本是在北京,由刚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这本书以1944年5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基础,选编了20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主要篇章是从曹葆华、天蓝合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萧三翻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中选录的,周扬对所有译文都做了校订。马恩列之外,本书还收入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评论与演说。该书的出版延续了延安时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统,一再重印(1953年重印时改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发行量大,影响广泛,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1958年,苏联学者里夫希茨编选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3],还编选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4],这两部书也被翻译成中文。
然而,这个源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读本此时也没有一统天下。与它同年面世的还有一部同类读本,即由上海平民出版社也是在1951年推出的、由王道乾翻译的法国学者让·弗莱维勒(J.Freville)选编的一部马恩论文艺的读本《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5],该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恩的文艺思想。不少选段之前,编者还加了简短说明,介绍全篇内容及其他有关情况,有助于读者对所选段落的理解。1953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一部译自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的著作[6]。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对列宁文艺论著的翻译、出版。从1949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相关著作,如苏联学者克鲁奇科娃编选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7]《列宁给高尔基的信》[8]《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有两个译本)[9]、《列宁论托尔斯泰》[10]《列宁论作家》[11]等。当只有《列宁文选》(两卷本,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而《列宁全集》还没有全部在中国翻译、出版之时,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苏联国家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论文学》的汉译本[12],对于推动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处于亲密合作的蜜月期,中国学界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引介与接受更是成为热点,翻译并刊发了斯大林致几位作家的信,翻译出版了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编选出版了《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13]。引介斯大林关于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一时间形成热潮。
1950年6月4日至10月15日,《人民日报》先后分四次刊发了《斯大林全集》中的斯大林当年给高尔基等作家的5封信的译文。首先刊发的是斯大林《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14]。在这封信中,斯大林指出“左倾分子”“右倾分子”在苏联严格来说是党的概念,将“左倾分子”“右倾分子”这些概念“应用于像文艺、戏剧等这样非党的和无比广大的领域”,那就奇怪了。在这封信中,斯大林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竞赛”原则,他认为,“‘批评’和要求禁止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很容易的。但是最容易的不能认为就是最好的。问题不在于禁止,而在于用竞赛的方式,用创造能够取而代之的、真正的、有趣的、富于艺术性的、具有苏维埃性质的剧本,去一步一步地把新的和旧的非无产阶级的低劣作品从舞台上驱逐出去”。第二次刊发的是斯大林《给高尔基的信》[15],这封信主要谈了如何看待青年、关于创办刊物以及如何看待战争小说等问题。第三次刊发了斯大林的两封信,一是《给费里克斯·康同志给伊万诺沃-沃兹涅森斯克省中央局书记柯洛季洛夫同志的副本》,一是《给别塞勉斯基同志》[16]。在前一封信中,斯大林批评了文学上“名人”压制青年人的现象;后一封信则是斯大林对一些同志将诗人的作品看成是反党作品的过于敏感与错误之处的纠正。第四次刊发的是斯大林《给季谟央·别德讷衣的信》[17]。针对讽刺诗人别德讷衣在其创作中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逐渐变成了对整个苏联的诽谤,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强调“共产党员作家必须服从党的决议,领会党的决议的实质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共产党员作家必须谦虚”。《人民日报》认为,“这些信不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而且对于其他革命工作,也是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18]。斯大林《给季谟央·别德讷衣的信》在当年甚至成为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文件之一,1951年12月10日的《文艺报》也转载了这封信。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个年代里,不仅斯大林过去写给作家的信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而且连斯大林1949年才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也很快就有了中译本。1950年由解放社出版的这本书,曾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不仅有学者认为,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对中国语言学研究有原则性的启示[19],斯大林的语言学说启示了中国语言学的新任务和新方向[20],而且还有学者指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新中国整个学术工作都有指导意义,强调“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发挥了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从根本上肃清了在这些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各种错误观点”[21]。正是从斯大林的这部著作中,新中国学界获得了这样的一些基本认识:第一,语言并不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上层建筑根本不同。第二,语言是全民性的,而不是阶级性的。第三,语言是历史的,随着社会的产生发展灭亡而产生发展灭亡;语言的主要东西是词汇,但词汇本身还不能成为语言,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拒绝同化的极大的抵抗性,语言从旧质到新质的转变不是突变(爆发)而是慢慢变化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接受领域,更为重要的当然是新中国学界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解读,是那个年代中国学人所译所写且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重要报纸上的各种文字,如《斯大林论文学》《斯大林与文艺》《斯大林论民间艺术》等。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人民日报》就刊发了茅盾与萧三的文章《斯大林论文学》,介绍斯大林的文学观。茅盾认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斯大林在文艺上最正确的指示。萧三则指出斯大林对进步文化与文艺的三点贡献:一是提出“作家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的论断;二是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三是提出“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观点[22]。紧接着《光明日报》刊发了杨晦的文章《斯大林与文艺》,介绍斯大林与文艺的关系以及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对于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要观点[23]。不久,《人民日报》又刊发一位苏联学者一篇文章的译文,原文发表在《苏维埃文学》1949年12月号上,该文论述了斯大林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文学表现中的乐观主义、关于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竞赛原则”以及“大胆地、放手地培养与提拔青年作家干部”的观点[24]。
这一时期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甚至延伸到领袖人物在民间文艺上的观点。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光明日报》就刊发了一位苏联学者所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该文介绍斯大林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观点,指出“社会主义的艺术创造,应该是为了人民,并应以人民的艺术为基础,这是斯大林一切有关艺术的言论的精义”[25]。该文还介绍说,斯大林熟悉不少民族诗歌,在其演说与著述中经常征引民间谚语、格言、传说、歌曲等。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发行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26]。
应该承认,斯大林对作家创作的论述、对艺术规律的尊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以及对民间文艺、语言学等方面的阐述,对于那个年月里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来讲,影响是深远的。及至1954年,国内有学者从五个方面总结斯大林对于文艺的主要贡献:一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的文艺思想;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三是在斯大林的教导下,苏联民族文化获得了巨大的繁荣;四是斯大林十分亲切地关怀文学家、艺术家的成就;五是斯大林重视古典文学遗产[27]。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斯大林文艺观点的引介与研究,对于正在探索中的我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引介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为突出的译者是曹葆华、王道乾。周扬主编的《马恩列斯论文艺》(后易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一书的主要译者是著名俄语翻译家曹葆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斯大林文艺思想的引介,曹葆华也是主力。王道乾是著名法语翻译家,法国学者让·弗莱维勒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的汉译就是由他完成的。王道乾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工作,1950年7、8月间,《文汇报》刊发了《恩格斯论海涅》[28],还有《恩格斯论歌德》[29]以及《恩格斯论卡莱尔》等系列译文[30],都是出自王道乾的手笔。这几篇文章较早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十分重要的命题——恩格斯关于文学作品的“美学的”与“历史的”评价标准。
这一时期,引介马恩列斯论文艺的基本文献资料主要取道于苏俄,也有从法国引介的;但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解读著作则主要取道于苏联,陆续翻译了不少苏联学者的著述,如泽尼克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31],苏波列夫的《列宁的反映论和艺术》[32],马狄青的《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庸俗化的艺术观的斗争》[33],牟雅斯尼科夫的《列宁与文学艺术问题》[34],谢尔宾纳的《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35],伏尔科夫的《列宁和社会主义美学问题》[36],伊凡诺夫的《列宁论文学党性原则》[37],阿波列夫的《列宁和艺术的人民性问题》[38],叶高林(叶戈林)的《斯大林与文艺》[39]《斯大林与文学问题》[40]《斯大林关于语言学著作中的文学问题》[41],维诺格拉陀夫的《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42],彼沙列夫斯基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43],罗米什的《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44],特罗雯莫夫等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45],斯尔仁斯卡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46],吉谢夫等人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教材大纲》[47]以及福明纳的论文《普列汉诺夫的文学与艺术观》等[48]。在这些译介的著述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文艺观、文学的党性和人民性、文学艺术的功能等观点得到了多视角的阐释。除此之外,也引介了一些英国、德国学者读解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著述,例如1951年三联出版社推出了一部英国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与艺术的著作[49],邵牧君曾将1953年6月23日的《新德意志报》上W.贝逊勃鲁赫所写的《马克思论戏剧中的冲突》译成中文[50]。该文涉及“对剧本‘济金根’的批判”“典型”“党性”“个别形象和普遍现象”“冲突论”等多方面的问题,较早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有关戏剧冲突的观点。
从出版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尤其是对苏联学者读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不仅有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的出版社也有十分积极的投入。1952年至1954年三年间,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曾编辑出版了《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六辑,每辑刊发10篇著作。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开始编辑出版《文艺理论译丛》,至1958年这四年间,共出版了四辑40部(篇)著作。《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与《文艺理论译丛》两套译丛的编辑出版,揭开了新中国外国文论引介史上有规模译介的第一页。
1953年2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马恩列斯论文艺的基本文献也得以有规模地引介。1956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问世。
1958年12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等三套丛书。丛书的编委有巴金、钱锺书、朱光潜、季羡林、李健吾、楼适夷、杨宪益等。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系列中还翻译出版了那个年代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人物的著作,例如日丹诺夫的《论文学与艺术》[51]。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伊始,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被置于重要地位,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主要还是取道于那个年月几乎是我们唯一的朋友、被奉为“老大哥”的苏联。俄罗斯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重要文论,早在1929年就有鲁迅的译本,书名为《艺术论》。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里,除了重印鲁迅翻译的《艺术论》之外[52],对普列汉诺夫文论著作的译介主要还有《论西欧文学》[53],20世纪60年代初又出版了曹葆华等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两部文论的合集《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54]。在引介普列汉诺夫文论思想的同时,还翻译了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如上面已提到的福明纳的《普列汉诺夫的文学与艺术观》。50年代里,新中国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著[55]。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艺界在讨论现实主义、真实性、典型等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当年苏联学者论述这些问题的译文,作为支撑中国文艺理论界研讨的理论资源。例如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典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典型问题的译介,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瞿秋白。他将恩格斯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件译成中文,使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界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典型理论的核心内涵。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里,学界围绕着典型问题的讨论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2年,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报告里将文学的典型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这个观点很快就被中国学者引介。1952年11月上旬出版的《文艺报》第21号,以“学习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学艺术的指示”为通栏标题,刊发了马林科夫总结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部分的译文,这个译文同时还被收入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周扬等人都曾肯定、宣扬过马林科夫有关“典型”的论述。赫鲁晓夫上台后重新制定文艺政策,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55年第18期上刊载了专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对马林科夫的典型观进行清算。中国1956年2月上旬出版的《文艺报》第3号刊发了这篇专论的译文。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专论,从这篇文章可以发现,中共的观点与苏共已经有了一定的差异。这表明我国学界开始摆脱苏联的理论影响,有意识地独立思考上述问题了。新中国围绕典型理论的第二次争鸣始于1956年。在这一年4月出版的《文艺报》第8号上开辟“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专栏,连续发表了张光年、林默涵、钟惦棐、黄药眠、陈涌、巴人、王愚、李幼苏等人的文章,以及苏联学者Д.塔马尔钦科的文章《个性与典型》的译文(周若予译)。同一时期,何其芳、蔡仪、以群、鲍昌、李希凡等人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张光年的文章结合三部话剧在理论上遭到粗暴批判的事例,反思文艺形象的塑造问题;巴人在其专著《文学论稿》里对典型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值得关注的可能是何其芳的观点。1956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阿Q》,从“共名”的角度反思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第一次讨论相比,1956年的讨论较为深入,对什么是成功的艺术典型有两种基本的认识倾向:其一是认为典型就是代表性,巴人持此论。这种认识实际上是突出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物共性特征的观点。其二是坚持了恩格斯的基本认识,认为典型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如张光年与蔡仪都持这种看法。这一观点虽然注意到了个性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的意义,但又强调个性必须统一于共性之中,忽视了恩格斯所强调的在形象塑造上应莎士比亚化的要求。
何其芳的《论阿Q》一文对典型理论的阐释是有独特贡献的,其观点被概括为“共名说”,即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不仅存在于书本里,还存在于生活中,成为人们称呼某一类人的共名;这个人物形象要么被人们所效仿,要么为人们所厌恶,“共名”是一个艺术形象得以成功的标志。显然,何其芳对典型的思考是从艺术形象所产生的社会接受效果来考虑的。他对典型人物具有“共名”特征的概括,体现出试图在各种成功的艺术形象中发掘具有普遍特征的追求。当然,用“共名说”来概括典型的意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文学接受中普遍流传的人物形象并不见得都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且这些形象所共有的那种特征,也并不一定就是某个具体形象的根本特征。但是何其芳能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思考典型问题的理论旨趣,在那个年月里确实难得,值得珍视。
应该看到,关于典型问题的探讨,不只是一个与“艺术形象”相关的理论话题,而且更是一个涉及文学创作实践的现实问题。关于“典型”的讨论尽管较少理论上的创新,却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的文艺创作在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希望摆脱斯大林—日丹诺夫模式的意向。《文艺报》在其编者按语中指出:“要克服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自然主义化倾向,和文艺理论、批评、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种倾向的来源,当然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不过,对典型问题的简单化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缺乏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联系我国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实际展开对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56]林默涵在其《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一文里明确提出,“现在是应该把批判庸俗社会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57]。他的这番话和同一期的《文艺报》的“编者按”,都在隐约地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对典型问题的简单化的、片面化的理解,其实都和接受苏联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这种影响,是导致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应该肯定,这一时期对“典型理论”的探讨,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反思那个年月里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实践品格。
二、第二个十年(1959—1969)
第二个十年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汉译有了很大进展。截至1965年,也就是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中央编译局已经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列宁全集》39卷和《斯大林全集》13卷的翻译出版,为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提供了基本的文本。1958年1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后为外国文学研究所)组建编委会,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合作,翻译编辑出版了“三套丛书”。“三套丛书”的编选与翻译出版,堪称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史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这“三套丛书”中的第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只是这套丛书的编选者在当时并没有急于打出“丛书”的旗号。这套丛书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和《列宁论文学与艺术》都是直接地从苏联学者编辑的文本翻译过来的。
较为全面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始于对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学者米海伊尔·里夫希茨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的翻译。此书是里夫希茨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选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乎所有论述,正如原书编者在“序言”中所说,“现在这部书首先是以十分完备为特色的”[58]。该书中译本除个别篇目采用了中共中央编译局已经翻译、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外,其余均由曹葆华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译本分为四卷,历时六年(1960—1966)方才出齐,体现了当时文论翻译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是当时最权威的选本。通过这部书的翻译,国内文艺界才比较全面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很高的文艺素养,对西方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均有广泛、深入的了解,他们关于文艺问题的丰富而精辟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略去了俄文原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生活》(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组文章的摘录)这一部分。1962年,据苏联学者索洛维耶夫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的中文译本也面世了[59]。这套丛书中还有罗大冈翻译的拉法格《文学论文选》[60];有别于拉法格著作的命运,有另一位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勒菲弗尔的文论选[61],则只能被列入“内部参考”,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由苏联学者尼·克鲁奇科娃编选的苏联国家出版社1957年版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两卷本)[62],译文全部采用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文艺论著的全面译介,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年月里,俄罗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似乎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中的一个小小的热点。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论著作《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新译本[63];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做出布置。他说……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30本书都要出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64]。作为毛泽东提出的30本马列著作之一,三联书店在1964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的大字本[65]。
在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里,卢卡契的文艺思想被引介到中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在1960—1965年,陆续刊发了卢卡契的一些文论与美学著述的译文[66],同时还翻译和刊发了研究卢卡契文艺思想的一些文章[67]。后来新时期出版的两卷本《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的编选工作,其实也是始于60年代初,迄至1965年,该书的译稿已基本集齐,只是未及出版,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68]。1964年,《国外社会科学文摘》还刊发了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的一篇文章[69]。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艺术史研究所编写的长篇巨著《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70]、苏联艺术科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71]。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的译介上,与新中国第一个十年相比,这十年里的数量减少了,涵盖的范围也小了。这种情况与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环境不无关系。在第二个十年里,前有反右运动,后有“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过,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学界还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之前,历时六年(1960—1966)完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四册)与《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上下册)的翻译,给中国学者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经典文献资料。
这一时期弥漫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氛围,也影响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的译介规模。即使从为数不多的引介中,也可以见出那个时代的话语印迹。如匈牙利学者西格蒂·尤诺夫的《卢卡契美学中的艺术创作与党性》[72],还有苏联学者В.谢尔宾纳的《党性与人道主义》[73],以及Г.涅朵希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反对资产阶级美学及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74]。
如果说,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里主要是投入马恩列斯论文艺基本文献的译介,那么,在第二个十年里,已经进入研究之中了。研究的主要论题涉及艺术的真实性、文学的倾向性、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等,这些研究为新中国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开展文艺批评、如何认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性质等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个十年里,中国理论界就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展开了第一次争鸣。1959年第2期《文艺报》发表的周来祥的文章,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已被艺术生产适应于物质生产的新现象所代替”的观点[75]。该文引起了争鸣。1959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了张怀瑾与周文进行商榷的文章[76],认为周文把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两个基本含义——“在艺术领域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个艺术领域和社会的一般发展的不适应性”——并列起来显得重点模糊,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相一致。张怀瑾指出,周文对马克思的“把希腊人或者甚至把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这句话不仅作了不正确的解释,而且机械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没有阶级的原始公社类型和阶级社会类型。张文针对“过时论”,提出这只能说是“发展了”而不是“过时了”。还有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对周文的“过时论”提出商讨意见[77]。1959年的这场争鸣,是新中国文艺理论界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开展的第一次讨论,这场讨论对认识我国文学发展的性质和文学创作活动是有现实意义的,也为第四个十年即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相关讨论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新中国理论界对恩格斯提出的“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在对恩格斯致拉萨尔、敏·考茨基以及致哈克奈斯的几封信的学习与思考中,中国学界展开了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不同观点之间也出现了一些交锋。1960年第6期的《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由恩格斯的几封信来谈文学的倾向性的文章[78]。该文作者提出,一切否定文学的倾向性的论调,都可能导致文学回避当代的重大政治斗争,耽溺于主观主义的空想或自然主义的碎屑描写。其结果不只丧失无产阶级艺术的战斗作用,实质上就是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损害无产阶级革命利益。有学者甚至主张,“应从文学的特点和工人阶级的战斗需要出发来解决文学的倾向性问题”[79];但也有学者将对文学倾向性的理解与作品的真实性关联起来,看出恩格斯所说的“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之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不仅仅是指艺术的特征,还含有更重要的内容,即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原则,即文学的倾向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同时还是对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错误创作倾向的批判。文章主张,“只有当作家描写他所深刻理解的生活时,他的主观倾向才能得到真实有力的表现,因为这种倾向性,亦即对人物事件的一定政治态度和感情倾向是深深扎根于对生活的真实体验的”[80]。这种将文学的倾向性与文学的真实性关联起来进行论述,反映出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已达到了较高水平。应当肯定,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问题的这些讨论,对于人们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思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遗憾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展开中断了这样的探讨。
三、第三个十年( 1969—1979)
新中国的马克思文论引介的第三个十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9年到1976年,在这七年里,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导致出版社停业、杂志停刊、翻译家“失业”,给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与研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第二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开始至1979年,在这三年内,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文化领域的思想禁锢得到了解除,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与研究工作渐渐步入正轨。
这十年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介,主要是通过一些正规的出版社和期刊向社会公开发行,其中许多著述或是译作都是再版,如北京三联出版社1973年2月根据1964年12月大字本重排印行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81],或者是被认为“没有问题的作品”,如列宁所写的纪念鲍狄埃的文章《欧仁·鲍狄埃》以及《鲍狄埃诗选》等。总体看来,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虽然在口头上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实际上不读马列,致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受到严重干扰,陷于停顿、中断,但也并不就是一片空白。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就是在“文革”期间开始准备的,钱中文在该书“后记”里回忆道:“选编工作始于70年代初,何其芳、蔡仪同志都曾亲自指导过这一工作。由于连年运动,光阴蹉跎,工作几经中辍。1978年重新开始这一工作。”[82]在“文革”后期,已经有学校在编写马克思主义文论资料,如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学习参考资料》[83]。
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三套丛书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与研究新高潮的到来做了准备。1978年出版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84]与《蔡特金文学评论集》[85],便是得到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之中最早面世的两部译著,而这些在1978年得以出版的著作,其编选与翻译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文革”期间业已开始的。1983年面世的《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是程代熙在1973年自“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期间译出的。译者回忆道,“当时,‘四人帮’还在作孽,我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还没有得到恢复,所以压根不曾考虑付梓出版的事情”[86]。陆梅林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编辑了《毛泽东论文艺》《鲁迅论文艺》和《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三部手稿[87]。
1978年12月14日~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华中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马列文艺论著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有现实主义问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和悲剧问题等。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即“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这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引介与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待续)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子课题的中期成果。
注释:
[1] 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
[2] 如曹葆华、天蓝合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延安:新华书店,1940年;萧三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重庆:读书出版社,1943年;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延安:解放出版社,1944年。
[3] [苏]米·里夫希茨编选:《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曹葆华、程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4] [苏]米·里夫希茨编选:《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共产主义》,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5] [法]让·弗莱维勒编选:《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王道乾译,上海:上海平民出版社,1951年。
[6] 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编选:《文学与艺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集)》,刘慧义译,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
[7] [苏]克鲁奇科娃编选:《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萧三编译,无锡: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
[8] [苏]列宁:《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张古梅译,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
[9] [苏]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司徒贞译,北京:新潮书店,1950年;[苏]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曹葆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10] [苏]列宁:《列宁论托尔斯泰》,立华译,重庆:中外出版社,1952年;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
[11] [苏]列宁:《列宁论作家》,吕荧辑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
[12] [苏]贝奇科夫、普倩采夫、克拉斯诺娃编选:《列宁论文学》,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3] [苏]斯大林:《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4] [苏]斯大林:《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日报》1950年6月4日。
[15] [苏]斯大林:《给高尔基的信》,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日报》1950年6月11日。
[16] [苏]斯大林:《给费里克斯 ·康同志给伊万诺沃-沃兹涅森斯克省中央局书记柯洛季洛夫同志的副本》,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日报》1950年7月2日;《给别塞勉斯基同志》,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日报》1950年7月2日。
[17] [苏]斯大林:《给季谟央·别德讷衣的信》,曹葆华、毛岸青译,《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5日。
[18] 见《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5日刊发斯大林《给季谟央·别德讷衣的信》的编者按。
[19] 金轮海:《从斯大林论语言学派到中国语言的改造和发展》,《文汇报》1951年4月25日。
[20] 罗常培:《从斯大林的语言学说谈中国语言学上的几个问题》,《科学通报》1952年第7期。
[21] 胡绳:《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对中国学术工作的意义》,《人民日报》1952年6月20日。
[22] 茅盾、萧三:《斯大林论文学》,《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1日。
[23] 杨晦:《斯大林与文艺》,《光明日报》1950年1月15日。
[24] [苏]伊凡诺夫:《斯大林——作家的朋友与导师》,王金陵译,《人民日报》1950年2月12日。
[25] [苏]Г.娃娜克玛:《斯大林论民间艺术》,引之节译,《光明日报》1949年11月6日。
[2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7] 李梁:《斯大林与文学艺术》,《文艺报》1954年2月28日。
[28] [德]恩格斯: 《恩格斯论海涅》,王道乾译,《文汇报》1950年7月13日。
[29] [德]恩格斯:《恩格斯论歌德》,王道乾译,《文汇报》1950年7月15日。
[30] [德]恩格斯:《恩格斯论卡莱尔》,王道乾译,《文汇报》1950年8月8日、9日。
[31] [苏]泽尼克:《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焦敏之译,上海:光明出版社文光书店,1950年。
[32] [苏]苏波列夫:《列宁的反映论和艺术》,谱萱译,北京:中华出版社,1951年。
[33] [苏]马狄青:《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庸俗化的艺术观的斗争》,倪亮译,《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3年第3辑。
[34] [苏]牟雅斯尼科夫:《列宁与文学艺术问题》,李梅曼译,《文艺报》1954年第2期。
[35] [苏]谢尔宾纳:《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景选译,《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4年第4辑。
[36] [苏]伏尔科夫:《列宁和社会主义美学问题》,史慎微译,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37] [苏]伊凡诺夫:《列宁论文学党性原则》,史慎微译,《文艺理论译丛》1956年第2辑。
[38] [苏]阿波列夫:《列宁和艺术的人民性问题》,戈安译,《文艺理论译丛》1956年第2辑。
[39] [苏]叶高林:《斯大林与文艺》,水夫译,上海:海燕书店,1950年。
[40] [苏]叶戈林:《斯大林与文学问题》,水夫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
[41] [苏]叶高林:《斯大林关于语言学著作中的文学问题》,何勤译,《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2年第1辑。
[42] [苏]维诺格拉陀夫:《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张孟恢译,北京:时代出版社,1952年。
[43] [苏]彼沙列夫斯基:《斯大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科学的最高成就》,高叔眉译,《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3年第3辑。
[44] [苏]罗米什:《斯大林与苏维埃文学》,胡鑫之译,《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4年第4辑。
[45] [苏]特罗雯莫夫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则》,金霞译,《文艺理论译丛》1955年第1辑。
[46] [苏]斯尔仁斯卡娅:《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论》,杨慧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
[47] [苏]吉谢夫等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基础教材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
[48] [苏]福明纳:《普列汉诺夫的文学与艺术观》,张祺译,《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3辑。
[49] [英]克林兼德:《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艺术》,未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
[50] [德] W.贝逊勃鲁赫:《马克思论戏剧中的冲突》,邵牧君译,《电影艺术译丛》1954年第1号。
[51] [苏]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戈宝权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2] [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53] [俄]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吕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54] [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55] [苏]卢那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56]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编者按》,《文艺报》1956年第8号。
[57] 林默涵:《关于典型问题的初步理解》,《文艺报》1956年第8号。
[58] [苏]米海伊尔·里夫希茨编:《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曹葆华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37页。
[59] [苏]索洛维耶夫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曹葆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
[60] [法]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61] [法]勒菲弗尔:《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柳鸣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年。
[62] [苏]尼·克鲁奇科娃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上下册),集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
[63] [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曹葆华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64]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中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33页。
[65] [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
[66] [匈]卢卡契:《作家与世界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卢卡契:《一篇美学专论的序论》,《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2期。
[67] [德]斯太因勒:《卢卡契的文艺思想》,《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0年第7期;叶封:《乔治 ·卢卡契:〈美学的特点〉》,《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12期;耀辉:《齐塔:〈乔治 ·卢卡契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辩证法、革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5期。
[68] 见《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7页。
[69] [法]亨利 ·列斐伏尔:《关于结构主义与历史的几点思考》,《国外社会科学》1964年第9期。
[70]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著:《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陆梅林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
[71] 苏联艺术科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编著:《马克思主义美学概论》,杨成寅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
[72] [匈]西格蒂·尤诺夫:《卢卡契美学中的艺术创作与党性》,李孝风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73] [苏]B .谢尔宾纳:《党性与人道主义》,周永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74] [苏]Г.涅朵希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艺术理论和反对资产阶级美学及修正主义的斗争任务》,吴启元译,《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2辑。
[75] 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文艺报》1959年第2期;参见《周来祥美学文选》(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3~1265页。
[76] 张怀瑾:《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是过时了吗?》,《文艺报》1959年第4期。
[77] 李基凯、梁一儒:《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第76~89页。
[78] 解驭珍:《关于文学的倾向性——重读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几封通信》,《文艺报》1960年第6期。
[79] 樊离:《读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信〉》,《湖南文学》1961年第11期。
[80] 蒋培坤:《读恩格斯给敏娜·考茨基的一封信》,《长春》1963年1月号。
[81] [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曹葆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
[82] 钱中文:《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57页。
[83]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学习参考资料》(第一辑),1973年;《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学习参考资料》(第二辑),1973年;《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学习参考资料》(第三辑),1974年。
[84] [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蒋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85] [德]蔡特金:《蔡特金文学评论集》,傅惟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86] [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程代熙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
[87] 高建平主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08~4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