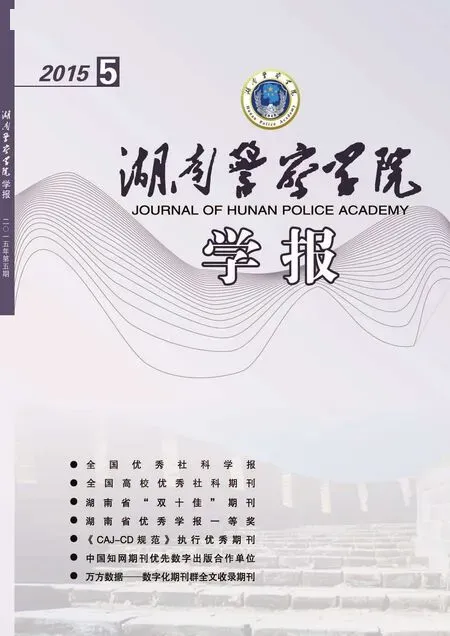影响边疆农村警民互动的因素分析
王维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影响边疆农村警民互动的因素分析
王维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边疆农村的警民良性互动是公安边防部队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由于边疆农村的地缘情况较复杂,边防民警在工作中思想认识不到位,管理方式上脱离实际,不贴合群众,同时,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日益增强,政府和边防部门未提供相应的村民参与治理的平台等因素造成边疆农村警民互动的困境。借鉴社会互动理论,边疆农村警民互动新模式的建构路径是:寻求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思想观念,创设互动情境;构想有意味的符号,调适互动双方的行为;以“角色领会”与“想象性预演”增强互动的有效性;设计相互监督机制,激励互动双方积极作为;以双向回环的方式,形成警民互动的有机循环互动格局。
关键词:社会互动;边疆农村;警民关系;群众工作
关于边疆农村的社会治理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有的学者探讨边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有的分析边疆农村的少数民族教育、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等。有的学者运用互动理论中的符号互动论和拟剧理论分析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警民关系建构中的涉警舆情管理。然而,从社会互动理论的视角分析边疆农村社会治理中警民互动问题,尚未有人研究。本人尝试运用社会互动理论建构边疆农村治理中警民互动的新模式。在边疆农村治理中,警民互动的具体情况如何?警民互动的障碍有哪些?如何创造良好的警民互动环境?国家的相关治理主体如何引导、吸纳边疆农村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进而实现以农村群众意识为导向的乡村自主治理?这些是本文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互动”理论与边疆农村警民互动现状考察
(一)社会互动理论
社会互动理论是20世纪初欧美学者从微观视角观察社会所总结的关于人际互动基本过程的理论。他们认为正是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体在与他人或组织之间的互动才构成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正因为人际互动和交流,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才得以形成并鲜活地展开,每个人才能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体现人的本质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在边疆农村治理中,边防民警的群众工作是民警与农村群众展开互动的过程。双方互动是否顺畅,关系到群众工作能否有效开展的问题。社会互动理论对于分析边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警民互动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人们对社会互动现象的观察经历了一段探索时期。早期美国学者们主要关注点式“自我”。无论是詹姆斯的“社会自我”,库利的“镜中自我”还是杜威从实用主义角度理解的“心智意识”概念,其共同之处在于肯定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和察觉是在与他人或群体的互动中形成并发展的。在边疆农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动过程中,无论是边防民警还是农村群众都有对自我心灵的察知与关照,没有对自我的反思,就没有个体的社会化过程。正是在反思自我过程中,农村群众接纳了民警的行为,民警通过反思自我,更容易感同身受地立足于农村群众的立场和角度,利于其创新设计符合群众利益和需求的新的工作模式和方法。继前辈对自我反思之后,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论”认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的心智、社会自我与社会本身得以形成并发展完善。按照社会互动理论,由众多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的存续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互动主体之间通过一定的符号,诸如语言、形体姿态、神情、语气、动作、眼神、文字等与其他主体进行信息传播与交流,形成人际互动关系。边防民警的群众工作就是与群众打交道,建立良好互动关系,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群众工作中,民警的形体姿态、语言、动作等影响着其与群众沟通与互动的成效。米德认为,人类社会互动的发生有两个基本的预设:其一,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与其他社会关系发生互动。人们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的互动弥补了人的先天自然属性之不足,促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其二,人类的心灵有记忆、识别、保存以往的合作经验,以投入未来的社会互动中[1]。人们会参照以往的生活实践经验而倾向于发生社会互动行为。社会互动理论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层面,对分析边疆农村治理中警民之间的互动过程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边疆农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动及其特点
公安边防部队实施的爱民固边战略指导下的边疆农村建设过程,关键要做好边疆农村的群众工作,处理好边防民警与农村群众的关系。警民关系是否和谐,警民互动过程是否顺畅,这关系到边疆农村的群众工作能否展开的问题,这就需要对边疆农村治理中的警民互动过程做一番考察研究。
社会互动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边疆模范村建设中涉及多方主体间的互动。如边防民警与农村群众、农村内部成员之间、群众与违法犯罪分子、民警与违法犯罪分子、边防部队与当地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之间的互动关系。
2005年7月,公安边防部队开展了“三访四见”活动,认清访问重点、深入群众生活,访贫问苦、访疾问难、访外(外来人员)问弱(弱势群体),通过三访活动,改善民警与群众的关系,拉近警民之间的距离,缓和警民矛盾、紧张和冲突,使农村群众对边防民警看见、敢见、愿见、想见。在这“四见”中,体现了群众化被动为主动的互动过程。2008年底,公安机关实施百万民警“大走访”活动(爱民实践活动),即民警以走访的形式深入到群众生活的第一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增进了警民关系和警民互动的维度。随后,2011年开展“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让群众评价民警的工作,民警对于自身的不当行为向群众道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活动为警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发挥了群众对民警的监督作用,便于民警认识到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及时改进,从而提高工作质量和层次,同时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走访”开门评警活动贵在认识工作中的不足,以便下一步改进。社会互动理论认为互动是一个有机的循环过程,不仅牵涉到过去,还映射到未来的人际互动过程。开门评警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活动本身不仅仅是民警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的过程,更是改进其工作方式和方法的有效措施。民警担任村官和驻村警务室是边疆农村治理创新中所做的又一尝试。在此过程中,民警具有了双重身份和角色。通过村官身份,民警得以直接参与村级事务的治理,深入农村生活。通过警察身份,民警得以引导、发动、组织群众做好工作,为警民合作与互动提供平台,实现了警力下沉与上移,这成为警民之间展开良性互动的机制保障。
由以上措施可知,在边疆农村治理中警民互动呈现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一,警民互动以群体为背景。无论是边防民警还是农村群众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他们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互动,更是代表了两类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警民之间的互动体现的是双方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调适。如在旧的管理模式下,群众对于民警的治理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新的服务型治理模式的建立,使得互动双方更易接受彼此的行为。民警上门服务解决矛盾和纠纷,群众愿意将治安信息告知民警;在广阔的管理辖区,民警走访牧民常遇到不在家的情况,民警采取了留便条、警民联系卡的方式,使警民互动不受时空的限制,增强了警民互动的有效性;其二,警民互动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在互动中个人实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社会属性是在社会互动中完成、成就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个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个体的生命得以提升和丰富,每个人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存在。在边疆农村警民互动中,无论是边防民警还是农村群众,都实现了各自的社会责任,个体在互动中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生命的主体性得以挺立,个体实现了自由的发展和社会化过程;其三,警民互动的主体之间有相互依赖性。边防民警与群众有共同的治理愿景:如对安稳的乡村秩序、富裕多彩的乡村生活、文明有礼的乡村风尚的向往;其四,警民互动以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如秦皇岛市公安边防支队李亚磊在大走访中收集到村民的联系方式建了“警民QQ群”和“手机微信平台”,在村中每个中心户安装报警器,第一时间从群众中获取信息。此外,警民互动是双方的信息、情感和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碰撞。
从警民互动的新态势和特点上分析,可以尝试建构警民互动新模式,即警民互动以共同的论域为互动的思想前提,要创设能达成双方共鸣的场所;同时在互动中掌握互动的技巧,警民的互动需要在一定的监督下进行,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互动;此过程是动态的、经历一个个互动过程,每一个互动都与下一次互动相关联,故而需要双方不断地调适各自的行为。这种新模式要避免以往警民互动中的不利因素,将互动双方置于群体的背景中;在警民互动中,新模式需要强调警民互动过程是个动态的,具有前后密切关联的互动过程;新模式要关注民警在乡村治理中的一些与群众沟通的技巧,以及如何增强互动的有效性等问题。从宏观上分析,警民互动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格局。警民互动的新模式能够激发双方的积极作为,增进互动双方的感情。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的互动模式?需要从分析造成警民互动困境的影响因素上为切入点来逐步建构警民互动新模式。
二、影响边疆农村社会治理中警民互动困境的因素分析
边疆农村的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尤其是警民之间的互动关涉到国家对边疆农村的治理能力和成效问题。虽然国家在加强和探索边疆乡村治理方面取得诸多成绩,但是仍有边防民警与农村群众之间存在沟通障碍,妨碍警民关系的和谐建设,导致一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无法顺利展开。影响边疆农村社会治理中警民互动困境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农村的地缘情况较复杂,造成治理难题。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与中国腹地农村分布情况相比,我国边疆农村大多处于地域广大、经济落后、生存环境艰苦、少数民族分布较复杂的沿海沿边地区。中国腹地农村分布较为集中,农户的村庄院落相对密集,人口成分简单,比较好管理。而边疆农村村庄分布较为零散,户与户之间相隔较远,农耕活动较独立,个体化倾向严重,这种村落布局致使边疆农村治理者很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边疆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这也为民警与农村群众的互动带来难题;其二,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耕地和土地被征用,引发的农民失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农民便失去生活来源。生存得不到保障,造成群众对管理者采取抵触、不合作,甚至反抗的姿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到大城市,出现许多留守老人、妇女、儿童,这也为边疆农村带来治理难题。
第二,边防民警思想认识不到位。边防民警在思想上把自身定位为管理者,这种管制模式下,易造成民警漠视群众利益、摆架子、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等现象。边防民警处理社会矛盾的警务活动方式较生硬,在工作方式上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单一,造成群众对民警抵触情绪严重。民警往往单打独斗,群众不予支持和积极响应,警民关系日渐疏远和对立。“部分群众对边防民警不理解、不信任,对边防工作不配合、不支持,知情不讲,有情不报。”①周兢.群众工作的亮点——关于公安边防部队爱民固边战略实践的调查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51.周兢在此书的“创新了农村群众工作模式”部分中详尽阐述了农村群众工作创新的几个方面。本文中所引例子均来自该书。警民互动的模式单一,机械,警民沟通渠道不畅通。警民之间未能保持经常联系。愚见以为,警务工作可以朝着温情的、满足人性关怀的方向建设,同时将警务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治理。新形势下,公安边防部队应该“建立一套以‘服务’为基本价值导向的制度和机制,积极转变工作职能,努力打造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服务性机关。”[2]服务的理念,能够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进而促其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这种工作模式更有利于警民之间展开良性互动。
第三,边防民警在管理上脱离实际,不贴合群众。贴合群众,即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好群众工作,需要全方位、深入了解农村群众。警民之间在主观世界上的差异阻碍良性互动的开展。双方有无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社会背景、价值观等因素直接影响到警民互动的成效,造成群众与治理者之间信息交流困难,国家政令实施不畅通。这需要民警关注农村群众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形成自觉、良好的互动情境。
第四,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法制意识和权力意识日益增强,政府和边防部门却没有提供相应的村民参与治理的平台,造成警民互动的困境。乡村治理中,村民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愿望和能力,如很多村民关注新闻联播。但是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农民没有参与治理乡村的平台,地方政府、边防部队等作为管理者,在思想意识深处,亦没有重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之诉求,造成警民无法展开畅通的互动。“公安机关空有处理好警民关系的良好愿望,许多群众也有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加强治安管理的愿望,但由于缺乏使二者可以有机结合的切入点,所以警民关系建设仍产生了较大的滑坡。”[3]政府要引导、激发村民的这种治理愿望,为实现村民自治提供更多更广、更实用的平台,进而实现共同治理。此外,边疆农村的村级基层组织涣散,凝聚力不强,需要边防部队在一定条件下和范围内参与农村事务的直接治理,协助农村群众完善基层组织建设,这种农村实际情况,预示探索边疆农村治理中警民互动新模式的迫切性。
三、建构边疆农村警民互动新模式,完善边疆农村社会治理体系
(一)寻求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思想观念,创设互动情境
第一,寻求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思想观念,这是铺设警民互动合作情境的媒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语言传达思想和信息,民警在警务工作中需要掌握当地的语言。双方在互动、沟通、交流时需要借助对方易懂的语言,这是警民展开良好互动的必要前提。不仅要掌握当地的语言,还需要娴熟地学会并运用语言与农民群众沟通,而且要提高自身组织语言、合理用词、调节语气和注重谈话方式的能力。如在少数民族村落,民警发放留言条、提示条、反馈条,如果群众看不懂信息中的文字,必然会造成双方互动的障碍。
第二,创设互动情境。任何社会互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进行的,情境的创设要有利于双方进行通畅的行为互动,同时互动的情境要贴切农村的实际、农民的实际生活。如原先警民互动的场所仅限于警务工作室,民警坐等群众。这种工作方式较为被动,不利于群众工作的展开。新情境的创设要能使民警深入到群众的生产、生活中,深入到群众的思想意识当中。河北沧州边防支队干事牛红昌利用农村赶大集的习俗,将工作地点搬到了集市上,在农民赶大集的时间办公,将各项服务送给农民。如民警在摊位上给群众发放法制宣传册,咨询计生问题,办理户籍卡等提供一些贴近农村群众生活实际的服务。有的民警不仅仅入户走访,还深入到田间地头访问农户,拉近了警民之间的距离。新疆克州边防支队民警管海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主动“入乡随俗”,自制当地香烟,与群众同吃同住,一边与群众拉家常,一边了解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这些贴合农民实际的互动情境,使农民从思想上认可民警的行为,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有利于双方的互动。
(二)构想有意味的符号,调适互动双方的行为
在一定的互动情境下,人们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交流与沟通,在此过程中相互调整各自的行为方式,进而又促成双方进一步沟通的顺利进行。冯特认为“只要这种姿态意味着这种存在于它背后的观念,而且它在另一个人那里也导致这种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有意味的符号”。[4]即人们在沟通中呈现出的各种姿态映射其内在的观念,若这种姿态也引起互动对象产生相同的观念,则姿态就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民警深入到农户家开展“大走访”,这种行为本身就宣告了民警对群众的姿态,即民警的行为意味着“我愿意走近你,并与你建立好关系”。这是民警用行为姿态展现了与群众互动的愿望。这种姿态就是一种有意味的符号,有助于拉近与群众的心与心的距离。民警在工作中的姿态需要不断地调适,使语言和行为更具有“意味”,便于互动双方领会到姿态所表征的相同意义,进而达到双方相互认同,并积极调适其行为方式,且良性互动的结果能够不断积累,指导并影响着下一次互动的展开。
通过有意味的符号,互动双方将沟通彼此的思想观念,并努力达成一致的思想认识,通过相互调适各自的行为方式以促成互动的成功[4]32。故而要使互动双方在沟通中不断调适自我的行为以满足良性沟通的需要,就要求我们寻求姿态背后隐藏的意义、意味。
(三)以“角色领会”与“想象性预演”增强互动的有效性
在警民互动中,双方都承担着一定的角色,并通过角色扮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他们对自身承担角色的认可度和领会度关联着双方互动的维度。角色领会能够使互动双方站在对方的视角或群体的立场和视角上调适自己的行为。“通过在行动前,让行为者运用他人的群体的视角作为其考虑问题和情景定义的基础……人们就能够彼此调适,并适应社会情景。”[1]336在乡村建设中,选派一些素质高、能力强的民警兼任村官,赋予民警一定的角色,凭借其双重职务身份,参与到村务治理中,在思想意识上能够将自身当做农民中的一员,有利于从农民立场出发,拉近与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好地将警务工作和村务工作结合起来。在边疆农村治理中,边防民警可以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到本地治理中,并赋予农民一定的身份,这种身份象征并意味着让农民享有一定的治理权限。身份的厘定能够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并积极地承担起与其身份相符合的社会责任,进而采取与其身份相应的行动,在共同成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农民的自尊心和主人翁意识得以满足和实现。米德认为个体通过“扮演角色”与“承担角色”能主动地规划、预想和设计那些能够带来良好互动效果的角色。个体可以根据角色的理性设计,强化其角色扮演力度,进而在思想上增强角色赋予的使命和担当感[1]38。这种角色的理性设计使得警民互动具有可操作性。
警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的展开,除了“角色领会”之外,更需要“想象性预演”。米德认为,人类的心智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悄悄预演针对这些客体可选择的行动方案,并抑制不适当的行动方案,选择一种公开行动的合适路线。”[1]324通过换位思考,个体能深入到对方的角色当中,从对方的立场、意识和观点出发考虑问题并采取行动。互动主体通过“想象性预演”,能够对自身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衡量和评价,有利于双方及时调试各自的行为模式和处理态度、姿态,进而积极改进其下一步行为方式,这有利于提高警民互动的成效。[1]328
(四)设计相互监督机制,激励互动双方积极作为
奥斯特罗姆在对公共池塘资源实行自主治理的研究中指出在对公共资源的使用中,如何监督的问题是保持长期持续的自主治理的关键。他认为最好是在公共资源的占有者中推举几位守护者。他将之命名为“占用者—监督者”。[5]要是守护者自觉地承担治理的责任,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对其作出相应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需要与其未来的收益挂钩。(这里的收益不仅仅指经济收益,还包括社会信誉的维护与恪守道德)。只有这样,才能制约、监督守护者的行为,并激励其今后作出积极地行动。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中,积极吸纳当地村民进入自主治理体系中,能够有效提升政府或相关管理部门的行政能力,淡化公家与私人之间的界限,有利于积极促成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型互动的完成。但是,这里吸纳农民参与社会治理有个度的问题。虽然民警与群众一直处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但是要防止群众的力量无限制地渗透到政府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中,否则,国家的力量会面临式微、侵蚀,甚至灭亡。①曹志刚.实践中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读乔尔·S·米格代尔的《强社会与弱国家》[J].国外社会科学,2012,(1):148.曹志刚在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指出国家允许其他互动主体在有限范围内参与共同治理,以免其被侵蚀或式微、灭亡。在实践层面,虽然双方要积极促成互动的形成,但是双方仍需斟酌互动的分寸,如警民互动的方向性、互动的深度、互动的广度和频率。这些因素都牵涉到互动的成效问题。这就需要在警民在互动中制定相应的监督机制来保障互动的顺利进行。
(五)以双向回环的方式,形成警民互动的有机循环式互动格局
有效的治理模式不仅仅是政府的策略能自上而下地贯彻到基层组织中,还有一层是民众的意见能够及时、有效、畅通地上传到各级政府决策层。这种政治以民意为深厚的根基,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警民互动若要顺畅开展,亦需建立这种上下贯通,双向回环的互动格局。民警的互动姿态与农村群众的互动姿态相交呼应、相互影响,前一次互动的结果不断积累,逐步影响以后的一次次互动效果。警民互动是一种有机循环式的互动格局。前文论及互动主体要寻求彼此行为暗含的共同的意义。而“意义产生于一个既定的人类有机体的姿态和这种姿态所标示的另一个人类有机体的、这个有机体随后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领域”[4]83正是由于“意义”的存在,使社会互动过程的不同主体之间、前后行为之间紧密相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即在互动中抓住互动姿态背后蕴含的意义和意味。长久的、良好的、公平、公正的警民互动一定是在固根固本基础上的有机互动形态。警民互动并不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互动过程组成,而是有着前后关联的互动链。每次的互动都与其前后两个互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着。前一次的互动为下一次的互动打基础、做准备。民警在与农村群众互动中,要关注这种关联性的存在,它涉及到未来互动地更好展开。
边防民警在模范村设置由村民组成的治安耳目和信息联络员,形成一股治安防控体系的隐性力量,实现了警力下沉和上移,“人人皆警、警警皆民”的治安互动局面。人人皆警,体现了边防民警与农村群众的关系是不断革新变化的动态过程,民警与村民共同治理,依赖于警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共同治理的理念削弱了边防民警与农民、公共事务与私人事情之间的分界[6]。农民参与农村治理可以加强边防治理的力量。有关部门可以积极搭建一个鼓励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环境,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将一部分有觉知、思想认识较高的农民吸纳并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实现边防民警与边民对边境农村的共同治理。警力在民众中,人人皆警的社会格面弱化了警民之间非好即坏的简单分判,凸显了警民之间的互动合作,即边防民警从农村中吸纳新的人力资源即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治理边疆农村,进而达到边疆农村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
边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治理主体树立“社会治理与服务”的理念,由单方“管控”的工作方式向治理和服务层面转变,进而与农村群众建构积极、有效的交流渠道。边疆农村的治理要立足于农村本土实际,以农村群众意识为导向,依托农村群众自治,鼓励农民参与到治理中,强化农村群众对公安边防民警的认同感,提升公安群众工作的治理能力,只有形成良好的警民互动,群众工作才能更好地开展,进而营造良好的乡村秩序。
参考文献:
[1] [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27.
[2]张保平,李刚.边防群众工作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313.
[3]崔北方,祝大安,孙国恩,于晓光.警民关系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78.
[4] [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和社会[M].霍桂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49.
[5]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迾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15.
(责任编辑:天下溪)
[6]李姿姿.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J].学术界,2008,(1):272.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Frontier Rural Police- community Interactions
WANGWei
Abstract:The interaction of the frontier rural public is the basis of frontier forces and does mass work well. Due to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rural frontier, border police ideology at work are not in place, management on the way out,do not close to the masses; Farmers’increasing sense of own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and villagers in border services do not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platform for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factors such as frontier plight of rural police-community interactions.Profiting from social interaction theory, frontier rural pa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l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ce are finding a commo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ideas, creating interactive situation,conceiving symbolic signs, adapting interactive behavior of the parties,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action through“understand the role”and“imaginary rehearsal of”,design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encourag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sides actively, forming the pattern of interacting organic cycl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ce in a bi-directional loop way.
key words:social interaction; frontier rural area ;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e and the public; mass work
作者简介:王维(1980-),女,山西永济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政工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公安边防部队创新社会治理实践的调查与研究”(HB14GL004)
收稿日期:2015- 06- 29
中图分类号:D6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1140(2015)05- 0018-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