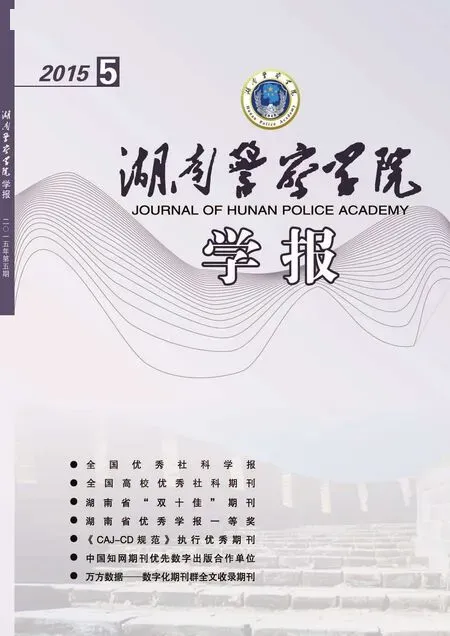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王永强,陈 成
(1.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四川 成都 610041;2.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4)
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
王永强1,陈成2
(1.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四川成都610041;2.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数据日益成为发现犯罪、证明犯罪的重要线索和证据。基于职务犯罪尤其是贿赂犯罪侦办及证明难度较大的现状,电子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运用尤有必要。研究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取证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电子数据的概念、特征及现行法律规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发现、固定与采信。同时结合实证的考察,深入分析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中电子数据取证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发掘相关问题存在的根源,即可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电子数据;职务犯罪侦查;证据收集;证据采信;对策
一、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不断呈现出信息化的趋势,“网络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大量的涉案相关信息开始以电子数据等形式呈现出来。基于电子数据在提供犯罪线索、证明犯罪事实方面的效果及作用,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明确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职务犯罪中,特别是“一对一”特征极为突出的贿赂案件中,证据资源及侦查措施极为有限,加之“经验型侦查模式”下侦查能力所受到的客观限制①笔者通过调研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内部实行轮岗,侦查队伍往往也不固定。这导致检察机关的自侦仍然以经验型侦查为主,无法像公安那样形成专业化的侦查队伍和行之有效的办案模式。,案件侦办的突破难度极大。电子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的正确运用,能够进一步拓展案件的线索与证据来源。而合法有效地进行电子数据取证,正是电子数据运用的首要前提。本文以此为着眼点,对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电子数据取证进行深度研讨,以期在丰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职务犯罪侦查实践有所助益。
二、电子数据的概念与特征
(一)电子数据的概念
准确界定电子数据的概念是电子数据取证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理研究中,关于电子数据的概念众说纷纭,并未形成统一定义。由于电子数据在形式上往往体现为文字、声音、图像等,因而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以前,相关理论研究及学说也曾将电子数据归类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抑或鉴定结论等[2]。基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及更新的频率,对电子数据进行学理及法律层面的界定应抓住其本质。依拙见,电子数据是以特定编排方式的电子、电磁、光信号或具有类似性能的形式而存在,并通过不同的电磁或光信号等编排方式表达特定的信息。同时,电子数据所表达的信息可借助相应的媒介设备为人们所认知,如电脑硬盘、U盘、储存卡等储存介质中的数据可通过显示器、扬声器等工具设备予以读取并被人们所认知。
(二)电子数据的特征
1.可再生性。电子数据与一般的实物证据不同,其具有自身独特的信息储存方式(如格式分区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借助专业的技术与装备恢复储存介质中被破坏或者删除了的信息。换言之,在犯罪侦查中,嫌疑对象在删除了相关电子数据以后,办案人员依然可以依靠专业知识并借助专业设备将其还原或再现[3]。以此,通过数据恢复技术的运用,达到准确重建犯罪情景的目的。
2.无形性与依赖性。电子数据可以包括信息数据库、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电子和声音邮件以及在计算机存储中存在的其他信息[4]。一般而言,我们无法通过自身感觉器官直接对电子数据中所反映的信息进行认知。只有借助专门的技术或设备,电子数据所反映的信息才能转化为人们可认知(如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等)的状态。以此,给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收集和处理提出了较高的技术性要求。换言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科学性要求通过证据认定事实[5]。即是,电子数据的收集、分析、判断与再现等必须通过相关技术设备以及技术手段来实现,依赖性较强①参见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虞磊浩.论电子证据对刑事搜查的挑战[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6):52.赵东平.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与方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162.。
3.多样性。如前所述,电子数据存在的方式与状态具有无形性。因而,对于电子数据所承载的案件信息进行认知,往往系通过多媒体显示或者打印等技术手段以声音、图像以及文字等方式予以展现①。以此,“无形”存在的电子数据在进行相应转化以后,就几乎“涵盖”了所有“有形”的传统证据类型,即转化后的形式具有多样性[6]。这也是传统证据种类划分中会将电子数据纳入“视听资料”、“书证”或“物证”等的原因[7]。但应当注意的是,“转换”后的电子数据并未改变其证据种类,而只是证据载体发生了变化。
4.客观性。电子数据是基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产生的证据,其生成及传递等严格遵循相关的计算机数据运算机理,且往往具有完备的安全保障系统[2]。因此,在无人为修改删除或者技术差错而引起相关数据破损的情况下,电子数据系一种客观证据,能避免主观原因所造成的的证据偏差。同时,基于电子数据储存环境的特殊性,一般不会发生诸如腐烂变质等物理、化学变化而造成相关证据信息的毁损灭失。因而,未经修改或破损的电子数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准确地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的客观性较强。
三、关于电子数据的立法概况
在电子数据的法制化方面,较早进行立法的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且主要集中于民商事领域②如马来西亚1997年通过的《数字签名法》、新加坡1998年通过的《电子交易法》、加拿大1999年通过的《统一电子商务法》、欧盟2000年通过的《电子商务法》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通过了《电子商务示范法》和2001年通过的《电子签名示范法》。参见张凯.电子证据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6.33-38.。我国对电子数据进行专门立法相对较晚。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标志着我国电子数据立法的开始。然而,基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法定证据种类的“封闭式”规定,其并未对电子数据进行明确规定③参见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且前述《电子签名法》主要适用于民商事领域,刑事领域关于电子数据的立法长期以来始终付之阙如。
2010年7月,“两高”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其主要规定了死刑案件中不同证据的审查与认定问题。此外,除涉及法定七种证据,《死刑证据规定》还专门规定了电子证据④关于“电子数据”与“电子证据”,一般认为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本文亦不对二者做区分。但相关规定也有过区分二者的情形,如公安机关《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公信安[2005]161号)第二条规定:“在本规则中,电子证据包括电子数据、储存媒介和电子设备。”参见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62.、辨认笔录等的审查与认定,并对电子证据的类型范围进行了列举①包括能证明犯罪事实的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参见《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应当说,这是我国刑事诉讼领域首次引入“电子数(证)据”概念。
2012年,基于刑事诉讼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实践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其中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直接将“电子数据”纳入法定证据种类。应当说,这是我国首次在基本法中确立电子数据的法定证据种类地位。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电子证据”亦成为民事领域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院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检察规则》)以及《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规定》)也据此相继制定了电子数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及操作规定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七十条;《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等。。
在关于电子数据的操作细则方面,公安机关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及行业标准③如《公安机关电子数据鉴定规则》、《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公安机关执法细则》以及《数字化设备证据数据发现提取固定方法》(GA/T 756-2008)等。此外,《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七章专章设置了“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细则。。较之公安机关在电子数据取证与鉴定方面的系统性、全面性规定,检察机关方面目前仅有《人民检察院电子证据鉴定程序规则(试行)》,其重点涉及电子数据鉴定的相关问题,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电子数据的搜查、扣押以及提取规则和方法等缺乏规定。
四、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收集、固定与采信
(一)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取证的原则
电子数据取证,是通过各种合法取证手段对相关储存介质中的涉案信息进行发现、收集与固定。基于前述电子数据的特征,较之传统证据,电子数据的的收集与固定既需遵循合法取证的一般性原则,也要遵循电子数据取证的某些特定原则,以确保所获取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完整性[8]。
1.合法性原则。合法性原则是调查取证的基本原则,也是证据合法性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取证主体抑或取证程序的失当或违规,将直接影响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证据法上,瑕疵物证存在补正的可能性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以此,明确了实物证据的“可补正”原则。。然而,基于电子数据精密的运行机理,取证中的一点小瑕疵就可能改变其性质[2]。因此,强调电子数据取证的合法性原则,是对“正当程序”与“实体真实”价值的双重追求。
2.比例性原则。比例性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公权运行的基本原则,认为“任何旨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都必须寻求符合基本法的目标,并使用适当的、必要的手段,以便使对公民权利的干预被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9]电子数据取证中,比例性原则体现为侦查机关在进行相关电子数据取证活动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考虑相关措施的必要性等,以适度方式将对公民隐私权及财产权的侵犯降至最小程度,从而实现案件成功侦破与公民合法权益保障间的平衡。
3.及时性原则。电子数据取证中,取证的及时性尤为突出。一方面,基于电子数据的可擦写性以及职务犯罪的智能性特征,相关证据在案发以后极易被嫌疑人篡改甚至毁灭。尽管破损后的电子数据往往能够进行数据恢复,但相关恢复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很可能使案件侦查错过最佳战机,更遑论一些较为特殊的电子数据一经破损灭失,便再难以修复和再现[10];另一方面,部分电子数据具有时效性,若在一定时间内或在固定空间内不加以专门备份等就会自动清除。对于这样的电子数据,“一旦错失最佳取证时机,便无法保证电子数据证据的完整性”。[11]
4.全面性原则。基于电子数据存在形式的无形性以及认知方式的依赖性,对于涉案电子数据的发现较之传统证据更为困难。实践中,嫌疑人往往可能通过更改计算机中相关文件的扩展名(如将.jpg篡改为.txt)或是设置文件的隐藏属性等将其隐藏,侦查人员在进行电子数据检查时很可能将其误认为系统文件等而忽略对其的检查。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电子数据发现与收集中取证方法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全面而细致地发现可能存在相关电子数据的储存点,以免错漏案件的相关线索与证据。
5.专业性原则。电子数据作为一种高科技证据,除存在方式及认知方式的特殊性外,在案件的查办中更体现为取证方式的专业性。如前所述,电子数据所反映的相关信息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设备予以认知。与之相适应,在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中,一方面,取证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予以具体实施或者协助;另一方面,电子数据取证必须采取具有专业性的手段和工具,如专业的提取设备、保全设备以及数据恢复设备等。
6.无损性原则。无损性原则,要求在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完整性。此系电子数据取证的核心原则[12]。基于电子数据的特殊存在形式,“对存储介质和系统环境的任何操作均能改变电子信息的属性,极有可能损害将来需要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11]31因此,电子数据的收集方式应当主要以镜像拷贝(Bitstream Copy)①镜像复制与普通复制在以下几方面存在不同:(1)普通复制只复制可识别文件,镜像复制能将目标驱动器中的每一个字节都复制下来,包括所有文件、空白空间、主文件表和元数据等;(2)普通复制在计算机运行时进行,镜像复制一般在数据机器处于关机状态时进行;(3)普通复制不改变文件属性,镜像复制形成的都只是只读文件,进行数据分析时不会发生数据变动;(4)普通复制后不必进行校验,镜像复制后需进行校验,往往采取哈希函数检验数据的完整性。参见刘品新.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1.等方式进行。换言之,实践操作中应将电子数据本身及其它数据痕迹等一同复制。同时,除情况紧急的重大案件,抑或技术条件限制,对电子数据的检查工作原则上应当在其备份储存媒介上实施。
(二)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取证方法
1.电子数据的发现(搜查)。一般认为,职务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现场往往并不具备勘验价值[13]。因此,对职务犯罪中电子数据的发现一般集中于对嫌疑人的住所或者办公场所的搜查过程中。实践操作中,电子数据的搜查方式并不一致。域外方面,欧美等国家在计算机搜查中的“最佳选择”[8]34主要是通过扣押原始介质建立镜像复制件,并在复制件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即所谓的“两步式”搜查:第一步,进入相关储存介质存在的物理空间,扣押涉案储存介质;第二步,对所扣押的储存介质进行数据分析,从中找出涉案数据并予以扣押[8]34。以此,一方面能够通过实验室的科学分析,准确全面发现涉案数据,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在储存介质原件上操作可能造成的数据灭失风险。具体而言,在“第一步”搜查中,基于相关设备在实践中的使用频度,应重点注意对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安装有通讯软件的计算机设备的发现与检查。操作上,在控制了相关嫌疑人以后,应当及时暂扣其随身携带的电子通讯工具及移动存储设备,保证相关储存介质所载信息在取证过程中不被破坏;在“第二步”搜查中,基于相关对象可能存在反侦查的意识,应注意对隐蔽涉案数据的查找,如前述通过改变文件扩展名更改文件属性及设置文件夹的隐藏属性等情况。
2.电子数据的提取与固定。基于证据合法性及相关性的要求,在电子数据的提取与固定过程中,取证活动应当由侦查人员主持,并由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实施具体操作,且取证主体不得少于二人;具体方法上,首先应通过镜像拷贝将相关数据复制到专用证据储存设备中,并就拷贝等过程通过启动数字摄像机或者安装屏幕录像软件(computer screen capture)①屏幕录像软件系用于截获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并生成视频文件的软件。等方式对整个过程进行视频记录;其后,应将数据信息的储存介质进行封存。同时应当注意,证据的提取即封存过程应制作文书,并由相关证据的取证操作者、提取文书制作者以及见证人等签名或者盖章。最后,将证据储存设备中的数据进行检验,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的数据恢复并从中提取出涉案数据。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与技术人员应当保持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一方面使得专业技术人员能够明确电子数据检验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能使侦查人员及时充分从检验结果中掌握案件的相关线索信息。
(三)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采信标准
可采性,即“法律规定的何种电子证据能够作为合法证据的采用标准”。[14]对职务犯罪案件中电子数据的采信标准,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38条。。实践操作中,对于电子数据的采信应分别从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等方面予以审查。
1.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审查。客观性标准要求电子数据必须客观真实。实践中,电子数据客观性的审查主要通过推定与鉴真等方式进行。推定的方式,是指通过确定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而推知认定相关电子数据的形成、储存及传输等具有可靠性,即该电子数据具有客观性。实践中,应注意审查生成电子数据的计算机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此外,还应注意是否存在人为因素影响,即“人们可能因差错(mistake)、欺骗(fraud)或者偏见(bias)而添加、遗漏、修改或删除计算机内的某些信息。这些错误的风险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数据输入人员的动机和其所受过的训练,录入信息的数量,以及程序被监控的质量”。[15]鉴真(authentication),即“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真实性的审查方法”。[16]对此,《死刑证据规定》及《法院解释》等均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③参见《死刑证据规定》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条;《法院解释》第九十三条。,要求审查电子数据的收集是否符合法律及相关技术规范,有无删除、修改、增加等情形。
2.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电子数据的合法性,要求电子数据的提取与固定必须合法。从目前颁布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一方面应当遵循电子数据取证的程序性规定,另一方面应当注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电子数据中的适用。
第一,应当注意审查电子数据收集与固定的程序与方法是否合法。即是,电子数据的收集程序与方式在符合技术规范的同时,还应符合法律规定,做到证据合法性与证据科学性的严格统一。具体而言,应当审查电子数据的取证过程是否有相应的笔录、清单等,相关记录是否经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见证人签名;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等是否规范注明等。
第二,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获得的电子数据也应视情况予以排除。侦查人员在电子数据取证的过程中,应当遵守程序规定,否则即可能存在程序上的瑕疵甚至违法。基于电子数据属于客观类型的证据,因而应当适用类似物证、书证之“限制排除原则”。然而如前所述,电子数据取证的一小点瑕疵就可能改变其性质。因此,对于电子数据取证中所做的补正或者合理解释应当严格予以限制,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合法性。
3.电子数据的关联性审查。“关联性是证据的自然属性,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17]“电子数据的关联性标准与传统证据并无实质性差异”。[18]基于我国当下实践中所采用的“印证”证明模式[19],在认定电子数据的关联性时可以考虑综合印证的方式。具体而言,应当考虑嫌疑人是否具有与相应电子数据相适应的计算机操作水平等。同时,在审查某一特定电子数据具备相关性、合法性以及客观性的基础上,还应当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性的审查与判断,分析证据结构及证据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得待证事实均有证据支撑且证据间能够得以“相互印证”。此外,证据体系应当客观、科学地再现相关犯罪活动,在动态上“照应”整个案件主要事实的发生、经过和结果,并能以此对案件作出“排除合理怀疑”的认定结论。
五、当前职侦工作中电子数据运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应当说,电子数据这一新型证据的独立价值凸现,在查办职务犯罪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时下侦查人员对电子数据的认识和运用尚有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
(一)电子数据应用观念落后,思想重视程度不够
从实践操作来看,尽管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已将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种类予以明确规定,但侦查人员受传统证据观念的影响,对电子数据的收集与运用还缺乏应有的认识,侦查实务中对电子数据仍极少运用。调研显示,我市从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至今,共办理300余起贪污贿赂案件,在这300余起案件的全部证据类型中,电子数据所占的比例不足3%,而言词证据所占的比例达70%。该数据一方面反映出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与侦查办案中电子数据罕见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虽然在侦查理论上一再强调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变革,要实现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供证结合”的转变,但受制于侦查手段、侦查技术和传统思维方式、取证方法等的制约,一线侦查人员往往更愿意收集言词类证据材料。是以,不少侦查人员往往固守陈旧的证据收集观,缺乏对电子数据在案件侦破及证据体系中积极作用和重要地位的认识。进而,在实践操作上缺乏相应的电子数据识别和取证技能。
(二)法律规定尚不完善,缺乏具体实施细则
如前所述,刑事诉讼领域关于电子数据的规定肇始于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颁布实施的《死刑证据规定》。随之,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在检察机关方面,关于电子数据较为完整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下发的《人民检察院电子证据鉴定程序规则(试行)》,该规则是目前关于电子数据鉴定专门性的司法解释。应当说,上述法律或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中电子数据取证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基于侦查阶段电子数据取证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规则的缺失,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难以有效、科学、系统地实施并受到规制。以此,不仅影响了案件侦破的效率,同时也影响到涉案电子数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降低其对特定案件的证明作用,甚至会因取证方式失当或违法而造成证据排除的严重后果。
(三)专业知识技能缺乏,内部合作机制阙如
电子数据的科技要素含量,决定了该类证据的收集及固定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协助或者实施,同时需要专门设备和技术手段的运用。目前,自侦部门侦查人员的专业及学历层次差异较大,多数干警仅具备基础性的计算机操作与运用能力。此外,侦查人员与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往往难以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有机结合”。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技术人员几乎很少参与侦查人员主导的证据收集过程,而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般依据个人经验判断而进行,在收集到证据以后再交由技术部门的技术人员进行数据分析或者恢复,技术人员在电子数据收集环节更多处于被动接收状态。以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子数据的发现与获取。另一方面,可能对一些具有重大线索或证据价值的电子数据无法做到及时、全面收集,影响侦查取证的效果。
(四)实践操作混乱,欠缺规范性
第一,电子数据取证中相关笔录制作不规范。实践中,多数案件都没有制作相关的电子证据提取笔录。在有电子数据提取笔录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只是在扣押物品清单中简单记载该案所扣押的手机、电脑、U盘等的型号和数量,而没有证据材料持有人或者见证人的签名,也未注明未签名的原因等。此外,在70%以上的案件中,相关电子数据在经恢复、鉴定后并未让犯罪嫌疑人、证人等进行签名确认。以此,因无法严格鉴真而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审查。第二,电子数据取证内容的不完整。按照电子数据所承载的内容进行划分,一般可将其可二分为“内容数据信息”和“附属数据信息”。内容数据信息是指记录了嫌疑人涉案信息的电子数据,如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正文等。附属数据信息,是指记录内容信息电子数据相关环境和适用条件等的附属信息,例如word文档的文件大小、位置及最近修改时间等。实践中,侦查人员在收集电子数据时,往往忽视对附属数据信息的收集,如对QQ聊天记录只单纯通过拍照的方式将聊天内容予以保存,而未对QQ号的基本情况等附属数据信息进行提取,造成电子数据取证内容的不完整,进而导致无法证明内容数据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造成证明体系的不完整。
六、相关解决对策
“无论是从国外还是国内的现状来看,电子取证都面临着技术提升和法律规制的双重重要任务”。[8]11同时还应注意,在电子数据取证活动中先进技术的运用以及对法律规定的遵循,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取证执行者的侦查人员是否具备了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以及专业知识储备。
(一)转变思想观念,提高思想认识
电子数据,是经济社会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丰富了法律事实认定的方式。如何家弘教授所言,“就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而言,人类曾经从‘神证’时代走入‘人证’时代,又从‘人证’时代走入‘物证’时代。也许,我们即将走入另一个新的司法证明时代,即电子证据时代”。[20]因此,只有不断适应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从观念上和认识上重视电子数据,进而在实务操作中提高发现、收集和固定电子数据的能力水平,使之真正成为侦查办案的一大“利器”。
(二)制定取证规则,加强取证法制化建设
一般而言,一类新型证据若在收集与审查等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制规范引导,实践势必随意为之,甚至出现违法取证的乱象,相关证据的收集与审查效率也随之降低。“电子取证的形式多样,但基于其在技术方面日渐趋同,因此在法律规制方面也呈现出趋同的规律”。[8]5换言之,电子数据取证存在规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由此,电子取证“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迈上法治的轨道”。[8]11当务之急,检察机关应当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系统可行的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以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的建立,带动电子数据取证的标准化建设。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电子数据取证行为的法制化,在增强电子数据取证可操作性及科学性的同时,进一步规范电子数据取证行为。例如,浙江省检察机关于2012年出台了《浙江省检察机关电子数据技术工作规则(试行)》,对检察办案中电子数据的勘验、送检、鉴定及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明确的规定[21]。广西自治区检察机关也于2013年审议通过了《广西检察机关电子数据技术工作规范(试行)》,以规范该区检察机关包括电子数据的勘验检查、检验鉴定在内的电子数据技术工作[22]。
(三)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保障取证能力
电子数据所储存的信息量大,客观性强。然而,只有通过与之相匹配的专业技术装备,才能全方位揭示电子数据所反映的案件线索与证据事实。即是,在专业设备上,应当“以更好的技术能力回应日益增加的司法实践要求”。[21]应当提升检察机关电子数据取证的技术装备水平,在关键技术设备如数据恢复设备等的配置方面应达到普及层度;另一方面,可建立专门的电子数据实验室。具体而言,基于电子数据可进行远程取证与鉴定的可能,在相关电子数据实验室的设立方面,“可把各自不同特色鲜明的取证实验室整合互联起来,进行人、财、物的结构调整,通过合理布局、有效调度,开展分布式处理,以求效益最大化”。[23]
(四)加强学习培训,完善内外协作机制
作为电子数据取证的执行者,侦查人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取证技能极为重要。对此,应当切合我国实际,从当下及长远两方面完善侦查人员专业化建设。当下,可通过专题培训等方式,提高侦查人员的电子数据业务知识储备,从而针对性地提升侦查员在电子数据取证方面的业务水平与能力。同时,自侦部门在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要主动加强与本院技术部门乃至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的沟通与交流,进一步协同配合,建立和完善内外合作机制,有效形成协作合力。但从长远来看,职务犯罪的发展必然是专业化与智能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基于沟通及理解在客观上所存在的偏差,法律专家找技术专家抑或技术专家找法律专家的实践效果与理想效果存在差距[24]。在犯罪侦查方面,应当培训一批具有法律与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交叉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27]。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侦查人员电子数据取证的专业化问题。
参考文献:
[1]赵志刚.拥抱电子证据时代[A].检察技术与信息化(第4辑)[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1.
[2]樊崇义,戴莹.电子证据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N].检察日报,2012-05-18.
[3]叶红.电子取证:打击计算机犯罪的利器[N].中国计算机报,2007-07-30:(C07).
[4] Givens, J. Shane. The Admissibility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t Trial: Courtroom Admissibility Standards [J]. Cumberland Law Review,2003,(34):96.
[5]霍宪丹.试论司法鉴定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26.
[6]游伟,夏元林.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J].法学,2001,(3): 60.
[7]刘品新.论电子证据的定位——基于中国现行证据法律的思辨[J].法商研究,2002,(4):38-40.
[8]刘品新.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8.
[9]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02.
[10]赵东平.职务犯罪侦查技术与方法[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162.
[11]丁谷平,卜磊.反贪侦查实务中电子数据取证问题研究[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3,(2):31.
[12]何家弘.证据调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2.
[13]马方.职务犯罪侦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9.
[14]皮勇.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53.
[15]杨雄.论电子证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6):79.
[16]陈瑞华.刑事证据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9. [17]何家弘,杨迎泽.检察证据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62.
[18]皮勇.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53.
[19]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法学研究,2004,(2):109.
[20]何家弘.电子证据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4. [21]浙江检察机关出台《工作规则》规范电子数据处理[EB/ OL].http://news.jcrb.com/jxsw/201210/t20121014_963271.html. 2015-03-02.
[22]广西省检察院通过“新规”加强电子证据技术工作规范性[EB/OL].http://news.jcrb.com/jxsw/201312/t20131208_ 1267920.html.2015-03-02.
[23]徐云峰.化云为雨:电子取证体系化研究[A].检察技术与信息化(第4辑)[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31.
(责任编辑:天下溪)
[24]刘品新.跨越法律与技术的鸿沟:网络时代刑事司法如何转型?[A].检察技术与信息化(第4辑)[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27.
Research on Electronic Evidence Discovery System in Duty Crime Investigation
WANG- Yongqiang1, CHENCheng2
(1. People’s Procuratorial of Chengdu, Chengdu, Sichuan, 610041; 2.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lectronic data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clue and evidence of discovering and proving crime. Considering the large difficulty in investigating and proving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especially crime of bribery,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apply electronic data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In respect to study collection of electronic dat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it shall be firstly understood the concepts, features, and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s of electronic data. On this basis, further study shall be carried out concerning discovery, fixation, and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data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Meanwhile, elaborate analysis, based on empirical survey, shall be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primal problems related to evidence collection from electronic data in the course investigation practice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and solutions can be proposed correspondingly by excavating the root of related problems.
Key Words:electronic data; duty crime investigation; evidence collection; admissibility of evidence; countermeasures
作者简介:王永强(1974-),男,苗族,四川宜宾人,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陈成(1990-),男,四川西昌人,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侦查学和证据法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度成都市检察机关重点课题“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数据的收集及证明规范研究”
收稿日期:2015- 06- 18
中图分类号:D6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1140(2015)05- 0045-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