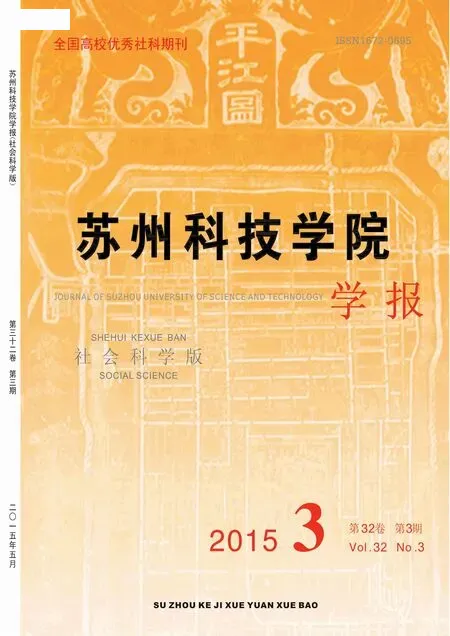从《长物志》和《闲情偶寄》看明清园林文化发展动向*
施春煜
(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 监测部,江苏 苏州 215001)
从《长物志》和《闲情偶寄》看明清园林文化发展动向*
施春煜
(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 监测部,江苏 苏州 215001)
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和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是两部被园林学界公认的中国古代造园著作。《长物志》和《闲情偶寄》代表了明清园林文化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并反映出一种动向。首先,两部著作都鲜明体现了明清园林文化中的“器物关注”特征,只是在两者之间又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点。其次,这两部著作的先后问世反映了明清园林文化理论发展的两个阶段:总结和创新,并且从《长物志》到《闲情偶寄》,园林文化领域中审美话语权的归属趋向又发生明显的转变,即从一元向多元扩散。
文震亨;《长物志》;李渔;《闲情偶寄》;园林文化
园林文化是明清江南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以往众多关于明清社会文化研究的成果都有反映明清园林文化的发展状况,如谢国桢在《明末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艺术的发展》一文中专门开辟一节阐述晚明资本主义萌芽推动的北京及江南地区盛大的造园风气。同样在王卫平《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奢侈风气及其评价——吴地民风的嬗变研究之四》、吴承学的《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李玉宝的《从〈五杂俎〉看晚明士人的心态》等论文中也有相近的论述。也有很多直接以园林为题的论著,对明清时期园林文化发展的特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如童赛铃在《明末清初江南园林的发展及其美学思想》一文中认为以假为真、小中见大、崇雅反俗、注重个性、实用与艺术结合是明际江南园林美学思想之特点。邓洁《汲古出新——论明清江南园林文化特征的形成》一文指出了明清园林文化之“隐逸”标签化特征及造园行为趋向大众化普及化的特征。顾凯《重新认识江南园林——早期差异与晚明转折》从建筑学的角度揭示了晚明以来江南园林实体特征表现为建筑数量增多,配置密集,各种构成要素形体关注加强,整体营构效果突出。这些论著、文章对园林文化之时代特征进行了整体性思考。。而明后期以来出现的造园著作如《长物志》、《园冶》、《闲情偶寄》等,是以往明清园林文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文震亨编著的《长物志》成书于明崇祯七年(1634),李渔编著的《闲情偶寄》成书于清康熙十年(1671),两书被公认为明清江南造园理论专著*很多针对著作的个案研究,主要分析著作所秉持的造园理念思想、技巧方法、文化心态,挖掘的主要还是个体对象,如桂强《〈长物志〉的艺术美学思想》一文全面剖析了该书在园林营造、室内设计、工艺制作等方面的主张,最后点出了文震亨所代表群体的焦虑心态。傅丽叶《中国士大夫的“优良设计”——通过〈长物志〉看中国晚明时期的物质文化传统》一文把文震亨对精致典雅生活的追求解释为因政治焦虑和官场失意的回避,以此获得精神补偿,并命名为“优良心物观”。李志明《阅读〈长物志〉:从文本到话语》一文指出《长物志》所宣扬的品鉴知识和美学准则的表象下隐藏着一种排斥性的话语机制,这种机制的产生与晚明消费社会背景下士大夫阶层身份地位的变化有关。杜祖锐、周逢年《适性人生,诗意栖居——李渔造园思想探微》多方面分析了李渔造园理念中独创性、率真性、实用性特点。黄果泉《回归世俗:〈闲情偶寄〉生活艺术的文化取向》把《闲情偶寄》中的园林生活艺术界定为世俗化。。以当今理论著作的一般标准而言,两者在体例、内容、语言等方面的系统化规范化程度不足,但其主观性、个性化的思想理念及叙述方式,正鲜明地体现了文、李两者在造园和赏园方面的不同意趣。这种不同是他们各自代表的群体以及各自所在时代的园林文化理念的差异*一些论著则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出各自的相似和相异点。如段建强《〈园冶〉与〈一家言·居室器玩部〉造园意象比较研究》对两文本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叙述结果加以系统分析,从而对两文本造园意象叙述所反映出的园林意象进行比较研究。任红兰《〈园冶〉与〈长物志〉造园思想比较研究》以两文本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作为研究切入点,对它们在结构、造园理念、手法、要素与意境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原因进行探讨,揭示园林文本现象之后的相关内涵。。两者反映了晚明至清初园林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并且代表了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园林审美话语权的归属又趋向于不同的状态。
一、器物和艺术:园林文化物质条件的双向发展
《长物志》全书十二卷,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每一卷都是针对与园林相关的器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它把园林文化的焦点落到具体的器物之上。而唐宋时代园林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大空间整体构图之美及自然山水诗画意境之美。这种变化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晚明以来工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人口向城市集中*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指出,道光《苏州府志》卷10说晚明的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亦即城市人口占到全府人口的十分之八九。虽然这个说法无疑有夸大之嫌,但城市人口在苏州府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高则是可以肯定的。苏州府本是明清江南城市化水平最高之处,而苏州地区(即吴、长、元三县)又是苏州府内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人均占有土地空间势必缩小,对优美居住环境的普遍追求促使“城市山林”蓬勃发展。据考证,明代苏州大小园林达260多处,府城范围内有80多处。[1]202这些园林的占地空间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其二,奢侈性消费的社会风尚促进手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制造业技术工艺水平大大提高,各种器物的技术、艺术含量增加。正如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提到的“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乎”[2]79。
《长物志》对器物的关注不仅投射在室内的收藏陈设品,且将房屋建筑同样看作一类器物,因而讲求整体的风格式样和局部的装饰纹理。与《长物志》同一时期,被后世奉为造园学经典的《园冶》,可谓是一部标准的教科书。全书系统地阐述了从选址、规划到选材、制作等造园的各个环节,可谓涵盖全面。虽没有以“器物”为纲,但是其中对器物的关注也非常具体深入,如对屋宇、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等部均有详细的文字描述和规范的图样,其中图样共计235幅。明后期以来园林文化的“器物关注”特征,凸显了园林中各种细部的线条、色彩、质感之美,以及丰富的文物储量和文化内涵之美。
虽然晚明园林艺术关注的焦点是器物,但是,这时的器物仍然具有较强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文物考古价值,而非纯粹是工具性的器物。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文化话语权的簪缨世族之审美情趣。这时的器物兼具工具实用和艺术审美的双重价值,两者仍没有发生明显的分离。审美的对象仍然是园林中实际存在物,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所有权关系。
在李渔《闲情偶寄》中,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该书仍以器物为纲,园林被分解为具体器物,如居室部被分为房舍、窗栏、墙壁、联匾、山石等章节,器玩部中的制度一章分别以几案、椅杌、床帐、橱柜、箱笼箧笥、骨董、炉瓶等十三种器物为节。但是,在此器物的实用主义绝对加强,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则显得次要。李渔所代表的阶层没有条件拥有奢侈品性质的器物,因而更加注重实用性。当社会上流行的园林生活与他们原来日常生活的界限逐渐消弭,实用主义与园林文化逐渐合流,以至于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都被纳入园林文化的范畴:
洒扫二事,势必相因,缺一不可,然亦有时以孤行为妙,是又不可不知。先洒后扫,言其常也,若旦旦如是,则土胶于水,积而不去,日厚一日,砖板受其虚名,而有土阶之实矣。[3]130
当于书室之旁,穴墙为孔,嵌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尝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3]131
《长物志》序中反映的“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4]10现象,虽然是在附会传统士大夫的风雅,但是庸奴钝汉所涉及的器物毕竟还是趋向于风雅,属于艺术鉴赏性质,园林还未沦为俚俗的事物。而《闲情偶寄》把园林也沦为俚俗日用之物。李渔表达的这种喜好趣味具有广大社会基础。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提到:
或进于养生名家,若明人万全之《养生四要》,明人高濂之《遵生八笺》,均系造福万民,声被九州。惟流俗间浅俚日用杂志,顺手参考之作,亦往往诸症杂备,方剂齐全。[5]72
《万宝全书》实为明清民众社会生活最真实最质切之参证宝典,全部代表明清下层社会之真实需要。以其太过鄙俚浅陋,甚至荒唐下流,淫乱肮脏,但却真正反映明清下民全面社会生活。[5]95
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一书也提到:
晚明时期,山人堕为以文艺射利之反面形象,陈继儒藉其文艺而“声华浮动,享高名食清福”行径类于山人且名倾朝野,盛极一时,令天下山人艳羡而竞相学习。影响之厌深恶极处,在四库馆臣看来,“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只需摘录“邻翁院僧谈接花艺果、种秫劚苓之语”即能获得声名利益,传统视作崇高神圣的著述立言被转换成牟利图名之器且轻松便宜。[6]34
可见,把鄙俚浅陋的日用事物纳入著书范围来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在明后期以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李渔的书中,艺术欣赏的对象或是失去了高雅的标准,或是变得飘忽不定,没有明确的所指。艺术欣赏无所不包,又无所存在。如在“书房壁”一节中:
先以酱色纸一层糊壁作底,后用豆绿云母笺,随手裂作零星小块,或方或扁,或短或长,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圆,随手贴于酱色纸上,每缝一条,必露出酱色纸一线,务令大小错杂,斜正参差,则贴成之后,满房皆冰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无一不成韵事。[3]148
李渔自以为是的艺术品,无非是籍以孤芳自赏的雕虫小技。这样的例子又如其“梅窗”之制,“外廓者,窗之四面,即上下两旁是也。若以整木为之,则向内者古朴可爱,而向外一面,屈曲不平,以之着墙”[3]143。
李渔以移动的目光和景框代替了固定的围墙,景观随借随用,而不是实际的拥有,如其在“取景在借”一节所言:
是船之左右,只有二便面,便面之外,无他物矣。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且又时时变幻,不为一定之形。非特舟行之际,摇一橹变一象,撑一篙换一景,即系缆时,风摇水动,亦刻刻异形。是一日之内,现出百千万幅佳山佳水,总以便面收之。[3]135
在此,园林作为艺术品,不再是实际拥有之物,代之以不固定的景观,趋向于彻底的虚无化。
李渔当然是别出新意,表示自己与世俗不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社会群体现象,绝非李渔独有。晚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渐渐增大,不乏旧贵族的家道中落,也不乏贩夫走卒混进士人行列。社会上存在很多文人高而不贵,孤芳自赏。他们精神追求很崇高,物质条件很匮乏,所以“虚无自恋”的艺术思想和文化潜意识就此产生。
明末汤传楹自称“荒荒斋”为“予所居书斋,仅容膝地,屋宇卑朴,墙垣窗户,都无雕垩,其中所有,止古今书数卷及笔砚一二事。……苦逼窄,不能植此君,亦不能杂植嘉树,砌上惟牡丹数种,其旁丛桂四株,大不逾檐,杂花几色,点缀曲槛”[7]73-74。而与李渔多有来往之剧作家尤侗,所居“亦园”,他自称“亦园隙地耳,问有楼阁乎?曰无有;有廊榭乎?曰无有;有层峦怪石乎?曰无有;无则何为乎园?园之东南岿然独峙者,有亭焉,问有窗棂栏槛乎?曰无有;有帘幕几席乎?曰无有。无则何为乎亭?曰:凡吾之园与亭,皆以无为贵者也”[8]81。言语中表现出一种自我满足的神态。此时的园林艺术不是构建在园主拥有的物质条件之上,而是构建在自我满足自我排遣的主观感受之上。因此,《长物志》反映的园林文化特征是基于对器物关注的审美意识,器物与艺术仍紧密结合。而到了《闲情偶寄》阶段,园林文化特征发展为:一方面园林中器物的实用主义意识强化,另一方面园林艺术与实际拥有的物质条件相分离。
二、总结和创新:园林文化发展的必经阶段与必然要求
晚明市民阶层兴起和文化普及潮流,使得原来作为士大夫阶层文化生活专利的园林已经发生了质的逆转,园林文化趋向于浮泛化。《吴风录》记载的“虽闾阎小户,亦饰小山盆岛为玩”之说,说明园林门槛之低,数量必定剧增,正如前文所举的“荒荒斋”、“亦园”之流。另一方面,出现在社会上的各种新时尚遭到《长物志》批评,说明园林器物的审美标准也出现了分化,正如“近更有以大块辰砂,石青,石绿,为研山、盆石,最俗”[4]110;“忌穴窗为橱,忌以瓦为墙,有作金钱梅花式者,此俱当付之一击”[4]37。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园林文化新旧时代的交替。在此转折时期产生的《长物志》是一本兼具批判和推崇意识的著作,它把传统和时兴、高雅和流俗划分成两大界限鲜明的阵营,而把著书人归入传统和高雅的一方。对时兴和流俗的一方,给予了无情的重击,如“时尚以列几案间者为第一,列庭榭中者次之,余持论反是。最古者以天目松为第一,高不过二尺,短不过尺许,其本如臂,其针如簇……若如时尚作沉香片者,甚无谓。盖木片生花,有何趣味?真所谓以‘耳食’者矣”[4]97。文震亨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对传统和时俗进行褒贬之时,实际上是对两种风尚和流派的全面总结。从时间的长度来考察,《长物志》所表达的艺术品鉴的思想和知识不仅限于文震亨在世的时段,也不止于明代,而是可以回溯到宋、唐,甚至更远。后人评价《长物志》为:“玉敦珠盘,辉映坛砧,若启美此书,亦庶几卓卓可传者。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4]423因此,《长物志》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总结性的必然结果。
然而到了李渔的时代,适应新型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园林文化本身发展将走向何方?如果要撰写一本园林文化专著又该如何定位?对李渔而言,无论是赞成文震亨,还是赞成文氏批判的对象,都没有新的著述价值。
实际上李渔对文震亨抱有一种隐含的对立情绪。从《闲情偶寄》来看,李渔很有可能堕入被文震亨所诟病的庸奴钝汉的行列。如在“书房壁”一节中,他提出“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3]149。这一点正与《长物志》的“忌穴窗为橱”相对立。在“厅壁”一节中,他提出“乃于厅房四壁,倩四名手,尽写着色花树,而绕以云烟。即以所爱禽鸟,蓄于虬枝老干之上”[3]146,却与《长物志》的“忌墙角画各色花鸟。古人最重题壁,今即使顾陆点染、钟王濡笔,俱不如素壁”[4]36相对立。按照文震亨的标准,李渔的技法简直俗不可耐。
李渔虽然没有对《长物志》及文震亨进行点名批判,但是在《闲情偶寄》中所表述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对《长物志》的否定。例如其对古董收藏鉴玩持不赞成态度,这一点与文震亨的尚古是相反的。美国学者韩南对李渔的观点归纳为:
1.人们崇尚古物,导致昂贵价格。2.那些买古董者宣称,与其说他们看重古董,不如说看古董时他们感到自己在古人面前。3.如果古人自己至今犹在,世人谁会愿意以如此昂贵的价格来买古董带回家。[9]177
此外,其反《长物志》的一面还表现为:
常见通侯贵戚,掷盈千累万之资以治园圃,必先谕大匠曰:亭则法某人之制,榭则遵谁氏之规,勿使稍异。而操运斤之权者,至大厦告成,必骄语居功,谓其立户开窗,安廊置阁,事事皆仿名园,纤毫不谬。噫!陋矣。[3]125
这段文字表达的反对模仿名人之制的态度,与文震亨尊崇古制的观念正好相反。如文氏所言“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4]18,“又鸱吻好望,其名最古,今所用者,不知何物,须如古式为之,不则亦仿画中室宇之制”[4]37等语已经表达了其追摹古人的倾向。李渔尽管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文震亨及其著作,但其出于内心的不满而讥讽也是极有可能的。另外,《园冶》产生于《长物志》相同的年代,由于作者计成与阮大铖的交往经历,使得该书长期被封杀。《长物志》作为正统文化形象代表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园冶》,但在李渔的书中提到“其制穷奇极巧,如《园冶》所载诸式,殆无遗义矣”[3]146,却绝口没有提到《长物志》。
李渔既与文震亨对立,又不愿入庸奴钝汉之列,那就必须要创新。所以,从《长物志》到《闲情偶寄》是一个前后联系的从总结到创新的过程。而李渔又在书中极力标榜自己的创新,如“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3]125,所以“一榱一桷,必令出自己裁,使经其地入其室者,如读湖上笠翁之书,虽乏高才,颇饶别致”[3]125。园林文化从对整体意境的追求,从对大场景构图的艺术表现力的追求,发展到对微观的个体器物艺术魅力、历史文化价值、工艺品质的追求,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了。再往下又该如何创新?李渔种种别出心裁的技巧,实际是在时俗的大方向上开辟了一条新路,是一种反奢华的时俗,其特征就是园林走向适应大众的俚俗化,并且以夸张、新奇、有趣来界定园林艺术新成就。另一方面,晚明以来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出版业也趋向于高度商业化*李伯重在《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一文指出:“明代中期以后,以牟利为目的、面向广大中下层社会民众的商业化出版印刷业日益发展,到了清代则已成为江南出版印刷业的主流。”。李渔著书的最终目的是吸引更多读者,必须绞尽脑汁销售著作,于是就通过另类思维和反向思维的方法求新奇求卖点。所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园林文化作为一种出版题材必须要创新。
三、逆流和分流:园林审美话语争权和分权
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正是新兴社会阶层逐渐分取文化话语权的时代。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文化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时尚开始崭露头角。尽管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对新事物的出现秉持着激进的批判态度,似乎相对于时俗表现的是复古主义倾向,但是,如果对其观念做一番仔细深入的咀嚼,则发现复古主义不能准确地定义其思想的本质。复古只是一种汹涌逆袭的表象,而非文震亨等人表达的最终极的意图。因为文震亨并没有一味地好古,如“(榻)他如花楠、紫檀、乌木、花梨,照旧式制成,俱可用,一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俱落俗套”[4]226。此榻既是仿古的,又是实用的,而且还是美观的,只是有所改动,就被指为俗。此外,关于“元制榻”,《长物志》也认为其“其制亦古,然今却不适用”[4]226。
另外,古和今也没有固定的区分标准,对古物的拥有也没有法律限制。如果文氏所指责的庸奴拥有了文氏所称赞的古物,他又将何以面对?以文氏所贬斥的各种器物款式,以今天看来也别具古典之美。他所褒贬的旧和新的款式,除了产生年代的不同,器物本身又有何实质的区别,实际上,古典主义何尝不也是一种时尚?古和今无疑存在相对关系。以今天看来,不管是宋式、元式还是明式,无一不为古物,无一不具有古典主义的美感。而在晚明文震亨的时代,只有宋式、元式才算是古典式样。如果不是当时各种新式样产生,在新兴社会阶层的簇拥下,进入园林艺术生活的领域成为一种新时尚,谁又反向推崇古典主义?文震亨所推崇的这些古典式样,只有在社会新兴阶层所追求的时尚兴起之时,才被作为古典来关注。辩证地思考,守旧、复古在此时无非也是一种时尚。
文震亨在《长物志》书中不是单纯地对园林艺术进行客观品评,而是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文震亨所代表的传统贵族阶层,具有拥有和鉴别“古”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知识技术的能力和经济能力。当对身份的限制失去法律的依据,能力就成为一道无形的门槛。这种好古的表达,实际上以自己既有的能力凌驾于别人能力缺失之上,以此捍卫旧阶层在社会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如果新兴阶层掌握了对“古”的拥有能力,文震亨等辈又将奈何?文震亨的崇古主义实际是一种自我主义、本位主义,反映了旧阶层强烈的壁垒意识。其文化主张是不接受不认可新阶层创造的新事物,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因而,可以把文震亨代表的流派定义为园林文化的逆流。
明清之际,“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工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勃兴,市民园林亦随之而兴盛起来。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浸润于私家的园林艺术,又出现文人园林的多种变体,反映了创作上雅与俗的抗衡和交融”[10]330。文震亨的时代,雅俗的抗衡关系总体胜于交融趋势。而到了李渔的时代,旧的崇尚仍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新时尚不可逆转地成为既成事实,而且异彩纷呈,雅俗交融显然胜于抗衡。李渔的主张不能够被归入任何一方,他既反对文氏的守旧,又不和社会时俗同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他高举着创新的旗幡,自我认为独创一派。虽然李渔的书中也有批判性的话语,正如其反对模仿名人之制,只是没有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表现得如此尖锐而喋喋不休。他不推崇奢华,但也不与奢华对立,尽管在书中提出“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3]126。但是,他和拙政园主王永宁有交游往来,并且为王作词题为《花心动·王长安席上观女乐》[11]484,而王永宁占据时期的拙政园是相当奢华富丽的。总体而言,李渔的态度是自由而随意的,正如其在卷首凡例中所言著作的目的:
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名曰《闲情偶寄》者,虑人目为庄论而避之也。劝惩之语,下半居多,前数帙俱谈风雅。正论不载于始而丽于终者,冀人由雅及庄,渐入渐深,而不觉其可畏也。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谓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也。实具婆心,非同客语,正人奇士,当共谅之。[3]2
如果说文震亨代表的流派是一股社会时尚的逆流,而李渔的流派则是一股分流。这一点反映了园林审美话语权归属状态的变化,即从《长物志》问世以前的一元独霸,到《长物志》前后时期的二元抗衡,再到《闲情偶寄》时期的多元并存。
从《长物志》到《闲情偶寄》,反映了晚明至清初这一时段中园林文化呈现出从器物的艺术性关注到器物实用主义强化的发展特征,前者表现为园林艺术与器物的结合,后者一方面表现出园林文化趋向俚俗日用化,另一方面表现出主观意识中园林艺术与物质所有权分离。从社会现实条件而言,这是由市民阶层兴起、文化意识普及和身份壁垒打破推动的。从文化艺术本身的创新需求和文化主体的商业追求来看,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又是对园林文化进行总结到再创新的必然过程。同时,随着新旧阶层地位的消长变化,不同的社会群体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园林审美话语权的纷争必然从二元抗衡走向多元并存的态势。
[1]魏嘉瓒.苏州古典园林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明]张瀚.松窗梦语[M]//元明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清]李渔.闲情偶寄[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明]文震亨.长物志校注[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5]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7][明]汤传楹.荒荒斋记并铭[M]//王稼句.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8][清]尤侗.揖青亭记[M]//王稼句.苏州园林历代文钞.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9][美]韩南.创造李渔[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0]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11]李渔全集: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周继红)
2014-09-01
施春煜,男,苏州市世界文化遗产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监测部部长,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及监测研究。
TU986
A
1672-0695(2015)03-005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