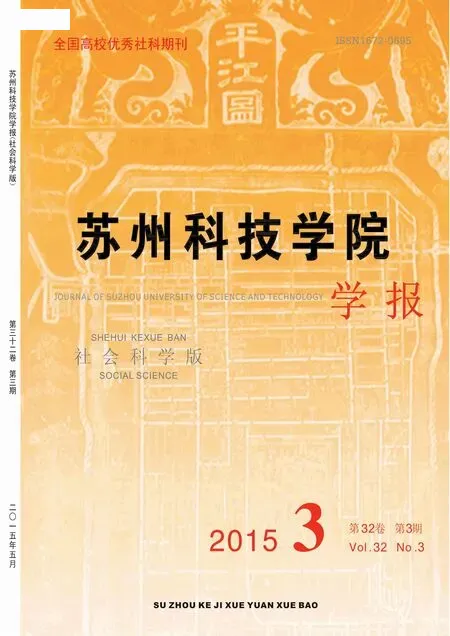《光绪会典》纂修研究*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潮州 521041)
《光绪会典》纂修研究*
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 历史系,广东 潮州 521041)
光绪会典纂修是在清代史馆制度转型时期出现的。晚清财政吃紧,光绪会典馆经费因此受到一定影响。将光绪会典置于晚清典志体史书勃兴的大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光绪会典的人员选拔有多种方式, 其选人标准在于馆部联贯和精通地理、善绘舆图,体现了“用人宜变通”原则,由此网罗了一批俊彦、硕儒从事会典编纂。光绪会典馆也无法避免清代史馆的弊端,出现了滥保、争夺提调和总纂权等问题,会典馆内部围绕是否设图上提调、会典编纂中的奖叙等问题产生激烈的争议和冲突。
私人文献;光绪会典;人员选拔;人事纠葛;提调职责
光绪会典纂修囊括光绪时期通晓典制的俊彦,修撰成卷帧繁富、包举数朝之大典。目前,关于光绪会典的研究,主要有柳诒徵和王一帆两人。柳诒徵的《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开启端绪,主要论述了光绪会典馆的人员构成和组织。王一帆的《清末地理大测绘:以光绪〈会典舆图〉为中心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会典馆画图处的用人机制和奖惩制度,对会典舆图发覆甚详。上述两人都注意到私人文献的重要性,但因研究视角、研究史料的问题,对光绪会典的章程、体例、会典馆人员的选择方式、会典馆内部人员的纠葛以及会典提调的职责等没有详细地分析和阐释。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上述四个问题做较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以期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即光绪会典编纂在体例和内容方面有创新和改造,在编纂过程中尽管出现人员的倾轧和矛盾,但因为有相对健全的机制,光绪会典在体例、内容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一、清代史馆的特点
清代史馆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指出,“清代史馆的形式增加,有常开、例开、阅时而开以及特开四种形式”[1]5,并“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和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2]。清代常开史馆主要包括国史馆、起居注馆、方略馆等,其编纂的内容需定期进行,在清代史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开史馆包括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律例馆等,援例而设,定期开馆,书成馆撤;阅时而开的史馆有会典馆、一通志馆等,根据具体情况开设,主要编纂具有接续性的典志体史书;特开史馆是为了修纂某部史书而专门开设的史馆,每修一书,必开一馆,书成馆闭,不再重开。清代诸种史馆都需秉承皇帝的意志来设馆修史,皇帝对于修史人员、史书的体例内容,史书的叙次和论述等都会亲自审定与裁决,以全面直接地干预修史的全过程。如乾隆时修纂《大清会典》,皇帝对于体例确定和人员安排都有明确的谕旨。乾隆还认为宗人府系宗室衙门,应独立于文武衙门之外,此次纂修《会典》,即将宗人府另列一卷居首,其文职衙门从内阁开始以次排列。康熙、雍正《会典》载大学士员缺无定,此次纂修,俱照定员载入等等[3],均涉及人员安排和体例问题。除此之外,对稿本的呈奏也有皇帝亲自加以裁决:乾隆十二年,修纂《大清会典》,清高宗又明确提出将稿本缮成一二卷即行陆续呈奏,“朕敕几多暇,将亲为讨论,冀免传疑而袭谬,且毋玩日以旷时”[4]28。
其次,在史馆的任职制度上,满、汉、蒙人员需要按一定的比例遴选,保证满人在修史过程中的特权。清代史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2]光绪会典纂修人员,正总裁官崑冈等四人(其中崑冈和刚毅为满人,徐桐和孙家鼐为汉人),副总裁官六人(其中熙敬、启秀、裕德为满人,廖寿恒、徐郙、徐用仪为汉人),提调官三人(那桐、贵秀为满人,刘永亨为汉人),帮提调官六人,汉文总校官兼汉总纂官四人,汉文总校官八人,帮总纂官二人,纂修官七人,前充协修官三十一人,详校官十四人,校对官四十二人,收掌官十六人,前充正总裁官至阿充校对官等各类人员共八十一人。[5]38-45以会典修纂人员的记述来看,柳诒徵所记载的光绪朝修纂《大清会典》所用员额是不确的:总裁,满、汉各二人;副总裁,满四人,汉二人;提调官,满二人,汉一人;总纂官,满、汉各四人;纂修官,满十九人,汉二十二人[6]586。可见,满人在高层握有史馆的管理权,是与满族所确定的选官制度有关,但在会典纂修过程中,真正发挥修史才能的还是汉人的总纂官、纂修官。总体而言,满人在史馆高层管理人员要超过汉人,但在实际从事会典修纂的总纂、纂修官、详校官中,汉人的比例要远超满人。清代虽竭力提高满人在修史中的特权,希翼将修史大权牢牢控制在满洲统治者手里,来为满族入主中原提供正统性。但因为满人并不擅长纂修官修史书,所以不得不延聘汉人作为总纂官、纂修官以实际从事修纂。清廷本希望藉此提高满人的史学修养,促进满汉的文化交融,但在修史的过程中,实际出力的汉人会因为在史馆修史中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心生怨谤,造成满股与汉股之间的矛盾。后文中所出现的满汉在奖叙环节的矛盾就是一个鲜明的注脚。
再次,在史馆组建程序上,一般是由皇帝特命,或大臣提出,奏明皇上,并拟定组成史馆之各级史官的名单,由皇上钦定。一般总裁、副总裁由皇上亲自指定,其他人员则由总裁、副总裁等一起拟定。总裁、副总裁确定后,由他们遴选纂修人员名额,再行文翰林院及各部院衙门,按照所修官书的性质选择相关人员,比如方略主要由军机处选择相关人员,实录和国史主要由翰林院承担,会典、则例主要由翰林院和各部“学问淹博,熟谙掌故之员”来承担纂修。作为钦命的官修史书,清代史馆有一整套严格的运作程序,以此来保障皇权的贯彻。然自鸦片战争以后,清廷因为赔款和太平天国起义等,财政日趋吃紧,史馆经费也因此受到影响。比如1886年(光绪十四年),会典馆纂修光绪会典,吏部无款可筹,不得不催湖北巡抚奎斌,措解二千两白银以应付开馆之需。1887年,因汇集档案资料也着刑部催各省交清旧欠饭食银两,结果湖北一分未交。[7]387。政治上需要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经济上又捉襟见肘,所以,总体上看,近代史馆修史成就很难与乾隆时期兴旺的官修史书相媲美。但近代官修史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比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再比如各部院则例、事例的编纂等,如果从典志体史书编纂的角度而言,晚清官修典志体史书应该比清初的康熙朝、雍正朝在数量方面要多,比乾隆时期要稍逊一筹。
二、《光绪会典》修史人员选择的途径和特点
光绪会典在人员选择方面,主要由清廷高层按成例在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詹事等官员中拣选总裁、副总裁、提调,再有总裁、副总裁通过保举、会典馆向地方咨文调取人员、考试录用等方式选拔总纂官、纂修官、协修官、誊录等。光绪会典馆设总裁、副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若干。正总裁官崑冈、徐桐、刚毅、孙家鼐,副总裁官熙敬、启秀等凡六人,由皇帝亲自拣选任命。有关人员选择,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李鸿章等奏:
开馆修书,总裁领其纲,纂修分其目。此次续修《会典》,除总裁官应遵照旧例,于大学士、尚书内简派满、汉总裁四员,侍郎、学士、詹事等官内简派满、汉副总裁七员外,至各馆纂修官,向用内阁翰、詹人员,会典事备诸曹,自应兼用部属,臣等谨仿上届事例,满纂修拟用内阁四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理藩院各二员。汉纂修拟用内阁三员,翰、詹二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二员,共三十六员。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各该堂官务择学问淹贯、熟习掌故,而且识见通敏、行走勤慎之员,保选充当。如到馆后不称厥职,许总裁官驳回另换。再此次额设纂修,倘不敷用,令总裁官再于各衙门咨取协修数员,帮同办理。纂修缺出,即以本衙门协修补本衙门之缺,庶群雄策群力之勤,以收日计月计之效。[5]28
会典馆纂修官与其它清代史馆相比,具有自身的特色。会典主要以记述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典章制度的流变,故会典馆总纂、帮总纂、纂修官一改其它史馆以词臣为主修纂史书,而以吏、户、礼、兵、刑、工诸部署官员为主,翰詹官员为辅。比如光绪会典的总纂官为翰林院编修刘启瑞、夏孙桐,帮总纂官、纂修官,除翰林院编修叶昌炽外其它全部由内阁中书、部院司员、京堂及个别御史充任[5]37-53,这充分反映了清代史馆以内行修史的指导思想。
会典馆拣选人才,除清廷直接任命总裁、副总裁外,还采用会典馆向地方咨文调取人员,网罗相关人才纂修会典,如画图誊录由会典馆寻访,除之前章程拟定由同文馆选取外,还准备从钦天监、南北洋及各省咨调,“会典馆为咨行事照得:本馆创办画图事宜,前经奏定选带同文馆学生四员来充画图誊录,如同文馆学生功测绘者出不敷调用,即由本馆行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在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及船政机器局各局教习学生中口谨精择二三人,送馆同充画图誊录……相应咨行贵督部营、将军、衙门、部院,查照前文速即拣派精于测绘学生数名咨送到馆,以便办理测绘”[8]473-475。再如,要求调取“在籍前云南弥勒县、平彝县黄楙材”,称该员“精通舆地测绘之学,堪充图上协修官”[8]476-477。从会典馆总纂、纂修的人选来看,会典馆人员选派标准与黄国瑾提出“绘图必精测算地理,尤号专家;宜速访精绘舆图者二、三人,精地理者一、二人,不拘中外大小官职,务在得人”的建议基本一致。傅云龙仅为监生,他的入选同样符合上述标准,正因为会典馆不拘官职大小擢升傅云龙,还引来缪佑孙的讥刺:“傅茂元居然亦纂修也。”[9]676但会典馆以其曾经出洋游历十一国,行程十二万里,历时两年,写出了各国《游历图经》、《游历图经馀记》达百万字,得到“坚忍耐劳,于外洋情形考究尤为详确”的批语,所以被吸收为会典馆的纂修官,可以说是突破资历限制的有益尝试。傅茂元入画图处,纂顺天府总图、分图,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上述破格挑选人才的方式,完全契合会典馆章程中所确定的“用人宜变通”原则,即“如访闻各部院人员,真有精通礼制、武备、天文、地理之学未派入馆者,亦可由馆咨取”[10]2689-2699。
同时,考试录用也是会典馆选取人才的重要方式。会典舆图编纂,需要丰富的史料和大量的测绘舆图,对于舆图的整理、编绘,需要精于地理而又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员、士人,所以有必要通过考试的方式招收誊录生从事这项工作。会典馆招考画图誊录的程序即为,“先于户部报名,定期到会典馆考试,题目为测绘、画图两道。”黄国瑾即为会典馆招收誊录生出过试题:“馆中招考画图暨誊录生,每人需各授一题,该故编修详为拟题,自园象、方舆以及礼制、乐律诸大端,分门别类,至百余道之多。”[10]854黄国瑾拟定的试题主要考察地理学和典章制度,这与会典的特色相吻合。
因为上书会典馆,提出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而被会典馆高层赏识,擢升为会典馆纂修官,也是会典馆网罗人才的方式之一。如湖南新化人邹代钧1890年直接向会典馆上书,影响了后来整个会典舆图的测绘进程。邹代钧在给会典馆的上书中提出以西方的舆图测绘方法来改进会典舆图的测绘技术,并进一步申述融合中西测绘方法的重要性:“兹际续修会典,于舆图一门欲加详考,已催各直省绘省、府、厅、州、县之分图,限期送馆,以凭入绘,是诚当今盛举。泰山不让土壤,江河不让细流,所以成其大也。方今六合仰风,万方效用,彼有所长,何妨择取!谨括西人之法合乎吾华古法者敬为陈之。”[11]15-17邹代钧向会典馆上书融合中西测绘技术的主张,与会典馆画图处高层融合中西绘图的方略相契合,故受到会典馆的激赏,并 “被当轴采纳,奏充会典馆纂修官”[12]656-697。
光绪会典的人员拣选方式,应该说既有优点,也有明显的不足,正如柳诒徵所评论的,“其可嗤者,在满汉衡齐;其可取者,在馆部联贯。行走期其克勤,兼差俨有实缺,既可广罗英彦,复不浪费俸廉”[6]530。其优点表现在:选拔渠道多元,重视选择各部“学问淹博,熟谙掌故之员”从事纂修,充分发挥内行修史的功用。其缺点在于满汉一体,满人高踞史馆的管理权,却在实际修史中并不能发挥作用,而在修史成书后又与汉人争夺奖叙的权益,即柳氏解释的致使会典人员选拔缺点的一个侧面。其缺点还表现在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亲自任命,而这些人本身还兼着内阁、六部的官差,所以实心投入馆务的并不多,再遇到总纂不负责任则会对会典的编纂产生不好的影响。比如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关于《光绪会典事例》纂修的亲身经历所揭示的:“京师史馆林立,余无分与修史事。时《会典》适开馆,余充协修之职,盖吏部一门,须由吏部司员起草也。余分得稽勋司三卷,原本尚多罅漏,随意修饰,数日即交卷。同时部中无好手笔,意馆中总纂必有一番斟酌也。谁知依样葫芦,而全书成矣。余且得升阶保案焉。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13]P95何氏的这番评论不无偏激之处,而且查光绪会典的《稽勋司》,也并非三卷,但其所述光绪会典人员流弊还是能反映会典纂修过程中的一些实际情况。
三、会典馆人事纠葛与冲突
会典馆人员选聘机制确实选拔了一批精通地理和典章制度的人才,如黄国瑾、蒯光典、王鹏运、朱祖谋、黄绍箕、秦树声、邹代钧、黄楙材等,但因为会典馆待遇的优厚和修书过程中及成书后的赏叙机制,促使官员和士人攀交总裁、副总裁以求得馆差,作为个人进身之阶的重要渠道。如那桐因为在部补缺无期,也借机攀交翁同龢,希望谋取会典馆差。翁同龢对此有记载:“丙戌(1886年)十月初四日,那琴轩桐来回事,兼求派馆差,伊选缺主事,补缺无期也。”[14]2054翁同龢还记载了刘启瑞的女婿国子监主簿王承洛曾向他求绘图差[14]2690,后任画图处校对官。
除滥保外,会典馆因为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围绕是否设图上提调、争夺提调、总纂权、会典编纂中的奖叙等问题,会典馆内部产生激烈的冲突和争议,其中既有利益的纠葛,也有人事、权力的摩擦。面对权力的诱惑,是念位、念权,还是从史馆修史的大局出发,不同的举措折射出会典馆的人事生态。1889年会典馆设立画图处,当时总裁徐桐等意欲设立图上提调官,并属意于黄国瑾,由其担任图上提调。清代史馆,提调综管人事、财务、馆务等,握有实权,故最为史馆官员所看重。所以,当总裁徐桐等意欲设立图上提调官时,会典馆不少史官意欲据为己有。为此,黄国瑾给总裁徐桐上书坚辞提调一职:“昨因礼卿(蒯光典)让图上总纂,诣辞。承吾师(徐桐)允所请,顷见仲强、梦华与礼卿书,并有图上须添提调之说,意欲请于总裁稗国瑾为之,且闻礼卿己略言于吾师,盖见此番协议。幸荷各总裁主持得以上请也。然果有此是,使国瑾心迹不明。”黄国瑾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凡所经营皆自为谋,蜘蛛结网、鸠雀争巢,岂非壮夫所深耻哉”[15]267。黄国瑾认为,优秀的史官不应该“鸠雀争巢”,念位、念权,此其一;另外,会典馆已有三个提调, 而且三提调运转比较顺畅的局面也不宜打破,再设图上提调叠床架屋,权责不清,不利于会典馆绘图处的有效运转,故从会典馆的修史大局出发,不宜再设图上提调,“前请冠以顺德总纂(李文田,字畲光,号若农,广东顺德人),而殿以三提调,并言明图上毋庸另派提调者,凡国瑾书上功课,皆顺德功课,图上筹度皆三提调筹度。何也?不掣肘也。使有龃龉,安能尽力乎?”[15]268并言明“凡国瑾书上功课,皆顺德功课,图上筹度皆三提调筹度”,不仅不恋图上提调的实权,而且将自己的功课和筹度算作他人的功课和筹度,反映了黄国瑾高尚的史德和博大的胸襟。
然而,会典馆其它诸人却对提调和总纂职位奔走角逐,意欲窃据而后快。叶昌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任会典馆纂修,十月为史馆提调。《缘督庐日记》所记会典馆人事纠葛甚详。叶昌炽即提到文廷式为角逐提调职位,与当时的总裁、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有抵牾,“丙申(1896年)正月二十七日,晨往会典馆,见庆椿卿前辈,知道希 (文廷式) 因争提调,与掌院有违言,甚可笑也”[16]125。文廷式与何人争提调,《缘督庐日记》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文廷式本人的日记体笔记也没有言及,但文氏最终并没有得到提调一职确是事实。不仅如此,总纂一职也能招致会典馆人员内部的不满与怨叹。1890年2月,缪佑孙在寄给其堂兄缪荃孙的信中,对会典馆画图处拟议人员深致不满,“会典绘图尚未开办,而议论纷纭,爽秋(袁昶)以不得总纂甚怪子培(沈曾植)得总纂,冯熙、刘岳云皆纂修,傅茂元(傅云龙)居然亦纂修”[16]246。表面上看,袁昶对沈曾植将要任会典馆画图处总纂一职不满,但透过文本背后所隐喻的含义,不难梳理出缪佑孙本人酸葡萄的心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会典馆画图处的人事安排颇有怨言。1898年6月,因东阁大学士、会典馆总裁崑冈偏私,总纂一职欲以许泽新充任,引起叶昌炽愤懑、不满,“三日得崑中堂师书,少嵩所遗总纂一缺,欲以许颖初前辈充补,纂修中功课有逾千闲者,颖初从不到馆,乃越次请补,如子丹何?如众议何?馆差非钻营不可得,惟史馆尚存公道,若再开此幸门,则此后尚复有人当差乎?”[16]129叶昌炽不满于许泽新“从不到馆”,功课上不出力,却要在总裁的荫庇下充任会典馆总纂,如此投机附会是对会典馆修史章程的严重践踏,作为会典馆提调的叶昌炽不徇情面,敢于抵制总裁的违规任命值得称道,事实上许泽新并没有列名于会典馆职官总纂、纂修人员中。
会典馆人事纠葛最盛、矛盾最为集中的环节当数会典书成后的奖叙环节,其中牵涉总裁和提调的关系、满股和汉股的关系等。叶昌炽对光绪会典修成后的议叙过程记述详尽,对于会典馆人事纷争分析透彻。1898年12月,“至馆,徐工供事呈杨卓林请优保名条,云崑中堂所交。前因违例送馆,子丹 (杜彤,字子丹,号仰兹。直隶天津人。清光绪时翰林院编修。)几于麟文慎(前充正总裁官麟书)决裂,亦此君也;欲痛惩之,则投鼠忌器,词臣本称清秩,乃至奔走伺候,受人牵掣,垂暮之年,若敖之鬼,又何所图而为此?”[16]255透过引文文本,可知作为首席正总裁崑冈欲违例优保杨卓林,引起提调叶昌炽的不满,总裁和提调的关系颇为微妙,叶昌炽投鼠忌器,但又不能不坚持原则,违例滥保。故1899年1月,叶昌炽谒崑冈,“辞未见。命门人传语,告以杨卓林画一传,未派覆校,此次进书碍难列保。又呈奏议官单,大拂师意,云奏议覆校,既经徐中堂派出十六员,无庸与闻。旋又云,欲添派一二人,可否告以此事,本总裁为政,即添派三四人亦惟中堂所命,复派出蔚若及许颖初前辈。此两人开单本为昆师而设,此次藉以解围”[16]255-256。由此可知,叶昌炽与崑冈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叶昌炽谒见崑冈,吃了闭门羹。作为宗室的崑冈,以权力干预会典的奖叙,遭致坚持原则的叶昌炽抵制,非常恼火,足见其人史品之低下。
满股和汉股如何平衡,怎样保举才能体现相对公平的原则,这也是摆在提调面前很重要的问题。1899年1月,“与嵩珊同列馆,子实、寿芝两君来,深以满股人多为患,又雅不欲核减。属于襄平处缓颊,姑应之。日昳,偕松珊谒襄平,云前届汉员自提调至校对,列保十八人。此次卷数较多,自可推广,而亦不能过于冒滥,各人请奖官阶,如经吏部议驳不准,另请核奖,告以师意。既在核实,不如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师深以为然”[16]258。叶昌炽提出保举的办法,仿上届会典告成的办法适当增加名额,但必须“先交吏部核定,其不合例者去之”,防止滥保。正因为叶昌炽在奖叙中坚持原则,开罪了满股的当权者,所以他们造谣说叶昌炽办事不公,收人钱财,此事甚至牵连到总裁徐桐。1899年1月,“午刻到馆,见嵩珊。满提调英、灵二君旋来,出示匿名揭帖一纸,云粘徐相师门墙,大致谓提调叶办事不公,与供事头徐雨门,得银三万,实官加衔,皆有价。并云徐中堂难保不分钱,其词似谣非谣”[16]258。由此可知,在会典保举中,满汉矛盾之尖锐。叶昌炽忠于职守,却难防小人之暗箭,故叶昌炽在剖白自己的心迹时说:“鄙人办理此案,意在综核名实,任劳任怨,屏绝请托。虽崑中堂师所交名条,亦均婉谢,乃竟遭此不白之诬,真暗无天日矣。嚼齿穿龈,夜睡耿耿达旦。”[16]259后此事经灵寿芝、满提调英、灵二君的调停、斡旋,矛盾稍解。
四、《那桐日记》所反映的提调职责
会典馆人员配备与职责分工非常细致,各有专责,这在会典馆规条中都有细致的规定。关于会典馆总裁、副总裁和纂修人员,柳诒徵在《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详见柳诒徵:《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1947年第1卷第9期。一文中,有详细的梳理和阐析,兹不续貂。笔者主要就柳氏文章中分析较为薄弱的提调,结合《那桐日记》,对其职掌作有条理的分析和阐释。提调,提举调度的意思。晚清常开、例开史馆一般都设有提调一职,其官阶虽低于总裁、副总裁,但在史馆握有实权,综管人事、财务、馆务等,凡调拨馆内人员,督催功课,文书往来,以及人事、经费、业务等诸事,皆由提调处理。所谓“提调掌章奏文移,治其吏役”[17],“凡一切往来文移咨查事宜及考核各员功课,实为提调官专责”。会典馆提调职掌也是如此,主要负责调拨馆内人员,督催功课,文书往来,以及人事、经费、业务等诸事。上引会典馆提调叶昌炽主要记录了会典馆议叙、保举方面的人事纠葛,还不足以涵括会典馆提调的主要职责,《那桐日记》为我们详尽地梳理会典馆提调的职责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协商馆务。那桐上任伊始,即与会典馆副总裁、众收掌、供事、茶役相见,正式履职。“十二日,未刻到会典馆到提调任,大堂上香行三跪九叩礼,众收掌、供事、茶役谒见,与伯珊(贵恒,会典馆原任副总裁)、博泉(刘恩溥)谈半时,酉初散。拜恭邸、启(启秀)、裕(裕德)、昆(崑冈)三位总裁(其时为副总裁)。”“十五日辰初到馆,上香、行礼、办事,与刚总裁(刚毅)谈时许,同贵伯珊(贵恒)、刘博泉(刘恩溥)同饭,未正归。”[18]244-2451897年6月25日,“辰刻到会典馆,延太守(宗室延煦,前充副总裁)到馆,谈时许,饭后未正散”。1897年7月,“巳初到馆办事,未刻归。未刻到麟中堂宅回会典馆事。辰刻到会典馆,同何闰甫回麟中堂馆事”。以上数条,主要记载那桐与会典馆总裁、副总裁协商馆务。1897年9月5日,“午刻到会典馆办事。未刻进署办事。未正一刻,东华门内三座门迤北恭亲王公所不戒于火,延烧房间。余在署,闻信即往会典馆救护,幸书籍、档案均已挪移,并未损失,房间亦未拆毁。各堂陆续到馆,赶办奏折,具报并未损失各情,明日具奏,酉刻散。到清阶平处出分,子正归”[18]253。11月,“卯刻进内,同罗质庵、裕郅臣回会典馆画图处事”[18]260。“十八日约刘博泉、何润夫、罗质庵、贵伯珊、德云舫、倭昆峰、裕郅臣早饭,议馆中公事,酉刻散。”
(2)综理会典馆财务。光绪会典纂修财务收支主要由文移处、收掌处经手,会典提调负责审理财务收支。那桐因为提调财务方面的成绩,为会典馆节省银两六万,而被圣谕奖励,这在晚清史馆中也是少见的,表明那桐在会典财务方面还是取得较显著的成绩。会典纂修需要大量的绸缎,所以向广源缎店订购,“申后广源缎店温寿臣来交延敬臣馆款二千二百一十两,结算清楚,照录节略,呈回总裁后交文移处存查”[18]246。1897年7月,那桐接任会典馆提调不久,会典馆需缎条足银五万四千八十两,可见会典纂修需要物资量较大,“敬臣支销清单一件(支一万六百两,缴还二千二百十两清充)、采办广源缎店缎条等件合同一件(共需足银五万四千八十两),均蒙标画日期。谕云:照办。拟明日到馆交文移处存案,申初归”[18]247。1899年10月,“会典馆总裁代奏办书,余存银两缴还部库。奉旨:提调官鸿胪寺卿那桐等奉公洁己,办事认真。十一月初二奉殊笔:那桐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钦此。会典馆具奏会典馆节省经费一折,本日内阁奉上谕:崑冈等奏会典馆办书节省经费银两请解交部库以备饷需一折,会典馆提调官鸿胪寺卿那桐等办理馆事,将节银六万两呈请缴还部库,实属奉公洁己,办事认真,所有节省银两着即解交部库。钦此。圣谕奖励,钦感莫名”[18]327。1900年7月,“交锡洁庵廉会典校勘处石印存款三千八百七十两(内系京平足银一千两,足银折合京松二千八百七十两)购置机器,总署缴回银三千两(系足银折合京松均系按加二色合),另立账簿,曰那大人寄存会典馆公款簿。光绪廿六年六月廿五日立。此事已与澜公、熙敬甫言之矣”[18]348。
(3)催交功课。1898年2月9日,“午刻到会典馆,会同博泉、质庵、伯山携功课人名单四包到徐相宅呈回,未遇”[18]267。1900年4月到会典馆,同提调总纂各官商办功课。“辰刻进内见庆邸五军机、徐相、崇受丈,为局馆营事也。”[18]313“廿五日辰刻到会典馆与长石农侍郎议功课。长麟,字石农,为满人。会典馆,孙莱山总裁到馆谒见。辰正到会典馆领礼部事例一卷,托正斋代看。”“初五日午刻会典馆会议功课事。”
(4)议叙。1898年2月,“巳刻到馆,与刚大司寇议保举事”。2月,“廿二日会典馆全书过半。保案今日具奏,奉旨一道,内户部银库郎中那桐著以四品京堂候补。会典馆全书告成,在事各员奏请奖叙。桐在夹片保奏,不敢仰邀议叙。奉明发谕旨一道,桐蒙恩交部从优议叙”。
(5)会典校勘。1900年5月,光绪会典全书告成半年后,清廷决定成立光绪会典校勘处,任命徐桐、熙敬等为校勘大臣,那桐与刘永亨为总办,委派校对官和供事各20名,拨出专门校对经费,负责对光绪会典进行全面、系统地校对,“巳刻到会典馆校勘,新馆拈香开馆。昨日奏奉旨派大学士徐荫相(徐桐)、尚书熙叙庄(熙敬)、徐颂阁(徐郙)为校勘大臣,桐与刘子亭(刘永亨)为总办,裕治臣(裕隆)为帮办,又派校对官廿员,供事廿员”[18]336。“今日由校勘处公款提京松壹万两存恒利,三厘行息,一年归还,另立字据利折。又提京松三千两片送总署备用,治臣、昆峰两人经手”[18]340。那桐对会典满本校勘破费心力,并与会典馆校对处其它人员相与往还,履行校对处总办之职恪尽职守,“初九日午刻到会典馆恭阅呈进会典满书。赴会典校勘校对官十五人安徽馆之约,申正归。”[18]338会典纂修进行之中设立专门的校对处,是清代会典馆纂修的常态,但会典成书后设立专门机构校对处,任命高规格的校勘班底从事会典全书的通校,确是清代会典纂修的创举,反映了清代最高统治者对国家大典的重视,对成书后光绪会典的质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那桐日记》保存有关校勘处的重要史料,为我们了解光绪会典的纂修情况提供了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对我们客观地估计光绪会典的价值有重要的裨益。
结语
将光绪会典编纂置于近代史馆制度和典志体勃兴的语境下考察,以私人日记、文集、回忆录为主要史料,来解读光绪会典编纂过程中人员选拔、会典馆的人事纠葛、提调职责等,是饶有兴味、颇具价值的议题。以往关于史馆制度、史书编纂的研究,追求档案等官方文献的搜集和识读,对于日记、文集等梳理和解读不够,造成包括光绪会典在内的官修史书编纂的实态、编纂细节的疏略,制约了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光绪会典等官修史书的编纂特点、编纂价值、编纂成就,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对官修史书的客观分析。官修史书作为近代史书中的重要一级,在近代社会学术日益西化之时,可能在历史观、史学思想方面有落后时代之虞,但在史馆制度、史料搜集保存方面仍有一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梳理和总结光绪会典编纂人员选拔、会典馆的人事纠葛、提调职责等,希望用平情的观点、多维的视野,去分析和识读近代官修史书的利弊得失,这对近代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当有参考价值。本文不可能对光绪会典方方面面的问题做深入研究,只能选取一些有价值的“点”进行细致讨论,目的是希望史学界在研究视野、史料运用方面有所转化,如能有所激励,则厚望焉。
[1]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2]王记录.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J].史学月刊,2008(12):89-96.
[3]清会典馆奏议[Z].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帝起居注:六[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崑冈,等.钦定大清会典图[M]//沈云龙.近代中国资料丛刊:第13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6]柳诒徵.记光绪朝会典馆之组织[G]//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朱批奏折:104[Z].北京:中华书局,1996.
[8]孙学雷,刘家平.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内阁六部档案续编:2[M].北京: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
[9]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0]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1]邹代钧.上会典馆言测绘地图书[J].格致汇编,1892.
[12]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M].台北:明文书局,1985.
[13]何刚德.春明梦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14]陈义杰.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5]黄国瑾.训真书屋遗稿[M].紫江朱氏存素堂,1943.
[16]叶昌炽.缘督庐日记[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
[17][嘉庆]大清会典:卷55[M].台北:文海出版社,1992.
[18]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苏 南)
2015-01-28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历史编纂的演变路径、主要成就与当代价值”(10YJA770043);2014年度韩山师范学院教授启动项目“私人文献所涉之近代官修史书纂修研究”(QD20140324)
舒习龙,男,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
D69
A
1672-0695(2015)03-00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