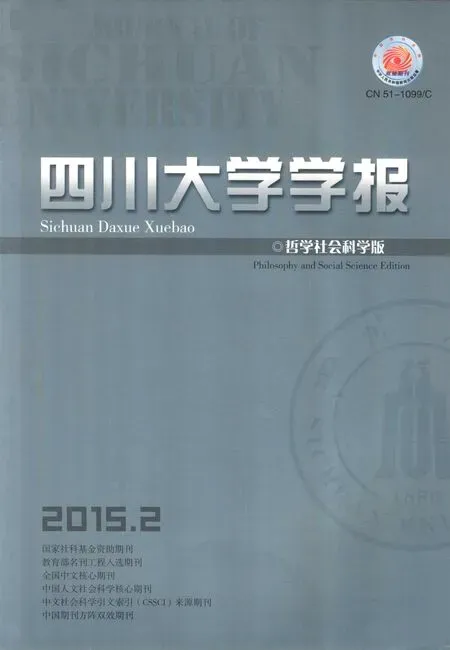马基雅维利与现代哲人的品质——施特劳斯的剖析
刘小枫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所开创的“现代文明”的开端——的标志之一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新哲人。权威哲学史家克利斯特勒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中列举了八位意大利新哲人 (从彼特拉克到布鲁诺),奇怪的是,其中并没有马基雅维利 (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①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姚鹏、陶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作者评述的最后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哲人布鲁诺出生于1548年,比马基雅维利晚出生差不多整整80年!
这并不奇怪,通常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大都不会提到马基雅维利,原因很可能是:马基雅维利没有写过理论性的哲学论著。马基雅维利在修学年代虽然受过当时的理论性哲学训练,但他被迫离开政坛之后赋闲时写的是政书,甚至小说剧本之类的文学作品。于是,马基雅维利不被视为哲学家,似乎理所当然。可是,后世的新派哲人如培根、卢梭,都明显与马基雅维利一样写政书,我们显然不能说马基雅维利不是哲学家。鉴于真正启发后世新派哲人的其实是马基雅维利,而非克利斯特勒列举的那八位意大利哲人,我们就得说,马基雅维利身上定然有着文艺复兴时期新哲人的某种品质。鉴于马基雅维利 (而非其他八位同时代哲人)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发挥现实影响,我们甚至有理由说,新哲人的某种根本品质在马基雅维利身上彰显得远比其他同时代哲人更为突出或鲜明。
认识西方现代新派哲人的一般品质对我们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搞清西方哲人品质在近代开端发生的嬗变,就不可能清楚我们自己可能会被教育成什么品质的学人。毕竟,现代中国学人几乎无不是西方现代哲人的学生,是由近代以来的新派哲人的思想养育起来的。倘若如此,认识马基雅维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新哲人品质,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要认识马基雅维利的新派哲人品质,就得从他写下的作品入手。可是,无论策论式的小书《君主论》还是学究性的大著《李维史论》,都非常难以读懂。这种难不是像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纯粹思辨地难以读懂,因为,这两部书讲的都是西方历史上远近过去的涉及政体的世事,并没有抽象的思辨。然而,《君主论》尤其《李维史论》远比《纯粹理性批判》难以读懂。毕竟,西方学界如今并没有因如何理解康德而争执不休,相反,如何理解比康德早两个半世纪的马基雅维利,西方学界迄今仍然争执不休。无独有偶的是,马基雅维利所引发的争执,又恰恰与理解西方近代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派哲人的品质有关。从根本上讲,围绕马基雅维利的争执涉及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哲人的德性——或者说,应该如何看待新派哲人所带来的哲人品质的嬗变。
西方学界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专家不可谓不多,但真正关注马基雅维利身上的新派哲人品质的却并不多。严格来讲,真正关注这一问题的西方大思想家,唯有施特劳斯。他在1950年代末发表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如今已成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哲学经典。①施特劳斯:《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申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以下随文注页码),译文据英文版有所改动,不一一注明。由于这部大著所思考的绝非仅仅是马基雅维利问题,而是通过识读马基雅维利挑明西方哲人的品质嬗变问题,其理论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思想史研究范围,以至于有业内人士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本身就堪称哲学经典。②参见迈尔:《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余明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可以设想,如果我国学界有更多研究哲学的人像研读《存在与时间》或《逻辑研究》那样认真研读《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我们对问学品质的自我理解也会大为不同。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共分四章,施特劳斯开篇就说到,要理解《君主论》尤其是《李维史论》,非常艰难。在第一章里,施特劳斯集中辨析了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艰难,或者说阅读《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艰难。在接下来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施特劳斯分别解析了《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中所有重要的晦涩段落。然而,在题为“马基雅维利的教诲 (teaching)”的第四章一开始,施特劳斯马上又提出,前两章直凑单微的解析仍然不足以透彻解释其每个“晦涩段落” (obscure passage)的含义,还必须从马基雅维利与古典传统的关系来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写作。《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一书共300页,前三章加在一起约160页,单单第四章就有约125页 (按英文版计算),占近半篇幅,由此可见第四章本身的分量。正是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施特劳斯提出了马基雅维利的身份问题: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不是一个哲人——如果是,又是怎样的一个哲人?
第四章开场是如何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施特劳斯首先对马基雅维利的读者亦即我们提出要求——严格来讲,是再次提出要求,因为在该书第一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施特劳斯已经对作为马基雅维利的读者的我们提出了要求:《君主论》和《李维史论》两书之间的关系“隐秘叵测,难以把握。两部书中的每一部,都着眼于某个特定的读者群”(页65段2行2)。通过第二和第三两章分别对《君主论》和《李维史论》的识读,施特劳斯已经表明,读者在研读马基雅维利著作的时候,“必须遵循”作者自己提供的途径,因为,“像《李维史论》和《君主论》这样的书”不会直白地展露作者要说的东西,需要读者“夜以继日地”“反复思考”(ponder over)很长一段时间 (页266行7)。因此,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要求“已经恰切地有所准备的读者”(the reader who is properly prepared)(页266行8)。所谓“有所准备”指的绝非仅仅是对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各种“拒不直接说出来的提示”(suggestions which refuse to be stated)“有所准备”,施特劳斯强调,“有所准备”的含义是懂得“这样一个真理”(the truth):“不应该说的就不能说”(what ought not to be said cannot be said)。如今的我们作为马基雅维利的读者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吗?知道“不应该说的就不能说”不仅是西方传统哲人的德性,也是中国传统哲人的德性吗?如果不知道或者尽管知道却不能理解“这样一个真理”,我们能够理解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吗?
施特劳斯接下来说,“拒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的“这种书”在思想史上为数并“不多”(not many)①原话是:“这样的书,为数并不多,这对于思想史家们来说 (for the historians of ideas)是件幸事 (fortunate)”——中译本将“思想史家”误译为“思想家”。——这无异于说,并非对于历史上的所有书籍都需要“有所准备”,对任何古书都需要尖起眼睛看“拒不直接说出”的东西。然而,鉴于今人普遍认为古人的智慧与自己一般齐平,甚至乎还认为古人的智商不如自己,施特劳斯随即说,这种“拒不直接说出”自己想要说的东西的书还是不少,至少比“人们会容易相信”(one would easily believe)的要多。施特劳斯相信,历史上的“伟大人物”(great men)比我们今人“容易相信的”要多,这些“伟大人物”甚至会与“未来[的时代]不合拍”(out of step with the future)——或者说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合拍。可以设想,由于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合拍,我们很容易认为,他们不如我们有智慧。
“伟大人物”总是“少数人”(the few)——无论在历史上的过去还是现在,都如此。施特劳斯借歌德诗剧中的人物之口给出了“少数人”的界定:第一,他们“对于世界、对于人们的心肠和思想有所理解”(understood something of the world and of men's heart and mind);第二,他们并不愚蠢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所见”(their feeling and their vision)②值得注意的是,vision这个语词在基督教中指的是所见“异象”。对俗众 (the vulgar)和盘托出——否则,就会落得被钉上十字架烧死的结局 (页266倒4行以下)。施特劳斯之所以说到这样的“少数人”,与他紧接着下来要讨论的马基雅维利是什么样的人有关。“不应该说的就不能说”并非意味着,马基雅维利在自己的书中没有说“不应该说的”,否则他就不会写书了。毋宁说,马基雅维利仍然在自己的书中说了“不应该说的”,只不过他说得十分晦涩难懂而已。马基雅维利的书之所以有不少“晦涩段落”,是因为他想要说而且的确说了“不应该说的”。
其实,施特劳斯在书的第一章开始不久就说到马基雅维利属于这样一类“少数人”:第一,他们“有能力洞悉”(are able to discern)涉及实际的统治者的“严酷真理”(the harsh truth);第二,他们“不会敢于对抗那些无力发现这个真理的多数人的意见”(do not dare to oppose the opinion of the many who are unable to discern that truth;页19倒3行)。这段关于“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的说法,直接与马基雅维利的具体言辞相关。换言之,马基雅维利对于自己属于“有能力洞悉”涉及实际的统治者的“严酷真理”的“少数人”有明确的自我意识。③值得比较第三章注释157(页231)中的一个说法:“占据狭窄的、只有少数人可以留居的地带也是不审慎的。”不过,与这些地方不同,第四章开篇说到“少数人”时,指的是“对于世界、对于人们的心肠和思想有所理解”的那些人,而且并没有与马基雅维利的具体言辞联系起来。显然,“对于世界、对于人们的心肠和思想有所理解”与“有能力洞悉”涉及实际的统治者的“严酷真理”不是一回事情。我们可以说,前者属于哲人式的“少数人”,后者则可能仅仅是政治家式的“少数人”。同样,在政治主张方面慎言与在哲学观点方面慎言是两回事。
在引用过歌德笔下人物的话之后,施特劳斯用自己的话说了两件事情:第一,在属于哲人式的少数人中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能够做到“守口如瓶”(restrain his full heart)——这话反过来理解更好:并不是每一个哲人式的少数人都能够做到“守口如瓶”;第二,歌德是记得哲人式的少数人应该做到“守口如瓶”的“最后一位伟人”(the last great man)——在歌德之后,“社会的理性、情绪和决断”(social reason,sentiment and decision)已经结成一股巨大力量,毁灭了“对哲学原初所意味着的东西最后残存的记忆”(the last vestiges of the recollection of what philosophy originally meant;页267行4)。
第四章的这段开场白把如何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著述变成了如何理解“哲学原初所意味着的东西”,或者说把如何理解马基雅维利的著述这一问题变成了如何理解哲人的问题。从而,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维利当然是哲人,问题仅在于他是怎样的哲人。
可是,为什么施特劳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歌德的话?要找到与歌德这句话类似的其他同时代作家的话不难 (莱辛就是一个现存的例子)——为什么偏偏引用歌德?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歌德是一个伟大时代——启蒙时代——的伟大标志:歌德处于启蒙运动搞得非常热闹的顶峰时期。所以施特劳斯说,在歌德之后,“社会的理性、情绪和决断”已经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毁灭了原初意义上的哲学。由此看来,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怎样的哲人问题,在施特劳斯那里与后来的启蒙运动联系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启蒙运动思想与文艺复兴思想有内在关联,但我们未必清楚,这种内在关联究竟是怎样——至少不会是所谓“张扬人文主义”之类的大而无当的关联。不仅如此,施特劳斯在这里所下的一个注释让我们感觉到,歌德与近三百年前的马基雅维利似乎有某种隐秘的内在关系。
这个注释大有看头,因为其形式就让人觉得蹊跷。首先,正文引歌德作品中的话时没有下注,句号之后礼赞歌德一番才下注。不仅如此,这个注释其实并未给出浮士德对瓦格纳说的那句带引号的话的出处,而是另外引了歌德评价《拿破仑》一书的作者斯考特 (Walter Scott)的一句话。①这段话见于《浮士德》第一部分“学者剧”中浮士德与助手瓦格纳第一次对话的结尾部分 (行588-593):“嗨,什么叫做认识!谁又可以直言不讳 (das Kind beimrechten Namennennen)?少数人 (die wenigen)诚然从中认识到一点什么,却十足愚蠢,没有保管好全部内心 (ihrvolles Herznichtwahrten),竟然向庸众 (Poebel)泄露自己的洞察(Schauen)和情绪。这些人自古以来都没好下场,不是被钉十字架就是被烧死。”歌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斯考特颇为审慎,他“刻意防止自己受到整个马基雅维利式观点的影响”。可见,启蒙运动时代曾流行“马基雅维利式观点”(Machiavellian view),亦即关注“此世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d)的观点——我们知道,全心全意关注“此世”的真理恰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特色。“此世的历史”这个提法后来因黑格尔的《此世历史讲演录》(旧译《世界历史讲演录》未必准确)而变得非常著名,而且成为现代性普世-普适论的标识之一:人类历史具有一个普遍的演进目的——对此我们还可以想起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此世历史的精神就在拿破仑征战的马背上。然而,这与马基雅维利是否是个能做到“守口如瓶”的哲人式少数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注释还没有完,事实上,这个注释有三段内容。施特劳斯随即又提到歌德责备费希特的话:“关于上帝和神圣的东西”(about God and divine things),费希特没有做到“保持一种深奥的沉默”(preserve a profound silence),而是“口无遮拦”(unguarded utterances)。鉴于费希特是受康德启发的观念论哲人,而且是德意志观念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所经历过的中介阶段,费希特就属于未能做到“守口如瓶”的那类哲人式的少数人。不仅如此,费希特也是著名的政治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他像马基雅维利一样关注“此世的历史”,与在德意志学界流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深刻的关联。②在早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施特劳斯让费希特充当过启蒙精神成熟的标示:“一旦我们不得不与费希特一起嘲笑尼柯莱 (Nicolai)时,我们便已被启蒙。”参见施特劳斯:《柯亨与迈蒙尼德》,刘小枫编:《犹太哲人与启蒙》,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迈内克写到:“在德意志,马基雅维利现在终于找到了理解他的人们。”——这指的首先是费希特,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普罗米修斯式态度和现代异端主义另有终止美言和深刻评论”。见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7、519页。“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是“少数人”也不再懂得约束自己内心真实见解的原因,从而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是启蒙的肇因。
在援引歌德批评费希特的话之后,施特劳斯又说到歌德自己对“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的理解:“诗的创作要素中的每一种斯宾诺莎主义者的东西 (Everything which is Spinozist),在反思的要素中 (in the element of reflection)都成了马基雅维利式的 (Machiavellian)。”最后这段注释蕴含着两个要点。首先,鉴于斯宾诺莎既是近代欧洲观念论的重要倡导者,又是近代自由民主政治论的重要先驱者,歌德把斯宾诺莎主义理解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便意味着,所谓“马基雅维利主义”既是一种观念论哲学,也是一种自由民主政治论。其次,“反思的要素”与“马基雅维利式的”对举意味着,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绝非仅仅涉及实际的统治者的“严酷真理”,也具有观念论的哲学品质。但蹊跷的是,施特劳斯在这里引用的歌德的书名是《格言与反思》 (Maximen und Reflexionen)——如果诗人歌德也搞思辨的“反思”,他自己是否也是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诗人呢?难道施特劳斯在正文中赞美歌德,同时又在注释中隐晦地揭示歌德有可能是个隐藏的马基雅维利分子?毕竟,“毁灭对哲学原初所意味着的东西最后残存的记忆”的能动力量恰恰源于“马基雅维利式”的“反思”。
无论如何,施特劳斯的这个精心构拟的注释让我们看到:第一,歌德对“马基雅维利式的观点”并非持旗帜鲜明的否定态度,从而,他在正文中对歌德的赞美得大打折扣——毋宁说,歌德顺应了启蒙的时代潮流。第二,如果与正文中的那句“在歌德之后,社会性的理性、情绪和决断……已经共同联合起来去毁灭对哲学原初所意味着的东西最后残存的记忆”联系起来看,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个哲人:他开启了“毁灭对哲学原初所意味着的东西”的能动力量——开启了启蒙哲学的品质。
倘若如此我们就可以问:马基雅维利的书是“不应该说的就不说”的书吗?回答是否定的。马基雅维利以暗示的方式说了“不应该说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成了哲学的一种时代特征——启蒙哲学作为新哲学就是说“不应该说的”哲学。如果我们再回头看正文中的那句话就会别有一番体味:马基雅维利的“这种书”在历史上不多,对思想史家们是幸事,“更不用说对其他人”!因为,马基雅维利没有持守“不应该说的就不说”这一古来的哲人德性原则,尽管他用大量“晦涩段落”来传达持守“不应该说的”东西。不仅如此,通过注释我们还已经得知,所谓“不应该说的”东西就是“关于上帝和神圣的东西”——在整个第四章,施特劳斯都在揭示马基雅维利如何用种种“晦涩段落”来传达“不应该说的”东西。马基雅维利固然属于历史上的少数“伟大人物”之一,但这位“伟大人物”与在他之前的那些伟大人物在品质上截然不同,而且与“未来”的时代也并非不合拍——毕竟,他造就了“未来”的启蒙哲学。
接下来施特劳斯就进入了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哲人。施特劳斯进入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审查一个在启蒙时代就流行的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是个“异教徒”。①对比第一章开头5段,我们可以发现,施特劳斯在这里又从意见开始:第一章开头针对的流俗意见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意图的说法,这里针对的意见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是个异教徒的说法。施特劳斯说的是“大多数作家”(many writers)②值得对比前段用到的“少数人”。此外,中译本将“作家”(writers)译作“论者”不妥。将马基雅维利视为“异教徒”,但在这里下注时他仅仅引用了费希特的话:马基雅维利是个伪装的基督徒。前一个注释里已经出现过费希特,现在紧接着又出现费希特,可以确定,两个注释将分开的两个自然段紧紧黏在一起。不仅如此,这两个分别属于两个自然段的注释之间有着某种内在关联——然而,怎样的内在关联?
我们不妨先注意施特劳斯不惜笔墨引用费希特的方式 (或者说施特劳斯的言辞表面):施特劳斯共引了三句费希特的话 (前一个关于歌德的注释同样引了三句话),前后两句是直接引语,中间一句是间接引语。不仅如此,第一句直接引语说马基雅维利是“公开立誓的异教徒”(a professed pagan),后一句直接引语则说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虔敬的基督徒。两相对照,费希特无异于揭开了马基雅维利的真实面目。中间一句间接引语则说:无需为马基雅维利辩护,没必要非把他说成是个基督徒不可——直到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不少思想史家们为马基雅维利辩护,说他是个正派的思想家、坦诚的学者。相比之下,费希特更接近马基雅维利的真实面目吗?
施特劳斯引用费希特的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直接引语有如一种公开宣称,中间夹着一段转述。如果直接对比两句直接引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对比:“公开立誓”与伪装。换言之,既然马基雅维利会伪装成一个基督徒,难道他不可能也伪装成一个异教徒?毕竟,“公开立誓” (professed)这个语词也有“伪称”含义。由此来看,鉴于这个注释与前一个注释不仅形式上大致一样,而且很可能有内在关联,我们就应该想到:歌德也被叫做异教徒。换言之,歌德也有可能是一个伪装的异教徒。无论如何,启蒙哲学的确凸显了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尼采那里,基督教与异教绷在一起的那根弦终于断裂了。可以推想,基督教与异教的关系,将是施特劳斯审理马基雅维利究竟是什么样的新哲人这一问题时的着眼点。
何谓“异教徒”?施特劳斯用了颇长的一段间接陈述来展示“大多数作家”的看法,①页267倒5行至268页行2。仅有一句话加了引号:马基雅维利“爱 (loving)自己的祖国甚于爱自己的灵魂”——但施特劳斯并没有给出这话的出处。施特劳斯转述“大多数作家”的观点说,他们责备马基雅维利“忘了或否弃效法基督”(forget or rejected the imitation of Christ),忘了去“思考”(think)不属于狭义的政治的任何东西,狂热反叛“基督教道德”(Christian morality),不去“冷静思索”(dispassionate thought)基督教道德的神学前提,因此,他们把马基雅维利“想像成”(imagine)一个美迪奇式的人物。这一观点包含着两个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要点:首先,离弃基督转而崇拜世俗政治权力,用“异教罗马的此世性荣耀”(worldly glory)取代基督,这无异于渎神——毕竟,“荣耀”这个语词只能用在基督身上。第二,马基雅维利虽然善于思考,却没有把自己的思考用于神学。施特劳斯的转述两次用到“思考”这个语词,似乎意在凸显马基雅维利的哲人品质,可是,马基雅维利并没有被“大多数作家”的看法视为哲人,而是被视为科西莫·美迪奇那样的现代僭主。
施特劳斯对“大多数作家”的看法既否定又肯定。由于他通过间接陈述实际上区分了这个看法中的两个不同要点,他的既否定又肯定就不仅不自相矛盾,反倒直凑单微。首先,施特劳斯否定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理由在于“异教主义是一种虔敬”(Paganism is a kind of piety;页268行3),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找不到丝毫“虔敬”。所谓“异教”当然指的是古希腊宗教,但施特劳斯说异教徒必须有“虔敬”(piety),指的是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式的“虔敬”。因为,施特劳斯用不无反讽的口吻说: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从敬拜基督改宗为敬拜阿波罗”(268页行5)——在柏拉图的《会饮》和《蒲法伊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苏格拉底是个虔敬的阿波罗神敬拜者。
接下来施特劳斯用“另一方面……”将话头一转,说将马基雅维利视为“此世的智者” (the wise of the world)“并非误导”(not misleading),肯定了“大多数作家”的看法中的第二个要点,即肯定马基雅维利忘了去“思考”非政治的事物。不过,在为这一肯定提供理由时,施特劳斯提供的是萨沃纳罗拉修士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在讲道时对“此世的智者”之类的人的痛斥,而且借用的是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换言之,谴责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此世的智者”,是“按照萨沃纳罗拉”(according to Savonarola)的说法,而萨沃纳罗拉的说法又出自马基雅维利的说法 (页268行7以下)。这样一来,马基雅维利与萨沃纳罗拉修士的说法就搅在了一起。首先,施特劳斯提到马基雅维利说萨沃纳罗拉痛斥“此世的智者”,然后说“按照萨沃纳罗拉”,“此世的智者”是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治理国家不能靠基督教主祷文,必须“仅仅相信”(believe anything except)“理性的论说所证明的东西”(what rational discourse proves)。这个说法表明“此世的智者”是一帮子哲人,因为哲人才“仅仅相信理性的论说所证明的东西”。施特劳斯随即引证了萨沃纳罗拉曾经亲耳“听见”(has heard)“此世的智者”“彼此争论时”(in their disptations)的情形:这帮人“谈得很哲学,而且蔑视超自然的东西”(speaking philosophically and disregarding the supernatural),说什么“此世是恒在的”,“信仰不过是意见”云云。这时施特劳斯下注,同时给出马基雅维利和萨沃纳罗拉的原著,似乎上述说法是两人共同的说法,不加区分。
下注完之后,施特劳斯才说了自己要说的话:马基雅维利是这样一类“此世的智者”或哲人,他们“拒绝了异教徒的种种神话”(the myths of the pagans),①原文没有中译本的“荒诞”两字。拒绝了“启示和启示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教诲”,转而崇拜单纯世俗的“政治上的聪明”(political cleverness;页268倒5行),②中译本把“政治上的聪明”译作“政治权术”不对。无视这种聪明的“限度”(the limis)。施特劳斯最后总结性地说,这帮“此世的智者”就是“哲人”(falasifa)或者阿威罗伊主义者 (Averroists)——Falasifa是阿拉伯语的“哲人”一词的拉丁化写法,“阿威罗伊主义者”对这个语词作了进一步界定,毕竟,在伊斯兰教宗法国家中,并非所有falasifa都是阿威罗伊主义者。
然而,为什么施特劳斯在这里要用阿拉伯语的“哲人”一词的拉丁化写法,而非用希腊语的“哲人”一词的拉丁化写法?尤其需要思考一下的是:善于辨析入微的施特劳斯为什么要把马基雅维利与萨沃纳罗拉的说法搅在一起?这样做难道有什么用意?
实际上,施特劳斯说萨沃纳罗拉曾经亲耳“听见”的“此世的智者”们的“彼此争论”出自《李维史论》卷二12章戏仿过的经院论争——在那里,马基雅维利嘲笑了讨论“超自然的东西”的经院哲人。③参见马基雅维利:《李维史论》,薛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358页 (以下随文注页码)。施特劳斯很可能是在戏仿马基雅维利自己的笔法,因为《李维史论》卷三30章明文提到萨沃纳罗拉谴责“此世的智者”时,其实是在赞美萨沃纳罗拉(《李维史论》,卷三,30章,页541)。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第一章,施特劳斯曾分析过《李维史论》卷二12章“戏仿经院学派的论争”(a parody of scholastic disputations),以及马基雅维利如何用哲学的智识取代诗的寓言(异教神话)和圣经 (启示教诲)。在那里所下的注释中,施特劳斯提到马基雅维利对萨沃纳罗拉的赞美:“他的著述表现了他的博学,他的审慎以及他的头脑的德性”(his learning,his prudence,and the virtue of his mind;页62注释倒5行)。不仅如此,施特劳斯在那里还展示了亚里斯多德著作与圣经的对峙。由此看来,施特劳斯在这里要把马基雅维利的说法与萨沃纳罗拉的说法搅在一起,而且在注释中对两者的说法不加以区分,意在暗示马基雅维利与基督教修士萨沃纳罗拉是一伙,甚至可以说是萨沃纳罗拉的学生。④比较第一章35段 (页59以下),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以神学为前提。
萨沃纳罗拉这个历史人物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中累计出场18次,出场之频繁仅次于李维和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出场还多。⑤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一章第六自然段 (12页倒2行),那里的说法与这里的说法完全一样。萨沃纳罗拉虽然是多米尼克会修士,实际上是个热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异端分子,而且是立志献身于实现共和政体的政治家。他在29岁那年到佛洛伦萨布道,吸引了一批追随者,1494年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政权,主持制定宪法,以致于在46岁那年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定为异端,绑在树桩上烧死——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六章中曾这样总结萨沃纳罗拉的失败教训:
一旦大众 (la moltitudine)开始不再相信他,他就同自己的新秩序 (suaordini)一起毁灭了,毕竟,他没有一种模式 (modo)使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和使不信仰他的人们信仰他。像这样的人物,在行动中有着巨大的困难。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的所有危险,他们必须运用力量 (la virtú)加以克服。一旦克服了这些危险,他们就会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当他们消灭了嫉妒他们的品质 (suaqualità)的那些人之后,他们就会保有权势、安全、尊荣和幸福。⑥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六章,潘汉典、刘训练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23页 (凡有改动依据1995年意大利Einaudi版)。
可见,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萨沃纳罗拉失败的教训在于,他在实践政治品格上有欠缺,还不善于创制出一种“模式”来掌握“大众”——而掌握“大众”的唯一方式是“运用力量”消灭嫉妒自己的“品质”的人。对于萨沃纳罗拉的失败,马基雅维利充满惋惜之情,即便在责备萨沃纳罗拉仍然想要使佛罗伦萨的大众相信自己“与上帝交谈”时还说:“我不想评判他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对一个如此伟大的人,应怀着敬畏谈论。”(《李维史论》,卷一,11章,页184)过去的“大多数作家”把马基雅维利视为科西莫·美迪奇那样的现代僭主,看来没错,至少他推荐的是现代僭主“模式”和“品质”。
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第一章中,萨沃纳罗拉出场两次,在第二章中仅出场一次 (页72行5),在第三章出场5次 (两次见于正文,三次见于注释),①页234注释161倒5行;页249注释181倒7行;页261注释189。在第四章中则出场9次 (3次见于正文,6次见于注释)。在第三章正文中的两次出场,施特劳斯为我们展示了他在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形象以及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关系:在马基雅维利笔下,萨沃纳罗拉“以新阿摩司或新摩西的面目出现”,“沿袭仿效圣经的先知们曾经从事过的事业”(页93段2行6);当时的读书人并非都追随古典主义者,也追随萨沃纳罗拉 (页124倒10行)——这话暗示的是马基雅维利也追随萨沃纳罗拉。②在随后的页261的注释189中,施特劳斯说,“马基雅维利可能会同意萨沃纳罗拉”。毕竟,凭靠亚里士多德哲学来释读《圣经》,是经院僧侣学人开的头,萨沃纳罗拉正是这样的人。
我们再回头看那句“他们是“哲人”(falasifa)或者阿威罗伊主义者”,就别有一番味道了:萨沃纳罗拉和马基雅维利都是新哲人,尽管前者是教士。施特劳斯在否定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的同时,肯定了他是个哲人——否认马基雅维利是异教徒,不等于否认他是个哲人!但在肯定他是哲人时,又把他与萨沃纳罗拉绑在一起,这意味着与阿威罗伊主义者绑在一起。这样一来,施特劳斯就不仅指明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哲人的本质特征 (拒绝启示宗教的教诲,信赖单纯世俗的“政治上的聪明”)——马基雅维利不敬拜基督不等于是异教徒,③比较尼采从一个牧师之子变成狄俄尼索斯信徒 (异教徒);在第四章 (页306的注释)中,施特劳斯比较了尼采与马基雅维利攻击基督教时的差异。而且指明了这种新哲人的来源:“阿威罗伊主义者”——萨沃纳罗拉尽管写过De contemptu mundi(未完成)这样的书。按照教科书上的一般说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复兴古希腊文化反对基督教,施特劳斯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哲人不仅反对启示宗教,也反对异教神话 (柏拉图)。④对观第三章,页247行4。因此,施特劳斯通过“虔敬”把古希腊异教与基督教摆在了一起,两者毕竟都是宗教 (这个语词的原义就是“虔敬之事”)——新哲人的基本特征是反对宗教。
最后值得提到,施特劳斯这段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哲人品质的论述框架采用了倒叙法:从歌德和费希特到阿威罗伊主义者——或者说从启蒙哲学的巅峰到启蒙哲学的源头。甚至再往前看关于少数人是懂得“不应该说的就不能说”的人的说法,现在我们也许能明白施特劳斯的笔法:在正文中,施特劳斯礼赞歌德,在注释中却提到歌德与马基雅维利的关联。⑤歌德深受卢克莱修影响,《浮士德》第二部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从马基雅维利到歌德 (以及注释中的拿破仑),施特劳斯在短短的篇幅里展示的不仅是启蒙哲学从其历史开端到顶峰的全幅场景,而且是启蒙哲学的品质。这就为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做了很好的脚注:“马基雅维利与大传统彻底决裂,发起了启蒙运动。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是,这场启蒙运动是否名符其实,或者,它的真实名称是蒙昧蛊惑。”(页265)
——《君主论》献词隐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