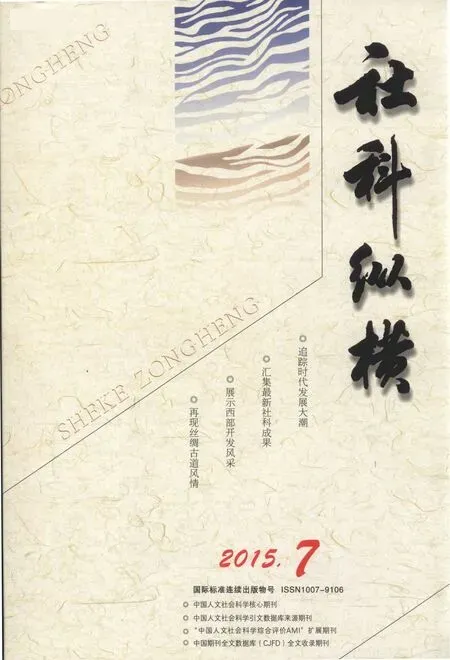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机构行政运行实证分析——以甘肃省Z县民政局为例
李伟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1)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县级政权的政治运作及改革,而对于县级政府机构的实际运行关注甚少。组织机构是职能实施的载体,不仅直接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还影响政府职能的实施。县级政府机构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县级政府职能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2012至2013年间,笔者在甘肃省Z县挂职担任县民政局有关职务,期间获取了大量的实证资料。本文试图以县民政局的行政运行为缩影,描述笔者眼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级政府机构行政运作模式和机制,以及这一模式和机制所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效果。
一、县级政府机构运行的基本模式
Z县位于甘肃省中部,以其贫困而出名。Z县民政局是县政府主管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机构,主要职权包括:基层政权建设、区划地名、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民间组织管理、婚姻登记、殡葬管理等110余项职能。县民政局设有办公室、优抚安置股、救灾股、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股、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民间组织管理股、民间组织执法监察股)、区划地名股等6个内设机构,还设有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老龄工作办公室、县社会救助办公室、社会福利院和收容遣送站等其他机构。现有编制内工作人员24名(实际日常办公人员不到20人),其中局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局长1名、副局长2名、支部书记1名、纪检组长1名、社工委副书记1名、老龄办主任1名。
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需要通过决策、执行、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实施具体的治理。笔者从决策、执行和监督三个环节来考察县民政局行政运行的程式与形式。
(一)决策
决策是行政运行的第一步。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由于权力结构的集中性,行政体制的运行过程表现为明显的命令服从式,即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县级政府的决策属于贯彻执行的决策,即是把上级政府的决策和本行政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加以落实。县民政局作为县级政府的组成机构,既承担着贯彻落实本级政府决策的责任,也担负着落实上级民政部门决策的职守。以县民政局为例,行政运行的周期以年为单位,周而复始的规范化模式贯穿始终,年度的工作任务安排即属于决策的一部分,笔者暂称之为年度决策。在年度决策执行过程中,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
对于年度决策,其产生的依据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县政府全年工作目标,主要是根据县政府确定的年度指标数据,这些指标数据的确定往往是来源于县委的决策;二是市民政局全年的工作部署。县民政局的工作安排必须既符合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又符合上级民政部门部署要求。从实质上看,县民政局自身所作出的决策几乎没有。以2012年为例,2月份县里召开了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对全县一年的各项工作作出安排;3月份市民政局召开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对全市民政工作提出要求。根据这两次会议要求,县民政局将工作进行分解和具体化,4月9日,县民政局召开全县民政工作会议,对本年度工作进行安排。
这种决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层层加码。县里和市上的发展要求是基于本地区条件较好的县域发展速度和水平设计目标,这个目标对于欠发达县区在实施上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县民政局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必须再留有余量,因此,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二是违背常理。决策目标的制定完全根据上级任务要求,与本地区发展实际有所脱节。比如,在全县民政工作会上提出,要建设一定数量的乡镇养老机构,以符合上级关于养老机构发展的任务要求,但是按照现有的经费安排,这种建设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决策的后果就是,可能出现偷梁换柱的情况,比如可能把“五保家园”等其他建设项目作为养老机构建设项目,甚至有可能出现统计数据的造假。
此外,在行政运行的实际过程中随时可能需要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县民政局的决策权也是不完整的。在县级政府行政过程中,本行政部门的事,往往分管副县长甚至县长或者书记要直接介入。县民政局在出现需要决策的问题时,也会主动向分管副县长请示,甚至需要逐级请示。在这种情况下,科局长的作用已被部分的取代,乃至在部门决策的过程中处于无力状态。因此,对于县民政局来说,其权力在很大部分上是收归县政府所有了,有时甚至县政府也不能决策,而要依附于县委的决策,行政部门的自主性受到多方的监控和控制,难以施展。
(二)执行
1.执行的主体
县级政府机构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执行权力的分解与转移,即除日常性行政事务外,本来应该是行政部门职权范围的事,却被主动或被动地交由其他部门或机构来处理。
一种情况是被动转移。一些上级重视或者比较能出政绩的工作,往往会移交给县委、县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来处理,这些专门机构挂着县委、县政府的名号,把涉及的职能部门和乡镇全部纳入,虽然实际工作人员主要还是职能部门的人员,但工作业绩可能都要计算在县委、县政府的账上。以民政局为例,2012年,根据甘肃省统一安排部署,对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实施提标,从职能分工上看,该项工作属于民政职权范围内的事。县委、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以“两办”名义下发了提标工作方案,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开展这项工作,民政、财政、各乡镇,甚至信用社成为这个领导小组的成员单位,县里四大班子领导悉数成为领导小组成员,但实际工作都还是由县民政局实施完成。这种做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工作落实更有力度,尤其在进村入户调查摸排工作中,各乡镇都将此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完成;有弊的是万一在这项工作中出现问题,往往难以确定需要承担责任的部门。比如,如果在这次提标过程中出现了弄虚作假的情况,入户调查是乡镇承担的,审核确定是民政部门完成的,到底谁承担责任可能会存在扯皮的情况。
二是主动转移。还有一些工作,在作出决策之初就明知不可能完成,或者难办的、费力不讨好的,往往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将责任上交或下移。如,关于社区建设、养老福利机构建设等投入多、见效慢的工作,就通过签订责任书等形式分配给有关乡镇完成。这样责任主体就由县民政局转移到乡镇,即使相关任务不能完成,县民政局也有向县委、县政府解释的理由。
2.执行的方式
从县民政局行政执行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通过会议、文件、检查、考核的方式来完成。直接做工作的相对比较少,绝大部分工作是移交给社区或乡镇完成。
一是会议。会议是县级政府机构喜欢运用的一个方式。以县民政局为例,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将日常的业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通过会议的不同层级,以显示所要部署事务的重要性。特别重要的事务,请县委分管副书记到场提出要求,各乡镇一把手参会,这类事务在落实上会比较顺畅;一般的事务,请分管副县长到场,这类事务处理上还会比较顺畅;而以民政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在落实上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
二是文件。与会议类似,发文也是落实工作的重要手段。通过不同的发文方式,也可以突出事务的重要性。重要的工作,比如低保提标、优抚安置政策等,以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府办公室“两办”的名义下发,权威性最大,执行起来最为方便;以本部门的名义发的文,在当前这种文牍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作用就比较有限了。
三是检查。检查是确保工作落实的重要手段,在通过会议、文件将工作部署后,接下来就是检查。对于县级民政部门,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下乡检查。以2012年上半年为例,2月至3月,各乡镇民政资金使用情况检查;3月至5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提标情况检查;4月到5月,基层组织建设情况检查;6月到7月,优抚安置、退伍军人补贴发放情况检查等等。从实际情况看,检查对促进工作落实有很大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最突出的问题是覆盖面的问题,乡镇一般都会拿出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典型供检查,通过检查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比较难。
四是考核。所谓考核,即对目标管理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以县民政局为例,每年年初,县民政局分别要和县政府以及市民政局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县民政局再将任务分解,与各股以及各乡镇(民政工作站)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以2012年县民政局和各乡镇签订的目标管理责任书为例,共涉及12大类56个小类的工作,基本上是将县政府和市民政局的目标管理责任书再细化分配给各乡镇。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将责任落到了乡镇领导的头上。
(三)监督
以县民政局2012年实际工作情况为参照,对县级政府机构行政运行的监督主要是靠上级检查、人大监督和年终考核来实现的。
一是上级检查。主要是上级对口部门对某项工作落实情况的业务检查。以县民政局为例,2012年上半年,市民政局先后开展了民政重点项目进展情况检查、老龄工作落实情况检查、低保提标工作检查、双拥优抚工作情况检查、上半年中期工作业务检查等。这种检查的主要问题是形式化严重,检查往往就看县里安排好的几个点,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有下级糊弄上级,一级糊弄一级的嫌疑。即便如此,下级还是希望上级能经常来检查,原因主要是上级手中有项目的审批权,接受检查意味着有可能获得项目、资金支持或者其他便利条件。
二是人大监督。人大监督是行政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监督往往还处在“提意见”的范畴,形式上也主要是以调研为主,一般不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效果。但是,这种调研最终要形成调研情况报告县委,并大多数会以“两办”的名义在各乡镇和县直部门发放,因此,对此类监督、调研,行政部门还是非常重视的。以县民政局为例,2012年上半年,先后接待了县人大关于民间团体管理情况的调研,市人大关于抚恤优待安置相关法规执行情况的调研。当然这种调研,绝大多数也是走马观花式,说好话多,提意见少。
三是年终考核。对行政部门最为重要的监督就是年终考核。这是县里每年年终的头等大事,县级党委政府一般要组成联合考核组,对照该部门与县政府签订的目标考核责任书,对一个部门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详细考核打分。Z县根据考核情况要实施一定的奖惩,年终考核成绩不好的部门负责人可能在仕途升迁上受到较重的影响。由于目标责任考核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从政治学习到社会治安,从计划生育到安全生产,真正职责业务范围的工作所占比例不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县级政府机构行政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行政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权多元,效率低下
从理论上讲,县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是按照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县级政府机构也应该在职权范围内按照首长负责制的原则建立。但是实践中,职能部门的权力往往被分管副县长直接“包办”下来。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得到更多的支持,往往需要得到行政体系内的“上司”即分管副县长的认可,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甚至需要更高级别的领导的认可,如县委书记、县长的认可。这样容易造成“一仆二主”,甚至“一仆多主”的情况,领导之间的协调妨害了正常的行政效率。协调不善,容易造成行政权力运行陷入无序和冲突之中。例如,县民政部门在正常行政体系之外,还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分管民政工作,一名副县长负责民政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协各有1个副主任(副主席)联系民政工作,县委组织部长担任老龄委主任也在管民政工作,政法委书记担任双拥办主任也在管民政工作。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一项正常的工作往往要协调多方面的领导,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二)权责分离,推卸责任
县级政府机构运行另外一个问题是权责分离。突出表现为有权无责和有责无权的情况。县委书记是全县真正的“行政首长”,县委书记直接介入行政事务是真实存在的,县委书记的行动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县委或县政府对一个部门本应承担的职责作出决策,而这个决策的实际责任承担者却是这个职能部门。以Z县为例,2012年该县经受了一次自然灾害,灾情发生后,救灾资金拨付到县民政部门,这笔资金如何使用,本来应该是县民政局根据受灾情况决定的事,但其实这笔救灾资金的用途是要经过县委会议决定的。如果在决定过程中,有一部分资金被用在不是直接与救灾有关的用途之上,虽然决定是由县委会议集体决定的,但是承担责任的主体有可能是没有决定权的县民政部门。权责分离的另一面就是推卸责任。在县级行政的各个层次中,对于那些能体现政绩、又好办的工作,各级负责人都会不遗余力地积极承担,但对于一些难办的、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往往责任上交或责任下移,本该自己负责的,要么拉着上级领导一起负责,要么交给乡镇一级处理处置。
(三)权力滥用,职能扩展
从县民政局的实际运行来看,在县级行政中县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县级政府机构的行政行为往往难以加以明确区分。实际工作中,县长成了大局长,副县长成了分管局长,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往往成了办理具体事务的办事员。县级政府机构普遍缺乏独立的决策权,决策过程实质上被上移。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由于县级党委政府领导考虑工作时会从更宏观的层面考虑整体性的工作,因此在决策中往往掺杂了其他考量因数,行政目的不再纯粹。比如,农村低保本来是保护农村低收入群众生活的一项措施,但是由于县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好,县里就出台土政策,凡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在申请低保时要给予一定限制。这其实是与国家的政策相违背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构成了权力的滥用。
同时,县级政府机构一直存在着权力扩张的内在倾向,行政边界不断扩展。一些县级政府机构,根据其一项项业务不断分设出新的机构,新的机构再不断地扩张产生自己的内设机构。以县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为例,虽然一个县的民间组织数量并不多,管理也主要是形式上的管理,但是随着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县民政局已经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股、民间组织执法监察股,有的地方如邻县M县,已经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职能得到进一步扩张。扩张机构可以有效解决人员安置,解决与上级对接等问题,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产生了,就是大量超编人员、聘用制人员和合同工的办公费用和工资如何解决。从Z县的实际看,靠财政资金已无法维系办公和工资费用,只有依赖所掌握的资源条件不断开源。对于县民政部门来说,工作中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争取上级专项经费上,同时通过行政性收费、老年福利院对外招租盈利等方式获取额外收入。
三、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行政运行中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县级党委政府和县级政府机构之间的特殊关系。县级政府机构权力直接来源于县级党委政府,县级党委政府在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权力的分配严格掌控着县级政府机构,这种关系导致县级政府机构运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是县级政府机构权力来源于县级党委政府。县民政局局长是由县长提名,并且通过县委审核和组织部门考察之后才能获得人大任命的。因此,在县行政等级制中,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授权并不存在;为宪法所规定的县政府组成人员均由县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遴选任命,即便科级副职亦由县委组织部门先行确认其任职条件。在县级行政运行中,由于党政混一的现实促使地方干部将自身利益的获得和仕途晋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地方权力核心,也就是县级党委政府上。县级党委政府由于控制着县级政府机构的财政、人事、审计等权力,因而造成县级政府机构对县级党委政府的过分依赖关系。
二是县级党委政府通过权力的分配控制着县级政府机构。县级党委政府以国家代理人身份直接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并将这种占有转换成权力分配形式,从而构建行政机构设置中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功能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行政权力上的分配即是资源基本配置权的分配。权力功能上的差别则意味着支配和控制资源的多寡,同时意味着获得资源和利益的可能性。这就是县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内容。[1](P82)县级政权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主体,其为了自身利益不断侵入本应是县级政府机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实施着过分的干预。
本文的分析不在于也不可能给出县级政府机构行政运行存在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更不是认为当前县级政府机构的行政运行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而是力图通过对县民政局行政运行实证分析的这个窗口,描绘现实的县级政府机构运行的实际图景。通过对县级政府机构及其具体结构和运行进行白描式的调查分析,才能使各项改革措施建立在客观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如果本文能对这一目标的实现起到稍许帮助,也就实现了其基本的价值。
[1]周庆智.中国县级行政结构及其运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