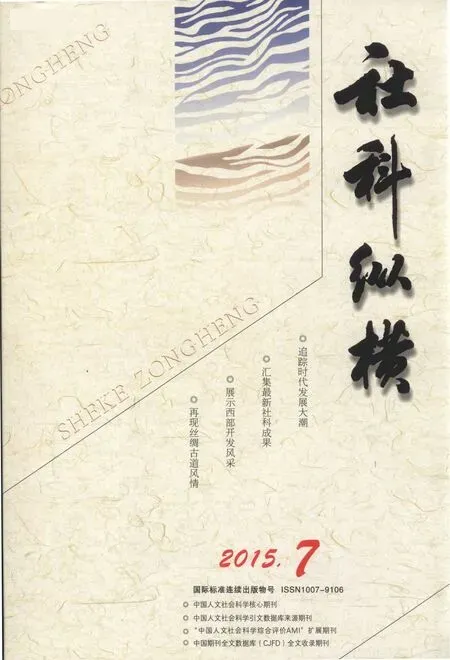金代山东文士地域特色考
聂立申
(泰山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金代山东文士的研究成果,目前学界是凤毛麟角,而对于金代山东文士的地域特色与成因,更是少有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结合文献资料及今人成果,对金代山东文士的地域特色作些探讨,冀望能对今后金代与山东区域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有所启迪与推动。
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基础,也是地区文士性格产生的重要因素。山东地区素来敦厚、质朴、重教、尚学的民风及强悍尚武的习气,无疑在历史的进程中铸就了金代山东文士质朴刚劲的个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该时期文士的豪爽敦厚性格和地区文学清新自然的风气。金人元好问就曾感慨地说:“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1](卷十七)
金代女真政权存在之时,由于政权纷立,战乱频繁,这种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文士自身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金代山东文士阶层空间流动性强、家族文学盛、隐逸思想浓厚、人文主义强烈和沉郁慷慨而又带沧桑的地域风格,而此风格在李之翰、王绘、党怀英、刘长言、石震、赵沨、杨宏道、阎长言等山东文士活动与诗词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领袖文坛的名家多
金代,泰山周边的作家数量尽管在全国所占的比重,至目前还无准确的数据统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金代统治时期泰山的名士出现了众多领袖文坛、引领时代、影响宋金及后世的大家,如大定初期的平阴王去非、王去执兄弟;济南五士中的李之翰、王绘、刘长言等;大定中期主盟金代文坛的奉符党怀英,书法卓越的东平赵沨;能书天下的金末平阴的王仲元,倡导儒学的东平李世弼及其子李昶等等。他们影响了一个时代,并且大部分时间是在泰山周边故乡度过,他们的活动也都与乡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
二、文士空间流动性大
文士的流动往往会带动地域文学的发展与繁荣,金代文士空间的大规模流动,不仅极大带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有力促进与推动了金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终金一代,金代文士然因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等因素影响,就不断地经历着空间流动与变化,这种流动与变化从时间和流动方向来看,大致分三个阶段:一是北宋末金朝初期,文士流动主要从燕云十六州和河南之地流向山东,即从西北部和南部流向中东部,流动的原因主要是逃避战争;二是金朝初中期,主要以宋流向金和金本部或北部燕京之士流向山东为主,流动的方向从北或南部流向山东,造成此种状况主要是由战争俘获、宋使金被扣和政府移民主动迁徙至此形成;三是金末贞祐南渡至元初,文士先流向南后转北。
此状况,如明昌二年(1191年),安阳人赫兟“仆乡为令长山(今山东淄博),被檄泰安。”[2](卷中,P1950)明昌三年(1192年),孔端肃“自阙里之徂徕,访石君德润山齐,游览名胜。”[2](卷中,P1955)彭城毛端卿,“游学齐鲁间,备极艰苦,饥冻疾病,不以废业。凡十年,以经义魁东平”。[3](卷八,P428)王庭筠大定二十年(1180年),调馆陶主簿,因以赃去官,遂置家产于相州,买田隆虑,隐居十年,“山居前后十年,得悉力经史,务为无所不窥,旁及释老家,尤为精诣。学益博,志节益高,而名益重。”[2](卷下,P2892)
对于金代文士的这种流动,有学者指出,“不少士族纷纷由北向南或由西向东迁居。特别是金南渡后,原来出生在黄河以北的许多著名的士族文人大多流落于以汴京为中心的黄河以南地区,或山东、关中等地区。”“贞祐南渡后,活动于豫鲁地区的重要士族文人主要有来自元氏家族、刘氏家族、李氏家族……这些文人在文学、理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使这一地区成为金末全国文化的中心区。”[4](P26)在此背景下,山东文士也大致经历着相同的流动。如泰安奉符人党怀英,便是由于其父党纯睦从冯翊任职于泰安军而寓居奉符(今山东泰安)。此事,正如金人元好问《中州集》卷三《党承旨怀英》小传所言:
“父纯睦自冯翊来,以从仕郎为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遂为奉符人。”[3](卷三,P88)
世代居家山东临清的毛氏家族,因靖康之乱,而迁至大名,后遂占籍焉。而从先祖就迁居云中的衣冠士族刘勋、刘谯兄弟,又客居济南十余年。济南长清人阎长言,长期客居他乡。金人元好问《中州集》载:
“阎长言字子秀,济南长清人。客居兖州之磁阳。……卒于亳州。子鲁瞻、鲁安。今一孙在洺州。”[3](卷九,P470)
朱自牧,字好谦,棣州厌次人(今山东省惠民县),皇统中南选宋端卿榜登科,大定初以同知晋宁军事卒官。从他《晋宁感兴》所说“儿音半已渐秦晋,乡音无因接鲁洙。三见秋风落庭树,年年归意负蒪鲈”和《送麟州节判任元老罢任东归》“春生汶水庭闱近,人去雕阴幕府轻。”“都骑骎骎指汶阳,关门应识弃繻郎”[3](卷二,P72)等诗句中有大量怀念“鲁洙”、“汶水”、“汶阳”等大量文词来看,朱自牧祖籍应为泰山之阳汶河一带,后因科举仕迁才迁徙至山西晋宁一地。
金代山东文士集团群体空间流动性大的原因,首先主要是受战争、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影响造成。如金初“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5](卷九八)“自建炎南渡,中原故家崎岖兵乱,多失其序。”[6](P665)淄川人李楫,“系出陇西。唐末,其远祖官汴梁。石晋之乱,流寓辽之北京,是为大定府。金朝取辽,有昭信校尉讳福者,避乱云中,生子彦直,为汴京行台令史,仕至明威将军、宛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尝尉淄川,乐其风土,遂为淄川人。”[2](卷下,P2895)
金朝末年,由于金蒙之间战争频繁,使“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后裔,不颠仆于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2](卷下P3309)“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人。”[7](P217)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金代文士的生存,进一步促成他们的不停迁徙。原籍易县的濮州刺史侯叔贤,“贞祐之乱,侯年甫十一,从其亲避兵至济南之章丘……以功补昭信校尉,遥授章丘尉。……遥授邹平、齐河两县令,……时其父及先妣王氏,乱后病殁于章丘,……立新茔于鲁城之东原。”[1](卷三十)金代文士空间的这种流动,进一步丰富了山东文士的思想和人格风范,拓展了金代文士家族文学和文化的内涵。
其次,金朝强制移民和科举仕进所需,亦是山东文士流动的一大因素,如辛愿、刘勋等家族迁居河南福昌、山东济南,就是典型的例子;像东平刘长言、真定冯璧、奉符党怀英等。刘长言,河北东路东光县(今河北东光县)刘挚的后裔,因其祖上曾就学东平,而占籍贯。《中州集》卷九载刘氏“字宣叔,东平人。”而检《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知“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人……就学东平,因家焉。”[8](卷三四○,P10849)
大定十年(1170年),泰安奉符党怀英进士及第,调城阳军事判官,十三年又迁新泰县令(今山东新泰市),十五年移官汝阴令(今安徽省阜阳市),后入京。东平赵沨,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进士及第授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军事判官,后累迁至襄城县令(今河南襄城县)。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寿国文贞公东阿人张万公,乃“唐名臣公谨之后,唐末有自东海徙汶上者,后又徙东阿,遂为东阿人。”[2](卷下,P2885)这些文士或任职朝廷,或游宦一方,由于他们身份特殊,无疑对仕宦之地的文化影响至为显著,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怡情山水的特色鲜明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金代,由于社会动荡、战争频繁和自然灾害频发,使金代文士对泰山或以泰山为主体的周边山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游历或寓居或归隐。如奉符人党怀英长期隐居泰山、徂徕山一地;东平赵沨等隐居于鱼山(今山东东阿县)一地;马钰、丘处机等全真诸子则长期活动于昆嵛山一带。据统计,在金代文士群体中有稽可考,有近160余位生于泰山或周边,8位隐居于此,32位供职于泰安,80余位莅临畅游过泰山,近112位活动于泰山周边。像济南长清的陈寿愷“自幼聪慧,博学强记,倚马成文,不求贤达,徜徉自放,及其老也,游灵岩爱泉石之胜,遂卜居焉。与云公和尚解释禅旨,悉入精奥……三十年不出山,寿九十有五。”[9](卷一三,P857)真定人王若虚一生数次登临泰山,后卒于泰山登临道中;元好问“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于1236至1256短短二十年间,不仅七次漫游或寓居于此,而且还留下了大量关于泰山的诗词赋等文学作品,由此可见,金代山东文士怡情山水的思想非常浓厚。
四、崇圣、重理、轻死的儒家治世特点浓
中国古代士大夫作为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集合了社会上的精英,形成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风气,并预示着一个政权国家的兴衰。正因士风之重要,金人刘祁就曾深刻道出“自古士风之变,系国家长短存亡。”[10](卷一三,P103)
山东自古民风素有人好儒术、人情朴厚、尚诗书,尚俭素的美德。正如明代汪子卿《泰山志》卷四《岳治》之风俗曰:泰岳一带“人情朴厚,俗有儒学。去洙泗百余里,人好儒术。风俗淳朴而尚俭素……士尚诗书,民执常业,视昔益加美焉。”[11](卷四,P212)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这种地域文化特征,有效地保持了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趋势。金代山东文士,在继承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又积极汲取这种地域文化的独特风貌,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地实践着儒家固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这可从当时金人的诸多记载中窥知。
“齐鲁,儒学之乡。近世东齐,尤多学者。至于行义修饰,文章学问,可以追配古人,著闻山东,一时后进推尊景慕”。“(莒州镇西军节度副使张商老),以乡先生称之……幼强学自立,家贫无师,闭户独学,日诵千余言,祁寒隆暑弗懈……公为人寡□而事亲孝,居丧如礼,足不至妻之室者三年。两任河州……人以为难,与人交,久而弥笃,语言恂恂,无少长皆为尽礼。至临事,挺然有守,不可干以非义。天资仁爱,弗忍害一生物。老犹笃学,手不释卷……闲居议论,无一妄语。至于俚俗、剧谈、戏论与夫词曲谶绝之作,略不挂口。处已俭约,出无车马之饰,居无器玩之好。勤于吏事,精确不苟。”[2](P1362-1363)
“(张行简)家世儒臣,备于礼文之学。典贡举三十年,门生遍天下……太夫人疾,不解衣者数月。居丧哀毁过礼……自幼至终,未尝少违颜色。与诸弟居三十余年,家门肃睦,人无间言。率励子弟,不知为骄侈。虽处富贵,与素士无异。平生无泛交,无私谒。慎勤周密,动循礼法。居无怠容,口无俚言。身无径行,虽古君子无以加。故天下言家法者,唯张氏为第一。言礼学言文章言德行之纯备者,亦唯张氏之归。”[3](卷九,P468)
济南长清人阎长言,“乃更折节,遂以谨厚见称。”终老于泰山的王若虚少时“质直尚义,乐于周急。乡人有讼,多就决之。”侨寓济南、聊城的固安人李天翼在政期间,“所在有治声。迁右警巡使,汴梁既下,侨寓聊城,落薄失次,无以为资,辟济南漕司从事……且有志于学。与人交,款曲周密,久而愈厚。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为流涕。予谓天道悠远,良不可知,而天理之在人心者,亦自不泯也。”[3](卷八,P434)
金代山东文士们的这种治世理家思想,不仅充分展现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而且还成为本家族的基本道德操守。如《金史·列女传》就曾记载两例金廷追封山东烈女的事例。贞祐元年(1213年),蒙古大军攻陷潍州(今山东潍坊一地),劫掠监察御史李英之妻子张氏后曰:“汝品官妻,当复为夫人。”张氏宁死不屈而被杀害,金追封她为“陇西郡夫人”,谥“庄洁”。贞祐三年(1215年),当红袄军攻占莱州掖县(今山东莱州),在杀害县司官吏相琪一家后,又当奸掠其妻栾氏时,遭到拒绝而惨遭杀害,金廷亦追封她为“西河县君”谥“庄洁”。《金史》在评议此一现象中曰:“若乃嫠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有列丈夫之风,是以君子异之。”[12](卷一百三十,P2798)
五、重视教育,家族文学盛
山东文士重教、尚学,是该地区的突出社会风尚。北宋苏东坡密州任职时,“至今东武(诸城)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的诗文,充分反映了该地域民众尚学的良好社会风气。在这良好地域氛围中,不同时期都曾涌现了大批典范人物,而这些典范人物的存在,又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地区文化的发展昌盛。正如学者所说,“典范人物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可以带出特定地域的文化特色……一个地域典范人物的业绩,能持久地感动他的乡亲……典范人物是一个地区的‘民智资源’”[13](P25)
金代,众多的山东文士,就是该地区的典范人物。他们的活动事迹、诗词著述,无疑推动着该区域文化的发展,并长期影响着本土后人的价值观、荣誉感。由于山东文士多是饱读儒家经书的学者,在他们看来“学圣人之道者也,岂徒诵说其文而已”,继而往往以布宣儒教,淬励风俗为己任。当时学校作为“化民之本,仁义道德之所兴修也,礼乐教化之所宣布也,人才之所作成也,风俗之所变易也”[2](P2119)的最佳传播场所,就成为他们施政的重点。终金一代,山东文士非常重视地方学校的兴建、修葺和发展。如他们在位执政时,往往大力发展地方州县学;退位在野或应举不得意时,也始终关心地方的教育建设,他们或撰写庙学碑文、弘扬义举;或设馆授徒、教授乡里,从而促进了本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
在大力从事地方教育的同时,这些文士又善于利用自己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所处地位的政治势力,积极开拓家族文学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代文学特点,即家族文学和庄园文学的昌盛。譬如奉符徂徕石介—石震—石珪—石天禄家族;东平刘挚—刘长言家族;济南孙荣—孙庆世家;莒州张莘卿—张行简—张行信家族;济南长清闫氏—闫长言家族;奉符党纯睦—党怀英家族;临清毛瑜—毛询—毛君家族;乾州杨震—杨奂家族;淄川邹平的刘异—刘时昌—刘汝翼家族;洛阳史良臣—史公奕家族等。
对于金代家族文学的繁盛,有学者研究称,“仕金汉人中的一些名门显宦、文学世家,家学渊博,从小就注意对子嗣的文化教育,且往往是父母兄长亲自督教,学成名就显于一时。”[14](P23)如淄川刘氏汝翼家族,“世为淄川邹平人。曾大父讳异,政和末,擢进士第。释褐隆平主簿……大父讳伸,不乐仕进,以财雄乡里,周急继困为多。父讳时昌,大定初律学出身,历孟州军事判官,终于左三部捡法。用法详慎,多所平反。后用公贵,累赠大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颖悟,日诵数百言……山东诸儒间声名籍甚。贞祐四年,经义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赐绯鱼银鱼,调兖州录事……子男五人:长曰衍,奏差清沧监司都提举;次曰衡,真定河间路都提举;次曰横,清沧监司都提举;次曰復;次曰元。诸子皆传家学。女二人:一适进士谢芝,一适士族张简。”[2](P2980)再如济南孙庆孙氏家族,“(孙)君讳庆,字伯善,姓孙氏,世为济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考荣,皆隐德不仕。君资禀信厚,早有成人之量,乡父兄以起宗期之……乃授君忠武校尉、济南府军资库使,改行尚书省应辩使……兼行东平府录事……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宠。女一人,嫁金乡县丞栾珍。”[2](P3102)
金代在家族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伴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经济的整体向好和山东经济的快速恢复,庄园经济出现并逐步走向繁荣,以这些庄园为中心,汇集了像党怀英、路铎、路伯达、崔巍、郭安民、刘仲杰、高延年、高公振等一大批金代文学家们,于是在各地文士聚集的区域出现了庄园文学。如路铎笔下的驻春园,梁子直的成趣园,师拓笔下的同乐园,赵秉文笔下的遂初园,高公振笔下的西园,刘迎笔下的归去来园、孔德通东园,杨宏道笔下的秀野园,东平严实的东园、灵泉园等。在庄园内,这些来自于不同地域的文士汇集于此,他们或徜徉山水、或品酒论诗、或诗词题咏、或臧否人物,构成金代文学一大亮点。对于金代文人在庄园活动的概况,金人杨奂在《东游记》中记述说:“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东平行台公宴予东园,是日衣冠毕集,既而请谒阙里。迨丙午,乃命监修官庐龙、韩文献德华、上谷刘诩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华、子中……梁山张宇子渊、汴人郭敏伯达,出望岳门。幕府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阳卢武贤叔贤、亳社李祯周卿……祖于东湖之上。”[2](卷下,P2758)
造成金代这种家族文学昌盛和庄园文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山东地区具有浓厚的思想文学基础;二是以这些文士为主的家族不断地迁移,进一步拓展了家族成员的生存空间,促进了这些家族文化与所居地区本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三是山东地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金代统治者对山东经济文化的重视与推崇。“家族文化代表着一种地域文化……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包括河东理学文化、齐鲁礼乐文化、幽燕游牧文化等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水平。”[4](P29)
六、家族集团大,乡土观念强
钱穆先生曾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15](P51)金代统治的百年间,山东地区由于长期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既有周公仲尼遗风、好儒习礼,又有宽缓阔达、不喜群斗、重乡土、尊家族的风俗,从而有助于形成金朝山东文士家族集团强大和乡土观念强的地域特色。
山东文士群体中,像莒州的张氏家族(张莘卿),一门就有十余人问鼎。史载“公未第时,以诗赋教授乡里几二十年,门人子孙,相继登科至十数。其淹回场屋,以词学闻于时者,尚不可胜数。最后孙行简大定十年赐状元及第,皆公亲教之。虽晚入官,仕不大显,观其门人子孙卓立成就,见效如□,则公之学为可知矣。”[2](P1363)亦如《金史》卷一百七《张行信传》所记:“公初至汴,父讳以御史大夫致仕,犹康健,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行信为礼部尚书,诸子侄多中第居官,当世未之有也。”[12](卷一百七,P2371)“金代一些家族之间、家族成员内部之间的真诚相助,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罕有其比……家族之间的友爱互助更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长久生命力与影响力。”[4](P29)
当然当我们透过山东文士发展运行的轨迹,去深思这种发展的根源时,不难发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山东文化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时代性、大众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且历经几千余年而不衰,关键就在于此种文化源于的地域环境和典范人物的实践及时代的氛围。而正是基于山东地区悠远厚重的文化底蕴,经过金代一百多年的发展,在金朝不同历史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同乡、师友、同僚关系的山东文士群体,并将金代山东文学推动至鼎盛,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元代。
[1][金]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阎凤梧.全辽金文[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3][金]元好问.中州集[M].中华书局出版,1959.
[4]杨忠谦.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J].北方论丛,2012(1).
[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
[6][宋]杨万里.诚斋集[M].古籍出版社出版,1989.
[7]李修生.全元文[M].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
[8][元]脱脱.宋史(卷340)刘挚传[M].中华书局出版,1977(11).
[9][清]舒化民修、徐德城篡.长清县志,清道光15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1976.
[10][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M].中华书局出版,1983(6).
[11][明]汪子卿著,陈伟军点校.泰山志[M].泰山出版社,2005.
[12][元]脱脱.金史[M].中华书局出版,1983(11).
[13]王宁.中国文化概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14]史韵.仕金汉人与金朝的教育和科举[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4).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