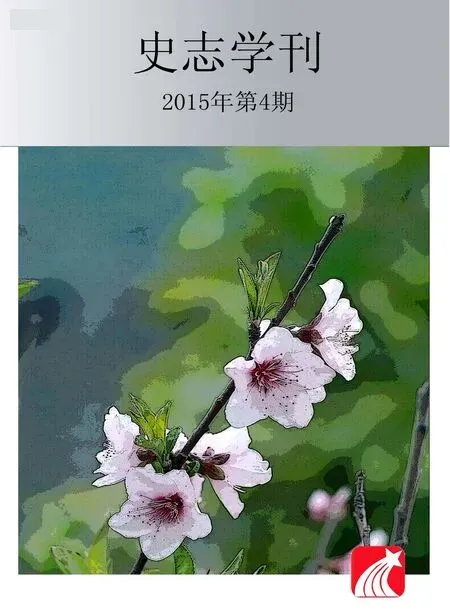书写法律:明清案狱故事中的民众法律认知与司法文化
何永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法律认知是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态度的总称,既包括人们对法律的零散、偶然、感性的认识,也包括一些系统、必然、理性的认识。长期以来,学界有关古代法律制度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而对于民众法律认知的研究却少有问津[1]已有研究成果,参看徐忠明.从明清小说看中国人的诉讼观念.中山大学学报,1995,(4);范忠信.从明清市井小说看民间法律观念.法制现代化研究,1998;萧伯符.中国古代民众法律意识是儒家化而非鬼神化——兼与郝铁川教授商榷.法商研究,1998,(4);徐忠明.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徐忠明.众声喧哗: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黄宗智先生曾呼吁从经济、社会和文化多面向研究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2](美)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明清是中国古代法律条文最为周详、法律制度大为完备的时期,由于缺乏有关一般民众意志和表达的第一手资料,民众的法律观念在正史和律条中往往难以反映,而笔记小说中的案狱故事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3]本文所谓“案狱故事”主要以单篇的形式散见于各笔记、野史或小说集中,以各色案件为题材,以作案、断案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为主要叙述内容,有诸如公案小说类的虚构故事,兼有作者亲身经历并加以记录者。。正如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所言,常规的历史叙事表达了权力与策略,口口相传的故事则是理解民众的基准[4]Michel de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P23)。
案狱故事早在先秦时期已有记载,如《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叔向刑不隐亲”[5]陈茂菊.叔向刑不隐亲.现代法学,1986,(2).。宋元时期,随着话本的出现,公案体裁的小说亦不断涌现。明清时期公案小说及书判体作品得到蓬勃发展,一如《龙图公案》《百家公案》等公案小说集。明清文人笔记中记载案狱故事者则更多。其中对司法活动、诉讼心理的描绘堪称民众法律认知的典型反映。案狱故事以市井细民为描摹对象、以世态人情为描写旨趣。故事中的冲突、纠纷不仅多方面展示了审案断狱的司法活动,同时也传达了当时民众对于司法、罪罚的认知、态度和情感,为了解明清乡民的法律认知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1]梁治平在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时使用了较多的笔记、小品和故事,参看氏著《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不仅将小说笔记、戏曲、杂剧与正史相结合,更涉及谚语、竹枝词等材料,参看氏著《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美国学者Robert E.Hege与KatherineCarlitz利用文学材料与法律研究相结合,考察法律文本与法律知识的普及,参看Hegel,Robert E,Carlitz,Katherine.Writing and Law in Late Imperial China:Crime,Conflict,and Judgment.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7.。尽管一些故事不可避免地有着文学艺术的夸张虚构,所表达的诉讼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人与乡民的混合物。然而其“寓劝戒,广见闻”[2]四库全书总目(卷140).(P1182),“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3]四库全书总目(卷51).(P460)。
法在必行:民众心目中的官与法
在中国古代庶民百姓心目中,法律是严肃而公正的,为民濯清冤情,向社会惩恶扬善,所谓“天网恢恢,曾何漏哉!”[4](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 1).叙述生动、情节跌宕的案狱故事借助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之口表达了民间社会对法律和司法的最大愿望:法律维护公道,才实现了司法的根本目的。
法律是统治者权力意志的体现,对作为弱者的乡民来讲,官吏的严格执法是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而为民伸屈抑冤乃地方官职分所在。明太祖曾对州县官提出明确要求:“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咸尸位素餐,冒贪坏法,自触宪法,尔等其慎之。”[5]明太祖实录(卷19).洪武元年秋七月丁丑.对于知县执掌,《清史稿》首先指明,“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6]清史稿(卷 123).职官三.(P3357)断理词讼的地方官既拥有国家官吏的身份,可行使职权为民主持公道,锄强扶弱。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为官者亦会在公堂上行刑逼供,甚至出于利益的驱使、道德的沦丧,成为包庇罪犯、惩善扬恶的“贪官”“昏官”。在这种情况下,法就成为了成为敲诈、压迫人的工具,导致冤情出现。
案狱故事中有许多笔墨涉及贪官污吏制造冤狱,不乏对酷刑诬服等司法腐败的揭露。如“沈鸟儿”一案。故事因一只画眉鸟引发多起血案。为讨回公道,当事人累讼于官。在官府刑罚逼供的淫威下,数次成狱,继而引发案中案,牵扯无辜者四人性命[7](明)朗瑛.七修类稿(卷 45).(P471)。“沈鸟儿”之祸根乃断案者懈怠民冤,一味把刑讯作为司法的纠察工具,不能秉公执法所致。“孙霖冤狱”记:“南京刑部员外郎孙霖,熟于刑名。有二人同殴一人致死,死实由甲,乙惟解劝,同逮至部。甲家富,令所亲求于孙,因以酷刑逼乙认其罪而脱甲,乙终被决。临刑,冤号不已。次日,孙赴部,见乙立于马前,叱之不退,回即吐血,七日而死。”[8](明)王.寓圃杂记(卷 10).(P85)孙氏因“甲家富”而贪图贿赂,对无辜者滥施酷刑。不但酿成冤剧,也亵渎了百姓心目中法大于天的公平。《雪涛小说》中有一冤狱:南郊祭祀丢失一只金瓶,怀疑是一厨工所为,“遂执之官司,备加考掠,不胜痛楚,辄诬服”。后查明真相,实系冤枉。作者亦说:“然则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国家开矜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9](明)江盈科.雪涛小说.(P56)类似的故事无不在控诉官府强加刑讯以使小民畏服,反映出庶民对严刑害人的惧惮,对为官者舞文弄法、任意出入人罪的讽刺,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民众对为民解除缠讼、平反冤抑的清官循吏的呼唤。
一些案狱故事通过鬼神灵怪的介入、因果报应的循环表达了对官吏疏于刑案、执法不公的不满。《滦阳消夏录》中有一事例:献县县令明晟曾欲申雪一冤狱。面对存疑的冤案,唯恐上级不允,故在“平冤”与“委命”间踌躇不已。故事即借助鬼怪狐仙之口指出,“明公为民父母,但当论其冤不冤,不当问其允不允,独不记制府李公之言乎?”[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滦阳消夏录(一).(P10)身为父母官,既身握事权,理应为民洗冤平屈。束手委命只能有愧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官之箴。另一个故事中,掌管阴间事务的阎罗王哂笑某县官:“公一身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县官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辩称。阎王继而斥责道:“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1](P12)案狱故事借助诙谐生动的鬼神故事,宣扬惩恶赏善的宗旨,呼吁官员能治狱精察、伸张正义。“鬼神皆得而窥,虽贤者一念之私,亦不免于责备。”[1](P13)在乡民视野中,以鬼灵神怪为代表的超自然力知人心微暖,道出了民众希望为官者都能成为清官、好官、父母官的心声。
案狱故事中因果报应观念的书写,反映了民众的一般观念:为恶者必有恶报。纪昀笔下,民人张福在过桥时因与当地豪强争路,而被后者推入桥下,奄奄一息。不料伤人性命的里豪却“遽闻于官”。官府“利其财,狱颇急”。张福自知命不久矣,甘愿“乘我未绝,我到官言失足堕桥下”,只请求里豪为之赡养母亲。二人立下字据,生供凿凿,官吏也无可奈何。不料张福死后,里豪背信弃义。张母以字据“屡控于官,终以生供有据,不能直”。里豪与官府勾结,张家冤屈不鸣。而这一故事最终以“豪后乘醉夜行,亦马蹶堕桥死”告终,向人们传达了“负福之报”的道理。此中,法理与情理、因果与报应环环相扣。作者在故事结尾不禁感叹:“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有贿和者,甘鬻其所亲。斯已猝不易诘矣。至于被杀之人,手书供状,云非是人之所杀。此虽皋陶听之,不能入其罪也。”[2](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滦阳消夏录(五).(P193)
与司法黑暗、官吏昏庸对应的是法律清明、人间正气。“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畏吾能而畏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和廉洁促成明察与威严,这无疑都是司法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而失去秉钧之心则阻塞公正,导致“枉直而惠奸”“赏僣而刑滥”[3](明)徐榜.宦游日记.(P1)。“惟公生明,偏则生暗”,这一明清官场的主流认识,与案狱故事所传达的官员应秉公执法不无契合之处。因为秉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官员在司法活动中能否分清是非,能否坚持原则,能否为民持正。一些案狱故事详细刻画了官员处理案件时悉心鞫问、审慎析疑的形象,而最终断案得宜,人皆称快。
制府唐公执玉,尝勘一杀人案,狱具矣。一夜,秉烛独坐,忽微闻泣声,似渐近窗户。命小婢出视,噭然而仆。公自启帘,则一鬼浴血跪阶下,厉声叱之,稽颡曰:“杀我者某,县官乃误坐某。仇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讯。众供死者衣履,与所见合。信益坚,竟如鬼言改坐某。问官申辩百端,终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其幕友疑有他故,微叩公,始具言始末,亦无如之何。一夕,幕友请见,曰:“鬼从何来?”曰:“自至阶下。”曰:“鬼从何去?”曰:“歘然越墙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无质,去当奄然而隐,不当越墙。”因即越墙处寻视。虽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后,数重屋上,皆隐隐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囚贿捷盗所为也。”公沉思恍然,仍从原谳。讳其事,亦不复深求[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滦阳消夏录(三).(P103)。
这一故事中,囚犯本该伏法认罪,却试图委托盗贼装扮成的“冤魂”向执法者求情,以达到翻案的目的。唐公轻信了假扮者“仇不雪,目不瞑”的谎言,在提讯后做出改判。然而,细心的幕友戳穿了其中的阴谋。终于在“申辩百端”后,“以为南山可移,此案不动”。得益于幕吏的详究得实和县官的精察治狱,最终避免了冤屈的出现。这样的故事结局正是为里巷细民所拍手称道的。
众声喧哗:“息讼”与“好讼”
《周易》“讼卦第六”云:“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将“讼”视作不吉利的卦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诉讼的价值评判:诉讼会打破秩序的和谐,应避免。《论语·颜渊》记载孔子曾说“必也使无讼乎。”康熙帝颁《圣谕十六条》,在宣扬“讲法律以儆愚顽”的同时也强调“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息诉与无讼正是传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
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古代庶民的法律意识是十分淡薄的。然而从明清笔记小说中的案狱故事来看并非如是。每当涉及纠纷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诉诸官府。“杨评事辨舟子奸”一案中,周生与赵生本相约出行,遍寻三日而不见后者,周生惧怕官府调查就先“具牍呈县”自证清白[1](清)宋邦僡.祥刑古鉴(卷上).。《续只麈谭》载有“捉奸误杀”一事。故事中,哥哥怀疑弟弟与妻子有私,试图捉奸而错杀他人[2](清)胡承谱.续只麈谭.泾川丛书(第 25册).。哥哥本一介乡野农夫,却也懂得“在奸所误杀者无罪”的刑名。虽然可能这只是对法律中有关规定的简识粗知,但这一事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大众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书安邑狱”一案中,杨继业和张歧指两表兄弟发生争执,家人闻声出劝,然而因事情复杂,争论不一,随即“群拥至县廨”,找县官评理,以求实情[3](清)吴芗厈.客窗闲话(卷 4).。“徽商案案中有案”中,丈夫不知实情,误以为商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随即“讼于郡”[4](明)冯梦龙.增广智囊补.。此类情节案狱故事比比皆是。可以说,几乎每个故事都由民众直诉官府而起。
在一些案狱故事中,如果百姓大众决定诉求官府,则会坚持诉讼,甚至经年累世互不相让。《阅微草堂笔记》有一事就颇具代表性。故事中两家争讼坟山,每逢祭祀必争斗不休,每次争执必械斗不止。双方坦言,不足一亩的地皮诚然“无锱铢之利”。而此事涉及两家的“祖宗丘陇”,双方都以敬“先人之体魄”为由,不愿为他人所占据。不论是根据契券还是地粮串票,官方都不能做出使人信服的决断,故打了持续四、五十年的官司,骇然“阅两世矣”[5](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7)·姑妄听之(三).(P883-884)。纪昀也感叹:“天下有极细之事,而皋陶亦不能断也。”此类案狱故事一方面反映出乡民遭遇不平即求诸官府县衙,自认有理有据即坚持讼告。另一方面折射出明清某些地区纷然好讼、健讼成风的社会风气。明代清官海瑞曾对江南刁讼的风气大加斥责,“淳安县词讼繁多,大抵因风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已是私,见利则竞,以行诈得利者为豪雄,而不知欺心之害;以健讼得胜者为壮土,而不顾终讼之凶。而又伦理不惇,弟不逊兄,侄不逊叔,小有蒂芥,不相能事,则执为终身之憾,而媒孽讦告不止。不知讲信修睦,不知推己及人,此讼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6](明)海瑞.海瑞集.(P114)在海瑞看来,某些诉讼者受利益驱使,一味求胜的心态忽视了乡土社会讲信修睦的道德观念,认为这是对道德的贱踏。清康熙时休邑县知县吴宏曾接连发布告示“禁健讼”,称:“或因口角微嫌而驾弥天之谎,或因睚眦小忿而捏无影之词。甚至报鼠窃为劫杀,指假命为真伤,止图诳准于一时,竟以死罪诬人而弗顾……更有不论事之大小,情之轻重,理之曲直,纷纷控告。一词不准必再,再投不准必三,而且动辄呼冤,其声骇听。及唤至面讯,无非细故。”[1](清)吴宏.纸上经纶(卷五).(P205)这则告示描述了负气告状且毫不收敛的市井民人,反映出为官者对纷然好讼者的贬斥态度。累牍连篇的状告给官方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市井细民争相讦讼的世风日薄使之不得不对健讼者进行纠正引导。“好讼”与“健讼”与学界提出的明清社会“诉讼爆炸”现象形成呼应[2]相关讨论参看,卞利.明清徽州民俗健讼初探.江淮论坛,1993,(5);邓建鹏.健讼与息讼——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解析.清华法学(第四辑).2004.180—198;徐忠明,杜金.清代诉讼风气的实证分析与文化解释——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2007,(1);夫馬進编.中国訴訟社会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出版會,2011.829—832;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2012,(4).,而其显然带有盲目性、冲动性。“据理好争”和“不忍”性格造成的重复渎陈和谎捏虚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行,亦扰乱了“和为贵”的社会秩序。正如清人刘衡在《庸吏庸言》中所说:“夫小民钱债田土口角,一切细故,一时负气。旁有匪人耸之,遂尔贸贸来城,忿欲兴讼,实则事不要紧,所欲讼者,非亲即友,时过气平,往往悔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3](清)刘衡.庸吏庸言.《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为我们理解乡绅士人和百姓大众两种人群对“讼”的不同态度提供了一个视角:
申苍岭先生,名丹,谦居先生弟也。谦居先生性和易,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介则如一。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先生以两家皆士族,劝妇父兄勿涉讼。是夜,闻有哭声远远至,渐入门,渐至窗外,且哭且诉,词甚凄楚,深怨先生之息讼。先生叱之曰:“姑虐妇死,律无抵法,即讼亦不能快汝意。且讼必检验,检验必裸露,不更辱两家门户乎?”鬼仍絮泣不已。先生曰:“君臣无狱,父子无狱,人怜汝枉死,责汝姑之暴戾则可。汝以妇而欲讼姑,此一念已干名犯义矣。任汝诉诸明神,亦决不直汝也。”鬼竟寂然去[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滦阳消夏录(四).(P168)。
苍岭先生“性爽豪,而立身端”,是乡绅士族中较有威望者。当族里“有妇为姑虐而缢者”时,先生先以两家和睦为由,极力劝诫死者父兄毋告官成讼。面对当事人的冤魂“深怨先生之息讼”时,苍岭先生则力陈“姑”“妇”之辨,甚至没有过多地表达同情就以“无狱无讼”叱之而去。当“息讼”与“孝义”等社会秩序建构相捆绑,诉讼即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墙。
“无讼”恰似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息讼”仅是一种试图消弥纠纷的手段。官方强调“无讼”与司法实践中的严刑峻法成为形塑乡民法律观念的重要因素。应当注意的是明清官方所惯用的措辞,凡“睚眦小怨”“口角细事”“蒂芥小事”“鼠雀细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该如何界定?如《虫鸣漫录》中有一“击母舅齿落者”,愤怒的舅舅随即告官[5](清)采蘅子.虫鸣漫录(卷 1).。这确属于鼠牙琐事,因为类似的纠纷不必动辄诉诸官府。而诸如“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等在官方话语中的“小事”,比之庶民则可称是有关是非善恶、生存所需的情法理断了[6]皇明制书(卷 8)·“教民榜文”.(P287)。社会讲求无讼,官方无不希望臣民守法,民人诚然希望身膺民牧的父母官能为民伸冤理枉。而为引起官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对讼案漠不关心的官员尽快解决纠纷、做出公断,当事人很自然地夸大民事案件的危害程度。因此,官方话语那些极为普通的“细事”案件往往反映出某些官吏的隐微心理,“健讼”尤变得耸人听闻[1][1]黄宗智认为,直到民国时期概念的引进和词汇的使用才区分了细事与重案之别,代之以民、刑之分。而在旧架构中,细事与民事同是对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触犯,仅在刑罚程度上不同。参看氏著.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P176)。两种不同语境的鲜明对比,恰恰反映出官、民对法律意识和诉讼态度的差别认识。官方书写者对“健讼”的描述与“无讼”的意图一样,是一个基于道德和现实层面的价值判断[2]吴佩林.清代地方社会的诉讼实态.清史研究,2013,(4)。
掩映之间:法意与人情
对于法律与情理道德间关系的讨论,既是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学界反复讨论的学术话题之一。通常认为,传统中国法律的基础是道德与情理,这不仅体现在立法上,而且表现在司法审判上。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官员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起着上通下达的作用,国家所有法律政策都要靠官员去推行实施。但案狱故事中的断案官员较少遵循正当的“法定程序”,往往强调处置和判决时必须合情合理,而不一定要合乎法律。案狱故事中的司法活动不像刑案汇编那样,将当事人、原被告的陈词条讼具体录入,且断案者极少援引具体的法律条文。明人张瀚任庐州知府时曾处理了一桩“兄弟构讼财产案”:
大名有兄弟构讼财产,继而各讦阴私,争胜不已。县令不能决,申解至郡。余鞠之曰:“两人同父母生耶?”曰:“然。”余曰:“同气不相念,乃尔相攻,何异同乳之犬而争一骨之投也!”取一杻各械一手,各重笞之,置狱不问。久之,亲识数十人入告曰:“两人已悔罪矣,愿姑宽宥。”唤出,各潸然泪下,曰:“自相构以来,情睽者十余年,今月余共起居、同饮食,隔绝之情既通,积宿之怨尽释。”余笑曰:“知过能改,良民也。”遂释之[3](明)张瀚.松窗梦语(卷 1).(P24)。
作为理讼人的张瀚首先教训争产的两兄弟,随即采取“一杻各械一手”的轻微惩罚做以警示,并将二人置狱不问。两兄弟在监狱中同吃同住,重新唤起了隔绝的亲情,往日的积怨亦渐渐消解。如此非常规的断案方式,不仅使词讼得以平息,且曾经针锋相对的两兄弟也成了张瀚眼中知错能改的良民。
案狱故事中,地方官们倾向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采用说理、劝告、教化的方法为当事者上一堂“教育课”,而非采用刑罚施以威严。清人陆陇其任知县时,处理了一桩著名的“兄弟争产”案。陆氏在审理时并不问曲直,而是让兄弟“在法庭之上,此呼弟弟,彼呼哥哥”。如此,“未及五十声,已各泪下沾襟”,最终“念尔兄弟均已悔悟,免予重惩”。陆陇其在判词中写道:“夫同声同气,莫如兄弟,而乃竟s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从此旧怨已消,新基共创,勉之勉之。”[4](清)陆陇其.陆稼书判牍.这份判词并没有引用律文,但它的所起的社会效果超过了简单的依法判决,甚至在民间传为美谈。
案狱故事倾向于陈述情理高于法律的理念。故事中弱势群体往往为执法者和民众所同情,故官员对弱势群体多施以私人救济,或予以法外开恩。晚清魏息园编有《不用刑审判书》一书,其书名就表明作者对执法者“不用刑审判”的关注与反思。魏氏“叹为治者之用刑不明,痛被法者之已死不可复生”,故此书“付之手民,用以质之有私牧之责者”[5](清)魏息园.不用刑审判书·序.。《不用刑审判书》中,有一人偷砍山中小树,山主将其绑到县衙。县令并未判砍树者有罪,而先是训斥山主没有礼让之风,批评说“人斫寸木作刀柄亦涉讼”,最后“斥之去”[6](清)魏息园.不用刑审判书(卷 4).。所谓“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讼也者,势之所趋,人情之所断不能免。”[1](清)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P940)在一些案狱故事中,人情超越法律,从而维护伦常,保全体面,也体现法律的公道。《子不语》“赵友谅宫刑充军”一案较具代表性:年老的赵成平素无赖,竟然凶恶到“奸其子妇”。儿子赵友谅与儿媳搬家投靠到邻村牛姓亲戚家,试图“迁远处以避之”。而赵成一路探听,以金钱诱惑村中恶霸孙四。二人协力将牛家灭门,并将金银细软席卷一空,继而嫁祸给赵友谅。官府接报后前去捉拿,并施以严刑拷打。赵友谅出于孝义,不愿揭发其父罪行,屈打成招。但因杀人凶器“屡搜不得”,始终不能定案,牵连了乡邻人十余家。后来赵成被带去复审,自以为已经结案,喜形于色。不料儿媳道出案情。官府照旧采取“烧毒烟熏其鼻”的刑讯逼供最终翻案。按《大清律》,杀死一家五人者,亦须自家五人抵命。按察使与抚台念及赵友谅的孝行为其求情。最终,乾隆帝下旨:“赵友谅情似可悯,然赵成凶恶已极,此等人岂可使之有后!”赵成凌迟处死,赵友谅免死改宫刑充军。此中,人伦情理与法理法意此消彼长。最终,最高统治者的一条谕旨突破法意,扭转了案狱故事的结局。
《子不语》虽专记鬼神怪异之事,然其搜奇猎异,或取好友述闻,或录公文邸抄,“赵友谅宫刑充军”即确有其事。《清实录》记录了乾隆帝对此案的改判:“原以此等凶恶之徒,已绝人之嗣,自不应复使其尚留余孽。固属准情酌理,罪所应得。但详核此案情节,赵友谅因伊父欺奸伊妻,即行携眷迁避。及伊父犯案后,复代为认罪。若按例寘之重辟,情又可悯。然赵成杀死一家六命,绝其后嗣,残忍已极。若今因赵友谅情节可矜,即行宽释。是赵成淫恶凶犯,转得有后,于情理未为允协。朕酌之情理,著将赵友谅从宽免其死,但改为宫刑。俟百日平复后,再发遣乌鲁木齐。以示法外施仁之至意。”[2]清高宗实录(卷1176)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庚子.袁氏笔下所记与实录无二,而案狱故事借助作者生动的笔墨与省思展示了古代司法活动中的诸多细节。其中的“准情酌理,罪所应得”“寘之重辟,情又可悯”“情节可矜,即行宽释”等关键字眼无不反映了司法审判上的人情与法律的复杂斗争。诚然,按照当时的法律,赵友谅本当斩首抵命。而官吏为其求情,最终仍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开释。乾隆帝反复陈述“酌之情理”反映了其“法外施仁之至意”的良苦用心。人情的介入无疑使得司法裁量的客观性与确定性相对弱化,即违背法理而顺应情理,却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下维护伦常、宣扬孝义的绝好诠释。所谓“必不能断之狱,不必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10)·如是我闻(四).(P470)。
此外,故事中还体现了较明确的证据意识,即定案须有证据。故事中县官多次传讯乡邻。但由于定案强调物证,命案要见尸身、凶器,即使赵友谅遭昏官重刑蒙冤招认,也不能蒙蔽百姓大众,不能违背核心的“天理”与终极公正。广大民众心里,正是把“天理”放在首要位置,无论是执法者的私力救济,或“不用刑审判”,任何决断都不能“伤天害理”。所谓“天无心,以天子为心;天子无心,以百官为心;百官亦无心,以万民为心也”[4](明)汪天锡.官箴集要(卷上).。当情和法产生矛盾冲突时,判决合乎情理或不愧百姓大众的心理预期,法外开恩、罪名开释可被接受。情理对法理的超越虽然大大削减了法理在断案中的分量,却恰恰反映了民间意识与官方意识中对官方“息讼”意图的形塑。
余论
案狱故事贴近百姓生活,从向民众讲述猎奇的案件,到为民众宣扬人情法理,传达了“以刑为本”“终极正义”的观念。它所表现出来的奇人、奇事、奇情不仅符合大众的审美需要、道德需要,也符合官方教化民众的实际需要。诸多的案狱故事教导民众如何应面对生活中的纠纷、如何应对刑事案件,从而形成了关于民间法律秩序的独到的认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民众可以通过求助官府刑诉来解决纷争。官员应当遵循“讼情万变,司刑者可据理率断”的原则,保证司法实践的公道[1](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 5)·滦阳消夏录(五).(P193)。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司法制度的腐败,公正的实现并非易事。即使如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义终将会实现,冤狱定能濯清。
将案狱故事用作史料会引出相应的“历史阐释”问题。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文人笔下的案狱故事是基于实际经验与观察所书写的,但与此同时,它们也被作者自身的情感和价值观所左右。作者在写作中或许不太关注叙述的准确性、细节性与全面性。然而,单就以上因素而言,这并不能阻碍我们透过案狱故事找寻古代民众遗失的话语。与单纯的政治事件的研究不同,前者研究的有效性取决于精度,而民间法律意识的研究则是民众对法律感知的余音,正得益于案狱故事模糊性的描述。当然,现实中的刑案诉讼活动只会比案狱故事所描述的更为错综复杂。案狱故事并不能完整地勾勒出古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全景图。虽然如此,案狱故事仍可视为凝聚和传播法律知识的重要载体,表达了他们对法律、诉讼、刑罚和执法者的认知和感受,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引乡民建构出符合官方意识的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