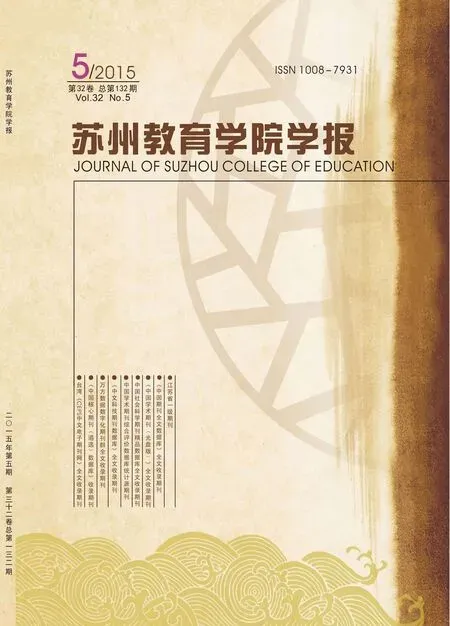南社人“捧角”中的戏曲现代性因子
周淑红(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南社人“捧角”中的戏曲现代性因子
周淑红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南社(1909—1923)这一文学团体在晚清对戏曲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除了来自南社成员发表的理论主张,还来自他们的艺术实践,其中他们把“捧角”作为倡导政治革命和戏曲改良的手段。从南社成员捧京剧演员冯春航(1888—1942)这一行为出发,可以管窥晚清戏曲中出现的现代性因子:与晚清戏曲改良的关联,戏曲演员社会地位的新变以及南社人“捧角”所展现的晚清都市大众文化。这些现代性因子对中国现代戏曲的自我确立意义深远。
关键词:南社;捧角;冯春航;戏曲改良
南社是1907年由青年爱国诗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在上海发起,1909年在苏州正式成立的一个以文章相砥砺、以气节相标榜、以诗歌相酬唱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这一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写下浓墨重彩篇章的文人群体对晚清的戏曲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南社人“捧角”①南社人捧角中的“角”一般指冯春航和陆子美,本文仅谈冯春航。1909 年11月,南社在苏州成立并第一次雅集,恰逢京剧兼新剧演员冯春航在阊门附近某剧场演出。柳亚子和社友俞剑华每日前往观剧。1911年2月,南社第四次雅集,又逢冯氏演出,柳亚子偕社友再次捧场,因感动赋《海上观剧赠冯春航》七绝二首,其一云:“一曲清歌匝地悲,海愁霞想总参差。男儿纵有心如铁,忍听尊前血泪碑。”(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6页)南社的“捧角”风习从这一次观剧中开启。此后,柳亚子经常携同其他南社社友一起观看冯氏演出。以柳亚子为核心,在南社中培养了包括陈布雷、林一厂、姚石子、俞剑华、庞檗子、叶楚伧、朱少屏、沈道非等人在内的冯春航的忠实观众。柳亚子还与南社社友们在主持的《民立报》《中华民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日报》等诸多报刊及南社社刊《南社丛刻》中发表了大量揄扬冯春航的文字。这一由单一行为导向的一系列文化变革中,可以管窥晚清戏曲中出现的现代性因子。这些现代性因子与传统有别,对后来戏曲的自我确立影响深远。
一、南社与冯春航:对象的锚定
戏曲改良运动的理论鼓吹以及舞台实践在晚清戏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后,社会各界呼吁变革,一些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熏陶的爱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国家民族处于存亡危急关头,从戏剧与社会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强调戏剧的社会作用,极力将戏剧与民族存亡、社会改良、国民精神改造结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戏剧自发轫起就多重视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以利于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而这一时期戏剧改良的提倡者,利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观念,涤荡了中国传统戏剧原本包含的封建伦理教化的庸俗内涵,赋予它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功用,使它承载“革命救国”这一新的时代思想。
早在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认为小说、戏曲能“使民开化”,“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①。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要把小说、戏曲同维新变革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要求小说、戏曲为社会改良服务。②以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戏曲改良,主要由知识分子在案头进行,虽然进行了一些创作实践,编写了一些新剧本,但这些剧本大多不符合舞台演出要求,所以很难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通过舞台表演来感染观众从而给他们以启蒙的效果。1904年10月,陈去病、柳亚子、汪笑侬等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在发刊词中,他们明确表达了以戏曲改良挽救中国时局沉沦的革命立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惟一之目的。”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其潜台词就是要求反清革命。事实也确乎如此。在发刊词中,柳亚子(亚庐)极力主张排演“扬州十日” “嘉定三屠”以及法国革命,美国独立等中外历史剧,以激励民众“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④。这些言论在舆论界、戏剧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而且,南社的这些成员也非常重视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的艺术实践,并通过与戏曲艺人的密切合作,使自己的改革主张真正体现在舞台上。南社成员把“捧角”作为倡导政治革命与改良戏剧的手段,有力地配合并促进了近代轰轰烈烈的戏曲改良与政治革命运动。
南社成员把“捧”这一行为的对象定位于冯春航,可以说是南社人自己对戏剧的期待和“角”的思想、行动等特征的不谋而合,因为冯春航自身就主张戏剧应以改良社会和启迪民智为己任。据《中国戏曲志•上海卷》记载:“冯春航除演出传统戏《三娘教子》 《花田错》 《鸿鸾禧》 《贵妃醉酒》 《儿女英雄传》外,又热衷提倡内容进步的新编清装或古装戏,清光绪三十年(1904)和夏氏兄弟在丹桂茶园以《玫瑰花》一剧开风气之先。新舞台建立后,又排演《妻党同恶报》、《新茶花》、《恨海》(一名《情天恨海》)、《江宁血》、《贞女泪》(一名《刑律改良》)、《黑籍冤魂》、《冯小青》、《红菱艳》、《杜十娘》、《花魁女》、《孟姜女》、《薄汉命》等‘醒世新剧’。”[1]因此,他的演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真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南社人捧冯春航并不是单向度的文人对伶人的捧,而是一种惺惺相惜、志同道合,甚至有点相见恨晚的意味。或者可以说,南社人在戏剧上的理论主张在冯春航这个“角”身上得到了呼应,捧者与被捧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南社人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对戏剧的理论见解,而“角”冯春航在舞台上践行着这种理论主张。但是,这并不是理论对实践的单向度指导,而是二者之间的一种不期而遇,相遇后又互相影响的关系。冯春航早在十五岁(1902)时,即自编自演新戏《玫瑰花》,内容是说一个叫玫瑰村的地方,有一位能文能武的少女玫瑰花。村子被猛虎侵入,伤人害畜,村民请来前村猎户相助驱虎,虎害虽除,但是猎户盘踞不走,带来人祸。在玫瑰花的带领下,众村民齐心协力方才赶走猎户,恢复家园。该戏显然是影射借清兵招来后患的故事,表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该戏演出后反响很大,剧中人物被称为“法国自由女神”的中国象征。另外还有一部戏叫《江宁血》⑤,是反映辛亥革命的。早期南方京剧就有如此关怀时事、结合现实的创作实践,是十分难得的,给予后来者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南社成员之一陈去病(佩忍)的《论戏剧之有益》是阐发文艺之社会功能的名篇,他在其中强调戏剧的社会意义:“彼也囚首而丧面,此则慷慨而激昂;彼也间接于通人,此则普及于社会。对同族而发表宗旨,登舞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垂涕以道……”[2]308也就是说,戏剧的作用不单单是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它还有启蒙的意义,能在观众中调动起一种想象性的诗性正义[3],使社会各界在不知不觉中,“情为之动,心为之移”,最终有助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陈佩忍认为只有在戏剧里面潜藏着暴动和秘密这两种相为表里的质素,才可以通过它表达目的。他认为戏剧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作用如此巨大,是因为它保存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并且能够直接面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惟兹梨园子弟,犹存汉官威仪,而其间所谱演之节目之事迹,又无一非吾民族千数百年前之确实历史;而又往往及于夷狄外患,以描写其征讨之苦,侵凌之暴,与夫家国覆亡之惨,人民流离之悲……通古今之事变,明夷夏之大防;睹故国之冠裳,触种族之观念;则捷矣哉!同化力之入之易而出之神也。”[2]310即是说,戏剧的妙处在于能够以一种表面的合法的形式将那些反抗的、潜在的颠覆性的力量不露痕迹地伪装起来。并且,他认为,戏剧团体本身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它可以成为汇聚革命力量的组织。其实,陈佩忍已经把戏剧作为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他用一种转喻的修辞勾连起戏剧舞台与现实的关系,不仅仅要求舞台上的表演具有移风易俗、开启民智、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作用,而且,他还期待戏剧孕育出现实中的革命行动。从这一点,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德国戏剧理论家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的行为表演美学,这种理论主张把身体的扮演作为一个符号过程,这个符号的意义指向体现在把精神和身体这两个世界连成一体的过程中,把戏剧舞台与日常生活场景结合起来,使事件的发生在两者中穿梭。[4]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一种社会性的驱动和变革,不管是20世纪初作为南社社员的陈佩忍,还是当代德国戏剧理论家,其实都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伦理呼唤。
事实上,在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梨园中人已不满足于仅仅在舞台上进行宣传,表达爱国热情,而是从粉墨登场变为拿起武器走上战场。在这一时期,上海成立了伶界商团,夏月珊、夏月润兄弟与潘月樵均为商团负责人,并兼任上海伶界救火联合会会长。武昌首义后,夏氏兄弟和潘月樵等人率领伶界商团及救火会的武行演员们参加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战斗,冯春航也参与了这场战斗,他们用真实的肉身实践了上演壮剧的抱负。同时组织募捐义演,志愿革命,为光复上海作出了贡献。其实,南社人与夏月珊、夏月润兄弟早在1902年就有交往,而且汪笑侬就和夏氏兄弟等戏曲界有识之士决意将戏曲改良作为振兴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所以,完全可以说南社人捧角所推动的戏曲改良,确实影响到了戏剧界内部的自我认同建构。伶人亲身实践革命,书写了清末革命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南社人强调表演,其根本意义在于要求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建立政治性的联系,这对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自我确立意义深远。
二、南社人捧角中“角”的新社会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捧角”,“角”虽然被捧,但是是作为一种“物”供捧家赏玩,捧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角”的。而南社文人的“捧角”,是把“角”作为朋友,因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而“捧”,以文相捧,看演出、写赠诗,更多理解和关怀,更多推心置腹。南社人捧角首先预设了“角”是独立、自主的个人,这种平等打破了文人和伶人在社会身份、等级、地位上的等级界限与不平等。换言之,“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不是社会地位的平等,或者说,它根本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5]。而且,冯春航后来加入南社,成为南社的一员,也证明南社人捧角并不是单向度的对“角”的“捧”,捧家和角之间是互相影响、共同进步的关系。
如果以同时期—1912年末至1915年—上海京剧界和舆论界的另一支捧北旦贾璧云的队伍作参照,以他们刊印的《璧云集》和南社刊印的《春航集》①这是当时著名的“冯贾党争”:1912年9月,在北京已经声名稳固的京剧演员贾璧云南下上海演出,受到欢迎,撬走一些冯春航的戏迷,南社成员“恶紫之夺朱”,贾和冯形成竞争态势,于是贾的支持者称为“贾党”,包括有很多南社成员在内的冯春航支持者称为“冯党”,在各种报刊上对孰优孰劣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作比较,可以得到更加明晰的认识。
1.体例
《璧云集》先刊登罗瘿公为贾璧云作的《贾璧云传》,随后便是易顺鼎、樊增祥、狄葆贤、包天笑等20位京中遗老名士和上海报界精英捧贾璧云的旧诗词,共有31首。前后两部分加起来一共12页纸,虽然是为贾璧云宣传炒作,但是仍带有文人逸士玩赏名旦、雅集酬唱的性质。而且这种先小传后题诗的形式,实质上并未脱去清代乾隆五十年(1785)安乐山樵之《燕兰小谱》奠定的“小传/序+赞诗”模式的花谱传述体例。
《春航集》分上、下两册,洋洋240页,在篇幅上,大大超过了《璧云集》。上册先附冯春航化妆小影22幅,接下来的“文艺”栏收录柳亚子和其他南社社友与冯春航相关之通信。“诗苑” “词林”则主要收录南社诸君与冯春航的酬唱诗文。“剧评”栏,录柳亚子《箫心剑态楼顾曲谭》、寄尘《太平洋文艺批评》、之子《横七竖八之戏话》、定仙《梨园羼抹》四种报刊的剧评、剧论,从各个角度讨论冯春航其人、其艺。《春航集》可以说是一部带有同人性质的捧角专集。而《春航集》下册,开篇“剧史”栏刊载柳亚子长文《〈血泪碑〉本事》,评论它的思想倾向、艺术成就,对冯春航的艺术表演才华极力赞赏。接下来的“杂纂” “补遗”则辑录当时大量报刊上的冯、贾剧评论争,其中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声音,主要还是扬冯贬贾的文字,但无论如何,《春航集》的规格形式不同于“小传/序+赞诗”模式的花谱传述体例,它已远远突破了传统捧角专集的体式,带有现代人物传记的色彩。
2.内容
以包天笑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刊登在《璧云集》的旧诗词创作多来源于对贾璧云的审美性关心,他们关注的是贾璧云所体现的美感与魅力,而对花旦技艺的评价却并无兴趣。例如“文艺”栏开篇易顺鼎的《贾郎曲》中,一开始就把贾璧云比作小家碧玉的女子,将男旦演员女性化的意识展露无遗:“广陵一片繁华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黄金大半销歌舞。”[6]707接下来连用了几个古代美女的典故,描绘贾郎的风姿神韵,极尽赞誉之至。包天笑的诗句“最难巧笑与轻颦”也并不是对贾璧云的表演进行评价,体现的则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包括后面对诗的补充说明中,有的记述了贾璧云演婢女很拿手:“贾郎善演婢女,所演《翠香寄柬》 《青云下书》《打樱桃》 《明月珠》诸剧,均工妙入神。”[6]714但这些都好像是在对咏物对象进行细心观察。
以包天笑为中心的文人群体是通过捧贾璧云来开展自己的文学活动的,与其说这些清朝遗老、上海报人不约而同地喜爱贾璧云,不如说“捧贾璧云”这一行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以文会友、以艺会友的机会,可以说《璧云集》的出版也是他们发表旧诗词的一个机会。《璧云集》里包天笑、罗瘿公、樊增祥诗的和韵诗以及送别诗、宴饮诗很多,即可作为旁证。
易顺鼎的《哭庵赏菊诗》中叙述了这样一件轶事,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剪掉留到民国以后的长辫之际:
贾郎未剪辫时,予亦尚未剪辫。有人问贾郎何以不剪辫。贾郎曰候易先生剪后,我始剪耳。此为予与贾郎第二次之记念……癸丑春,予再入都,始剪辫,闻贾郎尚未剪,予颇愧之,旋闻贾郎亦已剪矣。[7]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易顺鼎虽然在这段文字中想要表现的是自己剪掉长辫的行为是为了履行和旦角贾璧云的约定,这段文字将他政治身份的变化巧妙地蒙混过去,但却从侧面泄露了贾璧云这个伶人的被动地位。
所以说,虽然都是众星托月般地“捧”,但是,《璧云集》呈现的伶人的身份是低于旧派文人的,而《春航集》中的伶人则拥有与文人平等的身份。
再看《春航集》。《春航集》中并没有过多关注冯春航的容貌,而是更加注重他的人格和表演。柳亚子在《海上观〈血泪碑〉赠春航》中把冯春航比作明末著名昆腔男旦王紫稼,并自况为王郎之知音吴伟业:
明灯华烛小温存,枨触人天旧爱根。绝代销魂王紫稼,可怜并世有梅材(村)。[8]136
南社社友庞树松看不懂王紫稼之喻的深意,柳亚子就作了《王郎曲》一首来解释。《王郎曲》概括了王紫稼的一生,称颂了他结交东林君子、不畏阉党气焰的高尚品格,暗含倡优戏子反而能识真英雄的慨叹。到诗篇末尾则“图穷匕见”,称“剥复相乘几百年,自由花放正婵娟”[8]151,再引出“今世王郎”冯春航,目的是赞颂古今两位进步优伶给社会带来的美好,令世间自由之花绽放。
南社人除了关注冯春航的人格,也关注他的表演。柳亚子在《箫心剑态楼顾曲谭》中对冯春航所演剧目有许多细致的评析。冯春航跷功扎实,他利用这一优势踩跷饰演小脚女子照相,柳亚子评论道:“且以六寸圆肤,饰为纤趾,其不雅观已甚。”[9]124后来冯春航就放弃在京剧表演中使用跷功了。又如柳亚子评《血泪碑》说:“五六本法场一幕,为最精警。临刑时增添说白数语,为前次所未有者,尤觉动人魂魄。惟官隶鸟兽散后,幕即下垂。时间太促,致绞台并颈之状态,匆匆掩过,未免可惜。”[9]126
另外,《春航集》中的剧评虽然扬冯抑贾的居多,但也有一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这些剧评不像捧角之争经常陷入一边倒的争辩,而是根据京剧的知识和理论,围绕着演员的技艺展开了公正的辩论。例如,很多论者就都持有贾璧云擅长演喜剧、冯春航擅演悲剧这样一种看法。管义华在比较二人时说:“考璧云所善之戏,为红梅阁梵王宫,而春航不能也。春航所长之作,为刑律改良血泪碑等,而璧去不能也。二人各有所长不能相较。”[10]7编茅《论冯贾(其三)》一语道出了实质:“其实各有所长,亦何必争?”[10]18这些剧评从客观的视角对冯春航和贾璧云都进行了肯定,这些评论者并不是“为捧而捧”,而是有自觉的剧评文体意识,使剧评这一文体得到发展。
可以说,《春航集》和《璧云集》在体例和内容上呈现出来的表象差异从本质上讲是由对待伶人这一群体的不同心态造成的。捧贾璧云的清朝遗老和报界精英把伶人这一群体看成“物”,所以过多关注其表象,而南社人把这一群体作为独立的人,更加关注他们的艺术。对艺术的更多关注,无疑是具有现代色彩的。
三、捧角,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捧角风气在晚清蔓延,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晚清社会大众文化萌发的结果。大众文化本质上是特权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变,特权和等级对个人的制约降到最低限度,个人只要有闲暇功夫和经济实力,都可以参与其中,可以自由选择各种不同的文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像封建社会,个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选择都受到当权者意志的严格规范和干涉。大众文化具有商业性,大众的诞生,也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大众”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这个政治问题本身却是由商业引发的,因为大众文化之“大众”的社会学视角恰恰是同质的个体。大众的诞生,首先是个体独立的过程。徐甡民在《上海市民社会史论》中就说过:“近代社会的变革和重构,也在于异质个体的产生以及它们在社会政治关系中日渐形成的自主性、多元性和自由选择的权利。”[11]这一个体独立的过程也即韦伯所言的“祛魅”过程。人依赖某物,臣服于某物,无疑会使某物“神秘化”,使它具有魔力。在早期崇拜中,人们把自然神化、把帝王将相神化以及把国家神化都是“魅力”发生的过程。涂尔干深刻地指出人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崇拜他们的社会的,“神圣的东西首先依赖在集体的、非个人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恰恰就是社会本身的再现”[12],这其实就是“魅力”的发生机制。因此,真正的主体独立性、平等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必然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也就是说,是魅力平凡化的过程,或是一个摆脱依赖性的过程。韦伯精彩地指出,这个过程是通过现代经济来实现的,他强调“平凡化的前提是消除魅力对经济的陌生性”[13]。当魅力变成食俸禄者,这一过程也就完成了。
晚清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14]。大众文化的商业特色是晚清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虽然商业化和现代性之间并不等同,但是,戏剧表演艺术渐渐拥有独立的身份并可以与都市中其他娱乐活动竞争,而且可以用经济收益来衡量。戏剧表演已经不再是宗教祭祀、仪式等的附庸。随着上海新舞台的落成,戏剧的商业化使其得到社会的肯定,它的独立性正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方面。
晚清戏剧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影响着戏剧欣赏与演出的价值体系的转换,捧角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少数士大夫以及权贵阶层的特权。须知捧角在整个封建社会乃至前清时期和普通大众的生活相距甚远,而到了清末民初,它越来越被融入更多世俗的成分、平民的成分,成为一种大众文化。“要知道戏剧是大众的娱乐,不能离平民而独存的”[15],使得戏剧这一行业与现代传媒、商业活动越来越密切相关。捧角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当京剧表演中名角制产生后,一些著名的京剧角儿成为戏迷们追捧的对象。捧角作为城市社会的大众娱乐行为,不管是达官贵族、社会名流,还是文人、平民百姓,都疯狂地投身这一娱乐活动之中。
捧角使得角儿们的社会身份公共化,角儿们自身成为舆论的焦点和话题,从而形成社会大众的一种娱乐资源。京剧名角制的产生,表现为角儿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大幅提升,成为社会大众追捧的对象,以至于形成“追星”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都市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与演艺活动有关的社会公众心态,也从对戏曲艺术的欣赏、着迷,分化为对名角本人及其生活的关注,出现了社会性的迷恋、推崇某位名角的风气的流行。
捧家和角之间出现了具有现代色彩的“粉丝”和“明星”的关系属性。表面上,捧家们追看演出花钱如流水,要无条件地、热情地消费名角的艺术。例如南社捧角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演出。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并第一次雅集,适逢冯春航在阊门附近某剧场演出,柳亚子等人就“天天涉及梨园”,“做了顾曲周郎”[16]。本质上,捧家对名角的“捧”是一种情感经济。情感经济指的是市场上出售的不再仅仅是物质产品,还有非物质的、符号性、情感性体验。消费越来越多地与意义的创造相关联。澳大利亚学者贾莱特认为,消费者可以利用他们的“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商品的“文化内容”。对于品牌来说,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情感关系。消费者的忠诚和情感是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17]在这里,捧家们不仅要关注角儿们的色、艺,也热爱对自己具有特别意义的名角,关注名角演绎的文化形象。大众文化也同其他文化一样,是由一定的符号和象征组成的,而且这些符号和象征都代表或指向一定的意义。名角的符号意义,是美好的社会理想。所以对南社成员们来说,名角不仅寄托革命理想,而且才德亦须兼备。庞树松在《冯春航传》中云:“偶与春航谈,作语颇名隽,以是疑春航非无学者。嗣春航之师夏月珊语余以春航在学之成绩,余以是重春航。欧风东渐,新剧盛行,春航所编之血泪碑,惠兴女士诸剧,先后出世,春航隐隐以改良社会教育为己任,人亦以是益重春航。”[18]这一对冯春航品行的宣传就好比今天的粉丝致力于总结偶像的优秀事迹四处宣传。庞树松在冯春航的传记里,指出他一生中高尚的表现,这是粉丝的共同表征。必须要注意的是,名角的符号和意义,捧家是参与塑造和认同,而不是被动接受的。角儿们需要传达群体的思想和独特文化,以此来达到群体的文化认同,加强这个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一致性。南社成员也正是通过他们的报纸栏目,以写剧评、诗词等方式实现这一特性的。
在捧角过程中,不仅要消费角儿们创造的文化产品,而且还要对角儿忠诚。正如美国学者哈特所说:娱乐工业和各种文化工业的焦点都是创造和操纵情感。[19]在媒介娱乐领域,情感经济的意义更加不容小觑。粉丝既是明星品牌意义的创造者,他们的情感强度和持久度也直接决定着品牌的经济价值。或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戏迷已经成为名角的重要个人资产,至少与名角本人的魅力和才华同样重要。所以,南社人对冯春航的情感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使承认对手也有价值,但必以自己偶像为超常之品,无与伦比,不可以常理度之。对偶像的竞争对手,会有强烈的反对和抨击。“冯贾党争”就是典型案例。即使是南社本社人之间,也曾为“捧角”大开笔战,同时,他们不能容忍对自己偶像的批评和攻击。1912年夏,雷铁崖给柳亚子的信中称赞他在汉口看戏时看到的伶人郭凤仙非常美丽,并且给“美”添加了“第一”这个最高级限定词,这使柳亚子非常生气—郭凤仙如果“第一”,那么置冯春航于何地?柳亚子立即回了一封信。叶楚伧记述了柳亚子、姚鹓雏等人为冯春航大起争论的经过:“林一厂、柳亚子、俞剑华之于冯春航,不啻视为上天下地之第一人物;而姚鹓雏、胡寄尘毁之,又穷形尽致。旗鼓对峙,锋针相向,大有如中俄交涉更无退让余地之概。”[20]后来,冯春航身材走形,梅兰芳红了之后,南社成员有的去“粉”梅兰芳了,柳亚子对这种“变心”转而欣赏其他明星的行为不赞同,姚鹓雏在《菊影记传奇》里写柳亚子说:“惟有梅州林一民,百折不挠,助我张目。其余竟连檗子、楚伧,深法定力,也都见异思迁,立马梅家军下了。”[21]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捧角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原本大众文化的诞生是个人从封建的权力支配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但悖论的是,却又陷入了金钱支配下的另一种权力拘囿。而且,金钱支配下的娱乐难免出现格调低俗的状况,低格调捧角是为色而乐,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林黛玉十八扯,怡园电灯亮如水,大家争把正座包,万头耸动如毫毛。齐齐心,喊声好,喊破喉咙我不老。眼波溜,眉峰锁,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适才瞧见否,黛玉分明望着我。”①转引自徐建雄:《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第116页。在这里,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遗。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城市大众娱乐文化内容的,这种娱乐文化内容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捧角到极端,不可避免地会与色情相撞,这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在消费社会中,肉体和性扮演了新的角色,鲍德里亚认为:身体变成了维持这个社会运作的两个重要因素:美和色欲。[22]肉体也成了运作中的价值符号,成为人们盲目追逐的对象。消费社会给予身体一种“文化”的礼遇,使身体成为了“文化”的一个事实。肉体纳入物体的符号系列,是由于肉体可以成为符号系列中最有潜力的资本和崇拜物。消费时代的身体文化显示出:身体的解放是真正合乎人的本性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应该是审美的、反对拜物教的,但现在这个被解放了的身体却走向了市场,变成了消费品。这是当前一个尖锐而又有待解决的悖论,这个悖论和上文所述的大众文化的悖论又是统一的。所以对有美好的形体、容貌、声音的欣赏,包括有情色意味的欣赏,是捧角文化的必有内容。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南社同仁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理想。相对于北京清贵们的绮靡淫滥,南社人对冯春航的要求是一种克制的不妖艳的美,要“清”而不要“浊”,要“清艳异常”,或“哀感顽艳”。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南社人捧角这一行为与晚清戏曲改良的关联,其对伶人这一群体的尊重、对演员技艺的关注,及其体现的晚清都市大众文化的特色,都可以作为戏曲中的现代性因子。捧角并非始于南社,但这些现代性因子把南社人的捧角与其他人的捧角区别开来,赋予捧角更多新的内涵。南社人捧角的实质在于倡导一种戏剧新理论和新观念,在戏曲界推行一种新风气与新面貌,在于以评促改。虽然这些现代性因子离戏曲本身呈现现代的本质变异还很遥远,南社对现代戏曲的主要影响也并不在此,但是这些因子作为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戏曲领域内的表现形式,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的戏曲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上海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6:873.
[2]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M]//柳斌杰.中国名记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NUSSBAUM M. Poetic justice: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M]. Boston:Beacon Press,1997:1.
[4]FISCHER-LICHET E. The show and the gaze of theatre:a European perspective[M]. Lowa:University of Lowa Press,1997:25-40.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1.
[6]罗瘿公,易顺鼎,樊增祥,等.璧云集[M]//傅谨,谷曙光.京剧历代文献汇编•清代卷: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7]易顺鼎.哭庵赏菊诗附录[M]//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775.
[8]柳亚子.海上观《血泪碑》赠春航[M]//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柳亚子.箫心剑态楼顾曲谭[M]//郭长海,金菊贞.柳亚子文集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春航集:下册[M].上海:广益书局,1913.
[11]徐甡民.上海市民社会史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136.
[12]涂尔干 爱弥尔,莫斯 马塞尔.原始分类[M].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0.
[13]韦伯 马克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8.
[14]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34.
[15]施病鸠.伶人拜客之风应停止[J].戏剧周讯,1942,1(11):11.
[16]郑逸梅.南社丛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
[17]JARETT K. Labour of love:an archaeology of affect as power in e-commerce[J].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39(4):343-344.
[18]庞树松.冯春航传[M]//南社丛刻.影印本.扬州:江苏广陵出版社,1996:1364.
[19]HARDT M. Affective labor[J].Boundary,1999,26(2):95.
[20]叶楚伧.横七竖八之戏话[M]//叶元.叶楚伧诗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67.
[21]姚鹓雏.菊影记传奇[M]//杨纪璋.姚鹓雏剩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171.
[22]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00.
(责任编辑:时 新)
The Moder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Boost Actors” of South Society
ZHOU Shu-h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South Society (1909—1923) had an affect on the traditional oper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influence comes not only from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members in South Society, but also from their stage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y also make boosting actors a way of advocacy of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drama innovation. From actor-boosting practice of Pekin Opera actor Feng Chunhang by the South Society members, the modern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opera can be se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drama innovation, the new social status of actors, and the urban mass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se meant a great de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opera.
Key words:South Society;boost actors;Feng Chunhang;drama innovation
作者简介:周淑红(1989—),女,江苏苏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理论。
收稿日期:2015-04-25
文章编号:1008-7931(2015)05-0011-07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J80
——以广东社友的交游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