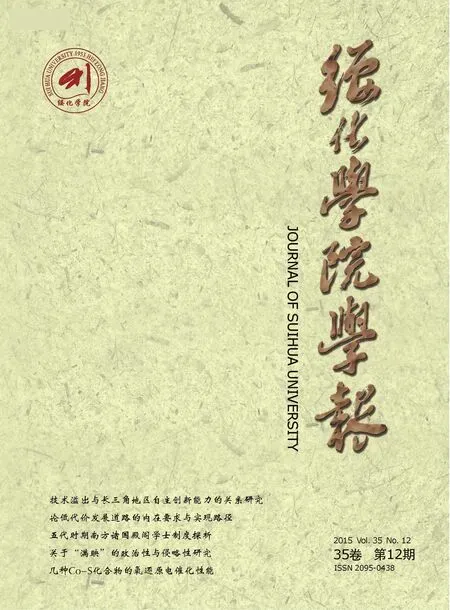论晚清狭邪小说中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
王宗辉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论晚清狭邪小说中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
王宗辉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在晚清狭邪小说中妓院与官场作为两个不同的叙事空间,构成一种叙事的张力,熔“排斥性”与“兼容性”于欢场的熊熊炉火之中。妓院主体之妓女、官场主体之官员,彼此所代表的价值规范、伦理道德、社会信仰等实体在相互碰撞中趋于裂变,导致主体形象因叙事空间的差异而萌生了逆转现象,即“我”的主体身份及行为准则均有了难以弥合的缝隙。而此现象的发生受社会转型期价值理想崩溃、人生失意而无正常宣泄渠道、拜金享乐主义的欲望刺激、东西方文明的持续碰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交错扭合又解构了晚清狭邪小说的纯粹性,即此一小说类型除却自身的创作手法外,又涵纳着其他小说类型的创作手法。
官场;妓院;狭邪小说;社会形态
“作为主体,人固然是从这外在的客观存在分离开来而独立自在,但是纵然在这种自己与自己的主体的统一中,人还是要和外在世界发生关系。人要有现实客观存在,就必须有一个周围的世界,正如神像不能没有一座庙宇来安顿一样。”[1]此“世界”言的是人物作为主体的活动空间,而“空间”又有大小之别,大空间意为时代、社会背景,小空间意为具体生活场所、环境。在晚清狭邪小说中,其主体人物所处的大空间为急遽转型的社会形态,所处的小空间若单纯以妓女、官员而论自是妓院与官场。但在社会形态转型的滔滔洪流的侵蚀下,妓院、官场之间的流动更为频繁,近于混而为一。而伴随妓女、官员的空间转移而来的却是角色的置换,即可言之“人物存在的流动性状态”,而“存在状态的流动性即存在主义所说的‘在路上’状态。‘在路上’意味着对过去的否定、对现在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追求。”[2]可见妓女与官员因叙事空间的不同而衍生的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是绝望中的一种反抗、变态中的一种常态、行动中的一种言传。
一、妓院诉诸于官场时官员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
妓院作为城市构建的公共娱乐空间必然辐射出无穷魅惑气息,诱使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之人至此寻欢作乐,而人物在此疯狂聚集的结果便是妓院潜在矛盾的总爆发,如妓女、老鸨、姨娘、恩客、相帮、龟奴、富商、达官和家主妇等因两两关系的重新组合而激发的新一轮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作为社会微型版本的妓院也无法躲避在人物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网络之外。对于妓院内发生的冲突或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事件,其解决方式大致有两种,或私下协商或对簿公堂,若最终不得不诉诸于官场时,以官员即权力的部分拥有者对事件处理的态度而言,官员扮演着正义化身、伪善代表、西人傀儡等多重角色。
言其是正义的化身表现在其对妓院风流孽障之事处理时的大公无私,如在孙家振以暴露上海妓女可恶一面为主的《海上繁华梦》中,初集第二十六回叙述邓子通枪杀潘少安又饮弹自尽的桃色事件,而案件一经一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县官”着手,便快刀斩乱麻般使此番因争风吃醋而生的狭路寻仇之事得以公平解决,如对阿珍“鞭背五百,监禁三年,递解苏州,不准再来上海”的判决等。但予文本接受者造成的实际印象却是此一廉政之官来得过于突兀了,公正的有些让人质疑其存在的真实性及合理性——何以一廉政之官对此种案件如此轻车熟路?倘若从作者的创作意图而言当是其强烈介入世事愿望的主观表述,即以浩然正气来挽救日益倾颓的世风。
言其是伪善的代表表现在其在处理妓院风流孽障之事的过程中,又伴随着以权谋私等种种同法律所标榜的公平性相龃龉的行为,如在张春帆以旅行者视角演说各地妓女形态的《九尾龟》中,第八十四回便塑造了一位“卖良为娼”的刘大老爷,而其“卖良为娼”目的仅是为了出一口个人被戴绿帽子的恶气。被戴绿帽子固然可恨,然以维护法律的名义而撒个人受辱之气怕不是处事的正常行为吧。“卖良为娼”本是法律断然禁止的事情,而刘大老爷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却公然知法犯法,可见法律已然成了此类貌似正派实则伪善之人庇护情面、狭私报复的工具了。另外刘大老爷所掌握的权力并未应用到对刑事案件的有效处理中,而是以一种粗暴的态度藉挽救其男性尊严来彰显法律的有效性,伪君子形象可见一斑。
言其是西人傀儡表现在其对风流孽障之事处理时,因外国人的强行干预而持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如在《海上繁华梦》后集第十六回、第十七回中,叙述金子富被花子龙等赌棍做翻戏之后,西人麦南替他写了一封代报当官、恳请从严究办的信,而“官场见是洋人代禀的事情,当下急风如火,把禀单立刻批准签稿,并行标差拿究。”[3]而同时展开的另一件事却是西人保罗在妓院里肆意酗酒滋事,而于此有违租界章程的事又无人对其进行严肃处理,相反倒是假洋鬼子贾维新备受他人的嘲讽与奚落,最后只能将所受之气转嫁于作为同胞的妓女身上,藉此获得一种心理优越感。可见在西人的嚣张气焰之下映衬的是国人的媚态倾向,普通百姓如是,身居官位者亦如是。
以上三种人物形象又可归在“清官”与“腐吏”两厢对照的美丑二重人物群像之中,此二重人物的设置折射出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对于国将不国的深重忧患意识,与个人人生价值、理想难以为继的无比焦灼心态。在晚清狭邪小说中此类人物分量虽不重但同样不容忽视,可以说“清官”是跻身于仕途的传统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寄托,是其对人生理想与行为准则的呵护与坚守,而“腐吏”则一方面暴露出晚清整个官场肌体的千疮百孔,另一方面又可看作是在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侵蚀下,正当职权无法展开的战战兢兢的国民中一类代表性人物。对“清官”“腐吏”人物群像的塑造,在晚清狭邪小说中虽不能定义为边缘性人物,但给予的照顾有失偏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孰不知官场与妓院作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空间载体,却存有很多的交叉甚至重合之处。官场辖制妓院,妓院流毒官场,因此必然伴随着矛盾的冲突与碰撞,势必会衍生出种种千奇百怪的现象。晚清狭邪小说对“清官”“腐吏”人物群像的抒写,勾勒出旧的社会制度濒临崩溃而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得以建立的转型狂潮激荡之下,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负有管理职能的官场人员的矛盾心态,或持孔孟之道积极入世为力挽传统文明而斗争不息,或持老庄逍遥心态混迹秦楼楚馆而消极避世,不同的人生选择决定着不同的价值取向,那么究其一生的人生轨迹便会分裂成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晚清狭邪小说将官场文化置身于妓院梨园中进行打磨,使彼此熔铸不同的社会、人文等多重内蕴,并显现出不同的气质类型,可以理解为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规律为其重新灌输血液,但新鲜血液的注入并不一定伴随着生命的浴火重生,相反倒会因血型的差异而加剧彼此生命的枯竭,所以伴随着社会转型滔滔洪流的奔进,妓院、官场一同滑向了堕落的深渊。在不同的叙事空间中,妓女、官员的身份呈现出不同形态,彼此表现得行为相互抵牾。如果以主仆关系而论的话,那么在谙熟的生存空间则为主,在陌生的生存空间里则为奴,也就是说不同的生存土壤孕育了不同的人物类型。而当把不同的人物所裹挟的异质文化强行移植到不适宜的生存土壤或环境时,便会结出畸形且食之无味的文化果实,一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但又因各自空间的独特魅力而刺激双方进行好奇性的尝试,结果就像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一样自食苦果,受到的戕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晚清狭邪小说的主体形象因叙事空间的差异而衍生的逆转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官场耽溺于妓院时官员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
当官场人员(在职者或者是被迫撤出官场者)进入妓院时则又是另一番让人大跌眼镜的状况,在妓院里,官员的身份不仅发生了逆转,而且行为也变得荒诞不经。他们身上所保留的世俗禁忌在此地几乎被消解殆尽,爆发出的是人性中长期受到压制的一面。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在远离政治的同时也远离了日常所尊奉的道德标准及行为准则,进入妓院的官员已然不是纯粹的官员,或把妓院当作逃离丑恶社会的世外桃源,或把妓院当作千金买笑的人间天堂,但无一例外是嫖客。且不论其目的究竟为何,当其面对妓女时呈现出与衙门中迥然不同的色调,扮演着以下三种形象。
一为阿谀奉承、奴颜卑膝的叭狗形象。如《九尾龟》第九十五回、第九十六回便塑造了陶观察此一“叭狗形象”。通过“平康巷里的惯家、烟花队中的侠客”章秋谷的叙述视角展现了一组嫖客(陶观察)与妓女(薛金莲)之间的非常态现象,嫖客的行为与妓女的语言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当两人乘坐的马车先后驶到张园门口时,陶想要搀扶薛下车,被薛斥责“不要涅,算倽介,耐搭倪先跑进去。”当进入张园陶想要同薛坐在一处时,薛把手在桌上一拍,“耐勿要坐勒倪搭,坐勒格面去末再啘。”当陶问薛吃不吃点心时,又被一顿训斥“耐格人总归实梗鸭矢臭,一日到夜吵勿清爽,吵得倪头脑子也涨杀快。”当薛向章吊膀子却被章大肆嘲弄时,薛便迁怒于陶身上,“倪原说格两日探了牌子,勿出去哉,耐定规拖牢了倪一淘出去,害得别人家头脑子里向痛煞快。”尽管被薛数次无端责骂,但陶却始终毕恭毕敬,笑容可掬,不驳一言。如此一来,嫖客与妓女的身份呈现倒置状态,似不是嫖客在嫖妓女倒是妓女在淫嫖客。
二为被淴浴的蠢物形象。淴浴是妓女的惯用伎俩,妓女假意以从良为借口,骗恩客为其偿还债务,一旦目的达到,便在恩客来娶之前逃之夭夭。若妓女无奈之下嫁与恩客,最终大都选择卷财而逃并重回妓院营生,因为她们习惯了吃大菜、看大戏、乘大车的自在生活,根本无法忍受长期被束缚于家庭此一狭小空间的现实处境。在《九尾龟》第一百十八回至第一百二十八回叙述了康中丞一家的风流艳史,妓女王素秋以“淴浴”的目的嫁给康中丞,但“不想到康中丞家内,康中丞宠爱非常,竟把他当个正室夫人一般,把家里头上上下下的事情,一股脑儿交给他一个人管理。”于是,不再想着“卷了珠宝逃走出去”,并“拿出浑身手段来牢宠这位康中丞”,使其“由爱生畏起来”,最后“康中丞只要见了这位姨太太的面,就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当王素秋在康家独揽霸权之后又开始姘戏子、通家奴,而康中丞却被蒙于鼓内,何其蠢不可及。
三为被肆意讥讽的假道学的痴顽形象。如在《九尾龟》第六十四回至第六十八回,刻画了王太史这样一个“平日间满口道学,好像一个正派儿”的藉芸窗十载而平步青云的人物形象。文本中叙述者的“画外音”道:“原来这班专读死书专做八股的书呆子,往往少年时节不敢荒唐,一到中年以后,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自以为功成名就的了,免不得就要嫖赌起来。却是不嫖则已,一经涉足花丛,定是那天字号的曲辫子。”[4]王太史先后做过金寓、花彩云两个妓女,王太史对金寓可谓是百依百顺,但换来却是金寓“冷冰冰的面孔,待理不理的样子”。当他在朋友面前吹嘘金寓把自个当家里人看待时,却不知金寓另有所爱,并最终瞒着王太史嫁给了他人。花彩云是王太史做得第二个妓女,虽嫁给了王太史,但仍以省亲幌子逃了出去。正所谓一之谓甚,其可在乎?而王太史闹了两番笑柄之后,仍旧乐此不疲,又在人家席上看中了红倌人陈文仙,后被章秋谷大肆抢白一顿讪讪而去。如此一来,传统知识分子假道学的一面被妓女一层层剥落了下来,使他们无处遁形,最终沦为笑料。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按正常逻辑来理解,妓女于嫖客当持一种温顺甚至敬畏的态度。嫖客则以居高临下、高屋建瓴的姿态,既可拯救妓女脱离苦海,又可令其境况更为凄惨,但却无法忍受妓女敲诈恩客。如此一来,妓女、嫖客因身份、地位的差异便造成了认识上的奇观。但随着上海等近代都市的畸形繁荣及外来思潮的强行涌入,妓女的心境为之一变,逐渐认识到身体是其谋生的资本,“嫖与被嫖”构成一种以获得银钱为最终旨归的商业性行为。于是在大部分妓女眼中,唯钱才是其所衷之物,狭邪小说的“溢美”之作《青楼梦》是男性最高人生理想的诉说,但却几乎沦为白日梦般的呓语,钱不在妓女的视阈之内,“近真”之作《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虽有好坏之分,但对钱的考虑并不见少,而“溢恶”之作《九尾龟》中的大部分妓女则完全以钱为最高标准。嫖客有名士、瘟生、流痞等各色人等,妓女有长三、幺二、野鸡等不同级别,彼此在市场中均可以按照商业活动的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购买活动。而道德标准并不构成肉体交易活动的主要竞争法则,如果嫖客恃钱而以玩赏的心态满足个人欲望,妓女采用淴浴等以恶制恶的手段亦无可厚非。官员在妓院里所扮演的以上三种主体形象,自然与妓女征服嫖客的花招密切相关,但也与这些官员的心态相伴相随。官员不是妓院的主体,因为有唐以来禁止士大夫在教坊勾栏涉足,更禁止其挟妓侑酒,而到了晚清这些规定已然形同虚设,官员才逐渐品尝此一被长期封印的禁果。妓院作为供人消遣娱乐的公共领域,自然不会将官员拒之门外,而官员也往往会给妓女带来意料之外的快感,与另一种新奇体验。官员中既有饱读诗书之人,亦有腹内草莽之人,但在妓院里的行为却大体表现出一致性,那就是官场上一本正经的面貌被私生活的放荡不羁逐渐撕掉了。
三、妓院、官场混而为一时所创的其他洞天
晚清狭邪小说实际上也饱含着谴责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甚至侦探小说等创作痕迹,如钱锡宝的《梼杌萃编》、张春帆的《九尾龟》、魏秀仁的《花月痕》等,但又不是纯粹的谴责小说、侠义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因为其仍是以狭邪中人物事故为全书主干,以妓院梨园为主要表现空间,叙述的仍是嫖客与妓女之间的孽海情仇。至于其所含的其他小说类型的创作因素,只能看作是华而不实的装饰品,虽不构成文本的主要事件,但当妓院、官场化二度空间为一度空间之时,却又形成了“别有洞天”之境。
《梼杌萃编》熔谴责小说和狭邪小说为一炉,在小说中不仅对比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等谴责小说,同时也与陈森的《品花宝鉴》等狭邪小说进行映衬,化妓院、官场不相容的二度空间为妓院、官场可等而视之的一度空间。此前分别以官场、妓院作为主要表现空间的作品,虽然也会点缀一下异质空间,如妓院涉及官场,或官场涉及妓院,但大都主次分明、有所侧重。而在《梼杌萃编》》中,妓院、官场藉不断切换的场景来推进故事的展开,可谓是彼来我往、分庭抗礼,大有二分天下之势。如陈平原言:“写闺房,写妓院,再加全书随处可见的关于‘色’‘淫’的精彩议论,大都是为了透视官场中人的内心世界。既保持了谴责小说的政治锋芒,又继承了狭邪小说的细腻风格,借颇为精彩的心理描写,滤去了前者的简单化漫画化倾向,也甩掉了后者的过分琐碎与脂粉气太浓等通病。这似乎是个特例,是给清末的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作总结。”[5]
《九尾龟》“上半部形容写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而以前者为主,附有谴责小说的痕迹,“同时还接受另外两种小说类型的影响:一是古老的狭义小说,一是刚刚输入的侦探小说。”[5]言其带有谴责小说的痕迹是因为在文本的展开过程中,其观照的领域涉及妓界、官界、商界、甚至科场、家庭等,无论是妓院里的老鸨、妓女,还是官场里的各色官僚,亦或是大谈国事的留学生,统统笼罩于作者犀利的笔锋之下,谴责的成分是相当浓烈的。言其带有古老侠义小说的痕迹是因为文本里塑造了一个“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人物形象之章秋谷,他在妓院梨园施展武功,既为朋友排忧解难,又降服一个个妓女,同时也博取个人在妓院中的声誉。而“于青楼中行侠仗义,既有言情小说中才子的缠绵悱恻,又有侠义小说中英雄的粗犷豪侠,”[5]言其带有侦探小说的痕迹是因为小说不惜笔墨写章秋谷如何识别他人给自己或给朋友设计的各种奸谋,如识破王云生扎火囤的阴谋诡计等。
《花月痕》的创作既类似于才子佳人的写作模式,“其书虽不全写狭邪,顾与伎人特有关涉,隐现全书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说定式。”[6]又带有怪怪奇奇之处,“至结末叙韩荷生战绩,忽杂妖异之事,则如情话未央,突来鬼语,”[6]通读文本可知其前后分期的创作造成了主旨衔接的断裂,初稿截止四十四回,以刘秋痕、韦痴珠的相继而亡作结。续稿至五十二回止,着重铺演又一情侣韩荷生与杜采秋的传奇历险故事,充斥着奇幻侠义的情节,似是另起炉灶重新书写的魔幻篇章。从小说的整体性而言,初稿与续稿因脱离了正常的叙事逻辑,而无法进行合理协调,俨然一副混合着多种题材因子的“杂拌”文体。如王德威言“《花月痕》的结尾如此生硬矫情,所留给读者的痕迹,正表露出魏子安心向往之的与他实际达成的,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小说论小说,魏氏的作品只有在不经意地嘲弄自身的前提时,才算收束了全篇。”[7]
通读以上几部小说可知,在晚清狭邪小说中糅杂其他小说类型的创作手法,并不能更为凸显其本身的艺术魅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上的艺术价值。因为其浅尝辄止、形似神不似,没有从一制高点来统摄全局,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晚清狭邪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正值中国社会形态转型的临界点,而社会转型是社会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其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动。那么身处社会转型期内的人,必然会因外来思潮的涌入及自身变革的需求,而于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打上社会转型期的烙印。而晚清狭邪小说的作者亦是身处其境,其无法以蚍蜉之力撼动社会这个虽已日渐枯朽但却死而不僵的大树,唯有执笔立言借文本揭示出其病状。他们力图在文本中融汇来自各种渠道的社会信息,以求全方位的展示社会更迭之际的现象,但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作者的文韬武略并不足以支撑得起其笔下流露的庞大社会内容。他们试图借用某一单个文本类型来记录社会的万般现象,但却忽视了艺术的创作规律,或者说百科全书式的杰作并非一定属于那些雄心勃勃力图把握住时代脉搏的人儿。如此一来导致晚清狭邪小说的杰作寥寥可数,有些简直不忍卒读,或着重于诗词的堆积,或立足于淫情艳事的披露,或将转瞬即逝的露水婚姻硬扯为感天动地的生死相依。当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晚清狭邪小说的作者毕竟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尝试,虽不够成功却又大步奋进,为晚清狭邪小说增添了“别有洞天”之境,即让文本接受者领略到其试图将多种小说类型熔为一炉以立体化展现社会转型期诸般现象的艺术探索精神。
妓院主体之妓女、官场主体之官员作为具有行动力量的人,在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受到来自物质、精神等多重方面的挤压,那么构成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对象化活动,便会因之发生异化。而当彼此进入不同的叙事空间时,便会产生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莫名恐慌与焦虑,人生的痛苦与虚无便会因世纪末情绪的干扰而更加难以排遣,使人的主体性趋于崩溃。官场虽不是妓院的主要表现空间,但妓院中却在在弥漫着政治气息的味道,妓院虽不借官场来谋取生存发展,但有时为保证营业秩序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向官场寻求庇护。于是,妓院、官场的双向流动便造成了彼此的冲击,彼此的冲击便催生了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而主体形象的逆转现象便构成了晚清狭邪小说此一饱含其他小说类型创作成分的又一特色。
[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新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社,2005.
[3]孙家振著、邹子鹤校点.海上繁华梦[M].济南:齐鲁书社,1995.
[4][清]漱玉山房撰.九尾龟(上)[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
[5]陈平原.小说史:理论和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206.5
A
2095-0438(2015)12-0035-04
2015-07-08
王宗辉(1990-),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