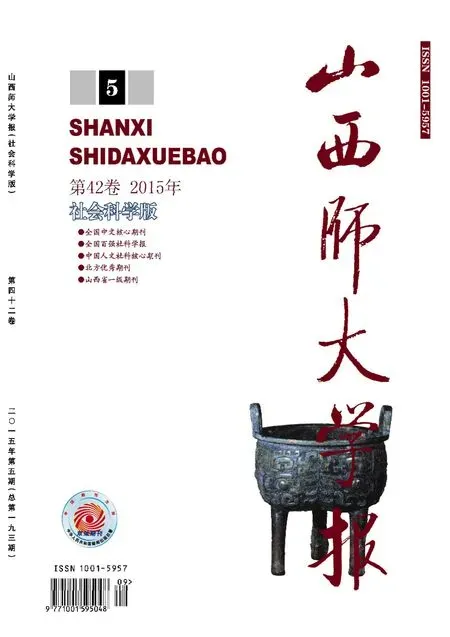论马克思和自然中心主义在主客关系上的反转
余 满 晖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01)
自然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视阈中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立的派别,其以辛格、雷根、奈斯、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为代表强调突破传统道德只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藩篱,而将伦理学的适用边界扩展到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他们坚称自然是一个“结合体”,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存在分界线,因而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1]57一样,在主客关系方面都有革新性的解读。然而,在这种革新性的思维方式中,他们与马克思却走向了分殊与对立。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39,因此很有必要梳理二者在主客关系上的反转,以澄明相关学理与我们的价值选择,反思与追寻当下生态危机的“超升”之路。
一、马克思视阈中的客体融合于主体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54。这说明“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1]54认为人现实生活的感性对象世界仅仅只是以自然形式存在的客体,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1]76。马克思既然断定这一点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并且使用了“只是”一词来批判,也就表明他虽然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样坚持唯物主义而认为人的感性对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但是他又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相区别,并不认为感性对象世界是先在的、既成的。[1]54为此,他特别提到“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1]54。这是因为与唯物主义不同,诸如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提出“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3]21,因而在他们看来,人现实生活的感性对象世界不是既成的,而是由人的精神活动生成的属人的东西。马克思肯定了唯心主义对“能动的方面”[1]54的发展,不过另一方面又指出唯心主义并“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1]54——物质实践活动本身,这使他们认为生成感性对象世界的不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而是人抽象的精神活动,从而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人能动的方面。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阈中,人意识的对象或其“周围的感性世界”[1]76是人通过自己能动的物质实践活动生成的一个人化的自然界。
关于这个人化的自然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论著中一再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4]50,“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4。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应该把人化的自然界“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4,应该把它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确实,人们为了生活,因而其每日都必须进行的生产实践,就是以先在自然为“自然基础”或“天然的基质”从“有”化“有”促使劳动对象化或形成对象化的劳动的过程,也即是动态的实践向静态的实践的转换过程。其中的先在自然当然“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5]400,它仅仅只是改变了存在形态以“基质”或一般内含于人化自然当中。而人化自然则是特殊的自然,它一方面作为个别内在包含了一般(先在自然);另一方面由于其实践生成性它又不是一般(先在自然),而是一般的特殊转化形式,即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本身,只不过不是动态的实践,而是静态的实践、对象化的劳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7这表明尽管人和动物的区别非常多,例如人有意识,信仰宗教,动物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信仰宗教,因此“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1]67。但是,意识等本身却是需要由人的劳动、人的实践活动来说明的东西,它们“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81,所以马克思并不赞成有意识与宗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只有“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的生产劳动才真正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7由此可知,人的生产劳动也即实践活动是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67的根本特质,也即人的本质。这样,由于实践是人的本质,因此当马克思肯定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时,它也就是人的本质,因而作为人“周围的感性世界”[1]76或客观存在的客体。人化自然并不在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之外,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主体之中,是以主体在场的人自身的本质性存在。
二、自然中心主义视阈中的主体消融于客体
自然中心主义依附于现代科学,注意到了人现实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把所有的事物都组合成个体生命,并使它们之间的结合如此地松散,以致仍能作为其环境中极为珍贵的部分而存在;同时,这种结合又是如此地紧密,以致生养万物的生态系统优先于个体生命”[6]248—249,甚至人们日常生活中毫无奇巧的大地也“并不仅仅是土壤,而是能量在土壤、植物和动物所构成的循环中流动的源泉”,其中“食物链是引导能量向上的通道,死亡和衰败则使它回到土壤”[7]205。与此相联系,在自然中心主义看来,地球上的每个自然物,土地、山脉、平原、河流、海洋、大气圈等都是地球不同的器官或者器官的各个零部件,它们每一个部分都有神秘莫测的特殊功能与特殊地位,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态位置,彼此间相互依存,共生发展,履行着其他事物无可替代的独有作用。同时,“正是由于有机体拥有这样一些协调的、完整的功能(它们都指向有机体的‘好’的实现)”[8]36,因而自然界这个“有机体是一个具有目标导向的、完整有序而又协调的活动系统,这些活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延续和繁殖”[8]36。因此,自然中心主义赞美人袖手旁观的自然,自己用“自然之手”去控制与管理自己那里一切无人的“荒野”,认为“河流应当是真实的河流,而不是筑起了大坝的河流;山也不是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而是渺无人烟的荒山”[9]12,即使建立自然保护区,也不能抽掉“荒野”的实际内涵、它的真实性与原始性,而使之成为用金钱再造出的一个虚假的“荒野”。总之,自然不是人的自然,“其中山川、河流、鱼、熊等的存在有权按其自身的方式生活,这种体验过程能够促使人从大地的征服者角色向作为大地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的角色转换。”[10]108
至于人,自然中心主义指出地球刚刚从太阳系中分化出来时,不仅没有一种生物,甚至连最简单的构成生命所必需的高分子蛋白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距今几百万年以前才演化产生出了人类的远祖——类人猿。所以,人是人生的,但并不永远如此,往前追溯,总会遇到这样一点:人不是人生的,他们只不过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荒野自然的作品。因此,人从属于自然,受制于自然。“我们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使资源关系成为必不可少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归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从那种资源关系的原型中得出自然界不归属于我们的方式。”换言之,“我们是想要把自己限定在自然界的关系中,而绝不是把自然界限定在我们的关系中。”[11]不仅如此,“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7]195,因而“人类动物与其他一切动物一样,都受制于迄今所发现的所有的自然规律”[12]43,“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然规律都在我们身心里起作用”[12]43。这一切都表明人与物的同质、同构性,人这个“神圣的主体”完全可以还原成客观存在的物质自然。这样,所谓人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本能的、动物式的活动。正如罗尔斯顿所说:“如果我们将自然定义为一切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总和,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把人类的能动行为也包含在自然之内。”[12]43
因此,在自然中心主义的视阈中,传统作为对象世界的客体——自然界被认为是一个有目的导向的自组织性“生命共同体”,并不因为人生活和行动于其中而是人的自然;相反,人这个“神圣的主体”在支持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中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它像自然界的其他动物、植物甚至山川、河流一样同质、同构地消融在自然当中,也即“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有的就只是物质——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物质”。[9]18—19
三、马克思和自然中心主义在主客关系上反转的根本缘由及其价值选择
马克思和自然中心主义在主客关系上的反转,其根本缘由在于他们出发点的不同。具体说来,自然中心主义是“从天国降到人间”[1]73,他们的出发点是“天国”或抽象的“思辨”。从表面上看,自然中心主义张扬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先在性,似乎严格遵循了现代科学成果。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1]76。因此,自然中心主义极为推崇并作为批判人主体性出发点的“荒野”,只不过是他们奇思幻想构想出来的东西,包括自然中心主义者在内的人们现实生活和从事劳作的自然不是未受人类扰动或尚未开垦的原生态的自然,而是人的生产劳动中介过的属人的存在。当然,因为人不能从“无”中化出“有”,所以真实的、自在的自然的存在毫无疑问具有客观性,否则人中介过的“第二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这并不能否定人现实的自然是“通过工业……形成的”[13]193事实,只是说明我们生活的感性世界必须要有自己的客观物质基础。而正是由于从想象中的“荒野”出发解释自己关于主客关系的自我意识,自然中心主义在论证过程中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1]54,因而“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54,陷入了自然观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观上的主观唯心主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73也即从人的物质实践出发去解释现实对象。这样,自然中心主义视阈中与冷冰冰的“荒野”同质的自然人就跃迁成了活生生的具有能动创造性的社会人。为了能够生活,他们能动地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一边引起“环境的改变”,使之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边也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自我改变”[1]55,以更顺利地改造环境。在这种“环境的改变”和“自我改变”长期的双向作用中,人生成了越来越强大的生产能力,从而让他们有条件能建立起“普遍的交往”。[4]39这促使他们“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4]37,而是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个人”[4]39。这种“个人”因其普遍性不再局限于狭隘的地域,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去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从而能有效控制源于强制性分工导致的异化,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由此可见,在当今人类正面临严重生态危机的“艰难时世”,自然中心主义虽然关注科学事实,体现了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但是它肯定历史虚无与想象的原则,倡导弃智复古,回到“荒野”不过“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1]62抽象思辨与意识的空话,难以在当下的环保运动中发挥真正的作用。而马克思关于主客关系的意见却一直站在现实面前,从物质实践出发让“在场者”看到了在人的实践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1]55,从而开辟了保护生态,努力走向未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现实路径。因此,要建设美丽中国及至美丽世界,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让马克思的主客关系理论走进当代以指导自己的实践。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德)黑格尔.自然哲学[M].梁志学,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8] 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孙道进.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困境:一个反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0] 雷毅.深层生态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11]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著,王晓明、霍锋、李立男译.价值走向原野[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6,(1).
[12]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