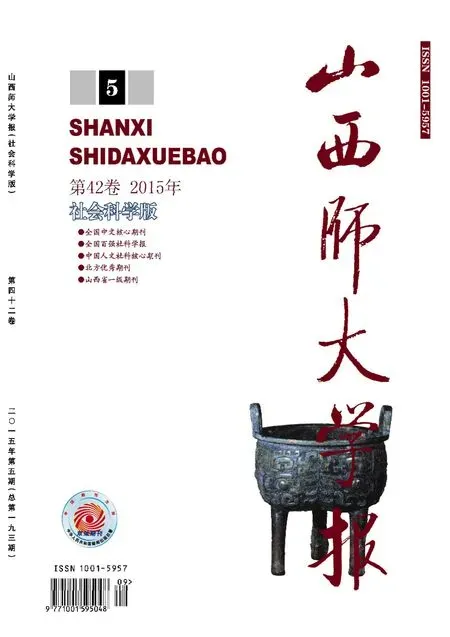传统节日的总体性与人性反思
甘代军,李银兵
(1.遵义医学院 人文医学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0;2.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花溪 550000)
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在其名著《礼物》中考察了古代社会的总体社会事实——与交易相关的道德与经济——礼物和夸富宴,并论述了解答现代社会法律危机与经济危机、“发现建构我们社会的一方人性基石”的依据。[1]6莫斯认为,所谓总体社会事实,是指“能够同时展现全部各种制度:宗教、法律、道德和经济”的社会现象[1]5,这些社会现象展示的是总体的人,总体人具有综合的人性:自利与利他、荣誉与责任、尊重与互惠等品质。
莫斯所谓的总体社会事实与总体人并非仅仅表现在礼物和夸富宴这样的古式习俗中,自古至今存在的不少节日习俗也蕴含着上述总体性特征。传统社会的节日是一个极富包容性的文化体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结构和文化图式在节日中得到全面、生动的展示。人的个体性、社会性,人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人的自利性、利他性,人的责任与荣誉,人的身体与文化的同构等,都在节日体系中予以总体呈现。而在从传统时代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节日的总体性表现出日益碎片化、断裂化的形貌和趋势。这种变化对人类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足以成为反思现代社会人性变化的重要历史经验和思想基础。
一、灵力与信仰
节日最初起源于祭祀活动,后来大多逐渐演化为集祭祀性、纪念性、社交性、娱乐性、经济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庆典活动。在传统节日期间,举行节日的地方社区、族群往往全民总动员,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民众纷纷参与到节日的仪式和活动中,各种信仰关系、道德关系、性别关系、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都得到总体呈现和再造。这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往往借助象征方式予以实现:在仪式活动中,在舞蹈音乐之中,在各种道德联系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物质联系、精神纽带不断再现和强化。
很多节日在历史起源或现实状况上,首先表现为一个群体与某种(某些)神灵的信仰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群体对神灵的集体祭祀活动予以实现的。
仡佬族吃新节祭祀展示了仡佬群众对神力的顶礼膜拜,这强化了神灵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贵州六枝的吃新节于每年农历八月的第一或第二个虎场天开始举行,节日持续三天。第一天是采新祭祀。人们穿着盛装去田地采摘新谷、新果,如小米、毛稗、山药和新熟的蔬菜瓜果。新谷被剥或舂出来后,用挑来的新水做成九个饭团,再准备祭祀。男的把牛马牵到筑在三岔溪沟边的三岔点宰牛场,将牛系在树下,奉上饭团食粮瓜果,寨老用仡佬语请天地和九座大山来吃新。完毕后,寨老唱祭祀歌。然后,人们用棍、斧杀牛并煮肉同食,还把剩下的牛肉与牛心平均分给各户带回家。[2]这样,人们以杀牛祭祀的仪式完成与神祇的关系建构。在吃新节中,人们对神灵的祭献最为隆重、慷慨。此时,人们庄重祭祀的是仡佬族的先祖和灵力。节日中的一些物品以象征的形式承载了先祖的生活历史和族群精神,如小米、毛稗、山药和新熟的蔬菜瓜果,再现先祖当年的生活方式,在吃新节中采摘这些粮食,是表达人们对先人艰苦生活的铭记和感念。人们用新米饭捏成的九个饭团表征的是仡佬先祖的九个兄弟,大家是这个九兄弟的后裔、直系,因而要永远团结凝聚在一起。祭祀地点选择在三岔点,因为这是对祖先生活在三岔河边的仪式化记忆,只有年年在这里杀牛祭祀,后辈才会永不忘记先辈当年生活的栖息之地。由此可见,这些固定使用的祭祀物品、地点,只不过是人们表达对先祖感恩并祈求其佑护生产生活顺利的象征手段、符号,通过这些象征符号的仪式化展演,达到纪念、感谢、敬奉和祈求先祖神灵保护等目的。
在涂尔干看来,禁忌是一种特殊的图腾方式,它是以消极的方式表达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3]396在吃新节采新谷过程中,人们禁止采“田娘”的新谷,据说这是远古母亲开垦的第一块田地。显然这样的禁忌具有深刻的象征含义。在中国文化中,“第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意味着源头、本源,是万物孕育的始基。而“母亲”也是人类孕育的母体,是新生命的哺育者,因而无比伟大。因此,由母亲开垦的第一块田地,是最肥沃、最具生产力的沃土,这无疑是仡佬族后代繁衍生息的不竭源泉和根本保障,因而需要无条件地给予最大保护。这样,人们就以禁忌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了对主宰着整个族群兴旺发达的繁殖力、生产力的顶礼膜拜。
此外,用作祭品的牛心也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人们把牛心切碎均分给各户,每人分食了牛心就会带来健康和活力,人类的世代繁衍传承需要的就是强大的活力和健壮的身体。在他们看来,牛心是生命力的象征,因而,分食牛心是健康、活力的保障。而牛心又来自于具有强健体魄和活力的牛,因而人们对牛心生命力象征的赋予实际上又是人们对深深依赖的生产工具——牛的依赖和崇拜的隐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处于山区的仡佬族既把牛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又把牛肉作为增强生命营养的来源。因此,牛成为他们生命繁衍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故而在文化习俗中把对牛的依赖和情感仪式化,隐喻化,并慢慢变成一种深层的文化结构不断延续传承,这又进一步显示了人类社会对于超越人类能力范围之外而又深深制约着人类社会生存的强大异己力量的敬畏和膜拜心理。
总之,节日中人们通过信仰观念和行为所编织的文化习俗之网所反映的实际上是这样的社会结构:人与对影响自己的异己事物及其强大力量的象征性、事实性社会关系,这是人类难以摆脱的最基本社会关系之一。
二、物质流动与道德义务
在节日期间,除了上述人与神灵的关系以多种方式予以演绎之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现实关系也得到展现和再生产。这些现实关系既有道德、情感等方面的精神关系,也有物质、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关系,往往难以单独从道德、情感或物质、经济某一个方面界定节日习俗的性质,物质联系与精神联系的融合成为节日习俗的基本特征。人类既把肉体生命赖以维系的物质条件呈现在文化形态中,也把精神生命所追求的生活意义编织在文化网络上,最终不同的物质环境与多样化的思想观念结合,促成了多元节日文化的形成。因而,在节日体系中,我们能够发现精神性与物质性社会关系的多样共存。
在仡佬族传统社会,祭山节也是一个隆重的节日,是仡佬族传统的年节,于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举行,祭祀山神、树神和祖先是节日的核心内容,同时也通过娱乐庆祝活动迎接新春的到来。节日这天,本族人汇聚在祖坟所在的草坪,族长鸣放爆竹、火铳表示新年开始了,人们自由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庆祝节日。到了下午,大家一起到祖宗坟前进行祭祀。祭品是5只公鸡和5只母鸡。之后人们又祭祀山神、树神,杀猪宰鸡,用猪、鸡的心肝作祭品。祭祀完毕,大家聚集在草坪上同吃年饭。祭山节是同族人的公共社会活动,共同的血液纽带铸就了浓浓的血缘、亲缘情感,面对已逝的共同先祖,他们拥有集体祭祀、供奉、怀念的相同情愫和伦理义务。在祭拜的前一天夜里,寨里的人点着灯笼到路口用仡佬语喊:“老祖公,三月初三快到了,老人家快回来吧! ”[4]这表达了他们对祖宗神灵回归的期待,第二天的祭祀仪式以周期性、制度化的方式重复着对先祖的上述情感。同样,面对现实中共同交往、生活的本族人,相互之间也有基于同宗同源而形成的宗族情感和道德责任,这些情感关系不仅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得以体现,而且也在祭山节中不断巩固和强化。在祭祀祖宗时,首领带来的10只活鸡分别来自10户人家的供给,每年以轮流的方式由不同的家户承担,这是本族人必须完成的义务。在生活水平低下的时代,鸡是人们生活中珍贵的家禽,养一只鸡要耗费不少粮食和人力,因而,祭祀用鸡每年轮流由10户人提供能够减轻人们的经济负担。这体现了村民共同、平等承担祭祀责任的集体道德规范。苗族芦笙节也有类似的道德规范。芦笙节当天,过节村寨的妇女要早早起床准备酒食,因为附近不过节村寨的村民要进行“乞食”活动。青年男女三五人结为一群,或40岁以上的妇女单独行动,到过节村寨的每家每户“乞讨”。“乞讨”人群中的男性吹起箫笛,姑娘则用苗语吟唱“乞讨歌”,等待奏唱完两曲后,主人就给“乞讨”人群几碗甜米酒。喝完米酒后,“乞讨”者又奏唱几曲感谢与祝福的歌曲,主人则拿出熟糯米饭和第二轮米酒,让“乞讨”队伍带着走向下一家。[5]节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仪式活动,在节日期间,参与节日的各类主体在文化传统的作用下获得了一定的仪式身份和仪式角色,相应的他们也获得了在仪式活动中的某种权利与义务,因而在仪式中他们都必须按照文化习俗的要求认真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否则,一旦违反就会遭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芦笙节上,“乞讨”方与“施舍”方分别遵守上述社会规则:“乞讨”者被赋予了获取酒食、“乞讨”福气的权利,但同时也要履行奏乐唱歌、表达感谢祝福的义务;而“施舍”者则拥有享受音乐、收获感恩和祝福的权利,并相应承担赐予饮食和吉祥的义务。这种以权利与义务对称为基本特征的结构关系,反映的是不同文化社区之间的物质性、精神性互助互补:在相互之间的仪式性、周期性联系中,彼此给对方以物质性补给、精神性满足和社会性认同。
按照莫斯的观点,古式社会是经济系统没有独立出来的社会形态,经贸关系与文化道德活动是融合在一起的[1]166,纯粹的谋利观念是不发达的,它以礼俗、道德思想的形式存在、展现。进而,人们进行的礼俗交换交流既具有以物易物的性质,也具有情感、道德交流交换的精神性质和功能。因此,这是一个与纯粹的商品交换根本不同的社会关系,它离不开物,但又不以物为根本目的,它是以物质付出与回报基本平衡为基础的道德关系。这种以道德义务来统领物质“流通”的现象在芦笙节中有明显的展现。举行节日的村民要向未举行节日村寨的代表“乞讨”队伍施舍酒食,并获得对方的“文艺展演”和祝福,而在下一次自己又可以以同样的逻辑和理由向对方“乞讨”类似的酒食并施与祝福。这样的社会互动过程仍然是以文化习俗方式实现着物质流动与道义互助的融合。“乞讨”者与对方在不同的时空对接中保持着物质与道德交流的总体平衡,人们之间、族群之间以道德纽带、精神满足为指向,以物质流动的对等为基础,以节日为载体,促进了社会内外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三、身体与文化
人对神灵和强大力量的信仰及象征性互动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关系的另一种表达就是人类身体姿势的展示,此时的身体作为文化象征符号而存在,它是人类思想观念的对象化、社会化展现,“所有的思想类型能够被身体所反应,宇宙学、性别和道德划分着身体,所以物理的身体也是社会性的。”[6]247
据学者研究,舞蹈艺术最初与宗教祭祀活动高度融合,“在原始部落中,宗教构成了生活的极大部分,因此舞蹈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宗教意义。”[7]1尔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丰富化,一些舞蹈的宗教功能逐渐淡化,甚至完全脱离宗教活动成为世俗生活的构成部分。但是,在很多节日活动中,舞蹈仍然保留着宗教思想所烙下的痕迹,作为歌舞表现载体的人类身体以生动、丰富的形态继续诠释着身体所有者及其所属社会的思想、信仰。身体成为文化观念的表达工具,并进一步被文化观念塑造为特定的肢体形态,构成文化的身体化展现方式。
因而,我们看到,在不少节日活动中,人们用千姿百态的舞姿和仪式动作表述其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和观念。四川省丹巴县境内的嘉绒藏族在各种节日、重要仪式中都要举行“跳锅庄”活动。跳锅庄的产生、内涵和形式有着深远的信仰和族源记忆根源。在嘉绒藏族中可以见到“左旋”、“右旋”两种类型的跳动方式,前者被认为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后者则是传统的文化表达模式。传统的右旋方式反映了嘉绒藏族古老的信仰观念。在其原始的自然崇拜中,太阳崇拜的痕迹保留在右旋的舞动形式中。在地球上观看到太阳从右往左逆时针转动的现象被融入到太阳崇拜之中,苯教中所描绘的太阳符号“雍仲”——“卐”或“卍”即表示太阳及其光芒,这个符号是逆时针右旋方向,与跳锅庄右旋的舞动方向吻合。直到今天,苯教信徒祭祀神山时也是以逆时针方向绕行,以获得神的庇护和加持。[8]由此可见,作为物质性存在的人类身体除了承担其生理功能之外,它还具有特定社会传统所蕴含的文化表达功能,此时它是作为所属社区文化形塑的结果而存在,它以文化传统所规定的方式诉说着族群的集体意识和心理需求。不同文化对身体姿势的塑造虽然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但身体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却体现了节日习俗的某些共同本质和规律。在贵州榕江县侗族的萨玛节中,我们也能发现相似的文化结构。萨玛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节源于对传说中母系氏族时期在抗敌入侵中牺牲的一位女英雄的纪念和祭祀。此后,当村寨出现水旱灾害或人畜瘟疫时,人们认为是有人得罪了萨玛女神或女神离开了村寨故而招致了灾祸,这时,要举行名为“鸾萨”的祭祀活动。鸾萨祭祀也有定期举行的,以预防萨玛神的离去或惩罚。祭祀当天,除孕妇以外的全村男女老幼来到“萨柄”(侗族共同供奉的女祖先)坪前,芦笙队伍分为两行站立于供奉“萨柄”的“坛”门前,并高奏乐曲。身穿长袍礼服的二十多位父老排列在“萨柄”牌位前,“登萨”(负责看管、祭祀萨玛的人)向萨玛焚香敬茶,然后父老依次饮茶。饮毕,父老随登萨慢步走出向芦笙队员“赐茶”。茶毕,“桑腾”(专门设置第一次祭祀对象的人)与众人连续高呼三遍。这些呼喊意为请萨玛随行祭田,以保佑田地丰产。在去的行程中,“登萨”肩扛着伞(萨玛的化身)走在最前面, “桑腾”、父老、芦笙队、盛装姑娘队等紧随其后。“登萨”缓步前行,“桑腾”踏着前者脚印,亦步亦趋,手持铜锣每隔数十步敲击一声。祭田时,忌讳快走,“快”意味粮食少,不够吃。“慢”意味粮食多,吃不完。到达祭田后,祭祀队伍绕场三周,由“桑腾”行祭祀礼,将铜锣扑地,焚香化纸,然后用脚象征性地蹬铜锣三下,收回铜锣,祭田完毕,队伍按原路以同样方式返回“萨柄”坪。请萨神、祭田持续两天,第三天举行“转寨”活动,也一样要请萨、祭田,但是在游行队伍中增加了一些有趣的化装游行者,他们装成乞丐、补锅匠、猎人、逃荒者,进行各式各样的滑稽表演。[9]161
在上述萨玛节中,身体被萨玛信仰观念和传统习俗所形塑。参与节日仪式的所有人的身体都以特定的形态、动作展示了其作为文化身体的属性和功能。身体首先成为文化规训的对象,这显示了文化对人类肉身的塑造作用:文化把人的身体分割为日常的身体和仪式的身体,使同一个身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时空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意义。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体表达主要服务于社会规则和生理功能的要求,而在萨玛节中,人的身体则从属于族群萨玛信仰的需要,身体成为人与神灵沟通、表达人对神灵敬畏和祈祷、展示集体团结协作的象征符号与手段。在当地侗族人的观念中,萨玛是其庇护神,是崇拜的偶像,因而,他们进行社会总动员,以庞大的队伍、虔诚的姿态、整齐的动作、统一的语言、动听的音乐和趣味的表演,表达对萨玛的尊敬、信任和期待。因此,信仰的力量塑造了人们特定的身体动作、肢体语言,并由此强化了人性中敬畏、互利和责任等美好品质。
总之,在不少节日中,身体作为文化的外显符号和手段,表达着人类与外在现实世界或想象世界的密切关系,这些关系是总体性的,既有物质性关系,也有精神性关系和道德性关系,既有实在的关系,也有象征的关系。身体成为连接这些关系的重要纽带和媒介,并表达、阐释这些关系,促进这些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荣誉与责任、自利与利他、自由与自律等光辉品质不断展现和深化。
四、总体性与人性反思
莫斯在《礼物》中描述了这样的社会道德及行为原则,即权利的情感、仁慈之情、社会服务之情、团结之情,还有自由与义务、慷慨施舍以及给予将会带来利益等,[1]160这是对总体人性的概括,它们在传统节日中得到全面的体现,节日中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道德、法律、经济和宗教等关系塑造了人性的综合面向。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既有相互独立、自由和约束对方的权利,也有相互施舍、互助的义务和精神思想的互动;人在这样的关系中既培养了信义、同情、慷慨,又形成了荣誉、热情、团结协作、自利与利人等人性美德。传统节日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庄重神圣的节日活动和仪式中,完成了道德教化和人性培育。在此基础上,优良的社会美德才一代代传承下去,转化为人性中最光辉的内核,并成为地方社会团结、兴旺的精神源泉和支柱。
传统节日中的光辉人性无疑是引导现代节日重构的道德基石。在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传统节日的性质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节日精神发生异化,总体的人性美德也开始碎裂,这一切根源于传统节日总体性的瓦解。传统节日的总体性表现为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集体的高度融合以及这诸多关系的并存与统一,并通过活动仪式、肢体形态控制和躯体与心灵合一等方式塑造了群体的文化传统,实现着世代的延续与强化。而进入现代社会,节日传统从形式到内涵发生重大变化,节日总体性发生消解:展现神灵信仰的祭祀性活动或者消失,或者空壳化、表演化,人对神的去魅化助长了人欲的过度膨胀,进而使宗教的制约功能丧失或弱化;在传统节日中蕴含的人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自然生态的维护、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朴实智慧也随着节日的现代转化而不断消减,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和过度攫取倾向日益明显;个体深深融合于共同体并与共同体保持精神、物质统一性的纽带也开始崩溃,现代节日中日益增强的个人中心主义和自我利益使传统的道德责任与情感削弱,节日变成自利排斥利他的私欲竞逐之地;在现代社会中,商业化、经济化乃至过度政治化的节日属性逐渐形成,传统节日活动中身体符号与文化内核的一致性被破坏,身体不再是文化传统的自然流露、诠释和传承,而是变成了供游客观赏并可以带来经济收益的符号资本——身体通过记忆文化传统这一异域“特色”获得观众的认可和消费。因此,节日总体性的消解使人性的光辉黯然失色,莫斯所预见的 “经济人”、“单向度人”开始出现,“传统节日被异化为商家‘促销节’和人们的‘吃喝节’。”[10]“官商主宰或官商合谋以左右传统节日走势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愈来愈明显。”[11]节日逐渐蜕变成以金钱为核心和目的的场域。传统节日中人的权利与责任、自利与利他、“经济与道德”和谐统一的总体人性面相开始碎裂,在商业化运作和金钱逻辑的支配下,节日中欺诈蒙骗、自大傲慢、丧失人格的不良现象层出不穷,信誉、同情、慷慨、团结等美好情感不断被抛弃。“经济人”的出现毁弃了总体人性之美,这是现代社会片面发展的不良后果。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节日的人性光辉中汲取道德养料,对现代节日、现代道德进行深刻反思和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真正幸福文明的和美社会。
[1]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M].汲喆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 韦名应.六枝仡佬族“吃新节”的主要特征及其价值[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0,(3).
[3]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袁瑛.论仡佬族节日文化及其现代价值[J].贵州社会科学,2006,(5).
[5] 吴正彪.“区域性板块”结构中的活动仪式链接与符号系统——从贵州岜沙苗族芦笙节的文化象征意义谈起[J].贵州民族研究,2004,(4).
[6] Anthony Synnott. The Body social: Symbolism, self and Society. Routledge, 1993.
[7] 刘建,张素琴,吴宏兰.舞与神的身体对话(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8] 李菲.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嘉绒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J].民族艺术研究,2011,(1).
[9] 黄才贵.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10] 于凤贵.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创新[J].山东社会科学,2012,(7).
[11] 刘锡诚.传统节日文化的继承与发展[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