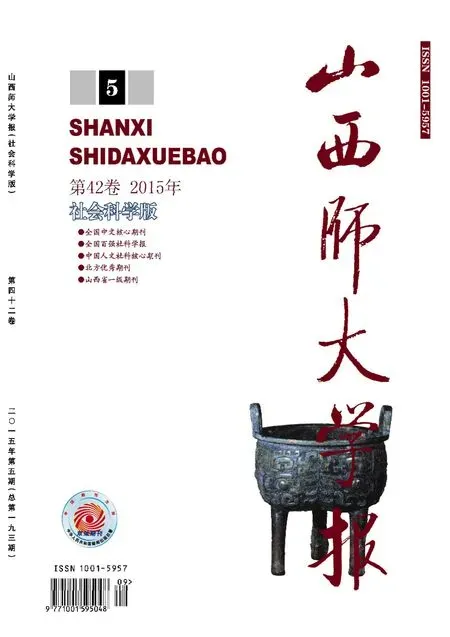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军户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张 月 琴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目前对明代军户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于对军户群体的整体性探讨。也有学者将明末军户放置于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人口与土地、社会变迁等问题中进行考察。学界对于明末军户在清代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分化和解体的,他们的实际生存情况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很少有人作历时性的研究。明代相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军户的分化只是在小范围内发生。本文暂不讨论旧军户群体内部的分层和流动,仅将军户群体研究,放置于明末清初边疆内地化的社会大情境之下,将长城沿线一度驻军最多的大同府属区域作一考察,尝试探讨明末清初旧军户群体的分化、解体和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明末清初旧军户群体的分化
“云中为山右重镇。昔日镇城环之以二十三营路,星罗棋布。而云城居中而驭外,虽与平阳相为犄角,然山川之雄健、关隘之险阻,甲于西北,故云中之兵亦倍于南镇。”[1]320明代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屯集了大量的军队,其中有世袭的军户,也有募兵。据《三云筹俎考》记载,大同镇的驻军编制为90966人,战马31785匹,还不包括增援部队和临时招募的士兵。明蒙之间战争最紧张的时期,大同的驻军曾达到13万人,时有“大同士马甲天下”之称。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给官兵请赏的奏报中提到,“大同镇官军八万四千五百三十七名”[2]1201,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支援辽东战事的兵士。明末清初,沉重的军役、频发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推动这一规模庞大的军户群体加速分化并走向解体。
军户作为一种军役职业群体,在明朝与瓦剌、鞑靼的长期战争中承担着繁重的军役,同时,还有“里甲”、“均徭”等名目也要支应。“卫所军家缴纳的子粒比州县从民户(这里所说的民户包括卫所军家在原籍的军户)征得的税粮要重得多。”[3]明末辽东战事,加之饥馑、粮饷欠缺,随时会引起军户的哗变和逃亡。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大同总兵焦垣领兵八百名援辽,先是任用纨绔子弟出任领兵军官,沿途军纪不整,军心动荡,后来又用酷刑统兵,“至怀安城,夜哗,城几不测”[2]1197。崇祯十四年,边患、灾荒之下,右玉一带,“军民动辄鼓噪,盗贼所在窃发”[4]293。
发生变乱的军户,或被安抚,或被镇压,或被重新拘捕为军,或沦为寇。天启元年,陕西都司陈愚直以固原兵入援辽东战事,溃于临洺,延绥、大同、宁武等处都因为军士掳掠鼓噪,先后奏报于朝廷。“兵部请行督抚逮治首恶,以正军法,领兵都司守备责令赴辽待罪立功。”[2]1210流寇,“始于榆林军,劫略近地,不即扑灭,遂至蔓延”[5]202。在流寇向全国扩散的同时,吸纳了边地军士,“大抵贼首皆边军,且良家子及武弁世职,故隐其姓名,而以绰号称”[5]202。不过,各镇军户沦为流寇只是小范围之内的变动。
清初,战乱是长城沿线旧的军户群体趋于瓦解的直接原因。“朔界北边,平定之初土著寥寥,生息无几,世被边患。自明季迄我国初复罹兵燹,十亡八九。”[6]448姜瓖兵败城破后,清军对大同进行了屠城,“斩献姜瓖之杨振威等二十三员及家属并所属兵六百名,俱著留养,仍带来京。其余从逆之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将大同城垣自垛彻去五尺”[7]1857。城中的兵士和居民俱遭杀戮,大同变成一座荒城,府治移至阳和卫,名为阳和府,县治移至怀仁县西安堡。《重修大同镇城碑记》中记载:“戊子之变,谁非赤子,误陷汤火,哀此下民,肝脑涂地。是非莫辩、玉石俱焚,盖以楚猿祸林、城火殃鱼,此亦理与势之所必至者,睇此芜城,比于吴宫晋室,鞠为茂草,为孤鬼之场者,五阅春秋。哲人以黍离之悲,彷徨不忍释者”[8]。直到顺治九年(1652年)府县才复还故址,从附近移民逐渐复兴。
以军事起家的军户,很多丧身于清初的变乱中。何士琏,祖上从江南到威远卫戍守边疆,到了姜瓖之乱时,“家居者靡有孑遗矣”[1]546。类似的还有跟随姜瓖起事的其他卫城军堡的军户。据记载,左卫城(在今左云县)明中叶时,已经达万户,清初遭屠戮之后,“其所遗者不过中心街衢居民数百户而已”[9]458。
二、旧军户群体的解体和新军户群体的成长
入清以后,国家政策是直接推动旧的军户群体走向解体的主要力量。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国家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涉及范围也不尽相同。对军户群体而言,则是经历了一个由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逐步被裁减的过程。
顺治初年,首先从军户群体的上层入手,革去世职。“洪武初,置大同所属卫、所、指挥、千、百户、镇、抚、总、小旗共八百九十一员。顺治三年,尽革世职。卫之掌篆者由部推,并每卫推千总一二员。”[10]229对于已经成为清军一部分的普通军户而言,并没有采取较大的动作。顺治十一年,开始通过“裁卫设县”,以行政力量推动军户解体。“裁山西振武卫右中前后四所、镇西卫左右中前后五所、太原左卫中前后三所、太原前卫右中前三所、汾州卫左右中后四所、潞州卫右中前后四所、平阳卫左右二所、又裁汾州卫前所百总一员、太原右卫守备、及五所千总。”[7]2176此时,虽然不是被裁卫所的首例,但是尚未涉及对长城沿线卫所的裁撤。清初长城沿线一带,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军事力量。
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四日,康熙帝给大学士马齐、席哈纳、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的上谕中说:“卫所改为州县,断断不可。前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即预以卫所改为州县,朕不允。所请后,陈世隆又以此条奏,九卿议从其言,因而准行,至今百姓尤以为苦。近者如此况远者乎。御史陈勋所奏,著不准行。”[11]752康熙帝的上谕中,关心的是百姓疾苦和裁卫设县的实际效益。事实上,长城沿线和全国局势的尚未稳定,是卫所没有被大规模裁撤的根本原因。卫所仍在,其中的军户就在。
雍正三年,国家西北战事基本结束,山西巡抚诺敏请裁去沿边卫所改为州县,相应官职也一起裁撤。这一提议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设山西朔平、宁武二府。改右玉卫为右玉县。左云卫为左云县。平鲁卫为平鲁县。并割大同府属之朔州、马邑县。俱隶朔平府管辖。改宁武所为宁武县。神池堡为神池县。偏关所为偏关县。五寨堡为五寨县。俱隶宁武府管辖。改天镇卫为天镇县。阳高卫为阳高县。移原驻阳高通判驻府城。俱隶大同府管辖。改宁化所为巡检司,隶宁武县管辖。朔平、宁武,各设知府一员。宁武府,设同知一员。右玉等九县,设知县九员,典史九员。宁武,设巡检一员。裁太原府中路西路同知二员,右玉等卫守备十员,宁武等所千总十三员。”[7]6349在裁卫设县的过程中,并开始关注地方行政管理是否便利的问题。雍正六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疏言山西之蔚州与直隶之蔚县界址交错。应俱归直隶宣化府管辖。广昌县与蔚县县治村庄俱相交错。而蔚县向设广昌巡检一员。止经管广德一里。请将广德地方归并广昌,仍隶山西大同府管辖。其巡检缺可以裁汰。至广昌守备向系宣化蔚州路管辖今应专属山西灵邱路参将管辖”[7]6893。十年,又以大同府属之广昌改隶直隶之易州。
裁卫设县改变了原来卫所驻地的行政区划,对原属卫所的军户来说则是直接变为民户。这并不是说长城沿线一带不需要驻扎军队,而是新的军事需求,直接催生了新的军户群体:一种是特权军户群体,主要指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另一种则是新成长起来的军功群体。
八旗驻防,起源于各地“土贼窃发”。《清实录》记载:“近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如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著满洲统兵驻劄。务期剿抚得宜,以安百姓。以上八处驻劄满兵,著给以无主房地。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7]1673实际上,驻防是清王朝为了镇压与防范汉族、少数民族的反抗,或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驻防各地的过程中,有的圈占驻防地原有城池的一部分,有的规划建设了新城池,以驻扎八旗官兵。至清代中期直省(内地18省)、东北和西北各地的大小满城即增加到40多个。康熙帝,“以雁门关外逼近边陲,为畿辅肩背,特命将军率禁旅驻防,与直隶、宣化、陕西、宁夏相为犄角。”[12]1195康熙三十二年九月披甲蒙古兵三千零六十五人驻防。“统帅禁旅弹压严疆者,非公侯勋戚则宗室天潢,望隆位尊,班在督抚之上,责綦重矣。”[12]288朔平府城,当时在右玉县,“城内驻劄将军都统府县参守等官及镶黄正黄两旗官兵,为关外重地。”[12]163满城驻防直接滋生的就是新军户群体。
新军户群体,除了八旗驻防的军户以外,还有历次征战中形成的军功群体,也有后来发展成为军功家族的。“仝光英,由行伍起家。顺治六年,任江苏水师协都司。海贼郑成功陷崇明,遂犯江宁。光英从总兵官梁化凤率兵击走之,克服崇明,以功超擢副将,协镇其地,海疆晏然。加授骑都尉,世袭。”[1]400高鼎,明末聚乡勇保五台,顺治时为参将,后来镇守松藩,“在镇十四载”,“第四子麟端勇捷,有父风,以荫授蓝翎侍卫,历川北镇右营游击,升参将。尝从征滇、蜀,累树战功”[1]400。史成,“康熙丙子以把总随征噶尔丹,战召磨多,有功。……成起卒伍至大将,历官二十余年。……子载贤,湖广提督;从孙宏蕴,广西提督,俱克世其家。论者比之前代麻氏云。”[1]401这些新的军功群体,大部分出身行伍,深受祖辈影响,从小勤于习武,在明末的战乱、平定三藩和康熙征西的过程中,累次获得战功,甚至荫及子孙,成为军功望族。八旗驻防和新军功群体的产生,彻底宣告了旧军户群体的命运走向终结。
可以说,从明代至清代,军户是大同地区一个曾经数额庞大又慢慢被分化、融合和发展了的群体。军户,作为一种职业群体,其转变对于地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军户群体的变动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
边疆内地化,是长城沿线区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从地理空间上讲,明代的边疆之地,变成了清代的内地。从社会文化上讲,文化边缘地带向文明开化之地的转变,并逐步成为“腹里”之区。诸多的因素一起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进行,其中,旧军户群体的分化和新军户群体的形成,对于历史演进中大同地方的社会结构产生了直接、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了人口性别结构,改变了地方的民族结构,丰富了地方的职业结构。关于军户改为民户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影响,由于缺乏直接的数据,无法深入研究。对民族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八旗驻防、杀虎口税关官员及其随行人员的驻入,使地方上满族人口增多。在此对这两点暂不作讨论。以下主要就军户群体对于地方社会职业结构的影响作一探讨。
《明史·食货志》“户口”中指出:“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着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13]1878可见,明代户籍分等是以职业作为基准的。民户、军户、乐户等,皆以职业断分,也以职业命名。王毓铨在《明代的军户》一文中讨论的军户也指的是“民人之中供应军差的特定人员”[14]。那么,军户的职业就是承担军役。万历《大明会典》载,洪武二年,“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各以原报抄籍为定,不许妄行变乱;违肯治罪,仍从原籍”[14]一九.户部六.户口一。明代相关典籍中对于户籍的规定,说明了军户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承担军役的职业群体。
一个相对稳定且数额庞大的职业群体的解体,对于地方职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军事职业群体规模缩小,其他职业群体人数增加。清初开始的裁卫设县使大部分军户著地为民,成为固着在土地上以种田地为主、兼以畜牧的农民。“北路各州县及口外各厅地多沙碛,宜于畜牧,如骆驼、山羊、骡马之属,均为出境货品之大宗,乡人业此致富者甚多”[16]职业篇第三。那么,究竟有多少军丁变成了民丁呢? 据《山西通志5田赋》载:大同前卫及各城堡归入大同县屯丁4142名,大同前卫怀仁所归入怀仁县屯丁924名,大同前卫中前所归入浑源县屯丁350名,山阴卫所并大同前卫归入山阴县屯丁905名,安东卫并入应州屯丁1482名,朔州卫并马邑所归入朔州屯丁8877名,井坪所、乃河堡、贾家堡归入平鲁县屯丁1470名。屯丁是在卫所屯田的军户中的男子,不包括妇女儿童。据上述,共有屯丁18150名成为了民丁,但是这并不是所有在“裁卫设县”的过程中成为民户的军丁的数字。该项记载中没有阳高、天镇、右玉、左卫等屯田卫所的屯丁数额。阳高,“自洪武创建城池,即以军籍实之。而后生齿渐繁,成丁者咸入册,定等为三,例则为五,而深山穷谷皆隶籍焉”[17]77。转为民丁的军丁的实际数额要大于18150。据顺治《云中郡志5食货志》记载,大同府属阳高卫、天镇卫、大同前卫、后卫、左云卫、右玉卫、威远卫、平橹卫、朔州卫、安东卫九卫及大同、左等十四团操与安、浑中所、井平所、马邑所、山阴所、怀后所五所,“人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一名”[10]169。将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后者比较接近转为民丁的实际军丁数。
除了转化为农民之外,也有出身军户的世家继续为军的。史朝顕,“性豪爽,不拘小节,世袭副千户”,在明末李自成攻陷大同后,全家遇害仅留下幼子史笔。后来,史笔的儿子史成,“于国朝任浙江宁台总兵,诰赠三代荣禄大夫”[6]642。史成的儿子载贤任湖广提督;从孙宏蕴任广西提督。时人的评论是,“比及前代麻氏”。[1]401麻氏,为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族。穆生辉,祖先为临县人,原属天城卫军籍,顺治初年,“以克服朔州功,授大同镇左营参将,徙征江西,转战楚越间,所向无敌,积功至副将。”其子朗佐,“袭职,官至汾州参将”[18]467。罗光乾,是明代金吾左卫指挥的后裔,“累世以武功显”。其父为兵部进士,曾任参将。光乾“生而勇毅,善谈兵,有父风。少孤,依季父映坮徙戎行间”[18]469。
军户中也有的改为文人,或者在其后代中有的子孙成为文人。威远卫,范鼎铉,“博学高才,工诗律书画,皆臻其妙”[12]772。路玙,其祖先以武功著称于世,他却在官署担任文书,后来以考试取得廪生资格的生员享受廪膳补贴,一时之间在学校的名声大震,曾经以“博览多闻见,寡交少是非。”[1]431二语自警
有一些还可能成为矿业苦力或者小手工业者。矿业苦力不仅指小煤窑的生产者,而且也指其他矿的生产者。乾隆时期大同府有民众偷挖银矿的记载:“(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据该参将禀称,察访得镇边堡口外北山干柴洞地方,聚集三四百众,刨洞口二三十处,偷挖银砂,各有窝铺容身,安炉烧炼,内有供用盘费头领人等”[19]598。天镇,“物产:南川多盐,县川多碱,悉煎土而成,村民以为专业,故县境诸村多有以窑名者。盐色白如雪而味颇清淡,又皆细末,不能成粒,土人谓之小盐,远逊蒙盐之美,故今年业之者稀,仅敷南乡诸村食用而已。碱则随地有之,富商大贾为备器具,募工匠,遍设作坊,岁所得不下百万斤,贩往京畿,每获重利。然商皆来自汾太,县人无此重资也,唯刮土淋卤,稍得工值,余润所及差免冻馁。然不毛之地,以之代耕,未必非天哀边民之穷,俾自食力,特为此无尽藏也”[18]56。新修的《天镇县村镇简志》中记载距县城33里的兰玉堡村,清代中后期制碱业已步入盛期,民国37年(1948)有碱户150余家,盐户62家,碱池53个,盐池25个;碱锅1套20口,日产碱1块300公斤;常年1个盐池产10石盐。年产碱10.8万公斤、盐7.35万公斤,销本地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及兴和县一带。[20]150天镇,“介燕云间,居晋极边,前代尝为兵卫”[18]序,天镇的制碱业、制盐业的发展极有可能吸纳了旧的军户作为劳动力。
以上所举主要是转为民户的个人,就军功家族而言,其转为民户的命运同样不可避免。位于大同市大西街清真寺中,存有14通碑刻,记载了麻氏家族在明代以来的生存状况。麻氏家族在明代以军功著称,到了清代以后,逐步演化成普通民户、商户和其他行业从业人员。清嘉庆二十二年《送于寺中田舍碑文》中,有麻公捐献粮地、铁铺及商铺租金的相关文字。清道光九年《盖闻修葺天房者而思造物之源》碑文中提到麻公“送红果香牛皮二张,营中修置食盒十架,以备公用耳”[21]70。这些碑文,说明了清代大同地方的麻氏家族种地、经商,开设铁铺,并进行房屋租赁等营生。麻氏家族是长城沿线地区,军户群体分化流动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明末,军户群体的分化流动开始加速,沦为流寇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清初的战乱和裁卫设县等政策使得军户群体开始大规模转向民户,以种田或畜牧为生。与此同时,军户群体开始向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转变,有的为商,有的从文,有的成为煤窑工人或者小手工业者,等等。在旧的军功群体走向终结的同时,为了西北战事和维护国家稳定,八旗驻防右卫城,新的军功群体开始产生并成长起来。八旗的驻防和右卫杀虎口税务监督署的设立,则改变了大同地方的民族构成。这些转变是国家政策直接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边地开始变为腹里之后,社会向常态化运行的一种必然结果。
[1] (清)黎中辅,许殿玺校注.大同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 李锋,等.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下册)[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3] 顾诚.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2).
[4] (明)霍瑛.云镇兵荒疏.马邑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5] (清)抱阳生,任道斌点校.甲申朝事小纪[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6] (清)王嗣圣修,王霷纂.朔州志[M].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7]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 邹玉义.《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考辩——曹雪芹祖籍辽阳的又一权威史证[J].红楼梦学刊,2003,(96).
[9] (民国)高鼎臣.左云县乡土志.左云县县志编纂办公室翻印本,1992.
[10] (清)胡文烨.云中郡志[M].大同市地方志点校注释本,1988.
[11] 中仁.康熙御批[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12] (清)刘士铭修,王霷纂,李裕民点校.朔平府志[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
[13]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4] 王毓铨.明代的军户[J].历史研究,1959,(8).
[15] (明)张居正.大明会典[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转引自王毓铨.明代的军户[J].历史研究,1959,(8).
[16] (民国)山西风土记.职业篇第三.任根珠点校.山西旧志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 (清)房裔兰修,苏之芬纂.中国方志丛书:阳高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18] (清)洪汝霖修,杨笃纂.中国方志丛书.:天镇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9] 朱批奏折.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 天镇县史志办公室编.天镇县村镇简志(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21] 赵玉珍.明清时期长城沿线回民聚落的变迁[D].中央民族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