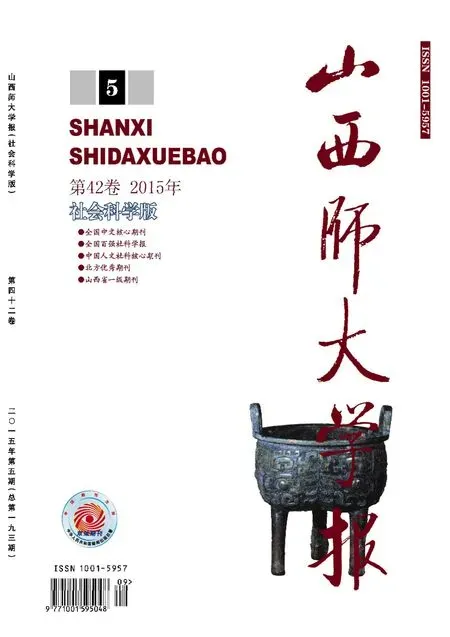小城镇建设中的生态美学思维
梁 晓 萍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一、几个关键词及问题的提出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οικοs,原指栖息地或居住处所。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提出生态学这一科学概念,旨在关注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强调一切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相关的生物链关系。生态学以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反抗和拒绝着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使一个人类生态学时代成为现实,并催生了各种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形态,如生态社会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以及生态美学等。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和美学两门学科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型思考,兼具两门学科的特点,既有生态学关注整体生物的理论视野,又有美学关注人与其现实关系的理论自觉;既吸收了生态学这一自然科学的客观理性之思维特点,又汲取了美学这一人文学科关注人类感性的价值取向。生态美学就孕育并生长于生态学与美学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纽结点上。不过,生态美学又并非是生态学和美学这两门学科的简单相加,它有自己独特的关注对象和研究理路,有自己独特的思维特征和审美判断,因为它不仅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诸种关系。
小城镇的出现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小城镇具有大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如进入成本相对较低,文化适应比较快,人口吸纳吞吐能力强。可以说,小城镇是乡镇企业的再生地,也是县域经济的富民地。尤其在当下,它越来越成为破解“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有力助手,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平台,也成为加速农村城镇化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便捷通道。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小城镇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强调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战略;“十二五”规划中,中央再次强调,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小城镇作为“大中小城市”的一个单列部分被着重提出,其特殊性与重要性不言而喻。2014年6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时再次强调指出,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使其功能互补,并主张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推进城镇化建设。
然而,当前的小城镇建设中尚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譬如认为小城镇建设主要是经济建设,至于生态建设,等经济好了自然可以修复与完善;或者认为小城镇建设就是搞好绿化,做一些表面性的工作,照顾好视觉感受便可以了;或者认为小城镇建设是小城镇自己的事,与其他大、中城市、乡村等没有多大的关系,等等。形成这些短浅想法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即与缺少生态美学思想有关。因此,很有必要强调,在生态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务必要坚持生态美学思维。
二、整体性思维
“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想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世界的核心思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思想更为加剧,“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也变本加厉地膨胀,“人是最为高贵的”、“人是万物的灵长”、“人是宇宙的中心”等思想跃居人类心灵的首位,压倒一切,不可一世,并成为人类向自然肆意攫取的借口和不二理由。近代以来,这种思想乘着西学东渐的船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尤至近些年来,这种思想受着金钱的诱惑,出入于各个领域。表现在小城镇建设中,则有以下各种情形:一些小城镇为追求经济利益,打着“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旗号,或大肆开采当地的矿物质;或在离居民居住区不远之处开办燃着黑烟的小型工厂;或盲目向大中城市学习,一味谋求高楼大厦。将居民区变成了建筑工地,树木被砍伐,水质和空气变坏。殊不知,生态一旦被破坏,绝非用金钱便可在很短时期内买回来的,而人类却已遭到惩罚。
正是意识到这种观念与做法的极端性和现状的严峻性,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鲁枢元、徐恒醇、曾繁仁等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美学”的概念,并大力提倡以此视野进行生存论思考。小城镇是居民生存的场域,它关涉着居民的生活起居和幸福指数,小城镇清澈水域的保持和洁净天空的坚守,都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打造。而要想真正建设生态小城镇,就要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禁锢,以人与自然乃一元的思维方式以及“齐物”思想作为行动的指导。余谋昌认为,生态系统最重要的客观性质就是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因此他强调“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1]33。地球上的诸多物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物种之间、物种与大地、物种与空气和水源都是一个有机整体,破坏任何一环的做法都会造成有机整体的坍塌,都意味着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必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意识到,所有的物种和实体都是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平等的。人类不再高高居上,不再位于万物中心,而是居于万物之中,与众生同排列在一个有机的序列上。如此,则人类生存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其与周围事物的诸种联系之中,这就是整体性思维,也即普遍联系的思维,或一元思维、天人合一思维。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人已经具有这种一元思维,他们对自然抱有一份敬畏之心,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天然朋友,将人视为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其他诸子的思想,都在这种宇宙观中展开,尤其是道家,更具有一种万物平等的齐物情怀。“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2]21,以“道”的观点来审视万物,细小的草茎和高大的庭柱,丑陋的癞头和美丽的西施,都是相通而浑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25。尽管古人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一元思维与今人所说的“整体性思维”尚不相同,然而这种为自然保留一份“魅”的做法却依然是现代人需要坚持的可贵品质。
因此,生态小城镇的建设首先应当以这种整体性思维为指导,真正认清与人相关的一切物种与实体均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与人类相关相通,相融相生,唯有在此背景下建设小城镇,方可实现其“生态美”居所的真正目的。
三、形质兼美的思维
有人认为,生态小城镇的建设无非是增加些绿色植被,增大些绿化面积, 为小城镇增添些绿意罢了。这种理解很有视觉感受,但亦很能迷惑人们的深层判断。实际上,这种理解十分不利于生态小城镇的建设。因为这种理解不过仅仅停留在表面,认为小城镇建设只要能够满足人们的视觉感官享受就可以了。绿意的增加的确可以为小城镇居民带来意想不到的惬意,如,春天,漫步街头,映入眼帘的到处是欲滴的绿色;夏天,进入公共场域,迸入眼界的到处是姹紫嫣红的树木花草。然而生态小城镇建设不仅有表面的工程,更有实质性的内涵,形质兼美才是生态小城镇建设的真正理想。
生态小城镇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居民诗意地栖居,而居民能够诗意地栖居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绝不仅仅是户外公共场域的绿化。生态小城镇是小城镇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与平衡统一,也就是说,生态小城镇关涉的不仅有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是否能够和谐相处的问题。如果说,生态小城镇建设中人与居所环境的关系是有关“形”的方面的话,则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属于“质”的层面,这其中又包含小城镇的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深层环境生态。就是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居所周边环境的关系,还包括其他更大范围的环境生态。
小城镇的社会生态,典型地表现为居民有自觉的社会生态意识,即在人际交往方面不是互相仇视,互相使绊,互相构陷,互相拆台,而是能够遵循和谐共处的原则,谨记和恪守平等相待的原则,彼此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为镜子,以简单的程序彰显出一种舒适的节奏,以互尊互让的礼遇开拓出一片宽松的社会生存空间。
小城镇的经济生态,典型地表现为在其生产、销售与消费的过程中,不是过度崇拜科技决定论,或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不是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斤斤计较,而是能够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原则,公平交往,互利共赢。在衡量经济水平的高低时,不仅参照GDP的增长数额,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实际质量,追求洁净生产和文明消费,追求资源的再生利用和循环利用,谋求更为长远的经济利益。
小城镇的环境生态除了增加绿化面积的办法外,还应当做到尊重与居民密切相关的一切自然,保护周围的一切环境,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性格局,将人的活动限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做到合理开发自然资源,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这才是符合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深度生态之举。
如是,则对生态小城镇建设的理解便不会仅仅停留在“以绿色涂抹”的表面层次,而是做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引领下,重视生态小城镇的“质”的建设,既注重自然环境生态的建设,也注重社会生态和经济生态的建设,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都能够和谐共处。这样的小城镇,既不失其自然田园风光的底色,又有现代城市文明的色彩,是一种花香树茂、山清水秀的花园式小城镇;这样的小城镇,人们热爱自然和尊重自然,也能够顺应自然,是人与环境友好相处的天人合一型小城镇;这样的小城镇,居民懂得节能减排和废物利用,是环保型和节约型小城镇;这样的小城镇,时空都充裕舒适,办事程序简单合理,生活节奏恰切如意,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宜居型小城镇。也唯有如此,小城镇才真正堪称具有生态美的小城镇。
四、合作共赢思维
在生态小城镇的建设中,不仅要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守旧思维和生态梦魇,具有整体性的建设思维,还要去除做表面工作、树形象工程的狭隘理解,做好形质兼美的全面打算。做到这些还不够,另外,还要摒弃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局限思维,与其他区域合作,实现共赢的建设目标。
目前对小城镇的界定有多种,费孝通认为它“由乡村中比乡村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组成”,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乡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乡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3]18。袁中金基于城乡动态变化的观点,将小城镇看成一种中间状态,即城乡过渡体[4]18。他们都认为小城镇属于城市之末,农村之首,是一种城乡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桥梁和纽带。*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经济调查总队《小城镇建设与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中,将小城镇分为七类,并对每种类型的比例进行了大致估算,分别为综合发展型(35%)、乡镇企业型(25%)、市场拉动型(10%)、交通区位型(5%)、旅游开发型(5%)、行业服务型(10%)、科技卫星型(10%)。2006年,建设部确定为四种重点类型:工业型、农业产业型、商贸流通型、旅游型。详见鲜祖德的《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第17—19页。建设部项目组的《新时期小城镇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第45—50页。除了集镇、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外,较小规模的县城也常被界定为小城镇。不过,无论哪一种理解,小城镇都属于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因此,有人认为,小城镇的生态建设是其自己的事,与其他地方关系不大。
与大城市相比,小城镇的确是小,但是它不是绝缘体,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或其他城镇,因而,小城镇的生态状况绝不仅仅是它自己的事。一方面,周围的大、中城市与乡村的生态情况也会影响到小城镇;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生态情况也会影响到周围的大、中城市及乡村。因此,生态小城镇的建设需要与其他的大中城市一起联手。
世界各国的城乡发展经验表明,小城镇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小城镇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长足的发展。1980年代,中国的小城镇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社会的功能也逐渐趋于完善,对周围城乡以及社区的辐射力、吸引力和综合服务能力都明显提高。事实证明,越是靠近大、中城市的小城镇,无论从社会生态、经济生态,还是从自然环境生态角度而言,其发展速度都相对较快。可见,大、中城市发展了,小城镇自当也会受益,反之,其他区域发展慢,也会影响到生态小城镇建设的步伐。
小城镇周围乡村的发展同样会影响到生态小城镇建设的步伐,我国江浙一带的乡村发展迅速,一些乡村在环境生态建设、经济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些乡村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周围小城镇的生态建设。另一方面,小城镇的生态环境也会反过来影响大、中城市和周边乡村的整体建设与发展速度。生态小城镇建设好了,周边城市或乡村一定也会受益匪浅。中心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小城镇的发展,乡村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小城镇全方位的生态建设。目前中国成功的生态小城镇模式主要有工业型、农业产业化型、市场劳动型、旅游开发型、综合型等,这些小城镇的生态建设都会或通过促进乡村企业的发展,或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或通过产业集群,或通过农业产业化等途径,不同程度地促进周边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从而加快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也加快农村人口的现代化进程。
通过城镇化而带动全国的城市化建设是我国目前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而生态小城镇建设与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又如此密切,因此,唯有坚持共赢原则,才是建设生态小城镇,从而实现城镇化目标的有力保障。
当然,中国在建设生态化小城镇的过程中除了上述问题外,还存在诸多具体的困难,如资金与人才短缺,土地与资源浪费,体制与管理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尚需要更为久远的计划与努力。不过从长远看,所有这些问题都关联到观念与思维问题,倘若能够以整体性思维来理解这一目标,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极大危害;倘若能够以形质兼美的思维来理解这一过程,认识到做表面工作的局限性;倘若能够以合作共赢思维来理解这一梦想,认识到合力的作用,则以上诸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
[1] 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 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 费孝通.论小城镇及其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4] 袁中金.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