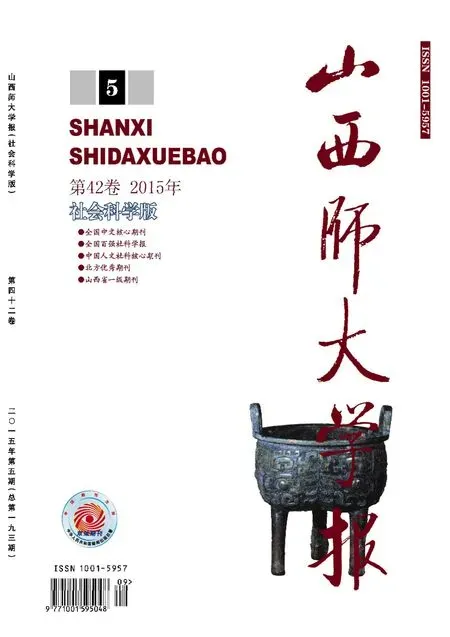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万国公报》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兴起
孙 海 军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万国公报》前身为《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创刊于上海,自301卷起更名为《万国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出至第750卷后曾一度停刊,1889年复刊后成为英美传教士在华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1907年底终刊。该报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时间跨度最长、最具影响的刊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已涌现出不少关于《万国公报》的研究成果。概言之,现有成果主要围绕着如下三方面展开:其一,研究《公报》在基督教传教史及宗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其二,研究《公报》在近代西学东渐进程中的角色及贡献;其三,研究《公报》对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现实政治运动所起之影响。但是,关于《公报》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即便提及也语焉不详,或许是有感于刘禾、冯骥才等人关于鲁迅国民性话语与西方传教士关系之论断,被人指认为陷入了西方后殖民主义的语言陷阱而心有余悸。但事实上,考察《公报》相关文章及其与梁启超等早期国民性话语实践者之间的关系,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存在。
一
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尽管19世纪中叶以来,传教士群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描述,甚至上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但从实际影响来看,此种观点对当时国人的影响十分有限,真正对中国近代国民性话语之兴起构成直接影响的,是传教士透过广学会的出版物,尤其是《万国公报》所传播的中国观。《公报》的发行及各种著述的结集出版,不仅使得在华传教士获得更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更借助于现代传播机制将他们对于现实中国的种种观感,传达给正在为救亡图存而孜孜以求的近代中国的先觉者们。因此分析一下以《公报》为纽带的广学会系统传教士的中国观及其对中国国民性的相关叙述,对于廓清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源起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万国公报》原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自编的刊物,广学会成立后,成为该会会刊,除去中间停刊的五年多,《公报》实际“总共出版的时间,长达十八年又九个月”[1]67,可谓广学会最具影响的出版物。正因为其长期性,在它周围聚集起一批较为稳定的作者队伍 ,因此,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将之看作广学会系统传教士中国观的集中展现。而《公报》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揭示又是跟其对中国文化教育及风俗习惯方面的批判分不开的。
首先,《公报》作者不约而同地以现代进化观念指责中国文化及教育制度之保守、停滞及其引发的排外倾向。李佳白(Gilbert Reid)撰文指出:“西人事事翻新,华人事事习旧。”[2]520另一篇题为《泥古变今论》的文章更是直接批判中国人“因循苟且,泥于古法而不知变通”,并且断言:“盖既有泥古之心,则出于其心必至害于其事。害于其事必至害于其政。无惑乎国家之时势,日邻于贫弱矣。”[2]203—204即是说,文章作者已经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泥古”思想导致了晚清以来国势的江河日下,因此必须痛下决心予以改革。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则试图寻找这种保守倾向形成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保守主义是传统教育中的崇古观念作祟的结果,“华友惟知重古而薄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缺乏“必改古人之错”、“必补古人之缺”、“必求古人所未知”[3]482的创新精神。中华帝国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近代遭遇西方世界异质文明时就很自然地表现为一种排外心理:“若士则自入学就傅以来,读圣贤书,行圣贤事,故每遇同道之中有习西学者,辄鄙薄非笑,以为是攻乎异端也,是崇奉西人而不知气节也。”[2]195杨格非(Griffith John)在谈到中国人之所以不接受外来宗教时,也有类似看法:“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做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其他中国哲人,则远远不如。”[4]175但是,中华帝国这样一种带有文化优越感的傲慢性排外,非但没有达到击退异质文明的预期,反而更加激发起西方传教士大力推广基督教育的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2]258实际上,这里已经流露出《公报》作者对中国国民性诸多方面的指责,尤其是因文化保守、排外所导致的国民性方面的崇古、傲慢与惰性,等等。
其次,《公报》作者还集中批判了晚清帝国存在的种种不合时宜的陋习,尤其是溺婴、殉节、裹足、纳妾等种种在他们看来几近野蛮的行径。因为上述陋习的受害者往往以女性居多,所以他们“备责华人待其妇女如罪犯”[3]486。在《公报》上,这种将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传统女性视为罪犯的观点并不鲜见,有人指责中国的闺房制度就是把女性“定罪监禁牢内”[3]486,从而使她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只能沦为繁衍后代的工具和男人的玩物。花之安(Ernst Faber)则从人道主义和男女平等的现代观念出发,严厉批评了溺女行为,指出“世间最重者性命,天下最惨者杀伤”,“而愚夫愚妇,不明斯义,竟有生女即溺杀之者,上既负天地好生之德,下并没父母慈爱之怀,害理忍心,殊堪浩叹!”[5]316当然,西方传教士最反感的还是裹足:“夫裹足之事,斨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使数千年来海内多少女子同受苦楚”。文章还进一步以现代视角指出这种陋习的审美误区,“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丑者不因乎裹足而不丑。”[2]192—193此外,传教士还批判了纳妾制度,认为这一制度不利于儒家一贯主张的“和”与“安”的传统精神,乃“卒使国亡家破”的隐患。
无论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保守排外,还是风俗习惯方面的陈旧陋习,集中到民族性格方面即为国民性弱点,亦即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可以说,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国民性的揭示,某种意义上是对上述文化教育及风俗习惯层面诸多批判的一种总结性发言,并且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性因果关系——风俗习惯方面的陋习固然是国民性所导致,而文化教育层面的保守和排外不仅导致了软弱、奴性、安于现状、懒惰等诸多国民性特质。反过来这些特质又制约着文化教育层面的创新。正是从这一关系出发,“人”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得以凸显。甲午战后,傅兰雅(John Fryer)敏锐意识到:“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并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它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倒在其次。”[5]458傅兰雅所谓的“道德或精神的复兴”固然带有基督教的宗教背景,但其从道德或精神入手,试图借此改造中国国民性进而挽救民族国家的做法,却与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内在逻辑若合符节。
其实,早在传教初期,《公报》作者就注重以基督教教义来对治中国国民性之弊端,有人撰文指出:“在昔欧洲诸国,当未闻道之先,其愚拙情形,亦如今日之中国”;“中国矿产之煤铁,实多于欧洲,特上之人愚而不明,狃于风水之邪说,坐令弃于地中,甘失富强”。可见,晚清帝国在传教士心目中,依然处于前现代的“愚拙”状态,主政者则“愚而不明”。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传教士基于“基督化即文明化”的宗教逻辑,开出的药方当然是奉行基督教,“今为中国计,惟有基督之道足以救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不仅能够去其迷信,大力发展生产,同时“凡有损之恶习,如吸烟、酗酒、赌博、奸淫、欺骗、窃盗等类,教规之禁例甚严”[2]116。即是说,上述种种基督教教规所禁之恶习恰恰是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积习,而这些在传教士看来无疑属于所谓的民族性缺陷。此外,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也从其对国民性之误导入手,指出中国国民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教育一手造成的,“学《诗》之失而为愚,学《书》之失而为诬,学《乐》之失而为奢,学《易》之失而为贼,学《礼》之失而为烦,学《春秋》之失而为乱。”[2]36此处所谓“愚”“诬”“奢”“贼”“烦”“乱”等传统教育的不良后果,与其说是对经典“六经”的非难,毋宁说是对现实中国国民性的指责。
二
此后,《公报》上谈及中国国民性的文字络绎不绝,也越来越具体。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撰文指出:“如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官兵平日怠惰,“对敌之时,贼退始皆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具报矣”;而“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者即有所见亦如无见”[2]165。还有人以土耳其之遭遇反观中国,指出“大约土与中官员均相似。怠惰骄矜,因循贪鄙,悉无忠君爱国之心。……二国中虽间有胜负之员,大概局量狭窄,贪受贿赂。”[2]186在此背景下,华人作者沈毓桂也意识到“中国之病,正在倨傲因循,苟且偷安,明知其故,而不能振作耳。”[2]297由此可知,在《公报》作者心目中,因循、自私、怯懦、欺骗、怠惰、缺乏爱国心、苟且偷安等所谓的民族劣根性已经成为晚清国人摆脱不掉的民族性标签。第501卷上一篇题为《推原贫富强弱论》的文章则较早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指出中国国民性的不足。文章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对狭小的国土上创造出比中国更强的国力,是因为英人尚简,华人尚奢:“英人冬不裘夏不葛,毡衣、布裳安之若素,即有富可敌国者,其服不过如此”;华人“夏则纱縠轻鲜,羽扇宫执,所费不赀;冬则重裘华服,炫耀人目”。不仅如此,在作者看来,中英国民性尚有疏懒与勤敏之别:“英人之为事,限以时刻,必躬必亲。即或有假手于人者,必亲自督率不敢一息苟安。而详慎周至,算无遗策,虽事之小,亦未尝忽焉。”相比之下,中国人“晓起则九点十点钟,犹且搔首伸欠不已,天时偶热,则畏暑不敢出也;稍寒,则又畏寒不敢出也,甘于误事,而不敢振作自奋,甚且事事假手于人。无论为官为商为绅为士,莫不相习成风,因循坐误。”[6]作者对英人尚简、华人尚奢,英人勤敏、华人疏懒的论断未必准确,但却标示着时人已注意从国民性之差异来分析国力之贫富强弱。换言之,在某些传教士那里,国家之强弱某种意义上已经被置换成国民性之优劣,这一置换无疑将复杂的现代化问题化约成单一的国民性问题,看似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实际上却埋下了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理论的诸多隐患。
作为《公报》的核心人物,林乐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论述更为集中,影响也更为深远,某种意义上可谓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兴起。他批判中国士人“食古不化”:“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也。”[2]160在论述鸦片之害时,还别出心裁地从中西国民性之异同入手,认为“东人好静不好动,故所嗜者,以静为缘,而收敛尚焉。……西人好动不好静,故所嗜者以动为主,而发扬尚焉。”在林氏看来,鸦片与酒恰好有“主乎静”与“主乎动”的差别,“是以东人性近于静,迷于鸦片者恒多,……西人性近于动,迷于酒者恒多”。不仅如此,林氏所指出的镇静无为、四大皆空的“佛教盛于东方”,而恻隐心动、四海一家的“耶稣教盛于西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5]496在《中美关系略论》中,林乐知再次阐明这一观点:“华人惟主于静,故如信佛教也,吸鸦片烟也。美人惟主于动,故有喜耽曲蘖之弊,……华人毫无自主之权,事事皆尊朝廷之命令,官司法度,其于安分守法讵不谓然。”[2]263林乐知对于中国人好静不好动的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五四”前后,杜亚泉、李大钊等人在东西文化论争中所持的观点,而梁启超、鲁迅等晚清人物对尚武精神的弘扬,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治中国人好静、柔弱之病症的一剂良药。甲午战后,林乐知在《险语对》中提出的“华人之积习”的八个方面影响则更为显著。林氏是在中日战争失利的背景下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在他看来,战争的失败并不在于“战具”方面,“非新枪大炮之不克致远也,非铁砚石台之不克攻坚而守隘也,且亦非将之寡兵之微,不克建威而锁萌也”。相反,“中国缺憾之处,不在于迹象,而在于灵明,不在于物品之楛良,而在于人材之消长”。中国人才“不能胜他国者,则以有形之规模矩度,可凭而实无凭,无象之血气心知,欲恃而实不足恃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林氏提出了中国国民性八个方面的积习:一曰“骄傲”。尊己轻人,对他国善政不屑一顾,以为戎狄而已,“中华不尚也”;二曰“愚蠢”。即不关心世界,安肯就学远人,徒潜心于诗文,“识见终于不广”;三曰“恇怯”。不知科学,惟尚迷信,久成怯懦之性,于人于物皆然;四曰“欺诳”。虚文应事,不知实事求是之道;祈天求福,妄听妄信而已;五曰“暴虐”。官府腐败,不问民间疾苦,重刑讯,草芥人命;六曰“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七曰“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八曰“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林氏指出这八大积习,“其祸延于国是,其病先中于人心”。为此,他总结道:“总之,心术即坏,如本实之先拔。是以招募军士,铸造枪炮,修筑台垒者皆犹饰枝叶而缀花蕊也。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2]301—304林乐知将战争的失利归结于“灵明”、“人材”、“人心”等主观因素,这一看法与前述傅兰雅对战争的反思如出一辙。可以说,傅兰雅、尤其是林乐知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认识及其内在逻辑,明显开启了清末民初国民性批判话语的内在理路。
三
从思想史发展进程来看,中西方之间相互认识的真正转折是从两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这一战争无疑加速了欧美列强对中国殖民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也加深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国民性的认知,中国形象的负面效应也随之逐渐上升。尽管如此,中国士大夫阶层仍只承认西方世界在军事、物质上的优势,搞起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与此相对,在文化层面上则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中体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体”“用”概念及其二者之关系,实则代表着当时国人对中西世界的认知:中国虽然输掉了实际的战争,甚至割地赔款,但中国的文化依旧是最优秀的,无需也不能变动。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中西方之间产生了基于现代文明观念的相互“误读”:“中国人把英国人当作野蛮人,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英国人也普遍把中国人当作半野蛮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文明的。”[7]760姑且不论这种中西之间的互相指责是否合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这种心态下,对中国精英阶层来说,国民性显然还没有作为一个困扰民族发展(现代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但甲午战争的败北、戊戌变法的流产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从根本上攻破了中国知识人的心理防线。甲午战后,严复的《原强》、《论世变之亟》等文章基于进化意义上对中西文化所进行的“比较”,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反响,某种意义上也从旁印证了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此后,在中西比较背景下对中国国民性的诘问便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
那么,作为近代国民性话语理论最初实践者的梁启超,是否受到以《公报》为媒介的传教士中国观的影响呢?回答是肯定的。其一,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与广学会系统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佳白等传教士过从甚密,尤其是在戊戌前后,两大阵营在变法问题上大致取相似见解。据李提摩太回忆,康有为曾对他说过:“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上同我们合作。”于是,逗留北京期间,李氏便带“李佳白、白礼仁等经常同维新派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的计划和办法”。[8]152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一度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其二,广学会出版的书刊包括《万国公报》亦是维新阵营重要的思想读物。早在1883年,康有为就“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9]11。谭嗣同在一份通信中亦指出:“除购读译出诸西书外,宜广阅各种新闻纸,如《申报》《沪报》《汉报》《万国公报》之属。”[10]166梁启超则在《西学书目表》中对《万国公报》作了重点介绍:“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创《万国公报》,后因事中止,至乙丑后复开至今,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11]14应该说,梁启超对以《万国公报》为主要媒介的西方传教士的中国观并不陌生,并且因为在中国现代化诸问题上两大群体表象上的一致性,很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梁氏在国民性问题上对传教士相关观点的肯认。其三,在国民性批判具体形态方面,梁启超与《公报》作者具有诸多相似性甚至同一性。以梁氏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为例,文中列举出旧国民性六大弊端,即“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12]415—419梁氏所谓的“六大弊端”在上述林乐知等人对中国国民性的相关描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抚今追昔,大谈国民性问题,应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之所以遭受挫折的一种深刻反思。这种反思无疑会受到其时日本国民性批判思潮的影响,但是传教士透过其出版物所传达的中国观、尤其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认知,无疑亦是梁氏国民性话语理论的一种潜在资源。正如周宁在谈到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思想资源时所说:“鲁迅、陈独秀、梁启超代表的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思想来源也不仅限于明恩溥或黑格尔。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理论,已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一个话语系统,有其自身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评判体系、意象和词汇以及修辞传统。中国现代国民性批判是在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影响下进行的。”[13]在“由多种文本共同构成”的“西方的中国国民性话语传统”中,以《公报》为主要载体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论述,应是近代中国国民性话语理论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1]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M].上海:中西书局,2012.
[3] 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2004.
[5]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6] 佚名.推原贫富强弱论[J].万国公报,1878,(501).
[7]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9]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0]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 梁启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 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J].文艺理论与批判,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