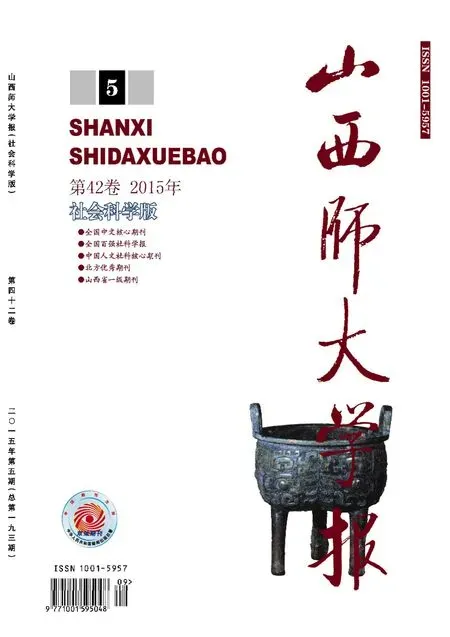70年来欧洲国家关于纳粹德国起源问题研究回顾
卢晓娜,柴 彬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730020)
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依照“白色方案”,从陆、海、空三面入侵波兰。英、法先后发出通牒,限德国48小时内撤兵。9月3日,在最后的警告无效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历史性时刻,对该问题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若不认识战争,便无法理解20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1]“二战”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在欧洲战场,纳粹德国难辞其咎。然而,德国本已饱尝“一战”苦果,为何又在短短20年后再次启动战车,疯狂地驶向深渊?纳粹德国究竟如何产生,其根源何在?早在大战刚刚开始时,欧洲历史学家便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亦不同程度参与其中,从各自学科出发对纳粹起源进行解释。
一、“特殊路径”及民族特质的必然结果
早在大战刚刚爆发之时,欧洲各国学者便就纳粹德国起源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德国历史是否存在延续性;换言之,纳粹主义是否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一部分学者从社会政治结构及民族性格特质角度分析,认为德国历史发展遵循着与欧洲他国不同的“特殊路径”,纳粹主义是其必然产物;日耳曼人尚武残忍,其民族性格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战争因子。另一派学者否认该提法,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发展的断层,是“一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导致了纳粹主义滋生,希特勒个人因素则将之推向顶峰。
(一)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
“特殊路径”理论伴随着19世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而萌芽。最初,它为帝国内部保守政客用以宣传政府统治的“中庸”之道。这些政客认为:“中庸”统治具有一大独特性,既规避了俄罗斯帝国的沙皇专制,也绕开了行政效率低下的英、法民主制;能在社会变革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不必受制于下层施压。[2]“中庸”统治亦成为民族信心的来源——“德意志是超然独立的中欧国家”,这种思想始终存在于保守学者、政客的观念中,直到1945年。 “二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深重苦难,纳粹德国作为确定无疑的罪魁祸首,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其历史发展进程。“特殊路径”理论作为一种现代学说兴起,并逐渐赢得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认可。这派学者从政治传统、社会变迁等角度对德国历史进行分析,认为德国长期以来的发展确实遵循着与欧洲他国相异的模式,以致其无可规避地滑向纳粹主义。
1.长期以来的政治传统。从德国政治传统中探究其战争因子,这种研究范式最早产生于20年代的法国。当时“一战”刚刚结束,协约国与德国战责之争高潮迭起。为了制胜,法国新闻界“试图从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及俾斯麦的霸权追求中推导出德国对世界大战爆发的责任”[3]。“战责推导”论一经发表便引发聚讼。“二战”期间及战后,这种研究理念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2003年,德国历史学家汉斯-乌里奇·韦勒借鉴韦伯“魅力型统治”概念,提出:俾斯麦与希特勒之间存在鲜明的政治延续;后者继承了前者的魅力统治,并将之推向顶峰,成为纳粹德国运转的动力。
此外,亦有学者将研究时限继续扩展,甚至上溯至马丁·路德宗教改革。1941年,美国学者威廉·蒙哥马利·麦戈文盖尔在《从路德到希特勒:纳粹法西斯的政治哲学史》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宗教改革便是纳粹运动的前奏,认为,唯有政治多元才能避免极权,而宗教改革通过强化国家削弱教会,打破了二元结构。[4]因此他痛斥路德是希特勒极权政治的先驱。这一观点得到了德国左翼历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的支持。1949年,西德战后第一届历史学家会议在慕尼黑召开。费舍尔在会上向路德传统发难,批判其牺牲个人自由,宣扬国家至上,从而为纳粹掌权铺平了道路。认为纳粹主义早在1914年前便已萌生,它绝非是《凡尔赛条约》盘剥所致,而是久已存在的权力精英野心的产物。
将纳粹起源上溯至宗教改革,这并非历史学家们的空穴来风。1510—1525年,路德先后提出了“两个国家”与“三种秩序”理论*1510-1520年,路德提出了“两个国家”理论:上帝建立了精神和世俗两个世界。前者即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国;后者与之完全不同,充满罪恶,必须要由世俗统治者用“神授之剑”来维持秩序。由于统治者的权力拜神所赐,故即使其法令悖逆《圣经》,民众亦不能暴力反抗,只能拒绝服从。1523—1525年,路德又提出了“三种秩序”理论,认为人间有三种秩序不可侵犯,即政府、家庭、教会。政府必须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中;家庭必须对政府服从。教会分为不可见的与可见的教会。前者存在于天国之中和信徒心灵之中;后者是世俗组织,归世俗政府管理。这三种秩序也是上帝建立的,应当绝对服从。,将世界划分为精神与世俗两个层面:前者由上帝直接掌管;后者的秩序由上帝安排,世俗贵族凭借“神授之剑”来统帅,教徒应臣服于此种统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对世俗统治者而言,这为架空教会、树立自身权威提供了依据与契机。诚如卡尔海因茨·布莱希克所言:宗教改革重建了国家组织,增进了国家权威,赋予国家在行政上管辖教会的权力。[5]然而在另一方面,该理论的核心“服从世俗权威”却过分夸大了国家权力,剥夺了民众自由。历史学家们亦指出,路德将改革与地方政府意识相协调的主张及其对1525年农民暴动的消极态度*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爆发,路德站在反对立场。他认为:上帝福音的本质是和平,农民战争违逆了上帝的意志。因此,他将反抗的农民斥之为“魔鬼”,并宣称:“我一直站在反对叛乱的人这一边,我不管他们的理由是多么不公正。我一直反对造反者,我不管他们的理由多么正义。因为,没有一种动乱会不伤及无辜,使他们流血。”更说明其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和拥戴者。
2.失衡的社会变迁。1961年—1979年,费舍尔立足于大量档案、文献,先后出版《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的战争目标》、《幻想的战争:1911—1914年的德国政治》及《从第二帝国到第三帝国:德国历史延续性原理,1871—1945》。在这三部专著中,费舍尔系统分析了德国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责进行了勘定。首先,第二帝国统治者的思维中充斥着与纳粹无异的政治逻辑,即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观念;霍尔维格是1914年的希特勒。其次,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在政策制定方面存在鲜明联系;两场世界大战都是德国为满足扩张欲望而挑起的。此外最重要的一点是,费舍尔突破了之前单纯从政治传统中寻求纳粹德国产生原因的研究框架,将德国社会变迁与领导人政治逻辑相联系,提出了 “国内因素主导论”。他认为,德国内部社会变迁失衡是其走向战争、滋生纳粹主义的深层原因。19世纪德国在经济及工业领域均取得飞跃,但政治上却仍裹足不前。政坛为保守精英掌控;他们排斥社会民主党势力,同时希望牺牲英、法、俄等国作为德国霸主之路的基石。正是这些保守精英的观念推动了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他们不仅要对“一战”负责,亦应对魏玛共和国覆灭、纳粹得势负责。*这些观点被称为“费舍尔学说”,1961年一经发表便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激烈论战,史称“费舍尔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即德国是否应对“一战”负责;德国走向战争的因素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围绕后一个问题,学界分为两派,即费舍尔主导的“国内因素主导论”及西德历史学家格哈特·乔治·伯恩哈德·里特尔主导的“国际因素主导论”。[7][8][9]费舍尔的论述在学界乃至政界引起轰动,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德国的对外政策。同时,费舍尔发现的大量文献、档案显示,对波兰、俄国进行种族清洗以争取“生存空间”的意图早在第二帝国时代便已有之。这更令历史学家们确信,与之类似的纳粹目标并非希特勒首创,而是反映了德国领导人久已存在的扩张野心。
费舍尔的观点赢得了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的赞同,围绕他形成了“国内政治主导论”派别。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莫姆森及其双胞胎兄弟沃尔夫冈·贾斯汀·莫姆森便是其中代表。他们认为,纳粹德国的产生及德国20世纪两场大战灾难的根源都在于其历史发展的“特殊路径”。关于这一点,他们的经典论述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在经济方面已走向现代化,但军政与社会要权却仍为容克贵族掌握;传统与现代、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激烈对抗。为转移民众注意力缓解他们的民主呼声,统治者发动了“一战”。大战后,十一月革命并未彻底清除旧贵族势力,这导致德国无可规避地走向了第三帝国[10][11][12]。
“国内政治主导论”的产生与战后西德历史学学科发展相关,首先是批判史学的兴起。在目睹纳粹危害后,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反思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传统,认为其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色彩及政治倾向在无形中助长了纳粹主义。因此,他们主张将德国思想与西方他国思想联系起来。其次是比勒费尔德学派的开创。该学派由韦勒、约根·科特卡、莱因哈特·勒克等西德历史学家建立,强调应改变过去以政治史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从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角度,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去考察历史。立足于这样的思想,韦勒结合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在1970年代提出了“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理论,对德国近代历史的“特殊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
2003年,韦勒出版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两个德国:1914—1949》,是为其《德国社会史》系列的第四部力作。在这本书中,韦勒发展了自己的观点,提出“社会政治结构的现代化延迟”,从“革命”与“社会阶层”两方面对纳粹德国的起源作了进一步解释。韦勒认为:首先,德国是在中欧农业革命衰微、工业革命起步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自下而上的军事革命建立起来的。这种立国方式在欧洲绝无仅有。因此,德国经济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在社会政治领域却保持着凝滞。这导致德国人的价值观念未完全开化,仍充斥着封建主义、贵族主义等与民主对立的内容。其次,经济大发展、私有制与国家主导制之间的矛盾加剧了阶层分化。在这种形势下,纳粹主义作为一种饮鸩止渴式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并获得民众广泛认可。[11]纳粹德国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特殊路径”理论作为研究德国近代历史的一大经典提法,关于其是否成立的争论从未中断。加之其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责问题密切相关,“特殊路径”理论受到了持不同政见的历史学家的强烈批判。
(二)德国人的民族特质
1941年,英国外交家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特男爵出版了《黑暗记录:德意志的过去与未来》,率先从德国民族性格中对纳粹主义起源进行了探究。范西塔特认为,日耳曼人残忍好斗,极富侵略性;纳粹主义只是这一民族特质的新近表现。同年,英国历史学家兼政府职员罗翰·巴特勒出版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1783—1933》,从意识形态发展角度分析,是德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了纳粹主义萌生[13]。大战结束后,关于纳粹德国起源的争论升级,其焦点有二:纳粹主义是否根植于德国民族性格?德国普通民众是否应为纳粹罪行负责?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的多为英国历史学家。路易斯·伯恩斯坦·纳米尔、艾伦·约翰·帕瓦西尔·泰勒便是其中代表。作为波兰裔犹太人,纳米尔对大屠杀有深刻感受,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观念带有反德色彩。在纳米尔看来,德国人是欧洲乃至世界文明的致命威胁。1945年,纳米尔的学生泰勒出版成名作《德国历史进程:1815年以来德国历史发展研究》,认为德国人从未平等地看待过斯拉夫人与波兰人,向东进攻、征服他们,这是全体德国人的梦想。德国人甚至为此将自由出卖给了帝国。希特勒与德国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希特勒依靠民众去杀伐侵略,而德国民众则依靠希特勒去奴役邻邦。[14]1961年4月,泰勒出版纪实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更加犀利地指出,希特勒通过撕毁《凡尔赛和约》及进攻波兰取得了德国民众的支持。因此,德国民众并非是无辜受害者,《纽伦堡宣言》忽略了他们的责任。[15]泰勒的父母均是左翼和平主义者,并为反对“一战”而将他送进贵格会学校。这种家庭环境与教育背景对泰勒观点形成影响颇深,他亦带有鲜明的反德倾向。大战爆发前的1936—1939年,泰勒多次与老师纳米尔在集会上批判绥靖政策及慕尼黑协定;呼吁英、苏结盟以应付纳粹德国的威胁。“二战”期间,泰勒效命于英国地方军,并作为政治战执行机构中欧问题专家发表广播讲话,对德国嬉笑怒骂。战后,泰勒对美国筹建并援助西德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会埋下“第四帝国”的隐患,有朝一日会酿成又一场世界大战。
以民族性格为切入点考察战争因素并非仅针对德国,美军在与日作战中亦采取了此法。这与人类学及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相关。1944年6月,正是美、日在太平洋上鏖战之时。虽然塞班岛登陆预告了日军覆灭,但美军在以往战斗中已然认识到敌人的可怕。因此,为了解日军今后动向,彻底摧毁顽抗力量,制定战后对日政策,美国战争情报局委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了“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原因”[16]23,她认为,儿童教育与成人教养的脱节致使日本人具有像菊花与刀剑般极端矛盾的民族性格,这催生了日本社会与西方“罪感文化”迥异的“耻感文化”。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便是这种 “耻感文化”的极端表现,意在赢得国际尊重。[16]275
二、国际形势及希特勒个人因素所致的意外悲剧
从“特殊路径”、民族性格角度探寻纳粹德国起源是以德国历史具有延续性为逻辑前提的。对此,一些历史学家并不认同。
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德国保守历史学家。赞同德国历史具有延续性便等于认为德国具有天然的战争倾向,这意味着德国将要背负两场世界大战罪魁的恶名。在大多数德国人看来,“一战”是由环伺敌对力量强加于德国的战争,“二战”罪责虽可勉强接受,但很大程度上仍是《凡尔赛和约》对德过分盘剥所致。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德国保守历史学家对“特殊路径”论大加挞伐,他们多从国际形势及希特勒个人因素来解释纳粹德国的起源。
1946年,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悲惨德国:反映与回忆》一书中提出了一组颇为矛盾的观点:一方面,迈内克认为:纳粹得势的原因在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存续,在于德国当时工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中产阶级与之极不协调的孱弱状态。然而,他同时又强调,纳粹德国的政策是由一系列国内国际意外事件促成的,与之前历史发展无关,不能归结为“特殊路径”的必然结果。[17]迈内克的观点与其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政见相关。在他看来,犹太人的凄惨遭际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拥护德国东进政策,对波兰边界计划大为称颂,[10]112—113甚至数次公开表态支持纳粹统治。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他致信齐格弗里德·奥古斯特·卡勒时兴奋地写道:“你一定也会因这一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18]
对“特殊路径”提法进行系统反驳的是西德历史学家格哈特·乔治·伯恩哈德·里特尔。1964年,里特尔出版《剑与权杖:德国军国主义问题》第三卷《政治家的悲剧:战争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纳粹掌权是德国历史的中断,而绝非路德极权主义或俾斯麦军国主义发展至今的产物。德国民众及德国本身亦是受害者。里特尔对纳粹德国起源作出了与其他学者完全不同的解释,提出了“国际因素主导论”的观点,将纳粹主义产生归结为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普遍存在的极权倾向。里特尔认为,“一战”大大加剧了这一极权倾向。“一战”使得西方世界的道德整体滑坡,继而导致基督教权威丧失、文明为野蛮所蚕食,最终恶果即纳粹上台[19]。里特尔的观点与其政见及宗教思想相关。他信奉路德宗及大德意志主义,认为国家同有机体一样,需要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与领土扩张,以谋求生存发展;同时他还主张君主政体,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引领德国取得欧洲霸权。
三、余论
70年来的纳粹德国起源之争基本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德国历史进程是否具有延续性,以致于其无可规避地走向第三帝国。持肯定论的学者多从政治传统、社会变迁及民族性格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首先,德国历史发展遵循着“特殊路径”。这表现在两方面,即路德与俾斯麦以来的政治传统与19世纪下半叶德国残缺的现代化。其次,民族主义深藏于德国民众的内心,他们具有天然的侵略倾向。持反对论的学者多受其保守政见影响,他们认为:纳粹德国是德国历史发展的断层,并不源于之前的积累。首先,纳粹德国起源与“一战”后德国所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协约国过分盘剥所致。其次,希特勒个人因素亦起到很大作用。
20世纪是极端的年代,和平间隙仍酝酿着大战危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整个时代,就是在世界大战中生活、思想。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熄,但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1]“二战”硝烟已永远消散在历史的风中,但战争的印记却亦永远留存下来,是每一位亲历者不能忘却的伤痛。不论是罪魁国家还是被侵略国,都是最终的受害国。德国历史是否存在延续性,纳粹德国究竟如何起源,学界对此问题仍无公论。然而这并非研究的意义所在。反观当下,虽整体和平,但日本作为“二战”另一责任国,其内部右翼势力及军国主义思想均有抬头之势,这为亚太地区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埋下隐患。对纳粹德国起源问题进行回顾便要在此种时事背景下警示人们远离战争机制,不致再次迈入战争,自我毁灭。
[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M].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 Hinde John ,“Sonderweg”, Dieter Buse, Juergen Doerr. ed, Morden German An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People and Culture,1871—1990.Vol.2,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1998.
[3] 孙立新.德国历史学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责任问题的争论[J].史学史研究,2008,(4).
[4] William Montogomery McGovern. From Luther to Hitler:The History of Fac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1941.
[5] Karlheinz Blaschlke.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Terriorial State”,James D. Tracy.ed. Luther and the Morden State in German. AnnaArbor,Michigan: Edward Brothers, 1896.
[6]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utschen Staaten .München:?C.H. Beck Verlag,2003.
[7] Fritz Fischer. German's Aim in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 W.W. Norton&Company,1967.
[8] Frti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1914,New York: W.W.Norton&Company,1975.
[9] Frtiz Fischer. From Kaiserreich to the Third Reich: Elements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1871—1945,London :Allen & Unwin .1986.
[10] Hans-Ulrich Wehler.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7.
[11] Hans-Ulrich Wehler.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unich:1995.
[12] Wolfgang Justin Mommsen. Imperial German 1867—1918.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ondon: Arnold,1995.
[13] Rohan D'Olier Butler . The Roo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783—1933, New York: AMS Press, 1985.
[14] AJ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Since 1815.Routledge, 2001.
[15] AJ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New York: Fawcett,1969.
[16]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刘锋译.萨苏评注.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
[17] Friedrich Meinecke. Th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s and Recollec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1963.
[18] Sebastian Conrad.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19] Gerhard Ritter.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litarism in Germany. Vol.III. The Tragedy of Statesmanship-Bethmann Hollweg as War Chancellor(1914—1917), 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