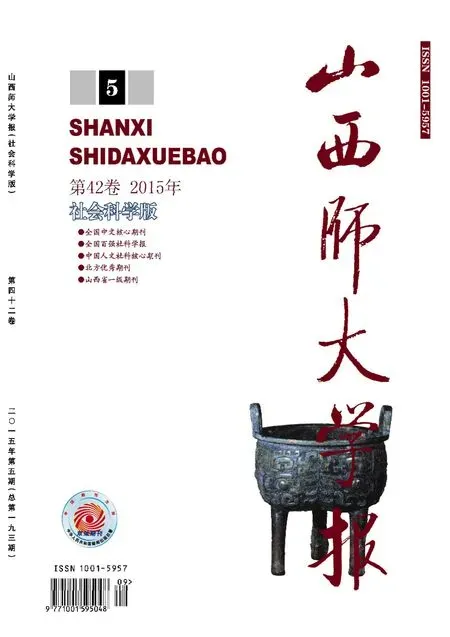阎宗临的中西交往史研究再探
张 炜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阎宗临(1904—1978年),山西五台人,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于1936年在伏利堡大学获得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赴难,先后在广西大学、无锡国专、昭平中学、桂林师院等校任教。抗战胜利后,先生于1946年来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并在1948年至1950年兼任历史系主任及历史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先生于1950年回山西大学工作,直至1978年逝世。
阎宗临先生在大学任教40余年,主要讲授世界古代史及中世纪史,但中西交往史始终是他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先生在瑞士求学期间,便主攻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其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法文本)曾获得当时学者的高度评价,并于1937年在瑞士出版,引起当时欧洲汉学界的广泛关注。回国任教后,先生继续在此领域钻研进取,先后发表了《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等一系列重要文章。而先生写于1962年的《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文则获得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学者普遍认为阎先生的治学以中西交往史的成就最大。[1]齐世荣序1也正如阎守诚教授指出的,先生在中西交往史这一研究领域中,是有筚路蓝缕、辛勤开创之功的。[2]10
目前学术界对阎宗临学术成就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对欧洲文化史及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著述的研讨上,而对他有关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虽已有较为全面的梳理,但尚缺乏对其研究特点的深入剖析。笔者不揣浅陋,拟以1949年为界,试对前后两个时期阎先生在中西交往史研究上的特点及其启示予以表彰与总结。
一、 文化交流是中西交往的重要推动力
1949年以前,阎宗临先生治中西交往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从宗教文化的角度,特别是以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为切入点,探寻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史事及对各自历史演进的影响。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阎宗临先生主要从文化史观出发探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尤其强调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别的文化来补充。在文化起源上,虽有播化论与创化论的争辩,但他则同意发明与传播各半的主张。[1]1也就是说,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他进而指出,任何文明缺少了宗教因素,也不会得以持续。[1]305因此,他将宗教文化作为其从事中西交往史的着眼点和归宿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及《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等文中。杜赫德(Jean Bapt du Halde,1674—1743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泰利埃的秘书,编辑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并撰写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志》。《中华帝国志》被西方学者誉为“18世纪最全面论述中国的史料”,该书与《耶稣会士书简集》和《中国丛刊》一道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的奠基之作。尽管学者们对传教士是否可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仍有争议,但这丝毫不会减弱阎先生对杜赫德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阎著并没有就事论事,局限于杜赫德本人及其著作上,而是通过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层层剖析,阐明了这个选题所涉及的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情况及其对法国自身的影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逻辑清晰、富于动态的文化交流图景。
在论述传教士西来的情况时,他以宏阔的笔调勾勒了耶稣会士到来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以及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阎先生指出,新儒学(阎著指宋明理学)的蜕化,是明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文人们受辱于明的后继者满洲人的统治,于是他们抛弃了这种思潮而趋向于积极的研究。[1]282阎著将此现象归为三个方面:首先,王阳明学派失去了威望;随之,人们开始着手于本质哲学的研究,通过经验验证自己研究的对象,并特别提及徐霞客和宋应星;最后是佛教的改革,改革者强调的是实践的理性。[1]282—283阎著由此向我们展现出16世纪末中国知识界的状态:新儒学再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权威,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状况而不断地寻求积极的知识。这些都意在说明,中国知识界本身的变化是促成耶稣会士们取得成绩的一个因素。[1]283此外,耶稣会士的成就还得益于与康熙皇帝建立起一种和谐与默契的相互关系。[1]291阎著指出,康熙皇帝具有博大精神和智慧,谨守父道,[1]295—296“对天主教和对其他宗教一样,总是表现出一种父亲般的亲情”。[1]293所以,康熙重视耶稣会士。他们的关系首先带有知识的特点,二者并保持着极好的宗教关系。[1]298,300这些关系的第一个积极成果是基督教的发展。[1]302第二个结果是,不少传教士由于为帝国效力而被提拔为大臣。[1]303第三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国。[1]304清朝在典籍研究中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都至少间接地受到西方的研究方法即分析法的影响。[1]319这说明耶稣会士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对于清廷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文明间冲突而常常对此种文化交流采取的消极态度,阎先生批评道:“它没有看到文化的孤立与其繁荣是背道而驰的。滚滚东去的大江是任何人力难以阻挡的,即使筑起了堤坝,所造成的灾难会更不可收拾。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文明就好比这样的大江。”[1]304这不光肯定了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其实也是从文化角度对清朝为何走向衰落的一种解释。
阎先生通过缜密的层层论证,将传教士来华与中国社会思潮的转变、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中国思想对法国文化的有力冲击等要素串联起来,使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连成一个有机整体,呈现出一幅中法文化交流互动的画卷,使该项研究早已跳出了对一部书的评判。正如阎先生的恩师岱梧教授所指明的,他所述及的这一交流过程其实称得上是一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中法知识分子的合作史”。[1]370
阎宗临先生从文化交流入手对中西交往史进行研究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受到法国汉学界的影响。事实上,法国的汉学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关注中法文化交流的研究热潮,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著,作为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兼具天主教文化背景的学者,阎先生在瑞士求学期间肯定也对法语学术界的这一动向有所感知。因此,他的相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是对这一学术潮流的接续。又由于阎先生在语言方面的优势非常显著(精通中、法、英、拉丁等多种语言文字),对外国学者容易忽视、中国学者难以见到或读懂的资料,因而能发前人未发,从这点上说又是对上述潮流的进一步开拓和创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研究思路与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全球史”研究在意蕴上颇有相合之处。譬如“新全球史”代表人物杰里·本特利曾强调指出,只有在人类长期的跨文化互动的历史中,才有可能理解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另外,阎宗临先生的博士论文围绕杜赫德《中华帝国志》的写作及其被接受的历史而展开,或于无意中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于欧美学术界、并被冠之以“新文化史”研究的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相投。
二、唯物史观是解读中西交往史的钥匙
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历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等等。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阎宗临的研究领域与治史方法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于是,在研究领域上,他转入了“西北史地”的研究,*阎守诚教授认为,由于阎宗临先生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因此他所说的“西北史地”研究,自然是指广义的西域。阎守诚:《阎宗临传》,三晋出版社,2014年,第258页。主要将目光聚焦于中亚地区。阎先生认为,中亚地区系亚欧大陆的中心,是古代游牧民族集聚与转移的地带,也是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在世界古代史上占有极重要的位置。[3]307由于中亚史研究所涉内容大都脱不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问题,所以,他关注的很多问题依然未离中西交往史的研究范畴。此外,他还对新航路开辟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研究方法上,阎先生经历了从文化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这一时期,阎先生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如此,阎先生也没有完全放弃原有的文化史观。因此,其著述呈现出以唯物史观为主、兼具多重视野的特色。
首先,阎先生十分重视中西交往史上的经济因素。关于丝路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当拜占庭经济繁荣的时候,自中国与印度输入的奢侈品,如丝绸、香料、宝石等,常受到波斯的控制,这给拜占庭带来很多困难。查士丁尼常思摆脱这种处境。但是,那时的海上交通仍受波斯主导,拜占庭海上发展的意图无法实现。因此,拜占庭由黑海向北发展,占领刻赤,与匈奴人相联系,由此至里海,复向东行,避开波斯,至康居地带,经葱岭,入中国,这条道路便是有名的丝路。[3]300他在分析拜占庭与波斯及突厥的二十年战争(公元571—590年)时,引述《魏书》与《册府元龟》的资料指出,因丝业的经营,突厥与波斯关系恶化。中国丝绢的输出,波斯为主要主顾,居间操纵价格,谋取厚利。大秦国“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3]261阎先生还从《册府元龟》中摘录了公元5世纪至8世纪波斯来华使节的名录29条,并从记述波斯知识异常丰富的《本草纲目》中摘录了波斯物产及其输入物品32种,以说明亚洲古代诸国的经济关系至为密切。[3]267—269同样,在论述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时,他通过对《本草纲目》、《酉阳杂俎》、《南方草木状》等历代史籍与笔记的分析,指出其中记述的物品有产自大秦者,有商人加工或贩运者,都说明了双方物资交流与往来关系的密切。[3]305
在此基础上,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阎先生在论述新航路的发现时就指出,新航路使中西交往开创了新局面,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激起了很大变化。他强调,地中海的经济中心地位已经移至大西洋了,“过去繁荣的威尼斯与马赛,现在变为凋零的城市。西班牙从墨西哥与秘鲁得到许多金子,转输至各地,促成工商业迅速的发达,形成许多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推翻那些贵族,激起一种社会革命。在知识方面,新人、新地、新动植物的出现,扩大知识领域,发生好奇、怀疑、分析、比较等精神与方式,促成科学的进步,而旧日的认识、伦理、偏见,渐次予以淘汰,要人重新来考虑一切。”[1]24他将上述内容有机融入到了其在20世纪60年代初完成的《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文中,表明他对人类不同地区相互交往的本质及影响又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其次,他重点从民族迁徙的角度,结合阶级斗争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观点,解读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问题。在发表于1962年的文章《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文中阎先生指出,西罗马的灭亡,结束了古典奴隶制度,是世界古代史上的大事。但是,无论吉本还是蒙森,都忽视了奴隶起义的力量,低估了蛮族入侵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忽视了匈奴西迁的重大事实。“实际上匈奴西迁是蛮族大迁移的主要推动力量,而匈奴向西几次的移动,却又与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分不开。”[3]272他还借助我国古代典籍资料指出,汉朝对匈奴的打击主要有两次,一次在西汉宣帝时,另一次在东汉光武帝时,这两次打击,使匈奴不得不向西迁移。另外,通过《魏书》等中国史籍和西方史实,阎先生对匈奴西迁的具体路线进行了考察。由于奄蔡人是匈奴西迁过程中的关键民族,因此,阎著重点对“奄蔡”在不同朝代名称的变化和移动情况进行了考辩,明确了匈奴西迁是由巴尔喀什湖进入哈萨克草原,再向西越过顿河,经乌克兰草原进入匈牙利草原的路线。[3]276—279匈奴不断地向西移动,促进了蛮族的大迁移。而当西罗马帝国快灭亡的时候,阶级斗争变得更为剧烈。奴隶们视蛮族为解放者。所以阎著认为,蛮族入侵加剧了西罗马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加速了奴隶制度的崩溃。[3]282—283
再次,他在研究宗教文化交流问题时加入了阶级分析和殖民主义的批判视角。阎先生对景教在中国被禁的探讨中指出,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受赵归贞影响,禁止外来宗教的传播。继后,唐宣宗虽有弛禁的意图,可是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爆发黄巢起义,予外来剥削者以有力的打击,此后景教便绝灭了。[3]305在此,阎先生将西来景教徒归入了“外来剥削者”之列,但他在对法显《佛国记》所做笺注中指出,由于《摩奴法典》确定四个瓦尔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后,规定不同种姓者不得通婚,如果违犯这种规定而生的子女,即为“最下的贱民”,贱民必须住在村外。他将此种现象诠释为阶级压迫十分残酷的表现,进而将宗教视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他说:“统治者建立寺庙,给予(寺庙)丰富的物资,寺庙经济得到有力的发展。通过这些寺庙,奴隶主巩固了他们的政权。”[1]237在《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文中,他特别介绍了法国派遣耶稣会士及引发的“礼俗问题”,过去对该问题的认识,阎先生只限于传教策略的纷争,认为这一问题“直接为公教(即天主教——引者注)流行之不幸,间接便阻碍西方文化之输入”。[1]120而在这篇文章里,阎先生指出:“‘礼俗问题’是初期殖民主义者侵略的组成部分,它企图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奴役中国的精神,这是中国绝对不能容忍的”。[4]34对部分传教士来华活动的政治背景和目的有所批判和揭露。
应该指出的是,阎先生在阐述很多问题时,虽积极运用唯物史观的视角和观点,但依然沿用了文化史观重视宗教文化交流的视角方法。在探讨波斯与中国的关系时,他以极大篇幅论述了祆教和摩尼教在中国和中亚的传播问题,考证了祆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唐室管理祆教的方式、摩尼教对于回鹘政治与经济所起重大作用等问题。[3]263—266同样,在论述中国与拜占庭的关系时,也对景教传入中国的情形予以较多关注。[3]303—304又如,在谈到传教士来华问题时,当时普遍认为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爪牙,阎著却仍然据实肯定了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贡献。在介绍利玛窦来华传播科学知识方面,他认为这使士大夫感到中国文化虽发达,但科学技术却是落后的。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传教士介绍的‘西学’起了一定有益的作用,扩大了当时知识界的视野”。[4]22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49年后,阎宗临先生治中西交往史的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就研究领域来说,阎先生将目光转向了中亚,应该说这也与20世纪法国汉学研究的传统相符合,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著有《高地亚洲》、《交广印度两道考》、《吐火罗语考》,闵宣化著有《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谢阁兰著有《中国西部考古记》等。就研究方式而言,唯物史观主导下的阐释占据了支配地位。如果单从学术研究本身来看,我们认为,阎著对唯物史观的运用确实扩大了其原先的研究视野,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更加深刻,以经济视角补充了原有宗教文化视角的不足。当然,其中也牵涉到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诚然,学术与政治不可能绝对分离,但问题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远远超过正常范围,因此才有不少论述难脱牵强之感。从资料运用方面,这一时期的阎著主要依赖我国传统典籍,对外文资料的利用极少,正如阎先生本人所言:“只是所见有限,功力自然不足,这是可以预见的。”[3]322
阎先生后期的论文基本上发表于1959年、1962年和1963年这几个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年份,而其余时间则基本沉寂。即便身处在这种环境中,他也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因此,与同时代不少同类著述相比,阎著已经称得上是史料扎实、论证谨严、观点明确的难得之作了。而阎先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表或完成的《〈身见录〉校注》(为国内首篇《身见录》的完整校注本,重新刊载于《山西师范学院》1959年2月号)、《〈北使记〉笺注》和《〈西使记〉笺注》(发表于《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以及完成于1965年的未刊稿《〈佛国记〉笺注》等,则是其中西交往史治学功力的集中体现。*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阎先生为上述四种史籍做笺注所参考的中外文资料达七十余种,涉及法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梵语等多种外语文字。又因上述重要史籍的作者均为古代晋籍人士,所以为这些作品做笺注也体现了阎先生对家乡的深情厚谊。
三、结语
饶宗颐先生对阎宗临先生的中西交往史研究做了如下评价:“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1]饶宗颐序1齐世荣先生也讲道:“阎先生关于中西交往史,特别是明清时代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属于第一流水平。”[1]序1不难看出,如将阎先生前后两个阶段的研究进行比较,前一阶段的成果学术界更多的是褒扬与认可。阎宗临先生在博综中西史料的基础上,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的文化互动画面,形成了将文化交流视为历史演进重要推动力的论述体系,树起了研究中西交往史的一种文化范式。这项研究不仅在方法上值得后学继承与发扬,而且他所述及的很多资料,特别是根据梵蒂冈等地的重要西文档案译介而来的第一手材料,对当前的中西交往史研究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从阎著的论述中,我们也可得出这样的启示,即只有从交互作用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的中国国家形象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等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不仅与中国自身的因素有关,而且也与别国的社会环境及需要密切相关。
学术界对其第二阶段研究的认可度则相对较低,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当前,中亚地区对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愈发凸显。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实施,中亚必将在欧亚大陆的经济战略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而物流也被视为其中的核心因素。不得不说,阎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在相对狭小的学术空间中的转向,虽属无奈之举,但也极具个人学术研究的“战略眼光”,因为他早已注意到了中亚在古代欧亚大陆格局中的突出地位,而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中亚古代及中世纪史,对于深入理解当今诸种现实问题尤其具有启发性。时至今日,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界在中亚史领域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因此,需对阎先生第二阶段研究的意义予以新的审视。阎宗临先生前后两阶段各有侧重的中西交往史研究,恰好提醒我们在探讨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时,既要重视宗教、文化要素,也不可忽视经济、政治因素。
同时,我们亦可深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爱国学者对国家与民族发展的赤诚之心。他在抗战时期曾撰文指出,对中国来说,民族意识是中西交往中最大的收获,我们以此应付幻变的世界,同时支持危难的抗战。[1]40[5]95—98此外,阎先生在抗战时期的不少著述也都从文化史观的角度提出抗战必胜的观点,这是他作为学者为抗战所做的贡献。推而广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学者如何为国家服务,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一个核心而重要的问题,阎先生的中西交往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富于启迪的答案,我们对其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目标、方法和观点所带有的时代局限性则不必过于苛求,因为学人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学术语境,此即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
[1] 阎宗临.中西交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阎守诚.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编者的话[A]. 任茂棠,行龙,李书吉.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3] 阎宗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阎宗临.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A].阎守诚.阎宗临史学文集[C].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5] 阎宗临.欧洲文化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