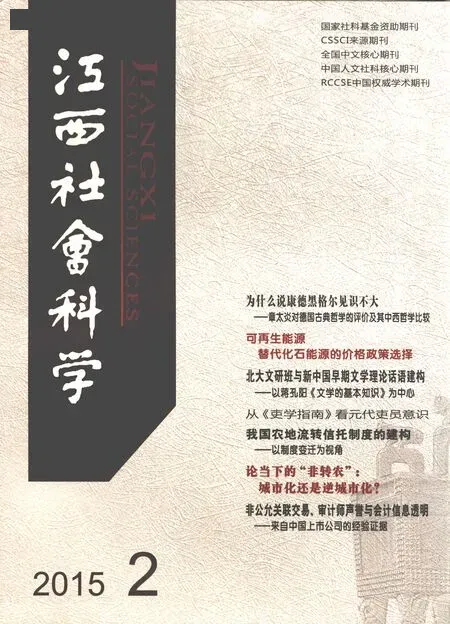为什么说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
——章太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许苏民
为什么说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
——章太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许苏民
章太炎之所以认为康德黑格尔见识不大,主要理由在于:与康德——于时空有限无限之辨而陷入逻辑矛盾,又因欲摆脱矛盾而主张主观时空观不同,中国哲学则从没有陷入这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与康德讲德福一致必设置上帝之存在不同,中国哲人以“依自不依他”之说来唤起人的道德自觉,更具有洞彻道德之本质乃人类精神之自律的深邃眼光;与康德在物自体面前止步不前不同,中国哲学则能超越分别智达于无分别智以证悟本体;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终局目的论”,不合乎“善亦进化,恶亦进化”的历史实际;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论是一种“陵藉个人之自主”的学说,与此相比,我国的庄子哲学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与黑格尔以文野之辨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张目的观点不同,“以齐文野为究极”的庄子“齐物论”则具有价值论的合理性。章太炎对中国哲学之大智慧、大见识的阐扬为熊十力、冯友兰所继承,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批评发杜威、罗素、诺斯罗普反思德国古典哲学的先声。
章太炎;康德;黑格尔;中国哲学;中西哲学比较
许苏民,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 210093)
章太炎是继方以智以后又一位说西方哲学水平不高的中国哲学家。方以智说西学 “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章太炎说西方哲学“精思过于吾土,识大则不逮远矣”,都认为西方哲学水平不高,见识不大。从方以智到章太炎,中间近300年,西方哲学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英国经验论、大陆理性派和德国古典哲学这样的思想高峰,为什么章太炎还要说西方哲学见识不大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章太炎说西方哲学见识不大,主要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他在《四惑论》(1908年)一文中,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以所谓“公理”、“进化”等各种名义而宣扬的理论都有学理上的片面性:“有如其实而强施者,有非其实而谬托者,要之皆眩惑失情,不由诚谛。”因此,他主张弘扬《易传》的破除蛊惑之义,来廓清其谬说:“《传》曰:‘蛊者,事也’。伏曼容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二经十翼,可贵者此四字耳。”[1](P443-444)《易传》的精神被他归结为不受谬见之蛊惑,与深受其影响的胡适把禅宗精神归结为“不受人惑”一样,都反映了中国哲人对待西方哲学的理性态度。
章太炎认为西方哲学见识不大,并不限于《四惑论》,更贯穿于他的全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中。在《俱分进化论》(1906年)、《无神论》(1906年)、《建立宗教论》(1907年)、《齐物论释》(1912年)、《筈汉微言》(1915年)等论著中,他继承和阐扬了中国哲学的思想精粹,并以此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相比较,对康德哲学的学理失误、黑格尔哲学的弊病,以及国人盲目崇信西方哲学的倾向一一作了深刻的批评。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哲人深厚的哲学素养和超越西方哲人的大学问和大智慧。
一、“庄生之言胜康德”——对康德哲学本体论的批评
章太炎认为康德哲学见识不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筊筊于时空有限无限之辨而陷入逻辑矛盾,又因欲摆脱矛盾而主张主观的时空观;二是论德福一致必设置上帝之存在,依然是基督教哲学诉诸人的利己心以维持道德的思路;三是在物自体面前止步不前,不能超越分别智而达于无分别智以证悟本体。他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国哲学都比康德哲学高明。后来熊十力和冯友兰论中国哲学,几乎都继承了章太炎这些观点。
(一)依他起性与康德的主观时空观
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说:“言哲学创宗教者,无不建立一物以为本体。”[1](P404)遵循佛教唯识宗“三性”说的思路,章太炎确立了“真如”本体的学说。所谓“三性”,即遍及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惟由意识周遍计度刻画而成”,其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妄有”或“实无”;依他起性“由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末那识,与眼、耳、鼻、舌、身等五识虚妄分别而成”,其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假有”或“似有”;圆成实性“由实相、真如、法尔(犹云自然)而成”,是“实有”和“真有”。[1](P404)依他起性处于似有非有之间,是证成圆成实性的过渡环节。只有排遣遍及所执性,顺随依他起性,才能证成圆成实性。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的前提下,承认了客观世界的实在性。
依据上述观点,章太炎对康德“拨空间、时间为绝无”的观点作了批评。他认为空间和时间与物质存在和人类的活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不可以把空间和时间仅仅看作是主观先验的思维形式的“绝无”。他说:“假令空是绝无,则物质于何安置?假令时是绝无,则事业于何推行?故若言无空间者,亦必无物而后可;若言无时间者,亦必无事而后可。”[1](P405)他理解康德为什么要以时空为“绝无”的苦心:“彼其所以遮拨空、时者,以前此论空间者,或计有边,或计无边;论时间者,或计有尽,或计无尽,互为矛盾,纠葛无已,于此毅然遮拨为无,而争论为之杜口。此不可谓非孤怀殊识也。”然而,身为哲学家却不能不正视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无限性的事实:“虽然,有边无边、有尽无尽之见,岂独关于空间时间而已耶?若以物言,亦可执有边,无边之见,所以者何?现见六十四种极微,积为地球,推而极之,以至恒星世界。此恒星世界极微之量,果有边际乎?抑无边际乎?若以事言,亦可执有尽、无尽之见,所以者何?现见单细胞物,复生单细胞物,经过邬波尼杀昙数层累阶级而为人类,由此人类复生人类。此—切众生之流注相续者,果有始终乎?抑无始终乎?”因此,“破空而存物、破时而存事者,终不能使边、尽诸见,一时钳口结舌明矣。果欲其钳口结舌耶?则推取物质、事业二者,与空间、时间同日而遮拨之可也。”他又说,康德也知道如果完全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是说不过去的 “偏激”之论。“故于物质中之五尘,亦不得不谓其幻有,而归其本体于物如。若尔,则空间时间何因不许其幻有耶?物有物如,空间时间何因不许其有空如时如?……生人心识,岂于空无所依而起此觉?故曰,损减执者,不知依他起自性也。”[1](P406)章太炎以此证明,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虽然是主观的,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则是客观的,因此,康德的主观时空观无疑是片面的。
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要否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性,是由于以往的西方哲学家在时间有尽无尽、空间有边无边的问题上“互为矛盾,纠葛无已”,而中国哲学则没有陷入这种矛盾之中,这是中国哲学家比西方哲学家见识大的表现。——因为中国哲人意识到哲学形而上学本质上是为人类的生活和实践提供终极合理性的学问,既然如此,又何必纠缠于宇宙有限无限的问题呢?他说:“大抵此土哲学,多论人生观,少论宇宙论。至世界成立万物起原之理,自《易》以外,率不论,而中古为甚。庄生记冉有问于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耶?’孔子曰:‘可,古犹今也。’此即禅宗当下即是之意。盖穷究世界之成立,万物之起原,即成有边无边诸见,在佛家亦不许论也。此种葛藤,中古哲学家多能斩截;而欧洲哲学家,至今犹自寻缠绕,然则精思过于吾土,识大则不逮远矣。庄生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朱元晦少时,问天之上更有何物,当时叹以为奇,其实终身讲学支离,即由此耳。”[2](P263)他认为正如孔子、庄子比朱熹的见识大一样,孔子、庄子这些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见识要大。熊十力之所谓“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独为之本”,其实正是对章太炎的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挥。
(二)真如与康德的物自体
他认为康德学说的不足与柏拉图“理念”论一样,都是由于忽视了“依他起性”而难以自圆其说。他说:“康德既拨空间、时间为绝无,其于神之有无,亦不欲遽定为有,存其说于纯粹理性批判矣。逮作实践理性批判,则谓自由界与天然界,范围各异。以修德之期成圣,而要求来生之存在,则时间不可直拨为无,以善业之期福果,而要求主宰之存在,则神明亦可信其为有。夫使此天然界者,固—成而不易,则要求亦何所用。知其无得,而要幸于可得者,非愚则诬也。康德固不若是之愚,亦不若是之诬,而又未能自完其说。意者于两界之相挤,亦将心情意乱,如含蒜齑耶? ”[1](P408)
有学者认为,这段话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康德伦理学既非让人 ‘修德之期成圣’,更非‘以善业之期福果’。”[3](P28)这一说法对吗?从表面上看,是对的,康德的伦理学是超功利的,是主张为行善而行善的,行善本身就是目的,犹如董仲舒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亦犹如程朱理学之 “严天理人欲之辨”、主张“存理灭欲”;而认为这一说法不对,说康德教人行善是“修德之期成圣”、“以善业之期福果”,却也不无依据,亦正如李卓吾说董仲舒并非真的不计功谋利而程朱有“大欲”存焉一样。康德之所以要在讲实践理性时设置上帝的存在,就在于人间的道德与幸福并不一致,只有上帝才能给予有德行的人以幸福的补偿,这不正是章太炎所指出的 “以善业之期福果”?所以我认为,章太炎这段话比如今一般专门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对康德哲学的理解更为准确和深刻,不仅看出了康德其实并没有完全排斥功利,而且把康德的理论困境也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们中国哲人读书,提倡“能识其正面、背面”,甚至能“从字缝中看出字”来的洞察力,而章太炎正是具备这一洞察力的。
如何走出康德的上述困境?章太炎为康德的信徒们指明了出路,他说:“欲为解此结者,则当曰: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现识要求而有。此要求者,由于渴爱;此渴爱者,生于独头无明。纵令有纯紫之天然界,而以众生业力,亦能变为纯青之天然界。此渴爱者云何?此独头无明者云何?依于末那意根而起。故非说依他起自性,则不足以极成未来,亦不足以极成主宰也。以此致眷证之,或增依他,或减依他,或虽密迩,而不能自说依他。偏执者,则论甘忌辛;和会者,则如水投石。及以是说解之,而皆冰解冻释。”[1](P408)在章太炎看来,如果康德懂得佛学的三性之说,那么就不仅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会像是在珍馐饼果内倾注了奶油而“更生胜味”了。
不过,章太炎并不赞成康德对上帝信仰的保留,他认为有神之说没有根据,“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可谓千虑一失矣”。他说:“物者,五官所感觉;我者,自内所证知。……而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而知。若物若我,皆俱生执,而神则为分别执。既以分别而成,则亦可以分别而破。”他说通过推理(比量)来证明的也可以通过推理来破除:“人之念神,与念木魅山精何异?若谓超越认识范围之外,则木魅山精亦超越认识范围之外,宁不可直接为无耶?”因此,“凡见量、自证之所无,而比量又不可合于论理者,虚撰其名,是谓‘无质独影’。……况于神之为言,惟有其名,本无其相,而不可竟拨为无乎”[1](P402)!
由此章太炎又发现了一个西方哲学不及中国哲学见识之大的地方,即:中国哲人教人讲道德,主“依自不依他”之说;而西方哲学教人讲道德,则需借助于上帝的权威;前者旨在唤起人的道德自觉,后者则诉诸人的利己心。因此,在这方面,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为纯正。他说:“至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说(墨子虽生孔子后,其所守乃古道德)。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语。……而今世宿德,愤于功利之谈,欲易之以净土,以此化诱贪夫,宁无小补;然勇猛无畏之气,必自此衰,转复陵夷,或与基督教祈祷天神相似。夫以来生之福田,易今生之快乐;所谓出之内藏,藏之外府者,其为利己则同,故索宾霍尔(即叔本华——引注)以是为伪道德(《道德学大原论》)。而中国依自不依他之说,远胜欧洲神教,……今乃弃此特长,以趋庳下,是仆所以无取也。”[1](P371-374)他的这一观点,为后来的熊十力所继承。
(三)“庄生之言胜康德”
章太炎采用的佛教唯识宗“三性”说的认识本体的思路,可概括为“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4](P71)。他认为在中国哲学中,庄子所采用的就是这一方法,因而胜过陷入逻辑矛盾而在“物自体”面前止步不前的康德。他说:“庄生数言‘以不知知之’,即谓以无分别智证知也。世人习睹以为常言。校以远西康德,方知其胜康德,见及物如,几与佛说真如等矣。而终言物如,非认识境界,故不可知,此但解以知,知之不解,以不知知之也。卓荦如此,而不窥此法门,庄生所见不亦远乎?”[4](P26)分析名相是分别智,排遣名相是无分别智,前者是逻辑的方法,后者是直觉的方法,康德不懂得以直觉的方法论证“物自体”,所以不如庄子高明。
他又说:“庄生临终之语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胜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见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夫言与齐不齐,齐与言不齐,以言齐之,其齐犹非齐也。以无证验者为证验,其证非证也。明则有分别智,神则无分别智。有分别智所证唯是名相,名相妄法所证,非诚证矣。无分别智所证始是真如,是为真证耳。所谓‘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离念境界唯证相应’,临终乃自言其所至如此。”[4](P28)对于认识本体来说,“明”——分别智,不如“神”——无分别智,逻辑的方法不如直觉的方法;因为分别智本不是认识本体的方法,只有无分别智——直觉——才能认识本体。
冯友兰在194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比较通俗的论述,有助于对章太炎以上论述的理解。他说,专就区分可知与不可知而论,康德与道家十分吻合。康德认为,尽管形而上学的目的是对经验作理智的分析,可是这些路子全都各自达到“某物”,这“某物”在逻辑上不是理智的对象,因而理智不能对它作分析。这不是因为理智无能,而是因为“某物”是这样的东西:对它作理智的分析就陷入逻辑的矛盾。“不论纯粹理性作出多大努力去越过界线,它也总是留在界线的此岸。这种努力有些像道家说的‘形与影竞走’。但是看来道家却用纯粹理性真地越过界线走到彼岸了。道家的越过并非康德所说的辩证使用理性的结果,实际上这完全不是越过,而无宁是否定理性。否定理性,本身也是理性活动。”[5](P589-591)冯友兰的这一理解是正确的,然而,章太炎的论述却比冯友兰的论述早了33年。
二、“庄生之说远胜黑格尔”——对黑格尔“绝对精神”论的批评
在章太炎1908年发表《四惑论》着重批评黑格尔哲学的前两年,严复发表过《述黑格儿惟心论》(1906年)一文,指出黑格尔哲学实质上是反自由的,同时还带有以进步或历史规律的名义对落后民族进行征服的意味;其之所以反对政治自由,是因为他认为君主乃是绝对精神的承载者,是“会亿兆之公志而为一人之大志者”,所以路易十四的名言“朕即国家”乃是真理;他之所以主张对落后民族要灭其国,是他认为这是“天理之极则”,即他之所谓历史规律的必然要求。[6](P214)章太炎的《四惑论》,似有承于严复的观点,而对黑格尔哲学之弊病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批评。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许多观点都是来自康德。虽然章太炎在文章中没有点康德的名,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一些批评同时也是针对康德的。在对黑格尔哲学做出深刻批评的同时,他指出我国的庄子哲学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他所阐明的观点,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威(John Duwey)反思德国古典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诺斯罗普(Filmer Stuart Cuckow Northrop)对德国古典哲学作进一步反思的先声。
(一)“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亦一切不得自由”
在中西哲学史上,都有把某种主张、道理或秩序神化为宇宙本体而强迫人奉行者,如宋儒之所谓“天理”,黑格尔之所谓“绝对精神”。但章太炎根本不承认其具有宇宙本体的地位,他说:“公理者,犹云众所同认之界域。譬若棋枰方卦,行棋者所同认,则此界域为不可逾。然此理者,非有自性,非宇宙间独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观念应于事物而成。”但一旦将其神化为宇宙本体,就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宋世言天理,其极至于锢情灭性,熏民常业,几一切废弃之。而今之言公理者,于男女饮食之事,放任无遮,独此所以为异。若其以世界为本根,以陵藉个人之自主,其束缚人,亦与言天理者相若。……其所谓公,非以众所同认为公,而以己之学说所趣为公。然则天理之束缚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缚人又几甚于天理矣。 ”[1](P444)
章太炎认为,要避免以这种所谓的 “公理”来 “陵藉个人之自主”,就必须从本原上说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盖人者,委蜕遗形,倏然裸胸而出,要为生气所流,机械所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相对于群体来说,个人更具有本原性,社会应是为了维护每一个个人的权利而存在的。个人当然要对社会尽责任,但这种责任感不是先验的,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个人在初生时,本无所谓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偿于彼”。所以,“人类所公认”的处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合理规范应是:既“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又 “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人伦相处,以无害为其限界。过此以往,则巨人长德所为,不得责人以必应为此。”[1](P444)从这一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章太炎的观点与康德、黑格尔以责任或“天职”为先验的绝对命令的观点的显著区别:章太炎的观点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先验论不同,而似乎暗合于马克思以“个人自主活动”为原点、以道德为社会关系之产物的说法。
章太炎又通过征引蒲鲁东公然鼓吹强权的一段话来引出对黑格尔的批评:“布鲁东氏之说则曰:‘天下一事一物之微,……盘旋起舞,合于度曲,实最上极致之力使然。有此极致,故百昌皆向此极致,进步无已。是虽必然,而亦自由。是故一切强权无不合理。凡所以调和争竞者,实惟强权之力。’”章太炎认为,蒲鲁东的这一论述的来源,就是黑格尔的学说:“原其立论,实本于海格尔氏,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采色有殊,而质地无改。既使万物皆归于力,故持论至极,必将尊奖强权矣。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后此变其说者,不欲尊奖强权矣,然不以强者抑制弱者,而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牵掣,亦由海格尔之学说使然。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也。”[1](P445)章太炎还指出,这种所谓公理论的危害不仅在于使人一切不得自由,更有甚者,是以公理的名义而为残忍之事:“若如公理之说,无益于社会者,悉为背违公理。充其类例,则有法人之俗,虐老兽心,以为父既昏耄,不能饬力长财为世补益,而空耗费衣食之需,不如其死,则自载其老父,沈之江水。是则持公理者,乃豺狼之不若、狸筍所不为耳。”[1](P448)
章太炎认为,这种“陵藉个人之自主”的公理论,其历史渊源有二,一是承封建政治之余习,二是来自基督教哲学。基督教说,人是为了上帝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康德说,人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黑格尔说,人是为了实现绝对精神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同一种思维方式:“欧洲诸国,参半皆信神教,而去封建未远,深隐于人心者曰:人为社会生,非为己生,一切智能膂力当悉索所有以贡献于大群。因政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虽瑰意琦行之士,鲜敢越其范围。”[1](P445)章太炎把“世之残贼”分为三类,一是言专制者,二是宋儒式的言天理者,三是黑格尔式的言公理者。他说:“世之残贼,有数类焉,比校其力,则有微甚之分。宁得十百言专制者,不愿有一人言天理者;宁得十百言天理者,不愿有一人言公理者。所以者何?专制者,其力有限,而天理家之力,比于专制为多。……言天理者……尚有讼冤之地。言公理者,以社会抑制个人,则无所逃于宙合。 ”[1](P448-449)太炎先生的局限性在于,他没有能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做出如同后来的罗素、诺斯罗普那样的具体分析,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一批评,却与后来罗素、诺斯罗普的观点相一致。他认为与黑格尔哲学相比,庄子的哲学才是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
第一,与黑格尔哲学以服从普鲁士国家的目的来衡量人的价值不同,庄子强调人的价值在于其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即实而言,人本独生,非为他生,而造物无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吾为他人尽力,利泽及彼而不求圭撮之报酬,此自本吾隐爱之念以成,非有他律为之规定。吾与他人戮力,利泽相当,使人皆有余而吾亦不忧乏匮,此自社会趋势迫胁以成,非先有自然法律为之规定。有人焉,于世无所逋负,采野稆而食之,编木堇而处之,或有愤世厌生、蹈清泠之渊以死。此固其人所得自主,非大群所当诃问也。当诃问者云何?曰:有害于己无害于人者,不得诃问之;有益于己无益于人者,不得诃问之;有害于人者,然后得诃问之。此谓齐物,与公理之见有殊。”[1](P444-445)
第二,与黑格尔哲学公然尊奖强权、以恶为实现历史的终局目的之必由之路的观点不同,庄子之“齐物”更具有价值论的合理性。只有正视“公理”论者之“以众暴寡,甚于以强凌弱,而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的事实,“乃知庄周所谓齐物者,非有正处、正味、正色之定程,而使万物各从所好,其度越公理之说,诚非巧历所能计矣。若夫庄生之言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海格尔所谓事事皆合理、物物皆善美者,词义相同。然一以为人心不同,难为齐概,而一以为终局目的借此为经历之途,则根柢又绝远尔。”[1](P449)
(二)“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对黑格尔“终局目的论”的批评
章太炎《四惑论》批评的所谓“进化”,主要是针对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终局目的论”的。他说:“近世言进化论者,盖碢于海格尔氏。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达尔文、斯宾塞尔辈应用其说,一举生物现象为证,一举社会现象为证。如彼所执,终局目的,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而进化论始成。”[1](P387)但《四惑论》所批评的这一观点,似乎又并不仅仅是针对黑格尔的。如王国维所指出,康德也把在地上建立天国看作是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天国之实现,乃世界之目的而历史之止境也。”[7](P171)章太炎注意到在进化论风行之时,“即有赫衰黎(赫胥黎——引注)氏与之反对”,“索宾霍尔(叔本华——引注)已与相抗”,但前者“未为定论”,后者又“苦无证据”,所以才要对这一学说从学理上作全面系统的批评审定。
其一,章太炎认为,讲进化不能只讲善的进化一面,还应讲到恶的进化一面;只讲一面而不讲另一面,是不可能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规律的。他批评进化论的观点说:“若云进化终极,必能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则随举一事,无不可以反唇相稽。彼不悟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智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1](P386)例如:“人与百兽,其恶之比较为小乎?抑为大乎?……虎豹虽食人,犹不自残其同类,而人有自残其同类者!……由是以观,则知由下级之乳哺动物,以至人类,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也。”[1](P387)善恶并进的事实说明,黑格尔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观点是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其二,善恶并进根源于人性。“生物本性,无善无恶,而其作用,可以为善为恶”,“种种善恶,渐现渐行,熏习本识”,由此在人性中植下善恶的种子,故人性中不仅有善,而且有恶。“希腊古德以为人之所好,曰真、曰善、曰美。……虽然,人之所好,止于三者而已乎?若惟三者,则人必无恶性,此其缺略可知也。今检人性好真、好善、好美而外,复有一好胜心。……此好胜者,由于执我而起,名我慢心,则纯是恶性矣。是故真、善、美、胜四好,有兼善、恶、无记(‘无记者,即无善无恶之谓’——引注)三性,其所好者,不能有善而无恶,故其所行者,亦不能有善而无恶。生物之程度愈进,而为善为恶之力,亦因以愈进,……而就一社会、一国家中多数人类言之,则必善恶兼进。”[1](P389-390)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互相依存说明:纯真无假、纯善无恶、纯美无丑、纯之又纯、洁之又洁的社会似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认为人类的进化有朝一日“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向往而已。恩格斯说得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8](P442)太炎先生似乎正有见于此。
其三,历史的发展不是只有进化,也有退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出现 “善亦退化,恶亦退化”的情形。章太炎认为,中国自宋朝以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形,“程、朱、陆、王之徒,才能自保,而艰苦卓绝,与夫遁世而无闷者,竟不可见。此则善之退化矣”。古人行事,即使是恶,也有“伟大雄奇之气”贯于其中。“然观今日……朝有谀佞而乏奸雄,野有穿窬而鲜大盗,士有败行而无邪执,官有两可而少顽筎。方略不足以济其奸,威信不足以和其众,此亦恶之退化也。”[1](P391)他认为,这种情形是“言专制者”和“言天理者”所共同造成的,不为无见。
从社会发展的错综复杂的事实中,章太炎看到,近代西方哲学对于社会进化的认识其实是很不完备的,而这种不完备性则是由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的。由于主体心识实际上在认识构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切认识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绝对真理,既不应把人的理性能力神圣化,更不应把有限的认识绝对化:“所谓自然规则者,非彼自然,由五识感触而觉其然,由意识取像而命为然,是始终不离知识……故纵不说物为心造,而不容不说自然等名为心造。物若非心造耶,知物者或未能过物;自然之名既为心造,则知自然者必过于自然矣。故真惟物论者亦不得不遮拨自然,而托之者至谬妄也。”[1](P455)他认为真正的唯物论者绝不会把对于自然界的有限知识夸大为仿佛已成定律的“自然法则”,更不用说把这种法则移植到社会领域了。鉴于西方学者已将其移植到社会领域而造成了负面的后果,章太炎主张应设法对治之:“黠者之必能诈愚,勇者之必能陵弱,此自然规则也。循乎自然规则,则人道将穷,于是有人为规则以对治之,然后烝民有立。”[1](P456)
对于西方近代哲学以“自然法则”的名义迫使人服从强权,章太炎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他说:“昔之愚者,责人以不安命;今之妄者,责人以不求进化。二者行藏虽异,乃其根据则同。以命为当安者,谓命为自然规则,背之则非义故;以进化为当求者,亦谓进化为自然规则,背之则非义故。自我观之:承志顺则,自比于厮养之贱者,其始本以对越上神,神教衰而归敬于宿命,宿命衰而归敬于天钧。俞穴相通,源流不二。世有大雄无畏者,必不与竖子聚谈猥贱之事已。”[1](P456-457)他看到,责人以不安命的“昔之愚者”与责人以不求进化的“今之妄者”,虽然主张不同,其实思维方式却是相同的。责人以不安命,是取消了人“可以做什么”的积极自由;责人以不求进化,是取消了人“可以免于什么”的消极自由。19世纪以来流行的所谓“你不进化,我强迫你进化”,与18世纪流行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一样,都是企图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和其他民族,是对人类自由的亵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诺斯罗普 (Filmer Stuart Cuckow Northrop)从学理上揭示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弊病,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康德和黑格尔 “将人类知识的理论部分错误地设想为绝对的和必然的,而不是像费英格和杜威那样如实地将其设想为仅仅是假设的、通过因果演绎间接认定的,因此其具体内容永远不会有终极的或绝对的确定性”[9](P214)。又说,康德及其追随者们把英美文化意思上的“自由”一词等同于 “免于……的自由”,并把它描述为一种纯粹消极的自由,同时将积极的自由视为服从道德律的确定性,而这种道德律的确定性,又是从属于人类的进化“必达于尽美醇善之区”的“终局目的”的。由此,一种起始于自由的道德也就终结于对决定论的服从。这些都是西方哲人在20世纪40年代才认识到的真理,而我们民族的哲人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认识到了。
(三)“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对黑格尔绝对精神论的文明观之批评
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名著《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人们可以读到以下语言:“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10](P353)“这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时期就是统治的民族……它具有绝对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对他的这种权利来说,其他各民族的精神都是无权的。”[10](P354)“文明的民族可以把那些在国家的实体性环节方面是落后的民族看做野蛮人 (略——引注)。文明民族意识到野蛮民族所具有的权利与自己的是不相等的,因而把他们的独立当作某种形式的东西来处理。 ”[10](P355-356)所有这些语言,都是在以历史的绝对精神的名义,和由此派生的区分所谓“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名义,主张在国际上推行霸权主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与黑格尔的以上论述针锋相对,章太炎提出了“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的学说。这一学说是通过对庄子哲学做深入研究而提出来的。在周秦诸子中,他最推崇庄子。如前所述,他认为西方哲学不如中国哲学见识大,也主要是依据庄子哲学与康德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他最重视《齐物论释》(1912年)一书,认为是 “千六百年来未有等匹”,“可谓一字千金”。而他之所以作这本书,其实就是针对黑格尔哲学的,可于 《齐物论释》第三章释文中见之。释文自云写作此书的意图在于:“原夫 《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鹦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11](P39)在这段论述中,他揭露了黑格尔一类的西方哲学家实际上是“志存兼并”,却偏要“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把他们对其他民族的兼并和蚕食说成是把他们的文明或文化带给野蛮民族;而他们的所谓“文野不齐之见”,正是“桀跖之嚆矢”。他发挥庄子的自由之义,针对的是黑格尔只要德意志民族的所谓 “全体的自由”、而不要其他民族的自由;他发挥庄子的平等之义,针对的是黑格尔只要西方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不要西方民族与东方民族之间的平等。《齐物论释》在本体论方面否定了各种关于绝对主宰的观念,其中就包括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宰世界的观念。他阐发了“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11](P3)的思想,为个人自由和世界各民族的自由提供了哲学依据。他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各种主观主义的独断观点,阐发了“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11](P3)的思想,为确立平等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第五章,其实就是一篇批评黑格尔一类的西方哲学家以其学说充当“桀跖之嚆矢”、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战斗檄文,也是一篇深入阐述庄子的齐物之义、为世界上的受压迫民族的生存和自由权利作义正词严之辩护的庄重声明。他说:“今之伐国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复蒙其眩惑,返观庄生,则虽文明灭国之名,犹能破其隐匿也。……或云物相竞争,智力乃进,案庄生《外物篇》固有其论,所谓 ‘谋稽乎筓,知出乎争’……知之审矣,终不以彼易此者,物有自量,岂须增益,故宁绝圣弃知而不可邻伤也。向令《齐物》一篇方行海表,纵无减于攻战,舆人之所不与,必不得藉为口实以收淫名,明矣。……或言《齐物》之用,廓然多涂,今独以蓬艾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杌、穷奇之志尔。如观近世有言无政府者,自谓至平等也,国邑州闾,泯然无间,贞廉诈佞,一切都捐,而犹横箸文野之见,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劳形苦身,以就是业,而谓民职宜然,何其妄欤!故应物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11](P40)在这段论述中,太炎盛赞庄子见识之高卓,“虽文明灭国之名,犹能破其隐匿”,其意也是说,庄子的齐物之义比黑格尔一类的西方哲学家的见识要高得多。庄子并非不懂得“物相竞争,智力乃进”的道理,但这种竞争决不应成为侵略别国、伤害别国人民的借口,更不应强迫别国人民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所谓自由、平等,无不需要建立在尊重各国人民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而不是把世界文明变成一个模式。
三、“会通东西学人之所说,华梵圣哲之义谛”——论东西方哲学会通的人性论基础及其他
太炎先生精研佛教惟识宗及周秦诸子学说,又“旁览……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4](P71),比较其学理之精粗、见识之高下,故有西方哲学“精思过于吾土,识大则不逮远矣”[12](P279)之说,又有“中国科学不兴,唯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之说。他既认识到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的学理失误和弊病,又看到了中国古代哲人的大智慧和大见识,故能把文化自信建立在清醒的理性基础上。因此,他既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时又主张会通 “东西学人之所说,华梵圣哲之义谛”,强调“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为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业识同则种子同,种子同则见行同”
在近400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凡是志在会通中西哲学的大学者,都无不讲“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特别是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做出雄辩论证的王国维、为会通中西哲学做出卓越贡献的贺麟,都明确认为哲学是人性的最高表现,而筊筊于所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乃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的表现。太炎先生作为国学大师,正是以“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圣贤古训作为其会通中西哲学的深层精神依据的。
首先,他认识到,东西方哲学之所以能够会通,就在于其具有共同的人性论基础。他说:“陆子静言:‘东海西海圣人,此心同,此理同。’通论总相,其说诚当,至若会归齐物,和以天倪,岂独圣人,即谓‘东海有菩萨,西海有凡夫,此心同,此理同;东海有魔外,西海有大觉,此心同,此理同’,可也。此义云何?一类众生,同兹依正则,时方之相,因果之律,及一切名言习气,自为臧识中所同具,故其思仑之轨,寻伺之途,即须据是为推,终已莫能自外。其间文理详略,名相异状,具体言之,虽不一概,而抽象则同。证以推理之术,印度有因明,远西有三段论法,此土墨子有《经上下》,其为三支,比量若合符契。此何以故?以业识同则种子同,种子同则见行同,故且是二物;如麻与绳,非有二性。执箸即是魔外,离执便为圣智。是故世俗凡圣愚智诸名,皆是程度差违,而非异端之谓也。”[4](P49)人是要讲道理的,讲道理就要 “同依正则”,就要遵循共同的逻辑思维的规则,因此,运用逻辑来进行思维、来追求真理,乃是人类心灵普同性的表现。
其次,人类具有相同的先验的认知结构,所以才具有相同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同依正则”的逻辑思维规则。他认为康德所讲的人的先验的认知结构,佛学和庄子都讲到了。依据佛学义理,人的藏识(即阿赖耶识)中含有七类种子,一是世识(过去、现在、未来),二是处识(点线面体中边方位),三是相识(色声香味触),四是数识(一二三等),五是作用识 (有为),六是因果识(彼由于此,由此有彼),七是意根有我识(人我执、法我执)。“其他有无是非,自共合散成坏等相,悉由此七种子支分观待而生。”这七识就构成了人的认识的先验结构,或“原型观念”。庄子的《齐物论》也意识到这一道理,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这里所说的“成心”就是佛教惟识宗所说的“种子”,“成心之为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未动,潜处藏识意根之中,六识既动,应时显现,不待告教,所谓随其成心而师之也”。至于第七意根中的我识(我执)种子,乃是非之见的根本,“若无是非之种,是非现识亦无”。[11](P14)正因为人类具有相同的先验的认知结构,所以才有相同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维规则;而无论是庄子、佛家还是康德都能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东西方哲学可以会通的证明。
再次,通过对东西方逻辑学作具体的分析,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使用的乃是同一种逻辑思维的规则。无论是印度的因明学,中国的名学,还是西方三段论,都是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构成。而区别在于:第一,三部分的次序不同。“印度之辨度初宗 (结论——引注),次因 (小前提——引注),次喻 (大前提——引注)。大秦之辩,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其立量次第,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13](P115)第二,印度的因明学比中国的名学和西方三段论更为严密,主要表现在“喻”(大前提)这一环节上。“喻依者,以检喻体而制其款言。因足以摄喻依,谓之同品定有性;负其喻依者,必无以因为也,谓之异品遍无性。大秦与墨子者,其量皆先喻后宗,先喻体者无所容喻依,斯其短于因明。”[13](P116)意思是说,墨子名学和西方三段论都将前提置于结论之前,至于前提可靠与否则无法确定,而因明三支中“喻”的优点就在于它能从正反两个方面考察前提正确与否,以及大小前提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以便及时察觉和避免论证中的错误。这就比西方的三段论和墨家的名学严密多了。章太炎把逻辑学的废绝看作是导致“中夏之科学衰”[14](P148)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对 《墨经》和荀子的名学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二)“唯物之极,还入唯心”
也是基于人类心灵之普同性的观点,太炎先生认为中西唯物论和唯心论皆可会通。对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他有一个独特的见解,即:“真唯物论乃真唯心论之一部分”,“亦可曰唯物论乃唯心论之一部”[1](P453),“唯物之极,还入唯心”[4](P49)。这一观点是从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关系的视角立论的:认识过程绝非单纯的“惟物”,一切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都不能脱离主体的心识,所以真唯物论者即是唯心论者。“惟物者,自物而外,不得有他。应用科学者,非即科学自体;而科学之研究物质者,亦非真惟物论。是何也?言科学者,不能舍因果律。因果非物,乃原型观念之一端。既许因果,即于物外许有他矣。”[1](P452)这个物外的“他”就是人,确切地说,是人心,人心中的“原型观念”。
从认识论转到伦理学,太炎先生认为“以物质文明求幸福”乃是“妄尸惟物之名”,“真唯物论者”决非如此,他们是注重精神追求的:“夫真惟物论者,既举本质而空之,惟以本质为心所妄念之名,是骎骎与惟心相接。然吼模(休谟,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引注)复不许心有本质者,以心亦念念生灭,初无自性,惟无自性,故一切苦乐,心得感之。若心有自性者,即不为苦乐之境所变。然则求乐者,但求诸心,毋求诸物,亦可矣。”[1](P454)他认为英国经验论发展到休谟,正是“唯物之极,还入唯心”的证据。从真唯物论者必注重精神追求的观点出发,章太炎对为求富贵可以放弃独立人格的说法作了激烈的抨击,他借批评世俗之所谓“惟物”而发挥说:“人而执鞭为隶,其行至可羞也。含垢不辞,曰惟存身之故;既存身矣,而复以他种福祉之故,执鞭为隶,其猥贱则甚于向之为隶者矣。”[1](P454)《论语·述而第七》有一句话说:“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太炎的论述,似即对此而发。太炎先生作为革命家,论及“革命的道德”,认为孔学断不可用,因为它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在他看来,在引导人们注重精神追求方面,孔学似乎还不如英国经验论哲学家休谟。
然而,他又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哲学毕竟又比西方哲学更注重道德实践和精神追求。他说从哲学的起源来看,西方哲学是从认识自然界的物质构成发生的,中国哲学则是从人事发生的,由此遂导致中国哲学具有其独到的优长之处:“西洋哲学虽然从物质发生,但是到得程度高了,也就没有物质可以实验,也就是没有实用,不过理想高超罢了。中国哲学由人事发生,人事是心造的,所以可从心实验。……这是中胜于西的地方。”[15](P77-78)又说:“近世远西哲学综以名理,故辞无矛盾;精意箸撰,故语无棘涩;道物之原,故不与泛言物质者同其繁琐。然言则不主于躬行,义则不可以亲证。……阳明尝非宋儒格物之说,斯于诚意则不涉,于事物犹可徵。言哲学者竟何徵乎?庄生云:‘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筕一筗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不省内心,不务质行,而泛言宇宙之原,庶物之根,所谓咸其辅颊舌也。绝去名理,遂无可玩弄者,禅家所谓 ‘胡孙失树全无技两’者矣。淫于此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4](P97)他认为庄子的哲学、佛教哲学和王阳明的学说都能洞察哲学之大本大源在于人的主观心性,所以说到底,还是中国哲学偏胜。后来熊十力讲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 “独为知本”,比西方哲学更有哲学味儿,其实也是来自太炎先生。
(三)“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合新识”
太炎先生深入研究了中国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和适乎时代进步潮流的远见卓识来分辨其中的精华与糟粕,重在阐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华,使国学“兼合新识”,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和论断。他说:“中国头一个发明哲理的,算是老子。老子……不相信天帝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所以不相信鬼,只不敢打扫干净。老子就打扫干净。……以前论理论事,都不大质验,老子是史官出身,所以专讲质验。以前看古来的帝王,都是圣人,老子看得穿他有私心。以前看万物都有个统系,老子看得万物没有统系。及到庄子《齐物论》出来,真是件件看成平等,照这个法子做去,就世界万物各得自在。……有人说老子好讲权术,也是错了。以前伊尹、太公、管仲,都有权术,老子看破他们的权术,所以把那些用权术的道理,一概揭穿,使后人不受他的欺罔。老子明明说的‘正言若反’,后来人却不懂老子用意。若人人都解得老子的意,又把现在的人情参看参看,凭你盖世的英雄,都不能牢笼得人,惟有平凡的人倒可以成就一点事业。这就是世界公理大明的时候了。”[2](P4)
对于庄子思想的精粹,他作了以下通俗的表述,他说:“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愿望,是人类所公同的……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人和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庄子临死有‘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一语,是他平等的注脚。”[16](P34)如今世界上致力于自然生态之保护的人们讲要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或许就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启发。
太炎先生对于儒学,早期多批评,后期则多有肯定。无论是其早年对孔子的批评,还是后来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都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儒家典籍,他非常重视《礼记》中的《儒行》篇,认为“两汉人之气节,即是《儒行》之例证”。但他不喜欢程朱理学却是一贯的,他批评程朱理学的根本弊病在于不懂得 “以百姓之心为心”,推崇抨击宋儒“以理杀人”的戴东原,这一基本立场始终没有变化。而恰恰是在他注重肯定儒学合理因素的时候,却对程朱理学作了更严厉的批评,他说:“范文正讲气节,倡理学,其后理学先生却不甚重视气节。……宋亡,而比迹冯道者,不知凡几。此皆轻视气节之故。如今倭人果灭中国,国人尽如东汉儒者,则可决其必不服从;如为南宋诸贤,吾知其服从者必有一半。”[2](P17)太炎先生为什么这么说,熟悉历史的人其实心里都很明白,无须赘言。他特别重视中国历史人物事迹中所表现出的俊伟刚严的气魄,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特点。他说在这一方面,“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的面目”。他推崇周秦诸子,推崇南宋伐金的岳飞,推崇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推崇抨击宋儒“以理杀人”的戴东原,认为这些人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12](P279)。
他看到了西方哲学和西方社会的弊病,故反对“醉心欧化”的风气,强调“自国的人,该讲自家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对于那些“略识西学”,就“奴于西人,鄙夷国学为无可道者”,予以愤怒的谴责。但他并不排斥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他说:“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这一论述,表现了一位国学大师的宏大气派。
[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章太炎.论中古哲学[A].傅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3]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章太炎.筈汉三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5]冯友兰.中国哲学和未来的世界哲学[A].三松堂全集(第11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6]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佛雏,校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F.S.C.Northrop,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An Inquiry Concerning World Understanding,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46.
[1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2]章太炎.章太炎政论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章太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5]章太炎.章太炎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16]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龚剑飞】
B259.2
A
1004-518X(2015)02-0005-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20世纪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历程”(06AZX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儒耶对话与中国现代观念的生成和发展”(11JJD7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