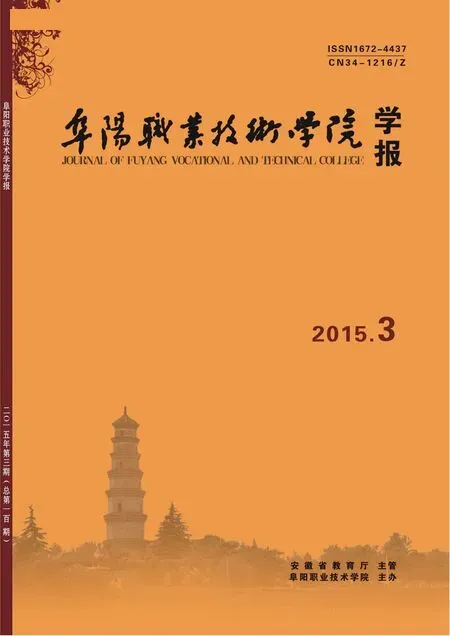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特征研究
孙 根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06)
西方的文艺理论一直以来都渗透着强烈的理性主义的气息,强调体用二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到了20世纪,理性主义危机大爆发,“反思现代性”的思潮不断涌现,种种这些促使西方学者越来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浑融性、感知性、直觉性等具有“主体间性”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像海德格尔、萨特、茵加登等西方学者的“本质直观”、“意向性结构”和“交互主体性”等现象学的一些理论受到了广泛关注。梅洛—庞蒂更是将“身体”置于了本体论的地位之上,创建了“知觉现象学”、“身体主体间性”等具有中国审美特质的理论。西方当代文艺理论对于身心一如、主客交融、物我一体的审美主体间性的关注,显示了在全球化思潮和当代文化反思的双重语境中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当代文论的交流对话的重视。这种对话的功效一方面是使中国古代文论进而使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转向中找到与西方美学的契合点,让中华文化艺术的生命精神融入到当代文化语境中。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当代美学,文化更加注重朝着人与自然共处,身心一体的人文性关怀方向发展。可以看出,在未来,实现西方主体间性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经验的交汇融合与对话将是中外美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这也将为两者的长足发展增添永久的活力。
所以说,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的特征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借助新的理论视角探究中国古典艺术精神,揭示其深广的思想文化精蕴,而且也能顺应艺术学理论的现代性语境,更好地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等战略目标的达成。”[1]我们在综合探究西方现代审美主体间性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特性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文论以下三个方面的审美主体间性特征。
一、崇尚浑融的艺术感知性
西方的文艺理论从古希腊开始就渗透着浓厚的理性主义的色彩,对于主客二分、体用二分的思维模式和审美思维是极端的崇拜的,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瓦莱里强调理性思维在诗歌中的作用……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全球化的危机不断加深,西方美学界也开始关注艺术的非理性思维,强调人们对于外界的艺术感知性,以便得到“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上文所说的萨特、茵加登等西方学者的“本质直观”、“意向性结构”和“交互主体性”以及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身体主体间性”等都属于这种思潮中诞生的理论。
不过,西方文艺界的这种感知性的体验其实可说成是肉体性、非理性或者相当怪异的理性话语,仍然带有强烈的理性思维的影子,而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从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两相融合,相互感知,逐渐进入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地。《礼记》中就有云:“凡音之起,由人心动;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钟嵘《诗品序》也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刘勰之《文心雕龙》亦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些都鲜明表明了外界物象对于诗人的情思的触动,而诗人也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外物,以达到彼此之间的相互融合。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主客体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状态。人作为感觉外在物象的主体,需要集中自己的内在的精神和意志,并且努力进入一种虚静、淡雅的精神境界当中,不应为外界其他繁杂事物所累,进而外在的物象也极尽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感动人心的因素,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且与人之精神相互契合,相互感应,而作者在充分感应外界物象的情感本质特征之后,又依据自己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具象的客体,以便人们对此进行相应的把握和感悟,这一过程就实现了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古人云:“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其他的艺术家诸如宗炳的“澄怀味象”(《画山水序》)、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绘境》)、严羽的“妙悟”,苏轼的“身与竹化”以及王夫之的“现量”说等都是与这种道理相互谋和的。有研究者指出:“‘感物’(‘物感’)→‘超物’→‘神化’(‘凝神’),是中国古代心与物之间互相作用、层层境深的艺术体验的三部曲,也是主客体由对立走向融一的过程。”[2]
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艺术的感知并不是诗人的冥思苦想,强迫为之,这种感知必须是自发的,由诗人内心中不知不觉的突发而出的,不需要借助逻辑的思维就能自行而得。宋代杨简《家记》云:“以兴、以观、以群、以怨,无非正用,不劳勉强,不假操持,怡然自得,所至皆妙。”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当中也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这些都是讲追求艺术的灵感和意境都不是勉强拼凑而来的,而应该来自自然自得,这样才会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孙过庭在《书谱》中讲到书法的违与适的关系时指出“神怡务闲,一合也”“意违势屈,二乖也” 蔡邕在《笔论》中则云:“夫书,先默坐静想,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这些也是讲艺术创作要做到心意自得,明见自悟的地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明艺术创作的时候需要自发感知,以进入物我相融的境界,这也是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审美主体间性特征的一个真实写照。
二、强调双向对举的艺术张力性
我们知道,中国的古典艺术审美感知强烈注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相互作用的心理体验,“作为一种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感性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形式,审美活动中的主体与客体双方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3]正因为中国古典艺术审美讲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所以在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之中出现的诸多艺术范畴都是通过双向对举的艺术形式显现出来的,突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强烈的辩证思维。
“天人合一”、”阴阳两合”是中国古老的宇宙哲学观,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的中国古典艺术包括古代文论从来都是讲究主客体的和谐统一的,它并不单独孤立的去表现主体或客体的某一方面,这便是“天人合一”古典哲学主题在古代艺术中的表现。中国古代大多艺术家、美学家,他们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美的物体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物质性存在,也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主体性存在,而是一种糅合了物与我、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感性与理性等多种对立统一因素的和谐广阔的自由体,而对于这种审美观念的崇尚则孕育了诸多的双向对举的古代文论范畴来,大多都充满了丰富的哲学思辨的意味。
纵观整个古代文论发展史,我们可以列举许多的具有这种双向对举的艺术张力的文论范畴,譬如有无、虚实、形神、骨韵、疏密、形质与风采以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等等。这种辩证对举的文学理论范畴都是源自于中国古老的阴阳二分这一原始范畴之中,《老子·四十二章》就有云:“万物负阴而抱阳”之说,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要兼备阴阳二气”④“文,经纬天地者也,其道惟阴阳刚柔可以该之”⑤所以说,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论,而且对于中国古典的其他艺术形式,这种双向对举的艺术张力都是始终存在的,都是在昭示着中国古典艺术的主客相融合,身心一如的审美主体间性。
以下借助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中的形质与风采对此稍作说明。早在《论语·雍也》中就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说法,这首先当然是说做人要在言行举止和服饰装束上符合“礼”的规定,后来引申到文学领域,指文章的内容和辞彩要相互统一,相得益彰。文章的形质(内容)风采(辞彩)不应该相互分离,而是应该努力兼容,相互印合,已达到相汇想融的境地。扬雄的《法言·修身》亦云:“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可以说是《论语》“文质”说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并明确地将文质这一范畴作为文论问题来看:“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这可以说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文质论的滥觞。后代的刘勰等也对此多有论述。而在绘画艺术以及书法艺术当中也有关于形质与风采的讨论,东晋顾恺之在《谁说新语·巧艺》当中强调“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是“以形写神”论的首创,说明了形神的不可分离,而在南齐书法家王僧虔的《笔意赞》中:“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这里着重强调形神兼备才能成为书法的上品。”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范畴是呈现着这种极为浓厚的辩证对举思想的,十分强调艺术-审美活动的相互映照、相互制约的特点,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审美主体间性的十分重要的一个特性之一。
三、注重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那种纯粹的抽象性的思维精神还没有形成一个既定的完整系统,只是作为一个“隐在状态”而存在,相反,中国古老的“意象思维”却在很早就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人们心中,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思想观念之中并没有明确清晰的关于文化类属概念的区分,“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刘勰《灭惑论》)是他们心中永存的至理,故而他们没有分门别类的对于各种艺术门类的审美特性进行单独的特定概括,而是在体验各种艺术门类的特点和美感之后做出了超艺类的范畴归纳,所以形成了诸如“道象”、“兴味”、“妙悟”、“传神”、“意境”、“风骨”、“情景” 等概括性很强的范畴。我们现在在古代文论中所了解到的各种文学理论范畴其实并不仅仅运用于文学这一单个艺术之中,而且还适用于其他诸如书法、绘画、戏曲等等艺术领域之中,这正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得意忘言”,不必刻意追求语言文本的特定归属问题,最重要的是从中得到感情的宣泄和性灵的抒发。
就拿中国诗歌美学中的核心范畴“意境”来说,在文学当中,它表现的是一种虚实结合、有形描写和无形描写彼此兼容,进而使得有限的具体形象和想象中的无限丰富形象相互统一,达到一种广阔的艺术境界,对于绘画来说,要做到“善于经营空白、善于处理形象画面中“藏”与“露”的关系,使之达到‘有无相生’,‘以形传神’的目的。”[6]。而对于书法来说,所要达到的最高意境则是超越书法本身、融入书法者的气质、灵魂与一体的境界。从这里看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意境”这一范畴并非单纯的就文学的审美性而言的,也涉及到其他的艺术领域。再看“传神”这一文艺理论范畴,最早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这是对绘画作品价值的最高评价,明代的李贽就借用画论中的“传神”来评论小说人物描写的得失。他借顾恺之画论观,对叙事文学的人物描写方法进行了概括:一曰“点睛”;二曰“益三毛”。前者是着重强调描写人物眼睛对于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性,后者强调对于人物个别、偶然的细节进行夸张、变形等描写再现人物心理特点。在这里,李贽就很好的将画论中的“传神”论运用到了文学领域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这种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形象十分普遍,在明清小说评点中,金圣叹、毛宗刚、张竹坡和脂砚斋四大评点家往往借用书法术语、山水画术语以及戏曲术语等来批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叙事作品。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使得各类艺术之间都能够更好地进行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能够使得我们对它们进行综合的概括性的艺术审美评价,以至和我们一直尊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相互契合,达到完美的境界。土耳其学者艾尔桢深刻指出:“在东方思想中,完全的物质性和审美的体验终结于将肉体或是物质分解为‘空’,或是分解为万物的统一,这种统一意为无始无终、无过程、无变化、无差异的‘一’”⑦这或许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很好说明,而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的这种特质也与我们所论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审美主体间性的特征相互契合。
综上所述,正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浑融的艺术感知性、双向对举的艺术张力以及艺类渗透的文本融合性,方才使得它具有无限光辉的色彩,而且对于未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特性的研究以及世界美学的发展都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1]陈示部.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主体间性特质[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5):72.
[2]姜耕玉.艺术辩证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6.
[3]王德胜.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5.
[4][5][6]刘熙载.艺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67、182、74.
[7]高建平,王柯平.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