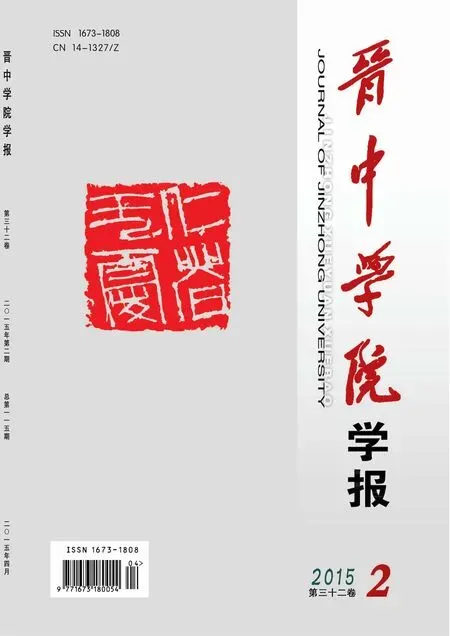公民德行的自然基础——论卢梭的性别秩序理论
朱清艳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8)
一、公民德行在两性关系中形成
十八世纪的法国是君主政体政治腐败与道德滑坡的典型。宫廷和贵族沉浸在奢靡纵欲之中,国家财政危机不断。为了维持庞大的花费,统治者利用苛捐杂税、卖官鬻爵、垄断贸易、发行劣质货币等方式收敛钱财。让道德学家感到惶恐的是欲望的歇斯底里,理性的经济人学说想要为商业发展提供人性论基础,但更想提供控制人类欲望的手段。但在卢梭看来这种哲学只是为自私激情提供了渠道,无法导向他们所希望的社会合作与道德秩序。卢梭怀念古典共和国的公民美德和纯朴道德风尚,他想从人性论中找出共和德行的来源以对抗同样来自人性的自私激情。他找到了古代共和国公民美德的形成机制就在两性关系从情欲到家庭的转化过程之中,爱国主义的源泉就在于女性克尽母亲义务所产生的最温柔自然的情感——家庭的爱。所以卢梭反对柏拉图取消家庭并让男人和女人都变成士兵的制度安排。他反问:“难道说不需要自然的影响就能形成习俗的联系!难道说我们对亲人的爱不是我们对国家的爱的本原!难道说不是因为我们有那小小的家园我们才依恋那巨大的祖国!难道说不是首先要有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然后才有好公民!”[1]535卢梭认为,公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于对包含了家园的共同体的认同和情感分享,所以家庭是培养公民的第一站。
在卢梭做杜宾夫人秘书时期写过两篇关于妇女的论文,一篇论述妇女在历史上无法公开行使权力,另一篇强调了妇女秘密行使权力导致了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比如特洛伊战争,罗马共和国的建立,克里奥兰的母亲之解放罗马,英国在亨利八世治下的变化等。历史重大事件往往被写成具有高尚的目的,其实按照卢梭的人类动机理论,历史事件的秘密诱因在于女人,男人的行为是由情欲引发的。人们对于男人,不是过分夸奖就是有时候又夸奖得不够。他们硬要把大部分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光辉事迹通通都说成是由于男人的雄心、勇气、对荣誉的追求、立志报仇之心或宽宏的气度造成的。实则,那些光辉事迹的起因无他,完全是情欲的驱使。外表上不甚显露的情欲,其效果是非常好的,一般人当然猜想不到它对伟大的男人的影响的。[2]165
看起来,卢梭把情欲看成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真正原因,而女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古代共和国,妇女们被禁止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但她们又对历史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说明她们精于秘密的行动,成功地绕过了这种限制。既然这种限制无法阻碍女性权力,那么卢梭为什么还要推行呢?原因就是:第一,通过这种限制达到两性权力制衡的目的;第二,女性秘密地与公开地行使权力的政治效果和社会影响力是不同的。如果女性秘密行使权力,通过男人发挥她们作为女性的权威,她们本身就必须具有庄重的美德,才能正当地影响丈夫和儿子,以达到激发公民-士兵勇气和荣誉感的目的。如果女性公开行使权力,进入政治领域,结果可能是两性混杂,道德风俗变坏,男人变得柔弱。而女人被限制在家庭内,两性被隔离,道德风俗就比较正派。
在《爱弥儿》开头,卢梭讲了斯巴达妇女询问战事的故事,这位妇女怒斥报信的奴隶先说五个儿子丧生战场的消息,当得知战胜了,她便激动地跑去感谢神灵。可以推测这位斯巴达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因此才培育出五个儿子的爱国主义德行,她的自然自私性被共和国政治彻底改造了。卢梭说“这样的人就是公民。”[1]10在古罗马“所有一切巨大的变革都是由妇女发端的:是一个妇女使罗马获得了自由的,是一个妇女使平民成为执政的,是一个妇女结束了十人团的暴政的,是妇女们把围困的罗马从流放的反叛者手中解救出来的。”[1]584她们通过什么方式做到的呢?“妇女们所歌颂的是伟大的将军的战功,妇女们所哭泣的是丧失了国家的元老;她们的夸赞和诉愿是神圣的,是对共和国事业的最庄严的裁判。”[1]533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和选择,形成了有利于共和国事业德行的偏爱。这些男人按照这种偏爱而行动是为了获得妻子、子女的尊敬。从而共和国的舆论和风俗就被塑造了。看起来,古罗马的公民道德与政治自由依赖于妇女的特质和家庭角色所形成的舆论力量。而且卢梭的家乡当时也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怕遭到女人的严厉谴责,有许多人不敢做坏事啊!在日内瓦,女人几乎起到了监察官的作用”。[3]147
所以,卢梭谈到女性的教育时,古代妇女在家做贤妻良母,并且塑造共和国美德的图景就成为参照标准。妇女们应该“产生一种高贵的雄心——要赢得伟大的和坚强的男人的尊重,要成为斯巴达式的妇女,要指挥男子。……一句话能够取得男人的尊敬和爱的妇女,只要她做一个手势,就可以把他们差遣到天涯海角,就可以叫他们到她所指定的地方去作战,去争取荣誉去牺牲生命。在我看来,这种威信是崇高的,是值得花一番心血去获得的。我们便是按照这种精神培养苏菲的……”[1]588
只有两性的区别、差异、相互吸引,通过家庭这自然情感的纽带才能产生这样的风俗。两性之间激发爱情的相互需要欲求,这在人类的心理与舆论场域中编织了由羡慕、荣誉、爱慕组成的网,这张网不但把男人与女人连结在一起,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关注崇高的价值而有益于社会。所以,卢梭主张制度和风俗要把男人和女人分开,让他们发挥有差异的社会功能,并成为彼此德性的公开评判者。在这种文化中,女性角色与男性角色相互补充,她们的工作与男性工作同样重要。而女性的角色不是情欲或性的对象,而是爱欲激情中的“德”,她们获得了男性在人格上的尊重。
但现在,古代的性别王国被两性混杂和风俗败坏取代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自罗马帝国之后,民族的融合和杂处,原来的风俗习惯便混乱了,善良淳朴的风俗可以自生,而混合放荡的生活方式却传染很快。
罗马帝国的灭亡,一批批的野蛮人的入侵,造成了多民族的混居和杂处,因而必然使他们各自的风俗和习惯逐渐消逝。几次十字军东征,通商贸易的发达,东印度的发现,以及航海、旅游和其他我难以胜数的原因,使风俗习惯愈来愈乱了。所有一切使各国之间交通便利的发明,带给一个国家的,不是别个国家的美德,而是别个国家的恶习,从而使原来适合于自己的风土人情和政治制度的风俗遭到败坏。[2]139
野蛮人部落把女人带入军队,随后兵营放荡横扫了欧洲,漂亮的女士使自己体面地被男人绑架,女性的现代统治就开始了。[3]126但是男女混杂的开始,两性分工不是那么严格(如原初家庭中男人出外狩猎,女人守在小屋),由战争开始的共同生活并未一开始就导致男性的衰弱或女性化,而是导致女性变得具有男人特征。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承认的,也是斯巴达共和国曾经的风俗。妇女变得强健,男人也没有衰弱,这当然是一种更健康的家庭生活。这时的民族是更具有生命力的,所以,历史上出现很多野蛮民族入侵文明民族的事例,但是他们渐渐地也要变得文明而腐败。现代人是野蛮部落腐败后的后代,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血性。古代的妇女会鼓励她们家中的男人去实践公民美德——勇气和公共精神。但这些美德在现代男人中是缺乏的,因为现代男人与现代女人是如此相像,他们都是自私激情主导的理性人。
其次,在古代,婚姻家庭的忠诚与政治义务共同构成了两个相互作用的权力场。对配偶的爱,和对祖国的爱,抑制了个人相对狭隘自私的激情。但是,基督教的出场,对二者都进行了排斥和贬低作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讨论了基督教对于共和主义的破坏:“当我说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时,我已经是错了;因为这两个词是相互排斥的。基督教宣扬只宣扬奴役与服从。”[4]179基督教对婚姻设置了过多的义务,对童贞的狂热崇拜并没有提升女性作为爱情的客体的地位。基督教宣扬是对上帝之爱和彼岸世界的向往,这种精神追求常常会使我们忘记应尽的义务,使人耽于幻想而不愿过活跃的现实生活。这就贬损了对祖国和对配偶的爱。在婚姻的槁木死灰之境,人必然要从侧面寻找浪漫激情的发泄场所,对情人的爱比对配偶的爱更为热烈和欢乐。骑士文学(chivalric literature)和绅士传统(gallantry)的出现都反抗了基督教对婚姻的禁欲式的抹黑(ascetic denigration),[5]64虽然部分地解放了人性,但是从政治原则的角度来看,对情人的爱比对配偶的爱是更不可欲的。对情人的爱虽然热烈却不稳定,其依恋关系比婚姻义务关系更为肤浅,不会让男性成为好公民的同时,也不会成为好丈夫。总之,爱情人的激情不会导向古代的爱国与爱美德的灵魂,反而会释放更多的负面激情。
但是,即使爱情人也比爱自己要好,“最坏的是那种最喜欢自我孤独的人。他把他心中的感情全都用于他自己;而最好的人则把他心中的感情与他的同胞分享。”[3]158社会合作需要相信和利他,最反社会的就是那种自恋的自私。两性之间的性与爱情是比其他社会联系更自然且更不易从心灵中抹去的,如果加以正当化和合理化安排,至少它可以作为自私自利激情的最强大也是最终的阻碍。
现在社会不可能再回到古代共和国,她们不再能发挥古代妇女的那种权力,但妇女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对于当时法国两性关系混乱、道德堕落的现象,卢梭开出的药方是:“要是母亲们都能眷顾她们的孩子,亲自授乳哺育,则风气马上可以自行转移,自然的情感将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振奋起来,国家的人口又将为之兴旺;这是首要的一点,单单这一点就可使一切都融洽起来。家庭生活的乐趣是抵抗坏风气的毒害的最好良剂”。[1]21因此,好的社会应该建立在两性有别且互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上。按照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卢梭要从自然状态中找到强大的证据才能使这个观点有说服力。实际上,卢梭要说明男女有别、互相依赖并互相影响是“大自然的呼声和人类一致的诉求”。[3]119
二、自然状态下的两性关系与家庭
(一)纯粹自然状态下男女野蛮人暂时的关系
卢梭努力让两性社会角色的设计具有自然的基础,以使其具有更为权威的说服力。不同于先辈洛克,卢梭把假象的自然状态又往前推一步的作法使得自由主义理论更有可能建立在原子化的个人之上,因而也更具有革命性,成为批判社会的最强有力的参照。“卢梭认为,并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一旦援引自然作为人类社会的参照,人类关系的所有形式都要按照有意义的前景来进行重建。”[6]46这种加长版本的自然状态就有了纯粹自然状态与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所谓的“第二自然状态”[7]294之分。这两个阶段是连贯的过程,纯粹自然状态中,人类处于漫长而平静的纯粹动物状态,后者是更为复杂化的前社会状态,蕴含了人性特质与心理变化的复杂过程。如果要考察卢梭思想中的两性观点就需要从纯粹自然状态开始,梳理两性关系的起始与变异,以考察哪些是合乎自然律法,哪些是合乎理性,哪些是社会腐败过程中的伴生物。
在纯粹自然状态卢梭推出的是一个无善恶、自立自足的野蛮人形象,是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动物。野蛮人的精神与心理活动只有围绕着自我保存的自爱之心,间或有天然的同情心加以调节。他们的想象力、预见性以及记忆力都非常有限,今日无法预料明日的事情。“他的欲望绝不会超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宇宙中他所认识的唯一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他所畏惧的唯一灾难就是疼痛和饥饿。”[8]104野蛮人只有生理方面的爱,而且不会很强烈和频繁。野蛮人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一生之中彼此也许遇不上两次,互不相识,互不交谈的人们”[8]104无法产生语言,完善化程度极为有限。用原子化孤立存在的野蛮人可以否定任何可能的关系,更不用说不平等和依赖关系了。其中,两性关系是在野蛮人普遍的孤立状态中偶然发生的。在偶然遇见了异性,发生随意的关系之后,就分道扬镳。因为一个人能够记忆为了生殖行为而选择了一个对象,需要人类的悟性具有更大的进步或更大的败坏,“而这里所说的人,还处于动物状态,我们不能设想他的悟性会有这样的进步或败坏”[8]181。
为了强调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或者统治关系,就必须在逻辑上要求即使是女性生育、抚养幼小的行为也无法导致男女长期关系的建立。这是卢梭自然状态中薄弱环节,但是也是他反对洛克观点需要重点辩驳的地方。卢梭认为,男女两性在纯粹自然状态下只是偶尔相遇,满足性欲冲动之后就谁也不需要谁了。原因有三点:其一那时的自然人还处于动物状态,他们的悟性和记忆力还达不到选择并记忆一个交配对象的程度。其二,我们并不能因为男女两性的结合维持长久对于人类可能有益,就肯定那是自然的创设。[8]179其三,卢梭认为女野蛮人与其他动物界的雌性一方一样,怀孕期间不需要照料也能独自抚养孩子。自然状态下的外界环境简单,人类母亲不同于其他动物,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可以携带幼儿,一面寻找食物,一面哺乳或喂养幼儿,因此十分便利,不会称为两性长期联系的理由。[8]79而母亲和孩子之间也不会产生长久关系,“孩子一旦有了自己寻找食物的能力,就毫不迟疑地离开母亲。”[8]89卢梭得出了两性关系的一个结论“夫妻的继续同居,是女人易于重新怀孕的最直接的原因”,所以,在纯自然状态下不会产生夫妻关系状态。这也是卢梭想要区别于洛克及其他哲学家关于自然状态学说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在自然状态,人们不需要合作获得食物、抚养后代或者满足心理需要,他们都过着孤独的生活,一个人没有理由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
女性与男性一样处于这种动物状态,处于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是所谓的“女野蛮人”。自然状态下的女性的生育和母亲身份也只是本能地发挥大自然安排的功能。这个功能也许产生了与男性对孩子上的不同的感觉,即相较于男性对孩子的冷漠,母亲可能会由于习惯而觉得小孩可爱而喂养他们,并进一步产生更多的母爱。[8]89即使这样,也没有改变女人作为女野蛮人的本性。此时的两性差别仅仅是雄性与雌性的差别,而不是卢梭后来描述社会中的两性在气质上的巨大差异,即男性积极主动,身体强壮,女性消极被动而柔弱娇羞。所以,对自然状态下的两性最适合做这样的描述,“就一切跟性没有关系的东西来看,女人和男人完全是一样的;她也有同样的器官、同样的需要和同样的能力;身体的结构也是一样的,身上的各个部分和它们的作用也是相同的,面貌也是相象的;不管你从哪一方面看,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大小的差别罢了”[1]527。
所以,在纯粹自然状态的设定中,卢梭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存在身体差异,但这种差异影响微小,即使是女野蛮人的母亲身份也不足以造成女性的弱势而产生依附性。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和不平等关系在纯粹自然状态下不存在,在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的过渡中才产生了人类精神的不平等。
(二)第二自然状态下的原初家庭
为了规范引导人类中的两性关系,通过爱情和婚姻联结完成种族繁衍的目的,卢梭在第二自然状态树立了两性分工合作的模式,为社会状态中的两性关系提供了自然权威。这个时期还处于自然状态之内,文明社会之前,但是人类生产工具有了大改进,生活方式也相应变化,语言、情感和理性逐渐形成。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第二部分一开始,卢梭说谁第一个圈起了自己的土地,并获得承认,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但是“私有观念不是一下子在人类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许多只能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的。人类在达到自然状态的终点以前,需要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获得很多的技巧和知识,并把这些技巧和知识一代一代地传授下去……我们不得不追溯到更为遥远的时代……”[8]112私有观念是家庭生活的一个后果,是在自然状态中就有了先行观念的萌芽的。
家庭的诞生是由于卢梭所谓的“第一次变革”——固定居所的发明。然后,丈夫、妻子、父母、子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习惯,使人产生了人类所有情感中最温柔的情感:夫妇的爱和父母的爱,每个家庭变成了一个结合得更好的小社会,因为相互依恋和自由是联系这一小社会的唯一的纽带。”[8]116
由于这是前社会时期,没有社会状态中的腐败性关系,又是人类最幸福的时期,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权威。这样看来,男女劳动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由于劳动分工只是在家庭范围,并且被“人类情感中最温柔的情感”所调节,所以,在这个小社会里,没有产生统治和压迫,而只有因为男女两性的自然差异而产生的分工不同,而且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好处——他们在共同协作抵御野兽方面更强大了。
但是女性主义者如米拉·摩根斯顿(MiraMorgenstern)提出了一些问题:“卢梭从未说明为什么女人会同意家庭的观念,以及根据性别所做的劳动分工。通过这种新的安排,她们能够得到什么呢?……显然……那些鼓励这种劳动分工的人把这个看作是自身获益的一个很大机会。而且,家庭的诞生是由于男人作为一个更强的一方建造了房子的结果。”[9]228
米拉·摩根斯顿(MiraMorgenstern)认为女人家居是以强迫性的手段来实现的,但是伊曼努尔·赛凯里(Emanuele Saccarelli)对这种女性主义者的过度敏感提出了反驳。在卢梭那里,自然状态里群体性通过暴力实现压迫是不存在的,而且那时的男性也无法预见后来的男权社会,又有什么动力去这样做?但是赛凯里稍后提出应该把女性主义的投诉进行性别角色反转,因为卢梭认为,真正被设计陷害的是男人,女性天生的狡诈以及对男性激情的刺激,使得女人能够通过隐秘的操纵手段来实现家庭的组建以利用男性的力气,弥补女性天生的柔弱。卢梭的确认为,男人比女人天然地试图避免依附他人,尤其是依赖于另一个性别。他认为妇女生理上就是柔弱的,自然有必要社会化;她们不可避免地要依赖男人,所以她们会引诱男人去依赖她们。
但是这样的角色逆转是否在第二自然状态中就发生了呢?如果如赛凯里所说,卢梭把女人与堕落联系起来,正如基督教中夏娃是导致人类被赶出伊甸园的女人一样。这种对女性主义解读的逆转,想要回应的是卢梭对腐败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女人的指责。但是,卢梭似乎没有必要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明面上恭维谄媚而实际上反对的方法。因为他在其他地方直接明确表达了社会中女人滥用天赋,他直接批判腐败社会中的女人奸诈、虚荣、空虚,把男人圈在房间里变得日渐衰弱。如果原始家庭的诞生是由于理智都刚刚萌芽的女野蛮人对男野蛮人的操纵,那就说明女野蛮人比男野蛮人的理智更胜一筹,这就显得突兀而不合理了。
卢梭的确认为“狡黠是女性的一种自然的禀赋,我深深地相信所有一切自然的倾向其本身都是很正当的;我认为,我们也应当象培养她们的其他的天性一样地培养她们的这种禀赋,问题只是在于怎样防止她们滥用这种禀赋。”[1]549
所以,即使原始家庭的诞生有女性狡黠的因素,卢梭也会认为,这是正当的应用,是对人类有益的。而男野蛮人也没表现出反抗,那么这里至少不存在不合理之处。卢梭说“相互依恋和自由是联系这一小社会的唯一的纽带”,而且这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一种状态”。卢梭批评洛克等人把社会状态中的事实误以为是自然状态中的情况,他自己又怎么会犯同样的错误,用社会状态中女人的行为来说明自然状态中的女野蛮人的行为呢?情况应该相反,他要用自然状态的推理来说明事物的性质,那么自然状态下的两性关系就构成两性天然秩序在社会中的形态的部分依据。
所以,可以推定原始家庭的组成一定是以平等双方自愿同意、互惠互利为基础。但是,这里虽然有了婚姻契约的影子,但两性关系却是松散的,也尚未固定在婚姻形式之中。赛凯里给出的证据就是接下来的话:“青年男女居住在毗邻的小屋里,基于自然的要求而发生的临时关系,继之以日益频繁的来往,不久就变成另一种同样亲密而更为持久的关系。”[8]118这更加说明了上述女性并不是原始家庭创立的操纵者,因为此时性对象尚未固定,男人也没有付出绝对的自由的代价。婚姻制度或者今天的一夫一妻制等强制性社会规范在原始家庭中尚未确立,他们之间只是由于固定居住的习惯而导致人与人频繁接触,产生了关于美丽、才德等观念和比较的心理,这才会激发偏爱的情感。刚刚产生的精神上的偏爱增加了满足欲望的难度,人们之间容易表现出嫉妒、虚荣心理以及冲突行为。所以,卢梭看到最初的甜蜜家庭生活潜藏着愈来愈紊乱的威胁,也预示着社会状态的最终产生。
(三)两性劳动分工的形成
家庭产生之后,“于是,在男女两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最初的差别,在此以前,男女两性本来是只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从此,妇女便经常家居,并习惯于看守小屋和孩子;男人则出去寻找共同的生活资料。由于得到了一种比较舒适的生活,两性都开始失去一部分强悍性和气力。虽然,每个人单独战胜野兽的力量不如以前,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比以前更便于集合起来共同抵御野兽了。”[8]116
而男女两性原来同样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最初的差别,这种差别意味着抚育幼弱和老人方面,女人承担了大部分工作。这种分工并未导致女性被隔离在家庭中成为依附男人的一方。原始家庭中出现的性别分工渐渐固化,加上不断加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不平等才导致了后来两性真正社会性别化并产生压迫关系。这个判断在下面的论述中得到了印证。这种两性劳动分工合作的形成,按照卢梭所说,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习惯,或理性(如果那时不完善的判断与选择也可以称为理性的话)的选择。那时的人“仅从事于一个人能单独操作的工作和不需要许多人协助的手艺的事,他们都还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并且在他们之间继续享受着无拘无束自由交往的快乐。”[8]121所以,他们的工作尽管有了差别,但两性之间,和同性之间从事的还是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或者临时合作,后可完全解散的合作,如渔猎、狩猎、采集,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当“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食粮的好处”这一巨大的变革,所以卢梭说“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8]121
所以,最初的家庭所产生的形式,存在的环境都不会造成两性之间的压迫或强制。这个阶段,可能如赛凯里所说的,对于卢梭来说,是一个在本能和理性,穷困和富裕,独立和专业化,自由相爱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男性和女性特质之间的构成可接受的妥协。在后一种意义上,这种不同或相反特性的混合与均衡时期——“世界的青春时代”——是两性产生性差别初期雌雄同体的孩子。[10]496这种形式的均衡性不同于自然状态下野蛮人完全在自然律法下,欲望与需要之间的平衡。第二自然状态下的均衡性更为复杂,涉及的要素也更多,但是整体上遵从“中庸”的原则。使得卢梭认为这种状态极不易发生变革,而且也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一种状态,而现代发现的野蛮人的事例,也证明了这个状态可以停留的时间很长。
可见,这是卢梭所怀想的理想生活的起点,也是他所抨击的社会表面进步而实际上退步之前的一个点。如果说对于现代腐败社会能够真正做什么矫正的话,卢梭最可能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寻找希望。当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以理性个体作为自由大厦的主体的社会,卢梭预见这个大厦的地基就是不稳固的。原子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社会的黏合失去了真正的基础,卢梭希望用家庭这个分子来代替原子,经过家庭的缓冲,原本由自私驱动的孤立个体才能有希望转化为一个道德个体。所以,对于卢梭而言,要为现代社会找到一个有强劲生命力的自然基础,形成良好的习俗,就要阐明“我们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由肉欲而过渡到道德观的,是怎样由粗俗的两性结合中逐渐产生温柔的爱情的法则的。”[1]532在这个批判腐败社会与再建新风俗的双重路线中,家庭一方面作为抵御不良风俗的堡垒而与公共领域划定界限,另一方面家庭又作为改革的前哨,需要与公共领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这种张力之下,为保证“公民们的共同幸福和共和国的荣誉”,女人要做“善良风俗坚贞的守卫者,人类和平的良好纽带”。[8]61所以,卢梭说,“我远不认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本身是一桩坏事。……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如果对统治着另一半人类的这一半人给以更好的教育,这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利益。”[11]46
三、卢梭性别秩序理论对现代政治治理的启示
上文说明最初的自然情感及家庭制度与国家之间存在必要的联系,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公民教育认可和转化这种家庭的爱。既然家庭生活是抵抗不良风气毒害的最好良剂,培育孩子成为新公民就需要男女分开活动,女人被设定为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这样才能形成既有隔离又有互动的关系。卢梭从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和个人主义立场推出不一样的社会人,从自然的两性结合中推出道德义务,用家庭这个分子来改造原子化的自我主义。卢梭的思想有利于我们思考公民教育方案,思考在一个传统断裂的年代,在“个人主义造成的普遍的漠不关心”[13]894的世界,如何培育一个健全有人性的个人主义者。这个个人主义者首先要能够履行人类基本的伦理义务,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自由并承担自由选择背后的责任和义务,能够进一步走向社会成为遵纪守法、对社会有益的人。当家庭与社会结构的道德规则实现真正联结和良性互动,个体的道德训练才能准备好适应社会条件的要求。所以,适当组成的家庭将是培养个人热爱自由美德的真正的学校。
经过家庭道德训练的个体进入社会之后能够更理性地服从法律的权威,因为他们的自主和对权威的服从已经调和成一种习惯。“在法律统治公民心灵的政体之外,绝没有良好稳固的政体。”[12]38卢梭对法律进行了分类,在政治法、民法、刑法之外还有第四章法律“风尚、习俗,而尤其是舆论”,“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者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4]70第四种法律是前三种法律存在的基础。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一个自由社会需要民情,而社会民情是由妇女创造的。[13]739
看起来妇女可以成为共和国道德舆论的策源地。她们在行使某种权力,在原则上、功能上不同于男人直接掌握政治权力。我们还要看到,公意的产生与运用需要女性提供一种健康的道德能源。女性能够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却不能直接参与公意转化为法律条文的政治过程。的确如此,这就是《社会契约论》实际上给女性的权力所安排的位置。女性的限制性角色背后是家庭与政治的相互渗透、道德风俗的良性循环,这实际上模糊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分界线。这种二分已经在培育合格公民方面表露了缺陷,它容易导致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相互推诿、脱节和冲突的现象。
他的社会蓝图不是资本主义商业体系,而是以农村农民为主的自给自足、贫富差距很小的农业共和国模式。在农业经济体系中,女性也参与农业生产和农作物交易活动,她们本身并不处于经济上思想上依附的状态,因而也不会因为不直接参加政治军事生活就受到男性全面的压迫。这样的环境限制使得卢梭的方案无法在现代工业社会加以推广。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即使古代共和国公民德行无法在现代复制,两性关系依然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关系,如果政治治理要有一个良好的道德风俗基础,就不能忽视两性激情和家庭情感的力量。
[1][法]让-雅克·卢梭.爱弥儿 -论教育[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法]让-雅克·卢梭.卢梭散文选[M].李平沤,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3][法]让-雅克·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法]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Schwarts,Joel.The Sexual Politic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6]Bloom,Allan.Love and Friendship[M].New York:Simon&Schuster,1993.
[7]让·斯塔罗宾斯基.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吴雅凌,译.刘小枫,陈少明.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8][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东林,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9]Morgenstern,Mira.Rousseau and the Politics of Ambiguity:Self,Culture,and Society [M].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6.
[10]Saccarelli,Emanuele.TheMachiavellian Rousseau:Gender and Family Relations in the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of Inequality[J].Political Theory,2009,37(4):482-510.
[11][法]让-雅克·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法]让-雅克·卢梭.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M]//刘小枫.政治制度论.崇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1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下[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