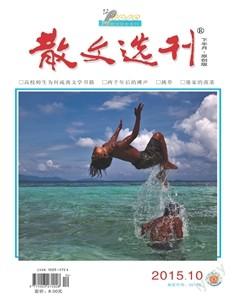幸福大合唱
朱桂嫦
“珠——珠……”几声清脆的呼唤声穿过屋顶上层层缭绕的炊烟,从一座客家大屋里传出来,打破了山村清晨早饭前的沉寂。
那是我母亲唤鸡回来“开饭”的呼叫声音——客家话管它叫“遛鸡”。这声音清脆、嘹亮、悠扬,听起来非常悦耳,从我记事时候起便一直在我的心窝里回荡,甚至渗进了我肌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母亲是典型的勤劳妇女。她每年要养两三窝鸡。每窝鸡大约20多只。从早春开始孵第一窝蛋,到夏收前,第一窝孵出来的鸡已“成年”了,每只少也有二斤左右;这时,第二窝鸡又出世了。到第二窝鸡“成年”后,秋收已近,转眼就到冬至。母亲接着就要着手孵第三窝鸡并考虑这些大大小小的鸡的用途出处:那只大阉鸡用来过年拜祖公,那几只肥鸡用来春节吃用,那只大公鸡和那几只母鸡留种,那几只鸡姑娘给祖父母补身体……农谚说,“重阳狗子冬至鸡”,冬至开始,这些鸡就要陆续为人民服务了。而冬至前,是鸡最多的时候。只要母亲“遛鸡”声一响,鸡们就四面八方闻声起舞。那场面有如战士们听到了集合的号声后的情景一样:敏捷、迅速、一致。
如果把这几十只鸡当作战士,我想,那母亲就是当之无愧的司令了。她当鸡司令,负责着鸡们一年的俸禄和健康成长。旧时,农村喂鸡主要靠的是糠饭。糠是把谷子做成大米后的附制品。这里有砻谷、踏米、筛糠、风米等一系列劳作。我家人口多,上有祖父母和父母(父亲在城里做生意),下有我们八个兄弟姐妹,所以,母亲每次做米都得一整天。做出来的糠也差不多有米那么多。母亲安排生活能精打细算,她用糠养鸡又喂猪。我家养的鸡总比其他人家养得多。只要我一走到外面去,到处都能见到我家的鸡。由于鸡多,四散觅食,所以母亲“遛鸡”时就先要拉高声调和拉长拍节,既响亮和悦耳,又婉转悠扬,令大小远近的鸡们都能听见。谁只要听到了这种“遛鸡”声,就立即能判断遛鸡的人肯定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健康农妇!邻居肖伯婆“遛鸡”时只用低调的“哆、哆、哆”几声,几只鸡就到齐了;她的媳妇曾达娘的遛鸡声就像母鸡下了蛋后发出的声音那样:“咯、咯、咯”。她们的家庭生活相对比较困难,所以,养的鸡不多,遛起来一点也不费劲。
小时候,我喜欢站在母亲旁边看她喂鸡。母亲喂鸡时,端一张凳子坐在盛糠饭的盆子旁边,一边舒心地跟鸡们说话,一边搅拌糠饭,直到盆子里的糠饭被吃得干干净净,鸡们散去,母亲才靠在凳背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唉,母亲实在太疲劳了。除了喂鸡,一天到晚我再没有看见她坐在板凳上休息过。可不,偌大一个家庭,一日三餐,里里外外,田头地尾,耕田种菜,挑水担柴,喂猪养鸡,进城赴墟,全靠她一人担当。她是世间最忙、最累、最慈爱的母亲。我多么希望她能坐在凳子上跟鸡们多聊一会儿啊!
1960年,母亲生病,我曾经回去探望她。那时候,人民公社的大饭堂已经揭不开锅。社员们都饿得面黄肌瘦。母亲也患营养不良,躺在床上起不来。这时候,她多么需要用鸡来补补身体啊!可是,我拿钱叫弟弟找遍了几个墟镇,连一只鸡蛋也见不到。农贸市场冷冷清清的。那几年,农村自耕自足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人们自由创造财富的权利被计划经济剥夺,整个社会都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全民挨饿了几年,鸡鸭都几乎绝迹!那几年,人们再也听不到我母亲那歌唱丰衣足食农耕生活的“遛鸡”声了!
1989年,我再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乡变了:乡道宽阔而笔直,道路两旁到处有成群结队的鸡鸭;家家户户住楼房新居,屋里都有电灯电话。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又有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了。母亲虽然已经80多岁,但仍然精神矍铄。她闲不住,总要帮家里做一些家务。其中,养猪喂鸡便是她的内行。那时,我在农村的弟弟已经盖起了新楼房,住地宽阔,院子大,母亲养鸡的本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养的鸡能站满整整一个院子!
早晨,我又能听到久违的“遛鸡”声了。并且,这种高音长拍的“遛鸡”声不止从母亲的喉咙里发出,还从左右邻居的屋子里发出来,形成了大合唱。啊,农村已经再没有穷人了,家家户户都养了许多鸡。正是五谷丰登,丰衣足食,六畜兴旺啊!
“珠——珠——珠……”“遛鸡”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啊,这是世界上最动听、最悠扬、最优美的幸福大合唱!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