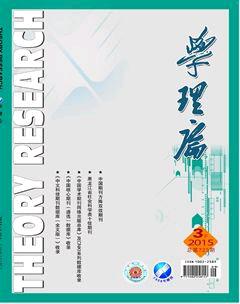谈谈新学术初版本的认定、研究与收藏
摘 要:围绕着“新学术初版本”的认定、研究与收藏,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与探讨,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更多研究者与收藏者的兴趣。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著作的版本问题,能够起到一些有益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学术著作;学术史;初版本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97-04
从1945年开始,唐■以书话的形式研究中国新文学的版本问题,并于1962年结集出版了《书话》,1980年又增补结集为《晦庵书话》出版,奠定了新文学版本研究的基础。1986年,朱金顺出版了《新文学资料引论》,建立了新文学版本研究的框架。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与爱好者人数众多,人们对于新文学初版本的认定、研究及其收藏,早就有了约定俗成的共识,陆续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对于同样可能更加繁荣的新学术初版本,却一直受到冷落。本人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又有点考据癖与收藏癖,尤其致力于近现代著名学者的文稿信札及其著作初版本的收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于有关的问题,慢慢有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陆续地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随笔式的书话札记。以此作为基础,围绕着“新学术初版本”的认定、研究与收藏,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探讨,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研究者与收藏者的兴趣。
一
谈到新学术初版本,首先要确定所谓新学术书籍的时间与性质,划出作者和论著的大致范围。
我们知道,新文学书籍时限的界定,一般是指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这段时间。而我对新学术书籍时限的界定,时间还要再放宽一些,指的是20世纪10年代新文化运动爆发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的这段时间。正如新文学有其特定含义一样,我对新学术的内涵也限制得比较狭窄,指的仅仅是在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出名的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或者教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所撰写的一批中国文史哲著作。
这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或者教授,受惠于所处的时代,称得上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他们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重新整理国故,引进西方的学术研究规范,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划分了哲学、史学、文学等学科门类,确定了内容具体明确的学科体系与方法论,撰写了一批具有标志性原创性规范性的奠基式的学术论著。像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划时代的论著,指引着学术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成为有关专题学术史研究回顾的源头。无论该学科如何发展下去,它们的价值都会一直存在,后来的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它们另起炉灶。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已经成为现代学术经典著作。
这一批优秀专家学者或者教授的论著,大多出版或者发表于20世纪10至40年代。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离开了中国大陆,继续着他们的学术研究。至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其中一部分的确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研究方法,一部分想改变却发现其实改变不了,另一部分则仍然坚持他们原有的研究风格。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一般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为止。而他们的某些著作,到了80年代才以遗作的形式首次问世,例如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因此,将新学术初版书的时间确定20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是比较合适的。
可以列入作者范围里的,主要有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朱希祖、冯友兰、汤用彤、钱穆、吕思勉、杨树达、顾颉刚、傅斯年、李济、董作宾、蒋廷黻、雷海宗、李剑农、向达、冯承钧、陈恭禄等人。如果说得具体一些,基本上可以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为中心点画一个圈,加进去各个著名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系的教授,大约有一百余人。至于可以列入论著范围的图书或者论文,数量就太多了。依靠有关的图书论文目录索引分析,估计起码有数千种,而其中称得上是经典的,也有几百种。
二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主要在于学术影响比较大,是某一方面阶段性的权威之作,拥有比较多的读者。因此,曾经多次地出版,进而形成自己复杂的版本体系,也就成为优秀新学术论著的一个主要标志。例如,《论再生缘》一书的学术价值在于,该书体现了陈寅恪后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风格,部分地解决了《再生缘》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反映出陈寅恪某些独特的思想与精神;而它的收藏价值则在于,该书多次以特殊的方式重版,流传过程曲折且富有传奇色彩,因而在中国现代学术著作版本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954年春季,陈寅恪完成了《论再生缘》的写作,并且自费油印了一百○五本。这一油印本为线装一厚册,设计得古色古香,牛皮纸封面,上面写着“论再生缘”,“莹题”,明显是陈夫人唐■的手迹。全书长24.5厘米,宽16.5厘米。竖排繁体,刻写得异常工整而潇洒。每页18行,每行38字。全书每两页标明一个汉字数字页码,因此正文一共78页,汉字页码却只有39页。折叠装订,蜡版刻印。在封面之后和封底之前,均有空白纸一张两页。另外,还有校勘表一张两页。《论再生缘》的油印线装手刻本,不仅顺理成章地成为《论再生缘》的初版本,而且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学术著作油印初版本中的精品[1]。
《论再生缘》的一部分油印本,很快就通过特殊的渠道,辗转流传到了境外。大约在1957年,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模仿《论再生缘》的印刷方式,重新制作了《论再生缘》油印线装本。1958年,余英时在香港《人生》杂志上发表了《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在余英时的联系安排之下,香港的友联出版社1959年将《论再生缘》出版发行,友联图书编译所还在书前加上了《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在1961年5月,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一文。从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接二连三地一共发表了9篇有关的文章。一些学者也陆续参与讨论,对郭沫若论文或响应或商榷,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再生缘》热。①在1963年,台湾大学中文系重新制作了《论再生缘》的油印复制本。1970年7月,台北的地平线出版社将《论再生缘》一书出版,书后附有牟润孙的《敬悼陈寅恪先生》、俞大维的《谈陈寅恪先生》两文。1970年8月,香港友联出版社又将《论再生缘》再版。除了继续收录初版时那篇《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之外,编者又加写了一篇《再版题记》。1975年1月,台北的鼎文书局出版了《再生缘与陈寅恪论再生缘》。前半部分是排印的《论再生缘》,后半部分是影印的《再生缘》。
中国大陆最早公开发表或者出版《论再生缘》,已经是在陈寅恪逝世9年之后。当时以“陈寅恪遗稿”的形式,将《论再生缘》发表在1978年7月、10月上海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八辑上。尽管这一版本增收了陈寅恪以后续写的《<论再生缘>校补记》,但是全篇被删掉了不少的文字。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寅恪文集》时,将《论再生缘》收入《寒柳堂集》当中,但是与《论再生缘》油印本或者香港友联版的文字略有不同。到了2001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陈寅恪集》时,仍将《论再生缘》完全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寒柳堂集》版排印[2]。
三
因为新学术书籍的版本比较复杂,所以对于收藏者来说,毋庸置疑是时间最早的初版本最有价值;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尽管书籍的哪一个版本都重要,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初版本最为重要。版本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讲究书籍的初版本,注重文献的原始价值,是对研究者最起码的文献学要求。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旦出版或者发表,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存在,也就作为学术论著的原貌固定下来,自动成为以后研究者研究的原始材料了。由于各种既复杂又微妙的因素,特别是由于有了新资料或者新观点,甚至可能是借鉴了以后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至少是受到以后其他人研究成果的某些启发,作者常常会倒过来对以前的论著做出某种程度的修改补充,结果可能显得更加完善更加丰富,当然也有越改越糟的情况出现,因此形成文本各异的不同版本。我们如果要评述某些人物的学术贡献或理论创新时,只能使用有关论著的初版本。有的研究者没有把握好里面的分寸,在撰写某些人物的传记作品时,依据他们在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修改过的版本,来推论有关著述在当初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这样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可靠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四
既然新学术初版本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就要来考察一下新学术初版本的内涵与外延。我收藏的新学术初版本不能算多,但是通过各种途径目验过的,数量却不少。收藏的与看见的加在一起,大约有500种左右。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总结分析,可以归纳出三个有意思的特征:
一是在新学术初版本中,有不少是讲义本。新学术主要涉及的是文史哲等基础文科,而从事基础文科研究的学者,除了是在高等院校教书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职业可供选择。因此,大学教授在论文或著作完成之后,往往会先以讲义本的形式问世,在课堂上尝试使用,再听听社会上的反响,如果大体上过得去,那就修改补充一下,交给出版社出版发行。所以新学术名著的初版本,很多都是讲义,其实并不奇怪。不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初版本是北京大学的讲义,而且连陈寅恪的学术名篇《支愍度学说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四声三问》的初版本也是清华大学的讲义,以后才分别发表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清华学报》上。
二是在新学术初版本中,有不少是油印本。所谓的油印本,是指用蜡纸、铁笔(或字码机)、油墨、钢版制作,再用油印机印刷出来的书籍和文献资料。油印技术在清末传到中国以后,应用就十分广泛,不少重要书籍或资料,最先以油印本形式出现,甚至永远以油印本的状态存在。目前有一些藏书家还瞧不起油印本,然而从20世纪初期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不少著名学者的讲义和著作,最初都是以油印本的形式问世的。因此,许多专家教授的学术论著油印本,不仅是一种版本,而且常常是初版本,因为油印是一种便于征求意见而采取的印刷方式。有意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新型打字机特别是电脑技术的迅速普及,油墨印刷技术完成了它的使命,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恰好算得上是与新学术初版本的时间范围相始相终。当然,由于油印本的存世量还比较大,因而并不是所有的油印本都值得收藏。对于油印本的收藏,还是要特别讲究一些,应当注重初版或者精品,尤其油印初版本中的精品,内容丰富,时代感比较强烈,装帧美观大方,刻写印刷精美漂亮,具有较高的版本学价值。例如,辽宁教育出版社在1998年编辑出版了《春游纪梦》一书,收录了张伯驹的著述一共六种,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书画目录著作《丛碧书画录》。在收录《丛碧书画录》的时候,尽管明显是来源于油印线装本,但却没有在书中注明是依据油印线装本排印,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疏忽。《春游纪梦》这一版本的印数达到了一万册,比较容易找得到。因此,如今人们大多是从这本书里读到《丛碧书画录》的。其实,在张伯驹的生前,曾经印行了《丛碧书画录》油印线装本,而这就是该书的初版本。这一油印线装本,浅蓝色封面,31叶,62面,长25厘米,宽15.4厘米,蜡版写刻,字迹工整。书前书后均无版权页,但是开头的序言落款是壬申(1932年),正编的最后附有跋语,说明书画录撰写于壬申(1932年)至己亥(1959年),而补遗的最后亦附有跋语,注明是庚子(1960年)写毕。因此,可以断定该书印行的时间大约在1961年或者1962年,但是印数不详[3]。
三是新学术初版本中,有不少是论文集,而论文集中的论文都曾经先发表过。因此,刊登论文的报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初版本。和专著相比,当时知名学者可能更看重论文,认为论文更能看出自己的学术水平。等到论文数量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结集出版,等于是一部专著问世。陈寅恪的名作《秦妇吟校笺》,于1940年4月自刻于云南昆明,由他的夫人唐■题签。该书一共23页46面,长21厘米,宽14厘米,厚0.5厘米。但该书却不是初版本。此书最初作为一篇论文,以《读秦妇吟》为题发表于1936年10月的《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上。顾颉刚在1963年出版的《史林杂识初编》,是他的一部学术名著,来源于1949年的《浪口村随笔》油印线装本,而《浪口村随笔》中的文章,先是分期发表于齐鲁大学的《责善》半月刊上。所以,《责善》杂志上刊登的才是初版本。
五
研究与收藏新学术书籍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于研究来说,主要注意的是论著的内容,而对于收藏来说,在重视内容的同时,还要讲究作者的名气大小,讲究书籍的刻印是否精美,特别是要讲究封面封底、版权页、纸质、装订、破损程度等外在的东西。
《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是顾颉刚的一部学术名著,是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具体实践,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该书的初版本就是顾颉刚于1928年在中山大学写成的《中国上古史讲义》,当时有油印本,但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以此为基础,顾颉刚于1930年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一课,并重新编写了《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的油印线装本。这部油印线装本,长20厘米,宽14厘米,厚2厘米。但是它制作得比较随便,封面封底均为空白,没有版权页,没有书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只有在序言的最后署上了“顾颉刚”三个字,才让人们知道该讲义是顾颉刚所作。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线装油印本同样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初版本。但是《浪口村随笔》线装油印本却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全书长27厘米,宽19厘米,竖排繁体,蜡版写刻,线装一厚册。封面上注明“浪口村随笔”,“顾颉刚著”。在每页折叠处,根据书中的内容,分别刻有“浪口村随笔”“浪口村随笔序”“浪口村随笔目录”、“浪口村随笔卷×”“浪口村随笔补遗”字样。全书包括序言和目录一共是150页,大约有19万字,当时仅仅印行了一百册。从学术价值上说,《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油印线装本高;但从收藏价值上说,《浪口村随笔》油印线装本高[4]。
代表陈寅恪学术成就的著述,无疑应是《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因为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1944年12月在重庆初版)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5月在重庆初版)的初版本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均为是土纸本,不仅纸墨不佳,而且印制粗劣,加上保存亦不易,所以流传到现在,品相完好的很少,远远不如他的另一部名著《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本那样受到收藏者的重视与欢迎,它们之间的市场价格差距极大。《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本开本阔大厚实,由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于1950年11月出版,用传统线装形式印刷装订,显得古朴淡雅,因而极受推崇。从学术价值上说,《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初版本高;但从收藏价值上说,《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本要高出很多。
在油印本当中,手刻的本子优于打字的本子,线装的本子优于钉子装订的本子。陈寅恪大约在1954年交给高等教育部代印了一部《两晋南北朝史》油印本。该油印本为小16开本,封面上部有三行字,上面是注明“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正中是书名“两晋南北朝史”,下面是署名“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编”;封面下部则写着“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代印”。目录页以及正文中,每页天头皆书刻有“两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字样。全书一共是251页,大约有17万字,竖排繁体,蜡版刻印。书中的字迹,全部用隽秀楷体,一笔一画,写得异常工整,像打字印刷出来的一样,几乎看不出是出自于几个人之手。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即它不是线装本,而是用钉子装订的本子[1]。
《雪鸿山馆纪年》一书,本来是清人赵守纯的自编年谱手稿,一直没有交付雕版印刷。中国广州市古籍书店于1958年将赵氏的手稿本,予以油印复制,线装问世。《雪鸿山馆纪年》的油印线装本,一共上下两册,每册长26.5厘米,宽17厘米。每一页9行,每一行38字。全书每两页标明一个汉字数字页码,因此正文一共78页,汉字页码却只有39页。该书采用的是折叠装订,竖排繁体,蜡版写刻。在蓝色封面之后和蓝色封底之前,均有空白纸一张两页。其实,20世纪50、60年代留下来的油印线装本数量数不胜数,一般都不会受到古籍收藏者特别的注意。然而《雪鸿山馆纪年》的油印线装本却有所不同,它一直受到收藏爱好者的关注与追逐,甚至还曾经出现在中国一流文物大公司的古籍珍本善本拍卖专场上。其中的原因,除了《雪鸿山馆纪年》的制作特别精美、纸质与刻写均为一流之外,还因为《雪鸿山馆纪年》原稿上有不少的涂改之处。为了保持该书的原貌,《雪鸿山馆纪年》油印线装本将所有的删改部分完全照样复制,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原作的本来面目。这在当时油印线装本的刻写中,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5]。
六
总而言之,新学术论著的初版本,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或者爱好者,能够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目前最重要的是,相关学者通过一定的分析探讨,就新学术初版本的认定、研究及其收藏,达成一些应有的共识,尽快出版《新学术版本概论》之类的工具书籍,以便在这一领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蔡振翔.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线装本[N].藏书报,2011-08-15.
[2]蔡振翔.陈寅恪的《论再生缘》香港友联版书后[J].加拿大《文化中国》,2009(4).
[3]蔡振翔.张伯驹的《丛碧书画录》油印线装本[N].藏书报,2013-05-27.
[4]蔡振翔.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油印线装本[N].藏书报,2010-08-02.
[5]蔡振翔.赵守纯的《雪鸿山馆纪年》油印线装本[N].藏书报,2013-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