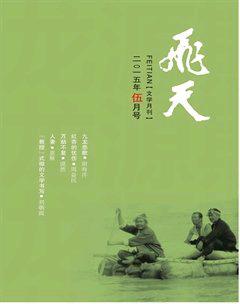一幢布满雕花的木屋
姚明今
徐小英终于将我带到了她的老屋。进了院门的前方是一排正房,左手边是一排厢房,紧贴着进门的右手边用一堵围墙与邻家隔开,沿着围墙种着一排的葡萄树,葡萄树上挂了些仍还青涩的果子,看来成熟还需要些时日。一幢很普通的院落,因为久不住人多少有些冷清。风从西面高处的山坡吹来,叶子在风中轻轻地飘动。
自从上学离开少年时居住的西部戈壁,在长安城中待下来,一晃已二十余年了。时间真是一个改变人的东西,这些年,蛰居喧嚣的都市,戈壁旷野已经成为一种模糊的记忆,也已经习惯了无风的日子,偶尔去山间走走,一切变得是这样熟悉又陌生。此次过天水来到陇南,看着沿途的山野,在踏进院子的那一刻,恍然间有一种时空的位移和交错,踩着院中用砖砌成的小径,我才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庭院了。在这样的庭院中间四下环顾,对于现在的我来讲,已经是一个很珍贵的体验了,这种体验年轻的时候当然不觉得,但是对已经渐渐迈入中年的人来说,有这样的一所院落,对于生活和生命来讲,似乎意味着太多的东西。
正房和厢房朝着院子的一面墙用木头砌就,砖石的基座上是木质的窗棂和墙面,上面还雕了很多的小花。这使整座建筑呈现出中国传统式建筑的韵味,也使原本孤陋寡闻的我多少有点诧异,原以为,只有在江南水乡才能看到这种木结构的民居,殊不知在西北的腹地,人们会为自己建造这样的建筑。看来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有一番道理。
传统的中国式建筑无疑应该有着既定的格局,虽然因为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先前的样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修改,但世间却存在着一种力量,在一切变与不变之间努力复原着原初的体验轨迹。在这个改变的东西之上,旧时的记忆顽强地将一切崭新的变化抹去,使那一切事物的旧时模样又渐渐清晰。
于是这眼前的庭院,不再是静默矗立的砖石木材堆砌成的建筑空间,当每一块砖瓦与每一片墙面开始苏醒,眼前的庭院变成心灵的归宿,镌刻成一种生命的印记,在心灵的深处铸造成一处庭院。尘封的大门会徐徐打开,庭院里会走进一个个身影,这一个个身影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熟悉,恰像我身旁几个一进门便开始忙碌的女人,以生命的温热来穿透寂静的岁月,为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轻轻拨动时间的罗盘。于是在那思绪的灵光开启处,就有了徐小英笔下充满着记忆的这许多文字。
一幢雕花的木屋
据徐小英讲,这幢房子是父亲执意要给她盖的。按照一般的习俗,中国家庭总是会给儿子盖房子,以使其成家立业,却很少听说要给出了嫁的女儿盖房子的,于是她极力推托,但是父亲执意要盖,于是房子便盖了起来。后来因为要去省城工作,丈夫原想把房子卖掉,最终因为儿子说这是姥爷给妈妈留下来的纪念,房子便保留下来,这便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很长时间没有住过人的屋子,在几个女人的张罗之下,渐渐地开始充满了生气。
冷艳孤傲的弗吉尼亚·伍尔芙宣称,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她这样讲当然是因为在她看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对于一个女性的独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想这种独立当然不仅仅指物质上的独立,更多的应该是指女人对自己心灵的守护。纵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因为才华横溢,从而备受男人们的呵护。不知道她这样的宣称,是因为拥有之后的感悟,还是因为缺乏而发出的悲叹。
然而在中国,在变动不定的新与旧的拉锯中,一切存在的形式都要遭受各种检视,曾几何时,喜欢盖房子也被视为中国人的一种陋习,而备受非议,但是到了徐小英的房屋,我才真正体会到一间老屋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对于房间的继承者来说,一间留存着记忆的建筑,往往就像一个记忆的储存器。岁月在不停地沉淀着,周而复始,然而当报时的钟声响起,往日如昨,一切的过往就像人的影子投射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而在某种程度上要接受这样一幢房子,又如同接受了一种授权,接受者既要承担起建造者赋予这个建筑的希望,也要承受着建造者一生所积蕴的失落,无论是希望还是失落,都会构成一种压力,越是珍视这种记忆的人也就对这种压力感受越深。而当这种感受需要表达的时候,文学便适时地出现。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徐小英在临近退休的时候,却要顽强地再次踏入人生的河流,重新咀嚼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当你读她的文章的时候,会发现在她的眼中,一切都是这样新鲜,一切又这样美好,正像一个出生的婴儿。每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都会得到一种崭新体验的滋润,这无疑是文学赋予徐小英的神奇造化。
因为以往的各种道听途说,甘肃总给人留下贫瘠的印象,这种先入为见的原因归根结底还在于各种各样的隔膜。而当你真正见到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所展现出来的惊人的坚韧以及对于生活的热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一种贫瘠的外表下有着难以想象的丰饶,这种丰饶,就像那荒野之下的矿脉,经过了岁月的剥蚀之后,一旦袒露在阳光下面,便会展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丽。
在一个美已经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时代,我们的感受也在慢慢地固化,最终变成为见怪不怪的漠然。然而这种板结在特定的条件下也会发生溶解,一种原生于自然的爱与热情无疑是这种溶解所发生的条件,而且还不需要什么炫目的形式与时髦的思想。环境越是艰难,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也就越发使人感动,正因如此,在一种相对艰苦的环境中,那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会无限地进行延伸,最终指向存在的深处,给人带来生命的感悟。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走进徐小英的老屋,听她娓娓道来她的所思所想的时候,老屋上的每一处挑檐、每一片瓦当,更有那木墙上所雕刻的说不上名字的小花,仿佛都在向人们讲述着它的主人为什么对生活如此充满热情,又为什么要这样痴迷地进行写作。临到末了,最终你会承认这是一幢具有魔力的房屋,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种神秘的东西,决定着一个人要做什么以及她该有着怎样的人生。
一个真实的建筑,一个一览无余的空间,却是主人精神的栖息之所。父亲、母亲、哥哥、奶奶、外婆、妹妹、婆婆,还有太多太多留在她的记忆里的人,他们如果一同走进这个屋子,这个房子应该人满为患了。但这样的担心似乎又显得多余,因为徐小英早已在记忆的世界为他们建造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大很大,足以使所有人在这个地方拥有一席之地,与这个房间的主人一同来讲述他们共同经历的悲欢离合。
父亲与哥哥的故事
如果用一幢房子来形容一个家,男人好像这个家的屋顶,无论披星戴月还是日晒雨淋,男人们的职责就是为了妻子儿女有一席安身之地,免受各种生命的恐惧。倘若时运相济,这个男人能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妻子儿女一个安稳富足的家,这已经是中国大多数男人的最高价值实现了。
在朴素的文字中,徐小英充满深情地讲述了父亲的一生,从少时丧父,由母亲养大成人,到出外学徒,从而支撑起一家的重担。1949年之后,公私合营,父亲还从事商业工作,因为精明能干以及奉公克己备受领导和同事的信赖。
徐小英总是提起父亲是如何的睿智,用她当面所说的话来讲,“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在给她修这间宅子的时候,告诉她,如果以后旁边修了马路,就可以推倒东面的墙,这些房子便可以成为门面房。而我们到的时候,一条新修的大马路刚刚在房子的旁边落成,对于我们这些天天皓首穷经不事生产的人来讲,一个乡村士绅的智慧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这很难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感叹,一个普通的乡村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智慧,如果能够使他们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施展自己的才干,我们的国家今天该有着怎样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徐小英父亲这辈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动荡不定之中,这些人大多数时候的谨小慎微,更多的表现为在一种危险的生活环境里的一种明哲保身,在一种无形的力量面前拼命收敛着所有的锋芒。
在一个家庭成分决定人的命运的时代,能够顺利地度过这个时代,无疑需要具备一种高超的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往往也意味着个人人格的扭曲,而且这些扭曲甚至也未必能使自身和家庭逃离巨大的风险。在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大形势下,整个家庭将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还是因为居住地的大队支部书记感念自己队部的家具都是从徐小英家充公而得,所以才将这家人留在了所在地的第二生产队。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改变了这个家庭随后的生命轨迹。人们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又忍不住对这个历史进行假设,如果那个时候,大队支部书记没有说这样的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很难不使人联想到,有多少的家庭因为同样的原因,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开始自己的人生。在社会平等的名义下,我们的社会不是让低就高,而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剥夺许多普通家庭的剩余财产,作为政治话语实现的形式,最终的结果却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在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中,支部书记的感恩实际上是一种立场不坚定的表现,但恰恰是这种不坚定,表现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所遵从的一种传统伦理。正是这种无意识中所流露出来的同情不由得令人感叹,不论主流意识形态对人的强制是如何地酷烈,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还是会通过传统伦理的形式表现出来。
人们也许会说,任何一个人要适应这个社会,话虽然不错,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真的想以某种理想来构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最优化的实现路径也要尽量使人尽其用,如果只是通过贬抑一个阶层来抬高另一个阶层,最终的结果就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到沉沦,我们在这方面无疑有着非常沉痛的教训。
从旧的时代过来的父亲竭尽所能却又如履薄冰地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找寻着自己的位置。而作为家庭的长子,徐小英的哥哥却为了一个新世界的梦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长子对于中国传统家庭来讲,无疑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他虽不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但却可以决定一个家庭在社会中所占的地位。根据徐小英书中的记载,哥哥的死是因为参加红卫兵的串联才留下了病根,为了一个现在看来毫无意义的梦想而搭上了性命,无疑也使哥哥的死蒙上了一些悲剧的色彩。徐家两个男人的生命轨迹,也是这一时期中国许多家庭生存状态的一个背景注释。
在哥哥的死因背后,也有着一个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这样来假设,如果当时的家庭条件再宽裕些,哥哥能够被送到一个具备现代医疗条件的地方,或许哥哥便不会离开;或者当地农村的医疗条件再好一些,哥哥也就不用只是服用那些疗效低下的中药,或许哥哥也就不会死去。然而这一切只是一种事后的假设,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偏远乡镇的普通家庭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在一种无助的懊悔中承受这一切。
哥哥的死无疑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个创伤可以从父亲如同遭受了命运诅咒般的重击上见出来,也可以从母亲绝望的哀痛中见出来,人们到了这个时候,才会认识到在命运面前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成了笨拙的应对,当社会巨大的阴影将家庭笼罩的时候,不管个体是多么的能干,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暗自祈祷,不要成为暴风雨过后那片坠入泥泞的叶子,因为任谁也无法挣脱一个时代所投射下来的阴影。
女人们的故事
如果我们说男人是一个屋子的房顶,我们可以将女人视为屋内支撑着房檐的柱子。她们虽不抛头露面,但是却支撑着屋顶在暴风雨中安然不动。尤其是当男人为一种无形的力量磨蚀之后,这个家庭的女人就必须更加地坚韧,这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错位。而双亲所遭受的打击也深深影响到了徐小英,或许是因为年轻,徐小英在短暂的惊慌和绝望之后,便鼓起了全部的勇气,这一刻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长子”。当一个家庭需要女人来支撑的时候,成功抑或不成功都会给人一种忧伤的感受。
哥哥死了之后,徐小英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源于她自身的坚强,另一方面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她努力想减轻父母丧子之后的悲痛,于是便承担起长子的责任。除了分担地里部分的农活之外,徐小英还要肩负起为家庭疏通社会关系的责任。在家庭面临下放到农村以及弟弟招工这件事情上,她的坚强干练也就成为了家庭的坚强依靠。我们不能说家庭的不幸反倒成就了徐小英,但严酷的社会现实的确让一个年轻的女性迅速成长,当家庭的根基摇摇晃晃的时候,她勇敢地站了起来,重新使这个家庭站稳了脚跟。父亲之所以在后来为她专门修建了一幢房子,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她视为家里的老大,这个老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大,而是事实上的老大。
当一个女性成为了家庭的依靠,这一切的变化,必然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这个过程可能在刹那间完成,也可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但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一切,无疑会改变其面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在这里我不禁产生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想法,当一个家族中女孩被当作男孩时,会逼使她极力地去改变自己,她会学着以男性的方式来说话和思考,而她模仿的这一个过程,也成为她与这个世界相处的独特方式。
西方女权主义者说,女性的写作总是女性化的,这是由她们的性别所决定的。我们姑且可以说,西方女权主义者这样如此强调女性属性的特殊性,目的是为了强调女性在与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竞争时也有着自己的优势。但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因为极度的贫困,中国的女性基本上都要承担起维持家计的责任,我不知道这种被迫的独立是不是符合女权主义者所宣称的独立,但我知道,这种独立背后有着多么大的付出。这种付出在一种环境中成为了习惯之后,也常常会使人回避男人并不比女人更加坚强这一事实。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作为女性作家,徐小英在不断地为自己建筑着一个屋顶,这里有她少女初长成时的记忆,有着其青春时期的梦想,有着她所爱着的人。当她下意识地觉察到这个屋顶并不像她想象的那般坚固时,她所做的就是使自己努力地撑开,极力地为自己以及她所爱着的人创造出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放得下父女之爱、兄妹之爱、夫妻之爱甚至母子之爱。这也是为什么在徐小英的笔下,男性会被有意识地与具体的空间隔绝开来,并给予无限的宽容的原因。
而这种已经养成的宽容,在面对女人时,则表现为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既怜悯亲近又在怜悯中抱有严肃的要求,这在她对待自己的婆婆、妹妹,以及其他相关的女性时都表现得比较明显。她在直接书写她们的故事时,既赞美她们的优点,也不放过描写她们的缺点。她在这里表现出的与其说是一种宽容,毋宁说是在感知自己的另外一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她在描写这些女人时,将其置于时间的流动之中,任凭时间之舟将这些女人载向人生的彼岸,就像看着自己的影子消失。人们常说,时间之于人来讲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它能够改变一切。其实她们还忘了,时间常常将那些没有变化的存在不动声色地送进了人们的记忆。
徐小英的散文给人一种这样的感悟,你不能不去追寻生活中的意义。看着她的散文我总在想,生命中总是存在着些什么,也正是因为这种存在使我们知道,这种人生不是过去之后也就过去了而不留下些什么。我们在这里既要感叹徐小英对人生惊人的热情,也要赞叹文字的魔力,因为只有用文字我们的生命才能闪光,才能将那些生活中所经历的苦难消融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徐小英作品中看到了许多生活的苦难,但相对于一般人所说的中国女人身上所具有的忍耐精神而言,徐小英会将这些经历转化为一种生命的智慧,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常常会听到徐小英在讲述自己的一段体会之后,会情不自禁地叹息:哎呦,咋这么好呢?
有时候我总在想,是徐小英对人生的体验方式成就了她的文字还是她的文字成全了她对于人生的体验方式?虽然我更倾向于前一种情形。但我又不能不赞叹语言的神奇。如果说男人掌握语言,更多的是为了表述他们对于人生一些大的命题的思考,那么女人掌控语言则长于从身边的琐屑小事开始最终进入了人生的内部,而这种进入的方式因为更加具体而微,也就使女性的作家常常会展现出一种令人恐惧的锐利。虽说文学的价值正在于或直接或隐晦地表达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总体性理解,但女性作家的优势在于她们能通过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便能感受到生命的整个轮廓。
其他人的故事
如果在对自己亲人的描写上,时代背景表现得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在对家族外人物的描写上,这些人物则被深深地烙在了时代背景之上。存在主义讲,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这个目光规定着人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种说法固然揭示了人们的相互影响性,但似乎又过高地估计了这种影响性。因为在实际的操作上,观察行为本身也有一个远近之分。从徐小英的文章来看,对于家族之外其他人的描写,因为站在一个较远的距离上进行观察,所以对这些所描写的人的认识就更加客观,而正是这种客观,也使事件和人物背后的时代得到了更加明显的展示。
《那个猪年的哭声》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徐小英的文字,看这些文字你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而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震撼,其原因正在于这些文字写出了现实中普通人的苦难。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种苦难不仅仅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例,而是具有真实的普遍性,唯其具有这样的普遍性,才真正体现了作者直面生活的文学态度。我一直在想,这种直面人生的态度应该是文学最一般的法则,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了一种勇气?更糟糕的是,在所谓选材和视角的名义下,许多人将文学纯粹变成了一种文字的游戏,更是背离了文学所应该有的责任。
传统的文学理论常常讲,写作者在选择题材的时候,要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题材,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典型性的事例,来更加深刻和全面地反映这个社会。而从接受者的角度上来讲,这样的题材,也可以引起读者更大的共鸣。但理论毕竟是理论,在执行的时候,更多的人还是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原则进行背离,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原本应该成为所有人遵循的原则,在现在的中国文坛上却成了稀有的存在的原因。
这也就难怪,我们会看到那些熟悉比例搭配的作家们,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文字技巧,对现实的题材进行剪裁。具体来讲,就是将所描写的对象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经过一种语言的化妆,其背后的背景也就被完全地弱化下去,于是作者所讲述的这段故事也就成为为说故事而说故事。时间一长,这些写作者将自己笔下的世界与现实混淆在一起,从而忘记了真实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的文字即使微言大义冠冕堂皇,其实也不过是一些漂亮的废话。
但是在徐小英这个“学习者”手中,另外一种视角或者说是态度则得到了直接的展示,一种实录的方法在她的手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对于她这种直观的写作方式,可能成熟的笔触会说这种直观是一种幼稚的表现,甚至会被批评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但正是这些“只看到现象的文字”贯穿了作者的激情和创伤,而这些贯穿了作者创伤和激情的文字又能直接勾起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这也是徐小英的文字能够给人以最大程度感受的原因。
对于有着真正文学使命的作家来讲,写普通人才是他们文字真正成熟的一个标志。人们一般会对自己的亲人投入最大程度的感情,正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的情绪可能非常流畅,但视野却相对比较狭窄,而对于那些普通的人,因为关系的疏远,感情可能会因为关系的疏远而淡漠,但这种淡漠,不是说不投入情感,而是将这种情感转化为一种真正的审视。情感固然是写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要素,但这个情感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妨碍写作视角的建立,如何把握情感和理智之间的界限,不仅仅只是一个视角问题,实际上也是一种写作的功力问题。
而将亲近的人推到普通人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将叙述的一切放到了时间的河流之中,使充沛的情感得到涤荡。即使曾经存在的一切都会过去,但对于一个严肃的作者来讲,她应该思考的却是,那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这个问题里,包含有人生和历史、普遍和个体的辩证法。只有将自己精神的视野紧紧地集中在这种存在的辩证中,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文学的真谛。而这个真谛便是:使生者更好地生活,而使死者能够获得死的尊严。
死 亡
徐小英的作品中有着太多缅怀的文字,也正是因为这种缅怀,就必然会涉及到缅怀的人和物的逝去。对于一个执着的笔触而言,死亡不但不能构成一个屏障,相反由这个笔触所牵引的情感和思绪反倒能在生与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据徐小英介绍,她创作的最初动力便是要用文字来祭奠逝去的亲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就使她关于死亡的描写具有了仪式的功能。这一刻也使我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慎终追远的原因。死亡本身就是自然万物的一种必然规律。而人类之所以不同于自然万物,是因为人们在亲人离去时的送别和召唤变成了一种纪念。而语言文字作为一种通灵之术,它就像离去的人在度过冥河的刹那向亲人投来的最后一瞥目光。
中国人对于死亡总会产生许多离奇的说法,像湘西的干尸,就是巫术文化背景下关于死亡的一种传说。传统上陇南也是一个巫术盛行的地方,应该有着自己独特的对于死亡的理解。在徐小英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描写,这些描写对于死的描写细致入微。像婆婆一直等到徐小英回到家中才撒手西去,不论这是一种文学描写的手段,还是一种事实的直录,作者无疑是将自己与婆婆的关系放在了死亡的背景上进行主观的宣泄。
这种曲折动人的情感宣泄无疑使文字具有了很强的戏剧性张力,如何理解这种表现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解人们如何面对死亡的一种途径。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对死亡的好奇是一种本能的天性,也因此这些对于死亡的描写,不论是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加以表达,还是用区别于口头文学的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死亡本身态度的差异,无论是以淡然面对之,抑或以热络面对之,这种面对本身便体现了作者的成熟和勇气。
应该说每个人一生的经历都是一个大时代里的一个小故事。一个个个体消失了,这个时代也就消失了,对于有的人来讲,过去应该是一个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被忘却的存在,而对于有的人来讲,过去是一个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始终无法忘却的存在。对于希望将其忘掉的人来说,死应该说只是一个物理的时间标记,死了就像一个普通物质的消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在死亡这个生命的大限之中,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于活着的人还有着非凡的意义。
从传统到现代,许多的东西都渐渐地远去,那些我们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事物,都渐渐远离我们,死也成为了一种超脱的方式,将人们从一切的变化和失去中解脱出来,在一种终极的消失中,使那一切的变化成为一种执着,死亡在这里成为一种申明的方式,申明着那些已经消失的人们的存在,以及他们对于所爱的一切的眷恋。而对于这些努力在追忆的心灵来讲,死则成为了一个漫长的体验过程,在这种体验中,那些死去的并未完全死去,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而存在着。
死作为一切存在的一个阶段性的终点,成为我们反思生命的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点一点点地绽开,那呈现出来的,以及被遮蔽的最终都落到了他们生存的土地上,就像植物的种子,经过四季的轮回,一种永恒的轮回,透过这种轮回,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那些我们生长的地方,最终变成了活着的人与他生长的土地之间的纽带,从而也就成了一代又一代人长久的栖居之地。某种意义上,敬生重死是徐小英对于家园如此依恋的最根本原因。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死亡只是一种再生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我们记忆能够触及到以及触及不到的地方离去,因为生者的眷恋,这些逝者便不会远去,在记忆的深处,他们成为生者的守护神,也成为生者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安慰,生者与死者的相互守望本身就是人类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因此,人们有义务和责任记录下每一个人的死亡以及每一个时代的死亡,给予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传统上来讲,文字无疑成为对这一思索进行记录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也是文学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欢乐和悲哀
看着徐小英的文字,我常常在想,在其笔下,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经历了这样多的事情之后,还能够这样的愉快,除了哥哥的死直接给她带来了深重的悲哀之外,她笔下所描述的人生悲剧实际上还很多,即使是只作为一个旁观者,她对别人的遭遇也如同感同身受,因此我常常想,一个能够始终感受着别人的感受的人,心灵必定是纤细和敏感的,但又是博大和坚韧的,否则,这样一颗心灵该如何承受人世间这许多的痛苦。
看到诸多的评论说,徐小英的文字是质朴的,但是我们想,这里的质朴固然是在说一种风格。然而更应该强调的是作者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生活与体验、体验与表达、表达与生命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问题。在具体的创作上,这些问题最重要地落脚在语言的选择上。从总体上来讲,徐小英的语言是一种口语化的语言,也就是说她笔下的语言是其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语言。
我在徐小英的文章中很少看到什么冗赘的文字,我实际上并不是太相信一个没有受过正规语言熏陶的人能够在文字上这样的凝练,于是就找寻这里面所深藏的缘由,最终我将这一切归结为徐小英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天生优势。这种优势便在于生活和语言是完全统一在一起的。两者之间没有我们常常所看到的背离。作者心中所想的和表达出来的东西表现为完全的统一。
或许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语言,是一种长期生活而形成的语言。奥地利的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语言是世界的边界。为着这句话的意思,长时间以来人们聚讼纷纭,但似乎也难有定论。但就徐小英的文字而言,语言是其生活或者人生的边界却毋庸置疑。我们在她的文章中常常会发现,当她以有限的体验去揣度无限的存在价值时,常常会无力伸展。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她常常陷入一种痛苦之中,只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来书写她对于人生的认识。
人们常常讲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一切存在,都蕴含着万物之理,有着其所以存在的理由。也正基于此,人们可以通过对一个微小存在的观察,进而了解到世间的万事万物。这从物理的世界和区域来讲,似乎不可能,但在文学的世界里,人们却能够进入一个有限却又无限的空间,去体会关于存在的所有意义和价值。因为文学,我们不一定要经历过一切才懂得一切,相反,这些颖悟者即使面对着一个非常小的对象便能感悟到一切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将徐小英纷繁的思绪最终纳入到一幢属于自己的木房的原因。即使世间纵有万般的变化,守住自己也就守住了世间所有的一切。
现代科学经过三百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彻底统治了人们的心灵。受科学的熏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地知道,什么才是文学真正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但就在许多人宣称文学已经死亡的时代里,身处现代时间和空间中的人们,依然能够以文学为灵媒,点滴的触发就可以使人们进入一个他们所未曾去过的世界。也正基于此,当我们循着文学自身的逻辑,面对着人生,便能超越于人生。
如果我们把欢乐和悲哀作为人生的两个边界,无疑这两个边界会渐渐地侵蚀着另外一方,这两者之间的侵蚀,虽然也可能最终导致心灵的麻木,然而只要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不断反思,痛苦固然更加痛苦,但快乐也才能更加快乐。语言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生存境遇,以尖锐的思想穿透了快乐帷幕以及痛苦的绝望。文字在这里也就变成了一种中和,将痛苦和快乐加以中和,最终人能够勇敢地面对面前的一切,将深沉的思索转化为一种面对未来的平静。
西面的山岗
朝着西面山坡的厢房,开着一扇窗户,徐小英说她就喜欢坐在热炕头上,看着园中的风景。在春天,早开的花香应该能飘进这个房间。夏天的时节,蜜蜂和青蛙在院子里相互应唱着。秋天的时节,葡萄和各式各样的水果结满了枝头。冬天该是一个更好的季节,因为,这个时候在炕上放着一个火炉,是喝西和特有的早茶的时候了,细雪飘来,落在青黑色的大地上,喝一口早茶,太阳还只是在对面山尖上。
喝完早茶,于是开始了一天的平凡的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一院子的物种,需要她来经营,对了,相对于那些始终在家中转圈的女性来讲,徐小英还要进行写作,写作成为了她生活的一种方式。但是当她回到这里,她应该没有时间进行写作,她在这里只是进行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劳作,然后将自己的身影留在房子里的每个角落,她以这样的方式纪念着那些远去的人们。
这是一幢布满雕花的木屋,父亲留下的木屋,当她回到这里,一切生命中的记忆也应该回到了这里。在记忆里,徐小英与逝去的人一个个的对话,就像他们最初一样,所有的人聚在一起,谈着每一天发生的快乐以及不快乐的事情。往昔的日子虽然有着这样和那样的无奈和压力,但是他们曾经的记忆在这里都成为难以忘怀的美丽。
一间雕花的木屋,是一个精神的聚居地,也是众多灵魂的归宿,守护着这里,也就是守护着家中的一切。风轻轻地吹着,扬起了她无尽的思绪。她的父亲,她的哥哥,还有她的妹妹,她的婆婆,还有那些在她记忆的深处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风轻轻吹着,轻轻翻开岁月的画卷,卷上的人物来了又走了,上演着一个家庭永不落幕的故事,任岁月老去,人对于往日的记忆却越发的清晰。
守护着这里,徐小英也便能守护着心灵的独立,自己的喜怒哀乐便有了一个盛放的空间。在这里,她是这个空间的主人,她可以嬉笑怒骂,臧否人物,尽情挥洒着对于世间万物的好恶嫌憎。最后,当一切的人物故事消隐,只留下馨香的木屋,太阳和月亮的光亮会印在墙上,人世间一切的隔膜、伤痛都被温情、聪颖和机智穿透。这片土地也就变成一个心灵修炼的场所,当她的思绪随着身心的体悟无限扩散,最终与这幢房屋融为一体,也就能够达到自己的澄明之境。
并非题外话:关于文学
因为此次甘肃之行纯粹是以文会友,回来之后,便向陕西作协的朋友转告了一个甘肃诗人的问候,于是也就顺便聊起了甘肃的文学情况。朋友简单地说了一句,甘肃写作的人比陕西要多而且更加认真。前一个判断,我无法进行确认,但后一个判断,如果是在说甘肃作家更加执着于文学和人生,则其话语中自是藏有对时下文学的期许和无奈。以文学来揭示人生和发现人生,无疑是启蒙主义之后文学创作所坚持的一条崇高法则,然而这条在19世纪创造了文学辉煌的法则,在进入20世纪之后却命运多舛,几经颠沛流离之后,人们在这条道路上已无所适从。
然而这毕竟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离得越远也就眷恋得越深,因为这一创作法则总是关涉着文学的土壤以及文学的传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所以也是文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前者是说作者要体验生活以及表达生活,后者则是讲文学的表达和技巧有着历史的继承性。应该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文学创作的维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讲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但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总是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愿意来谈谈民间文学的写作。对民间文学创作者的赞许,虽然并不意味着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希望寄托在民间创作上,但这种当下的创作毕竟构成了我们文学未来发展的土壤。民间创作者可能在技巧和思想上存在着问题,然而他们的创作从创作意图上来讲实际更加的纯粹,以一些民间作家的创作来讲,如果不是机缘上的问题,他们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可能比现在一些成名的作家更高。
作为民间文学创作的一员,徐小英的文字对人生的体验和表达是统一的,而且有着浑然天成的力量。也因此她的文章能够给人们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会批评很多成名的作家,但是我们在这里却对徐小英的文章赞不绝口,我反躬自省,自认为并非是一种偏爱,而是为一种蓬勃的创作热情所感染。
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恰恰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写作,在徐小英这里就不是一句空话。对其创作的心路历程理解得愈深,也就对其转化自己生活体验的能力体会越深,对于她这样一个基本上算是无师自通的自学者而言,文字和生命的结合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实在是她创作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惊人的学习能力。如果说情感是天生的,那么语言的表达则需要苦心孤诣。在徐小英的行文中,虽然我们在一些章节中可以感受到一些学习的痕迹,但能够把握得这样准确着实让人感到惊叹。
写作,无疑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展示。然而这种独立的人格,说起来容易,真正要达到却殊为不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近现代史上一些成名的作家,也未必达到了这一目标。虽然这种缺失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美学问题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否具有这样的一种完整的人格形式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实际上非常的关键,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她对于社会和人生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如何培养自己的独立人格,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但如果一定要提出一些什么具体的注意事项,那么在我看来,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情感非常轻易地落脚在已经被人们转述了无数遍的俗烂语言上,因为这些语言形式和表达形式会表明创作者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精神流动还没有真正的掌握。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习作者来讲,要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写作?在我们看来,这就需要剥掉包裹在语言之外的流行语气,尽量使自己的语言靠近故乡语言的表达方式。
在文学史上,通过这种方式写作出来的文字,被称作乡土文学。这种文学应该具有一种非常本真的乡土观念以及一套完善的表达手段。看了徐小英的文字,我才真正认识到,乡土文学的表达是一个多么珍贵的事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发展虽然时时被提起,而真正体现乡土气味的作品实在太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贾平凹之于陕西写作的意义。这无疑也算是我这次甘肃之行的另一个收获。
真正质朴的文字归根结底也就是真实的文字,而要达到这种真实,就必须对脚下的土地有着真挚深厚的爱。徐小英的文字无疑是这种爱的自然的流淌,而当你看她文字的时候,也就会自然而然地爱着她的所爱,喜悦着她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