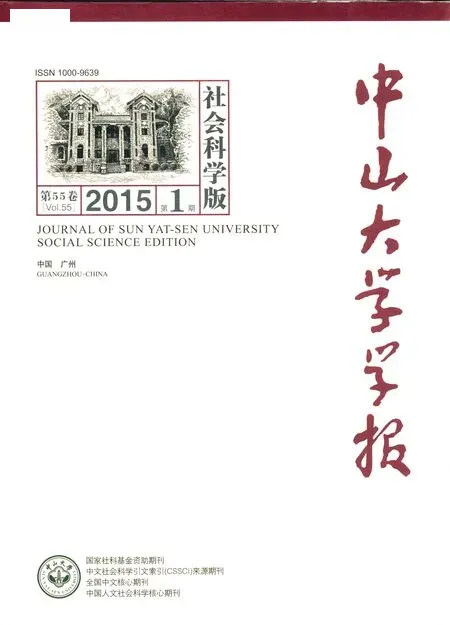《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石雷
《隋史遗文》:明清之际隋唐讲史题材的新变*
石雷
在讲史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因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隋唐讲史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特征。《隋史遗文》把视线从帝王转移到乱世英雄,它叙述的中心由帝王将相置换成草莽英雄,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
《隋史遗文》;讲史小说;名节;袁于令
一、《隋史遗文》与讲史隋唐小说的演变
《隋唐演义》名播天下,而《隋唐演义》重要来源之一的《隋史遗文》反倒少有人关注,其实袁于令所撰《隋史遗文》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一部重要长篇小说。它的相当一部分章回被编入《隋唐演义》,声名遂为《隋唐演义》所掩。《隋史遗文》六十回描述以秦琼为代表的瓦岗寨英雄在隋唐改朝换代的变革中的悲壮经历,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按鉴演义”的新视角,以此展现的是唐朝开国历史的另类面貌和气象,其意旨不在演绎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而在讲述乱世中英雄要识时务,要善于择主。
讲史小说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对同一段历史题材的文学演绎,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主题。明清演述隋唐历史的小说有几部,它们有承传,也有创新,其演变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个规律。“隋唐”历史已经定格,不再流动,然而演义这段历史的小说主题却在不断地变化着。《大唐秦王词话》是民间说唱词话的整理本,其来源应当较早,反映的是民间对隋唐历史的认识和评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隋唐两朝志传》是坊间作者不满于民间说唐的荒诞不经,改为“按鉴演义”,因基本抄史,缺乏文学性而行之不远。明末出现的《隋炀帝艳史》并非讲史,其作者的旨趣并不在历史重大事件的演述,而在隋炀帝宫闱生活的描写,通过这些描写展示一个亡国君主的日常生活和灵魂。作者采撷了宋代传奇小说《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等所提供的素材,但它决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借古讽今:明朝嘉靖,万历皇帝的淫逸荒政不亚于隋炀帝,乃是明朝覆亡的先兆之一,《隋炀帝艳史》写隋炀帝荒淫亡国,实是警示当世。
明亡清兴,出现了《隋史遗文》,它把视线从帝王那里转移到乱世的英雄身上,不但把叙述的中心位置从帝王将相置换成一帮草莽英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叙事中插入大段的议论,使得长期流传的瓦岗寨英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鲜明独特的政治道德指向。究其要旨,是在宣扬英雄处于乱世要善于择主,不可拘于“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隋史遗文》作为明末或者清初的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除了它的艺术成就之外,其历史和社会思想内涵是十分深厚的。它不但微妙地表现了当时士人的心态,而且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种种真实,小说中充满了明清易代时独有的时代气氛和时代意识,是一部为明清鼎革中的贰臣们所撰的辩护之作①参见石雷:《史为我用:论〈隋史遗文〉的创作主旨及与时代之关系》,《南京师大学报》2 0 1 1年第4期。。
《隋史遗文》是一部文人创作的小说,不是此前书商们制造的粗糙的“按鉴演义”,也不是将说书人的讲述记录下来的修订读本。“旧本”既不可见,但今本却提及《开河记》、《隋炀帝艳史》,文本中还保留着说书叙事方式的痕迹,又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和《大唐秦王词话》。我们据此大体可以梳理出《隋史遗文》成书的眉目,同时解读这部作品的象征意蕴,并了解处于改朝换代历史旋涡中的士大夫心态②参见石雷:《史为我用:论〈隋史遗文〉的创作主旨及与时代之关系》,《南京师大学报》2011年第4期。。
今本作者袁于令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戏曲家和小说家。他的传奇《西楼记》曾享誉天下,然而关于他的小说《隋史遗文》,则罕见文字记载。一热一冷,足令人深思。《隋史遗文》决非等闲之作,何以不见时人评述和著录,个中究竟有何曲折?再者,有关袁于令的生平记载文字亦寥若晨星。这种集体性的冷漠,我认为与袁于令曾代苏州士绅草拟降书投降清朝、有失名节一事有关③参见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心史丛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崇祯二年(1629),袁于令以阉党迫害东林党人为题材写成《瑞玉传奇》,表明其政治倾向在东林党人一边,更说明其在当时反阉党的拨乱反正潮流中的积极态度。东林派向来以名节相砥砺,而《隋史遗文序》署时为崇祯六年(1633),仍在名节思想亢奋的年代,袁于令如何可以在《隋史遗文》中反复发表对于忠节的悖论?袁于令是一个识时务之人,在崇祯六年前后发表这种很容易遭至清流们攻击的言论是难以想象的。《隋史遗文》成书在崇祯年间吗?令人怀疑。知人论世,结合袁于令的身世思想来诠释《隋史遗文》的写作时间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二、与《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隋唐两朝志传》的关系
明代讲史小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④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三年杨氏清江堂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与《隋唐两朝志传》⑤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嘉靖三十三年杨氏清江堂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基本上是按鉴演义,二书都是以李世民为中心人物,主要演述唐朝开国的历史。二书又有不同,前者标识“唐书志传”,从“唐高祖袭封履历”说起,更接近史书的范式;后者标识“隋唐两朝”,从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大乱,窦建德起兵、瓦岗寨起义说起,更接近民间说话的叙述角度。但前者终于“唐太宗坐享太平”,并未演完唐朝历史,与书题不尽相符;后者终于“王仙芝大寇荆南”,叙及唐末,叙唐史较为完整。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九十节中,秦叔宝入回名者仅见于四:第二十七节“窦建德大胜唐兵,秦叔宝简打潘林”;第二十八节“程知节散金行间,秦叔宝弃郑归唐”;第三十二节“三跳涧秦望鏊兵,双换简叔宝建功”;第五十五节“建成画计邀元吉,叔宝拥盾救秦王”。《隋史遗文》情节框架与此书完全不同,至少在文字上看不到因袭的痕迹。
但是,《隋唐两朝志传》因袭《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的痕迹却依稀可见。以著名的故事——美良川三跳涧为例:《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三十三节“美良川锏鞭逞战,三跳涧勒马飞渡”与《隋唐两朝志传》第五十三回“美良川秦王三跳涧”⑥《隋唐两朝志传》,万历四十七年金阊龚绍山刊本,藏日本尊经阁。均描写这一故事。相比较,二书完全相同的文字是赞三跳涧之事的一首古风:
隋政不纲君弱懦,天下苍生罹惨祸。颠危四海贼寇多,城郭人民半凋落。山后独夫刘武周,枭雄屹起骇诸侯。高皇震怒旌旗出,白日交兵天地愁。美良川上玉龙飞,豪杰挥鞭紧急追。杀气震撼山岳动,两并输赢颦鼓催。今来川畔良叹惜,水面洪波无马迹。当时事业已成空,绿杨枝上有寒日。
从叙事角度看,《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一气呵成,古风一首殿后极其恰当;《隋唐两朝志传》将古风一首夹在情节之中,使情节中断,况且“古风”系今人吊古,插在情节之中,不伦不类,而叔宝与敬德过涧再战之描写过详,显然是画蛇添足。古风云“美良川上玉龙飞”,《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描写尉迟敬德眼中所见李世民分明是一条龙,这与古风所云相吻合;而《隋唐两朝志传》却写李世民得五爪金龙护体,与诗意不合。细校文字,《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成书在前,《隋唐两朝志传》踵武其后,二者存在着因袭关系。
《隋史遗文》完全摈弃了“三跳涧”情节。袁于令采用写实风格,过去民间传说和小说中一切神化李世民的情节都去之不用。袁于令出于自己的创作宗旨,基本上不依据史传,因而距离按鉴演义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较远。用他在《隋史遗文序》的话说,所叙情节“什之七皆史所未备”①《隋史遗文》引文,均引自北京图书馆藏《隋史遗文》名山聚刊本。下不再注。。不过,局部的因袭还是存在的。比如李密谋杀翟让,《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十节“杀翟让魏公据众,降李密王庆背隋”与《隋唐两朝志传》第十八回“李密诱杀翟让”相比较,《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所叙李密杀翟让,基本上有史传抄本为据,见《资治通鉴》卷184隋恭帝义宁元年(617)。但亦有虚拟,叙述中有几个不清之处。第一,翟让赴宴究竟率领几名随从?按《通鉴》,应当有翟弘、翟摩侯、裴仁基、郝孝德、王信儒和单雄信等,但叙座次时仅及仁基、孝德,杀翟让后,才知翟弘、王信儒亦在场,二人被埋伏在廊下的武士杀死。第二,徐世勣、王伯当二人的角色不明。徐世勣为何见势不对欲夺门逃走,被守者砍伤?王伯当为何可以命令守者住手,守者居然听令,放徐世勣负痛而去?这些都没有讲清楚。《隋唐两朝志传》据前者修订,将原本“让许之”(非史传文字)错刻成“让诈之”即为一证。《隋唐两朝志传》有鉴于原本叙事的漏洞,作了一些修补工作。在叙座次时,加上了翟弘之名;但伏兵“将信儒并让之兄侄尽皆捆缚杀之”,则王信儒与翟让的侄子皆在场,而此前却无交代;此外删除徐世勣受伤情节,笼统说“王伯当、单雄信等人”,“皆来叩头请命”。
《隋史遗文》显然是因袭《隋唐两朝志传》第四十七回“杀翟让魏公独霸,破世充叔宝建功”来叙此一段情节:
次日置酒请翟让并翟弘、翟摩侯、裴仁基、郝孝德同宴,坐定,李密分付将士,须都出营外伺候,只留几个左右在此服役。众人都退,只剩有房彦藻、郑颋两个。数人陈设酒席,却有翟让、王信儒与左右还在。房彦藻向前禀道:“天寒,司徒扈从请与犒赏。”李密道:“可倍与酒食。”左右还未敢去,翟让道:“元帅既有犒赏,你等可去关领。”众人叩谢走出,止有李密麾下壮士蔡建德带刀站立。闲话之时,李密道:“近来得几张好弓,可以百发百中。”叫取出送列位看。先送与翟让,道是八石弓。翟让道:“止有六石,我试一开。”离坐扯一个满弓。弓才扯满,早被蔡建德拔腰下刀,照脑劈倒在地,吼声如牛。
可怜百战英雄,顷刻命消三尺。
翟弘见了,离坐便走。摩侯道:“李密,你敢害我叔父么?”争奈手无寸铁,都为蔡建德、房彦藻众人所杀。李密又叫把翟让从来官属王信儒砍了。诸从行将官都错愕不知缘故,李密分付道:“我与君等同起义兵,本除暴乱。司徒专行贪虐,陵辱群僚,无复上下。今所诛止翟让一家,诸君无预。”又着王伯当、单雄信到翟让营中安慰,自己也到营中抚赏。令单雄信、王伯当、徐世勣分领了他的兵,以后事权都归李密掌握了。
《隋史遗文》在《隋唐两朝志传》的基础上又参照史传进行修补。参与宴席的名单中增加翟让的侄子翟摩侯,弥补了原本说“将信儒并让之兄侄尽皆捆缚杀之”却从没交代侄子在场的漏洞。王伯当、单雄信被纳入李密阵营,抹去他们见翟让被杀而“惊扰”的情节,却写李密派他们到翟让营中做将士的抚慰工作。原本说李密拿出来叫翟让看的雕弓为三百石之力,这里改为说八石,更倾向于写实。
由此可见,《隋史遗文》虽然抛弃了《隋唐两朝志传》按鉴演义的情节结构,将叙事焦点集中在秦叔宝身上,演述他在隋末动乱中寻找真主、建立功业的英雄历程,但在某些局部情节中还是摭拾了《隋唐两朝志传》的一些片断,稍作加工编织入书。
三、与《大唐秦王词话》的关系
明刊《大唐秦王词话》①《大唐秦王词话》,明刊“四明通家陆世科从先甫”序本。出自民间说书艺人之口,书中仍保留有大量的唱词,故称“词话”。此书名曰“秦王词话”,主角实际上是尉迟敬德。从第二十回至第六十四回主要演述尉迟敬德的故事。元人王恽《浣溪纱》词曰:
隋末唐初与汉亡。干戈此际最抢攘。一时人物尽鹰扬。 褒、鄂有灵毛发动,曹、刘无敌简书光。争教含泣到分香。②唐圭璋:《全金元词》(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0页。
“褒”公为段志玄,“鄂”公为尉迟敬德。元代说隋唐,主角是段志玄和尉迟敬德。《大唐秦王词话》以尉迟敬德为主角,距离传统讲史中隋唐故事格局还不太远。《隋史遗文》将尉迟敬德安排为一般角色,所突出的是秦叔宝,传统故事中表现尉迟敬德英雄气概的“伏妖降魔”、“夺先锋”、“战八将”、“三跳涧”等情节均被尽行删除。若将《大唐秦王词话》回目与《隋史遗文》比较,二者面目的根本不同便昭然若揭。
《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李公子晋阳兴义兵,唐国公关中受隋禅”,所叙之事,在《隋史遗文》的第四十八回“唐公晋阳举义,李氏鄠县聚兵”,《隋史遗文》的情节这时已过四分之三,二书的故事情节在时段上的差距甚大。二书叙同一件事情,情节文字亦完全不同。“唐公晋阳举义”与“李公子晋阳兴义兵,唐国公关中受隋禅”不同;第五十二回写李密、王伯当之死,与《大唐秦王词话》第十六回也不同;第五十六回写罗士信屠城和被擒死节,《大唐秦王词话》无屠城情节;第五十回写罗士信陷于淤泥河被乱箭射死,而且将罗士信与罗成合为一人。如果说《隋史遗文》曾经以一个说书人的本子作为最初蓝本的话,那么这个说书人的本子也绝不是今存的《大唐秦王词话》。
但是《大唐秦王词话》既然是说书人的本子,与《隋史遗文》的最初蓝本也为说书人本子,都属于“说书”系统,应当有某些关连之处。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实在不多,却也不是绝对没有。《大唐秦王词话》第三十四回写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大战落叶坡,对二人的穿戴打扮,用韵文作了详细描写,这是说书通常喜欢铺张渲染的地方。它写秦叔宝戴的是一顶“凤翅盔”,擐的是一幅“银锁甲”;尉迟敬德戴的是一顶“铁幞头”,穿的是一领“皂罗袍”,擐的是一幅“乌油甲”。《隋史遗文》第五十四回“寇河东武周入犯,战美良叔宝竖功”写秦叔宝:
凤翅金盔,鱼鳞银铠,面如满月,身若山凝。飘飘五柳长髯,凛凛一腔杀气。弓挂处一弯缺月,简摇处两道飞虹。人疑是再世伍胥,真所画白描关圣。
“凤翅金盔”,也就是“凤翅盔”;“鱼鳞银铠”,也就是“银锁甲”。再看尉迟敬德:
两道黄眉,一团铁脸。睛悬日月,气壮虹蜺。虎须倒卷,峭似松针;猿臂轻舒,浑如铁槊。铁幞头配乌油甲,青天涌一片乌云;乌锥马映皂罗袍,大地簇一天墨雾。想应是翼德临戎,一定是玄坛降世。
“铁幞头”、“皂罗袍”、“乌油甲”,与《大唐秦王词话》所写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描写尉迟敬德的韵文中有“气壮虹蜺”之说,“虹蜺”指李世民、尉迟敬德、秦叔宝三跳涧的“虹蜺涧”,但《隋史遗文》并无“三跳涧”情节,可知这两段韵文很可能从说书人底本移入,作为说书人的本子,它也就显露出与《大唐秦王词话》的相同点。
四、与《隋炀帝艳史》的关系
《隋史遗文》第三十四回文末总评谈到《隋炀帝艳史》,其文曰:
此节原有《开河记》,近复畅言于《艳史》,若不言则逗留,再言又重复,此却把狄去邪一节,叙入去邪与叔宝言谈。陶榔儿一节,敷衍作事。宋襄公一段,叔谋众人语言中点出。或虚或实,或简或繁,可谓极文人之思,极文人之致。
此评语讲得很清楚,《隋史遗文》第三十四回据《隋炀帝艳史》第二十回“留侯庙假道,中牟夫遇神”、第二十一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大鼠”以及第二十八回“木鹅开河,金刀斩佞”①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崇祯四年序人瑞堂刊本。改写而成,亦如此评所叙,只是对虚实、繁简和叙事角度作了调整而已。二者根本不同之处在《隋史遗文》以秦叔宝为主角,在这一段叙述麻叔谋奉炀帝之旨开凿运河,食人之子,勒索钱财,狄去邪入深穴见皇甫君刑讯大鼠(阿摩),预言隋炀帝(小名阿摩)在位仅十二年。这一段故事中,《隋炀帝艳史》没有秦叔宝参与,而《隋史遗文》中秦叔宝是这段情节的主角。正因为以秦叔宝为主,以致对原故事必须作叙事焦点的转移和虚实繁简的调整。
此外,文字抄录《隋炀帝艳史》的地方也有,如第十一回“返龙舟炀帝挥毫,清夜游萧后弄宠”叙隋炀帝挥毫御制《望江南》八阕,《隋史遗文》第二十六回将此八阕完全抄进情节,有所创造的是让萧后等嫔妃按题和上八阕。
《隋史遗文》叙秦叔宝的故事,《隋炀帝艳史》叙隋炀帝的故事,二书历史背景相同,故事情节有某些交叉之处,主要的是有关隋炀帝的情节。第三十四回是一例。第二十六回也是一例,它抄录了《隋炀帝艳史》的八首词,但全回文字还是以袁于令个人创造为多,文中还特意引录“剑啸主人”摹写隋炀帝春夏秋冬四时寻欢作乐的韵文,“剑啸主人”即袁于令。第五十回“化及江都弑主,魏公永济鏊兵”写宇文化及杀隋炀帝,与写同一事件的《隋炀帝艳史》第三十九回“宇文谋君,贵儿骂贼”、第四十回“弑寝宫炀帝死,烧迷楼繁华终”相比,要比后者简略得多,但显然是依据后者节略修订而成。
《隋炀帝艳史》8卷四十回,题“齐东野人”撰。“齐东野人”的真实姓名不详。今存崇祯四年(1631)序人瑞堂刊本,藏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由以上简要之分析,袁于令作《隋史遗文》曾参阅《隋炀帝艳史》,是毫无疑问的。
五、与史传的关系
袁于令在《隋史遗文序》中说,此小说的情节“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基本上不是信史。但是毕竟还有十分之三是见于正史的。也就是说,全书并不完全向壁虚拟。那么他依据的正史是什么,与正史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隋史遗文》是为秦叔宝立传,最直接的史料应当是《旧唐书》中之秦叔宝列传。小说的情节框架,是秦叔宝大业中为隋将来护儿帐内,次归附李密,再随王世充,最后投降李世民,与《旧唐书》相合。但是,秦叔宝在来护儿帐下任职之前的闯荡江湖的情节,占了全书六十回的过半。第三十六回“隋主远征影国,郡丞下礼贤豪”才写到秦叔宝辞别母亲随来护儿远征高丽。第三十五回“徐世勣杯酒论英雄,秦叔宝邂逅得异士”是全书大关节,它不仅点明“兴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择真主而归之”的主题,而且对于当时除李世民之外的英雄豪杰作了点评,为后半部情节发展作了铺垫和伏笔。这前三十五回情节,基本上来自民间传说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的说书。
第十三、十四、十五回写秦叔宝到姑父罗艺帅府的事情,清初柳敬亭说书有《秦叔宝见姑娘》(见余怀《板桥杂记》),即叙此事。俞樾曾据《旧唐书·罗艺传》对此作过考证,证明与史无稽,“是艺妻孟氏,非秦也。所传秦叔宝事,多非其实”①俞樾:《春在堂随笔》附录《小浮梅闲话》,《笔记小说大观》第26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70页。。罗艺之妻姓孟不姓秦,当然就不是秦叔宝的姑母。既然不是姑母,有关秦叔宝见姑母的情节都出于虚构,便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回写秦叔宝上元灯节仗义打死宇文述之子宇文惠及,这是全书中精彩的片断之一,还照应着秦叔宝征高丽中被宇文述诬陷为“通夷纵贼”险被处死的情节,是全书一大关目。这段情节不止在《隋史遗文》中很重要,而且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英雄豪杰在灯市之类佳节中打死横行不法、欺凌百姓特别是强抢民女的恶少,从而与权奸结下深仇大恨,屡遭迫害,但终于为朝廷除掉大害的情节,形成一个模式,不断为后世小说所袭用,如《万花楼》、《薛刚反唐》等等。秦叔宝与宇文述父子的冲突,在《旧唐书》中没有记载。史书记宇文述有三子:化及、智及、士及。《资治通鉴》卷183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记曰:“初,述子化及、智及皆无赖。化及事帝于东宫,帝宠昵之,及即位,以为太仆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及冒禁与突厥交市,帝怒,将斩之,已解衣辫发,既而释之,赐述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轻智及,惟化及与之亲昵。述卒,帝复以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由此看来,宇文惠及可能据“化及、智及皆无赖”而加以虚拟,秦叔宝将其打死的情节当然更是子虚乌有了。
至于第三十八回写宇文述为报杀子之仇,欲将秦叔宝扣上“通夷纵贼”的罪名治死的情节,显然也是出于作者创作需要而杜撰。《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八年(612)记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诈降,打交道的是隋朝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假若秦叔宝果真跟随来护儿出征高丽,也与“通夷”搭不上边。来护儿所率江淮水军首先战败,“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授诸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宇文述出扶余道,三支军队不在一个战场。作为来护儿部下的秦叔宝不大可能出现在宇文述的军队作战之地。作者编撰秦叔宝“通夷纵贼”罪名,并在回末总评中加以议论,谓“真通夷者,断不被祸”,“其被祸者,大都敌国所忌,奸徒所憎耳”,自有深意存焉。
《隋史遗文》第三十五回以后的情节,袁于令还是小心翼翼地追踪史迹,比按鉴演义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隋唐两朝志传》更接近史传。比如李密之死,《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详细记载:
(李)密因执使者,斩之。庚子旦,密绐桃林县官曰:“奉诏暂还京师,家人请寄县舍。”乃简骁勇数十人,着妇人衣,戴羃离,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帅之入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徒众,直趣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应接。
右翊卫将军史万宝镇熊州,谓行军总管盛彦师曰:“李密,骁贼也,又辅以王伯当,今决策而叛,殆不可当也。”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公以何策能尔?”彦师曰:“兵法尚诈,不可为公言之。”即率众逾熊耳山南,据要道,令弓弩夹路乘高,刀楯伏于溪谷,令之曰:“俟贼半度,一时俱发。”或问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向洛,实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施为,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
李密既度陕,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出。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密及伯当,俱传首长安。彦师以功赐爵葛国公,拜武卫将军,仍领熊州。②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6,《四部丛刊》景宋本。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第二十二节“贾闰甫忠劝魏公,盛彦师计斩李密”所叙“(李)密遂斩高祖使命,简骁勇数十人,尽穿妇人衣服……可怜王伯当与众军俱着乱箭射死,无一得脱者”一段,即据《资治通鉴》敷衍,只是丰富了李密中埋伏后“困兽犹斗”的细节。《隋唐两朝志传》却另辟蹊径,别一样写法,其第三十八回“秦王十计羞李密”所叙,与史传基本不同。史传叙设伏诛杀李密者为盛彦师,此回写秦王李世民亦在场;地点也由熊耳山改为马回川,着意突出王伯当的忠义,这一点与《大唐秦王词话》的旨趣相同。《隋史遗文》第五十二回“世充诡计败魏公,玄邃反复死熊耳”忠实地依据《资治通鉴》,只是文字较为简略而已。《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和《大唐秦王词话》叙述这段情节,均有同情李密、王伯当之意。《隋唐两朝志传》此回总批称:“(李密)礼贤得士,乃田横之徒欤,贤于陈涉远矣。意使李密不为叛,其雄才亦不能容于世云。”《隋史遗文》意在表现乱世英雄应当择真主而归之,不识真主、妄思割据者,都没有好下场。其第三十五回徐世勣就批评李密“自衿其才”,又“误任不贤”,不能算是真主。第五十二回写李密死后,徐世勣以王礼厚葬之,文中评论说:“(李密)图王不成,反至身死名灭,与陈涉、吴广同,岂不可惜!”《隋史遗文》借李密之败欲昭示世人的,只是这个教训而已。此书写在清朝定鼎,然天下尚未归于一统,南方抗清战争并未平息之时,其现实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隋史遗文》第五十六回写罗士信千金堡屠城,此事见于史传。《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620)记曰:
甲辰,行军总管罗士信袭王世充硖石堡,拔之。士信又围千金堡,堡中人骂之。士信夜遣百余人抱婴儿数十至堡下,使儿啼呼,诈云“从东都来归罗总管”。既而相谓曰:“此千金堡也,吾属误矣。”即去。堡中以为士信已去,来者洛阳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于道,伺其门开,突入,屠之。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8,《四部丛刊》景宋本。《隋史遗文》据此加以铺叙,使情节更加丰满和细腻,并把罗士信在洺水战死说成是屠城之报:“罗士信只是少年情性,忍不得一口气,害了多少人。后来守洺水,被窦建德余党刘黑闼攻城,雪深救兵不至,被擒死节,年不过二十岁。虽然成忠义之名,却不免身首异处,也是一报。”这说明作者不但熟悉这段历史,而且创作意图十分明确,同时也表现出作者驾驭史料的能力要高出《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
梳理这段演义的流变,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文人创作的《隋史遗文》没有因袭《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完全摆脱了“按鉴演义”传统讲史的旧套,另辟蹊径,截取了隋末战乱至李唐立国的一段历史,故名《隋史遗文》。而且这部小说叙述李唐立国的一段历史,摒弃《大唐秦王词话》以帝王为中心的主题,把主题焦点转移到以秦琼为代表的草莽英雄身上。作为文人的创作,它叙述隋史,基本框架固然不违背历史,但是主要情节却出于虚构,作者显然有自己想表现的创作主题,必有借古鉴今和借古讽今的寄托。
综上所述,《隋史遗文》是一部创作性很强的作品,隋末乱世出英雄,秦琼曲折艰难的奋斗经历昭示世人,乱世中最关键的善于择主,而不是“从一而终”。这是改朝换代时的一个严酷的政治道德问题,所以小说以秦琼等乱世英雄为中心,通过秦琼等人四易其主,最后归附李世民的情节,强调真英雄不必局于忠贞常理,应当审时度势,择良木而栖。当时的贰臣如龚鼎孳等也曾以数易其主的魏徵自命,这足以证明隋唐之际英雄数易其主而最终归附圣主明君的历史,是清初贰臣引以自辩的话题。这部《隋史遗文》便是袁于令为贰臣脱“诬”的形象辩护词。
六、《隋史遗文》的传播与匿迹
今存《隋史遗文》名山聚藏板本并非原刊本,而是经过剜改过的重印本。这说明它初刊后销路不错,不久便重印。既然此书在当时畅行,为什么很快就销声匿迹,而且除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提到外,再没有人谈到它?
(一)被禁毁的悲剧所在
《隋史遗文》的意旨何在,今人也许感到杳不可测,扑朔迷离,然而在清朝顺治年间人们却是明白易晓的。随着明朝的覆亡,前朝遗留下来的士人便分裂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投靠新朝,顶戴花翎,高官厚禄,仍然享受荣华富贵;另一部分人或者自戕尽节,或者隐逸山林,有的积极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有的虽然不参与反政府的政治活动,却抱着敌视清朝的态度,绝不与之合作。前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但在精神上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被世人指为寡廉鲜耻、名节丧尽,其中有人也要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后者则生活在危险和困苦之中,不过他们在精神上是胜利者,他们无愧于名节,而且可以义正辞严地指责和批评变节的贰臣。王夫之《搔首问》堪称其中代表:
为国大臣,不幸而值丧亡,虽归休林下,亦止有一死字。贺对扬、刘念台两先生于此决绝,则怡然顺受之而已。熊鱼山、郭天门已落第二义矣。留生以有待,非大臣之道也。且有待者终无可待,到末后无收煞处,念此使人惭惶。①王夫之:《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624页。
王夫之出语冷峻而极有力度。“怡然顺受”者已经突破了为臣之道,人生虽似有待,其实已断然无可待了,因此“惭惶”之心自此其实也很难得以安稳了。
贰臣在清初经受的舆论压力之大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自我惭惶,清议菲薄,是任何一个贰臣无法回避的。晚清王景贤(伊园主人)《谈异》记云:
四明周公容仕明至大官,鼎迁后杜门不出有年矣。一日以亲串遭无妄之讼,不获已,一见太守解之。门一开遂不可杜。偶与乡人公宴,一人论及武王伐纣,一少年起曰:“商容后仕于周矣。”座中骇问语出何典,曰:“吾尝见其谒武王,名曰周容顿首拜,此明证也。”此与《阅微草堂》所记黄叶道人语更为轻薄,然立身一败,万事瓦裂,不得为人咎也。②王景贤:《谈异》卷2《周容》,上海:扫叶山房,1914年石印本。
这里描述的只是一个少年的话,但作为贰臣“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现实就是这样残酷地摆在眼前的。《谈异》所记也绝非少年孟浪之言,名节的观念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贰臣的孤独感也就挥洒不去了。
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中,《隋史遗文》树立隋唐动乱中四易其主的秦叔宝,提出“兴朝佐命,永保功名,大要在择真主而归之”的命题,并且警告那些“不识真主,妄思割据”者,只能得到李密、王世充的下场。如此题旨的《隋史遗文》,当时人如何难懂呢?要知道,顺治二年南京的弘光朝廷虽然灭亡了,但史可法的精神还存活在汉族人民、特别是江南人民的心中。占据西南地区的永历王朝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才被剿灭。郑成功割据台湾所创立的抗清事业,坚持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才告失败。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归顺了清朝的士人,还是敌视清朝的士人,都很容易读懂《隋史遗文》。
顺治十七年(1660)张缙彦因小说《无声戏二集》而获罪,这是小说创作领域的一个重要信号。李渔和袁于令一样,在名节问题上也是变通哲学的鼓吹者。这种哲学当然会遭至明朝遗民的抨击。清朝统治者在建立政权之初,为巩固政权、收买人心,拉拢广大汉族士人,不得不利用大批贰臣,并容忍变节哲学。一旦他们觉得天下已定,就会来收拾这些再没有利用价值的贰臣和贰臣言论。陈寅恪曾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③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
陈寅恪没有特别提到“易代”的话题,但士大夫阶层的转移升降与新旧道德标准、新旧社会风气变化的关系,其中体现出来的“贤不肖拙巧”的差别,关键正在于对时势环境是否善于利用而已。陈寅恪晚年花费大量时间撰述《柳如是别传》虽然与“易代”的话题相近,但与上引思想实有一致之处。文化与道德的抉择在易代之际会更显艰难,但也只是“更”艰难而已,非易代之时,也会遇到这样两难的抉择。陈寅恪当然是褒奖柳如是,因为在他看来,正是柳如是对钱谦益的思想灌输,才有后来钱谦益的参加复明之事;而对钱谦益当初之软弱无行,陈寅恪当然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嘲讽。这本身没有什么,关键是政治与道德所依托的思想标准所在,如果不明了这个前提,要去追索陈寅恪的“深意”,也就注定是更为艰难,或者说,根本就是不可能。
其实,清初对于文人的大量“征辟”,出于自身稳定的需要才是根本。如果把统治者的这种征辟看成是尊重和网罗人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那最多也只是表象,而希望由此能扭转甚至摧毁士大夫的精神,才是更为切实的目的。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一》于此言之真切,他认为统治者的“霸天下之氏”,其实也“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①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页。。这是一种思想的策略。到乾隆时期,不但遗民的著作成为禁书,贰臣的著作也一律被禁毁。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人都没有逃脱查禁,而且牵连到选有他们作品的集子;由他们鉴定、评点的作品;称引了他们的作品;由他们写序的作品。清朝统治者很明白,从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考虑,应当表彰有气节的忠臣,贬抑丧失名节的贰臣。讲述名节话题的《隋史遗文》,不管它当初如何奉承清朝“真主”,到头来还是会被清朝“真主”抛弃。更何况书中有夷狄之类的违碍词语,仅此一点就已具备了被禁的资格。
现在还找不到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查禁《隋史遗文》的文件,但从现存《隋史遗文》版本的稀少和版本被挖改的情况看,它在社会上流传的时间不长,若保持原貌,断然逃不脱“文字狱”的厄运。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无声戏》在顺治十七年惹祸之后,《二集》中写张缙彦“不死英雄”的作品便消失了,还删去了一些敏感话题的作品,再重编改题为《连城璧》刊行。顺治年间的许多小说都亡佚了,现存的不少作品,如《照世杯》、《闪电商》、《觉世杯》、《清夜钟》等等都是被动过手术的残本。《隋史遗文》的命运又与《无声戏》有所不同,它不是改头换面,而是部分地移植到《隋唐演义》中。然而,《隋史遗文》的灵魂也就被阉割了。
(二)移植于《隋唐演义》
《隋唐演义》20卷一百回,今存康熙三十四年(1695)序刊本。卷首褚人获《隋唐演义序》谈到该书的成书,是以《逸史》所叙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为情节框架,合《隋史遗文》和《隋炀帝艳史》而为之。其序曰:
昔人以《通鉴》为古今大帐簿,斯固然矣。第既有总记之大帐簿,又当有杂记之小帐簿,此历朝传志演义诸书所以不废于世也。他不具论,即如《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唐剪彩,则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合之《遗文》、《艳史》,而始广其事,极之穷幽仙祉,而已竟其局。其间阙略者补之,零星者删之,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汇成一集,颇改旧观。乃或者曰:“再世因缘之说,似属不根。”予曰:“事虽荒唐,然亦非无因,安知冥冥之中不亦有帐簿,登记此类以待销算也?”然则斯集也,殆亦古今大帐簿之外、小帐簿之中不可少之一帙与!②《隋唐演义》,康熙三十四年序刊本。
《逸史》为唐代卢肇所撰传奇志怪小说集,节存1卷,又辑成3卷。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从《太平广记》、《七籤》、《类说》、《绀珠集》、《说郛》等书辑文凡八十八条,但未见载隋炀帝与朱贵儿、唐明皇与杨玉环再世因缘之条文,袁于令所藏《逸史》不知是何版本③详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70—692页。。不过,褚人获在序言里讲得很清楚,《隋唐演义》的始终关目取之于《逸史》,从而确定了《隋唐演义》主题的取向,它既不是按鉴演义,也不是《隋唐帝艳史》和《隋史遗文》的借古喻今,它把隋唐历史解构重组成一个因果故事,把历史的庄重化解成市人的俗趣。
《隋唐演义》一百回,第六十六回叙玄武门之变,此前情节,基本上用《隋唐帝艳史》和《隋史遗文》拼合而成。具体如下表:

表1 《隋唐演义》据《隋史遗文》、《隋炀帝艳史》情节摘编对应情况
《隋唐演义》的某些文字还袭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和《隋唐两朝志传》①参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16—318页;何谷理:《〈隋史遗文〉考略》,台北幼狮月刊社1975年,《隋史遗文》排印本首卷。,《隋史遗文》大部分章回的相当多的文字被移植于《隋唐演义》,但其主体精神却被销蚀掉了。《隋史遗文》大量议论文字和评语被删去,一些重要章回,例如作为其大关节的第三十五回“徐世勣杯酒论英雄”完全被舍弃。这段情节是《隋史遗文》主题的点睛之笔,但对于《隋唐演义》却是不协调的音符,不能不删去。也就是说,《隋唐演义》尽管吸纳了《隋史遗文》大部分文字,但《隋史遗文》的灵魂并没有附着在《隋唐演义》身上而存活。《隋唐演义》刊行之后脍炙人口,《隋史遗文》反而因此受到冷落。《隋唐演义》第四十一回摘抄了《隋史遗文》第三十八回宇文述诬陷秦叔宝“通夷纵贼”的文字,单是“夷”字便是清朝“违碍”字眼,终于没有逃脱禁毁的命运。《隋唐演义》被列为禁书,更何况《隋史遗文》!该书仅存名山聚藏板本的重印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隋史遗文》在当时产生了怎样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尚未见文献记载,在浩瀚的《中国基本古籍库》里亦不见其踪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行之未远,到了康熙年间,褚人获将它的部分情节吸纳进《隋唐演义》之后,便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隋史遗文》与《隋炀帝艳史》一样,已完全走出“按鉴演义”的疆域,它们写历史,不过是借史说古,史为我用,从而把讲史小说的创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追溯《隋史遗文》的成书及成书后的演变过程,不仅可以勘察讲史类小说叙事模式、演义中心等的变化轨迹,也可由此考察一个特殊时期文人政治、文化心态的生态特征。其价值于此特显。
【责任编辑:张慕华;责任校对:张慕华,李青果】
I206.2
A
1000_9639(2015)01_0010_10
2014—09—18
石 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