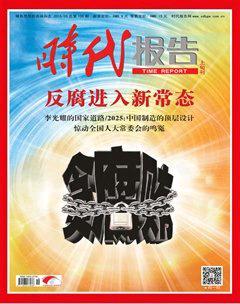惊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鸣冤
范庆锋
《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是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写的一篇稿件。通过朋友,第一时间我得到了授权,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媒体上刊出。
稿件的主人公就是同城媒体《郑州晚报》群工部副主任殷新生。
事起的缘由是,1989年9月14 日,郑州市金水区公安分局杜岭派出所查获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拐卖儿童的是河南省柘城县邵园乡高店村农民高清池,被拐卖的儿童刚满周岁。《郑州晚报》群工部副主任殷新生听说后,第二天便开始追踪采访。几天后,河南电视台和《郑州晚报》分别播发了杜岭派出所寻找被拐卖儿童父母的消息。前来认领孩子的父母络绎不绝。经过一番核实,最后剩下两对夫妇 坚持说被拐卖的孩子属于自己。一是豫西伊川县苗全亮、李会玲夫妇;一是豫东柘城县的孟庆德、李雪芝夫妇。
为了查证孩子属于哪一家,案件负责人韦兵役和殷新生几下柘城县进行调查。办案人员和殷新生发现,虽然孟庆德、李雪芝夫妇一再强调孩子是自己的,但他们对孩子的出生地点、出生年月却说法不一,而且拿不出孩子的出生证明。办案人员只好暂请郑州铁路局退休老工人宋荣成夫妇抚养孩子。
办案人员和殷新生还发现,拐卖小孩的犯罪嫌疑人高清池声称孩子是患有精神病的弟弟高清峰的,而李雪芝原先又是高清峰之妻。殷新生等人开始怀疑孟家夫妇和高清池及其家人与这起案件有关。殷新生与另外两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陈朝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洪恩和他自己的名义,向公安局审查站写了一张字条:“市公安局审查站,最近两个月来,我们三个新闻单位调查了一起拐卖儿童案,案情复杂,牵涉人员较多,柘城县大孟庄村的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孟凡祥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惑疑是拐卖儿童的同伙,现在这四个人都在郑州,我们请求你们帮助审查,以求得此案早日结案。”
在这之前,伊川县李会玲夫妇向审查站递交了举报高家数人是拐卖儿童团伙的材料。当天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审查站以涉嫌参与拐卖儿童为由,对孟庆德、李雪芝、孟庆勤实行收容审查。
11月23日,承办此案的杜岭派出所民警带领苗全亮、李会玲和孟庆德、李雪芝夫妇及被拐卖的孩子,携河南省公安厅的介绍信,到该厅指定的法医鉴定单位——洛阳医学专科学校作亲子鉴定。殷新生以记者身份跟踪采访。鉴定表明,被拐卖儿童与孟庆德、李雪芝夫妇没有血缘关系。
拿到的戴煌所写稿件的关注点,并不是这个案件本身,而是后来检察院凭“以怀疑孟庆德等4人系贩卖儿童团伙为由,要求公安机关将4人收容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138条,构成诬陷罪”将殷新生实施逮捕,让殷新生度过了近9个月的监狱生活。
戴煌调查证实,在这件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1989年12月,殷新生经过数月的调查后,在《郑州晚报》上连续三期报道了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介入一起企业合同纠纷案的事情,并针对此事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讨论,最后引起有关领导部门重视,恢复了由于郑州市检察院介入而被强行中止的合法合同,维护了企业及企业承包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刚刚推行不久,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国家《合同法》的尊严和严肃性。
然而,殷新生这一不畏权势的舆论监督行为,引起了郑州市检察院的强烈不满。有可能就是因此让检察院的某些人借故对殷新生打击报复。
经过调查,戴煌写出了五千多字的《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
读完报道,我如鲠在喉,作为记者,我们应当首先站出来维护自己同仁的合法权益。我报经总编辑同意,把稿件安排在了第二天出版的报纸的第一版,并亲自操刀撰写了评论一并配发刊出。
为了不出差错,也为了稿件刊出后能经得起各方面的考证,我们反复对稿件进行了校正,同时,第一时间同当事人进行联系和核实。
应该说,稿件的当事人我是熟识的。在事件发生前,我同殷新生有过交往。知道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又热爱新闻工作,人很实在,而且非常敬业。长期从事报纸群众工作,所经手的稿件大多都是舆论监督性的报道,难免会得罪一些人。但检察院就因为其一个字条而对他定罪,确实有些不公。
因为同殷新生认识,为了避嫌,我也曾掂量过该不该刊发这个报道。但站在同行一方考量,加上当时全国媒体都以刊发第一新闻提升自己媒体影响力的大气候,我决定刊发《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并报经了总编辑同意。
但在大样已签,就要送往印刷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总编辑找到我,对我说,是不是考虑一下,明天的报纸先不刊发戴煌老师的稿件?虽然总编辑说话的语气是同你商量,但以我同总编辑多年的交往,我知道,在他内心里面已经决定这个稿件不发了。
我一脸诧异,本想张口力争一下。但我又深深明白,争也没有多大用处了。但是,我又感到非常为难。作为一个地方报纸,采用新华社一个名记者的稿件,并且得到授权,还告知对方稿件已经上版,就要送印刷厂印刷了,现在又突然不发,该如何同作者——戴煌老师解释?另一方面,脑海里浮现出了殷新生的面容。那一刻我似乎看到,当殷新生得知稿件在印刷前被撤换时会是多么的无助——一个新闻记者,在自己受到委屈时,自己的同行却不能为他申诉,对于新闻工作者该是多么地悲哀。
总编辑的决定又不能不执行。在媒体,你可以因为一篇稿件刊发不刊发同总编辑争个面红耳赤,可以同总编辑拍桌子打板凳,但一旦决定稿件不发,那你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说到这里,想起来一个前辈——中国青年报原总编辑王石,他为了让后辈能够及早成熟起来,主动让贤,从总编辑岗位提前退了下来,但组织上决定他可以参加编前会。期间,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稿件,编前会上将决定稿件见报不见报。王石认为那篇稿件可以见报,但是,编前会决定不能刊发。散会后,王石见到写那篇稿件的记者站在办公楼的走廊里在等结果,就上前拍了拍记者的肩膀,说:非常可惜,稿件没有通过。说这话的那一刻,王石眼里噙着泪水。那一刻,那位写稿的记者心颤抖了。据那位记者后来说,从前总编辑的眼泪中看到了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真诚的心。即使自己再有怨言,也被老总编的泪水给化解了。
我默默地把即将送往印刷厂的大样收了起来。但我心里决定,我必须给戴煌老师一个交代,我也必须不能让我的受了委屈的同行殷新生失望。
我拨通了当时已经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也在业界被多次夸赞、可以说在北京一枝独秀的《北京青年报》时任常务副总编辑、现《北京青年报》掌门人张延平的电话,告诉他,新华社戴煌那里有一篇《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迫害记者事件》的稿件,看他能不能派人和戴煌老师联系,看看稿件适合不适合在《北京青年报》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