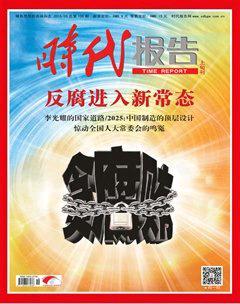一封未寄出的信件
妈妈:
您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了,好几位您的好友都写了纪念文章,可是我一直没写。在我心中,您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慈祥,像所有的妈妈一样爱孩子,也像所有的妈妈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小毛病,比如说过度节俭。直到最近,我在做性别研究时,重新翻出了当初对您做访谈时留下的录音记录,我才突然间意识到,您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多么地出类拔萃。
记得自从您看了电影《巴顿将军》,就对里面的一句话念念不忘: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我一再从您那里听到这句话,感到这正是淡泊人生的感悟。
印象中您吃饭之简单是出了名的。听报社的人说,报社食堂一点儿破菜汤、一个馒头就是您的一顿饭。住的地方也没有正经装修过,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有外地亲友来京看望时惊为“贫民窟”。可您给希望工程捐钱却不吝惜。有一回,河南老家的村里来信劝捐修小学校,您一次就寄去一万元,这在您一生的积蓄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农村老保姆退休,您坚持要给退休金,念她在我家照顾父亲和您多年。您最后给了她两三万元的退休金,而您留给我们四个孩子的“遗产”总共才几万元。
其实,您写作和说话都特别生动。我看您写的少数几篇文章,感觉的确是这样,并且有很高的抱负,只可惜并没有实现。这是我在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知道的。那次访谈里,有一个问题是问及什么是您心中理想的女性,您却所答非问地说了一句:我写的那些都远远不是我想写的。我知道,这就是报社的老人纷纷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您从来不动心的原因——您所写的东西由于各种原因并不是您最想写的,也远远没有达到您心目中的高度,而且您也并不在意出名。
我是从您一个简短的回忆录里知道您喜欢唱歌的。1936年您师范毕业,后来七七事变,您就去延安参加革命了。您是裹过脚的人,在河南农村,姑娘脚大是嫁不了好婆家的,所以您被姥姥裹了脚,幸亏裹得不是太小,时间不是太长。您就是用这双“解放脚”跟那批热血青年一起唱着歌一步一步走到延安去的。在您还没有老到不能写作时,我劝您写回忆录,可是您总是觉得自己太平凡了,不愿写。
您这辈子主要和农村问题打交道。具体都有哪些争论、经过哪些斗争我不了解,但是“大寨”“七里营”“包产到户”这些词一直听您讲过。这都是您多次采访报道过的人和事。记得那年您在改革后重访大寨的一篇文章还得了全国新闻奖。您是带着感情去工作的,因为长期搞农村,您的感情就给了农民。我还隐约记得,在我七八岁时,您和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带我们几个小孩去公园。有一次我们去了天坛公园。天坛公园那时候又大又野,里面还有农民种地。您和爸爸见到农民,就会过去跟他们问这问那,问他们的收入,问蔬菜的价钱——我后来做了社会学,启蒙的根子也许该追到这儿吧。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代表您去看望您的老友、前农委主任杜润生,他用一支大粗碳素笔颤巍巍写了“农民喉舌”四个大字,让我带给您。我从心底觉得,这确实是对您一生恰当的总结。
由于您的外表过于朴实,从来不会梳妆打扮,竟致被人误作文盲老太太。报社一位老阿姨给我讲过一个妈妈被人传为笑谈的轶事。有一次,您到报社前面的小书店去买书,那个小年轻的售货员问您:老太太,你识字呀?您笑眯眯地说:识得几个,识得几个。按照几率,在您这个岁数,又是个女的,百分之七八十应当是文盲的。这个小青年万万想不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位老奶奶岂止是识字,还是一位以文字为生的人呢。
您生命中最精彩的一笔是捐献遗体。您在遗嘱中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遗体捐献供医学研究之用。而爸爸当初也是捐献了遗体的。这是您二老商量好的。在一个有着“活人要靠死人的亡灵保佑”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文化当中,此举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在我心中,您这样的举动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标枪,向人世间的虚名浮利做了英勇、美妙而彻底的最后一击,以此为您作为一个女战士纯洁高贵的一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虽说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的烟云,但是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也可以活得很乏味。妈妈,您的一生虽然平凡,但是绝不平庸。虽然生命已经如烟飘散,但是您绝对属于出类拔萃之辈。
女儿永远想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