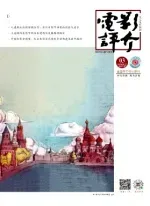潘金莲影视形象与女性性别歧视
郭 安 郑 燕
潘金莲作为“具有其心理的一切错综的人”,负载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拥有强大的阐释空间。潘金莲形象妖艳、淫荡、恶毒,具备“美而坏”女性叙事的一切想象,潘金莲“失配、乱伦、杀夫、杀嫂”[1]的故事原型充满情色、暴力、戏剧性与伦理张力。这使得潘金莲作为经典女性形象一而再地被移植、“翻案”、建构与重塑。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水浒传”“潘金莲”“金瓶梅”等为名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构成影像生态中的一处奇特的视觉景观。引人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这类影视文本中,潘金莲往往喧宾夺主,成为故事叙事的主要人物与视觉展示的中心。一个本应被人们唾弃的潘金莲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女性主义兴起的一个聚焦点。本文要关注的是关乎潘金莲形象的所谓“现代阐释”究竟是体现了新时期的进步,还是沦为了新一轮的女性消费。
一、影视中潘金莲的形象呈现
在潘金莲的影像叙事中,延续了小说文本中诸如挑逗武松、王婆说风情、私通西门庆、武大捉奸、鸠杀亲夫、武松杀嫂等主要情节,但在对潘金莲的角色重塑、细节拿捏、语境再造等方面进行再改编,呈现出一个更加感性、丰盈、也更复杂的潘金莲形象。
(一)“浪荡风情”的淫欲者
“淫”与“恶”是小说本文贴在潘金莲身上的原初标签。影视文本充分发挥了其视觉传达的优势,将小说中原本隐晦、有节制的性欲描写裸露化,使得影像文本充满了躁动与不安,潘金莲身上的性符号被放大,这也成为相关影视作品生产传播的最大噱头。在香港的一系列关于潘金莲的影像中,散布着大量的情欲戏、裸戏、床戏,充斥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性诉求,进而升级到“风月片”(情色片)的档次。内地影视片中,由于审查的机制,关于潘金莲的性欲书写要收敛许多,但在挑逗武松、与西门私通等情节中同样充斥着性与欲、灵与肉的展示。以新旧两个版本的《水浒传》为例,尽管潘金莲均以楚楚可怜、温婉贤惠的良家女子出场,影视创作者企图赋予其行为的合理性,但终究免不了放大呈现其淫荡的形象。央视版的《水浒传》在展示潘金莲情欲与床笫之欢之余,还设置了四场小说中本没有的“洗澡戏”,累计时间接近3分钟。而鞠觉亮新版的《水浒传》更将潘金莲的戏份扩大到5集篇幅,淫欲的尺度进一步放大。
(二)“阴险恶毒”的施害者
潘金莲作为臭名昭彰的“蛇蝎女人”形象,除了红杏出墙的“淫”,还有弑杀亲夫的“恶”。在小说《水浒传》《金瓶梅》中,对金莲的“恶”的描述可谓是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她弑杀武大、虐待丫环、害死官哥、毒死西门,小说文本中作者对潘金莲的道德评价也字句鲜明、随处可见。较之小说文本,影视作品中对潘金莲的“恶”做了相当的删减与淡化处理,并赋予了其“恶行”的诸多“语境”与“合理性”。比如,电视剧版《水浒传》中,潘金莲并不是以女妖祸水的形象呈现,相反是与之相去甚远的良家女子。潘金莲的行为也并不像小说那般恶毒,也未唆使西门庆去给武大郎一个窝心脚,毒死武大郎也是在“欲”令智昏更兼顾忌武松寻仇的无奈。但无论如何,潘金莲先是通奸已是恶,而后与王婆、西门庆媾和,毒杀亲夫,这些主要的情节以她身上潜在的丑与恶同时推向了极致。
(三)“命运摆布”的受害者
整体而言,影视的创作者多抱着“理解之同情”现代阐释态度,试图用现代意识重塑潘金莲形象,探掘形成其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影视作品在淡化削弱潘金莲“丑”与“恶”并赋予其“恶行”合理性的同时,扩张性地表达潘金莲作为受“命运摆布”的受害者形象。
潘金莲并非一个天生的坏女人,相反,在鞠觉亮新版的《水浒传》等影视作品中,许多情节将其知书达理、温柔贤惠、勤劳持家的品性放大。潘金莲自嫁武家后甚少抛头露面,就连武松打虎荣归阳谷县这样万人空巷的新鲜事,她也以“奴家不爱凑热闹”为由拒绝围观。我们在潘金莲细腻的经历、情感、心灵展示中,品读出其实她也是个值得同情与叹喂的受害者。她出身卑微,被迫在张大户家做使女,因不忍其辱,被贱卖给“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做妻子。后又在西门庆和王婆的计谋下与西门私通,东窗事发后了了性命。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并没有延续小说的描写:即被武松一刀夺命,而是改编为潘金莲主动寻死——她自己挡在了武松刀下。这个有意味的结局促使观众深层思考潘金莲的悲剧:自始至终,潘金莲都是被男性倒腾的“他人”之“物”,焉有作为独立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与尊严。其实,影片还部分地呈现潘金莲在欲望与挣扎背后追求自我、与命运反抗的“抗争者”形象,可归根结底,这种抵抗是何其微弱和有限。“潘金莲”从根本上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她与武大郎一样,同样是一个悲剧的角色。
二、影视作品中潘金莲形象的性别歧视
潘金莲已经成为中国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母题/原型。荣格的原型理论认为,原型是“无数同类经验的心理凝结物”,原型具有“恒久历时性”。所谓“恒久历时性”是指“‘原型’能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的个体事物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即形成它的置换变体”。[2]潘金莲母题/原型正是在不同的时代经由各种叙事文学与影像文本经历了一次次的“置换变形”。时至今日,“潘金莲母题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异,由一个异质典型成为银屏女性的一个常态;由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人物成长为一个具有现代审美性价值的新角色”。[3]潘金莲形象本身作为封建男权文化制度权力/性别秩序的牺牲品,这点不证自明。本文要关注的是,当前影像生产中对潘金莲的形象重塑与景观消费,是否真的体现了“具有现代审美性价值的新角色”?还是仅仅沦为新一轮的身体狂欢与消费意象,依然没有动摇女性性别歧视/偏见?笔者的观点是后者。正如有学者指出:“对潘金莲的关注恰恰折射了时代密码和公众的隐秘心理:潘金莲仍然是男权社会下的一个‘被消费者’形象和角色。离开了‘被消费者’角色的充当,对谁演潘金莲的关注将烟消云散。”[4]潘金莲的形象,依然只是一个“被消费者”——时刻准备被编剧及大众“消费”;潘金莲的影像文本,也依然只是一个新时期的“男性文本”。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尔伯特在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论及,在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达了他们的厌女症心理。[5]影像中的潘金莲无论是打扮成妖妇,还是天使,其实都难以掩盖其女性消费与女性歧视的本质。
(一)“潘金莲”形象的“泛消费化”
费斯克认为,快感是大众文化最基本的内部驱动力量和根源,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快感文化,为受众提供感性愉悦是其主要目的。快感生产成为流行文化的基本生产机制。“它将流行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转换成通过流行文化为载体的快感的生产、流通和获得的过程。流行文化是快感的载体,它的价值不在意义,而在快感。”[6]潘金莲影像的景观化生产,正是因于潘金莲形象作为能指所蕴含的强大的符号生产能力,在这些影像中,潘金莲成为了制造快感和欲望的商业机器。
伴随着“欲望满足”“身体消费”的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潘金莲”几乎成为了女性形象与性别叙事的“泛模式”,潘金莲的女性魅力成为了消费社会中一种受众肯定的价值。“潘金莲”形象的滥用,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商业娱乐影视中得以直接展示,“淫”与“恶”的潘金莲形象成为消费文化将色情与暴力元素组织进影视文本的突破口。各种激情四射的性欲场景冲击着观众的视觉神经,生产着“性”与“欲”的狂欢与崇拜,成为影片诱人的卖点。影视创作者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影视作品中运用或映射“潘金莲”的角色形象,并且其总以淫妇、荡妇、恶妇的形象展现在荧幕面前,整体上展现出“泛消费化”的趋势,造成对其形象的滥用与歧见。这种“快感文本”正是以其颠覆性、极端性、猎奇性的“潘金莲”形象在奇观层面被组织进了大众文本,编织成一种新的消费形式,产生消费快感。这种过度的“泛消费化”的形象滥用,无论以何种现代阐释为名,呈现的都是一种“虚假的胜利”,而不可能体现真正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体。恰恰相反的是,男性中心意识通过这类形象符码稳固了自己的位置。这正是性别意识形态的歧见在消费文化中新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模式。
(二)女性身体的工具化
文化理论家波德里亚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今天的一切都证明身体变成了救赎物品。”[7]女性身体一贯是消费文化中最有利可图的结构性元素,它们在影视作品中常常被编码成奇观化的段落来吸引观众视线。回顾所有关于“潘金莲”的影视作品,充满了对女性身体的呈现及情色化编码。
影视创作者将女性的身体工具化用以制造看点、赚取票房,最突出的表现在对女性身体、性活动镜头的无限重复与渲染。影片中的“潘金莲”的身体形象几乎是以“爆炸”的方式向观众扑面而来,贴着“三级”“AV女优”的标签,伴随“大尺度诱惑”“身着薄纱”“胴体半露”“酥胸绽放”等营销宣传,引得观众遐想非非。在情欲放纵的镜头里,女性成为大众文化的牺牲品,“性”成为勾起观众强烈快感的重要原因。比如在李柏翰导演的《金瓶梅》的视觉编码中,潘金莲甩着湿漉漉的头发——一个瞬间的镜头被放大延长了,加之是特写镜头,这个镜头处理得极为风格化,充满了诱惑的味道,镜头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放大给予了观众充分的“窥视”的快感。如此使得这个原本不具有色情因素的镜头被色情化了。摄影机犹如“偷窥狂”“恋物癖”的眼睛,潘金莲的身体在摄像机来回“过滤”中得以细致呈现,这几乎是色情镜头最惯常的方式。一个本来健康明朗的女性身体,在过度强化的视觉语言编码中变得脱离它的语境,成为一个可以“分割”出来的消费工具。
女性身体作为“快感原则和生产力”,“身体被出售着。魅力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8]在资本逻辑与男性话语的逼迫下,女性身体异化为工具或商品,成为消费时代的的产品,被资本与欲望所侵蚀。女性身体“被占有、被控制、被侵犯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女性身体的工具化和女性人格的卑微化:女性不是一个鲜活的‘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而是在男性权力专横、独断、暴虐统治下的‘物’,一个空洞的没有情感与意志的存在‘物’”。[9]女性身体的工具化与情欲化,是当下女性叙事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
(三)叙事话语的霸权化
从表象看,有关潘金莲母题的影像叙事多以潘金莲为展示中心,并且极力拓展人物的丰富性,呈现“并陈善恶”“美丑并举”的新时代现代女性形象,这一切似乎是一种女性主体的叙事。但事实上,潘金莲“仍然是男性话语的一个符号,只是符号指代的意义不同罢了:由淫妇变成了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在男性中心的话语体系里,对女性的评价分为两极,一种是轻视贬抑态度,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要么被定义为俯首听命的贤妻良母、孝女节妇,要么就是被指斥为败坏纲纪伦常的祸水,潘金莲就是这样依照男权社会的伦理标尺、用男性话语描述出来的。”[10]
影视作品中的“潘金莲”是一个爱欲鲜明的女性,她渴望爱与被爱,但社会环境上注定了她在与男人的交往中是一个弱者,不可能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她的美貌无意中导致了她悲剧命运的开始,她对爱欲的渴求则导致了她“杀夫”的行为。影视作品中“潘金莲”这一角色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或自杀、或他杀、抑或是纵欲而亡。死亡换取了廉价的怜悯,但终究从未给予潘金莲真正的救赎。至此,她成了一个集施害者与受害者于一身的女性形象。从影视作品中的“潘金莲”形象的情色展现可看出,女性形象很大程度都落入了男性话语权力的俗套。潘金莲的一切行为与一切心理活动都是以男人为中心,潘金莲依然只是男性情欲与权力的“玩物”。影像中创作者不厌其烦地演绎着一幕幕性欲场面,这都服从于男性话语霸权下“阳性崇拜”的主题,在表达方式上则是越粗鄙越偏激越痛快。“潘金莲”仍作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而存在,营造了某种具有情色观看价值的荧幕奇观。
在性欲泛滥中,女性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成为男性社会中的“他者”。“潘金莲”这个欲望客体成为了受众可窥视的合理化对象,在这种感官刺激下,侧面地塑造了以“男性中心意识、性崇拜”为主的“潘金莲”形象,一种新型的“看与被看”的关系得以确立,借此成为被观众用来消费的目标所在。
结语
影像中“潘金莲”形象,说到底是一种性别话语构建。客观地说,潘金莲的悲剧模式,在影视作品的改编与重构中包含了一定的现代理念的意义与追求。但创作者试图去重塑潘金莲形象以建立新的视觉、心理冲击美感,却又往往迷失在对消费与欲望的诉求上。近年来,“潘金莲”的影视作品中各种情欲表演招到了质疑与指责,究其原因在于创作者们放弃了女性主体性的追求与女性美感的真正建构,无形中背离了影视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审美追求,从而沦为女性书写的新的“贬抑”(annihilation)。
在当下以“情感制作”与“快适伦理”为表征的“后情感主义”社会语境里,女性叙事“往往陷入娱乐透支后的身心疲乏和性感聚焦后的精神空幻,形象的欲望满足取代了文化的意义追索,审美正义与文化伦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化完全无视生命中的‘痛苦’‘严肃’‘庄严’‘意志’一端,沉溺于‘人生幻觉’‘瞬间的快感’。”[11]大众传媒并没有用一种积极健康、两性均衡的方式来传播女性文化,对于影像作品中“潘金莲”形象的塑造,我们依然嗅到了陈腐的、本应式微的传统价值和性别观念的气息。因此,“潘金莲”形象重塑与美感重建尤显必要。不是说“潘金莲”母题的女性形象不可以出现于媒介镜像中,抑或媒介镜像不可以写女性的“欲”与“恶”,而是说应该以更加现代、进步、平等的创作思想去批判地揭示其形象结构的根源性、复杂性与多元性。创作者应依据传统文本挖掘出母题暗含的现代基因,反对偏枯的性别传统与权力体系,尊重女性的主体性与个性尊严,从而使一个凤凰涅槃般的女性形象获得现代性的内涵与光彩,这才是新时期重塑“潘金莲”形象的意义所在。
[1]苏琼.异性书写的历史——《潘金莲》:从欧阳予倩到魏明伦[J].江苏社会科学,2000(3):182.
[2]杨丽娟.“原型”概念新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3(6):114.
[3]夏中南.影像中潘金莲母题的现代性转化[J].学术探索,2006(1):128.
[4]黄霖,吴敢.《金瓶梅》与清河[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25.
[5]张磊.妖妇的悲哀——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看潘金莲和查泰莱夫人[J].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6(2):16.
[6]章浩.流行文化的快感生产[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131.
[7][8]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0,126.
[9]胡辉杰.萧红:寻觅自己的天空——从一组语词看萧红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悖论性[J].鲁迅研究月刊,2005(5):83.
[10]夏中南.影像中潘金莲母题的现代性转化[J].学术探索,2006(1):129-130.
[11]傅守祥.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伦理与哲学省思[J].伦理学研究,2007(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