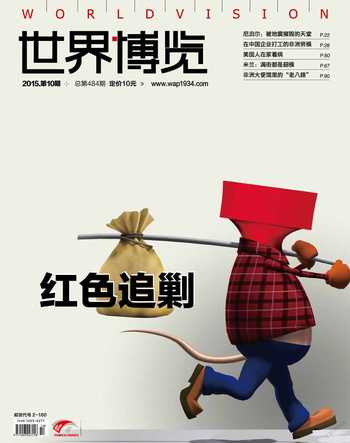来自大马士革的一封信

(编者按:此篇文章是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随员韩冰写给朋友的一封书信,文中详述了叙利亚的局势以及身为一名外交官的责任,读之让人感动。)
Z兄:
你好,很久没有写信,祝一切都好。
我作为驻叙利亚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来到叙利亚已经半年多了,半年里我有了不少宝贵的经历。今天,想跟你专门讲讲战争这回事。
“安全”是第一课
近日叙利亚最吸引眼球的消息是:令人闻之色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逼近大马士革,并占领了距市中心8公里的雅尔穆克难民营。有些媒体想当然地报道说,大马士革面临失陷危险。有几位国内的同事已经急切地向我发来微信询问平安与否,在此谢谢各位的关心,一并回复大家:我还好,暂时没有危险。
雅尔穆克难民营是逃到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说是难民营,其实就是个繁华的商业区,占地很小,原先人口有十几万,密度极大。叙利亚危机开始后,区区两平方公里的难民营竟然涌现出十几个武装派别,难民营人口不断出逃,现在只有不到两万。

“伊斯兰国”在大马士革南部盘踞已久,但他们实际上并非“正宗”“伊斯兰国”分子,多数是当地伊斯兰武装团伙易帜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的产物。他们此次攻入难民营,政府投鼠忌器,无法对其实施毁灭性打击,而他们也无力对政府军重兵把守的大马士革发起正面冲击,作为外交人员的我,暂时没有迫在眉睫的危险。不过,我的宿舍床头总是放着钢盔、防弹衣、逃生背包、甚至防毒面具(谁知道人家会不会使用化武呢?)。
对讲机别在腰上,睡觉前检查窗户,随时准备紧急撤离。这已经是我到叙利亚几个月后的习惯。其实进入大马士革的时候,我差点就以为,所谓战争,只不过是政客和媒体的危言耸听。
抵达那天风和日丽,天蓝得不像真的。从黎巴嫩坐车几个小时后,终于进入叙利亚境内。顺着阳光向山下看去,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市铺展在高原上闪着金色的光,除了军警对每辆车实施严格检查之外,一切都那么和平安详。
“你看那边,”到贝鲁特机场迎接我的张志昇参赞给我指点,远处几公里处的地平线上有两缕小小的黑烟,仿佛炊烟袅袅,“那就是迫击炮的落点。”
一刹那我全身肌肉绷紧。“这么近?”我问。
“这算远的,去年9月一枚迫击炮弹直接落在我们使馆后院,炸伤了一名本地雇员。”参赞接着说,“安全,是你来使馆工作要学习的第一课。”
果然,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领防弹衣头盔和对讲机等一干装备。我注意到,使馆内建筑的楼顶都铺了厚一厘米的钢板,窗户也被厚厚的钢板封死,因为使馆坐落在大马士革北部的马扎区,与总统府、总理府、国防部等核心政府机关相距仅几百米,时刻受到反政府武装炮击的威胁。你知道,反政府武装拥有的绝大多数远程武器是迫击炮和火箭弹,这两种二战时代的常规武器精确度实在低得可怜,所以使馆人员被要求尽量呆在室内,时刻保持警惕,远离窗户和门。因为大马士革每天都会落下几枚迫击炮弹,说不准下一个倒霉蛋会是谁。

叙利亚局势
现在必须介绍一下叙利亚境内这几类军事力量了,我少用点数字,尽量讲得不枯燥。
第一类是政府军,现在还是叙利亚唯一合法的武装力量,装备也相对精良。只有政府军有空军。控制大概全国领土的一半。像是学校里一个班的班长,人高马大,平时对本班同学比较霸道,也不擅长和外班同学一团和气,所以现在受了欺负,帮助他说公道话的人不多。
第二类是各种所谓“温和”反政府武装派别,都是“阿拉伯之春”后兴起来的武装团体,名字五花八门,什么“伊斯兰军”、“伊斯兰营”、“沙姆伊斯兰阵线”、“沙姆自由人”。小的几十人,大的也就几百。这些组织的联军就是之前所称的“叙利亚自由军”,其实每一个组织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刚开始时候风光了几天,但终究是散兵游勇,战斗力连年下降,现在仅占着全国领土的百分之五。像是班里的体育委员,学习不好不说,还因为拿着外班的好处跟班长对着干,被班长收拾得躲进地下室。班上的同学们也不怎么看得上这个体育委员,但是无奈外班人土豪出身嗓门还特大,到处喊着说应该让他当班长。他们说是“温和”,但打起仗來也是口口声声“安拉阿克巴”,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加入伊斯兰极端武装。
第三股就是“支持阵线”和“伊斯兰国”这些伊斯兰极端武装。“支持阵线”又名胜利阵线,是基地组织的叙利亚分支,两年来风头逐渐被从其中分裂出去的“伊斯兰国”超过。目前这两个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已经占据了北方大约百分之四十的叙利亚土地。这俩家伙平时谁也不服谁,有时候还会互相掐一下,搞个黑吃黑什么的。他们是校外的坏小子,想要占班级的教室,今天冲过来打班长几拳,明天再把体育委员削一顿。典型的欺软怕硬,看到体育委员被班长打得满地找牙了,就跑过来再踢几脚,占领的地盘主要都是从“自由军”手里抢过来的。
所以全国的战场形势就是:坏小子恐怖组织有别的班的老大们暗中支持,现在拳头越来越硬,教室里几个好位置都被他们给占了。当然,班长政府军也有别的班的两个班长俄罗斯和伊朗帮忙,暂时也不惧这俩家伙。最可怜的是体委自由军,被戏称为“美国史上最渣队友”,派系林立一盘散沙,现在被削得几乎站不住脚,只能在夹缝中等着有一天安拉扔张馅饼下来。
然而离大马士革最近的就是自由军,大马士革东北部的朱巴尔区就掌握在他们手里,离市中心只有几公里。没事儿往城里打个迫击炮啦,发个火箭弹啦特别方便。今年2月5日,“伊斯兰军”的首领在推特上发话将炮击大马士革,那天整个城市落下300多枚迫击炮和火箭弹。距使馆只有二十米的公寓楼三楼被火箭弹炸出一个大洞,张志昇参赞就住在一楼,惊险至极。由于政府军的步步紧逼,有时候他们也会在市里搞个恐怖袭击什么的报复一下,我来叙利亚的第二个月,大马士革大学门口的地下通道发生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两死一伤,炸点离使馆只有一公里多。外交官们每次出去办事、会见,防弹车和武装警卫是标配,剩下只能看运气了。
战争的创伤
作为外交人员,随时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关注驻在国局势是我的工作之一。每天我打开电脑,叙利亚通讯社的战报是这样的:“英勇的叙利亚军队在阿勒颇省摧毁了数个恐怖窝点,打死大批恐怖分子,销毁了他们的武器。”而反政府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网站的战报是这样的:“今天上午,阿萨德政权空军向杜马市区发起无差别攻击,使用油桶炸弹和化学武器,多名平民在攻击中丧生。”媒体战已是现代战争的一部分,报道真真假假难以分辨。这更凸显了前方使馆的重要性。只有它在一线靠前观察形势,不受媒体干扰,及时向国内报回真实情况,才能帮助国内作出正确判断和决策。
作为前线的外交一兵,从这些平淡的报道文字后面,我看到血、看到火、看到饥饿、看到哭喊、看到丧子的母亲脸上顺着皱纹流淌的泪水、看到失去父母的孤儿眼中不知所措的茫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过那厮杀的场面,但经常听到这样的消息:“大马士革省水源地可能被恐怖分子投毒,近几天内自来水不要饮用”、“一座主要的奶制品加工厂被反政府武装占领,近期大马士革所有市场无法供应牛奶”、“大马士革变电站被炸,市政供电从原来的每天6小时减少到4小时”。战争的阴云,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飘过你的心头,蒙上一层阴霾。
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创伤是巨大的。使馆的老司机拉德旺,危机开始前用大半生积蓄建了一座漂亮的房子,准备搬进去安享晚年。然而仅仅一颗炮弹,多年的辛勤工作化为灰烬,现在他和死里逃生的全家住在老姐姐家里,每月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大家子人。领事部的姑娘拉娜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2013年他的弟弟作为政府军士兵上了内战前线,并在化学武器攻击中痛苦地死去。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兄弟”这样的字眼。叙利亚内战爆发进入第五年,造成20余万人丧生,1100万人无家可归。由于大量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从78岁下降至55岁。
我不止一次赞叹,阿拉伯人是一个坚韧的民族,他们世代生活在亚欧非大陆连接地带,蒙受战祸或许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宿命。不论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前被拜占庭和波斯两大帝国欺压、中世纪跟欧洲十字军的百年大战、还是20世纪后英、法的殖民统治、抑或是与以色列的连年战祸。给予所有强者的反击,就是活着,他们坚强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仿佛沙漠中长出的胡杨林,只要这地球上还有水,他们就能继续将枝桠伸向天空。我到过大马士革的一些地方,有购物中心,有农贸市场,有街头的平民咖啡馆,也有庄严的大清真寺。平凡的叙利亚人脸上很少见到恐慌、紧张的表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还得继续。如果真的要哭要喊,那就等我被炮弹击中的时候吧”。
我也不止一次叹息,阿拉伯人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自形成以来,除倭马亚王朝曾一统江山外,其余时间要么是众多“埃米尔”国甚至部落连年混战,要么是沦为外族统治,文化、语言乃至人种上都留下了多种文明交汇的烙印。在外部强权争斗的背景下,如前所述,这里一个2平方公里的雅尔穆克难民营,里面就有十几个武装团体,各卫其主,互不相让,苦的是那些黎民百姓。如此情景,已经上演了近千年,不知还会延续到何时。
在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生活的半年里,我无形中忘记了什么是愤世嫉俗,放却了除了生存以外的许多欲望,开始庆幸我无论走多远都有家可回,我的家人同胞不会把安全当作奢侈品。我常想,每个到了国外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接受一场爱国主义教育,到了战乱地区的人尤其如此。每次在办公室一抬头,看到窗外旗杆上面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总会想念家人,想念祖国,更想念祖国没有硝烟的天空和没有被铁蹄践踏的土地。想家的时候,我有时也暗自会心一笑——祖国之所以安全,有我在这里守卫付出的一份。
祝愿中国永远繁荣富强,祝愿华夏同胞永远远离战火。
韩冰
2015年4月14日于大马士革
(本文作者为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