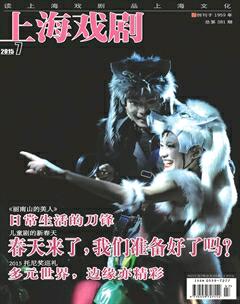高庆奎传(七)
李舒+余久久
从1921年到1933年,高庆奎迎来了演艺生涯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真正开创了高派风格,并最终以实力得到社会的承认,1931年京报提出老生三杰,高庆奎即是其中一位。这一时期,高庆奎从演员化身班主,他本身对京剧舞台上旧有的艺术规律,掌握得十分娴熟,所以纵横驰骋,与演员协力,排演了相当精彩的新剧奉献给戏友们。这一时期,穿插国破家亡之困境,高庆奎更是展现出伟大的爱国精神,连续排演了许多宣扬爱国思想的新戏,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他融会贯通南北京剧艺术,成为一名以京剧为武器进行战斗的先锋战士。这个时期的高庆奎,已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自在双庆社唱了大半年之后,1921年4月,高庆奎与赵世兴(原田际云的翊文社管事)从名字中各取一字成立了庆兴社,开始了挑班当班主的过程。高庆奎从上海回来之后,就一直搭俞振庭的双庆社,唱得红红火火,帮双庆社赚了大把银两。但时间长了,高庆奎也有不舒服的地方。起因就是班主俞振庭。从很多梨园轶事中都有说明,俞振庭做起戏班来,对人很苛,自己顾着赚大钱,只拿一部分钱开演员的戏份。日子久了,圈子也不大,大家就都明白了,纷纷要求离去。所以不到二十年,“双庆社”便溃不成军,自动解散了。高庆奎也有这种困恼,虽说俞振庭有知遇之恩,但长此以往,终是做了别人的枪手,于己无利。而此时,高庆奎从演唱技巧、名气以及人脉都相当成熟,也确实到了挑班的最佳时机。有了这番思考之后,高庆奎找到了原田际云的翊文社管事赵世兴,开始酝酿组班事宜。
为什么要找到赵世兴呢?这也跟梨园规矩有关。旧时梨园,凡事从事舞台工作,而非表演的人归“科”,分“音乐”、“盔箱”、“剧装”、“容妆”、“剧通”、“经励”、“交通”七科。其中“经励科”就是对外接洽演出事务、对内组织演员、支配戏码的人员,俗称“管事的”,在后台权力很大。要组织戏班,也唯有“经励科”的人,方有资格出面,再经梨园公会审核合格,才能进行。赵世兴就是民国以来相当有名的“经励科”之一。所以,他是高庆奎能挑班的必备条件。高庆奎演艺生涯如日中天,赵世兴对演员熟悉,了解观众心理,会派戏码,做了这么多年管事的下来,也积攒了不少戏院、税警机关、报社的关系。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各取一字起名为“庆兴社”。
在这个自己挑班的过程中,高庆奎展示了他强大的号召力,庆兴社(后改名“庆盛社”)一直活跃到高庆奎辍演的1936年,长达15年。搭班名角不计其数,带给观众们的名剧也相当丰富。
从演员阵容上来说是非常强硬齐整,庆兴社发展到后期全部演员多达一百多人,在当时实为罕见。下文中我们大概挑出几个来讲述一下合作经历。
高庆奎找演员并不是只去找名声大噪的,一些初露头角的潜力新秀也是很值得尝试的。程艳秋(后改名程砚秋)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20年始以梅兰芳学生的身份,在《上元夫人》中饰边配许飞琼。程艳秋也是个有心人,对剧艺勤学苦练,凡事有一定计划。1921年,他以第一期二牌旦角的身份加入庆兴社,1922年8月离去。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时间,但高庆奎对他的帮助很大。程艳秋有四出老戏、两出新戏的首演,都是在高庆奎的班里。
1921年4月16日,庆兴社打炮头一天,大轴为高庆奎、程艳秋合演的《汾河湾》。4月26日,大轴高庆奎、程艳秋之《打渔杀家》。5月1日,大轴为高庆奎《奇冤报》,压轴是程艳秋新学会的《奇双会》首演。高庆奎为了捧他,饰演“哭监”李奇,唱到“写状”为止。12月18日,程艳秋再演《奇双会》,高庆奎索性捧他到底,码列大轴,由“哭监”唱到“三拉团圆”。高庆奎自己再单唱一出《奇冤报》,不过,码列倒第三,可谓捧得用力。
在之后程艳秋演的《戏凤》、《弓砚缘》、新戏《南安关》及《梨花记》、老戏全本《芦花河》等,高庆奎都将其码列压轴,或者由自己及其他前辈合演。
1922年8月中旬起,高班旦角换了朱琴心。黄润卿是童伶须生黄楚宝的父亲,工花衫,不过后期当黄楚宝红了以后,他也就退出舞台,以辅导哲嗣为务了。韩世昌在高庆奎班,只在压轴单演一出昆曲,没有与高庆奎合作的戏。关丽卿、黄桂秋都是陈德霖的学生,两个人后来也都傍过马连良。关丽卿始终没红起来,黄桂秋后来到上海红了些年,创些柔媚的新腔,排了一出《蝴蝶媒》,非常叫座,老戏以《春秋配》拿手。高庆奎与小翠花、李慧琴合作的时间比较长,也一起合作过几出新戏。
红生中的王鸿寿(艺名三麻子)需要大书一番。他名头大了,是关戏宗师,南方的李吉来(小三麻子)、王荣山、林树森,北方的李洪春,关戏都是宗他的。其中以李洪春所得较多,李洪春也一直跟随着王鸿寿走南闯北演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洪春也来到庆兴社演戏了。后来李洪春成了北方关戏典范,发展得相当不错。
在李洪春的《京剧长谈》中记载道1923年王鸿寿先生再次来到北京,并与庆兴社结缘的事情。当时,王鸿寿本在北平某戏院经理梁德贵的邀约下,由天津来北京,在前门外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谁料想才演了两天,王鸿寿的帔以及换下来的鞋和衣服都不见了,无奈只好半夜去全盛鞋店买鞋,再准备衣服。结果,第三天的戏就没唱成。正巧这个时候,高庆奎和赵世兴一起来约他参加庆兴社的演出。梁德贵不干了,认为没唱够合同要求的天数,不成。后来,经过别人说合,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让王鸿寿和高庆奎合起来白给梁德贵唱一天戏”。高庆奎为了赶紧息事宁人,把王鸿寿拉到班子里,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在王鸿寿唱了《单刀会》、《八大锤》,高庆奎唱了《秦琼卖马》之后,这个插曲才算完结。王鸿寿的班子这才入了庆兴社。
王鸿寿在庆兴社的首演剧目是《挂印封金·灞桥挑袍》,码列压轴,大轴高庆奎《失街亭》。以后陆续还演了《关公月下斩貂蝉》,和高庆奎一起合演了《七擒孟获》、《三门街》、《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三国志》、《战长沙》、《七星灯》等剧,姜妙香、马富禄、郝寿臣、吴彦衡等都参加了演出。
其中需要重书一笔的是王鸿寿为高庆奎排的一出新戏——《七擒孟获》,在北平非常轰动。这出戏原是盖叫天在上海排演的,王鸿寿排时,自饰孟获,由高庆奎扮演诸葛亮。这出戏很有亮点,如布景、新式舞蹈等都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王鸿寿在扮演孟获时,带假下巴,执改良大刀,这都是新鲜之处。他还用架子花的工架、武花脸的开打来刻画这位蛮王。尤其在营中有一段喝酒“仰面朝天一声叹”的大段汉调,极为动听感人,在北平风靡一时。此剧初演于华乐园,之后连演多场,上座不衰。
但是因为王鸿寿的身体原因,他不得不于1923年9月离京返沪。之后,高庆奎仍常贴《七擒孟获》,不过孟获改为侯喜瑞,祝融夫人换为小翠花了。1925年,王鸿寿先生在上海去世,一代红生大师就这么离去。
王鸿寿和高庆奎在一起时日不多,甚至因体力不支的原因,传授《单刀会》时也只能由弟子李洪春代授,但他还是给高庆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的专业使得高庆奎为之折服拜师,二则是排练新戏的创造力深深打动了高庆奎,也对高庆奎后来的新戏编排生涯起到了领路人的作用,这些都对庆兴社的振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说完合作时间虽短但给高庆奎带来重大影响的王鸿寿,下面再讲一位和高庆奎合作最久,最得力的花脸演员郝寿臣。
郝寿臣是一位著名的京剧净角演员。他在刻苦学习金秀山唱功的基础上,又认真学习黄润甫的演唱风格,同时得到著名梆子演员的指导,打下了很好的基本功。他同时又是一个极具创新能力的人,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开创了“架子花脸铜锤唱”的艺术风格特色。他的唱功很有分量,唱或念出的每个字如咬金嚼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做功亦干净漂亮,如活生生的猛虎一般,让观者大呼过瘾。梨园除了老生和旦角,鲜少有观众为之专门买票观看表演的角色,但郝寿臣的戏,远非如此,他的艺术风格吸引了大把戏迷。所以,组建庆兴社时,把郝寿臣拉进来,高庆奎也费了不少功夫。但合作起来,非常意趣相合,两人一起舞台上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剧目,尤其是新戏创作上,郝寿臣助力很大。
高庆奎是个非常爱才爱艺之人,即便是当起班主,但从不会只顾着自己中饱私囊,而对其他人刻意盘剥。努力、有才之人,高庆奎从不吝付出,从高庆奎和郝寿臣的一则故事中也可见一二。当年剧院演出之地是北京华乐戏院,高庆奎和郝寿臣双挂头牌。每场包银,高庆奎一百元,郝寿臣为八十元。虽然在每次演出中,两人合演的重头戏很多,但高庆奎经常会有需要单挑起的大戏如《探母回令》 、《 哭秦庭》等,时间长,工力苦。再加上高庆奎才是当时的票房保障,所以有人劝高庆奎,认为如果以戏论酬,高应多郝一倍。高庆奎却是从艺术观点上分析说:“寿臣演戏,不惜气力,戏虽小而消耗力亦大。我们俩协力合作,不能斤斤于各自演出的戏幅大小而戏份悬殊。宁可叫你们瞧我值得多,我绝不多取而叫钱压着我的能耐。”这话后被郝寿臣得知,十分感动,也愈觉高庆奎的忠厚坦荡让人钦佩,更是专心致志和高庆奎一起合作。
身负名望,专业够强,却不甘原地踏地,在自己组班时仍拜师学艺,这样谦虚好学的高庆奎一直都走在前进的道路上,而心胸豁达,重才轻利更是让他得到一众好演员的追随。庆兴社,1924年改名为玉华社,1928年又改为广盛社,几经更名,却影响力不衰。后来更是名声远震,先后数次赴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巡回演出。1925年,高庆奎及班社为上海老天蟾舞台(原名新新舞台)举行首场演出。同台有李吉瑞、荀慧生、白玉昆等名家搭档。1930年1月30日,高庆奎的庆盛社(原庆兴社)又为上海黄金大戏院(后改为大众剧院)举行首场演出,并有张遏云、金少山等一批名角配档,阵容齐整浩大,演出非常成功。从材料上看来,从1923年到1930年,高庆奎率领他的班社至少五次到上海参加演出(有时是和其他班社合演),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