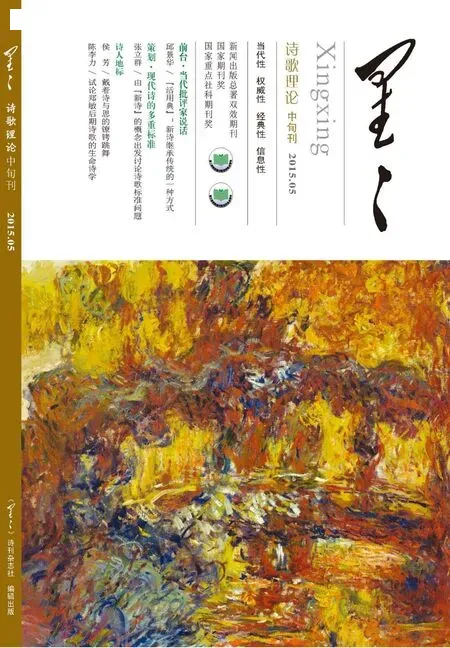寻找一首好诗的难度
罗义华
每月诗歌推荐
寻找一首好诗的难度
罗义华
诗总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首先,诗人没有我们想象的干脆利落,在诗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的两端,诗人总是犹豫不决的,有时候他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前沿,但在不经意间,他可能不断回望。将近十年前,华万里也曾醉心于词语和意象的先锋实验,譬如他的长诗《阶梯上的云朵》有云:“在花朵的缺口,我目睹了日蚀/光芒全是黑暗的蕊”,这是触目惊心的诗性表达!但是本期推出的《我的母亲》,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诗思和格式上的综合。其次,一首诗的面向与空间往往是受限的,诗或多或少,或显或隐,都要关涉到现实的政治、文化、伦理问题,诗人总是要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适度的空间。这方面的一个症候是,当诗人向外拓展,试图去理解和辨证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可能会直面个体与时代的紧张;而当他向内沉潜,悠游于个体的生命经验时,他更多可能获得自我的超然。第三点,并非所有的好诗都能够顺利问世,好让一般的读者仔细端详。诗人的圈子,选家的眼光,当然还有其他诸种因素,可以在一个时间段内划定一首诗的生死“界限”。事实上,选家总是有所顾忌的,不容易做到诗人的纯粹。所以,本期
《星星》推出的三首新诗,依然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在《我的母亲》中,华万里似乎有意收敛了他先锋实验的姿态。尽管,母亲“淡紫淡紫地死去”,“淡紫淡紫地闪烁”,自缢的绳上“打满了月光的结”,诗人的痛嚎“像石头在空中翻滚”,这些诗句依然泄露了诗人对词语和意象的唯美诉求,但是诗的色调更为沉着蕴蓄。很显然,当诗人面对已离开六十多年的“母亲”这一特定对象时,词语本能地让位于对象本身了。诗人对母亲的思念是从一种“牺牲”开始的,母亲“很空,很干净”,以至于她无法承受“生活的重和男人的脏”,简简单单的两行诗,道出了母亲的社会属性和她遭受的双重罪恶。这个母亲让人联想到了冯至“十四行之五”中那个“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的农妇:“像整个的生命都嵌在一个框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冯至的诗是超然的,他从一个作为个体的“农妇”看到了被固化的女性历史——“一个绝望的宇宙”;华万里毕竟没有冯至面对“农妇”的超脱,他要让母亲在梧桐花间“闪烁”、“摇曳”,恰恰是这种温馨的色调产生了慰藉人心的力量。
又见月光!马行的《阿尔金山之夜》也是本行、本色之作。马行的本行是野外勘探,这种独特的经验赋予了诗歌以某种“野性”。一个仪器工人从悬崖上坠落了,“他头盔里流出的血/怎么看/都像月光”,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对,很可能出自极端环境中的本色,更照见那些素昧平生的人生!马行的诗具有厚重的美,适合以观赏油画的姿态进入,不过,“阿尔金山之夜”的寥廓与浑厚,又非一般油画所能比拟。
不得不说,广子的《礼物(或春天的会议)》,带来了久违
的惊喜!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广子笔下的乌鸦不是一般的黑!这些兴师动众的乌鸦夹着春天的文件夹,并且步调一致,很显然它们是训练有素的,是被体制化了的乌鸦。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它们的喙,“怎么看都像一张鹦鹉的嘴”,“竟然换上了喜鹊的西装”,并且“聒噪声漆黑一片”。整首诗的内在肌理紧张得让人无法挑剔,但是,人间的广子只好以妥协的姿态收场。辽阔的“北方”让人充满了遐想,“四子王旗”的具象又将读者的视线拉近到一个拒绝联想的原点上。诗人不经意“闯入了乌鸦的地盘”,问题是,“谁能断言就没有喜鹊或麻雀混进了乌鸦的队伍”,这个细节制造了一个身份问题。很显然,诗人不是要辨析或者了断这个身份问题,恰恰相反,身份的含混化有助于诗歌旨趣的延伸。一首诗,让我们看到了广子突起的枕骨!一首能让人看到诗人枕骨的诗,注定会成为这个春天的经典!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冯至《蛇》的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