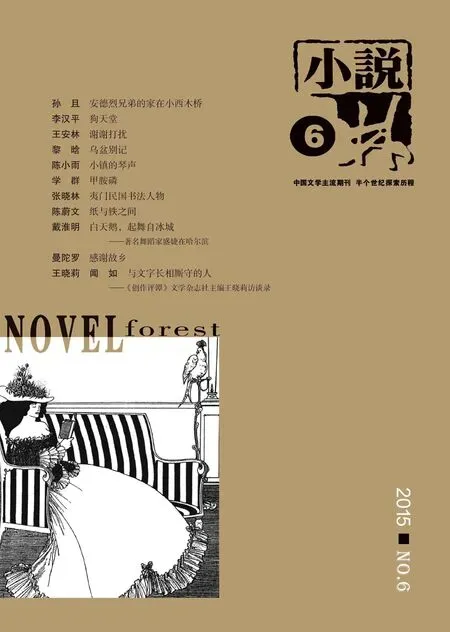纸与铁之间
◎陈蔚文
约了中午一点到美发工作室,在商场的18楼,第一次去。电梯内只我一人,数字键变换,一会儿显示“18”。
咦,门怎么没开?又等了几秒,它严丝合缝,没有开的意思。故障?我有点儿慌,虽然是白天,但待在一个封闭空间的感觉让人有种窒息感。
摁了电梯的报警键,电梯内响起连串嘈音,无人响应。我注视那个悬浮的红色“18”,大脑开始有点儿缺氧,我随手胡乱摁了几个数字,几秒后,电梯启动,停在我摁的某一层。同时,相当吊诡的,我身后突然冒出一个男人!
我被他吓了一跳,电梯门不是紧闭的吗?怎么他会从身后冒出?如果这是夜晚,如果他是个女人(夜晚的女人仿佛比男人更接近“鬼”的形象),如果这个身后的女人着素衣,留长发……
可这是正午,即便惊骇,我还是努力保持镇定,回转身时我发现——他身后,电梯门正缓缓关闭。原来,这电梯是双门的!我刚才悬浮在18楼时,其实另扇门已在我身后打开(可能电梯质量好,开门声音非常小),但我执著地仰望那“18”,等待当初进电梯的那扇门打开。我就这样和“18”僵持了好一会儿,摁了报警以及其他楼层键,直到这位乘电梯的男子进来。
电梯没有故障,是我的经验发生故障,将“电梯门”简化成了只有一扇的推断。
有年深秋在东北,住在延边安图县的一家宾馆,洗澡水放了好一阵仍沁骨冰凉,去找服务员,原来冷热水的标识错了!红色标识的是冷水,蓝色才是热水。而习惯了在某种经验范围里的我,宁愿苦等红色龙头流出不可能的热水,也不愿动手向另个方向扭一下。
——仅仅需要一个转身,仅仅需要拧一下另个水龙,可思维定势又是多么强大,它好似定身咒语,把人困在原地。
欧阳江河的《纸手铐》中的“思想犯人”因为用有毛主席头像的纸折了只鸟儿给女孩,被判大罪),在七十年代一座极为偏僻的,近乎抽象的监狱里被囚禁数年。那是一个物质极匮乏的年代:近千名囚犯,只有十来副铁手铐。
于是,纸手铐被发明出来。囚犯如果违反了狱规,其惩罚不是直接用铁铐实施,而是以狱管人员即兴制作的纸手铐来象征性地铐住囚犯的双手,惩罚时间从三天到半个月不等。惩罚期间,若纸手铐被损坏,则立即代之以铁铐的真实惩罚(铁手铐每副重达30公斤)。如果惩罚期满时,纸手铐仍然完好无损,则不再实施铁铐的惩罚。
纸成为铁的替代。轻被注入重,虚被转为实——这真是一项充满隐喻,富有想象的发明!
那位对毛主席“大不敬”的囚犯出狱多年之后,这种“纸手铐恐惧综合症”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他双手解放了,但内心的手铐固定在某处,永远呈现出被铐住的样子。他只有在被铐”的状态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觉到手”的存在,才能安然入睡。他依靠对纸手铐的想象活在世上,纸手铐对他来讲既是恐惧又是一种类似乡愁的“迷恋”。
有没有比恐惧更隐蔽,但又更直接,更具有原理性质的东西在起作用呢?纸铐铐住的其实不是真手,而是纸铐发明出来的非手。纸铐铐住的现实,看似荒谬,却普遍存在于现实。纸铐既是刑具,也带来莫大“安全感”,这种吊诡关系使人在一种固见中生活下去。密不透风。即便你站在广袤的荒漠上,精神或者意识仍然在身体的纸铐中。
有些人,行过万里路,却还在原地。“走”的动作只是一种拟态、无意义的迁移,如果纸不撕碎,手铐一直在。人并没有离开,始终在纸拷中。
在纸铐的“无意识”中,一切只有一个面向,一种可能。
“想象中的监狱比真实的监狱更可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关在里面,但又可以说人人都关在里面。这个监狱是用可能性来界定的”。
这可能性就是生活环境、观念给人烙上的印记。
曾在聚会中碰见位多年不见的同窗,在去酒店的一刻钟车程中,他滔滔不绝地发表言论,用看透这世界一切猫腻的口吻,批判人际、政治、单位以及女儿的学校。有人试图反驳,他马上打断,以宣布真理的绝对重申他的观点。他瘦小身躯迸发的偏激令人吃惊,或许是某些遭际造就了今天的他。他的定论伴着激愤,他就像戴上了一副纸手铐——那副手铐就是生活认知带给他的褊狭,他被禁锢其中而不自知,因此他也根本不打算挣脱一下。
“纸手铐之所以具有威慑力量,是由于纸里头有‘铁’这样的物质”,这个铁,就是生活的惯性,视角的惯性,它有时将人带进自我的死胡同。
那次聚会,那位同窗有事先走,他的离开似乎让所有人暗自松了口气。在他的口头禅“现在的社会……”中,散布着病毒般的怨愤之气。当然这与他现实处境有关,他做过若干行当,但都没赚到他期望的钱,他认为自己智商不比任何人差,甚至高出普通人,他有技术,懂些音乐,末了,却是个辛苦的“失败者”——这“失败”他认为是由社会的不公造成的。另一方面,他从“失败”中提炼对这种激愤的依赖,在激愤中他既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也为自己的见地,为自己比其他人对这社会更“深入”的了解而亢奋。
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所受的苦如果只是化作了一堆“看透”,那么或许真的白受了。
命运的最大敌人,往往不是外部,是来自内心的偏见对自我的禁锢。
“和别的客人在一起时,我总觉谈话就像一个超越障碍的训练场,矛盾、竞争和误解等构成了重重沟壑和围栏。我理想中的谈话应该能让参与双方都能畅所欲言,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完满,而不是无休止地设定和重设条件,为结论辩护。它甚至可以不需要得出什么结论。”
麦克尤恩小说中的主人公说的,这的确也是种理想之境的谈话,无论是与亲人,或爱人。只为交流而说,敞开心扉,不设置任何围栏,不把奉行、推销那个“我”当作谈话最高目的。
这种完满的表达并不易,需要平心静气。
许多人身体里大概都住了一个固执的“我”,年深月久,有些“我”甚至已锈死,再不能扭动半分。
有时我们管这种见识的执拗叫作“个性”,或不妥协的骄傲——其实,那未必是见识,很可能只是偏见。
在许多的“个性认知”中,有着盲目的认知封闭:电梯只有一扇门;蓝色开关是冷水,红色开关是热水;凉粉一定不能加醋,牛肉里必须加土豆;孩子一定要打,不打不成材;甜的水果中一定注射了甜味素;爱好文艺多半是出于附庸风雅的需要;只有抽离了感情的零度写作才是大师范儿;一个明星贴出家事申明一定只为炒作……诸如此类的定式“经验”太多了,饭桌边、微信中,到处充满不容置疑,到处是鹰眼识破,高明见地似乎只有在层层“撕开”中才得以成立。
信任、包容、倾听,这些最基本的人际美德去哪了?那么多的心上装了三重保险的防盗——它不对善开放,只对恶,只要是恶的消息,人们宁信其有。而善的讯息,人们宁信其无。
不是揭露“恶”才有价值,有时维护善更需要宽大的襟怀。它是对世相、人性有更多理解后,仍接纳这个泥沙俱下的世界,因为知道,自己也属它的一部分。
在网上看一帖,一个女子为如今要不要赡养母亲而纠结:父母从小离异,母亲那时喜欢上一个男人,随他而去。她和妹妹一直跟着父亲,如今她长大成人,结婚生子,母亲和那个男人已分开,身体不好,希望女儿能负担自己的生活费。
跟帖的网友骂声一片,自然是说这母亲如何不知廉耻,好意思来找女儿,当初干吗去了?也有骂帖主,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不赡养!让母亲死一边去,现在怎么不去找那个男人呢?
女子说到当年在厦门打工,母亲来看过她,却因为长期不在一起而无言,母亲默默住一晚走了。
面对这些骂声,人们是否也稍微地想过一下那位母亲的感受?据帖主说,父母没什么爱情,也是造成她母亲当年离家的一个原因。是的,人们要求一个当了母亲的女人只能是母亲,而取消了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爱与自由。一旦她有感情的需求,想从这个“家”里出走,她就要像《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一样,被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这个耻辱的标志伴随她一辈子,甚至她为此要剥夺掉被儿女赡养的权利。
在“道德”旗号下,这种审判的声音不容置疑。任何一个跳出为母亲说几句话的网友都遭来谩骂,这种骂声太熟悉不过,各个时代各种场景下,都能听到同频率同语调的骂声。
感谢可敬的托尔斯泰,给了出走的安娜一个为爱情绝望赴死的经典形象,而不是一个自作自受的荡妇。但,距小说首版发行的877年过去这么久,让人失望的是,对女性的审判标准仍是如此粗暴、单一。
在骂之前,显然骂者们都先爬上了道德的高台,他们简化现实,从单数涌向复数,他们不欲了解这个“母亲”曾经历什么,她的苦痛,无奈,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遭遇了哪些事情。他们只是喷出口水,将臭鸡蛋奋力砸过去。
许多暴行就是这样产生的,不欲了解,加上可怕的偏见。他们抽离了自身,让自己悬置起来,成为假想中的上帝。只剩下简单抽象的价值判断,缺乏常情,他们忘了,自己或亲友也可能遇到和当事人同样的情境,同样可能遭遇简单粗暴的审判,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许他们肯花点时间,从一个义正辞严的审叛者返回去,成为一个人。
曾经,为找一首歌,搜到一首陌生的粤语歌,里面有几句歌词:
不管为何 沿途如何 它都长流
铁和石也可割破 这是过山的河水
它奔前流流流 不管蹉跎
为流入滔滔大海 方会安心而存在
不管为何 沿途如何 它都长流
我怀内那些爱 也像这一江河水
永为你也永向你一生奔流
我喜欢这歌词里的执著,以及“不管为何,沿途如何”的相信——“我不相信”很容易,不相信之后的仍然相信,很不容易。
“我不相信”,只需要一种单一的判断,就像认为电梯门必只在正前方开启。“我相信”,那是在判断里加进了情怀、信仰、包容,对这世界和自我的体恤。是转过身,让视野朝向更多的门。是相信穷荒绝漠鸟不飞的地方,仍会有一眼清泉在地下汩汩而流,等渴者前来汲饮;相信千帆过尽,仍会有一叶小舟乘风而驶,接应羁旅游子。
在《圣经》中,“信”出现了565次,足见信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希伯来书所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不仅是信自己的可见,也信那些“不可见”。在“不可见”中,也许有陌生的景象,甚至不被我们理解的事物——但或许有一天,你突然就理解了,领会了。你发现,曾不被你理解甚至排斥的事物,它们其实是“常理”,它一直在那儿,等待与你的相遇。
就像近几年,我与白色的相遇。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衣柜里全是灰蓝黑,尤其青春期,我认为白色就是一种“不可见”,危险而浅薄,它会使人体形膨胀,暴露无遗。我那时的最高美学奇怪地相悖着:一方面喧哗与骚动,另一方面力求隐蔽。记不清,哪一天突然有了与白色的相遇。它典雅,白洁,使人在灰暗的日常中有一抹亮色。这个转变其实依托于一种心绪,带有自我接纳、镇定,以及对“自我能见度”的提升。
在衣柜寂静的深色系中,增添了若干件白。像是一间封闭的屋子,开了扇窗,光照了进来。
有些事物没发生时,不代表不存在。是人未得所见,退一步,转个身,从自我意识里出离一下——就像挣掉具有铁的内质的纸手铐,它就显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