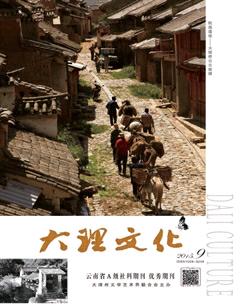聚会
胡子龙
傅富
两天的时间太长了,长得漫漫无涯。
两天的时间又太短了,短得就像我暂短的上学生涯中最后一堂课老师特别给我们讲解的那一个形容词:一瞬间。将近十多二十年,时间在我的感觉里就是这样的,别说两天,哪怕十天半个月,也都是一瞬间,叫我无比惋惜——活到一百岁又怎么样,还不过是眨眨眼睛的事情,何况很少有人能活过一百岁的,我爷爷辈、父叔辈没谁活上八十,想必我无论怎么保养也活不到一百岁。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支配着,仅仅四十出头的我,总觉得享受纸醉金迷的时日已经不多,对生活对生命产生了强烈的留恋。还是我这老家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们会形容啊:人穷春长,家富冬短。上学时总是找不到感觉的那些词句,什么“光阴似箭”,什么“日月如梭”,什么“朝如青丝暮成雪”,在这些出人头地的好日子里一下子就找到了。
这长与短的感觉,都让人刻骨铭心!
我是今天一早从一千多里外我自己干大事情的那个城市连夜回到老家月亮坝烂泥湾的。略一默算,我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回来了。上次回老家离开的时候,我预计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一回到这个让我穷寒怕了也曾经让我憋屈够了的远乡僻壤我就心堵。父亲前年里随早六年去世的母亲走了,二老相伴着长眠在卧龙岗龙眼处的松荫下,老家也就再没有让我不得不牵挂的,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再能牵引着我回来了。虽然有两三个跟我称哥们的人,在一起喝上几杯,也能找到一点愉快轻松的感觉,但愉快和轻松早已充斥了我的生活,膨胀着我的生活,和他们在一起给我带来的那点愉快轻松也就属于可有可无不关轻重。跟这几人称兄道弟,也是在老家这地头了,要是在外边,在我纵横驰骋的那个天地里,明显是辱没我的身份的。在当今中国,我不算最富有,甚至理智时想想,我充其量也只算是中富,比我富裕的人多的是。但我名下也有将近八千万元的资产啊!八千万元,就是八十个老家村子绑在一起和我同时放在天平上,显重的一头也绝对是我。别说傅连和他们这几个小瘪伙,就是多少政府官员,还有多少不当官但也吃着国家俸禄的,都想方设法跟我套近乎,风穿墙裂缝地想跟在我屁股后边转。当然,看在光着屁股就在一块儿玩泥巴的份上,看在一块儿去林洼里偷梨子的份上,我不会彻底拒绝和这几个小瘪伙交往,给他们一些唾沫星子样的好处我也乐意,但要想得好处,往后就必须出去找我朝我拜我,而决不是我千里来迁就他们——凭啥?
意想不到的是,我还是回来了。没有带我的司机,也没有带平时的任何一个随从,连我的保镖我也没带,让两个特殊身份的人陪着,开着他们的车连夜回来了。在上路前的那个刚刚下了一场雨的残阳黄昏,我感受到好多年不曾感受过的浓重的孤独,在冷嗖嗖的早春风里,几乎是在一秒中做出决定:回老家一趟去,与当年的少年伙伴们来个聚会。
大概只有我心里明白,这个聚会对我意味着什么。
傅连和
大老板就是大老板,有钱人就是有钱人,能当上大老板,能拥有成千上万的钱,就是人样,想玩黑的就玩黑的,想玩红的就玩红的,想来风雅就来风雅。人家搞大学同学聚会,搞中学同学聚会,傅富连小学五年级都没上完,虽然也有同学,但在大学生高中生伸手一抓就是几个几十个的当今,这种层次的同学是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同学的,搞了就容易逗人嗤笑,就别出心裁地来个少年伙伴聚会。操他妈的,我傅连和这辈子算是定型了,成不了器,更成不了像傅富那样的大器,下辈子托生的时候,阴间地府里,三叩九拜,眼泪巴拉求,鼻涕口水求,也一定要请阎王爷给我傅富一样的脑子一样的胆量,像他傅富一样,玩巧玩奸玩黑,玩上个大老板当当,然后再十倍百倍的玩巧玩奸玩黑,什么时候来心肠了,也风雅它一把。
傅富一回到村里,车停下,就到我家找我。那时刻正是太阳从坝子东边卧龙岗绿林里探出半片脸的时刻。我是昨晚上背着铺盖卷从外县回来的。跟着堂舅在基建工地上泥泥水水干了一个月,红闪闪的纸币倒是挣了四五张,可也把我累得骨头快散了架,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干过这样要命的苦活呢,真恨老天不公平,世界上有那么多既轻巧又拿钱的事,却怎么也轮不到我。当然让我毅然决然回来的原因还有一个:一个月多,我没能摸摸我心爱的猎枪了。昨晚回到家,吃了老婆给我热的菜饭,取出我藏得非常隐蔽的猎枪,擦了又擦,然后进里屋,一膀子甩开毫不羞耻地想跟我黏糊的麻脸婆娘,倒在床上蒙头大睡,一心一意养精神以便天亮了到老林子里追兔子撵野鸡,好不快活。傅富来到我家大门口的时候也恰恰是我睡过了头急急忙忙提了悄悄藏下的猎枪打开大门往外奔的时候,在大门口和他撞了个瘦脸对胖脸。我的瘦脸对着他的胖脸,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以为今早上是大个的太阳呼隆一下子滚到了我家的大门口。他的突然出现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是,他竟然到我家来找我,给我这样大的脸面,虽然从辈份上讲我要大着他一辈,他该喊我小叔的。他没离开家时也曾不止百次千次裤管高一只低一只头发乱乱地上过我家门,“小叔小叔”喊我去抓鸟蛋、偷桃梨、下猎扣捕流浪狗,有时候我因为心肠不好或者爹妈安排事做不去,他还苦衷哀地求过我,可自从他到外面闯出了一片令人头晕目眩的天地后,他什么时候再喊过我一声“小叔”,他什么时候不经三邀四请就主动上过我家这道穷门?就是我腆着老脸不断地三邀四请,也就是他带着新老婆回家住了整整三个月的那次,禁不住我的软磨硬缠,到了我家一趟,屁股没在我特意为他揩了又揩的沙发上压一下,站在堂屋门前坎子上吸了一支他自己的烟,烟头一摔就走了。每次,都是我去拜他。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人家是有大钱有大身份的人,凭什么主动来我家门上找我,就凭我辈份上比他大,是他族中小叔?去他妈的叔了爷了的,如今社会,天不大,地不大,那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只听说过的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更谈不上大,爹更不大娘更不大,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让人家这样大个老板白己主动上我这道穷门,不就是想让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嘛!那样,这个世界不就颠了个倒了?
今天,就太不正常、太不正常了。难道他仗着他老爹老妈的坟葬到了卧龙岗龙脉上,在外面把事情做得更大了,大得钱堆成了一座喜玛拉雅山,饮水思源,突然想起两年前他强占卧龙岗荫家国家的祖坟坛作为他家新的祖坟坛的时候,我鞍前马后为他出过大力气,现在特别地来关心我这个早就跟他出了五服的小叔了,我傅连和从此可以仰仗他,在他这棵参天大树下掠几个枝叶的阴凉了?
我很快知道他带着两个人屈尊上我家门来找我的原因:他要把他尚在家乡的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少年伙伴邀请拢来,热热闹闹搞个少年伙伴聚会,请我亲自上门去为他发请帖——不,准确的是发邀请函。
邀请函——这叫法他妈的要多气派有多气派!
这毫无疑问也是好事,或者说是好事情的开始。任何事情都有个过程,就像我到老林子里打野物,先要造好铅弹,然后背着枪上山,然后满林子寻踪觅迹,然后开枪,如果猎物没有立即毙命,挣扎着逃出了一程,我还要寻着血迹找,然后带回家,然后宰杀,然后起火上锅炒炖,最后下着小酒美滋滋地享受。
老侄,哦,不!不!傅富大老板,你放一万个心吧,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保证,向咱们的伟大设计师邓爷爷保证,坚决地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任务!只是往后,你别忘记了论新旧功劳行赏,给我一些好处!
费兰兰
我是在海子边的菜地里接到傅连和送来的邀请函的。
我的右耳已经基本上聋了,那是少女时代耳朵红肿又遭遇了一个庸医的结果,我的全部听觉就依仗左边耳朵。恰巧当时傅连和将自行车停在了我右边的土路上,傅连和对我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有听清楚。傅连和大概是不耐烦了,大声说:“反正你家有个高中生,你拿回去让你儿子给你看吧。”递给我一个红本本,跳上自行车走了。
我端详着傅连和塞在我手里的红本本,看清楚这个红本本不是书,是……是什么呢?我一下子闹不清楚。站在菜地埂上想了老半天,渐渐地想出些眉目,对,请帖,应该是请帖。像我这样的人家,我家现在的社会关系,客我家倒是经常做,谁家都免不了有个三亲六戚,有三亲六戚就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客事。但我家从来没有接过请帖。他们亲戚间请客,都是上门说一声,或者请人捎个信。但这样的东西我在我那个在水泥厂工作的妹妹那里见到过,有一回一见就是四五本,妹妹直抱怨做客都把钱币和时间做穷了。想不到,现在也有人给自己发这东西了。
那呢,是谁给我家发来了请帖呢?是娘家二哥吧?娘家二哥下个月就要为大女儿找女婿了,请我家做客是理所当然的。想到这里,我心里立马就有些梗塞,有些不舒服。二哥也真是的,都是自己亲姊妹,忙得过来你到家里来说一声,忙不过来你就带个口信,何必送这样一个东西,你感觉新鲜,我还感觉生分呢!……不对,不会是二哥发来的。二哥是当上门姑爷到落鱼村落户的,而送这东西来的这个傅连和,是自己娘家村的。娘家村隔着落鱼村十里路,二哥跟傅连和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咋会找他来送请帖呢?我打开看,果然落的不是二哥的名字。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些年为生计奔波,把老师教给的那些个字差不多都还给老师去了,但二哥的名字我还是认得出来的。再合起来看封面,红底上像用金粉印的三个字,我只认得中间那个请字,好像也不是请帖。该不是什么人看自己老实本分,给自己下了一个什么扣子等着自己去上当?想到这里,我有些慌了,赶紧将红本本装到口袋,抱起菜回家。
回到家,我就把红本本拿给上高中正在家里过周末的儿子看。儿子打开粗粗一开,就欣喜地叫了起来:“妈,好事,好事情呢!”
我说:“什么好事情,让你欢喜翻了天?”
儿子:“这是傅富那个大老板给你发来了邀请函,邀请你去参加少年伙伴聚会。”
我说:“傅富?邀请函?少年伙伴聚会?”我一头雾水。
儿子说:“妈,你也真够可以的,对你这样出名的一个少年伙伴,你都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傅富,就是外婆他们村里的钱大头,在外面干出了大事情,当上了大老板,如今回来,请你们这些小时候跟他一起放过毛驴打过猪草砍过柴的人,到镇上逍遥客大酒店聚会呢。他掏钱,好酒好菜招待你们。”
原来是那个人发来的。想起来了,他的名字就叫傅富……不,小时候他的名字应该叫傅子富,不晓得什么时候把名字改了。娃娃时候倒是比较要好的,长大后,自己嫁到这村里,就少了来往,和他好多年没有打交道了,几年前在街上见过一面,互相没有打招呼。我把红色邀请函随手丢到有些油腻的桌子上,开始择菜。
儿子:“妈,你记准时间和地点,免得赶过了。要不,我帮你记着,后天我不去上学了,我打电话请一天事假,我送你去。”
我用眼睛白儿子:“去干什么?去吃他一顿?吃一顿能饱一辈子?”
是啊,去干什么?听说这个人有了大钱,什么都是几倍几倍地享受,都享受得疯狂了。不说别的,就连老婆,都像买糖葫芦,大老婆小老婆成串,有一回,一次就往家带了三个老婆。这样的人,自己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婆,去招什么腥!再说了,当年一起读书的那十几人中,个个日子都比自己过得光鲜,但都比不上他傅子富。他傅子富这样做,还不是想在老同学面前显摆显摆!自己日子是过得有些苦,可再苦,也是自己的日子,自己养鸡宰鸡吃养猪宰猪吃,但不会做着梦儿去想天上的凤肉龙肉吃。再说了,不说其他鸡杂狗碎的龌龊,就凭他两年前耍尽手腕迁开荫家国父母的坟占龙脉为他爹他妈造大坟的缺德事.跟他往来,自己还嫌降低了身份呢!不去!
儿子:“妈,后天我带你去。这是个机会啊!他那样大的老板,跟他有了交往,我考不上大学,我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也方便去他那里找份事情干。人家拔根汗毛都比我们腰杆粗呢!”
我生气了,把手里正在择的菜摔到了地上:“说出这样的话,你臊也不臊皮。你妈大字不识一个,却知道做人的道理。咱不怕穷,就怕没志。你妈起早贪黑苦挣着供你读书,你就这份没志的想,叫你妈寒心。我说,你真只有这点想,你干脆别读那书了,到街上乞讨去!”说着,将那大红的邀请函塞进灶膛里,烧了。
王玉清
接到那个把“傅子富”改成了“傅富”少年伙伴聚会的邀请函,我心情很沉重。
他这个从天而降的少年聚会证实了这几天来小村里的所有传讲都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他走到这一天,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他这些年这里那里的做作!他的很多事,虽然我们也只是耳闻,还有一些,甚至只能靠揣度,靠综合分析。但凡是稍微有些头脑的人,都会连前想后揣度出个八九不离十。常言道天网恢恢。当然漏网的也不是没有,但不会太多。太多的违法犯罪者都漏网了,无休止地逍遥法外,无休止地逍遥法外继续违法犯罪行凶作恶,那我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这个地球不就废了?
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他跟我是从小的朋友,从小的同学,从光屁股时候我们就在一起玩,然后一起上学一起干活。说实话,儿时的他并不坏,热情,机灵,虽然有些时候会来点恶作剧,做出些叫人头疼的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可这也是孩子的天性哪,我们哪一个在做孩子的时候不曾有一些乍看起来“出格”的言语行为?有一天,我们曾是少年伙伴现在也相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聚在我家喝酒聊天,还谈起过曾经的事情:头天,他带着我们悄悄摸进生产队果园,用一把坏锁锁住了看果园的老头,猴子攀枝一样地尽情享受,第二天一早上山砍柴,在河边遇到了一个神经失常的女人,撕扯一头开始发臭的死猪吃肉。我们都觉得恶心,纷纷掩鼻子跑开,只有他没跑。不但没跑,看了好一会,默默地将他带的在回家路上饿了吃的几个包谷粑粑放在那疯女人面前,然后去追赶我们。
他为什么变成了后来这个样子?很多人一致地认为是钱的缘故,是钱多了烧的。当然有钱多了的缘故,但把一切都归咎于钱多了未免太偏激。可以断定,他做出足以毁灭他人生的第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时,他压根就是个穷光蛋。他走到这一步,除了他自身,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比如从小就娇生惯养他把他这个独生子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风吹了的他妈妈,比如态度粗暴性情无常打他骂他是家常便饭的他那个酒鬼父亲,比如总看他不顺眼的乡亲,比如作为少年伙伴的我们——他将他带着饿了吃的包谷粑粑慷慨地给了那个饥饿中的疯女人,我们不但不认为他是在学习雷锋做好事,相反还集体狠狠地嘲笑了他一阵子,还有就是我们的老师,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也没有给他哪怕轻描淡写的一句表扬,只是在嘴角挂上几丝笑意。即便是当时还处于半懵懂状态的我们,也看得出,老师的那笑,是好笑。
如果说他成年的人生是歪瓜裂枣,那是因为他没有从瓜藤上枣树上得到一个好瓜一颗好枣所必须得到的正常的养分。
他现在肯定是很后悔的,否则他不会在他走到人生的绝境时,还要回来与他当年的伙伴们聚一聚。我也是很后悔的,后悔这多年来,我没有尽到一个少年伙伴应该尽的责任。
他邀请的这次聚会,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去,我是一定要去的。作为朋友,他走到这一步,我也有责任,明天我要是不去,我连表达自己良心歉疚的机会都永远没有了。
有人来我家了,是荫家国……
荫家国
少年伙伴聚会……聚会你娘个蛋,傅富你这个比马养毛驴下的骡子还杂种的杂种,你也有今天啊,猖狂得不可一世的你从来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我是从田里回家的路上,在村口那棵老柳树下几个做针线聊白话的姑娘婆娘那里得到杂种傅富倒霉了的消息的。我来到树后,她们声音很低的聊白被我在不经意间听到了最关键的:钱大头、公安局、手铐、枪毙。我平时很有些瓷实的脑子一下子好用起来:难道……那一刻我还不知道他发什么邀请函的事。只觉得这消息太意外了,意外得让人不敢相信。我丢下手里的工具,走拢他们:“嫂子,你们是说……”那个我喊嫂子的对我道:“家国,这大的事,你还不知道呀?全村都传开了,钱大头出事了,被那边公安局抓了,听说肯定会被法院判死罪,要吃枪子的。今早上,他回来了,是公安局押着回来的。”
我三步并两步回家,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老婆。老婆没说什么,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个我没有注意到的大红本本,递给我:“你高兴什么高兴,人家回来了,还给咱家送来了这个呢。你也不想想,他真让公安局抓了,真要等着判死罪挨枪子了,还会回来大饭店里请客?”
这个大红本本就是他发的邀请函。
端详着他发来的邀请函,我的脑子愈加灵光了,我那一刻激动的呀,浑身上下在抖,心也差点儿从喉咙里蹦出来了。我捏着大红本本转身往外。
老婆追着出来:“你可别听风就是雨的去闹呀!你不想想,连支书都把他放的屁当成圣旨,他会轻易倒霉吗?我们弱家小户,人家有钱有势,拿钱能让鬼推磨,咱细胳膊扭不过人家的大腿。那大的事情你都忍了,这点还忍不下?”
我不理睬老婆,激情间大步地径直到了王玉清家。王玉清一把藤编的圈椅坐在院子里,手里也拿着一个跟我手中一样的红本本,好像是在认真地琢磨。
我之所以什么也不说就来找王玉清,是我最敬重他,也最感激他。不仅仅我,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敬重他,凡事少不了要找他掂量个轻重,拿个法子。他也算是有钱的人,一幢房屋就值几十万。但他不像傅富,有了几个钱就狂,狂得连自己爹姓什么了都不知道,狂得见只猫见只狗都想糟蹋一脚。他从来都是心性平和,对老对少一副笑脸,谁需要他帮个忙,只要他能够的,他都乐意。特别让人钦佩的是他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别的不说,就说前年里,我被傅富和村支书软硬兼施迁走了我父母亲的遗骨,腾出地皮让傅富给他爹他妈造大墓。让我迁坟的时候王玉清不在家,到外省做松茸生意去了。傅富爹妈大墓落成的时候,他恰巧回来了。他听说后,立即赶到卧龙岗山,当着多少人的面,一脸厌恶地把傅富捧过来的一杯酒摔在地上,扬手就给了傅富一个耳光,打肿了傅富这狼心狗肺的东西的半张脸……
我说:“王哥,傅富这驴日狗养的栽了,我要铲了他傅富爹妈的坟,把我爹我娘迁移回来。”
王玉清往有山有水的大理石桌子上丢了红本本,抬头望着我:“现在要迁移回来,那前年你咋要把两位老人迁走?”
我说:“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他傅富,还有靳林那个狗养的,一天几趟往我家跑,说好话,说坏话,人家钱多势大,我害怕日子过不平安,才答应的呀。我答应了,我也就背了一辈子的耻辱,让人看不起。
王玉清:“你的意思是,他傅富进大牢了,被枪毙了,你把你爹娘的坟往回移了,你这心里的耻辱就没有了,就让人看得起了?”
我一时无言。
王玉清拉我在他旁边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慢声细语地:“家国,事到这步,我看就算了。别的不说,把你爹你娘的尸骨挖来挖去移来移去,你就忍心两位老人遭这份罪?让他们好好的歇息吧。你也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人心一杆秤,你是个啥人,他是个啥人,乡亲们心里明白着呢,天也明白着呢。再说了,他傅富能在自己走人绝境时最忘不了的是我们这些少年伙伴,说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保有几分良知的,我们作为他的少年伙伴,能连一点点同情心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