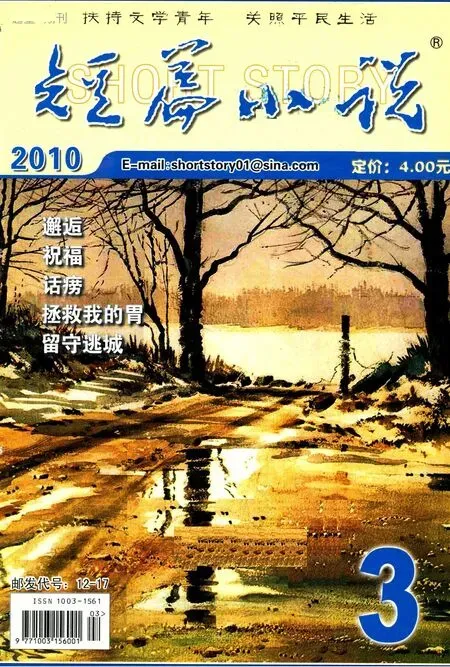游戏规则
◎张艳东
游戏规则
◎张艳东

一
艾厚军从县里回到村里时,已经过了晌午。这是坝上的六月份,还没到多雨的时候。坝上多雨的季节在七月。老天的性情谁也说不准,长短是不按庄稼人的意愿来的。返回的一路上,衣服干了湿,湿了干,冷暖了好几次。对于厚军来说,这都是无所谓的,要命的是心里冷。厚军堵得慌。为了这点破事折腾了七八天,脸色看了多少,冷言冷语承受了多少,精力和损失白搭了多少,心里明镜似的。
从柏油路拐下村子时,艾厚军下意识地往村子后面走。这条小路僻静。厚军很厌烦村里的人向他问询打听。转过这条小路几十步,厚军停住车,想想没什么丢人的,干吗要躲?可还是忍不住下了摩托,犹豫着。前面大路边的菜地里,有很多忙碌的身影,厚军隔着那么远,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张拾翠来。心里的不安和内疚一下涌上来,不知道自己的这份坚持是否值得。
拐上村前的大路,劈面碰上马宝。马宝开着拖拉机过来,拖拉机里放着耕种的农具,一路乱响。水泥路还没修到这里,搓板路,跌蛋坑哪个也躲不过。马宝板着脸跳下车来说,这回咋样?扑空没?眼睛却围着摩托车转。摩托溅了好多泥,侧面的护盖脱落了下来,歪斜着。厚军用腿夹了一下。厚军想告诉马宝,这次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虽说没见到正经管事的人,可是工作人员给了他电话。没打通是另一回事。厚军松开腿,护盖又掉下来,厚军说问了个电话……可是马宝并不关心这个,马宝拍着摩托说,叫我说你什么好呢,老艾。你看看给弄成什么样了?不是你的是吧,真舔球!厚军讪讪地跨下摩托,挠着脖子说,路难走,震的。你放心,下回去县里给你换——还有下回?马宝的话变成锋利的大片刀,一下把厚军的解释砍得没有了尾巴。厚军摸着嘴上的胡茬还想说,马宝却转过身上了拖拉机,真舔球!马宝挂档的时候又骂了一句。
大门虚掩着,厚军进了院子。门坎到门前水泥路的一段,没有过度,塌下去半腿深,好多天了,在那里张着嘴,又像掉了牙。和他一排的左右邻居早已修好了,下面还铺有排水管道。灰白平整的水泥路面,连着门前的大路,干净整洁,赏心悦目。可赏的是别人的心,悦的是别人的目。厚军看着只感到揪心。
张拾翠先到的家,听到门响,从外屋的灶台旁抬起头,看男人的脸色就知道十有八九白跑了。这些日子拾翠也疲了,自己男人的性情脾气她是知道的,这么多年拿不住,就只能顺着来。拾翠热了早上的旧饭,问,跑得咋样了?厚军说交通局的人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还没打。厚军没好意思说打不通。拾翠对这些并不是多上心,她关心的是地里的菜。说吃罢饭赶紧下地吧,七八亩我真是忙不过来。告状的事先搁一搁。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厚军停了筷子说。说话时饭渣子从嘴里往外喷。能缓吗?等工程一完,卷铺盖走了,我真成了村子里的笑把子。老婆劝不动厚军,擦了脸上的饭渣子,打几声嗝,下地去了。厚军很快地吃完饭,打了三遍电话,依然没人接。然后从园子里接了水管,把摩托仔细地洗了一遍。马宝的摩托骑得很邋遢,好像从来就没洗过,厚军把多少年的老污垢都清理了出来。要说马宝对厚军还是不错的,厚军刚开始和工头姚占红跳的时候,不光言语上向着他,在行动上也紧跟着,比如借给他摩托车。“老艾,你可要知道,我的摩托车没有往外借过,还是处女借。”可是后来就起了变化,尤其是今天,变得那么明显。厚军知道是他不依不饶地告,影响了马宝。马宝和他是邻居,水泥路的两边要栽路灯,因为厚军家的门坎,迟迟得不到解决,影响了路灯的位置。按照旧有的计划,马宝家的门口是该有一盏灯的。
二
新农村建设,体现在艾厚军所在的太平村,就是给村子里硬化街道的路面。街道干净整洁了,村子的面貌便焕然一新。尽管是表面上的新,可面上的新也会影响内里的旧。比如,没修路之前,马宝家的院子里坑坑洼洼、乱七八糟,修了之后,马宝的老婆刘粉盒,怎么看都添堵,硬是嘟囔着马宝拉了几车沙子把院子里垫平。
艾厚军门前的主路已经修好了,按照施工计划,就该硬化连接主路的那一小段,是很小的一段,五六平米的样子。可事情就出在这一小段上。艾厚军他们这条巷,有十多户人家,从东往西开始修,修到哪家,哪家就会放下手里的活,比如正锄着菜,正浇着地,或者正放着牛羊,都会毫无例外地停下来,加入到修路的队伍里,跟着帮忙。往往这些人倒成了骨干,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了。工人们倒背了手,指指点点,比比划划。这还不算。住户们还会买了烟,分散给工人们,姚占红,因为管着这个工程,烟就会抽得高级一些,低了10块是拿不出手的。于是10块的紫云就奉上来。大家都照猫画虎,按着这个路数来。姚占红嘴里说,不必不必,心里还是很受用的,欲拒还迎地将烟接过来。开始是捏在手里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或者别的什么动作,再看,烟就不见了,变戏法似的。然后就会说,工程的预算里面是没有这个面积的,可我呢,也是农村人,苦出来的,抓把灰比土热吧?就给大伙捎带整了。你们也看见了,这么多人,人马草料的,都是开销,全指着我吃饭呢!我图啥呀?积点德吧。村民们听工头这么说,就更不好意思了,烟递得更欢了,茶也泡得更勤了,力气呢,本来就是奴隶,去了还会来,更是不惜的。姚工头就感觉非常地良好起来,翘着二郎腿,坐在哪家门口早已准备好的凳子上,端着茶水,卡着烟卷,半仰着头,眼睛虚望着。要是哪家有妙龄的姑娘,或是好看的小媳妇,就会坐得久一些,也更能吹了,空中飞的水里游的,云山雾罩,天花乱坠。烟早灭了,还在指缝夹着。
要说艾厚军也不是小气的人,只是“各”(特别,与众不同)得很,在这一点上,人们都褒贬他,说他包文正的儿子,各列子(意思是倔犟,眼里不揉沙子,多少还有点讨人厌)。某种程度说,应该是优点,坚持自己的原则,恩怨分明,是非不二。可容易钻牛角尖。说厚军不小气也是有例子的,比如赶上婚丧庆典的份子钱,而且有时是还多年前的老账。五年前收了人家 100,依张拾翠的意思,还 150也能说得过去,人又不去。厚军说你这样打交道,路会越来越窄,末了会堵死。最后还是厚军说了算,给了200。有一次拾翠老姨的儿子出了车祸,挨个地和他的侄男外女借钱,子弟们很多,但关键时刻都派不上用场,推三阻四的,哭穷装可怜的,气得老姨暗自垂泪,这一群白眼狼!轮到厚军却格外地痛快,拿三千吧,厚军说,我们紧紧就能过去。岁数大了,什么都不值钱,就剩一张老脸。亲老姨值这个钱。还不了就算孝敬了。那是年底,厚军拢共也就五千块钱。老姨感动得涕泗纵横,不光因为外甥女多借给的一千块钱,还有对自己苦难的控诉。
同时艾厚军还喜欢较真。当他听到姚占红说的那番得了便宜卖乖讨巧的话,就憋不住。
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太阳疲惫地往山里落,晚霞一片。羊群罩了橘红的光晕,荡着尘土,菜农掮着锄,从菜地里三三两两地往回走,完成了一天的劳作。工夫不长,太平村就飘起了炊烟。沉寂了一天的小乡村,这时变得活泛起来。给这热闹增添色彩的是修路的工人们。那时艾厚军圈了羊,半披着袄,站在门口和马宝说闲话,自然是离不开菜的长势行情,牛羊的繁殖情况。今天因为路修到了门口,这个话题就没怎么展开。抽一根厚军甩过的烟,马宝就为工人们拿烟倒水,热情得像给自己盖房子。而他也不闲着,膀子抡圆了干。毕竟门口是马宝的,水泥厚些瓷实些,就能多撑几年。烟是昨天就打发刘粉盒备好的,10块的紫云,5块的黄山。还让老婆洗了桃,可没舍得都端出来,心下里点了工人的数,手捧着分给大伙。把“黄山”拆散了,给小工们往上递,顾不上抽的就夹在耳朵上。全有才七八个人,分的时候心里还紧一紧。马宝给厚军拿一个,人没过来,喊声老艾,桃子就飞过去,到了跟前,厚军却不伸手,桃子收了翅膀,没防住,掉在地上,摔个稀烂。厚军说,马宝你咋这样,说了不算,鼻子底下是嘴还是——每户出人和他干就不错了,还买烟,都是让你们这些人给惯的。你以为是真给我们义务修门坎吗?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施工方案里早就有的。他不给修,试试?工都交不了。还在这儿弄巧占便宜。马宝自知理亏,软下身子低声说,我也看不惯,可较不起这个真儿,置不起这个气,还是随大流吧。说完不再理厚军。艾厚军喘了一会粗气说,我还就不信了,喇叭不响两头吹,猫不吃咸菜是没有饿到家,烟一根没有,我看他给修不给修,不给修就找说理的地方去。姚工头一直在车里坐着,太阳下山了,正要招呼工人收摊子。工程进展不错,老百姓都巴结他,心里是舒坦的,熨帖的,瞌睡了就有人给拉枕头,美得厉害。想不到艾厚军看不出火候,不会眼色行事,给他添堵。姚占红没下车,摇下玻璃指着厚军说,老艾你别牛逼,我姓姚的要是给你修,我把眼珠子抠出来。有能耐你去告。
三
既然姚占红让艾厚军去告,那就不客气了。他先去找王得胜,王得胜是村长,村长不行就乡长,按部就班来,不能乱了套数。王得胜懂医术,开个门诊,村长成了兼职。王得胜的房子建得很漂亮,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院子很大,村子没修路之前,红砖漫了地,最近都起了,晾成两砖厚的水泥,比以前坚硬了不是一星半点,而且也漂亮了不是一星半点。王村长家不养牲口也不种菜,院子里漂亮得像篮球场。路过小铺,厚军买了盒烟,递钱时才想起村长是不抽烟的,又想自己来的目的,买烟算怎么回事,理亏似的。
王得胜正给一个妇女输液,穿着白大褂,往架子上挂药瓶,抬头看到镜子里的厚军,厚军啊,稀客!哪里不舒服?心里。厚军拉过凳子说,我也不跟你兜圈子,工头姚占红借修路的名义和村民索要财物……王得胜转过身,嘿嘿地笑,说,净扣帽子,不就是两盒烟几杯水吗,你呀,真是包文正的儿子,各楞子。艾厚军急了,瞪圆眼睛说,村长,你也这么看我?这是两盒烟的事吗?我是小气的人吗?这么多年白在一个村子住了。要是我计较小节,小气吝啬,我会管姚占红的破事。你去问问他,他们施工队刚开进咱们村时,因为挖路上的土方,刮断了徐二楞的网线,还是我给说的情呢,别人都不管,看笑话。徐二楞你还不知道,没缝还想下蛆呢!可现在倒好,姚占红恩将仇报,过河拆桥。王得胜给妇女拿了枕头垫在胳膊下,擦把手说,一码归一码。说到底是几盒烟的事,要不烟钱算我的?工程归交通局管,村里只是协调配合,不好指手画脚。递递话可以,别的真是为难我。姚占红只是施工负责人,而且是转包的,挺复杂,不是你想的那样。说罢,村长拿了茶杯,去了里屋倒水,半天没出来。厚军等不耐烦,站起来往外走,一面走一面说,反正我就等两天,两天没动静,我就去乡里。开门就是三步的台阶,看着村长宽敞明亮的水泥院,艾厚军心里凉了半截。
俗话说一年好过,半天难捱。何况是两天。两天里厚军又碰到姚占红一次,尽管一直躲着他,可就是那么冲,冤家的路就是那么窄。厚军从菜地里打农药回来,没看见,躲已经来不及了,勾着头往过蹭。姚占红正和工人们说笑,发现厚军冷不丁来了一句,背着手撒尿,我都不待端他。话里夹枪带棒,连损带骂,可又摸棱两可,扑朔迷离,让厚军干生闷气。厚军窝着火往回走。左右邻居的门口都修好了,平整整光亮亮,只有自己的门前破破烂烂,豁口打牙。厚军决定去乡里。小车不倒只管推。厚军给自己打气。拾翠说,不行再等等吧,这几天早菜都下来了,价钱也不赖,不能耽误了。乡里不比村里,来去得半天工夫,也不定能逮得着。去年给女儿迁户跑了多少趟?厚军犹豫着,吃饭也没胃口,喝了几口酒,闷闷地睡了。连日来他老是喝酒,不晕就睡不着。凌晨三点半,和拾翠爬起来,开了拖拉机到菜地砍菜,两车卖了 800,厚军也不多高兴。吃罢饭找马宝去借摩托。马宝前天刚喝了厚军的酒,拨不开面子,只是恼着脸,从西房往外推,说别跳了,有劲吗,不怕人笑话啊。你门口不修,电缆拉不过来。有个路灯多好啊,晚上挤奶也看得见。厚军心里说,还不都怨你,缩不前退不后,如果硬点,说不定姚占红还服软了呢。把摩托放在院子当中,马宝晃了油箱说,油不多了,别扔在半路上。
乡长叫陈上贵,是典型的走读干部,家在县城两头跑,堵住他真不容易,厚军知道这个点不保险,可是愿意去碰个彩。村里流传一个形容走读干部的段子:干部像候鸟,老往家里跑,白天寻不见,晚上影难找,办事得赶早,晚了就白跑。厚军赶好了,陈上贵正好在。别敲门!扫院的老汉说,午睡了,等着吧。你也不看看点。陈上贵挺能睡。厚军开始在门房里坐着等,老汉说要走,厚军就蹲在门房的北墙,躲着阳光的热,看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太阳渐渐西去,地上的阴凉也跟着往南挪。朦胧中有人喊,厚军睁开眼,老汉说,别挡道,去吧,敲门轻点。厚军擦擦嘴角的口水,抻抻衣襟。
厚军从门上拿开手,听得里面一阵桌椅响,传来个慵懒的声音“进”。厚军推开门,陈乡长从办公室后面的一个推拉门里走出来,一手往后捋着背头,一手用竹签剔着牙,拉开椅子坐下来,不看厚军也不说话,摆摆桌上的电脑,又推推烟灰缸。我是太平村的。厚军便一五一十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陈乡长说,哦,是这样,不应该。还有这种事?双水村啊?你得去找得胜,这个事他了解,是吧?陈乡长抚摸着椅子的把手说,下午还有一个会,很忙。陈乡长,厚军说,村长我已经找过了,他答应和姚占红说,可几天了不见动静,我家里种着菜,还有牛羊,耗不起,你能不能给村长打个电话……陈乡长把牙签折断了,放在烟灰缸里,说任何事都有个处理过程,不是才几天吗,再等等啊。陈乡长拿起衣架上的西服,穿在身上,看一眼表说,有个会,完了打。回去等吧。陈乡长!厚军近乎哀求地说,用我的打吧。厚军把手机掏出来。陈乡长穿好衣服,很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把桌子上的台历拉过来,朝上面写了几个字说,记下了。这时门响了,一个脑袋从门缝里挤进来,说,陈乡长。陈乡长对脑袋说,下去等。转过头说,我很忙。
四
今年太平村的雨来得早,还没到七月,就没完没了地下,连三赶四地下,下得厚军心里发了霉。交通局的那个电话始终没有打通,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也打消了再去找的念头。他看够了白眼冷黑脸。况且真是走不开,村头的菜地,家里的牲口,的确把他拴住了。厚军郁闷得只想睡,一觉醒来,所有的事都回到从前,或者早晨门一开,自家的门口和马宝家一样,光展平整。门前的主路已经修好,被雨水冲刷得一片白亮,可厚军心里的灰暗一点也冲刷不到。姚占红的施工队伍已经转战到了艾厚军的房后。房后有一条马路,正在做挖掘平整的工作,这两天的雨水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厚军心里舒服一些。厚军想只要路还在修,他的状就有告赢的希望。今天早晨雨下得有些犹豫,时断时续,若有若无,可西边的天依然阴沉着,翻滚着,暗暗积蓄着力量。厚军想,世界的万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这几天老天爷闷骚得很,不张扬,不咋呼,平实而有韧劲。雨也是真下到家了,反倒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地折腾,不见得有多大的作为。
因为左右邻居的门口已经修好,厚军这边就低洼了很多,几天来的雨水都流到了门口,厚军穿了雨鞋,拿着脸盆,一下下往外舀。拾翠从院子里往外搬砖,码在门坎上,防止院子里灌水。天气预报说,近几天还有雨。开始两人还穿着雨衣,不一会就浑身冒汗,伸手弯腰累赘得很,干脆就脱了,只戴了顶草帽。
房后的路有一段已经找平挖低,低下去一尺的样子,很多居民房根基都裸露在外。农村的房屋基本上都是石头干插着,石头的缝隙间没有用水泥填充,这几天接连下雨,有浸泡灌水的隐患。而且农村的房屋,很多都是土木结构的,危险性会增高。姚占红开着车在巷子里转,心里念着阿弥陀佛,观察根基的情况。绕了几圈,舒展了眉头,把心放回到肚子里。车的驾驶台上,有个金黄色的弥勒佛,姚占红拿起来,找出卫生纸,擦得锃光瓦亮,联想到半个月前开工时,给村里的小庙上香的情景,心里暖了暖,宽慰了不少。然后将车掉了头,往前面走来。
姚占红老远就看到艾厚军两口子在门前滚站的身影,心里高兴得要叫出来。姚占红把车开到跟前,打开门说,老艾,忙着呢?厚军直起腰,没理他。姚占红点棵烟说,来一棵吧,马宝给的。你也学学。做人办事要灵活,不能死搬硬套,看看人家马宝过的,再看看你。厚军盛了一盆水,发狠地往姚占红这里泼,泼得姚占红直抬腿。火气还不小,工头说,就是发错了对象,没用到正经地方。和别人斗要掂量掂量自己。王得胜和我啥关系,陈上贵又是啥交情,你想去吧。退一步说,就算他们能秉公办事,为民能做主,我也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实话和你说,不是不给你修,但可以放到最后,一个月两个月,只要不上冻,哪天都行,得看我心情。可你呢老艾,你耗不起,我能把你拖坏,拖得老婆挠你,拖得你成了村子里的焦点和笑柄。到那时你就会明白,伸张正义、维护权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你垫不起。说完姚占红嘭地关了车门,绝尘而去。气得艾厚军把脸盆摔在水里,溅了一脸的泥汤,骂,扑死去吧。拾翠从屋里拿了毛巾,厚军擦了一把,反而抹得更匀了,拾翠就笑,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说西边是天坑,抢着投胎去了。厚军抓住老婆给他擦脸的手说,你还能笑出来,哥们没能耐,让你跟着受罪不说,还受气。厚军有点动情,想这些天来跑着告状,老婆自己在菜地里忙乎,又得听人们的闲言碎语,便说,要不咱不告了,他不给修我们自己弄。拾翠说我看也是,没修路这么多年,咱也过来了。每天地里累得贼死,还得劳神费力地弄这个破事,不值。厚军说,那就不舀了。从小房里翻出盖房剩下的破门板,搭在门口。厚军撕了手纸去厕所。西边的山坳里又响起了闷雷。
厕所是新盖的,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项。只是农村人的院子里都有厕所,去的人不多。厕所盖得比较简易,不隔音。厚军拉开架势,听得隔壁有人说,这两天艾叔没动静了。另一个女人说,这事也只有他能做出来,太较真。厚军听出来嗓音尖细一些的是马宝家的闺女马铃。马铃刚高考完,听说考得不错。马铃接着说,艾叔干的都是大家想干却不愿意干的事。如果告赢了,大伙跟着受益,虽说这是几盒烟的事,可是解气,杀杀工头神气的劲头,往大了说,也是对不良风气的反抗。可如果告不赢,就成了人们讥笑的对象,笑他不识时务,笑他一根筋。因为事情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习以为常,小得没心思去计较。村里老百姓都是看客,艾叔所做的,横竖对村民都有利,自己不伤一点皮毛,最不济也是一个乐吧。另一个女人说,这些我倒没想,就是觉得张拾翠的脾气真是好,换我早就不让他了。两个人出了厕所,小玲,你家的房子漏没?不知道,没听我爸说。姨,你家的漏啦?也不是漏,从后墙往里渗水。女人说。
五
艾厚军酒量不大,可爱喝两口。在他看来酒就是个朋友,麻烦和高兴时都离不了,分外的想念。烦恼时来几盅,烦恼就长了翅膀,扑棱着飞离了身体,远了,更远了,看不见了。厚军就困了,眼睛发涩,拉了枕头,睡将过去。清醒了烦恼还回来搅扰他。可睡眠里的厚军是舒服的。如果高兴了,再抿上几口,就会看见两个小人跳舞,腰肢婀娜,水袖如虹,还伴着唱,珠圆玉润,余音袅袅,厚军便真的醉了,幸福的花朵便绽放开来。
今天厚军又高兴了,便盘腿上炕,脱了袄甩在被垛上,搓着手说,老婆扒拉几颗鸡蛋,拌个西红柿,整几盅。拾翠弯腰去柜里给他掏酒,说你还有心思喝酒,多大的心呢,连阴雨下着,菜都烂根了。厚军边倒酒边说,烂就烂去吧,也不是咱一家。大风刮跑的都是秕子,剩下的都能卖个好价钱。鸡蛋很快端上来,金黄泛着油光,像盛开的向日葵。拾翠炒罢鸡蛋去和面,准备烙饼,和好了用手巾捂着,慢慢醒着。然后洗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坐到炕沿上问,有啥好事,高兴成这样。保密。明天就知道了。好事说早了会降低它的分量。拾翠说,不说拉倒,谁稀罕,好人不说半句话。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夜晚。雨住了,天空还没有放晴,月亮和星星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夜孤独得厉害,便黑了脸,黑得像泼了墨,让人无名地恐慌。拾翠凑场打麻将去了,孩子住校在几十里的镇上。厚军把半盒烟抽完了,掐死最后一个烟头,之后扫了地,把还能抽几口的烟头,归拢到烟灰缸里,收拾停当,跺几下脚,把十指握得挨个脆响,又在镜子里将自己端详了一下,拍拍脸,紧紧神色,去院子里的窗户底下,摸到了拖拉机的工具箱,打开盖子,提出千斤顶,操在手里,开始上路。
艾厚军的房西面是一条待修的路,姚占红已经挖低平好。这条路贴着他家房子的山墙,向东拐过去,依次是马宝家,刘光有家,徐东河家……
艾厚军提着千斤顶,首先来到西面的山墙下,蹲下了身,摸索着寻找放置千斤顶的地方。西山墙紧靠着房根基的地方,挖下去有一尺多深,土质松软,下了几天的雨,都和成了泥,可要把千斤顶放在石头的空隙里,并非易事。厚军捣鼓了一气,弄得两手是泥,满头是汗,还是放弃了。扭头看看四外的情况,屏住呼吸,听听动静,短暂地喘息了一会,起身来到房后。顺着房后的根基,逐个掀动石头,碰见一块松动的,就停下来,使劲撬动。到第三块的时候,几乎没怎么费劲,很轻易地拽出一块来。艾厚军把糊满泥水的手往墙上蹭,凸出的地方硌了手,猛然想起,这个墙垛子是连接他和马宝两家的部分。这给了厚军灵感,于是干得更有劲了。拉出石头,找出底下的平面,垫进准备好的平整石块,将千斤顶塞进去,支稳了,然后擦把脸上的汗,再向四周看看,做个深呼吸。真想抽根烟啊,厚军心里默默地念。之后拿起千斤顶的加力杆,轻轻地缓缓地往下压,一下,两下,听得墙壁在轻轻地响动。厚军不知压了多少下,传来一声闷响,似乎是椽檩断裂的声音。厚军停下来。万籁寂静,针落有声,心在肚子里落稳了。然后打开手电,晃了一下墙壁,看到尺把长的裂缝,裂缝扭曲地伸向马宝家的房子。厚军关了手电,将千斤顶抽出来,把石头恢复了原位,回填了泥土,摊平了痕迹,顺着原路返回。
拾翠还没有回来。拾翠打麻将十赌九输,今天一定会赢。好事爱成双,厚军想。然后洗了手。
六
厚军换了衣服,点着烟,看看表,十点十五。想给拾翠打个电话,问问战况,掏出手机正要问,听见隔壁马宝家一阵乱,还有刘粉盒的哭喊声,厚军扔下手机,慌忙往出跑。马宝的院子里亮着灯,厚军隔着墙头问,咋啦老马?马宝顾不上回答,和刘粉盒在厕所里忙乱着。厚军从墙上翻过来,见马铃瘫在厕所的一角。马宝家的厕所紧挨着厚军家的东山墙,厕所是简易的,只有围墙,没有房顶。说话的工夫,马铃已经被父亲抱了出来,满身的恶臭。刘粉盒叫喊着,用毛巾包裹女儿的头,昏暗的灯光里,能看到蚯蚓似的血迹顺着马铃的额头往下流。马铃被砖头砸晕了,马宝说。厚军心里猛地沉了一下,说,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砖头。边说腿肚子边忍不住地抖,快给王得胜打电话,去医院。趁两口子不注意,厚军看一眼自家后墙的裂缝,还有烟洞上少了的砖头,心里直发冷。
在去医院的路上,马铃醒了,嘴里吸着凉气说,刚蹲下就被什么砸住了,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马铃头顶缝了四针,做了检查。当天夜里就住了院。
第二天厚军还没起来,马宝就跳过墙,敲他的窗户,老艾,老艾!快起快起!咱们房子都裂了,那么宽。我闺女的头也是让房上的砖头砸的。快起!这回轻饶不了他。姚占红,我日他祖宗。小玲有个闪失,我整死他。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姚占红跑了。工地有下夜的老汉,知道消息就通知了工头。跑了和尚庙还在。厚军和马宝顺根捋,根本就不用亲自找,直接给王得胜打了个电话。几个小时就捋到了主管单位交通局。交通局的态度很好,一把承担了过来,说先给孩子看伤,身体要紧,房子的裂缝啊下沉啊门前的硬化啊,都会有合理的安排。
七
腻歪了好多天的阴雨,终于走了。天放了晴,炙热的阳光抚摸着田野里绿油油的蔬菜,蔬菜也热情地承接着阳光的亲吻,兴奋地发出亮晶晶的光,远远望去,满眼的绿色,满眼的绿色中蒸腾着白色的雾气。蔬菜也憋坏了,铆足了劲,没明没夜地疯长。
马铃的受伤,让艾厚军心里产生隐约的痛。这件事他不敢声张,甚至是自己的老婆。他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否卑劣龌龊,他时时开导自己,姚占红是他的敌人,耍一些手段对付他,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连累了无辜。马铃的受伤,仿佛冥冥之中,是对他的某种警醒和谴责。
抽空厚军买了好多东西去家里看马铃。马铃已经出院了,没有什么大碍。只是缝合伤口的时候,头顶的秀发剃了一片,马铃梳了一个吊辫,遮挡掩饰着。马宝说成绩不错,考了个不赖大学,过几天就走。厚军躲闪着马铃的目光,心里还是高兴不起来。
修路的队伍又换了一班人马,他们施工的头一天,就给厚军修了门坎。那时厚军在菜地里忙,不知道,中午回去的时候早就变了样。工人们住在村子里的学校,厚军想去看看,让拾翠炖了两只自家的柴鸡,买了几瓶酒。工人们不客气,接了鸡和酒,脸上一副纳闷的样子,闹得厚军挺没意思。工人们说,坐下一块喝吧,厚军说不了,然后走出学校的院子。
月亮升起来了,皎洁得有些清冷。厚军裹紧了衣服。老远望见自己家里的灯光,暖暖的,只想哭。艾厚军快步往回走,他突然很想拾翠。
责任编辑/董晓晓